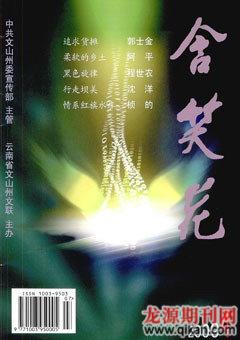行走在大香格里拉(二章)
张丽萍
1我也做回乞讨人
我不知道我这一生中会不会再做乞讨人。但在小中甸,我是做了一回乞讨人的。
一路风光。前面突然豁然开朗,平生从未见过的一块大草坪朗朗俊俊展现在眼前。它尽情延伸到四周的群山脚下,爬上绵延数里的青翠山。一条宽敞的柏油马路把草坪一分为二,真正是黑绿相间,一幅极美的水墨画。黑,是新修的柏油马路;绿,是洋洋洒洒的大草坪。一些藏民和游客穿梭其中,悠闲自得。我们猜想,这可能就是朋友说的小中甸了。便依照嘱咐,给她去了电话。
等我打完电话从车上下来,见老公他们已经被一个八九岁的藏族小男孩左右围住,“突围”不得。他伸出脏兮兮的小手,不断说着,我在挣学费呢,给一点钱,给一点钱嘛。语气熟练,可怜又执着。我们掏了一点钱给他。见马路上彩旗飘飘,乐声袅绕,围了很多人,就朝他们走去。
原来是当地藏民在欢度他们的节日。他们一个代表队、一个代表队地进行着表演。当中孩子的表演博得了观众们的阵阵掌声。他们穿着极新的藏族服饰,当真是一朵朵花,开得幼稚,开得艳丽。我们拿出相机,狂拍了一阵。女儿望着马路下面热闹的骑马场,说想骑马。我们就走出表演场,向骑马场走去。
给点钱嘛,给点钱嘛,我在挣学费呢。不知什么时候,我们面前又伸出了一只脏兮兮的小手。不同的是,这是一只小姑娘的手,只是说的话跟那小男孩一模一样。
我们不给。她就跑到我们跟前左晃晃,右晃晃地阻断我们的去路,并且仰起小脸,无限制地派出小嘴的两个角,挂在耳根上。再把眼睛挤成一条缝,哭丧着不断说,我在挣学费呢,给点钱嘛,给点钱嘛。朋友说,给过你了嘛,刚才给的。她睁开眼睛看看,露出笑脸,朝我们偏头一笑。拉着那个大女孩朝另外一伙刚走进草地的人跑去。
我这才注意到,她们是两个人。只是那个大点的女孩始终不说话,始终微笑着。一切都是由小女孩在说,她们的手,却是始终紧紧拉在一起的。我也不知道她们有没有想起其实我们是没有给过她们钱的,我们给的,是另外一个小男孩。
看着她们跑过去的背影,我突然有点心酸。两个女孩鲜艳的藏族花裙子在草地上如蝴蝶飞舞,但美丽的蝴蝶翩翩起舞可以给人类带来美的享受。她们的“飞舞”呢?我不觉产生了想走进她们的欲望。
在我这样想着的时候,她们乞讨了两伙人。都没有乞讨得一分钱,相反还挨了骂。我走过去拍拍小女孩,说,我跟你们一起要钱怎样?
小女孩仰起小脸看着我,又把眼睛眯成了一条缝。大女孩始终不说话,只是静静地微笑着看着我。随即,小女孩爽朗地说了一句,好,走。就拉着我的手快速跑向另外一伙人。我没有她跑得快,她很费力地拽着我。大女孩显然是在顾及我,也跑得不是很快。我就这样一左一右由两个小女孩拽着往前跑。
小女孩堵到人家面前,大声说,给我们三个一点钱嘛,我们在挣学费呢。我噗嗤一声笑出来,大女孩也掩着嘴巴嗤嗤笑。这小女孩真是太可爱了。有我这样的“大人”还在挣学费吗?真是童心稚趣,童言无忌。人家不给,边走边骂,还抬起手臂,在空中挥来挥去撵苍蝇似的,很是厌恶。小女孩仿佛没有听见,也仿佛没有看见。只是一个劲地又拼命拽着我们,抢上前去堵住人家,一遍遍重复着,给我们三个一点钱嘛,我们在挣学费呢;给我们三个一点钱嘛,我们在挣学费呢。结果可想而知,都是无功而返。这样两三次后,我说,我们不讨钱了,去吹牛。我给你们钱,好不好?
小女孩高兴地叫起来,并把小手麻利地伸到我面前。大女孩握着她的另外一只手,使劲拉她。拉得没处放了,就把它紧紧贴在自己的肚子上面,稍微躬下腰去,脸上始终挂着微笑。我开玩笑说,我没有钱,给你颗糖好不好?她响亮地回答,好。我掏出仅剩的一颗糖,刚要递给她。她一把抢过去,快速地剥开,分了一点给大女孩。又掰下一点,递给我。我被她的纯真感动了。这是一个心地善良的小女孩,就是仅有的一颗糖,她也要分做三份。哪怕就是我这个刚刚认识的大朋友,也有一份。我连连摇手说,不要,不要,你吃。
小女孩高兴地边吃边笑得弯下腰去。突然,她指着我的鞋说,阿姨,你的鞋子坏了。我一看,确实是鞋头都裂开了。这鞋子,是什么时候坏的呢,我怎么不知道?我哈哈大笑起来,她们也跟着我笑起来。我突然想逗逗她,就说,你看,阿姨鞋坏了都没有新鞋换,可怜不可怜啊?小女孩歪着头想想,脱下她的鞋双手递给我,满脸真诚地说,阿姨,你穿。我笑着说,太小了,阿姨穿不了,你给阿姨点钱,阿姨去修鞋子好不好?小姑娘爽快地点点头,伸出小手翻遍了所有衣袋,翻出一元钱,递给我,叫我去修鞋。我再次被感动了,伸出双手去抱住她。这是一个内心里多么纯净的孩子啊,当别人需要帮助时,她毫不犹豫地给予帮助,哪怕倾其所有。这一元钱,不知道她要乞讨多长时间呢?也不知道她今天要是空手而归,家里的大人会不会鞭子伺候她呢?我暗下决心,分手的时候,一定要给她10元钱。
我们聊起来。我说你们为什么要讨钱啊?小女孩快言快语地说,你们有多多的钱,我们有少少的钱。说的时候,她双手向左右最大限度地划开去,又把拇指和食指粘在一起,露出一小条缝,表示“我们的钱”和“她们的钱”的区别。我笑了,问,谁告诉你的啊?她说,爷爷奶奶。我又问,谁叫你们来讨钱的啊?小女孩说,爷爷奶奶。我问,你们讨的钱真的是买学习用具,交学费吗?小女孩答非所问地说,交给爷爷奶奶。我问,你们都读书了吗?小女孩说她7岁,读一年级。大女孩11岁,读四年级。
所有这些话,都是小女孩一个人在回答我,大女孩做翻译。因为小女孩的汉话讲得不甚好,我听不太明白。我注意到大女孩并不多说一句话,只是腼腆地笑着。就问了一个比较严肃的问题:你们讨钱不害羞吗?
小女孩马上大声回答,不害羞。脸上还挂着很灿烂的笑容,边说边用手去整理裙子的花边,边快乐地把头左扭扭右扭扭来回地看,边快乐地嚼着糖。我估计那糖早就到她的肚子里去了,只是核还在,她舍不得吐掉核,因为我给她的,是一颗杨梅果脯。
大女孩腼腆地一笑,说,害羞的,我害羞。我说,那你还来讨钱?她说,我家穷。我心里一咯噔。问,你家怎么穷了?她说,我爸爸不在了。我再一咯噔,那你讨钱,你同学们知道吗?知道。他们不笑话你吗?不笑。为什么?因为我家穷。
我不知道再问她什么了。整理了一下情绪,问道,那你为什么觉得讨钱害羞呢?她非常不好意思地笑笑,紧紧攥了攥一直握在她手心里的小女孩的手。说,因为我看书,知道……她不说了,是因为说不下去。但我从她的表情和语气,知道她要说什么,就问她,是不是知道讨钱不光荣?她点点头,羞涩地一笑。一种无奈迅速爬上她的脸庞,和本来应该很迷人的笑容融合在一起。我突然明白,这是一个被生活所迫,知道荣辱,又不得不背负着耻辱来进行乞讨的大女孩。
突然,小女孩一下子站起来,拉着大女孩就朝一边拼命跑去。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也赶紧站起身紧追着她们跑,可是前面一个人也没有啊。我懵了,
站住了。大女孩好像有所顾忌,边跑边回头。我跟她招招手,叫她们回来。大女孩停止了脚步,跟小女孩说了几句什么,小女孩还是死命拽着她往前跑。大女孩边跑边有些留恋地回头张望,我一直望着她们,满腹狐疑。
前面两张大巴上下来几个人。我突然明白了她们奔跑的原因,她们是要去向巴士上的游客行乞。我不知道这两张巴士是什么时候停下来的,但小女孩肯定知道,她一直在机警地四处张望呢。我不知道小女孩们能否在巴士上讨到20元钱,因为我是想给她们每人10元钱的。也想起就在刚才,她们快乐地奔到一辆刚刚停稳的大巴士面前,刚想伸出小手,就被导游恶狠狠地呵斥住了。
只是,现在她们奔向的那两辆大巴,是停在离我们五六百米远处的。它们以最蓝的天最白的云最青翠的山林为背景,清清爽爽透出一股逼人的纯净。一条崭新的柏油马路,穿过它们,通向远方。
我不忍心再看这幅美丽的图画。一偏头,看见女儿骑完马,在追一只黑猪玩。女儿撒开小腿,挥舞着双臂,欢快地跑着,叫着。黑猪一会越过土堆,一会钻过草丛,直溜溜箭一般直向前奔。旁边有人说,什么叫生态,这就是原生态,人与动物和谐相处。大家笑起来。
我再看那两个女孩,已经不见了踪影。不知道是不是融进了众多的游客当中,还是到另外的地方乞讨去了。要是她们在,我很想追过去,把欠她们的钱给她们。朋友来电话,说她已经在入城口等着我们了。我们只好驱车前往,但我一直把目光向四周搜寻,我真的很想再看见那两个女孩。
第二天傍晚返回丽江时,我也一直在心里默默祈祷,希望那两个女孩还在,我把钱给她们。可迎接我们的,是静悄悄的小中旬,没有一个人。就是猪,也不见。我眼前更加猛烈地浮现出两个小女孩。她们的笑容,她们的纯真,她们的腼腆,她们的无奈。特别是她们奔向蓝天白云时乞讨的样子,久久定格在了我的心里。我又一阵心酸。
也许,一辈子都挥之不去。
2、宁静祥和的中甸古城
很喜欢中甸古城。
它宁静,又祥和。
还未进古城,我们远远就看见一个圆圆的高高的建筑物,在夜幕下格外耀眼。它周身散发着琉璃色彩,金碧辉煌,栩栩生辉,不停地转动着。我们都被它吸引了,迫不及待地想去看看。朋友说那是转经塔,是亚洲第一大转经塔。它不停地在转动并不是机器在转,而是人在转呢。
一级一级爬上石阶,我们终于站在了转经塔前面。依照朋友的嘱咐,转了个单数,许了愿。才有闲观察四周。陪伴它的,是一颗颗高大的树,转经塔金色的佛光,闪耀在它们身上,宁静,神秘,又颇具魔幻色彩。再抬头看天,星星居然就在我头上,一颗一颗闪亮无比,晶莹无比,透着逼人的纯,逼人的干净。才恍悟原来这里离天最近,离心中的神灵最近。我们仿佛进入了神的家园,不敢大声说话。
下到古城,一再叫朋友一家回去。因为孩子尚小,该睡觉了。他们坚持还要再陪我们,孩子依着妈妈瞪着美丽的大眼睛看着我们争执,打了两个哈欠。我们笑起来,他们只好千叮嘱,万嘱咐一番,打道回府。
看看表,九点过了。我们一家一家逛起来,一路新鲜。古城多是紧密相临的二三层楼高的藏民居,它左右两排延伸开去,看不到头,一条青石板路弯弯曲曲伴随着它。实际上这种新鲜在还没有进中甸城时就扑面而来了。宽广的草原上,一幢幢生活中从来没有见过的藏房拔地而起。它下宽上窄,雕刻着很多图案,又刷着不同颜色新鲜的色彩,和我们平时看见的房子完全不一样。老公他们男士对那些矗立在门面一根根像饮水机一样又粗又圆的木柱子特别感兴趣,咂舌不已。现在能够亲手摸摸任何一座民居前的大柱子,就更是惊叹不已了。
古城里卖的多是当地特色,诸如牛角梳子,兽皮做成的衣服、帽子、牦牛尾巴等等。全都是本色的,冷色调的,并不像丽江古城那样,摆满了色彩艳丽的衣服、饰品。相比丽江古城的花绿,喧嚣,我是很喜欢中甸古城的宁静,祥和的。
记得5年前最后一次到丽江。也是很喜欢它的幽静。斑斓和浪漫的。那时的丽江虽也有很多游客,宁静,幽雅却是主色调,听听宣科讲经,看看著名的大型歌舞《丽水金沙》。一直萦绕我们内心的,还有四方街上从上而下的一串串红灯笼,放河灯。女儿念念不忘的是还要在红红的灯笼下,清澈的小桥流水旁再吃一顿饭。可是当我们再到时,再也找不到这种宁静了。此起彼伏,一家高过一家的卡拉声,把它变成了真正意义上的酒吧,不再是具有丽江特色的“酒吧”,和我们当地的酒吧不无两样了。我们沿着它走了一段,再也忍受不住高昂的乐声,歌声,就是女儿,也很失望地离去。
想不到在丽江古城消失了的宁静,幽雅,在中甸古城找到了。它静静地,就连空气中弥漫的,都是静的分子。古城里也有酒吧,但客人们都在静静地、悠闲地享受。有一家“马帮路上的客栈”,更是古朴得让你回到了三四十年代。我们走进一家卖刀的,名叫卡卓刀,据说是中旬最古老,最出名的刀具。男士们这把看看,那把摸摸,爱不释手。我们女士却多的是敬畏。说实话,我还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刀具聚拢在一起,它们大小不一,形式各异,用途不同。我胆颤心惊地拿起一把青色的剑,小心翼翼地试着弄了弄,切身感受了一下金庸小说里的大侠风范。却觉得沉甸甸地,一点也不能像鸡毛一样轻轻抬起,优雅地划个弧形指向敌人,又潇洒地放回剑鞘。只好怀着恐惧坐在沙发上等他们,不一会,我们女同胞全都坐在了沙发上。一只猫在我们眼前跳来跳去,不断玩弄它手里黄色的网球,憨态可掬。女儿蹲下身去,小猫看看她,自顾玩起来。女儿趁机抢了它的球,小猫翻转过身子,肚皮朝天,眼巴巴地看着女儿。女儿笑着拿球在它眼前晃晃,它伸出爪来扒了扒。见扒不到,很潇洒地一骨碌起身跑出了门外,我们直埋怨女儿破坏了一幅极美的画卷。突然,传来一阵嘘嘘声,原来是店家在用刀斩断一颗铁钉,真正是削铁如泥,不是神话。其实也是神话。在这个神话的地方,展示出来的神话。
走出宁静又粗犷的刀具店。我们来到一家卖藏族服饰的店里,这种色彩艳丽的店在中旬古城很少见。老板娘着一身藏族服饰,我们觉得很好看,就纷纷效仿。把有长长假辫子的头饰戴在头上,也很好看哦,一下子变成了美丽的藏族女人。我们一个扮了拿给另外一个人扮,欢笑声冲出小店,搅荡着宁静的空气。到我扮时,我不觉对着大家跳起了藏族舞。我边唱着《洗衣歌》,边举手抬足间优雅地比划着。这个舞蹈我看过很多次,上到著名舞蹈家们的表演,下到农村文艺队的演出。惟有现在,我才真正体会到这个舞蹈的精髓。我仿佛真的是进入到了雪域高原,在莽莽高原上为最可爱的人洗衣服。手冻僵了,一点不疼。脸冻红了,一点不疼。因为我的眼前,我的心中,满是解放军战士们忙碌的身影。他们在辛勤地为藏族人民做好事,也不怕苦,不怕累。这是一幅多么和谐,友爱的篇章啊。它定格在了苍茫的雪地上,也定格在了我的心上。想不到跟文化打了这么多年的交道,组织了很多场演出,在这里,自己却做了一回真正的演
员,真正体会到了舞蹈的内涵。有限的几个观众看着,笑着,拍着巴掌。后来几天,他们都还一再夸我扮相好,跳得好呢。特别是被老公夸时,他那种发自内心的真诚、喜欢的模样,让我很受用呢。
嬉闹了一阵,该走了。突然有些害怕,怕老板娘不肯轻易放我们走,要我们买她的东西。谁知她和蔼地笑笑,还嘱咐我们慢走,一边轻轻收回我们还她的头饰、衣服什么的。我们舒了一口气,才觉得闹得有些过分了。
出门看见几个小朋友在玩游戏。他们分为两组,由一组不断叫着:“向左滚,向右滚,向前滚,向后滚。”另外一组依照口令做出相应的动作,做错了的,就要被罚,再充当“棋子”,不得当“司令”。这个游戏很考智力,因为常常有反映不过来的人走错了方向,逗得大家嘻哈大笑。当中—个很调皮的小男孩,他快速地叫着向左滚,向右滚,向前滚,向后滚。语气快得就像绕口令,也大概只有他自己能听清楚自己说的是什么。但是小伙伴们都不跟他计较,照样跟着他的口令前后左右各跨一步。有可爱的小女孩忍不住上前伸出稚嫩的小手,笑着捶他一下。小男孩却严肃得像个将军一样,一笑不笑地认真发号施令,并不因为别人的捣乱乱了自己的阵脚。我们跟着他们笑了一会,继续向前走去。
没走几步,又碰到一个中年妇女在跟自己的孩子捉迷藏。她用一块红布蒙住眼睛,弯下腰,伸出双手一下一下摸自己的孩子。孩子只有四五岁,并不躲避妈妈,而是扶在大概是他家的门柱上窃窃笑着。我走过去摸摸他的小脸,他就把笑脸仰起来,送给我。朋友小琴则径直走到他母亲身边,直挺挺地夹紧了双臂等着母亲来摸。果然,母亲摸到了小琴,犹豫了一下。大概是觉得摸到了路人,想要道歉,赶紧摘掉眼布。看见我们都在对着她笑,她也笑起来,伸出双臂拥抱了一下小琴,说对不起,摸到你了。小琴笑着说,是我自己投怀送抱的呢。大家笑得更大声了。小琴做出很不好意思的样子,三步并作两步急忙往前走,连声说,你们玩,你们玩。我回头再看,母亲和孩子又玩起来了。这次孩子没有站着,而是欢快地叫着母亲,妈妈来摸我,妈妈来摸我。
这是很遥远的记忆了。要不是看见小朋友们玩向左滚,向右滚,向前滚,向后滚。我几乎忘记了自己是玩过这种游戏的。也是在这样的夜晚,在老家,我们几个小朋友玩得不愿归家,往往要大人们左喊右喊,甚至拿着棍子来喊,我们才会依依不舍地回家去。有时候大人发怒了,会在我们细小的脚杆上抽上几细鞭子。我们会边哭着,边告诫其他小朋友,别忘了,明天再来玩啊。
我是没有被父母打过的,父亲母亲从来就没有打过我。被父母打得最多的是儿时的伙伴小强,据说他也在中旬做生意。我这样想着的时候,不觉走进了一家店。老板热情地向我们介绍他的兽皮大衣、围脖、帽子什么的。一个小男孩气喘吁吁地跑进来,边叫着“爸爸”,边急匆匆地抬起口缸喝了一口水,又跑了出去。我认出来他就是刚才绕口令的那个小男孩,望着他笑笑,问老板:“是你儿子啊?”他笑笑说:“是啊,调皮得很呢。”这一问一答不要紧,我们相互凝视了几十秒钟,大声叫出对方的名字。他正是小强。我笑着说,中国人想不得,一想就见到了,真是说曹操曹操到。我跟他说了刚才的所见,所想,他也哈哈大笑起来。我们聊了一阵,说了一些近况和同学的近况。他一再邀请我们明天吃饭,我们说要去普达措公园,朋友都已经联系好了。见实在无法尽地主之谊,他一人送我们一把牛角梳子,说是上好的牛角做的呢。临出门,我突然想起什么,问他:“你儿子玩到这么晚不回家,你不找他?不打他啊?”他愣了愣,哈哈大笑,连声说:“不打,不打。也不找。他爱怎么玩怎么玩,爱什么时候回来什么时候回来。”笑够了,他又补充一句:“我们这里很安全的。也不见哪家打孩子。”我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他一个外地人变成了这里的主人,变成了“我们这里”。不过这里确实有很多的理由,让外地人想变成本地人。那些已经变成了“本地人”的人,无疑是最幸福的人。
“哈哈”,女儿连笑带叫起来,我们知道她又有了新的发现,赶快走过去,原来是一只小狗在玩匕首呢。它伸出小嘴,熟练地把匕首叼起来,放下,又叼起来。我很担心锋利的卡卓刀会划伤小狗的嘴嘴,蹲下身去看它。小狗歪着头看看我,大概是因为来了观众,刺激了表现欲望,便更猛烈地把刀叼起,放下;放下,叼起,还不停地变换方向,做出匍匐向前的姿势。我们都笑了。看来不但藏族朋友们喜欢刀,把刀视为神圣,要佩戴刀。就连狗狗也喜欢刀,并能收放自如。这真是一个爱刀的民族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