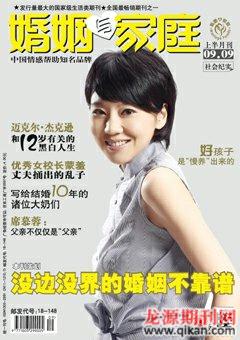席慕蓉:父亲不仅仅是“父亲”
李 赵
对孩子而言,父亲究竟是怎样的人?
是那个从小赚钱养家的人,
是那个拉着我们的小手接送我们上学的人,
还是那个时刻用目光温暖着我们的人?
2009年6月,著名散文作家席慕蓉
在她的散文集《蒙文课》里,给出了令人惊叹的另一个答案……
在许多儿女心中,父亲就是父亲,威严或慈祥、贫穷或富贵。这个男人之于我们的意义,就是我们的父亲。在过去许多年里,席慕蓉都这样认为。只是,当她“后知后觉”地意识到父亲不仅仅是“父亲”两个字那么简单时,一切都来不及了。1998年,席慕蓉的父亲去世,悲伤无以言表。从此,席慕蓉的文字里,不仅多了一份忧伤,还多了一份追悔莫及。2009年6月,席慕蓉携新书《蒙文课》到北京。面对记者,谈起父亲,她数次哽咽。她希望天下的子女,应该趁父母在世,知道除了父母身份之外,他们还是谁。
小时候,他是你身旁温暖的大手
席慕蓉出生在蒙古家庭,父亲是锡林郭勒盟的,母亲是昭乌达盟,外祖母是成吉思汗黄金家族的后人。很小的时候,父母带着她离开草原,辗转来到香港。她在香港度过童年,而台湾,是她成长的地方。
在席慕蓉儿时的记忆中,父亲是温和而乐观的人,天性浪漫。在香港那几年,他每隔几天就会带着孩子们去海边游泳、去山上野餐。“我们学校里有活动,父亲也踊跃参加,只要有父亲在,气氛就会活泼热闹起来。”
相比而言,母亲会严厉一些,所以孩子们不敢跟母亲提的要求,总是先到父亲那里疏通。一次,席慕蓉把父亲送给母亲的一支钢笔带到了学校,结果回家时,只剩下上面的笔套空空地挂在衣服的口袋上,笔杆不知道落到哪里了。席慕蓉至今清楚地记得那支钢笔是如何的精致。
显然,那支钢笔对母亲的意义非同寻常,她让席慕蓉沿路回去找,找不到就不准回家。席慕蓉既委屈又不情愿,但也只好沿着放学的路,慢慢仔细地寻找。她家后面有一处高坡,在那个土坡前,父亲赶上了她。“他用温热的大手扶着我的肩膀,轻声说:‘算了,找不到了,我们还是回家跟妈妈说说好话吧。”
孩提时,父亲是席慕蓉身旁那双温暖的大手,而她长大离开家时,父亲是她身旁那关爱的目光。1964年,席慕蓉离家去欧洲读书,因为想家,她经常会给家人写信,远在台湾的父亲每封必回,信里都是让她觉得温暖的词句。在一封信里,父亲这样说:“在家就爱一个人到处乱跑,一会儿上山一会儿下海的,我总觉得你是我5个孩子里最不听话的一个,就像一匹小野马。现在,小野马跑到那么远的地方去了,我还真有点不放心,有时候会轻轻叫你的名字。小野马,离我们老远老远的小野马啊!你也开始想家了吗?” 这些温暖而精妙的句子,席慕蓉读过一遍就永远难忘。
1986年春天,席慕蓉在布鲁塞尔与丈夫海北举行结婚典礼,父亲牵着她的手顺着风琴的乐音前行。看到爱人站在圣坛之前,正望着她,心急的席慕蓉只想赶快站到自己该站的位置上。虽然父亲几次在旁边提醒她走慢一点,但她的步伐却一点没有减缓,在乐曲结束前,她早已经开心地站在了新郎旁边。后来,父亲半是伤心半是玩笑地说:“从没见过走得这么急的新娘!怎么?有了丈夫就不要这个老爸爸了吗?”当时的她根本没在意笑意盈盈的父亲,眼中有淡淡的失落。
长大后,你要为他寻找和奔赴
随着年龄的增长,席慕蓉渐渐意识到了父亲的乡愁。小时候,她最喜欢听父亲讲他小时候在草原上的往事,尤其喜欢听他讲赛马。开始讲的时候,父亲还比较冷静,但说着说着就兴奋起来,有时甚至站起来,一直说到自己如何得到第一名。除了赛马,父亲最愿意讲的是故乡的风光。
席慕蓉有一次陪父亲在欧洲旅行,父亲随口说,自己不喜欢前面有东西挡住的风景。“我当时很奇怪,心里想,那么远的山也挡你吗?在我看来,欧洲蛮大了,风景又那么好。等我到了蒙古高原,才知道什么叫一望无际,360度,可以一直望到地平线。父母确实在其他任何地方都找不到这样没被挡住的风景。”
还有一次,她陪父亲在慕尼黑大学散步,校工在割草,周围有一股清新的香气。父亲突然说了一句:“真像我们老家的草香啊,多少年没闻过这种味道了。”说完这句话,父亲就继续往前走了,似乎压根儿没想听到女儿的回答。那时席慕蓉还没回过老家,等她真的回去了,每走一步,香气扑面而来,她突然想到:我的天呀,父亲当时讲完就走,是因他觉得孩子是不会懂他的。
从那时起,她常常忍不住会想:“在父亲心里,藏着的那些没说出来的乡愁,到底还有多少呢?”
一个从来没有回过家乡的女儿,是没有办法分担父亲的乡愁的。也因此,席慕蓉在1989年终于去了内蒙古,她是为父亲而来的。回到台北后,第一件事情就是给在德国教书的父亲打电话,然后把自己在内蒙古拍的相片粘贴成厚厚的一本,每张照片旁边还加上了她自己的说明和观感寄给了父亲。
“从1989年到父亲去世的1998年,中间有9年,我和父亲共享我们的蒙古高原。在那个时候我发现了父亲的快乐。他可以跟我谈论家乡,因为我能懂草原的味道。”
整整9年,席慕蓉与父亲之间聊得最多的话题就是故乡,父女俩的话突然多了,感情也亲近了许多。父亲因为女儿终于可以稍微了解他的乡愁而高兴不已,而席慕蓉也开始频繁地地奔赴蒙古高原。每次去之前,她都先到德国,和父亲商量此行的目的;而回去后,她也先去看父亲,把自己在故乡的所见所闻都绘声绘色地告诉父亲。
问她,父亲为什么不自己回故乡看看?席慕蓉说,因为父亲生性浪漫,他的心里装着一个精美绝伦的故乡,他怕一丁点的不美好都会破坏了它的美。在外漂泊辗转几十载后,父亲害怕回去见到一个面目全非的故乡。“所以我对父亲说,我替你回去。那个时候我的感觉是,我没有负担,我是在努力帮他寻找一个更完整更生动的故乡。这样,父亲的记忆永不会凋谢。”
他不在了,你不要追悔莫及
在父亲生命中的最后9年,席慕蓉觉得自己成为了父亲与故乡的传讯者,让父亲对故乡几十年的思念,终于有了出口。但是,就在父亲去世后,她突然意识到,自己做的还远远不够,她甚至都不了解父亲在“父亲”的身份之外,是怎样的人,这让她追悔莫及。
“我一直以为,父亲就是父亲,他是纵容我撒娇的人,是我提出要求他不满足我就可以生气的人。直到在父亲的追悼仪式上,听到父亲同事对他的评价,我才明白自己一直用女儿的眼光来理解生活中的父亲,那范围是何等狭窄。也许,这父与女的关系,在对父亲的了解中,反而成了一种‘蒙蔽。”席慕蓉这样告诉记者。
父亲去世是1998年,在追悼会上,父亲的同事、德国波昂大学中亚研究所的一位教授感谢席慕蓉的父亲说:“他经历了曲折的道路,从遥远的地方走来,为大家讲述了古老而丰美的蒙古文化,让很多人从此热爱蒙古。”而她父亲在慕尼黑大学的同事,在寄给席慕蓉的信中称她的父亲是高贵的典范。
这些让席慕蓉意识到,父亲不仅仅是“父亲”,他不仅仅是自己眼中那个因为熟悉而似乎已经固定了的形象。年纪轻轻就远离蒙古家乡的他和母亲,到底是用什么样的心情和态度过之后的日子?席慕容突然想起这个问题。
“我在内蒙古采访丹僧叔叔,两个晚上就把他的一生都采访完了。虽然我在父亲离世前9年一直跟他交流和提问,但作为一个女儿,我问得太少了。我仅仅只是以一个孩子的立场在问他。我对父亲的一生所知太少了,有多少需要知道答案的问题,我却从未触及。比如,我没有从客观的角度问问父亲,作为近代知识分子,你怎么过的一生?远离家乡,你怎样想念久违的难以再回去的故乡?”
席慕蓉说,她的一个朋友也跟她表达过类似的遗憾,这个朋友在父母离世前,从未问过他们除了父母身份以外的生活。直到他们离开,才猛然醒悟:自己对父母的了解太少太少了。
所以,现在的席慕蓉,只要一见到年轻人,就会跟他们说:“一定要趁父母健在时,好好地做他们的孩子。另外,还要从客观的角度,了解父母作为其他社会角色的生活、感受和悲欢。这样,我们就不至于非要等父母都离开了,才在泪水中用各种或真实或缥缈的线索,一个人孤单而惆怅地寻找已经不在身边的他们……”
(责任编辑/玄圭)Tel:(010)84220026
E-mail: xuanguiyu0181@163.com
网址:http://www.mf-china.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