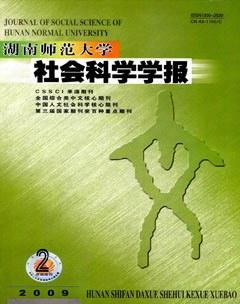戴震哲学重知之因探析
王艳秋
摘要:戴震的重知哲学的出现,有着深厚的历史学术背景。从明清之际到清代中叶批判理学的视角发生了转变,戢震试图以一种不同于理学的重知方式回到儒学;考据学率先确立了知识优先和实证的原则,戴震把这些原则变成了哲学观念;科学也在一定意义上为戴震提供了新的研究对象和新的方法。
关键词:戴震;重知哲学;道德理性;知识理性
中图分类号:B2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2529{2009)02-0029-04
戴震对“知”的重视,在中国哲学史上颇为引人注目。这不仅是因为它出现在以“行”颠覆理学的颜元哲学之后,与颜元的重行哲学形成对照,更是因为它把推崇“道问学”的朱熹哲学排除在重学之外,与程朱理学的重“知”也形成对照。戴震重知的特点曾引起过研究者的关注。胡适在《戴东原的哲学》一书中多次提到戴震的重知之意和“纯粹理智的态度”,并认为这是“戴学的真精神”。余英时从思想史的角度考察戴震的“智识主义”,认为它是“儒家智识主义发展到高峰时代的典型”,强调了它作为儒学发展链条上的一环同传统所具有的密切联系。戴震的重知已表现为其哲学的基本形态,他的哲学可以称之为重知哲学。这一哲学形态的出现,在一定时期内甚至导致了儒学重心的转移,表现出某些近代色彩。
所谓戴震哲学重知,不是就一般意义上的重视知识或轻视知识而言的,而是就它突出了“知”或“知识”在哲学中的地位和作用而言的。从一般意义上看,整个儒学传统在多数情况下都是重知的,然而在多数情况下,儒家对知识的态度都是服从于伦理道德的目的,从孔子的“未知,焉得仁”,(《论语·公冶长》)到朱熹的“尊德性,所以存心,而极乎道体之大也。道问学,所以致知,而进乎道体之细也”(朱熹:《中庸章句》)都体现了这一思维路向。与传统儒学这种以伦理学吞并认识论不同,戴震强调德性对知识的依赖性,道德只是第二义,求知本身是最重要的。德性不以任何形式存在于主体之内,主体只有超出自身,实现对外在事物必然性的认识,才能具备圣人的品质。知识来自于两个方面:一是对外物之理的精确认识,一是对儒家经典的正确解读。“明古贤圣之道”只在认识的结果中呈现出来。戴震这一颇具特色的哲学的产生,在当时给人以特行独立之感,然而它是在时代潮流的涌动中逼拶出来的一朵浪花,背后有着深厚而复杂的社会和学术背景。对这一历史背景的探讨将有助于我们更好地了解戴震哲学的重知特色及其在中国哲学史上的意义。
影响戴震重知哲学产生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就主要因素言,大体上可以归结为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明清之际诸儒批判理学的视角到清代中叶发生了的转变,从拆除理学的基本概念人手否定理学成了戴震哲学的任务;其次,伴随考据学的兴起学术领域出现了重视实证的观念,作为考据学重镇的戴震将实证思想和实证方法从一般考据原则提升为哲学思想和哲学方法;再次,西学的传人以及戴震本人对科学的研究也为他的哲学提供了重要工具。以上诸因素的存在和滋长,导致了清代学术领域中道德理性的逐步失落和知识理性的一再高扬,并最终汇成重视知识的潮流,戴震的重知哲学就是这一潮流的升华和体现。
一、批判理学视角的转变
戴震的哲学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在对理学的批判中建立起来的。然而戴震对理学的批判,与清初学者对理学的批判有明显的不同。后者是在一个十分复杂的社会背景下展开的,对理学的反对与对理学的拥戴、部分的远离理学与部分的归向理学、对理学理智上的难以认同与情感上的难以割舍,展现了思想、学术、政治纠葛在一起的复杂局面。总体上看,大批思想家如黄宗羲、王夫之、顾炎武、方以智、朱之瑜、陈确、傅山、唐甄等从不同方面对理学展开的批评和修正,已使儒学走向一个批判地进行自我总结的阶段。然而这些思想家的思想多由于其“山野”形态并没能真正主宰清初的理论走向,相反,一些跻身于新朝的汉族官僚和理学名臣,出于复杂的心理及现实原因,成了理学思想的守护者和推广者,理学在当时仍然占据着统治地位。但是,理学作为学术形态已走向衰退,因为尊崇或提倡理学者虽人数众多,可他们中没有人能将理学的既有形态给予实质的推进,甚至没能提出任何新的思想,株守成了他们的主要为学倾向。
清初对理学的批判,从哲学理论批评的角度看,显出两个主要特点来。第一,部分思想家从现实出发批判理学,这样的批判往往具有“外缘性”特征。就是说,批判往往从指责理学带来的不良后果开始,并上溯至理学的某一方面,作为批判的主要对象。它表现为从理学的外在影响来责难理学,以及以理学之外的标准作为批评理学的参照系。第二,那些契入理学内核的批评往往不能摆脱形而上学本体论的纠缠,且与理学的某一方面保持了一致。王夫之在理气问题上讲“理与气互相为体”(王夫之:《读四书大全说·孟子·尽心上》),就未能完全摆脱理学的“理在气先”的影响,有时还会夸大理的作用,说“天地之所以宰万物者,理而已矣”(王夫之:《周易内传·系辞上》)。黄宗羲以理依存于气的思想否定了理学理在气先的观点,并用“盈天地皆心”的命题修正了王阳明以“良知”为“心之本体”的思想,但王阳明的心物一体论仍然是他无法跨越的界限(黄宗羲:《明儒学案序》)。
以上两个特点说明,清初反理学虽然激烈,然而对理学理论的不足,思想家们的认识尚是外在层面的或局部的,还没能将其视为一个整体从理论的内核上透视它的缺陷。当时代进至清中叶,随着考据学的繁兴,思想家获得了审视理学的新视野和新方法,从理论内部剖析理学就成了学术领域的一个新的课题。这样的任务落到戴震等汉学家兼哲学家的人身上。戴震对理学的批判可以说是明清之际反理学思潮的继续和深化,但由于学术环境和时代要求的改变,他的批判明显地具有不同于早期批判思潮的特点。首先,他的批判完全扬弃了“外缘性”。这不是说戴震无视理学所带来的消极的社会影响,相反,正是对“以理杀人”的社会现实有着深刻的认识,他才没有停留于指责宋明理学末流的“空谈”上,而是将批判的矛头直指理学本身,从理学内部人手,试图根本推翻这种哲学。其次,与王夫之、黄宗羲等思想家没有跳出理学的形而上学本体论不同,戴震将这种本体论作为解构的对象,努力转变理学的问题方向及言说方式。再次,戴震对理学弊端的认识同清初诸儒不同,后者认为理学的主要错误是没有正确处理理气(道器)、理欲等的关系,戴震则认为,理学的根本错误在于其基本概念“理”是缺乏客观根据的主观意见,他们对其他范畴的运用也是错误的,因此他们的理论是毫无可靠性可言的臆说。正是这几方面的不同使得戴震在批判理学与建构自己的理论时选择了不同于清初激进思想家的进路,他突出了从现实存在出发的主体对客体的认知和从儒家经典出发的对文献的正确解读,这是一条重知的、经验的道路,也是戴震所认为惟一正确的道路。重视对客观事物的认知使他对理学的批判具有极其冷峻的一面,而试图正确诠释儒家经典文献又使他在建造
自己的理论时,充斥着一种理想的色彩。
总之,戴震对理学的批判是明清之际批判理学思潮另一种形式的继续,他哲学的重知特色与他对理学的认识和清代中期特殊的时代要求及学术气氛是分不开的。
二、考据学的推动
另一个与戴震重知哲学的形成有着密切关系的因素是清代考据学的兴起。它为戴震提供了知识优先的原则和实证的方法。
清代考据学是经学漫长演变过程的一个阶段。经学这一学术形态以一种特殊方式隶属于儒学传统,而考据学又总是与经学相左右。当然,儒家思想的演变和发展对经学这一学术形态的依赖在各个时代程度不同,以理学时期对它的依赖最少。理学是儒学发展阶段上最具创造性的时期,它对道家思想的吸收、对佛学理论的融合都使得它必须摆脱经学的束缚。与经学的疏离激发了前所未有的活力,庞大的理学和心学体系在独立于经学训诂考据的情况下得以建立。然而与经学的疏远并没有改变理学走上独断形态的命运,绝对真理以另一种形式即天理的形式出现在儒学传统中。
明清之际思想家责难理学时,首先要摆脱的就是理学的独断论,在没有更多外援可供借鉴的情况下,他们终于回到经学训诂这种延续儒学命脉的重要轨道上来。黄宗羲、黄百家、毛奇龄、胡渭等人清算邵雍的先天易说,阎若璩证明《古文尚书》为伪,“禹廷十六字”是拼凑的结果,所借用的都是考据训诂方法。他们认为理学的独立于经学的道德学说,其合理性是值得怀疑的。程朱的格物穷理、陆王的明心见性,均张扬一种超出任何具体知识的具有普遍意义的道德之善,善因不受经验约束而具有恒久的价值。而现在,思想家们开始关注它和古老的儒家经典是否发生关联。
清初考据学背后有着巨大的思想根源和哲学基础,它的结果反过来又渗透到思想和哲学之中。它所带来的直接后果是一定程度的思想解放和权威的动摇,而更进一步的作用是高扬了知识理性,将儒家所一贯坚持的理性原则作了最大限度的非道德运用,这为清代中叶的戴震形成自己的知识观提供了观念和思维方法上的资源。清代初期的训诂考据未必是立足于对理学的反动,但在事实上却动摇了理学的根基。这说明考据学本身所具有的内在原则对独断论是拒斥的。只是,那些学者运用考证质疑宋儒所依据的原始经典多少具有不自觉的特点,终没形成相应的理论与理学对抗,或者思想家们还没有这样的愿望。戴震则不同,他以考据作为击碎理学核心概念的武器,而且形成了自己独具特色的理论对抗理学。换言之,他将考据学作为建构自己哲学工具的做法是自觉的。
考据学至少为戴震提供了两个思维原则,其一是知识优先的原则,其二是实证的原则。与知识优先相对的是价值优先,价值优先是儒学的传统观念,至宋明理学发展到极点。清代考据学的兴起首先挑战的就是这一观念,汉学家几乎普遍反对“空谈”义理,主张问学只应关注训诂考据范围以内的知识,如文献的辨伪、版本的校勘、脱字讹字的补正、名物制度的考核等。这样的烦琐工作产生了一个积极结果,就是在一定范围内知识优先原则的深入人心。戴震是将这一原则运用于哲学研究的人。从两个方面可以看出他对这一原则的重视,一是他批评理学的“空凭胸臆”,一是他自己主张的“空所依傍”。他认为理学是无据立论,凭空构造出一个天理系统来,所以才会远离人的现实情感和欲望,对人的自然本性实施钳制的作用。反过来说,他是强调理论应以实际的知识为根据,不能预先设立任何先验的法则。重视实证更是考据学家的基本立场,在此无须作烦琐的论证。戴震也同样将实证观念提升为哲学原则,他主张所有理论都应建立在“求十分之见”的基础上,做到“传其信,不传其疑”(戴震:《与姚孝廉姬传书》,《戴震全书》卷六),具有“如悬绳树粲,毫厘不可有差”的可靠性(戴震:《与是仲明论学书》,《戴震全书》卷六)。正是知识优先原则和实证原则为戴震的重知哲学出现提供了方法论的保障。
三、科学及西学的影响
另一个对戴震重知哲学的出现产生了重要影响的因素是自然科学,而这一因素又与明清之际的“西学东渐”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西学的较大规模传人,在一定范围内改变了中国科学家的知识观,中国的自然科学渐渐摆脱了对儒学的依附,在封建社会后期有了相对的独立性。这一变化反过来影响了哲学,部分哲学家在作哲学思考时也站在科学的立场上,运用科学的知识观看待哲学问题。戴震即是其中较为突出者。
欧洲的科学文化,随着传教士的脚步走进中国。较早接触西学的徐光启和李之藻等人对西学均抱欢迎的态度。他们摈弃狭隘的民族偏见,主张全面吸收西学,力图使中国的科学观念、技术和方法获得突破性进展,不仅具备同西学竞争的能力,还要超越西学,走出一条富强之路。方以智作为明末清初的科学家和哲学家,更是主张“借远西为郯子”,将西方科学的实证精神和实测方法引进中国科学研究中(方以智:《物理小识·总论》)。他提出“质测即藏通几”的著名观点,将哲学奠定在自然科学之上,在当时理学独尊、“道问学”必须俯首于“尊德性”的情况下,开创了另一条哲学道路,即一条重视对事物认知的哲学道路,而且独立于传统伦理道德学说之外(方以智:《物理小识·自序》)。这一哲学道路在清代得到延续,并顺理成章地发展为戴震的重知哲学。戴震提出哲学即是研究“天地、人物、事为之则”,在哲学中将道德与知识分开,以及最终从认识论的角度探讨道德的合理性,这些都可以在方以智等人的思想那里找到某些理论资源。
就科学对戴震的影响看,首先,自然科学为戴震提供了新的哲学对象。与理学家追求天理相反,戴震把认识事物的“不易之则”作为自己哲学的对象。自徐光启提倡会通中西时,就特别注意吸收中国往籍中“多所未闻”的“所以然之故”与“确然不易之则”(徐光启:《修改历法请访用汤若望罗雅谷疏》),李之藻也认为西学可贵的地方在于能“缘数寻理”,“不徒论其度数而已,又能论其所以然之理”(李之藻:《请译西洋历法等书疏》)。清代的王锡阐、梅文鼎等科学家沿着徐光启、李之藻的道路,在历算研究中注重于数中求理。江永师从梅文鼎演习西法,而戴震又师从于江永,其数学才能深得江永赏识。从徐光启开始的追求事物不易之则的思想,中经清初学者的传承与发扬,到戴震那里已经逸出科学领地进入哲学论域。哲学对象的这一变化在当时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它表明中国18世纪的哲学具有明显疏离传统的倾向。
其次,自然科学为戴震提供了新的理论方法。如所周知,戴震由于深受西方科学特别是数学的影响,他在构造理论的过程中相当广泛地采用了形式逻辑的思维方法。在论述自己的思想时,他自觉地运用分析与综合、归纳与演绎的方法,如强调“分则得其专,合则得其和”(戴震:《法象论》,《戴震全书》卷六),“务要得其条理,由合而分,由分而合”(段玉裁:《戴东原先生年谱》,见《戴震全书》卷六)。在演绎推理方面,戴震注重概念的界定,要求概念“至当”,进而用概念去判断推理。他说:“明理者,明其区分也,精义者,精其
裁断也”(戴震:《孟子字义疏证》卷上,《戴震全书》卷六)。在归纳方面,他提出“一字之义,当贯群经,本六书,然后为定”(戴震:《与是仲明论学书》,《戴震全书》卷六)。戴震受西方数学影响最为典型的是按照《几何原本》的体例撰写了他生平最重要的哲学著作《孟子字义疏证》。他甚至要求哲学真理应该具有几何学公理的准确性,对事物条理的认识应“如直者之中悬,平者之中水,圆者之中规,方者之中矩,然后推诸天下万事而准”(戴震:《孟子字义疏证》卷上,《戴震全书》卷六)。
以上几个方面的因素在清代学术中相互激荡,导致了道德理性失落而知识理性上升,并最终促成了戴震重知哲学的出现。
清初对理学的批判虽然及少能深入到理学内部人其室操其戈,然而它是和时代大潮结合在一起的,足以形成一股力量,阻碍理学按既有方向前进。儒学自初创时起,一直是以伦理道德为本,坚持人道原则与理性原则的统一。理性原则又表现为服务于道德、以道德理性为主的思维路向。道德理性在儒家思想的演进和发展中起过重要作用,它以人的内在生命、人的价值作为关照对象,强调建立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关系,从而确保整个社会秩序的稳定。随着儒学的演进,特别是经过佛学的冲击后,儒学以理学面貌出现,道德理性精神逐渐内倾,过分注重伸张个人的内在生命和内在价值,忽视了将个体生命和价值与社会整体的生命和价值的关联。明清代际,社会思潮朝着实用的方向发展,道德理性笼罩一切的弊端立刻凸显出来。当顾炎武批评性与天道非圣人之学,王夫之讲性日生而日成,黄宗羲在历史的视野里谈心性、工夫、本体,颜元以重行代替重知时,他们都突破了道德理性的藩篱,用一种更宏大的眼光来看待儒家的学说,尤其是它的道德学说。理学所高扬的道德理性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落。随着考据学的日渐繁兴,道德理性的地位不断下降,知识理性的地位则逐日攀升。不仅对文字、音韵、名物、制度、金石、舆地、声律等等的研究成为专门学问,为知识而知识、为学问而学问的纯学术态度以胜于以往所有时代的姿态确立起来,学术获得了自身的独立性,而且儒家的伦理道德概念也在考据声中失去了形而上意味,变成了知识的对象。戴震就把理学“得于天而具于心”的“理”解释为事物的条理、文理、腠理、分理,“明道”则成了对这些必然之理的认知。
考据学坚守的是“无徵不信”的客观性原则,于事求根柢,于言求依据,在多重证实前提下达到贯通,最忌凿空和臆断,尤其反对无证立论。这些虽是一般考据学共同遵守的原则,但在中国清代这一特殊的历史时空中,它们又担当了思想领域所赋予的特殊使命。相对而言,科学虽然能直接促使知识理性的加强,但在清代其影响远不及考据学广泛,所以在参与社会思维方式和价值结构调整方面,它的作用也是有限的。然而科学对戴震的影响是较大的,这不仅因为戴震是一位科学家,还因为他作为负责天文、地理、算学等书籍校勘整理工作的《四库全书》纂修官,更有机会接受科学尤其是西方科学的熏陶。所以,西学对戴震哲学的影响主要是西方科学对他的影响。放在一个更为广阔的视野里看,这种影响是西方自然科学对中国古代哲学的影响。戴震从中吸取了某些科学的价值观和实证的方法,用以改造儒家的哲学。
戴震的哲学可以说正是知识理性占主导地位的社会思潮的产物,然而没有道德理性在经世实学、考据学等的冲击下日薄西山,知识理性成为主导性思维原则是不可想象的,戴震的这一特殊形态哲学的出现也是不可能的。
参考文献:
[1]胡适,戴东原的哲学[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
[2]余英时,论戴震与章学诚[M],北京:三联书店,2000.
(责任编校:李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