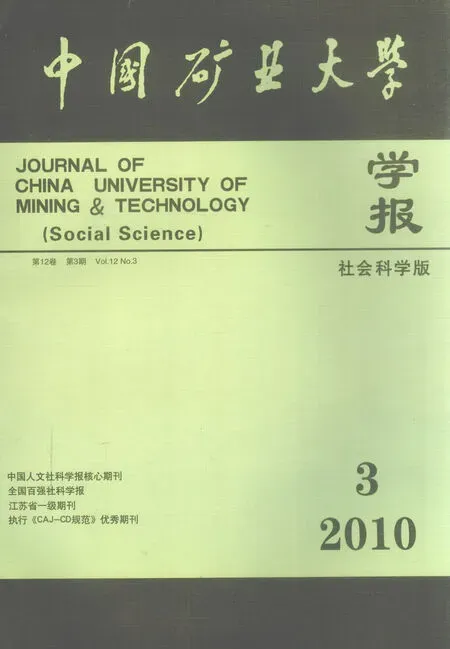论庄子“唯道集虚”如何可能
王 焱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中国语言文化学院,广东广州 510420)
论庄子“唯道集虚”如何可能
王 焱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中国语言文化学院,广东广州 510420)
“唯道集虚”是庄子传授给世人的一个悟道法门。“虚”乃是一种从不同角度否定常规的内心修炼工夫。从生存层面上说,虚能够使自己远离祸害,拥有一种安全感,进而悟道。从本体层面上说,虚能够使自己的本体——本性与世界的本体——道自行呈现。虚的工夫,类似于现象学所倡导的“悬置”方法,对现代人实现个体幸福而言颇具启迪。
庄子;道;虚;悬置;幸福
庄子在《人世间》篇中向世人传授了一个悟道的法门,那就是“唯道集虚”。意思是说,只有“虚”,才能领悟到道的真妙。“虚”字在庄书中频频出现,共有61次之多,如“虚则静”(《庄子·天道》)、“虚己以游世”(《庄子·山木》)、“虚则无为而无不为也”(《庄子·庚桑楚》),等等。“虚”乃是一种内心修炼工夫,与之异名同义的,还有“斋”、“忘”、“丧”、“外”、“损”等,都是具有剥离、忘却、摆脱等否定性意义的词汇。庄子在很多地方都提到了“虚”的工夫,比如最为世人所熟知的“心斋”与“坐忘”:
唯道集虚。虚者,心斋也。(《人间世》)
堕肢体,黜聪明,离形去知,同于大通,此谓坐忘。(《大宗师》)
这两种体道的工夫都有一个根本共同点,那就是“虚”,即对某些东西的去除与忘却。庄子认为,虚的工夫,能够通过排除普通意义上的感官关注、欲望关注、道德关注、情感关注、知性关注、是非关注等,获得对道的本真关注。
不难看出,所谓“虚”,其实就是一种生命的减法。按照一般的理解,一个人的获益,总意味着一个加法的过程,即现在比过去增添了点什么。比如儒家就主张,通过修善成德等正向积累的人格修养方式来体验道的存在。那么,庄子为什么要一反常理,认为人生的最大获益——悟道,只有通过生命的减法——“虚”才能实现呢?换言之,“唯道集虚”究竟是如何可能的呢?庄子对之并没有进行集中论述,而本文所探讨的正是这一问题。
一、除患与避害
首先,从生存层面来看。《庄子·山木》篇中有一寓言,集中表现了庄子对“虚”的生存功用的认识。寓言中,鲁侯去看望得道之人市南宜僚,市南宜僚见其面带忧色,便问其原因。鲁侯说他学习先王治理国家,敬奉鬼神,尊重贤能,不敢有丝毫怠慢,却仍然遭受祸患,所以感到忧愁。至于鲁侯究竟遭受了什么祸患,文中并没有说明。但只要联系到《人世间》篇就能明白,鲁侯所罹之患不外乎金木外刑等“人道之患”和焦虑内疾等“阴阳之患”。于是,市南宜僚向鲁侯教授了“除患之术”:“吾愿君刳形去皮,洒心去欲”,“吾愿君去国捐俗”。“刳”、“去”、“洒”、“捐”,都是具有否定性意义的词汇。“刳形去皮”即遗忘身体,“洒心去欲”即抛却欲望,“去国捐俗”即放弃名利。不难发现,所谓“除患之术”,其实就是一种虚的工夫。在庄子看来,只有做到虚,才能除患,进而“与道相辅而行”;反之,即使像“丰狐”与“文豹”一样谨小慎微,亦不能躲避祸患。
接着,市南宜僚描述了他心目中的理想之所——“建德之国”。生活在建德之国的人们,没有知性活动(“愚而朴”)、没有名利物欲(“少私而寡欲”),没有道德观念(“不知义之所适,不知礼之所将”),没有贪生意识(“其生可乐,其死可葬”),他们只不过是无思虑地凭着本真性情在生活(“猖狂妄行”),然而他们却与道相契相融(“蹈乎大方”)。市南宜僚认为,要达到建德之民的生存境界,其实并不需要“舟车”、“粮食”等外物,只需要“无形倨,无留居”,“少君之费,寡君之欲”,把成心、欲望放下。
最后,市南宜僚还讲述了一个“虚船触舟”的寓言。人之所以不会迁怒于虚船,就是因为虚船触舟完全是一个无心自然的行为;而有人之船则不同,人的存在,暗示着触舟这一行为的人为性和过错性,尤其当触舟的这个人“三呼”而“不闻”之时,被触之人定会认为此举乃是有意为之,因而“恶声随之”而就不难理解了。与此寓意相近的还有《达生》篇中的“复仇者,不折镆干;虽有忮心者,不怨飘瓦”。“镆干”与“飘瓦”都是无心之物,即使由于某种原因伤害了他人,也不会因此触怒于它,故而不会被伤。庄子的意思是说:只有当一个人处于“虚”的状态,葆有一颗“无心之心”,以本真性情来与这个世界相处时,他才能够避免敌意与危害。这也就是“人能虚己以游世,其孰能害之”所蕴涵的深刻道理。
庄书中讲述了类似道理的文字还有很多,比如《应帝王》篇中:
无为名尸,无为谋府,无为事任,无为知主。体尽无穷,而游无朕。尽其所受乎天而无见得,亦虚而已。至人之用心若镜,不将不迎,应而不藏,故能胜物而不伤。
庄子将这种弃绝求名之欲、谋策之知、专断之心而秉承自然天性的行为,称之为“虚”。庄子认为,当一个人将蒙蔽其真性的事物一一剥离时,那么他的心灵会如同镜子一般空明清澈,照物而不被物所扰动,就像《菜根谭》中所言:“风来疏竹,风过而竹不留声,雁照寒潭,雁去而潭不留影。故君子事来而心始现,事去而心随空”,故而能够“胜物而不伤”。
另外,《刻意》篇中还有一句话:“无所于忤,虚之至也”,也能够帮助我们理解“虚”之除患的道理。对于庄子而言,当一个人彻底地“虚”下来的时候,他就不会与任何事物相违逆,这就如同那“以无厚入有间,恢恢乎其于游刃必有余地”的“庖丁”(《养生主》),“和而不唱”的“哀骀它”(《德符充》)。既然与万物都不相违逆,那么自然也就不会与万物产生矛盾与冲突,故而能够避害免祸。所谓“不伤物者,物亦不能伤也”(《知北游》),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以上这些都说明,惟有运用虚的工夫,方能除患避害。而只有在避免了身体上所遇到的内外戕害和心灵上所遭受的情感动荡之后,我们才能够在生存层面上拥有一种安全感,进而领悟到道的存在。换言之,除患避害是悟道的基本前提。试想,当一个人时刻面临着生存威胁,被患得患失的情绪所左右而不能自拔时,生命尚且不能安顿,心灵尚且不能自主,怎么可能与道相辅而行。
二、复初与守本
下面再从本体层面来寻找答案。按照庄子理解,世界的本体是道,那么人,作为大道流行的自然产物,其本体(或曰本性)也应该与道相契合。《马蹄》篇中云:“彼民有常性,织而衣,耕而食,是谓同德。一而不党,命曰天放。”庄子认为,自求温饱,与道为一,这是每个人生而有之的真常本性。然而在现实社会中,由于受到欲望等各种因素的缠绕,人会逐渐远离大道,迷失本性,遗落自己最初的幸福。这时若是迷途知返,意欲重归大道与本性,那么就必须运用虚的工夫,将那些遮蔽本性的事物一一消解。
其实早在庄子之前,老子就曾对“虚”的本体功用进行过思考:“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观其复。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老子·十六章》)老子认为,当一个人把虚的工夫运用到极至,那么他就能够透过纷杂的现象观照到世界的本相,回归于自己的本根,从而体会到道的奥妙。这也就意味着,“虚”的过程,同时也就是回复本初之性的过程。正如陈鼓应所说:“老子复归的思想,乃就人的内在之主体性、实践性这一方向作回省工作”[1]。这种“复初”的思想在庄书中得以进一步发展,并成为庄子的一个浓重情结。《缮性》篇云:“缮性于俗学,以求复其初滑;欲于俗思,以求致其明,谓之蔽蒙之民。”世俗那些人生的加法,不仅不能够帮助我们找回真实的自己,相反,只会使我们离清明的本根渐行渐远。而只有运用人生的减法——虚的工夫,才能够使心灵回复到原初的真朴状态。这正如王博所指出的:“道是可以得的,但不是通过学。学只会让你增加些什么东西,让你离道更远。以学求道,恰似南辕北辙。相比起道来,人不是缺少,而是富余。”[2]
在《缮性》篇,庄子还对人的本与末进行了揭示:所谓“轩冕”,即名利富贵,并非人之性命所有,乃是外物,你偶然得到它,仅仅意味着它在你那“寄”存一段时间而已,“其来不可圉,其去不可止”;但人之本性不同,它根植于人的内心当中,作为人之根本而存在。“轩冕”等外物不过是人之末,而己之心性才是人之本。那些迷失于外物而遗忘了本性的人,便犯下了倒置之误。而惟有那些保全了真朴本性的人,方能持守人之根本,因而能够拥有永恒的幸福,所谓“乐全之谓得志”。这说明,“复初”也就意味着“守本”。
由此可见,“虚”的过程,不仅是一个“复”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守”的过程。换言之,我们对扰乱本性之物的清除,不仅意味着面向本性的回归,同时也意味着对本性自身的持守与保全。这一点可以从女偊向南伯子葵介绍自己闻道经过的文字中得以印证:“吾犹守而告之,参日而后能外天下;已外天下矣,吾又守之,七日而后能外物;已外物矣,吾又守之,九日而后能外生。”(《大宗师》)“外”即“虚”之义。不难发现,“守”与“虚”乃是悟道工夫的一体两面。因为只有持守住本性,才能破除扰乱本性的事物;同时,也只有把有碍本性的事物通通去除,本性自身才能得以守全与呈现。
“守”这个字在庄书中出现频率较高,如“守其宗也”(《德充符》)、“守其本”(《天道》)、“其天守全”(《达生》)等。“守”即持守人的根本所在——本真心性。庄子认为:“纯素之道,唯神是守”(《刻意》)。只有守全本性,方能与道合一。
《知北游》有一寓言,亦能够帮助我们理解“守”的意义。大司马年高八十,却仍然能够锤制钩带而无丝毫差错,其奥妙就在于“有守”。庄子借大司马之口对“有守”进行了解释:“于物无视也,非钩无察。”意思是说,只专注于他所喜好的钩带,任何与钩带无关的东西,他都不去关心。不难看出,“有守”,即专性凝虑而心无旁骛,也就是有所持守之意。“大马捶钩”的寓意在于:有所为,有所不为。“为”也就是“守”,“不为”也就是虚。只要我们守住了内心的道——本性,虚掉了道之外的事物——扰乱,那么自然达到一个无往而不胜、万物相济的融乐之境。与此寓言用意相类的还有《达生》篇中的“佝偻者承蜩”。庄子想以这个寓言告诉人们,要想掌握道的真义,就必须持守住心灵内在的能量,排除一切外物对心灵的干扰,所谓“用志不分,乃凝于神”。
三、“虚”与“悬置”
如此看来,虚的工夫,也就是一种使心灵恢复到原初状态,使本性得以守全的工夫。依庄子之见,只有当我们“疏瀹而心,澡雪而精神”(《知北游》),使附着于本性的东西一一脱落时,才能回归于自己的本体,使本性得以呈现;而只有当我们以本体的面目去面对这个世界时,世界的本体——道才会自行敞开。
庄子这种虚的体道工夫,很容易使我们联想到胡塞尔现象学所倡导的“悬置”的方法。在胡塞尔现象学中,“悬置”这个术语用来指称“将关于自然态度所特有的对实际存在的信念的一般论题悬搁起来,加括号或加以回避的活动”,“通常用作‘现象学还原’的同义词”[3]。很多学者都曾对庄子体道工夫与胡塞尔悬置方法的内在相通性进行了探讨:如徐复观指出:“现象学的归入括号,中止判断,实近于庄子的忘知。”[4]刘若愚指出:“心斋”与“判断的悬浮”“这两个词之间不仅仅是字面上的巧合,因为两者都包含有在感官知觉基础上的‘自然立场’的悬置,两者都指向对事物本质(神)的直觉把握”[5]。“悬置”的方法认为:只有将由常识所形成的那种所谓的“自然观点”悬置起来,对“自然观点”中种种认知的、价值的、道德的判断加上括号,存而不论,才能排除一切人为因素的干扰,去伪存真地使最终不可怀疑的东西清晰呈现。不难发现,这也正是虚的工夫所承担的作用以及所意欲达到的目的。
借助于现象学的理论,我们可以这样来解释“唯道集道”何以可能:虚的内心工夫,将种种遮蔽其天性的世俗观念和感觉一一悬置起来,悬置后的“剩余”便是心灵的本真直觉,亦即胡塞尔所说的“纯粹意识”,只有凭借这种心灵直觉,万物之本质——道的真义,才会自行开显,照亮生命。
四、虚与幸福
最后亦可从现实生活出发,理解庄子“唯道集虚”如何可能。我们可以把庄子的道境,理解为人生最高的境界——幸福,那么,“虚”对于个体幸福实现而言,有何现实功用呢?
幸福可被抽象地理解为所获得的东西与所欲求的东西之间的一种比例关系,因此提高幸福感可通过两种方式:或提高分子,即增加所获得的东西,即“生命加法”;或降低分母,即减少欲望,即“生命减法”。
在消费主义意识形态的刺激下,一般人总是通过生命加法,即不断地激荡欲望,使欲望对象物化,以增强幸福感。人常言“梦想成真”、“万事如意”,可见,欲望总是走在现实的前面。然而,这种做法有着很大的局限。首先,一个人要获得一样东西,往往取决于天时地利人和等诸多因素,换言之,一个人是否能获得一样东西,这不是他一个人能掌控的。其次,即使一个人幸运地获得了他想要的东西,实现了既定欲求,但由于他的欲望先行于现实,加之欲望又是无限膨胀的,因此,通过生命加法这种方式,并不必然提高幸福感。
而庄子思想所倡导的虚的工夫,则能够对这一局限进行弥补。虚的工夫,乃是一种通过不断地使自我减少欲求,以增强幸福感的内心工夫。庄子认为,一个人要体道,要获得幸福,其真正的奥秘在于生命的减法,也就是看淡、摆脱那些对心灵构成负累的包括名利、欲望等在内的一切内容。减得越多越彻底,离道与幸福也就越近。通过生命的减法所获得的幸福,乃是一种朴素、本真而永恒的快乐,即庄子所说的“至乐”。
虽然,庄子通过虚的工夫解决个体幸福问题,只能停留在心灵层面,无力落实到现实层面,但其对改善现代人的心灵生态还是颇具启迪的。刘梦溪曾指出:庄子哲学能够为现代人为外物所困的遭受“天刑”的处境,提供精神解脱的普遍性资源。西方思想界近年极重视老庄学说,原因就在于此[6]。的确,现代生活中,心为物役、自我异化的现象越来越严重,庄子所倡导的返朴归真的生命减法,也就
越能显现出其自身的光芒。现代人普遍面临着来自财富、名誉、情感等各方面的诱惑与重压,倍受焦虑与疲惫的煎熬。从这个意义上说,烦忙的现代人,的确应懂得淡然与退让,懂得留出一些精力与心灵空间,去体悟生命自身的自由与美好。
[1] 陈鼓应.老子今注今译[M].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3:140.
[2] 王博.庄子哲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4:109.
[3] 赫伯特·施皮格伯格.现象学运动[M].王炳文,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989.
[4] 徐复观.中国艺术精神[M].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 1987:68.
[5] 刘若愚.中国的文学理论[M].田守真,等,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92.
[6] 刘梦溪.庄子与现代和后现代[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4:5.
Why“Emptiness”Advocated by Zhuangzi Can Lead One to Apprehend Tao
WANG Yan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Culture,Guangdong University of Foreign Studies, Guangzhou 510420,China)
Zhuangzi holds that a method named“emptiness”could lead one to apprehend Tao.By means of“emptiness”,one can be far away from danger or disaster and acquire a sense of security,which is the premise to apprehend Tao.“Emptiness”can help one return to his reality——his nature,and at the same time,it can make the reality of the world——Tao show itself.The method named“emptiness”is similar to“phenomenological reduction”,which can help modern people to realize happiness.
Zhuangzi;Tao;emptiness;reduction;happiness
B223.5
A
1009-105X(2010)03-0001-04
2010-06-04
广东省211工程三期重点学科建设项目(项目编号:gdufs211-2-021)
王焱(1981-),女,博士,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中国语言文化学院副教授,外国文学文化研究中心博士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