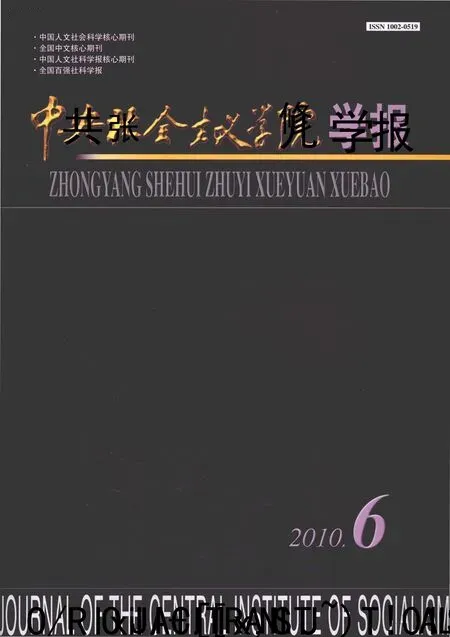对汉译阿含佛教经典关于宇宙和人生三个判断的探析
王 珍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北京 100081)
“诸行无常,诸法无我,一切皆苦,涅槃寂静”四法印①或三法印: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槃寂静。作为佛教与其他学说区别的标志,把“无我”放在了极为重要的位置。可以说,“无我”是原始佛教的一个核心概念,以致于印度古代思想家称佛教为“无我论”;霍韬晦先生则认为,佛教的“无我”主张,“足以代表整个佛教的特色”[1]。
“无我”这一概念首先出自原始佛教阿含经典。阿含 (ahan),意为法归。僧肇在《长阿含经·序》中认为:法归者,“万善之渊府,总持之林苑”。阿含之总持,“譬彼巨海,百川所归,故以法归为名”。《四阿含暮抄序》认为:阿含者,趣无也。这里把阿含旨趣归于导向涅槃,而涅槃正是原始佛教的理论与实践归宿。也有人将阿含经典译为《圣训集》或《圣言》,认为这是唯一的原始佛教经典,是唯一认可佛陀思想的凭证[2],正如吕澄先生所说,“佛说契经结集流布,莫先于阿含,亦莫信于阿含”[3]。佛教的一些基本概念和理论大都出现在《阿含》中,《阿含》是佛教大小乘共依共宗的根本经典。因此,阿含经典可以看做迄今为止最原始、最可信靠的佛教典籍[4]。
从阿含经典来看,概括地说,“无我”之建立通常有以下几种表述方式:无常—无我 (《增阿含》卷三十);无常—苦—无我 (《杂阿含》七十六经);无常—苦—空—无我 (《杂阿含》七十九经),或无常—苦—无我—空。这几种表述方式具有某种一致性,“无常”、“苦”、“无我”是它关于宇宙和人生的三个基本判断;而且,经典也常以“无常即苦,苦即无我”或“无常即苦,苦即空,空即无我”来表明它们之间的逻辑关系,进而建立起“无我”之论[5]。但如果我们进一步追问:“无常”是一种普遍必然的法则吗?无常必然是“苦”吗?“苦”者一定无“我”吗?如果“苦”已经表明无“我”,那么,“谁”在轮回?本文即是从阿含经典出发,集中于“无我”建立的环节进行思考。
一、无常是否为必然法则
无常、变易,是对自然存在事物 (包括人)的一种客观描述。在阿含经典中,不论是变易、苦、空、无我,还是苦、集、灭、道,都显然是佛教解道、修道的入口。换句话说,没有这一点,或者不从这一点谈起,整个原始佛教,乃至整个佛教理论、修道将不复存在。因此,在这种意义上可以说,它是原始佛教之所以建立的逻辑起点与入口。
在这里,在与人的关系上,我们可以进一步问:这种变易性是脱离人而固有的呢?还是与人的特有的相应规定性呢?第一个问题并没有实际意义,虽然它可能为很多人所认同。正如马克思所说:“被抽象地孤立地理解的、被固定为与人分离的自然界,对人来说也是无。”[6]同样,脱离人的自然变易法对人来说是没有意义的。
第二个问题,也可以更进一步地直接表述为:变易之法是人规定的吗?若按照康德所表述的“人为自然立法”,这种无常变易法,自然的变易性,恰恰是被人特有的生理心理结构等规定的,是人依据自身的规定性为自然建立起来的。类似的观点托马斯·阿奎那也做过表述:“被认识的事物按照认识者的模式存在于认识者之中”[7],也就是说,我们事先已经规定了被认识的事物,然后我们再去对它进行认识。若按照佛教般若宗观点,变易法也是与人身心的特定存在状况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因此,被奉为般若之心的《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借“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的观音自在菩萨之口说道:“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受想行识,亦复如是……是诸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是故空中无色,无受想行识……乃至无老死,亦无老死尽……”何以有此言论呢?对普通人来说空是空,色是色,诸法在生灭、有垢净、在增减、有老死;对小乘人来说,有老死尽,因此才去脱离老死;而对大乘般若来说,正如上文所引述,两者皆无。可以看出,人不同的身心存在状态,用佛教的话来说,人的修道次第不同,有着不一样的自然世界。如果上述观点是有道理的话,它意味着:“变易”不具有绝对的独立性,而是在关系、在与人的关系中存在和展开的。
由此,我们倾向于认为,如果说自然无常之法是一种必然存在的话,只能是一定关系中的必然。换言之,如果事物之变易性是一种真理,它应该是具体的、有条件的真理。这并没有否认自然的优先存在性。对世人而言,并不是说,离开了变易法,还另存一个其他法。但是,自然与自然的存在方式毕竟是两个很不相同的概念,人们必然要由后者才能了解前者。
二、无常是否必然“苦”
如前文所述,阿含经典认为无常、变易即是苦,进而以“无常,苦,是变易法 ”,说明“无我 ”。例如,《增一阿含》卷二十七明确指出:“此五盛阴是无常义。无常义者即是苦义。”把无常和苦联系在一起,是一件有意味的事情。无常是自然现象;苦是人的主观感受和判断。为什么无常的自然就必然引起人的苦受呢?大概因为“我”不喜病、老、死,而这些正是变易法;因为“我”不喜,又不得不遭受,所以“苦”,这似乎是一个必然逻辑。这个逻辑导致了原始佛教对现世生命的“彻底”断绝,导致了弃现世生死求涅槃的观念和行动。阿含经典反复强调人生“一切皆苦”,无半点可乐之处,让人厌生。但是如果没有希望,对生命的彻底断绝并不能确证生命的美和力量。因此,阿含经典也指出,绝望之处便是希望所在:
(佛陀道:)汝言“我身色四大,六入,父母生育,乳哺成长,衣服庄严,无常磨灭”。以此为我者。我说此为染汙,为清净,为得解。汝意或谓:“染汙法不可灭,清净法不可生,常在苦中。”勿作是念。何以故?染汙法可灭尽,清净法可出生。处安乐地,欢喜爱乐,专念一心,智慧增广。梵志,我于欲界天、空处、识处、不用处、有想无想处天,说为染汙,亦说清净,亦说得解。汝意或谓染汙法不可灭,清净法不可生,常在苦中。勿作是念。所以者何?染汙可灭,净法可生,处安乐地,欢喜爱乐,专念一心。智慧增广。(《长阿含》卷十七)
这里指出,因为“我”为染污,也为清净,也为解脱,所以才能至超越之境:“于色多修厌离住,于受、想、行、识多修厌离住,故于色得厌。于受、想、行、识得厌。厌已,离欲解脱,解脱知见,我生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作,自知不受后有。”(《杂阿含》四十七经)
只是与当时印度其他思想弃绝身体、现实本身不同,佛陀让人在缘起法中看苦,《中阿含》卷三十八的一则故事记述了这个问题:
当时佛陀问一名梵志 (即志于修梵行者——笔者)须闲提:“什么是无病,什么是涅槃?”
须闲提回答说:“身即是病,是痈,是箭,是蛇,是无常,是苦,是空,是非神。”以两手抆摸而作是说:“瞿昙,此是无病,此是涅槃……”佛陀说:“汝尚不识于无病,何况知见于涅槃耶?”
在他看来:“缘受则有,缘有则生,缘生则老死,缘老死则愁戚啼哭,忧苦懊恼,如是此生纯大苦阴。”无常、变易法的世界和人生是“纯大苦阴”。
与此明显不同的是,《周易》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源头,也是看到了事物之变易,但并没有认为现世是“纯苦阴”,没有弃绝,而是积极面对,提出“君子趋吉避凶”。所以,同样从变易法开始,佛陀在印度通过阿含经典提出了厌生弃生,目标是趣涅槃,不生;而《周易》则是运用物之变易,贵生乐生,“正性命”①《周易·乾卦·彖》:“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含太如,乃利由贞。”。这一点也可以从吕澄先生在印度佛学与中国佛学心性的对比中看出来,他认为:印度佛学认为苦、烦恼不与心性相顺,前者的性质是骚动不安,而心性则是寂灭、寂静的,可以称为“性寂”说;中国佛学 (如《大乘起信论》)则认为,人心为万有的本源,此即所谓真心。这种真心自性智慧光明遍照一切,而又真实识知,可以称为“性觉”说[8]。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二者虽然不同,事实上是一个事物——“心性”的不同方面。但是,印度佛教的“性寂”说偏重于从消极、否定、苦的意义上理解心性,而中国佛教的“性觉”说则偏重于从积极、肯定、乐的意义上理解心性②这一不同,不独是在印度佛教与中国佛教的对比中显现出来,在汉语系佛教教内理解印度佛教时同样能反映出来。例如,慧律法师讲述东初法师《阿含概说》中指出:五蕴与五阴只是名词翻译的译本不同;“蕴”是积聚之义,“阴”是覆蔽义,蔽覆本性,为蕴的异译;虽然如此,五蕴的翻译更符合佛陀的本意,而五阴的翻译比较而言不符合佛陀的本意。我们从这里也可以看出,五蕴是对事物的客观描述,而五阴则含有对事物描述的带有消极倾向的价值判断,即对本性的覆蔽,这样就需要去蔽。事实上,从阿含经典来看,五阴也无不可,因为正是为五阴所蔽,人才感到苦,但是慧律法师的取前舍后显然有着更为广阔的进展空间,也更容易导向中国佛教的“性觉”说。。上述对待变易法的不同态度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为什么厌生弃生的印度佛教传到中国之后,变成了贵生乐生的独具特色的中国大乘佛教。
《庄子·内篇》中说:生命“察其始而本无生,非徒无生也而本无形,非徒无形也而本无气。杂乎芒芴之间,变而有气,气变而有形,形变而有生,今又变而之死,是相与为春夏秋冬四时行也”。在庄子那里,生死变易并不是苦。死不必为苦,生未必乐,生死变迁不过如同春夏秋冬变迁一样恬淡自然。
可见,变易之法并不必然被认为苦,也未必为苦。但是,由佛陀对十四个形而上问题的置而不答来看,佛陀不讲他所认为的无用、无意义之法。他之所以从无常、变易出发大力强调苦,是为他的涅槃旨趣服务的。也就是说,无常与苦之间的关系由于涅槃这个目标才变得必然而有意义。
所以,对人生用“苦”进行绝对化的概括,其合理性只是就涅槃的“一个”层面的意义而言,是具有片面性的。换言之,如果涅槃的意义是“乐”,是人生苦、集、灭、道的证果,这就说明生之本身含“乐”因。那么,上述中国传统文化对待“生”、“死”、“心性”的态度也正是在阿含经典的这种意义上显示了它鲜明突出的尊严与价值。
三 、苦者 ,无我
虽然“无我”之“我”是“常”义,但也指世人对自己的称呼,这两种含义有时却无法截然分离,这里主要在后一含义上进行讨论。阿含经典多处阐述“苦者,无我”,是把它作为结论来用的,至于论证则很少。就人类趋向快乐的本性而言,“苦者非我”这一论断能够引发人们深切的认同。那么,苦者为什么就不是“我”呢?苦者必然“非我”吗?把“苦”与“非我”作这样必然的联结,就导致这样一个结果:对“我”、对“苦”的弃绝。上文已经论述,中国传统文化的某些方面,于变易之中看到的不是纯粹的苦,而是对变易的正向一面做了发扬。然而,做了这样的发扬,并非没有意味到苦,而是与“苦者非我”的取向不同。中国传统文化在某些方面没有避苦、弃苦、弃“我”。恰恰相反,它勇敢地迎面接受了这样的“苦我”。例如,《孟子·告子下》把“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之苦看做“天降大任于斯人”,这样才使其“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把苦看做是对“我”的完善与磨砺。与此相似,明朝陈继儒在《小窗幽记》中明确写道:“惜吾辈之受世折磨,不知惟折磨乃见吾辈。”两者都是把苦看做“我”应有的、必然的、积极的真义。
虽然大小乘佛教几乎同时传入中国,但中国仍然毫不犹疑地选择了大乘。相比较而言,世间即涅槃显然不同于出世求涅槃,前者首先是对苦我的接受,偏重于入世的担当;后者则是对苦我的弃绝,偏重于离世的担当。
应当看到,世间即涅槃,否定了与世间相对的涅槃的存在,但并没有否定涅槃本身。它把涅槃性融入世间,从而消弭了涅槃的独立性。世间即涅槃,使世间具有了涅槃性,涅槃并没有完全消失,反而在世间赢得了自身的存在。从这里也可以看出,中观、大乘是在原始佛教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它是对原始佛教既弃又扬的发展。因此,抛弃原始佛教理解中观、大乘一定是不完整的,甚至是倒退的。换句话说,世间即涅槃,正是因为涅槃德性融入了世间。否则,世间还是世间,不是涅槃;涅槃还是涅槃,不是世间。
四、无我,谁在轮回
阿含经典一方面讲无我,另一方面又讲轮回。既然无我,谁在活着?谁在受苦受乐?谁在受报?谁在轮回?这个问题在佛教发展史中一开始并不突出,后来才为部派佛教所注意,也成为佛教中的一个重要理论问题。事实上,阿含经典中并非没有注意到这个问题,它至少两次被提出来。一次是《中阿含》卷十一记载,当时佛陀正在讲诸法无我,“诸摩竭陀人而作是念:若使色无常,觉、想、行、识无常者,谁活?谁受苦乐?”另一次是《杂阿含》五十八经记载,当时佛陀也是在讲诸法无我,有一比丘心念“若无我者,作无我业。于未来世,谁当受报?”对于这个问题,佛陀两次回答基本类似,这里把其中的一次摘录如下:
……佛告比丘:“诸所有色,若过去、若未来、若现在、若内、若外、若粗、若细、若好、若丑、若远、若近 ,彼一切非我、不异我、不相在。受、想、行、识亦复如是。比丘,如是知,如是见,疾得漏尽。”
尔时,会中复有异比丘,钝根无知,在无明 [穀 -禾 +卵 ]起恶邪见,而作是念:若无我者,作无我业。于未来世,谁当受报?尔时,世尊知彼比丘心之所念。告诸比丘:“于此众中,若有愚痴人,无智明,而作是念:若色无我,受、想、行、识无我,作无我业,谁当受报?如是所疑,先以解释彼。云何比丘,色为常耶?为非常耶?”
答言:“无常 ,世尊。”
“若无常者,是苦耶?”
答言:“是苦 ,世尊。”
“若无常,苦,是变易法,多闻圣弟子于中宁见是我、异我、相在不?”
答言:“不也 ,世尊。”
“受、想、行、识亦复如是。是故,比丘,若所有色,若过去、若未来、若现在、若内、若外、若粗、若细、若好、若丑、若远、若近,彼一切非我、非我所,如是见者,是为正见。受、想、行、识亦复如是。多闻圣弟子如是观者便修厌,厌已离欲,离欲已解脱,解脱知见,我生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作,自知不受后有。”佛说此经时。众多比丘不起诸漏。心得解脱。佛说此经已。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仔细阅读上文,可以清楚地看出,佛陀虽然说“先以解释彼”,但他的解释始终似乎没有什么解释,或者说似乎没有正面回答这个问题,而是把刚刚讲的道理几乎重新讲了一遍。面对这个新的、在后来很多人看来极为重要的问题,也为后世很多人苦苦探寻的问题,他并没有在已有的基础上讲出更新的道理来,确实颇为耐人寻味。事实上,“无我,谁在轮回?”至少从阿含经典来看,是个虚假的问题。为什么呢?关于这一点,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认识:
第一,该问题本身表明了发问者“有我”。上述故事中,佛陀第一句问该比丘:“色为常耶,为非常耶?”该比丘回答是:“无常”。佛陀接着问道:“若无常者,是苦耶?”该比丘回答:“是苦”。认为有“无常之苦”,就是“有我”,怎么能是“无我”呢?也就是说,如果人感到“苦”,就是“有受”,还在“有我”,就在轮回之中。在轮回,就表明了“有我”,而不是“无我”。所以,这个问题说明发问者还“有我”,在执于“我”见,故而上述故事把这个问题斥之为“恶邪见”。
第二,在佛教那里,“无我”不仅是个理论问题,更重要的还是个实践问题。也就是说,在佛陀那里,仅解“无我”之理是不够的,还要证“无我”之境。因为如果只是字面讨论而未依行,只是“有字无义”,即说理而未达义。依阿含经典,如果人真的体证到“无我”了,就意味着可以脱离生老病死诸苦,步入涅槃。涅槃就是不生,不生也就没有死。无生无死,就不再轮回。不再轮回,谁在轮回?所以也就不存在“无我,谁在轮回?”这样的问题了。
第三,人不应该思考未来轮回的问题。阿含经典追求的是“我生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作,自知不受后有”,所以,当佛陀被问至未来如何时,他一般都拒绝作明确回答。例如,《中阿含》卷五十四记述道:人不应该问像“我未来是有,还是没有?”这样的问题。《杂阿含》一一六八经把对这一问题肯定或否定的任何回答都视为“动摇”,加以摒弃。《中阿含》卷二则把这样的问题视为“三结”之疑结,认为应当断除。因为依照阿含经典,对未来的任何想法都会“招未来有”,都会使人受生,从而不得从生死轮回中解脱出来。只有心性的寂灭才能到达“我生已尽,自知不受后有”未来世不生的境地[9]。所以,为了“涅槃”、不生,就要“断未来有”,就要根除能招至“未来有”的任何想法,至少要在五蕴和合的意义上断。这也是佛陀对未来是否轮回问题不做回答的另一个重要原因。
第四,联系大乘来看,在《大涅槃经》中又重新肯定了常乐我净,肯定了涅槃我。以此反观阿含经典,可知,抽象地讲,我并非我,也并非无我,无我并非无我。“无我”只是为破“我执”才显出其意义。如《大涅槃经》所说譬喻:良医为医众病,说乳是害人之物,非是药。如果此时非要在“乳不是药”的问题上探个究竟,依佛教来看,显然又进入了另一个虚妄的陷阱。因为这本来是一个不究竟的论断,以此为基础的衍生问题,必然无真实义。
在对佛教相关基本观念分析的基础上,上文对汉译阿含佛教经典关于宇宙和人生的三个判断,联系其逻辑环节“无常—苦—无我”进行了探析。这种探讨并不否认这一环节在印度佛教阿含经典那里具有一定的必然性,而是指出,当它进入其他文化如中国文化的土壤中时,它所发生的变化也许并非是对其原有含义的误读,而恰恰表明了不同的富有意义的文化价值及其必然选择。
[1] 霍韬晦.原确良始佛教“无我”观念的探讨[A].佛光大藏经·阿含藏附录[C].台湾:佛光出版社,2007.
[2][4][9]杜继文.汉译佛教经典哲学 (上卷)[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140.
[3] 吕澄.阿含经[A].中国佛教[C].北京:知识出版社,1989.
[5] 王珍.对汉译阿含佛教经典“无我”概念的思考[J].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0,(4):56-59.
[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 4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178.
[7] 约翰·希克著,王志成译.多名的上帝[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34.
[8] 吕澄.性寂与性觉[A].佛家二十讲[C].北京:华夏出版社,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