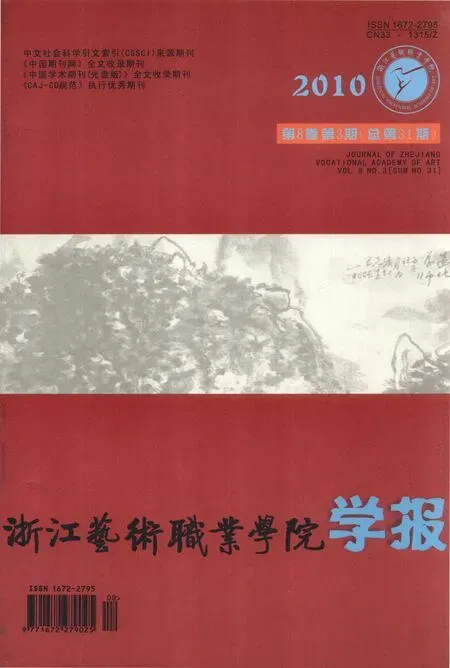关于当前影视创作的人文思考
仲呈祥
关于当前影视创作的人文思考
仲呈祥
在坚守中华民族人文精神的时候有四个必须坚守:第一,坚守中华民族在创造能力上的特长,失掉了这一条就失掉了我们的优势;第二,坚守一个民族的心理素质,比如欣赏电影,中华民族有中华民族的电影鉴赏心理;第三,坚守民族特有的审美思维方式,这个和创造力上的优势这条有同也有异;第四,坚守民族文化系统中的根本概念不变。如果做到了这个,也就可以承认坚守了人文精神传统。
人文环境;中国文化;影视创作;人文思考
Abstract:There are four principles to uphold Chinese humanistic spirit.Firstly,uphold Chinese nation’s strengths in creativity,which is our advantage.Secondly,stick to the psychological quality of a nation,as Chinese nation has his own appreciation psychology when watching movies.Thirdly,uphold the nation’s unique aesthetic way of thinking.Fourthly,stick to the fundamental concept of the nation’s cultural system.
Key words:humanity environment;Chinese culture;film and television creation;humanity thinking
各位同行,各位朋友,大家好。我与杭州素有渊源,我母亲是杭州人,我本身还兼杭州的文化顾问,所以今天我来学习,来向大家汇报。说起来我学过文学,从师于朱寨先生,治过中国当代文学思潮史;后来又师从钟惦棐先生,学过电影美学;再后来跑到电视界,当了很多年的不称职的中国电视艺术委员会的秘书长;如今又待在文联工作岗位上。我基本上属于党培养的、人民造就的门门懂一点、样样都不精的 “万金油”似的文化干部。这样说自己比较实事求是。
一、当前人文环境的思辨
举办“浙江潮”文化论坛,我觉得这是我们艺术学院非常有远见的文化举措。定期邀请全国文化界的志士仁人来这个论坛上发表一己之见,可以传播信息、激活思维。这是最大的好处。半天时间要传播系统的知识不可能,用句土话叫 “扯淡”。但是半天时间传播一些信息,激活受众的思维是可能
为什么我今天要从这个地方入题?我对当前的影视创作进行一番人文思考。人文思考是非常重要的。现在西方一些知名的大美学家、大哲学家、大思想家都在思考该如何看待人类从工业革命到信息革命这段历史。无疑,工业革命极大地推动了人类生产力的发展。这是一次革命,是好事,这是无疑的。但人们现在都清醒地认识到世界上没有有百利而无一弊的事情。这个话是我们浙江人鲁迅先生说的。鲁迅先生说过一段非常辩证的话:世间无有百利而无一弊之事,只可权大小。工业革命推动了人类的进步、生产力的发展,但也留下了一个越来越明显的弊端。工业要革命就要采伐资源,过度的采伐就破坏了自然生态环境,影响了人与自然的协调相处。现在科学发展观专门有一条叫 “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就是总结了这个经验。现在我们有个任务叫 “修补地球”。从 20世纪中后期开始,越来越迅猛发展的信息革命以电子技术、高科技为特征,又一次极大地推动了人类生产力的发展。但人们也发现它留下了越来越明显的负面效应:人文精神的滑坡。在某种程度上,道德伦理的沦丧可以概括成一句话:人文生态环境的破坏也显而易见。不再像工业革命那样是自然环境的破坏,而是人文生态环境的破坏。那么人文生态环境的破坏会给人类的未来造成什么后果呢?谁也说不清楚。但危机是存在的。经济全球化了,人们知道文化不能搞全球化,文化要多样化,政治是多极化。文化必须多样化。人们对人类的生存环境、对生物链的保存有清醒的认识。一会儿说东北虎没有几只了,很紧张;一会儿说大熊猫少了,生物链不能破坏。为什么?“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地球是一个多种生物共存的整体。有些事情我们不理解不等于不存在。过去 “大跃进”的时候干过很多破坏性的事情,除四害要把麻雀杀光,杀光麻雀会造成一种弊端,造成生物链的破坏和生态的不平衡,要吃亏的。大科学家杨振宁、李政道对天体物理、对最高等的自然科学了解得越多、越深入,就越清晰地发现宇宙安排得如此有序,哪个轨道是哪个行星的不能乱来,乱来是要出大事的。
最近北京大学出了一套书,是美国哈佛大学毕业的一个台湾学者写的,他一辈子研究哲学和诗,叫史作柽。他说人 40岁以前不要说 “成熟”。大家知道,故宫博物院的大专家朱家晋,年轻时候是个戏迷、票友,一生喜欢京剧。他最喜欢梅兰芳和杨小楼的《霸王别姬》。听了以后说 “绝了”。于是跑去和杨小楼说他想下海唱一出《霸王别姬》,扮霸王。结果杨小楼和他说:“你四十之后再演。现在你领会不了霸王当时的心情。”史作柽先生一生著作不多,只有两把板斧:一把板斧是著作《哲理笔记》、《生命现象》;另一把板斧是写诗。他说诗是他的生命。关于哲学,他说人投胎到这个世界都要面对几个东西,第一个科学,科学是求真的,是开拓人类通向真理的坦途的。第二是艺术,艺术是求美的,为人类探求真理营造氛围。这两个东西分别作用于大脑的两个部分。科学主要靠抽象思维、逻辑思维,作用于人的左脑,增强、提高人的智商;艺术作用于人的右脑,右脑主情商,专门提高、丰富一个人的情商。正常人的主要思维方式是形象思维,但也不是绝对化的,是有交叉的。现在的现代化建设主要目的是培养富有创造能力的人。脑科学家告诉我们,人的创造能力 20%靠左脑、靠智商,80%靠情商、靠右脑。科学家的解释是,一个人的情商高,情感丰富,内在驱动力就大,以丰富的情感 (说到底就是人文精神)调动内在的智商释放到最理想的程度。这是科学分析的结果。钱学森先生躺在病床上的时候,温家宝总理去看他。他老人家惦念着祖国的科技人才的培养,他说他担忧我们未来的科技人才不懂艺术。他老伴是音乐家,弹得一手好钢琴,他经常沐浴在妻子的音乐下,所以情商很高。他年轻的时候,父母叫他学自然科学先要学音乐。大家读过《傅雷家书》,如果不知道是傅雷写给儿子傅聪的,我们会觉得这是挚友之间的谈心,根本没有父子两辈的概念,探讨真理、探讨人生。这家人音乐修养高,艺术细胞丰富,感情丰富,所以在那种意境下能够相互交心。我们要看到我们艺术学院的学生的天职,从事着人类神圣的职业。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人之为人就因为人是区别于其他动物的高级的理性的情感动物。只有人才有其他动物没有的独特的精神家园。人类要健全地持续地发展必须经营好自己的精神家园,光有物质家园是不行的。精神家园主要靠艺术教育。这就是艺术从人类学角度的神圣职责。史作柽还说了一条,人类还面临宗教。他认为宗教是在科学与艺术之间搭了座桥。我们从积极方面理解就是一个人要有理想、信仰。
为什么西方科学家发现人文精神的滑坡、道德伦理的沦丧?其实我们身边也已经开始了。我敢说全国看电视剧看得最多的是本人。每年政府奖、“飞天奖”参评的 1000多集电视剧我基本都得看。按每天看 10个小时算就是三个多月。接着是 “星光奖”,就是电视文艺晚会的奖项。开始我认为这好办,晚会不外乎几大块:小品、歌舞、短剧等,看个开头、结尾就行了。可是用 “快进”比老老实实看还费事。又是六七百个小时,又要看两个月。接下来 “五个一工程”、司法部的 “金盾奖”、总政的 “金星奖”等等。我生命的一半时光是消磨在电视机屏幕前的。其中有好的,看了让我情感得到陶冶、灵魂得到净化的有,不多。大量的是平庸的。平庸的电视剧看得越多智商越低、情感越糟,是成反比的。这是我生活的氛围,是信息革命带来的,电视机带来的。我去日本访问时,NHK卫星部的部长三本先生用最高的礼遇接待我,不是去大餐厅,而是请我去家里。NHK是日本的国家台,全部要日本名牌大学的优等生才能进去。他们一家都酷爱中国文化。老大沉醉于《红楼梦》,正在谈恋爱。老二学经济,喜欢《三国演义》。他说《三国演义》里面有 “策”,可以悟经商之道。他们的情报很准。他说:“我知道你是研究汉文学的,我问你一个问题,我们家从我父亲开始,我们三代人都酷爱中国文化,为什么掌握汉字的能力一代比一代低?”我一看他家里摆的高清晰电视机,跟他说就是这个怪物造成的。他说有道理。日本文字假借了很多汉字。过去交流信息要写信、写文章,现在打个电话、看看电视,不用汉字了,能力当然越来越低。但是不用汉字是要改变思维方式的。这是个很深刻的道理。
过去我在社科院文学所跟着朱寨先生的时候接触了语言史。他们回忆起我们过去搞汉字简化,说干了一件非常不理性的事。有人提出人类的文字符号里最难学的就是汉字,方块字太难写,建议把它废除了,把它拼音化、拉丁化,像英语一样用 26个字母。后来又实行简化。这是不聪明的。人类的信息传播主要经历了两次革命:一次就是有了造纸术、印刷术,有了书籍文化;再一次就是电子文化。中华民族的思维方式形成的很重要的根基就是其使用的文字。我们的文字左右结构、上下结构、内外结构,形声字、形意字,是从象形文字繁衍而来的。比如说“染”字的结构是完全有道理的。为什么三点水?因为古时候染布要用染料,要用水;第二,染布的时候一定要多次、反复地在染料里滚过来、滚过去,“九”者数之极也,表示多次的意思;第三,“木”字哪里来的?是因为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染料是从树枝上取下来的一种东西。所以不要想当然写成“米”字。这是形意字。还有形声字。比如说 “切”字。一边是 “七”,一边是 “刀”,“七刀七刀”念快了就是 “切”字。中华民族使用汉字作用于思维方式,使形象思维特别发达。派生出的戏曲文化全是追求意象、以虚代实、程式化,这是有根基的;反过来讲,如果把根基推翻了,民族的思维方式都要变。现在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张德江说过两次这个话:一个地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与他地区、他国家、他民族在和平发展条件下的竞争,说到底是争文化的。这个见解非常深刻。他举了例子,非洲的一些国家早就独立了,按理说有政权了,但是一些民族没有文化传统,所以至今贫穷落后、挨打受气。反过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作为战败国的德国,当时一贫如洗,但它有文化、有反思的传统,大家知道,马克思、康德、黑格尔都是在那儿出来的,历来的大思想家、大思辨家不少从那儿出来的。德国人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进行了比较深刻的反思,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应该承担的罪责是承认的。多少年以后它又成为发达国家。日本也是战败国,当时基本上也差不多了。它也有文化,它的文化不在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反思有多深刻,而在所谓的“武士道”精神,在它民族中的某些人长期存在的军国主义思潮上。它现在又成了发达国家。我去过美国、日本两个国家的博物馆,显现出来的博物意识完全是两码事。美国只有 200年的历史,它办博物馆没什么历史值得炫耀的,于是就集天下之精华而展览之。到洛杉矶的博物馆,中国是中国馆,法国是法国馆,意大利是意大利馆,展品全是向收藏家租来的,让它的国民得到博物的享受,历史的影响。它本身是个移民国家,把其中的文化交融整合,显现出了它的个性和生命力。日本东京的博物馆什么都不要,就是明治维新短短的一段,用高科技手段把这段时间日本的发达史细致地展现出来,宣传它自己。和影视界的现象联系对照起来,日本人去年选贺岁片,看上了《首席执行官》,我没想到。《首席执行官》是写海尔的张瑞敏张总怎么创业、怎么把企业办到世界上去的。在东京作宣传的时候,广告上就打了一句话,“看中国人在怎样崛起”。日本人在新年到来的时候就在提醒它的国民注意周边安全:旁边的睡狮醒了,在崛起了。两相比较,我们这几年的贺岁,大家一窝蜂地在某种引导下,都盯着几个人给我们搞笑。不是不需要笑,过年嘛,笑是正常的。关键在于,一个民族不能只知道笑而不知道为什么笑,而且笑得没有品位、没有幽默,笑得日趋庸俗。所以研究我们民族的生存的时候要想到这个问题:生存与发展。前段时间满报纸都是 “和平崛起”,现在细心的人会发现不用这个词了,改成和平发展。“崛起”这个词太有刺激性,很多国家就有 “中国威胁论”了,不符合小平同志讲的 “韬光养晦”。我们是发展中国家,用发展就可以了。张德江当时就说要比文化,高度重视文化,比到最后还是要比文化,要比民族的人文精神。这是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西方的学者也都意识到这个问题。最近,几十位诺贝尔奖金的获得者云集巴黎,发表了《巴黎宣言》,其中有一段话让人感到既亲切又振聋发聩。翻译过来大致是说:为了人类的未来能够协调持续发展,人类应当回到2500年以前的东方孔子那里去讨教。以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一致提出科学发展观,再进一步提出构建和谐社会,这是一种世界潮流、人类进步的潮流。
孔子思想的精髓在于构建大同的和谐社会,哲学精粹在中庸之道。前段时间看庞朴先生发表的论文,称“一分为三”是中国人的最高智慧。我们都习惯了一分为二,因为那时候的哲学基础是斗争哲学。一个政党、一个国家要打江山、夺政权必须信仰斗争哲学。一分为二是有它的长处的,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混沌事物的两极。但是人类社会如果进入了和平发展阶段,不再是打政权而是搞建设阶段,就不能够再坚持这种“二元对立”、“非此即彼”的单向思维,而应该调整到全面、辩证的科学思维。所以庞朴先生说了,“三人行必有我师焉”,“三生有幸”,“三点定一平面”,都是 “三”。“一分为三”在和平发展的历史条件下,最大的优势在于既看到了事物的两极,又防止走极端。“执其两端,取法乎中,故曰先进”就是这个道理。到了北京,天安门、地安门,左安门、右安门全是对称的。当然现在的天安门多了个国家大剧院,大家认为 “甚不协调”。搬到另外一个地方,它可能是个艺术品,但在那里破坏了北京建筑的和谐美。
谢铁骊同志 (拍《早春二月》、《包氏父子》、《红楼梦》的导演)80周岁华诞、从影 55周年的时候在北京开了个会。人大副委员长许嘉璐同志一赶到就说:“这个会不是非要我来不可,而是我主动要来的。”我们知道,许嘉璐原来是北师大的中文系主任,后来是北师大的副校长,后来是国家语改委主任,再后来是人大副委员长。许嘉璐说,在当前的艺术语境下 (“语境”这个词本来是哲学家美学家用的,他说今天他也用一次),有识之士都发现了人文精神的滑坡,人文知识分子、艺术工作者神圣的历史使命就是把已经产生的负面效应缩小到最低限度。要想完全消除是不可能的,还是鲁迅先生说过的话,世间有百利而无一弊的事情是没有的,这是个历史过程。但知识分子的神圣使命就是把负面效应缩小到最低限度而把积极效应发展到最理想程度。如果我们在这点上看得很清醒,我们的社会、我们的事业就会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如果在这点上陷入盲目,会给后代造成好几代人都弥补不过来的损失。那天上午许嘉璐进中南海,锦涛总书记征求民主党派负责同志对经济工作会议讲话稿的意见,他诚恳地建议党中央从文化战略高度上重视文化产业。他说,现在美国的 “三大片”(即麦当劳的土豆片、好莱坞的进口大片、硅谷生产的软件芯片)登陆中国大陆,使我国青少年一代从物质消费到精神消费日趋美国化。一个国家、民族自立于世界之林的能力是它文化的根。文化的根受到破坏,将来就要影响它自立于世界之林的资格。同样的道理,中华民族的文化本身就是多元包容、丰富多彩、源远流长,而在世界的诸般文明里,是唯一经久不衰、没有断续的文明。我们怎么能够让自己国家民族的文明面临衰竭而无所事事、充耳不闻、熟视无睹呢?什么叫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包括文化工作者、艺术工作者、科学工作者,就是先期占有了某一领域人类文明较多成果的群体,干哪一行的就是那一方面的专家。这个群体的神圣使命就是传播文明。什么叫以人为本?从一定意义上讲就是把服务人、提升人当做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以人为本就是坚持以提升每一个体的综合素质、精神境界,促进其自由而全面发展为本。以人为本必然走向以人才为本。我们做的一切都要有利于提升人的全面自由发展,有利于提升民族素质、提升民族的文化利益,使我们的文化实力在世界领先、在人类领先。现在一些文化人类学家发现,要消解、弱化一个民族的文化,有两种文化非常见效:一种文化西方叫 “监狱文化”,我们叫专制文化。我们经历过 “文化大革命”的文化,高度集权,八亿人民八个样板戏,百花凋零。这种 “监狱文化”、专制文化可以严重破坏一个民族的文化,乃至濒临灭亡的边缘,到现在后果都没有完全消除。巴老生前说:“我一听到 ‘样板戏’三个字就胆战心寒。”因为在当时那种特殊语境下不仅是一种文化,还是一种政治。当然我们不能简单否认样板戏,样板戏也不能简单归功于江青,那是集体智慧的结晶。所以我们现在还在唱,还在演,但确实留下了专制文化特殊语境下的产物的后患。还有一种文化,现在著作都出来了,叫做 “娱乐致死”的文化,就是专门搞笑的文化。一天到晚嘻嘻哈哈,搞低级、庸俗的笑,这种文化可以把一个民族的精神瓦解掉。
二、中国影视的人文思考
明白了现在的大背景、语境,我们来看中国的影视文化,做一点肤浅的人文思考。当前中国影视创作空前繁荣,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多样化、这么创作自由,但在我的艺术经历里,新时期以来,也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令人忧虑。这是辩证的。成绩不说跑不了,问题不研究解决不了。为什么令人忧虑?因为我们是个多民族国家,什么事情都不能搞单一化,单一化是违反人类人文精神健康发展方向的。事情很简单,百花齐放才是春还是一花独放是春天呢?举个例子,诗歌写到唐代到顶峰了。讲唐代的诗,人们一下子想到两个代表性人物。一个杜甫,那是诗圣。“诗圣”是郭沫若说的:“民间疾苦,笔底波澜,世上疮痍,诗中圣者。”一想起杜甫,我们就会想到青铜器,它的古朴、沉重、现实主义。“三吏”、“三别”,一下子想到 “暮投石壕村,有吏夜捉人”,一直到 “老病有孤舟”、“戎马关山北”,都是非常现实主义的。另外一位代表性人物李白,一想起他就不是青铜器而是唐三彩。毛主席公开表示他更喜欢 “三李”,李白、李商隐、李贺,因为李白的诗歌比起杜甫注入了更多的英雄主义;更多的浪漫主义,“黄河之水天上来”,想得简直没边了;更多的牺牲精神。因为李白出生在碎叶,大概就在吉尔吉斯斯坦,他从小在西域文化、少数民族文化熏陶下成长,童年又来到了四川江油,接受蜀文化的熏陶,多种文化在他的个体身上交融整合。所以李白诗歌的想象能力、浪漫能力更强,迸发出一种独特的生命张力。
一样的道理,我们对自己的文化也面临着这个问题。“专制文化”和“娱乐致死”文化这两种文化可以消解民族文化,值得当今我们高度警惕。你们不知道现在这股势力来势之猛到什么程度!去年“金鸡奖”,《手机》为什么不得奖?有记者在下面提得很厉害。我说,“金鸡奖”是中国电影的最高学术奖,也就是说,每年选择一部 (如果票数相当才会有并列)代表当年中国电影最高审美水平。那么,我们要想一想,今年是不是《手机》最好?有些同志说了一句话:“《手机》好玩,但很浅薄。”它要经得起我们分析,特别要经得起人文分析。《手机》贴近了当代的民众,特别是青年一代的某种婚恋情态,但是有一条,《手机》从始至终贯穿的价值取向是否是现代化的?这可以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从葛优演的角色 (主持人)到张国立扮演的角色 (制片人,兼带大学里学美学的女研究生),有一个共同特征:以男性为中心。不要说影片里展示了葛优演的角色如何利用各种场合表现出对女性的不尊重,而且包括张国立扮演的角色,带着女研究生还要开个房间,在宾馆里幽会。如果反映了这种现实,对其进行有力度的审美批判,也对。但是,电影里呈现了甚至在某些方面还有点带有对从葛优到张国立扮演的角色的某种欣赏。这样一来,评论家就应该从人文精神的角度提出意见:这是现代化的精神还是与现代化精神相悖的以男性为中心的某种封建意识的呈现?另外,党中央在号召构建和谐社会,社会的基层组织细胞是家庭。该不该构建和谐家庭?一部电影弄得若干善良的女性学会了偷看丈夫的手机,以窥视他是否别有所好;若干本来忠厚的丈夫学会了寻找机会看看妻子的手机,是否在外面也有不轨。震荡、动摇了多少和谐家庭。我们不能把家庭矛盾全归咎于一部电影,也不能抹煞一部电影对于社会的潜移默化的影响。基于这两条,我们兼容并包,欢迎它的出现,让大家去思考、去讨论是可以的,但逼着我们给他最高奖项没这个道理。我借用那句话说:“《手机》好玩,但很浅薄。”我还没敢说很 “脏”。这下完了。第二天,《新京报》的头版标题:“强烈要求 ‘金鸡奖’评委会主任仲呈祥向导演公开赔礼道歉”。这个太有点霸道了吧?有些事情我们是可以分析的。又比如说,去年在宁夏颁奖的时候,宁夏回族自治区主席就问我:“你是弄电影的。你老说你们的电影好,怎么我秘书去看了直摇头,我叫我儿子去看,他回来说不怎么的,我叫我司机去看,司机说不好。你们究竟怎么回事?”然后跟我说了一件事:兰州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提了提案,要求把这部电影关了。兰州公安局破获了一个盗窃集团,小面包车里全是那部电影的光盘,一审的时候小偷交待说:“我们的集团本来是松散的,自从我们头让我们每人看了两遍以后,我们增强了组织纪律性,出去作案的时候成功率大大提高。”同样是这个话,我们不能简单地把犯罪集团的犯罪成因归咎于一部影片,但是我们否认一部影片产生的某些潜移默化的影响不是唯物主义。我们选贺岁片,选最佳演员,同样呈现出一种倾向,值得我们进行人文思考。
去年我去美国盐湖城的一个学校,那个学校三万一千学生,具有艺术传统,他们的艺术团到北京、上海都演出过,艺术修养很高。我去了之后才惊讶地发现,他们对中国电影只知道一个张艺谋,还知道半个陈凯歌,其他几乎都不知道。于是就提出要看《十面埋伏》。大家知道,《十面埋伏》前三分之一是在展示盛唐文化,张艺谋觉得营造的视听感官不够,马上把演员拉到了四川的竹海:盲女在前面跑,两个捕快在后面追,箭穿喉咙,鲜血直喷。也许导演觉得色彩对比还不够强烈,于是又把一帮人拉到乌克兰的冰天雪地,雪白的雪和鲜红的血形成对照。放给美国的大学生看了,我问他们怎么样,他们讲得很真实:这个电影画面很好看,制作很精致,但整个电影好像就是跳了两段舞,跑了三段路,死了一群人,完了。人家没有看出什么人文内涵。我当时就做了一个很有意义的实验。我同时带了霍建起的《暖》,这其实是个很简单的故事,就是人类对自己的初恋感情应该怎么看。一个村子里有一对恋人青梅竹马,女孩子叫暖,男孩子叫井。封闭的山村里,两个人荡秋千。女孩子渴望到外面的世界去看,她比较浪漫,情商比较高。秋千荡高了,就说:“看到了,看到了,我看到北京天安门了。”男孩子说:“我怎么什么都没看见?”表明了一种憧憬。本来风平浪静,改革开放了,城里的剧团来演戏,其中有个英俊的小武生。暖一生的艺术细胞都激发出来了,就跑去看戏,送瓜籽,送土豆,一来一往就送出了感情,就移情别恋。过了一段时间,小武生演完了戏要回城里,就跟她山盟海誓,说他一定想办法把暖弄到城里去,因为暖很有艺术天分。暖有了这个美好憧憬,于是月月盼、日日盼,望眼欲穿,但是音讯全无。自己的所爱被人夺走,井本来很悲伤。但他用自己的人性去温暖受了伤的暖,于是两人又重归于好。他们又一次荡秋千的时候,秋千的绳子坏了,暖把腿摔瘸了。两个人从此发奋读书,准备考大学。改革开放第一次恢复高考,暖成绩虽然比井好,但因为腿有残疾,体检不合格,没被录取。井收到录取通知书后对暖说:“你成绩比我好,我一定要进北京给你联系个学校。”又是一番山盟海誓。女人的冷静就表现在,她上了一次当以后,就显得比较矜持,不那么盲目了。暖对井说:“我们村就出了你一个大学生。你到了北京以后,好好读书,不要想我,也不要给我写信。你给我写信,如果我三封信不回,你就不要等我了。”井到了北京马上写了第一封信。暖看了以后心里一股暖意。信里描述北京怎么好,马上要给她联系学校之类。村里有个放鸭的小哑巴,很喜欢暖,但是够不上,这次一看邮差有从北京寄来的信,有和暖套近乎的机会,马上给暖送去。暖一看信是北京来的,出于女性的自尊,有意在哑巴面前表现得不那么重视,当场把信撕了,扔在小河沟里。哑巴一看,以后天天赶着鸭子等在村口,第二封、第三封、第四封……他就帮她撕了。于是悲剧产生了。十年以后,井已经大学毕业,跟一个同学安了家。为了帮中学老师解决合同纠纷,井回到了村里,在村口碰见了暖。这时候暖已经嫁给哑巴,组织了一个家庭,生了一个可爱的女儿。两个人回到暖的家,哑巴看见了。这里有很多感人的细节,哑巴要在情敌面前显示家庭的温暖。外面下雨了,井要把小女孩喜欢的自动伞送给她,暖怕他着凉,把伞拿过来跑到村口。这时候哑巴抱着小女孩追上来,比划了一番。小女孩跑到井面前:“叔叔,你明白我爸爸的意思吗?爸爸的意思是要你把我和妈妈带进北京。”因为哑巴自省了,他觉得不应该撕别人的信,破坏一对好姻缘。他不知道井已经成家了。电影的最后,井要回北京了,非常惆怅地挥手告别,哑巴一家 (夫妻俩抱着孩子)依依惜别。三个人都是好人,三个人都做过对不起对方的事:暖不应该移情别恋,井不应该等不及在北京成家,哑巴不应该撕别人的信,毁了一段好姻缘。影片告诉我们人类对初恋的感情。初恋往往是纯真的,但往往不成功。三个人在回首往事的时候,应该多一分自省,多一分理解,多一分宽容,人与人就会更和谐。这个主题有什么不好啊?陆游回到沈园的时候不是还写《钗头凤》吗?大词人、大诗人不是也想念初恋的对象吗?这是很正常的。这部影片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解释。有人就说,这个电影为什么得 “金鸡奖”?它把中国农村写得不是哑的就是瘸的。这个电影在美国大学一放完,那里的大学生说了一句话:“这电影有意思,好玩,让我们想起了《廊桥遗梦》。”这就证明,人类对电影文化人文内涵的追求有某种一致性:作为艺术的审美的把握,电影应该表现人类真实的、纯洁的、美好的感情。但是我们现在不是这样。大家注意现在炒得很热烈的在威尼斯电影节拿了奖的一部电影,跟大家说实际情况,我就觉得很为不妥。它用四川方言。现在就是一股风电影,从 212部电影里选出 29部进入 “金鸡奖”评奖的,大概有一半都是方言、10部以上都是方言。这样开掘人性我觉得张扬的不是我们崇尚的人文精神,展示中国的精神风貌我觉得不应该去投合西方某些人对中国人的一种扭曲的、变态的理解。投其所好去邀赏,这是丢国格丢人格的。
国际电视奖艾美奖今年在东京、明年在汉城 (现在叫首尔)举行。2003年的时候叫我去巡视,我提了一个意见,说他们不聪明。美国电视艺术科学院的院长、国际电视节的主席问为什么。我说,他们丢了一块 13亿之众的市场,排斥了最青睐电视艺术的中国电视观众和中国电视艺术家。我说要在中国办一次,当时他们选定了杭州。我还和程蔚东说了做好准备。当时他们问哪个城市好,我如实作了介绍。我说中国有三类城市他们会有兴趣的,一类以人文景观取胜,如古城西安,全是人文景观,兵马俑是世界上其他地方看不到的;第二类以自然景观取胜,如山水甲天下的桂林;第三类是将人文、自然景观交融整合、兼而有之的,如杭州。杭州不仅有天下美景的西湖,西湖边上一圈都是人文。鲁迅阻郁达夫迁居杭州说得很清楚:“坟坛冷落将军岳,梅鹤凄凉处士林。何以举家游旷远,风波浩荡足行吟。”而且毗邻上海。他们一听很感兴趣。我说上海的黄浦比曼哈顿还漂亮。但是后来凤凰卫视的老总刘长乐说他全包,中央电视台对出钱还有点犹豫,于是就到香港去了。香港选了一部电视剧,何琳演的《为奴隶的母亲》,说穿了就是借腹生子。我不是说那个剧不好,可以看出他们选择的眼光。本来柔石先生写的是旧时代,人家可不管,以为现在还是这样的。有钱人家的老婆没有生育,把人家的老婆租来,住三年生了个儿子后轰走,然后自己和租来的老婆争风吃醋。我觉得柔石先生在当时写是有积极意义的。老实说何琳的表演跟当时特定人物的典型心态差得还很远,毕竟她的人生积累、情感积累、生活积累还没到那个程度,还不懂得为人母之后又要为他人生儿子的辛酸和痛苦。刚刚开完的全国宣传部长会议,很明确地提出要构建大外宣格局,要正确展示中国人的精神风貌、人文追求,提出要反对 “三俗”:低俗、庸俗、媚俗。说到低俗、媚俗的东西,这次推荐上来要参评的一部片子,这个低俗就没法说了。大家想想,为了片面地追求观赏性,人文精神的滑坡已经到了什么程度了,就认为这种电影一定会有视听感官的刺激感。如果说《十面埋伏》靠高科技手段和构图能力、审美能力营造了一种视听奇观,那么,那部低俗的电影就走向了另外一面。这样的问题已经引起了很多有识之士的高度警惕。
我很钦佩的王元化老先生有一段话对我们很有启发,他是做过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的。他明确说了:“我不喜欢《十面埋伏》这样的时髦片。我觉得张艺谋的艺术造诣十分空虚浅薄。他的作品只是故作深奥状,其实不过是以新奇掩饰浅陋而已。”每个人对每部作品都有评论的权利,是个人的见解。下面这段话我认为是真理。他说:“艺术倘使都像股票一样以炒作来提高价值,陷入市场化的泥沼,那便是艺术没落的开始。”这是他亲手签了字的信。我们大家想想是不是这样?最近有部电影,电影还在拍,先发个消息:这部电影的上亿投资海外版权已经收回,以后国内的放映就是净赚了。一部电影作为精神产品,本来应该靠真善美取胜。不宣传电影的思想性、艺术性如何,而去宣传思想、艺术之外的。海外版权拿回来的言外之意是什么?洋人都要看,中国人不看不是傻吗?说句实在话,投资本来多半都是洋人投的,洋人要买你的版权也是一种炒作。昨天晚上大家都看到了,新闻里也播了,一部电影投资 3亿多,要代表国产片参加奥斯卡奖。我作为普通的观众要问一句:这符合中国的国情吗?3亿多花在什么地方不好,这 3亿多是我们的还是国外的投资?还有,中国电影的最根本的经验是什么?我在中国电影研究所电影研究中心工作了很多年,当了五年不称职的中国电影研究室主任。中国电影资料馆馆藏的 3万多部拷贝,那段时间我一天看 6—8部电影。当时我有条件一个人坐着看,看了我心里有数。
三、电影与中国文化
1895年法国杜米埃尔兄弟发明了第一部电影,比我们早十年。中国电影自 1905年的《定军山》开始,说明了什么?电影这种舶来品在中国土地上一落脚生根,与生俱来的血缘联系就是与中国民族文化、民族戏曲相联系。但是,20世纪之初,虽然背景是新文化运动和 “五四”运动,但是主要影响中国电影制作的是两种文化:文明戏和鸳鸯蝴蝶派。中国电影问世之初的二三十年,代表人物张石川公开讲 “我是要赚钱的”,他提出 “营业主义”。后来有些进步文化人提出批评,他加了一句话叫 “营业主义加一点点良心”。当时除了少数的像《劳工之爱情》《孤儿救祖记》比较有中国传统文化,大量的是《火烧红莲寺》这样打打杀杀的、言情的多,鸳鸯蝴蝶派的多,没有出现高潮。按照中国电影家协会主席吴贻弓同志提出的三个标准,第一,作品源源不断,且不乏经典之作。考察是不是高潮,很明显的一个标准就是有没有经典作品,没有是不能算的。那个时代找不出经典作品。一直到 30年代,在中国共产党的影响下,左翼文艺工作者介入,具体说来就是夏衍、田汉、阳翰笙等,开始有了吴永刚(吴贻弓的父亲)导演的《神女》,然后《渔光曲》《十字街头》《马路天使》一大批进步电影出现,一直到 40年代出了《八千里路云和月》《一江春水向东流》,这段时期的电影不仅在中国电影史,而且在世界电影史上都占有一席之地。所以称之为高潮是当之无愧的。第二个标准,人才辈出,且青出于蓝。也就是说要有承传关系。这个时期出了很多人才,吴永刚是这段时间出来的,包括一大批优秀的演员,白杨、刘琼、王丹凤等等都出来了。1986年我跟着白杨团长、刘琼副团长到新加坡去,一下飞机,来接的都是华人,拿着鲜花,令人感动,把刘琼 30年代演的《文天祥》照片放得很大举着。那些华人都是白发苍苍的老头、老太太了。当时我问他们,那些老太太说,那个时候在上海哪个人要是找到刘琼当先生,是一辈子最大的幸福。问那些举着王丹凤照片的男的,说那时候看她的戏,长得真漂亮,哪个人娶了她当太太睡着了都要笑醒。证明当时电影是深入人心的。第三个标准:观众源源不断,且为自发的,不是靠发文件组织观众来的。
前段时间,今年的 “金鸡奖”给了两个有成就的导演终身成就奖,一个是上海的谢晋,一个是北京的谢铁骊,称为 “南北二谢”。对历史、电影文化进行人文思考是非常必要的。从不同的视角思考得出的结论是完全不一样的。我最近看了两篇博士论文,中央一所艺术院校的两位博士写的,研究 1905年开始那段历史。一篇题为《论鸳鸯蝴蝶派乃中国电影类型片的正宗》。她的结论说,中国电影一开始就是《火烧红莲寺》,就是类型片、武侠片。其实,《火烧红莲寺》根本没有片子了,只有文字记载。今天《十面埋伏》的轰动证明了中国电影经历了一百年的时间又回到了正统。无独有偶,同一个导师指导的另一位女博士写了另外一篇《论鸳鸯蝴蝶派为中国类型片电影的基础》,找了很多鸳鸯蝴蝶派的东西,不仅电影还有电视剧 (没完没了的《京华烟云》)来证明鸳鸯蝴蝶派是中国电影乃至电视剧的正宗。这就完全把结论弄错了。实际上,以后的事实证明,中国电影的成功在于把舶来品中国化、民族化,是对中国人民争取自由解放的历史进程进行艺术呈现的重要形式。现在有些电影是把本来已经中国化、民族化了的,具有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电影倒过去变成了好莱坞式的中国电影。这就是民族文化要不要弘扬的问题。现在恐怕很多观众都有这个印象了,说看了某些所谓的大片,好像都是学好莱坞的。不是不要借鉴,但是这里有个坚守民族的文化立场、民族的人文精神的问题。这点并不是很简单的事情。最近中国文联总在纪念杰出的艺术家是有原因的。我们有个看法:一个民族审美思维的最高成果主要体现在这个民族的杰出的艺术家身上,而这些杰出的艺术家正是人民养育、时代养育的。这正体现了唯物史观。我们承认,大量的民间文化、民间艺术也显现出中国民族审美思维水平,但更为集中的是各个时期杰出的艺术家。前段时间我和何院长都去参加了韩美林艺术馆的开幕式。我注意到一个现象,好像美术院校的来者不多。我甚不以为然,我觉得艺术应该打破门户之见。为什么?一个根本的观念,韩美林的艺术是民族化、个性化、风格化、现代化。他的线条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书法、绘画、雕塑、陶艺他都能。在艺术领域里,专才易得,通才难求。一个国家里,有多少人能够给国家留下自己的艺术馆呢?他奉献给人民,这是大智慧,是大艺术家的大智慧。那天我说了这个话:韩美林乃是中国齐鲁文化和吴越文化杂交而生成的一个优良品种,他本身是山东人,母亲是浙江人,爱人也是浙江人。在美丽的吴越文化养育的西子湖畔伫立起一座呈现出齐鲁文化雄浑气派的韩美林艺术馆,不是使这个地方的人文色彩更丰富多彩吗?
再往后说到谢晋、谢铁骊的时候,这条是非常可贵的。谢铁骊本来是个新四军战士,后来当了新四军的文工团团长。解放以后受命组建电影研究所 (中国电影学院的前身),50年代才开始拍片子,学当副导演、导演。五六十年代的时候,我们的哲学是斗争哲学,以阶级斗争为纲,那时候老爷子已经拍出了《早春二月》,不能不佩服他。在那个大环境里,艺术家有对艺术的独立的追求,对人性的深刻理解,有独到的思想发现和审美发现。萧涧秋身上的东西在当时是犯大事的,所以后来挨批。那天在会上谢铁骊说了八个字:服从组织,据理力争。我认为他讲了真话,是有党性、有人民性的艺术家。他就在服从组织、据理力争中寻找了充分展示个性和才华的最大的可能空间。《早春二月》中留下了典型的细节:148元买了套西服。现在的青年人会说 14800元的西服也不算是最好的,但当时 148元已经是天价了。我们再想,“文革”里的八个样板戏他老人家拍了五个,因为他特殊的经历和特殊的位置。但一有机会拍故事片,他就拍了《海霞》,又挨批了。尤其到改革开放以后,1986—1989年期间,中国的电影杀声漫天、血流成河,娱乐派起来的时候,那年北京电影制片厂拍了 15部电影,从名字大家就清楚了,什么《艾米小姐和她的情人》《太监历史》啊,全是这种。结果他老人家独立地干了一件事情:拍《红楼梦》,六部八集,钻到传统文化、优秀古典名著里面去了。这就证明了一条,艺术家真要有独立的思想,自由的精神,这是陈寅恪先生的话。我认为这是对五四精神的必要补充。五四精神重要的是科学民主,这是不能推翻的。但另一面,作为艺术家独立的人格,独立的思想、自由的精神必不可少。谢晋也是个大导演,也很有成就,我们非常崇敬。但相比较之下,他在这方面又有留给我们一些经验教训。谢晋的老师钟惦棐说过一句话:“时代有谢晋,而谢晋无时代。”我认为这句话胜过了汗牛充栋的谢晋研究著作。五六十年代造就谢晋拍出了《女篮五号》《红色娘子军》这样的爱国主义力作。七八十年代,改革开放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年代造就谢晋拍出了《天云山传奇》《牧马人》《芙蓉镇》。同样,“十年内乱”的时代,又误导谢晋无奈染指《春苗》,这是个阴谋电影,打走资派的。时代造就了他,他逃脱不了时代的局限。90年代之后,东西方文化八面来风,传进很多时髦的西方的理论,什么“开掘人性深度”,又不开掘健康的人性。他导演的一系列电影《清凉寺钟声》《女儿谷》《老人与狗》《最后的贵族》,打上了那段时代的印记。这样说完全不等于否定一个艺术家的成就。我认为 “时代有谢晋,而谢晋无时代”表现了一位卓有见识的电影理论家对一位成就斐然的导演艺术家的耿耿真情和殷殷厚望。希望我们的艺术家对时代有独到的审美发现和思想发现。
结 语
我赞成在坚守中华民族人文精神的时候有四个必须坚守。第一,坚守中华民族在创造能力上的特长。失掉这一条就失掉了我们的优势。例如,京剧作为中国戏曲文化的集中体现,表现了中国人在形象思维、追求意象、艺术审美上的优势。有一次一位领导同志问我于魁智能不能算艺术大家、京剧表演艺术家。我说目前还不能算,因为作为艺术表演大家也要有几个标志。作为京剧,首先,要宗流派、有承传。这个我们还差得很远。欧阳中石是大书法家、大哲学家,他是学 “奚派”奚啸伯的。欧阳中石说,“奚派”的戏他都会,会一百多出。现在叫得很红的青年演员,不管学哪派的,会二三十出、三四十出就不得了了,差得很远。其次,必须有他的受众群体,流派要流得下去。再次,要有代表剧目。梅先生当年早期有《洛神》《贵妃醉酒》,晚年有《穆桂英挂帅》。现在的青年演员都没有,比如于魁智,说他代表性剧目是《梅兰芳》,可是《梅兰芳》根本不能算,唱成京歌了,由于舞台的花哨,湮没和影响了京剧艺术本体的发挥。最后,是最重要的,必须有理论家抽象概括他的表演艺术体系,现在也没有。第二,坚守一个民族的心理素质。比如欣赏电影,中华民族有中华民族的电影鉴赏心理,如果全部改成好莱坞式的形式,恐怕是不行的。第三,坚守民族特有的审美思维方式。这个和创造力上的优势这一条有同也有异。第四,坚守民族文化系统中的根本概念不变。如果做到了这个,也就可以承认坚守了人文精神传统。北京大学的教授叶朗先生提出,在先进文化建设中两个底线不能丢:人文精神的底线和伦理道德的底线。坚守住这两个底线,尽量以优秀的作品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摆在我们面前的课题,①如何在多元、多变、多样的文化语境下增强马克思主义美学观、历史观的引领作用;②如何在快速增长的经济形势下加快发展文化事业、文化产业,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多样化文化需求;③如何抵制西方强势文化的渗透,保证在全球化语境下既充分借鉴外国优秀文化,又抵御西化、分化图谋;④如何在现代化高新技术、互联网的新时代条件下占领文化阵地;⑤归结起来就是在改革进程中,如何处理好继承与创新的关系,既符合精神文明建设规律,又符合市场规律的新的机制和运作方式。这样,我们的电影电视文化才能健康发展。电视剧因为太多,现在说起来很复杂。简单地说一个例子,我们现在铺天盖地地在引进韩国电视剧,这就需要人文分析。韩流其实是 “汉流”,韩国电视剧从人文内涵或者文化内涵来说就是一句话:中国儒家文化出口转内销。就跟我们 90年代的《渴望》表现得差不多。从艺术特征上来说也可以用一句话:人之常情的细节魅力。但是要注意,我们适度的引进既挤占了中国市场还引来了一个问题,韩国电视剧一般说来大多表现妯娌之间、姑嫂之间、父女之间、兄弟之间的情感,太多了,容易失去一种高远宏阔的视野,计较个人身边的小悲欢,拿小悲欢当大事件。韩国人是聪明而智慧的。韩国现在热播中国的电视剧《长征》。他们明白引进中国的儒家文化不仅要厚德载物,还要自强不息。《易经》上的两句话:“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他们知道既要有厚德载物那一面,还要有《长征》那种所向披靡、自强不息的东西。
Human ity Thinking on the Current Film and Television Creation
ZHONG Cheng-xiang
J904
A
1672-2795(2010)03-0001-10的。在特定的接收场里,如果信息具有新鲜性,和过去习惯的思维方式发生碰撞,就可能帮助听者调整思维方式,让其思维方式尽可能地转变到科学发展观的轨道上,使其辩证化、全面化,尽可能克服片面性。昨天中国书法家协会换届,几位大书法家和我说,练书法日积月累,从临帖开始,书法最后是比文化积累。但有一个质变点,常常有一段时间,突然他的书法发生了一个飞跃,这常常是因为他写字的思维方式得到了调整。所以人们常说知识是一辈子的事,是经过日积月累、长期学习逐步积累起来的。而智慧是高于知识的,是比知识更高一层面的东西。这种讲座就是寻找智慧的,而不是获取知识。通过思维方式的调整,使智慧见长。而一个人的智慧长了,思维方式科学化了,是一通百通的事情。陈云同志在 “四保临江”的时候身体就很坏,都是病,但是他活到了 91岁。陈云同志在毛主席身边常常建议全党学哲学,哲学是总开关、总阀门,一通百通。后来,他在小平同志身边又建议学哲学 (《邓小平文选》里面有)。陈云同志作为党的经济帅才,他经常有些见解是非常独到的。坐了冷板凳后,他回到家乡,或回到评弹最兴旺的地方。他听评弹不是简单的艺术享受,而是从中获取哲学智慧。听了评弹以后他说了一句话,“出书、出人、走正路”七个字。前几天我和姜昆探讨,说这几个字够你用一辈子的。他现在当中国曲艺家协会的分党组书记,如果把这七个字做好就算干好了。这就说明一个人调整思维方式的极端重要性。
2010-04-28
仲呈祥 (1946— ),男,四川成都人,中国文联副主席、书记处书记、研究员,国务院学位委员艺术评议组召集人,教育部艺术教育委员会常委,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兼职教授,中国传媒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南京师范大学、中国艺术研究院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影视艺术及评论研究。(北京 1000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