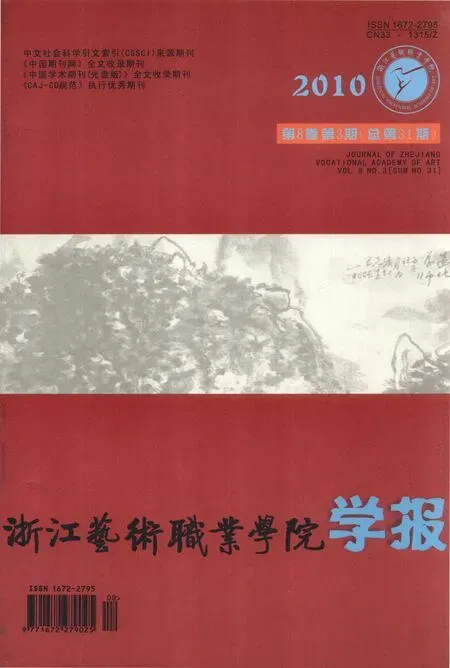论郑光祖《王粲登楼》中的 “双声言语”现象
张喜贵
论郑光祖《王粲登楼》中的 “双声言语”现象
张喜贵
杂剧《王粲登楼》是由魏晋时的王粲《登楼赋》演绎而来,一方面作者对此前的同一文体间的仿拟进行了改变,即由赋体改变为杂剧;另一方面又对原有的人物关系进行了整合,以更符合舞台上的演出及情节紧凑的要求。尤其是王粲这个人物的唱词中存在着“双声言语”的现象,既以历史人物王粲的口吻来代己抒情,又采用了角色转换的形式,把作者的体验加以间接化的方式来表达。郑光祖体验着代言带给他的愉悦,不好言说的情感借此得以表达。
郑光祖;《王粲登楼》;化妆抒情;双声言语
Abstract:Zheng Guangzu’szaju W ang Can Ascending the Buildingis based onWang Can’sOde of Ascending the Buildingof theWei and Jin dynasty.On the one hand,the playwright changed the previous imitation between the same styles i.e.changing from the style of ode tozaju.On the other hand,relations between the original characters were reorganized in order to better meet the requirements of stage performance and well-knit plot.Moreover,there is a phenomenon of“dual speech”in the singingwords of the character ofWang Can,with the tone of a historical figure to express emotion aswell as an indirect way to express the playwright’s experience by the change of role.Zheng Guangzu experienced the pleasure of representation and expressed special emotions.
Key words:Zheng Guangzu;W ang Can Ascending the Building;making up to express emotions;dual speech
《王粲登楼》是郑光祖创作的一出历史剧,杂剧作者之所以选择王粲的行为事迹进行重新演绎,是因为他要以历史人物王粲的生命来印证自我的生命。应当说对于对象的选择与认同,郑光祖是进行了一番选择的,他在众多的六朝诗人中选择了王仲宣。王粲当年避难荆州并作有 “魏晋之赋首”的《登楼赋》,赋中表现出的去国怀乡之感令相隔千年的郑光祖产生了强烈的共鸣。钱穆先生在《读文选》一文中说:“逮及建安,王仲宣《登楼赋》一出,而始格貌全新,体态异旧。此犹美人罢宴,卸冠佩,洗芳泽,轻装宜体,颦笑呈真。虽若典重有减,而实气韵生动……古人著述,六艺百家,途辙分明,存其胸怀间,其辞则仿扬马,其情则追孔老,固未能空所依傍,豁见己真也。王粲《登楼》则不然,即就目前之景色,直抒心中之存抱,非经非子,不老不孔,而粹然惟见其为文人之文焉。”[1]98王粲所处时代正是汉末大动乱的时代,到处哀鸿遍野,人民流离失所,“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郑光祖所处的时代也正值历史易代之际,二人真可谓是 “萧条异代不同时”。那么如何处理好史实与虚构的关系,是这部杂剧的成功与否的关键之处。为此杂剧对原本的历史文本进行了一系列的改变与虚构,全剧以拟王粲“双声言语”的口吻,把自己对象化为王粲,设身处地地体验王粲的经历和痛苦,既体验了当年王粲的困境,又抒发了自我当下的困惑,我们将此称作杂剧中的 “化妆抒情”现象。郑光祖不断地体味着原作者的情感和心理,将自己类似的遭遇及失志之悲在杂剧中加以表现。
一、《王粲登楼》对文体与历史事实的改变
郑光祖青少年时期经历了金亡、元蒙与南宋长期战争的时期,后半生来到江南亦是奔波于坎坷的仕途上,希望自己能够干出一番事业来,这一点与从少年起就经历了流亡体验的王粲极为相似。为了剧场演出及自我抒情的需要,郑光祖对《登楼赋》的文体与历史事实都进行了改变。
首先是文体的改变。《登楼赋》是以赋体来抒情,并且形成了一个源远流长的传统,模仿此赋的作家代不乏人,晋诗人陆云就曾以《登楼赋》为范本创作了《登台赋》,并在《与兄平原书》中说:“今送君苗《登台赋》,为佳手笔,云复更定复胜此,不知能愈之不?……视仲宣赋集,《初述征》《登楼》,前耶甚佳,其余平平,不得言情处,此贤文正自欲不茂,不审兄呼尔不?”还说:“登楼名高,恐未可越尔。”可见在《登楼赋》问世不久即有人加以仿作。魏晋时枣据亦有《登楼赋》,其模仿的痕迹也非常明显,其中有 “怀离客之远思,情惨悯而惆怅。登兹楼而逍遥,聊因高以遐望。感斯州之厥域,实帝王之旧疆。挹呼沱之浊河,怀通川之清漳。原隰开辟,荡臻夷薮。桑麻被野,黍稷盈亩。礼仪既度,民繁财阜。怀桑梓之旧爱,信古今之同情。钟仪惨而南音,庄舄感而越吟。情戚戚于下国,意乾乾于上京”,与王仲宣的《登楼赋》表达的情感极为相似。清人浦铣《复小斋赋话》中说:“王仲宣《登楼赋》,情真语至,使人读之泪下,文能动人如此。晋枣据亦有此赋,皆脱胎于粲。”[2]752此外,孙楚作有《登楼赋》、郭璞作有《登百尺楼赋》,这些都与王粲及《登楼赋》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对于这种现象,王玫先生如此加以评说:“《登楼赋》之所以有如此高的接受效应,与其表达思乡怀土的题旨显然极有关系,在中国赋史上可谓别开生面……《登楼赋》接受史给我们的启示是:艺术作品要获得长久的生命力,就必须揭示人类共有的心理感受。离家在外、思乡怀土,本是人生的一种普遍情怀。只要世间有别离,乡情就是永远表白不尽的主题。《登楼赋》无非以文学的形式写出世世代代人们的这种情感经历。它是世俗人生经验的艺术总结,其次在读者接受过程中,《登楼赋》已不单纯是一部文学作品,它的身上已凝结着历代读者的审美经验,随着时代推移,它也将作为一种艺术经验存留于我们民族心理深处。”[3]273-274可以说《登楼赋》已经成为一个标准的范本,许多文人都在用心地揣摩,亦步亦趋地加以模仿,以求得与其达到神似的目的。
郑光祖迥异于其他拟作的地方则在于他对《登楼赋》进行了大胆的文体转换,由向来以赋来抒情言志改变为以杂剧来抒情咏怀。也许这正符合王国维先生所说的 “盖文体通行既久,染指遂多,自成习套。豪杰之士,亦难于其中自出新意,故遁而作他体,以自解脱。一切文体所以始盛终衰者,皆由于此”[4]208。这也可以称之为另一种意义上的拟作,郑光祖在文体的转换中寻找到了一种更适于抒情言志的范式。从王粲的赋到郑光祖的杂剧的演变,正是中国文学从案头文学到舞台艺术的演进过程的缩影。郑光祖对王粲及其《登楼赋》进行了一系列的艺术创造,把历史的素材变成一种直觉的审美形式。艺术是人类感情的符号形式的创造,从《登楼赋》跃升为《王粲登楼》,这不是艺术的失误,而是艺术家的有意追求。于是我们发现了中国艺术长廊中的另一个王粲,我们未尝不可以说 “王粲登楼”已经是一个 “有意味的形式”,成为一个符号式的人物,也更具有了象征的功能。在一定程度上,作家是否擅长运用艺术符号,往往标志着其艺术本能的强弱。
其次是故事情节的改变。文体的改变自然会在创作观念上带来不小的转变。为了情节的紧凑与冲突的有效展开,故事情节的改变是必须的。历史上王粲的人生经历是什么样的呢?王粲 (177—217),字仲宣,山阳高平人。《三国志》有传,出身于高门望族,曾祖父王龚,祖父王畅,皆为汉代三公。父亲王谦为大将军何进长史。作为世胄家族的子弟,在汉末的大动乱中王粲并没有躲过一系列灾难的侵扰,184年,王粲 7岁时就经历了黄巾起义。从少年时代王粲就走上了流亡之路,张溥如此评说:“高平上胄,世为汉公,遭时流离,依徙荆许。以七哀之悲,为显庙之颂,择木而穷,雅诽见志。世谓其诗出李陵,今观书命,亦相近也。”[5]78初平元年 (190),遭遇董卓之乱,这一年洛阳被毁,董卓挟持汉献帝迁往长安,洛阳二百里内数百万人也被强行西迁,14岁的王粲就是由洛阳徙居长安的。蔡邕、曹植均为史有其人,二人与王粲亦有过交往,当年王粲从洛阳西迁长安,蔡邕热情相接。蔡邕倒忏屣相迎,王粲在长安见到了大名士蔡邕,“献帝西迁,粲徙长安,左中郎将蔡邕见而奇之,时邕才学显著,贵重朝廷,常车骑填巷,宾客盈坐。闻粲在门,倒屣迎之。粲至,年既幼弱,容状短小,一坐尽惊。邕曰:‘此王公孙也,有异才,吾不如也。吾家书籍文章,尽当与之’”[6]445。后来王粲又从长安逃难到荆州依附于刘表。
历史中的蔡邕与王粲本为忘年之交的好友,杂剧中蔡邕则成了王粲未来的岳父,同时又安排曹植出场,扮演翁婿之间的斡旋人物。历史中曹植与王粲亦有过交往,“建安七子”与 “三曹”共同成为建安诗风中的重要成员。在王粲去世之后,曹植在《王仲宣诔》中说:“君乃羁旅,离此阻艰。翕然凤举,远窜荆蛮。”而在杂剧中曹植则成了蔡邕与王粲之间的调和剂与见证人。历史人物中都实有其人,而组合在一起演绎的故事则具有了更多 “戏说”的成分。蔡邕为了“涵养他那锐气”,用尽各种方法使王粲承受羞辱与打击。杂剧中还有意地淡化了故事发生的背景,这样你既可以理解为汉末的王粲登楼,又可以理解为元代一介知识分子苦闷境遇下的登楼抒怀,这样的改变使全剧有了一个完整的故事。
为配合这一故事的框架,我们看到《王粲登楼》对王粲《登楼赋》以及王粲的身世经历都作了一番时空错综的处理。年龄上,史书中王粲入荆州时是 17岁,杂剧中则为 30岁;历史中的王粲父亲为王谦,为名公之胄,杂剧中则改为太常博士王默,与历史人物的地位相差甚远;历史中王粲的入长安是因为董卓之乱,杂剧中是蔡邕的屡次相约;历史中王粲入荆州是因为长安动乱,杂剧中则为曹植奉蔡邕之命告诉王粲赴荆州;历史上王粲登楼是在当阳,杂剧中把王粲登楼的地点由当阳移到了溪山风月楼;历史中由王粲独自登楼改为杂剧中与朋友许安道共同登楼;在当阳王粲是登楼作赋,杂剧中则是登楼作诗;此外还增加了店小二、蒯越、蔡瑁、许安道等人物,以推进故事的进展,形成一种戏剧的冲突。杂剧中还增加了登楼之时正是重阳佳节这一节日作为背景,于是才有许达设酒请王粲登高。秋天的季节给王粲抒发愁情提供了非常好的条件,他感叹道 “时遇秋天,好是伤感人也”,“一度愁来一倚楼,倚楼又是一番愁。西风塞雁添愁怨,衰草凄凄更暮秋。情默默,思悠悠,心头才了又眉头,倚楼望断平安信,不觉腮边泪自流”。王粲更多的是起到一个扮演者的作用,郑光祖正是以亦真亦假的王粲来承担起元代知识分子登楼所体验到的感受,经过这样的改动也许更符合元杂剧 “杂”的特点,元代胡祗遹《紫山大全集赠宋氏序》中说:“既谓之杂,上则朝廷君臣政治得失,下则闾里市井父子兄弟夫妇朋友之厚薄,以至医药卜筮释道商贾之人情物性,殊方异域风俗语言之不同,无一物不得其情,不穷其态。”[7]237杂剧内容与形式上的特点,都需要对历史题材加以重新组合。
二、《王粲登楼》中的 “双声言语”现象
郑光祖在《王粲登楼》中采用的是化妆抒情的写作手法,因为作者郑光祖与主人公王粲是 “有缘”而非 “同一”,他在舞台上直接呈现的是王粲的心声,于是诗人在抒情之时就进行了必要的化装,同时也进行了角色的转换,以利于元代文人生存境遇的显现。表面上看,作者是在代王粲立言,代王粲思乡,其实表达的是元代知识分子仕途坎坷的人生历程。郑光祖喜欢在杂剧中采用 “代言”的手法,既代人言心,也代己言心。代言的发生,通常是因为代言者被代言者的情事所感动,从而以他人的口吻表现彼此的思想和感情。元人剧作大多选择历史题材,有人统计,元杂剧中纯写爱情的只占 20%,而历史剧却占了 30%。著名的如关汉卿的《单刀会》、马致远的《汉宫秋》、高文秀的《黑旋风》等等,这说明元代杂剧作家不太敢于直抒胸臆,喜欢以历史题材来抒发自我的情怀,郑光祖的杂剧也是如此,王粲是那个时代流寓者的代名词,他无家可归,四处飘零,恰恰与元代知识分子的命运极其相似。元代是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他们把人分成蒙古、色目、汉人、南人四等,而且元代废除科举考试,知识分子无路可走,只好变身为 “书会才人”。《王粲登楼》是作者从纵向的视角对历史人物承先启后的接受过程,其中铭记着的是中国文学史上前后相继相承的行进轨迹。
首先,杂剧中一再提到王粲的傲气,蔡邕一再书信要调王粲入京,入京之后又一再拖延不见,相见之后又当着曹植之面几次羞辱,用蔡邕的话来说那就是要“涵养他那锐气”,也就是让他去掉身上的孤高之气。杂剧对王粲的傲气多有表现,“凭着我这高才和大手,稳情取谈笑觅封侯”,“贫贱亦可以骄人”。面对蔡邕见面酒的 “与”和 “不与”,王粲唱道 “男儿自有冲天志,不信书生一世贫”。对于这一点,杂剧先是通过王粲母亲之口说其 “胸襟骄傲,不肯曲脊于人”,后又通过蔡邕之口说 “只是矜骄傲慢,不肯曲脊于人”,此外还通过曹植之口进行反复渲染。这未尝不可以理解成是郑光祖自我的个性之体现。从钟嗣成《录鬼簿》中,我们知道他早年习儒为业,后来补授杭州路为吏,因而移民南方而居。他 “为人方直,不妄与人交,故诸公多鄙之”。就是说他并不善于与官场人物相交往,因此,官场诸公很瞧不起他,他的胸中块垒正好借王粲这个形象得以淋漓尽致地传达。
其次,是对功名富贵的向往,但现实中又怀才不遇。求取功名之难也是通过王粲之口屡次加以表达,“王粲也,人人都有那功名二字,惟有我的功名好难遇也呵”。而元代的民族歧视的政策使汉人知识分子的地位更为低下,所谓 “八娼、九儒、十丐”,汉人知识分子即使为官,也 “每每抑沉下僚,志不得伸”,“盖当时台省元臣,郡邑正官及雄要之职,中州人多不得为之”(《真珠船》)。其实历史上的王粲一直身体不好,“貌寝而体弱通脱”,并患有麻风病,故脾气暴躁,所以才有喜欢听驴叫的特殊癖好。但郑德辉将这一切都略去不表,只取其一端而演绎之。杂剧作家无意对历史人物加以真实的再现,而是将这个名字为己所用,故对历史上的王粲从多方面加以改版,从而成为杂剧中与历史中并不相同的另一个王粲。由于杂剧是在勾栏瓦舍演出,是一种通俗唱法,用观众最容易接受的方式表现出来。所以王粲的唱词多以 “纡徐绵邈,流丽婉转”的唱腔表达对社会弊端的发泄,更容易引发观众情感上的共鸣。郑光祖做过杭州路吏,这是个微不足道的小官,而且似乎一直也没有多大升迁,属于那种虽有才能但却不受当局重视,只能一生沉居下僚的知识分子。所以郑光祖愿意以恃才矜傲的王粲怀才不遇的故事,来抒发元代知识分子穷困抑郁的悲愤之情。
郑光祖在《双调蟾宫曲旅怀》中曾表达了作为一介小吏内心的种种愁怀,“弊裘尘土压征鞍,鞭倦袅芦花。弓箭萧萧,一竞入烟霞。动羁怀,西风禾黍,秋水蒹葭。千点万点,老树寒鸦。三行两行写高寒,呀呀雁落平沙。曲岸西边,近水涡鱼网纶竿钓槎。断桥东下傍溪沙,疏篱茅舍人家。见满山满谷,红叶黄花。正是凄凉时候,离人又在天涯!”满面尘土走天涯,这正是郑光祖仕宦生涯的形象写照,但从吏转官之路又是多么的渺茫,所以郑德辉一生始于路吏终于路吏。元朝取代宋朝这样的改朝换代带给知识分子的更多的是不愿接受但又无法改变的现实,他们的精神始终处于压抑的状态。他愿意仕元而为国家出力,但又升迁无望,空负一腔热血。于是他用王粲的故事为素材,用杂剧的形式来讽喻现实,抒发自己胸中的块垒。
此杂剧全名为《醉思乡王粲登楼》。之所以要采取用古人代言的方式,是因为郑德辉急于宣泄一种被压抑的心理情怀。《王粲登楼》既是模仿王粲《登楼赋》而作,那么其作者郑德辉就同时具有了《登楼赋》的 “读者”与《王粲登楼》的作者这样双重的身份。其中承载的是兼有原作者的思想,又要传达剧作者的思想。郑德辉设身处地感同身受体味王粲当外流落荆州的境遇。可以说郑德辉既要替王粲说话,也要替自己说话,从这个意义上说,杂剧《王粲登楼》也就具有了 “双声言语”的可能。“这个言语成为 ‘双声言语’,它替两个说话人服务,同时表达两种意图:说话者的直接意图和被折射出来的作者意图。这个言语中有两种声音、两种意义和感情。而这两种声音也同时有对话关系,它们仿佛彼此认识,……仿佛真正地彼此对话。双声言语总是有内在对话。”[8]68以人代己言心,是一种化装后的抒情。用王粲的口吻作代言。真切地展示了王粲复杂的内心世界。“代言体的秘密在于那个 ‘代’字,代言对象的内心隐秘是通过诗人的体验折射出来的,在体验的过程中难免有诗人的知识、才华、趣味的投影。”[9]感慨于文人的生存境地的困顿,借王粲之口而言之。如第三折:
【迎仙客】雕檐外红日低,画栋畔彩云飞。十二栏干、栏干在天外倚。我这里望中原,思故里,不由我感叹酸嘶,越搅的我这一片乡心碎。
【红绣鞋】泪眼盼秋水长天远际,归心似落霞孤鹜齐飞。则我这襄阳倦客苦思归。我这里凭栏望,母亲那里倚门悲。怎奈我身贫归未得。
【普天乐】楚天秋山叠翠,对无穷景色,总是伤悲。好教我动旅怀,难成醉,枉了也壮志如虹英雄辈,都做助江天景物凄其。气呵做了江风淅淅,愁呵做了江声沥沥,泪呵弹做了江雨霏霏。
【石榴花】现如今寒蛩唧唧向人啼。哎,知何日是归期?想当初只守着旧柴扉,不图甚的倒得便宜。则今山林钟鼎俱无味。命矣时兮,哎,可知道枉了我顶天立地居人世。老兄也,恰便似睡梦里过了三十。
年纪老大一事无成,只想着何日能够归去。何良俊在《曲论》中说:“王粲登楼第三折,摹写羁怀壮志,语多慷慨,而气亦爽烈。至后尧民歌,十二月,托物寓意,犹为妙绝。岂作脂弄粉语者,可得窥其堂庑哉。”[10]338其抒发的情感是羁旅愁怀,壮志未酬,如果再结合王粲在上场后的唱词 [中吕粉蝶儿]“尘满征衣,叹飘零一身客”,我们自然想到郑光祖本人的种种人生经历。
唐刘知己《史通模拟》“盖模拟之体,厥途有二:一曰貌同而心异,二曰貌异而心同”,“盖貌异而心同者,模拟之上也;貌同而心异者,模拟之下也”。[11]219郑光祖与王粲之间可以说是 “貌异而心同”,以历史人物王粲的口吻来代己抒情,用角色转换的形式,把作者的体验加以间接化地表达。郑德辉体验着代言带给他的快乐,不好言说的情感借此得以表达。他们共同体验着漂泊的感情。对文人生存境遇的反思。出于作者自我主观情绪的寻求表达,把自我的隐秘的心理体验借王粲的口宣泄出来。这与作者处在元代特定时代的生存境遇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这种代言式的写作手法存在着两个意义系统:一是杂剧中主人公王粲的处境与命运,一个是杂剧作者的处境命运和心理状态的系统。作者在为王粲代言,又借王粲为自己代言。在反复借代中潜隐着作者难言的苦衷。
[1]钱穆 .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 (卷三)[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4.
[2]王冠辑 .赋话广聚·四 [C].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6.
[3]王玫 .建安文学接受史 [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4]许文雨 .人间词话讲疏 [M].成都:成都古籍书店,1983.
[5]张溥 .汉魏六朝百三家集题辞注 [M].殷孟伦,注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6]陈寿 .三国志 .北京:中华书局,1999.
[7]羊列荣,刘明今 .中国历代文论选新编·宋金元卷 [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
[8]吕正惠 .文学的后设思考 [M].台北:正中书局,1991.
[9]杨义 .李白代言体诗的心理机制 [J].海南师范学院学报,2000(1).
[10]何良俊 .元明史料笔记丛刊 .四友斋丛说 [M].北京:中华书局,1959.
[11]刘知几 .史通通释 [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On“Dual Speech”in Zheng Guangzu’sW ang Can Ascending the Building
ZHANG Xi-gui
J805
A
1672-2795(2010)03-0011-05
2010-03-26
张喜贵 (1965— ),男,黑龙江拜泉人,江南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文学博士,主要从事六朝文学及中国诗学研究。(无锡 2141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