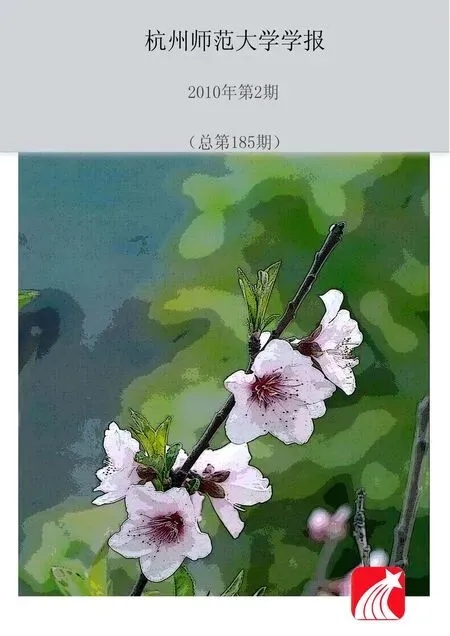“曹雪芹佚诗”案拾零
——以陈迩冬先生为中心
沈治钧
(北京语言大学 汉语学院,北京 100083)
文艺新论
“曹雪芹佚诗”案拾零
——以陈迩冬先生为中心
沈治钧
(北京语言大学 汉语学院,北京 100083)
32年前的初冬时节,陈方发表《“曹雪芹佚诗”辨伪》,揭开了一桩红学疑案的黑幕。近来获知陈方即陈迩冬与舒芜的化名,其中陈迩冬的诗词创作与红学随笔均颇见造诣。陈方的质疑集中在材料的来历问题上,一举击中了“曹雪芹佚诗”的要害,为查明事件真相作出了突出贡献。前些年又传出一首“陈迩冬佚诗”,其原始来历不无蹊跷。根据陈方所强调的辨伪原则,对这首结句为“商量脂砚到湘云”的剥皮诗,理应暂且存疑。
曹雪芹;陈方;曹雪芹佚诗;陈迩冬;舒芜
“曹雪芹佚诗”案已经过去三十来年了。此案曾经震惊海内外,1977年11月,署名陈方的学者率先站出来,在《南京师范学院学报》发表《“曹雪芹佚诗”辨伪》,揭开了疑案的黑幕。梅节两年后指出:“所谓‘疑案’,其实只是客气的说法。诗本来就是假的,‘疑案’不疑,应该叫做骗案。此案牵连到当今顶尖儿的几个红学专家,因此颇为轰动,有人称之为红学界的‘水门事件’。”[1]案子十分复杂,至今仍有不少细节有待揭示。这里扫叶拾零,只谈当年参与论战的一位重要人物——半个陈方,也就是陈迩冬。
一 陈迩冬的诗词创作与红学随笔
拙文《“聂绀弩赠诗”发疑》涉及此案,所以在写作中,逐渐萌生了查清陈方具体身份的愿望。经多方探询,终于获得了明确的答案——2009年7月28日,舒芜本名方管在病榻上确认,当年推出《“曹雪芹佚诗”辨伪》的陈方,就是他和陈迩冬的化名。
陈迩冬与舒芜都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古典部(二编室)的资深编辑,与冯雪峰、聂绀弩、张友鸾、王利器、周绍良、顾学颉、严敦易、李易及周汝昌等为同事,大家长期相处于同一间或相邻的办公室,低头不见抬头见。陈方不在“当今顶尖儿的几个红学专家”之列,却在“曹雪芹佚诗”案中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
陈迩冬(1913—1990),原名钟瑶,号蕴庵,广西桂林人。1937年毕业于广西大学文法学院,后加入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主编多种杂志或副刊,同时从事文学创作,先后出版短篇小说集《九纹龙》、新诗集《最初的失败》、历史剧《战台湾》、叙事诗《黑旗》与传记《李秀成传》等作品。1949年10月应聘为山西大学中文系教授,转而从事学术研究。1954年10月调人民文学出版社,任二编室诗词组组长,主要致力于古籍整理,有《苏轼诗选》《苏轼词选》《苏东坡诗词选》《史记选注》《韩愈诗选》及《宋词纵谈》《它山室诗话》等,其苏词选获钱钟书好评。[2]同时涉猎说部,曾校注《拍案惊奇》,审订《三国演义》,印行《闲话三分》,担任中国三国演义学会顾问。另有撰述《闲话水浒》的计划,因病未果。他一生喜好吟咏,有《十步廊韵语》传世。
陈迩冬与柳亚子为忘年交,志趣颇受影响。[3]陈氏诗词清雅隽逸,明丽奥峭,朋辈间有口皆碑。[4]与聂绀弩、舒芜、张友鸾等同事类似,陈迩冬对红学也有兴趣。1963年3月17日,他偕吴恩裕夫妇及吴世昌、周汝昌赴香山采风,访问了张永海老人,踏勘传说中的“雪芹旧居”。[5](PP.145-149)他的系列随笔《读红楼梦零札》散见于60至80年代北京《光明日报》、上海《文汇报》与香港《大公报》,以及《红楼梦研究集刊》,计有《高鹗引邓汉仪诗》《风干栗子》《葬花诗外记》《唐伯虎葬花》《海棠诗事》《关于贾宝玉出家》《秋爽斋中的疑迹》《李纨诗句与贾母谜语》《曹雪芹与孔继涑》《苏东坡与曹雪芹的观点》《一从二令三人木何解》等十余篇。这些学术随笔短小精悍,体现出了作者对《红楼梦》的谙熟与热爱。陈迩冬凭借着精通古典诗词的优势,在红学领域触手成春,其妙处不在《闲话三分》之下。
陈迩冬的这些红学随笔,很值得一读。例如他在《海棠诗事》中拈出,小说37回林黛玉的名句“偷来梨蕊三分白,借得梅花一缕魂”源自南宋卢钺(梅坡)的《雪梅》:“梅须逊雪三分白,雪却输梅一段香。”(《元遗山志》卷四)小说第五回《终身误》“空对着山中高士晶莹雪,终不忘世外仙姝寂寞林”来自青丘高启《梅花九首》其一:“雪掩山中高士卧,月明林下美人来。”(《高季迪先生大全集》卷一五)特别是高诗其四,措辞与意境跟《红楼梦》中的海棠诗非常相似,连用韵也是一样的。诗云:
淡淡霜华湿水痕,谁施绡帐护香温?诗随十里寻春路,愁去三更挂月村。飞去只忧云作伴,销来肯信玉为魂?一尊欲访罗浮客,落叶空山正掩门。
不言而喻,这些发现都是颇有意义的。[6]倘若不是同时熟稔古典诗词与《红楼梦》文本,则两者之间的微妙联系便不易察觉了。陈迩冬对诗学的造诣之深,对红学的留意之细,均可于此略见一斑。同时,这些学术随笔也表明,陈氏治学注重实证,不务空谈,言之有物,他的文章洋溢着浓郁的旧学气息。正如端木蕻良(曹京平)所说:“迩冬治学,旁搜冥求,常能在灯火阑珊处,蓦然发现出不寻常。但他决不大声张扬,却待读者去品味。他的文章耐人思索,但有时也会显得有些儿冷僻。”[7]
陈迩冬还有《大观园外竹枝词》16首,突出反映了他对《红楼梦》的浓厚兴趣,以及在红学方面的独到见解。
陈迩冬兼备诗词与红学这两方面的知识,则70年代后期出于学术义愤或一时技痒,而毅然投身于“曹雪芹佚诗”案的侦破与揭露,显非偶然。不难想象,“唾壶崩剥慨当慷,月荻江枫满画堂”云云,是瞒不过此老法眼的。
二 关于《“曹雪芹佚诗”辨伪》
《“曹雪芹佚诗”辨伪》的作者陈方就是陈迩冬和舒芜,如今大白于天下,知人论世,读者对他们的文章可有更深入的理解。陈方辨伪所针对的假诗其实是两首,即起句为“唾壶崩剥慨当慷”的七律,和起句为“爱此一拳石”的五律。后者可称《自题画石》诗案,以示区别,此处不作为重点。
陈方论文出现的学术背景值得注意。场韵七律“曹雪芹佚诗”于1971年12月26日由周汝昌致吴恩裕函传出,逐渐在学界内部引起骚动。至1974年底,吴世昌与徐恭时发表《新发现的曹雪芹佚诗》,造成了广为传播的局面,顿时轰动全国。1976年4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印行《红楼梦新证》增订本,录载全诗,并命名为《题松堂琵琶行传奇》,按语说:“按雪芹遗诗零落,仅存断句十四字。有拟补之者,去真远矣,附录于此,聊资想象。”[8]此举简直是在火上浇油。九年后,《新证》重印本则承认:“余曾试为拟补三篇,附录一首,聊资想象。”(1985年5月第2次印刷本)倘若一开始便如此坦白,也就风恬浪静,天下太平了。换言之,周汝昌在“文革”末期错过了最后一个澄清事实的最佳时机,《新证》所谓“有拟补之者,去真远矣”依然在刻意隐瞒真相,故作神秘,从而形成了推波助澜之势,不啻扬汤止沸,纵风止燎。事实上,在此之后,“曹雪芹佚诗”案非但没有沉寂下来,反而涌起了惊涛骇浪。
1970年秋,当陈迩冬和舒芜仍在湖北咸宁干校劳动改造的时候,他们的同事周汝昌已奉康生(一说江青)调遣先期回京,“曹雪芹佚诗”遂出笼了。一首假诗,由自己拟补,亲属欣赏,到传给朋友,散布学界,再到播扬全国,震惊海外,事态一步步恶化。当1976年春《新证》增订再版之际,作者居然录之载之,照旧不讲实话,蓄意蒙蔽读者,这标志着“曹雪芹佚诗”案的性质已经在根本上起了变化,至此正式演化成了学术造假事件。关于这一点,人文社二编室的同事林东海分析得比较透彻:
看来周先生把这补作视为得意之笔,想通过“新证”,以传诸久远。不过,这做法可就出格了,很难避开“作伪”之嫌。好比有人勾兑白酒,倘若请朋友尝尝,并无“造假”之嫌;如果拿到自己开的店铺去出售,则必定成为“打假”的对象。周先生把自己补作的所谓佚诗,和吴恩裕先生开开玩笑,自无“作伪”之嫌,而收入“新证”,从道理上说,就是在自己的店铺里卖假酒,岂是“原非作伪之意”
林东海与周汝昌私交甚笃,却也无法为其文过饰非,开脱责任。历史是残酷的,一失足成千古恨。即便以后从《新证》中删除“曹雪芹佚诗”,也已无法改变其作者曾经伪造史料的基本事实。不管出于何种动机,《新证》录载假诗本身都已构成了性质相当严重的学术不端。陈方的辨伪推出在《新证》增订本印行之后,其中自然存在着诸多客观条件的限制,有一点则不难看到,陈方在主观上显然已忍无可忍。
“文革”结束了,时机大体成熟,陈方便勇敢地站出来揭开了疑案的盖子。陈迩冬是“现行反革命”,舒芜是“摘帽右派”,当时都还没有平反,因而不能使用真名或常用笔名发表文章。[10]他们的批评对象包括周汝昌、吴恩裕、吴世昌——“当今顶尖儿的几个红学专家”,而且都是老熟人,使用化名倒更方便些。他们对《新证》处置“曹雪芹佚诗”的方式显然特别不满,遂用嘲讽的笔调写道:
周汝昌先生的话说得很妙:“有拟补之者”,究竟谁补?补即非真,又何所谓“去真”远不远?既是后人补作,又何必附录?既是“去真远矣”,又如何能够“聊资想象”?莫非是“想象”得“去真”愈远愈好。总之空灵缥缈,莫可究诘。*陈方《“曹雪芹佚诗”辨伪》,载《南京师范学院学报》1977年第4期。以下再引此文不另注。
陈方的态度很明朗,他们认为,《新证》根本就不该录载那首“曹雪芹佚诗”,除非同时说明真相,免得大家继续误会下去。在学术著作中运用“空灵缥缈”的言辞来忽悠读者,不够严肃,背离了治学的基本宗旨。
陈方没有具体剖析“曹雪芹佚诗”的字句,这是因为,他们觉得“根据片词只语,论定某诗非某古人写不出来,那压根儿是欺人之谈”,而且“诗的好不好本来就玄虚得很”。确实,诗词的优劣与真伪是两个逻辑层面上的概念,不能单凭优劣定真伪——尽管“思想、艺术、韵律、技巧未尝不能作为考辨材料真伪的根据”。从方法论上讲,这是无懈可击的。从治学经验上看,这确实是研究诗词的行家之见。陈方辨伪的重点不是别的,正是须要追根寻源的来历问题,一是一,二是二,使不得半点腾挪躲闪。他们指出:
考辨材料的真伪,有种种方法,而基本的一条,是必须首先弄清它的来历,这就是明人胡应麟所谓的“核之传者,以观其人”。两首“佚诗”究竟是真是假,只要查一查它们的来历就可以明白。
陈方所强调的这一辨伪原则,尤其适用于对当世新出的文献材料的考查。一般而言,新近出现的东西都是比较容易查明其来历的。如果怎么都无法查明,则其真实性便十分值得怀疑了。如果最初的当事人拒绝或无法提供可靠的来历证明,则必须存疑,直至其来历得以澄清为止。
陈方当然是有感而发的——“科学的态度是实事求是,但是有些人最害怕实事求是。例如要考察一个材料的真伪,寻究其来历,他们认为毫无意义。”陈方指的是吴徐,并援引了《新发现的曹雪芹佚诗》中的言论:“至于收藏者自己是否愿意公开,却与这诗本身的真实性完全是两回事,彼此可以毫不相关,则是常识范围内之事,不须多说。”*吴世昌、徐恭时《新发现的曹雪芹佚诗》,载南京师范学院《文教资料简报》1974年8、9月号增刊,转载于《哈尔滨师范学院学报》,1975年第1期。若依此言,则“连写文章引材料注明出处也纯属多余”了,陈方当然不能苟同,而是坚持认为“科学的态度容不得半点弄虚作假”,那种“师心自用的考证”必然是“自误误人”的。
要查明“曹雪芹佚诗”的确切来历,就必须敦促源头上的当事人讲出实情。因此,陈方着重强调:“问题的真相,有待于周汝昌先生出来澄清。”然而,周氏一直在拒绝澄清来历问题,五年多来始终闪烁其词,至《新证》的“空灵缥缈,莫可究诘”则登峰造极。于是他们大胆断言,这纯粹是一场“弄假成真”的“闹剧”,并严厉批评道:“在《红楼梦》研究领域中,炫耀所谓‘珍秘材料’的倾向,是和胡适派学风一脉相承的。某些似乎颇负盛名的《红楼梦》研究者,为了炫耀所谓‘珍秘材料’,甚至弄虚作假也在所不计。”联系下文对《新证》迷恋胡适口号的尖锐指责,读者不难明白,陈方的矛头所向,主要是他们身边的这个老同事。
陈方能够得出正确的辨伪结论,固然与他们深厚的诗词修养有关,与他们跟《新证》作者长期相处因而更加了解其品性有关,与他们的治学态度一贯严谨有关。但更为重要的是,他们掌握了正确的考据方法,采取了恰当的论证策略,即把核心注意力全部集中到了对“佚诗”来历的追根究底之上。陈方的论争对手吴世昌也是位唐宋诗词研究专家,只是偶尔看走了眼,随后固执己见,一意孤行,以致背水苦战,情理两失,懵懵懂懂落进了精心设计的学术陷阱。
陈方能够紧紧盯住来历问题,恐怕或多或少得力于他们近水楼台的区位优势。这首“曹雪芹佚诗”最初由本单位的同事传出去,熟人间的议论必定较多,他们也就更容易发觉马脚之所在,破绽之所由。陈方一再申明,“对这些材料持怀疑态度的,大有人在”,还说:“在这类‘新材料’甚嚣尘上的时候,广大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他们看得出真伪,辨得清是非。我们前面谈的,丝毫谈不上有什么创见。”都是些大实话。一年多以后的1979年春夏,张友鸾化名“宛平人”谈起了《曹雪芹佚诗疑案》,聂绀弩则发表了起句为“客不催租亦败吟”的七律,真是此呼彼应,捷于桴鼓。以聂为核心的陈、方、张本即挚友,此际俨然组成了人文社二编室内部的一个打假团队。至于1980年3月另一位同事王利器推出著名的《〈红楼梦新证〉证误》,同样不像是偶然的巧合。
对陈方进行猛烈反击的,还是吴世昌。尽管他的《曹雪芹佚诗的来源与真伪》依然在宣扬“来历不能定真伪”的偏激认识,但在陈方明确而坚定的辨伪主张的逼迫之下,吴文也不得不花费了大量的笔墨来探讨来历问题,于是披露了一则秘闻:1973年初,周汝昌在提供给《文物》的稿件《红楼梦与曹雪芹有关文物之叙录一束》中,曾经试图正式公布“佚诗”(本称“曹雪芹遗诗”)。吴世昌怒不可遏,严词质问:“他请吴恩裕先生交与《文物》准备发表的初稿第一个短篇竟是用六句‘伪诗’冒充雪芹遗诗,这是学术界的什么风气?……如果此诗确是‘伪’补,而周汝昌犹不惜冒险一试,其动机与目的,无非是外骗国际友人,内欺《文物》读者,以夸耀他是收藏曹雪芹文物‘遗’著的权威,试问将置国家信誉于何地?”吴世昌当然清楚——“如果此诗真是‘拟补’之作,而他竟要冒充雪芹‘遗诗’,发表于向国际发行的刊物上,那是犯罪的行为。”[11]吴文还公布了周汝昌致吴恩裕信函三通中的关键段落,让遮遮掩掩的造假过程更加清晰地显现了出来,因而当事人也便暴露在明亮的聚光灯下了。吴世昌的本意是论说“曹雪芹佚诗”的来历无可置疑,实际上他所提供的材料只能证明,它确乎是“来历欠明”的,疑云密布,疑窦丛生。陈方断定那是一出“弄假成真”的“闹剧”,完全正确。可惜吴世昌执迷不悟,一错再错,继续被耍弄了下去。吴氏此文的学术贡献在于,来历问题追查得越发细致、越发深入了,火药味十足的笔墨官司吸引了学界内外的强烈关注,使得造假者无处藏身,转眼间已面临着彻底败露的绝境。而这,正是陈方辨伪的冲击波所导致的必然结果。
显而易见,陈方的辨伪间接乃至直接促使了周汝昌于1979年5月发表《曹雪芹的手笔“能”假托吗?》,终于承认“佚诗”出诸己手,最后说:“有些同志来问它,我当时碍于某种原因,不欲说出原系自拟之作……今天既然将谜底揭出,我还是该向那些同志表示歉意。”[12]所谓“那些同志”,不晓得其中是否包括陈迩冬与舒芜。既然当时学界盛传陈方是人文社编辑,周氏当不难明了,老同事站出来发话了。对别人尚可装聋作哑,不理不睬,本单位的老同事知根知底,在光明正大的学术层面上,他们是断难忽视与敷衍的。况且,陈迩冬和舒芜的身后显然还站立着聂绀弩、张友鸾、周绍良、王利器、李易、顾学颉……不同于眼下乡愿得势,谀辞盛行,彼时举国拨乱反正,群情激愤,这股凛然的学术浩气,其压力之大,可想而知。关键是,追查的目标一旦锁定在来历二字上,造假者便无所遁其形了,势必要给出个交代,予以了断。一言以蔽之,陈方戳到了死穴上了。
三 关于“陈迩冬佚诗”
“陈迩冬佚诗”指新书《谁知脂砚是湘云》中所引的一首七绝,《天地人我》《周汝昌自传》等论著中均曾提及。诗云:
少年尊隐有高文,红学真堪张一军;难向史家搜比例,商量脂砚到湘云
这是盛赞1949年底周汝昌发表在《燕京学报》上的《真本石头记之脂砚斋评》在红学领域独树旗帜,成就非凡。周文的主要观点,就是曹雪芹的“新妇”脂砚斋即贾宝玉的“继配”史湘云。梅节曾经指出,和索隐派殊途同归的“龙门红学”以奇谲的想象(“悟”)为基础,特别善于编造耸人听闻的通俗故事。周氏此文乃“开山之作”——“它为‘龙门红学’开不二法门,现丈六金身,将之提升到学术层次。”[14]脂砚即湘云说后采入《新证》,作者自诩为“最得意、最精彩”的“考证”。“陈迩冬佚诗”夸奖“高文”《真本石头记之脂砚斋评》,实即颂扬《新证》。
因此《周汝昌自传》列举了赞同其说的五位名家,即顾随、张慧剑、陈迩冬、林语堂、李俍民。作者欣然写道:
第三位是陈迩冬,他在山西执教时,专程带领学生进京,对我说:此来有“二为”:一为专访聂绀弩,研《水浒》有专长;二为拜访你,特赞“脂砚——湘云说”,并云:“新近又出来一个‘舅舅说’,真煞风景,太讨厌,该打回去!”
后来他又“仿改”龚定庵诗见赠:(略)[15](P.181)
这里有陈迩冬厉声呵斥“舅舅说”的原话,对理解诗义有些帮助。“舅舅说”源自俞平伯,是1954年7月10日首次公开的。[16]据上引叙述,陈氏说那番话的时间比较明确,即当年7月中旬至9月下旬之间,时执教于山西大学中文系,《新证》作者则已从成都调动到了人文社二编室,成了聂绀弩的下属。
至于“见赠”此诗的时间,稍有些模糊。“后来”云云,当指1954年10月陈迩冬也调动到人文社之后。林语堂的《平心论高鹗》最初发表在台北《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29本下册,时间是1958年12月。《周汝昌自传》的叙述顺序似指陈氏以诗“见赠”于林著之前。换言之,当事人试图透露,“陈迩冬佚诗”产生于1954年秋至1958年冬之间。
周氏自传业已点明,“见赠”之诗乃陈迩冬“仿改”龚自珍《己亥杂诗》而成的。龚氏组诗共315首,“仿改”的是第241首。龚诗云:
少年尊隐有高文,猿鹤真堪张一军。难向史家搜比例,商量出处到红裙。(《定庵文集补》)
这是龚自珍以24岁左右所写的《尊隐》一文为自豪,还对自己的风流韵事感到骄傲。王国维对于此类淫丽邪僻的笔墨十分嫌恶,在《人间词话》中指责定庵道:“其人之凉薄无行,跃然纸墨间。”[17](P.52)
至于“难向史家搜比例,商量出处到红裙”云云,骄矜倨傲,恻艳轻狂,显然也是表现其“凉薄无行”的“儇薄语”。曾朴《孽海花》纵笔渲染龚自珍与《红楼梦影》作者顾太清之间的香艳绯闻,丁香花疑案亦播腾众口,聚讼纷纭,恐怕都不是空穴来风。[18]作为近代著名思想家和文学家,龚氏的总体成就自然是值得称道的,但他的情诗艳词彰显了人性的弱点与人生的污点,已经不是陶渊明《闲情》一赋那种白璧之微瑕了。
参照龚氏原诗,结合实际情况考察,这首“陈迩冬佚诗”不无可疑之处:(一)比拟不伦。把《新证》作者比作文史名家定庵公,却把脂砚斋和史湘云比作风尘女郎,未免乖张。(二)措辞不妥。二十多岁的龚不妨自称“少年”,但三十多岁的周已非“少年”,却颇喜自夸青春,如自传里说1955年“尔时我年方三十四岁”。[15](P.241)实则,他已虚岁三十八。(三)情况不类。同为“见赠”之什,聂讲“少年风骨仙乎仙”,陈讲“少年尊隐有高文”,过于巧合。同事中舒芜较年轻,比周小四岁,却未见聂陈称之为“少年”。(四)身份不对。陈阅历丰富,博学多才,不乏著述,与聂故交,原为教授,后任诗词组长,资历明显高过周,则其“见赠”之什当不至于那样轻佻。(五)口吻不合。陈长周五岁,虽属平辈,也不至于吹捧得那么肉麻。(六)为人不像。此诗的基础是陈周初会时的议论,陈迩冬跟俞平伯毫无芥蒂,居然斥责“舅舅说”道:“真煞风景,太讨厌,该打回去!”出言如此不逊,全无学者风度,令人讶异。同事林东海说陈“中和情性”,因而“和气致祥”,以及“颜色和蔼,平易近人”。[9](P.211)然则,他发语当不至于那样尖刻——尤其对于同样平和待人、同样精通诗词的长辈俞平伯。在1954年至1955年,周是批俞的急先锋,陈却是人文社二编室中没有撰文参与批俞的少数人之一。众所周知,周对俞始终衔怨于心,一遇机会便会发泄出来,其中最突出的事例莫过于“俞平伯匿书”案。[19](PP.198-238)如今借陈迩冬之口攻俞,恰似借顾随之口骂俞,实属意料之中的事情。
然而,上述理由均不足以证明“商量脂砚到湘云”非出陈手。值得欣慰的是,陈方所强调的考据原则依然具有不同寻常的指导意义,其最基本的一条是追查材料的原始来历,即胡应麟所谓“核之传者,以观其人”。事有凑巧,此“陈迩冬佚诗”恰恰就是来历欠明的。
目前公开出版的陈氏旧体诗集有三种——《陈迩冬诗文选》《十步廊韵语》和《陈迩冬诗词》,此诗均不见载。陈迩冬的其他著述也未道及。若说此诗原系“仿改”,属一时应景之作,不算独立创制,故未收入诗集,那是讲不通的。晚出的《陈迩冬诗词》[20]搜罗完备,编者尽可能尊重历史,即便是集句诗(如卷一《荃麟至出示鲁彦入殡时照因集鲁迅句致悼》)也予收录,以存其真,更别提“仿改”之作了。其《绝句四首》其四:“任凭人唱蔡中郎,历史舞台我退场。身后是非浑不管,已知正道是沧桑。”(卷三)此即“仿改”陆游《小舟游近村舍舟步归》:“斜阳古柳赵家庄,负鼓盲翁正作场。身后是非谁管得,满村听唱蔡中郎。”(《剑南诗稿》卷三三)陈诗最后一句“仿改”毛泽东名句“人间正道是沧桑”,转为满腹牢骚。“仿改”名篇属拟古杂诗的一种,叫戏仿诗或套改诗,俗称剥皮诗。若运用得当,此类杂诗可以达到神奇的艺术效果,脱胎换骨,推陈出新,有似独创。再如其《东坡赤壁之什》:“大江东去浪淘沙,千古风流人物赊。故垒西边留赤壁,山川如画夕阳斜。”(卷四)准此,假设结句为“商量脂砚到湘云”的剥皮诗不伪,则不至于被排除在陈氏诗集之外。
陈迩冬的诗词并非全部皆属精品,其中也有不少趋时之作,带有鲜明的时代烙印,但都公示在读者面前了。如《除夕吟》,全篇标语口号连缀而成,今天读起来真有些哭笑不得,不知道如此不高明的东西何以出自迩冬之手。[21]作为五言古风,《除夕吟》是非常“不高明的东西”,本来是应该藏拙的,《陈迩冬诗词》偏偏照原样印了出来,公开展览,有似游街示众。看来此书的编辑原则是存真,故有诗必录,不计高下工拙。
由此可知,倘若那首结句为“商量脂砚到湘云”的剥皮诗确属真品,即便很不高明,《陈迩冬诗词》也定会收录的。如今的情况却是,它在陈氏的三种诗集里均不见踪影。况且此诗披露于陈迩冬身后十来年,早已无法对证,又不晓得有没有健在的现场目击者、旁证知情人或真实完好的作者手迹原件,审辨实属不易。本着科学慎重的理性原则,也为了促使当事人及知情人提供可靠的凭据,对它只得暂且存疑。
2009年7月7日下午,我前往位于京城东北郊的西坝河,专程拜访陈迩冬的大女婿郭隽杰。此行的目的包括调查陈方的具体身份,及此“陈迩冬佚诗”的真伪。郭教授早已退休,曾与岳父合作校注《拍案惊奇》,后参与整理《聂绀弩诗全编》,也是《陈迩冬诗词》的责任编辑。关于陈方是谁,郭教授表示不清楚,但针对《陈方酬唱记事》则提示应问舒芜——“看看方先生愿不愿意承认”。关于那首剥皮诗,他坦言从未见过,并谈到迩冬先生认识俞平伯,很敬重他,二人关系融洽。《十步廊韵语》所在的《倾盖集》(福建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就是由俞先生题签的。郭教授强调,如果周汝昌认为这个“商量脂砚到湘云”是迩冬先生“见赠”的诗,他就应该出示手迹。
毕竟是陈迩冬的亲属,几句话便归到了来历问题上。请求出示手迹,即首先追究材料的原始来历。无论辨伪还是认真,这都是最基本的着眼点。切盼当事人能够尊重陈家子女的愿望——他们当然期待不断发现陈迩冬的佚作,像《西江月·咏中秋》那样来历明确的作品,愈多愈好。*按《西江月·咏中秋》一阕不见于《陈迩冬诗词》,原载1946年9月10日《新民晚报》副刊,署名皇甫鼎,即陈迩冬的常用笔名。参看何开粹《陈迩冬与陈开瑞的交往》,《中共桂林市委党校学报》,2002年第3期。此词来历明确,署名有据,当属可信。但愿结句为“商量脂砚到湘云”的剥皮诗也是千真万确、如假包换的,一旦获得最终证实,则无论对于陈迩冬研究还是红学史研究,都将是一份不可多得的珍贵史料。
附记:此稿草讫于己丑季夏,为慎重起见,初秋寄呈郭隽杰审阅。得蒙不弃,予以首肯。郭教授曾就陈方之谜、“曹雪芹佚诗”及“陈迩冬佚诗”诸事指点迷津,复慷慨馈赠《陈迩冬诗词》等文献材料,在此谨申谢悃。2009年9月7日岁次己丑白露记于京郊。
[1]梅节.曹雪芹“佚诗”的真伪问题[J].(香港)七十年代,1979,(6).
[2]施亮.诗词名家陈迩冬[N].文汇报,2009-03-02.
[3]陈迩冬.一代风骚——谈柳亚子诗事以纪念先生百年诞辰[N].人民日报:副刊,1987-05-28.
[4]程千帆.读《倾盖集》所见[J].读书,1985,(11).
[5]吴恩裕.曹雪芹丛考[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6]陈迩冬.海棠诗事——读红楼梦零札[N].文汇报:副刊,1962-06-24.
[7]端木蕻良.外行话三分[M]//陈迩冬.闲话三分.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7.
[8]周汝昌.红楼梦新证:增订本[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6.
[9]林东海.师友风谊[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
[10]舒芜.人海波涛共几回——哭诗人陈迩冬[J].新文学史料,1991,(4).
[11]吴世昌.曹雪芹佚诗的来源与真伪[J].徐州师范学院学报,1978,(4).
[12]周汝昌.曹雪芹的手笔“能”假托吗?[J].教学与进修,1979,(2).
[13]周汝昌.谁知脂砚是湘云[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
[14]梅节.说“龙门红学”——关于现代红学的断想[J].红楼梦学刊,1997,(4).
[15]周汝昌.红楼无限情:周汝昌自传[M].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5.
[16]俞平伯.辑录脂砚斋本红楼梦评注的经过[N].光明日报:文学遗产副刊,1954-07-10.
[17]徐调孚.校注人间词话[M].北京:中华书局,2003.
[18]苏雪林.丁香花疑案再辩[J].文哲季刊,1931,1(3-4).
[19]苗怀明.哪儿来的恩恩怨怨——俞平伯、周汝昌关系考辨[M]//风起红楼.北京:中华书局,2006.
[20]陈迩冬.陈迩冬诗词[M].澳门:学人出版社,2006.
[21]舒芜.陈迩冬诗词[N].文汇报:笔会副刊,2007-04-13.
(责任编辑:朱晓江)
On“CaoXueqin’sLostPoem”
SHEN Zhi-jun
(College of Chinese Languages Studies, Beijing Language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3, China)
It was in the winter more than thirty years ago that Chen Fang published the paper titledOntheFalsityof“CaoXueqin’sLostPoem”. The paper disclosed a doubtful case in Dream of Red Chamber studies. Recently, I have been informed that Chen Fang was an anonym for Chen Erdong and Shu Wu. Chen Erdong was an accomplished poet and had written good essays on Dream of Red Chamber studies. He doubted about the source of the poems, which was directly pointed out the core issue concerning “Cao Xueqin’s Lost Poem”, and made an outstanding contribution to finding out the truth. Several years ago, there appeared a “Chen Erdong’s lost poem”, whose doubtful origin was also to be further consulted. According to his principle of distinguishing the false, the last line of the poem also should be questioned.
Cao Xueqin; Chen Fang; Cao Xueqin’s Lost Poem; Chen Erdong; Shu Wu
2009-12-02
沈治钧(1960-),男,河北广平人,文学博士,北京语言大学汉语学院教授。
I207.411
A
1674-2338(2010)02-0109-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