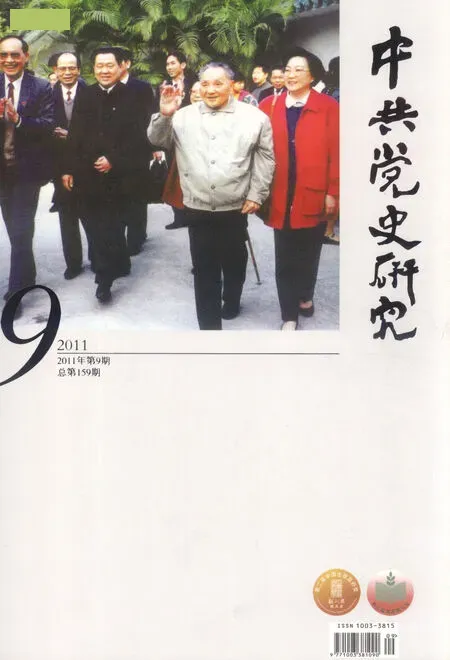党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第一次“左”倾错误的再考察
黄 琨
对于党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第一次“左”倾错误的研究已有很多①其中,系统、深入的研究是金冲及在《党的文献》2000年第2期上发表的《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时期三次“左”倾错误的比较研究》一文。他将几次“左”倾错误的发展过程贯通起来,从总体上进行考察和比较,揭示了“左”倾错误思想在党内产生的原因以及它们各自具有的特点。,但大多数的研究都是从中共中央和省委、特委之间来往的文件入手,关注的是各地的革命计划和影响较大的革命事件,这种视角固然在某种层面上对党内“左”倾盲动思想有所揭示,但不能回避的问题是,中央及省委的政策能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下级党组织?是不是能将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党组织视为一个思想、意识都非常统一的整体?事实是,如果我们对这一时期的中央和地方党组织的文件进行细致的比照,会发现其中有很多矛盾之处,并且实际的革命活动有很多也没有按照预定的计划进行。那么,各地党组织缘何会“违背”中央政策?实际的革命面貌又是怎样?这一系列问题都提示我们对第一次“左”倾错误的研究尚有很大的空间。
一、中共中央政策的传达
中共中央政策能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到下级党组织?这是在我们以往的研究中往往被忽略掉的一个问题。而与此相关有两个问题:一是党的各级组织之间的联络,二是党的下级组织对上级意图的准确把握。
在国民党的血腥屠杀下,很多中共组织被打散了,要重新建立起来非常困难(当时中共的领导机关多建在城市),所以在1927年底到1928年初的一段时间里,各地党组织之间出现关系断绝的情况并不少见。中共湖北省委的一位负责同志反映:“许多地委没有接到头。许多县委没有来函,如广水等。能与省委直接发生关系的不过几县,鄂东、江北等及好多特委统无关系。”①《湖北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省委文件)》(1926—1927年),中央档案馆、湖北省档案馆1983年12月合作编印(内部发行资料),第370页。上级组织在为失去联络而着急时,下级组织也为难以接头而抱怨。中共平江县委就曾在报告中对中共湖南省委抱怨说:“各县来省接头总比见皇帝还要难些,甚至于找上数天,囊中用尽了,空空而返”②《平江报告》(1927年9、10月间),湖南省档案馆藏,档案号96-1-18。。
一方面是在白色恐怖下中共的机关重建非常困难;另一方面,由于党组织内部的不纯洁,以及缺乏秘密工作的经验等原因,经常出现机关被破坏的情况。中共湖北省委在1928年3月、5月均遭到极大地破坏,11月又遭到大破坏,期间曾被迫迁到九江。下级党组织更时常面临被打散的危险。
各级党组织间没有正常的联络,就难以形成畅通的信息管道。在紧急关头召开的八七会议,为处在思想混乱和组织涣散的党指明了出路。但它在下级党组织中的传达和影响力又如何呢?以会议召开地湖北省的党组织为例:
1927年10月,汉口第二区区委在给湖北省委的信中疾呼:“可是时间已过两月,(八七)紧急会议的决议已有变更(对国民党左派与苏维埃),而近在咫尺的武汉干部同志,竟有许多不曾看见、不曾听到(外县同志当然是更不消说得!)。”③《湖北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省委文件)》(1926—1927年),第105页。
11月,省委的一位负责同志在一次谈话中提出:“不但‘八七’之决议末达到群众中,甚至干部分子统未看到《中央通讯》及党报。因此‘八七’开一种党之新生命,可惜并末达入群众中,武汉之下级党部尚听到一些,但外县党部一点都不知,甚至说省委不与他们发生关系。”④《湖北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省委文件)》(1926—1927年),第370页。
12月,省委一位巡视员在对下级党组织巡视后所写的报告中说:“鄂中同志们对党的策略是莫明其妙,除特委少数负责同志及汉川县委书记外,连‘八七’会议的名称都还未听到。政治观点可说是等于零,不但不知道南京有特别委员会之一幕,就是武汉的唐退,程、胡、李来都不知道,土地革命及政治的宣传,不但是没有深入群众,而且没有入到党内。”⑤《湖北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省委文件)》(1926—1927年),第399页。
在时隔两个多月后,连“近在咫尺”的汉口区委的同志都没有看到八七会议决议。时隔近四个月,除少数负责同志外,鄂中的同志连八七会议的名称都没有听说过。由此可见,在当时极端白色恐怖的条件下,中央政策是很难及时、有效地得以传达。当然,由于湖北省处在国民党统治严密的地区,这种情况可能不具代表性。但从其他省份来看,会议精神即使是在九十月份得以在省委层面传达,要到达县级党组织,也要更晚一些了。
造成政策传达不畅还有其他方面的原因。据1928年1月中共福建省委对发行工作的报告称,有些县委在接到文件后将其藏在箱子里,不仅不往下传达,甚至有的连县委委员都没有看到。报告中还反映了发行的技术问题:由于未在通告中写明号数和页数,文件的发送常常出现发不完全或漏发的情况;印刷设备和手段的欠缺在各地更是普遍存在。省委慨叹的“印刷技术不好,常有洗不出、看不清楚”①《福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省委文件)》(1927—1928年)(上),中央档案馆、福建省档案馆1983年11月合作编印(内部发行资料),第87页。的情况还算不错的,许多县级党组织连最基本的印刷设备都没有。
一些地方党组织即使能够接到文件,由于缺乏理论训练,在把握中央意图的准确性上也存在问题。中共福建省委巡视员在平和县发现,由于“从永定间接的传来的消息说,全国六次大会决定停止全国总暴动,一切斗争,要停止,要秘密,我们现在只要准备将来的总暴动”,于是,平和县的有些同志甚至连农民的抗租运动都要求停止②《福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省委文件)》(1928年)(下),中央档案馆、福建省档案馆1984年7月合作编印(内部发行资料),第365—366页。。省委最迟在1928年10月接到中共六大精神,此时已到12月,但平和县党组织对六大决议仍存误解。平和及永定县都是党在福建省发展的重点和基础较好的区域,至于那些因人才缺乏而省委无暇顾及的区域,这种对中央政策的误读情况更是可想而知。
所以,我们不能将现在对中央文件的解读等同于当时的各级党组织,并忽视它所能传播和影响的范围。一份1929年9月关于鄂东区的报告显示了这样的内容:“同志一般政治水平线非常低落,下级同志只知道打土豪劣绅、打清乡团、土匪军队就是革命,尤其到红军赤卫队托枪是革命,对于党的根本任务、政治主张都不知道,就是区委、县委中许多同志也不知道了解。”③《湖北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特委文件)》(1927—1934年)(一),中央档案馆、湖北省档案馆1984年合作编印(内部发行资料),第101页。这对我们研究这段党史作了一个重要的提醒。
翻阅当时的史料,各级党组织间关系断绝、对中央政策把握不准的情况并不少见,这提示我们在研究中应注意各级党组织在革命思维上的多歧性。还有如何对当时的文本进行解读的问题。在试图直接从中央文件中获得关于某个问题的答案时,要慎之又慎。
以建立苏维埃组织的问题为例。对于暴动后能否立即建立苏维埃组织的问题,中央文件是冷静而富有理性的。中央一再强调,当暴动“在一定范围的区域内得胜并有固守的可能”,苏维埃组织才能建立。但中央也指出,苏维埃组织的建立“更不能借口于军事尚未了解,基础尚未稳固,而延迟推宕”。④《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第460页。从语言逻辑上看,中央是既反对过于急躁也反对过于拖沓。但各地党组织好像无视中央的要求,暴动后立即要求建立苏维埃组织的心态跃然纸上。1928年7月10日,中共福建临时省委给闽西特委发出指示信:“一乡完全占领后,即应召集全乡群众代表大会选举一乡苏维埃,一区、一县或数县完全占领时亦如之。万万不可等待,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号召广大的群众,保障暴动的胜利。”⑤《福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省委文件)》(1928年)(下),第46页。苏维埃组织既然“不能在胜利绝未巩固之时开始”,难道是下级党组织没有收到或是误解了中央的指示?答案当然是否定的。这是中央在1927年11月政治局扩大会议的一个决议案中提出来的,在中央下发的其他文件中也多次提到这个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各地党组织的指导机关(至少省级的党组织)不可能不会收到;再者,中央的表达也没有可供误解之处,这段极具辩证色彩的论述是在同一文件中被集中表述的。
问题出在中共中央随后的论述上。暴动之后怎样才算基础稳固?这是一个很难实际把握的问题。再者,当时党对革命形势有乐观的判断,如果不在暴动后立即建立苏维埃组织,将要面临机会主义的指责。所以,暴动后急于建立苏维埃组织的现象就不可避免了。中共江西省委提出,暴动后要立即成立县工农苏维埃及各乡农民苏维埃⑥《江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27—1928年),中央档案馆、江西省档案馆1986年10月合作编印(内部发行资料),第165页。。中共广东省委在给琼崖特委的信中也是如此:“一乡暴动起来了,便成立乡苏维埃,一区暴动起来了,便成立区苏维埃,有三区暴动起来了,便可以成立县苏维埃”①《广东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省委文件)》(1928年)(一),中央档案馆、广东省档案馆1982年11月合作编印(内部发行资料),第116页。。它们在提出建立苏维埃组织时,都没有将暴动后的形势如何作为建立苏维埃组织的逻辑前提。
地方党组织的表述与中央精神之间出现逻辑背离,或者说地方党组织的行为与中央精神出现偏差的情况发生在很多问题上,如果只是在文本中进行字义的处理,将会有失偏颇。所以,在对文本进行逻辑清理时,不能忽视由更上层的问题所引起的在行为逻辑上的变化,由此而导致一种“新”逻辑的产生。在攻打城市的问题上也是如此。在中央文件中可以经常见到关于不要急于攻打城市的指示,但各地攻打城市的计划和行动并没有受到原则上的批评。那么,怎样分析中央在攻打城市问题上所持的态度?首先要将这个问题放到中央对革命形势的判断和暴动道路的认识等更高级次的问题中去。在刚走上暴动道路之初,鉴于力量仍很薄弱,中央只是对原来基础较好的两湖和广东地区寄予了很高的期望。所以,此时中央提出攻打城市确须慎重,在地区间的要求也有所不同。1927年11月政治局扩大会议后,由于一套系统的理论已经形成,情况就发生了变化:要走城乡武装暴动的道路,城市又必须是割据的中心,攻打城市是理所当然的暴动内容;况且,在“直接革命形势”下很快就会汇成总暴动的局面,暴动当然可以一开始就攻打城市。所以,必须认识到的是,虽然在两个阶段中央都有不要急于攻打城市的指示,但由于有关革命的理论发生了变化,这一问题的逻辑在无形中也发生了变化。
如果将中央文本中的论述称为有关某个问题的“显性逻辑”,那么在将这个问题放到更高级次的问题中时它所发生的逻辑变化,可以称之为“隐性逻辑”。上面说的地方党组织与中央在某个问题的表述上出现的“逻辑背离”,其实是在显性逻辑上的背离,在隐性逻辑上他们还是一致的。很多情况下暴动中的行为是按照隐性逻辑行事。并且,在有关这一问题的专门论述之外,或者说是在对更高级次的问题作出安排时,这种隐性逻辑的存在有时体现得更为明显。各地省委、特委强行命令攻打城市和对一些下级党组织没有攻打城市的“怕死”、“机会主义”的批评,就是在攻打城市问题上的一个隐性逻辑存在。有时在隐性逻辑的影响下,关于某个问题的论述在文本中会出现矛盾的表述。中央认为游击战是“势力不能攻打城市”时的方法,但它又指出游击战的内容也包括攻袭城市,尤其是小县城,即因如此。
二、城市中心论
两湖地区是暴动的中心区域。在两湖暴动计划中,很明显地体现了党以城市、地域所具有的政治、军事意义来进行暴动安排的思想。湖南暴动分为三大区:第一区以夺取衡阳而攻长沙,第二区以长沙为中心作准备,第三区以夺取常德为长沙声援,最终要形成各路会攻长沙的局面②《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册,第364—365页。。除了省会长沙作为暴动的最终目标,各区都是以传统的、有影响力的城市作为暴动的中心。与湖南不同,湖北则体现了对地域的重视。湖北暴动计划以鄂南为中心,鄂西、鄂中相配合而最终“威吓武汉”。为何以鄂南为中心?中共湖北省委对此作过解释:“鄂南区在政治上既可以直接影响武汉,在地理上断绝武长路的交通及电邮,又可以造成湖南军队与政治的恐慌,而大有利于湖南的农民暴动,所以省委决定湖北的暴动,以鄂南区为中心”③《湖北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省委文件)》(1926—1927年),第132—133页。。以鄂南为中心其意在武汉和处在交通重要位置的城市,从这一点来看,湖南与湖北并无原则差异。中共湖北省委在鄂南农暴计划中要求,“开始之第一日即须攻破蒲、咸二城,然后在政治上可以号召鄂南的农民,创成整个的鄂南的暴动局面”①《湖北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省委文件)》(1926—1927年),第49页。。以占领城市来扩大暴动的影响,希望以此来创造更大的暴动局面,这是占领城市的主要意图。
在敌我双方军事力量相差很大的情况下去强行攻打敌对势力盘踞中心的城市,其后果显而易见。现今我们对这段历史存有误解的是,认为党忽略了暴动的现实条件,将攻打城市作为暴动的唯一目的。其实,从当时中央给地方的指示中不难发现,中央要各地“积极组织”但并非一味地蛮干。它提出各地要量力而行制订暴动的计划,力量薄弱时,应从乡村杀土豪开始,并非不顾自身力量的强弱,一上来就要攻打城市。比如,在制定湘鄂赣粤四省秋暴战略时,中央提出:“除夺取乡村政权之外,于可能的范围应夺取县政权,联合城市工人贫民(小商人)组织革命委员会,使成为当地的革命中心”②《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册,第241页。。虽然从中不难看出中央有急于求成和城市中心观的思想,但暴动要从乡村到城市的战略却也清晰可见,“于可能的范围”也说明中央认为暴动的计划要量力而行。
一些地方党组织在攻打城市的问题上同样慎重。中共广东省委认为乡村暴动后,要先肃清地主绅士,没收土地,鼓起更广大的群众,然后才可以去攻城③参见《广东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省委文件)》(1927年),中央档案馆、广东省档案馆1982年10月编印(内部发行资料),第140页。。它对有些地区未集中力量就攻城的行为作出了批评。中共江西省委在制订秋收暴动计划时,针对各地农运状况的差异,提出不同的暴动目标和计划,并要求在过去农运略有基础或有会匪的县份,不能如农军势力统治或有相当力量的县份作夺取县政权的总暴动④参见《江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27—1928年),第23—24页。。
那么,一个明显存在的矛盾是:中共为何又不顾实力地提出了两湖暴动计划?两湖暴动计划及其实施是我们对这一时期中共的活动进行判断的主要依据。其实,在对两湖暴动进行分析时,我们还应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在两湖之外的地区,党采取了怎样的暴动方式?当我们发现急于暴动,急于攻占城市的举动多是集中在两湖区域时,就不能不对以往的判断产生怀疑。
事实上,在1927年11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精神传达下去以前,在两湖以外的地区,农民暴动多是打杀土豪之类的乡村暴动,攻打城市的举措屈指可数。检视这些省委的暴动计划,并无攻打城市的要求,恰相反,都是些杀土豪、夺取乡村政权的暴动安排。中共江西省委的秋收暴动计划似乎能说明问题。它认为:“江西农运过去无坚实的基础,而且发展未能普遍各县,所以只能部分的零碎的暴动,决不能实现全省总的大规模的暴动”⑤《江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27—1928年),第19页。。若是一味地强调攻打城市,这个“零碎”的秋收暴动计划就不可能出台,也不会得到中央的认可。
两湖暴动的计划和实施,与中央及两湖省委对当时两湖革命形势的过高估计有关。中共湖南省委认为,湖南的秋收暴动“在客观环境上现在确是到了一个很好的时机”,所以在给中央的报告中提出“决定以长沙暴动为起点,湘南、湘西等亦同时暴动,坚决地夺取整个的湖南”⑥《湖南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省委文件)》(1927年),中央档案馆、湖南省档案馆1984年4月合作编印(内部发行资料),第113页。。两湖暴动计划决议案也认为:“目前两湖的社会政治经济情形,纯是一个暴动的局面”,“两湖的暴动尚未开始,在时间上已经是失败”⑦《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册,第363页。。由于大革命时期党在两湖地区有很好的群众基础,马日事变后,党又在这两省组织了农军对抗,所以有较强的农民武装。这可能是两湖省委提出过高的暴动计划以及中央对这两省寄予很高期望的重要原因。正是对两湖革命形势有过高估计,才会出现会攻长沙、威吓武汉的计划,正因如此,这种急于夺取全省政权的行动只是在两湖地区谋划与施行。
对革命形势产生错误判断的原因是多重的,但在中央及两湖省委制订暴动计划时,却认为是稳妥的、可行的。若从全国范围来考察此时的中共暴动,“急于攻占城市”并不是一种确切的表述。
当然,“不要过早进攻城市”并不是对城市中心思想的改变。城市仍是割据的中心并要努力创造进攻城市的局面。在中央和地方党组织的计划中,当力量许可时要毫不犹豫地夺取城市。正如中共湖南省委所言:“在我们的力量可以攻城或占据某几县,必须坚决的实行”①《湖南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省委文件)》(1927年),第248页。,“在乡村开始暴动,须立刻夺取市镇,在市镇开始暴动,须立刻夺取县城,不进攻就会失败”②《湖南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省委文件)》(1927年),第318页。。
没有急于攻打城市也不是不具城市中心观念。当江西万安县开始打土豪的斗争后,“攻下万安城,铲除反动堡垒成为广大农民群众的呼声”,夺取万安城,建立工农政权包括在万安县委一开始就拟定的暴动计划之内③《江西党史资料》(第5辑,万安暴动专辑),中共江西省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中共江西省委党史研究室1988年1月编印(内部发行资料),第141—142页。。对于地方党组织来说,乡村暴动之后要力图攻占城市是确定的、无异议的暴动道路。因此不难理解,即使上级党组织没有攻打城市的具体指示,一些下级组织在自认形势许可的情况下,也有自主攻打城市的举动。江西星子县、万安县、广东海陆丰的农军都曾攻下县城,但都不是在上级党组织的计划下被迫进行的。对于那些在乡村斗争中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功,具备了一定基础的地区,很难断言他们攻打城市的举措是出于中央或上级的指示,有力量就要占领城市在他们而言是再正常不过的了。
有些则是在农民的要求下攻打城市的。当乡村暴动发起后,在一些地方造成严重的城乡赤白对立。城市是经济生活的中心,乡村对其有严重的依赖性。永定的附城变成割据区域后,城内与附城的交通无形中被断绝,各乡就发生经济恐慌,“因在这青黄不接时期,各农民多靠卖柴炭、借债生活。那时大地主不肯借债,柴炭又不敢担进城里卖,无论大小,甚至自耕农所有银钱米谷,俱几乎净。”在经济压力下民众都决心进攻县城,因为“1.进城去可没收地主土劣财产,救济目前生活;2.可杀土劣地主,减少压迫力量;3.与其不暴动被其拿去或饿死,不若暴动而死”。当党估计到敌我力量相差悬殊,提出只做游击战争时,“有一部分强悍的便不受指导,要去做土匪,一部分说负责人没有胆量,不敢暴动。同时,东溪有一部分同志另组小团体自由干,并宣传我党无用,都要求立即暴动”。④《福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各县委文件)》(1928—1931年),中央档案馆、福建省档案馆1984年合作编印(内部发行资料),第20页。在这种压力之下,永定县党组织改而决定攻打县城。中共醴陵县委对为何攻城也作了经济上的解释:“我们对城市实行经济封锁,同时无形中农村中也受到了反动派的封锁。如食盐的缺乏,金钱的绝源,城中不但有许多油盐,并且还有许多布匹、铁器、药品以及脱契、文契、各种凭借及牢狱中所坐的农民很多,所以农民更觉得非攻城不可!”⑤《湖南革命历史文件汇集(县委文件)》(1927—1930年),中央档案馆、湖南省档案馆1984年合作编印(内部发行资料),第68页。
因此,以“城市中心论”来描述这一时期党所领导的暴动是不确切的,但当时党的各级组织并没有先扎根农村以发展壮大的思想也是显而易见的。虽然很多暴动有攻城的举动,但以此作为“城市中心论”的依据却要做审慎的分析,即便是最能体现“城市中心论”的两湖暴动计划,在具体实施过程中也呈现着错综复杂的面貌。
三、一股逆向的潜流
两湖暴动计划要夺取全省的政权,但两湖是不是有一个良好的革命局面?以作为湖北暴动中心的鄂南区为例(下表显示了敌我双方的武装力量对比),在中共军事力量最强的嘉鱼县,所掌握的也只有150多枝枪,而国民党在各县的武装,不计民团也都有一个团的正规军队,况且,中共的枪支有些并不能实际控制。在准备攻城时咸宁县只能集中起农民800余人,其余几县的暴动也只见党和农军的活动,很少农民参加的记录。

鄂南暴动中国共双方武装力量对比表
其他区域的情况也不容乐观。在鄂东区的大冶、阳新等县,土豪劣绅在乡村很有实力,党在民众中的影响有限。派去阳新工作的同志发现,一方面由于民众没有深刻的认识并受土豪劣绅的蒙蔽,另一方面由于党的政策有失误,民众对党还有牢骚①《湖北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省委文件)》(1926—1927年),第196页。。湖南也不是一片革命的气象。在作为湖南暴动中心之一的岳州,特派员去领导暴动时发现,工作同志甚少,且不能指挥群众,甚至连20人的特务队都很难组织成功。而敌军却有正规军一个营,并有挨户团的三四百枝枪②《湖南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省委文件)》(1927年),第167、171、172页。。但特派员仍决定无论主观力量如何,岳州总要暴动起来。
革命是需要勇气的,何况以梭镖、土枪、刀棍等低劣的武器去应对敌人的快枪利炮,就更具冒险性。在实际斗争的残酷性与危险性面前,处在暴动前线的同志不敢随意行事。虽然省委制订了暴动计划,地方党组织不得不去执行,但在力量实在太薄弱的地区,所谓的暴动只不过是贴几张标语,放几个炸弹,割几根电线而已。没有力量想动也动不起来,两湖地区的大部分暴动并未能按预期发动。
在两湖秋收暴动中,在暴动的举行和攻城的问题上,很明显地存在着两种不同的态度。由省委派去指挥暴动工作的同志多是不遗余力地、忠实地去贯彻省委的计划,即使在了解情况后也认识到条件并不成熟,或根本没有攻城的能力;而当地县委、特委的同志在对暴动作出切实的估计后,多是持反对的态度。所以,在当时的报告中,经常可以见到省委和派去工作的同志对下级党组织作胆怯、不敢斗争之类的批评。事实上,有些暴动的如期举行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特派员们坚持的结果。
对于这种情况不能简单地以慎重与否来进行评判,可能还有一个责任该由谁来担负的问题。一位湖北的同志曾这样分析省委特派员坚持暴动的行为:他们明明知道暴动要失败,但还是要举行,因为不举行是他们的责任,而举行后失败了,责任由省委担去。省委领导同志的心理也是很值得研究的。中共湖南省委鉴于客观形势于己不利取消了长沙暴动计划,但省委书记在给中央的报告中还是认为湖南处在“革命热潮高涨”的环境之中,“须很好的运用这一时机,来鼓动第二次暴动”③《湖南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省委文件)》(1927年),第220页。。他将湖南暴动的失败归结为是单纯的军事行动、同志没有坚决暴动的心理、没有计划全省起来暴动等原因。
不管结果以何种形式出现,在党基于农民需要革命的价值判断来策动暴动时,还存在着一股与之相对抗的基于现实判断的潜流。游击战争的提出和运用也能给上述观点以支持。游击战争一词早在《中央对于长江局的任务决议案》中已被使用。当时期望夺取全省政权的两湖暴动已经失败,中央对两湖的局势并不像以前那么乐观。中央提出,两湖的革命如一时不能取得政权,“则须普遍的发展游击战争与没收地主的土地及杀戮土豪劣绅等工作”①《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册,第376页。。游击战争是力量不足以夺取总政权时的一种斗争方式,中共湖南省委很快接受了这一策略,并提出在总暴动未成熟以前,应当以游击战争为主要的工作方法②《湖南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省委文件)》(1927年),第247页。。
但是,游击战争在中央看来只是一种“权宜之计”,一种随后即将到来的大暴动的序曲,随后很容易发展成巨大的农民暴动,进一步达到在较大的范围内夺取政权。对于地方党组织的暴动道路而言,则加快了他们从乡村暴动到攻打城市的步伐。比如,中共福建省委在对平和暴动进行批评时,对进攻城市的战略却持肯定的态度③《福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省委文件)》(1927—1928年)(上),第215页。。这可能也是为何攻打城市的现象屡屡出现的重要原因。
在各地暴动遭到挫折之时,1927年11月9日至10日,中共中央召开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依照常理,挫折会让人清醒至少也会冷静下来,但中央却认为全国已具备了直接革命的形势,要在全国范围内创造总暴动的局面,“左”倾盲动主义开始取得支配地位。
在中央影响下,各地省委纷纷改变暴动的计划。中共福建省委曾认为,龙岩的形势“还谈不到暴动,就是游击战术,也还不能马上就用”④《福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省委文件)》(1927—1928年)(上),第49页。。但十几天后,它就改变态度,提出要由各地的暴动联合成一个总暴动,“在农运已有相当基础的地方”,如龙岩、永定等处,“应马上以暴动方法实现之”⑤《福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省委文件)》(1927—1928年)(上),第115、118页。。中共江西省委也改变了“只能部分的零碎的暴动”的主张,与团省委共同作出江西总暴动的决定⑥江西团省委在给中央的信中说:“根据全国的政治情形及江西的政治局面与党的省委有共同的决定——江西总暴动。”见《江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27—1928年),第180页。。
为响应中央的号召并实行总暴动的计划,就出现了类似两湖暴动时强令暴动的情况。以江西省南康县潭口暴动的出台过程为例。潭口处在赣州和南康之间,地势开阔。当时敌我力量在潭口相差很大。中共党员不到20人,有组织的群众也仅有五六百人,只有四枝步枪、一枝驳壳枪和少量子弹;敌军驻潭口有警卫团四五十人,附近还有地方民团,相距20公里的赣州有军队两团,相距15公里的南康县城有敌武装一二百人。针对这种情况,南康临时县委认为马上暴动困难很大,但赣南特委特派员却坚持立即举行暴动,还斥责他们是“机会主义”、“怕死”,于是县委只好通过了暴动的决议⑦《江西党史资料》(第4辑,赣南农民武装暴动专辑),中共江西省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1987年12月编印(内部发行资料),第181、266页。。
也有下级党组织根据实际情况对总暴动计划进行抵制的。中共鄂西特委接到省委秋收暴动的计划后,经过详细地讨论,对它进行了否定。特委在给中央的报告中作了解释:“如各军阀起了混战,鄂西下游各县,可以号召很广大的群众起一个大暴动。如照现在这样,敌人正在有计划的清乡,我们的组织尚难保存,遑论其他。故目前鄂西工作只能引导群众做小的经济斗争而已。”⑧《湘鄂西苏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特委文件)》(1928—1932年),中央档案馆、湖北省档案馆、湖南省档案馆1987年6月合作编印(内部发行资料),第58页。但鄂西特委的意见未能获得中央的赞同。
见诸史料,在当时“此起彼伏”的暴动中,党内对暴动问题有两种不同的态度。通常情况是,上级派来的同志都力主暴动,当地的同志会有赞同,但反对意见也出自他们。下级党组织接受暴动命令时的心态是很复杂的,纵然他们对情况有着较为清醒的认识(诸多不利于暴动的因素),由于害怕被指责为机会主义而不得不动。中共福建省委曾这样自我检讨:省委没有切实考察各地客观的情形和估定主观的力量,不计失败后的影响,遇着各地一个小小的斗争,便要该地进行超过客观情势和主观力量的斗争形式。各县党部受了这种影响,以为不作激烈的斗争,便是犯了机会主义的错误,所以常常不顾实际情形,图谋所谓的暴动①《福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省委文件)》(1927—1928年)(上),第132页。。中共湖北省委也曾指出,同志以为不动就是机会主义,于是到处盲动起来,这是湖北工作遭打击的最大原因②《湖北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省委文件)》(1928年),第535—536页。。
在于都暴动的过程中,这种情况得以清晰地展示。1928年1月初,赣南特委要求迅速发动农民暴动的指示传达到于都。于都的同志们认为目前不宜马上发动暴动,而特委的同志却坚持,其理由是,省委一再催促特委要发动暴动,哪怕杀几个地主豪绅都好,免得省委批评我们消极不动。2月下旬,特委又一次下达了最近发动农民暴动的命令,传达命令的同志强调说,省委批评特委年终没有发动各县举行反迫债暴动,现在必须立即暴动,不得延迟。于都的同志讨论了一整天。在暴动问题上,有同志认为最好能推迟暴动;有同志同意马上暴动,再等,群众的热情就要冷下去了。在攻城的问题上也有不同意见,有同志认为无法攻入,不如不攻县城,去打附近的土豪;有同志认为特委要求我们暴动后攻打县城,若不去打是不对的,但要弄清情况,相机而行,不要硬碰,以免过多的伤亡。最后,他们一致决定拥护特委的决定,制订了攻城计划。③《江西党史资料》(第4辑,赣南农民武装暴动专辑),第201、204、205页。于都的同志对暴动失败的情况也有准备,没有全部公开参加暴动,隐蔽了部分同志将来可以留下来工作,并考虑了失败后同志的去处问题。在围攻于都县城的第三天,当得知敌人调兵解围,他们就放弃了攻城。
综上所述,对“左”倾盲动主义仅做中央政策层面的研究是不够的。党内各级组织之间信息并不畅通,一些地方党组织难以接到中央和上级党组织的决议,即使能够接到,也要考虑中间的时差和他们对文件的理解力。不可否认,“对国民党屠杀的愤怒和复仇的渴望”,使他们产生一种近乎拼命的急躁的心理④《党的文献》2000年第2期。,但在残酷的革命斗争中,基于生存的压力,各级党组织都有一种自认“切实”的判断。而上级党组织与处在暴动前线的党组织在问题的判断上是不同的,从而导致了具体革命过程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只有从上述角度出发,摆脱对政策文本分析的窠臼,进行大量、细致的研究工作,庶几可得切实、全面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