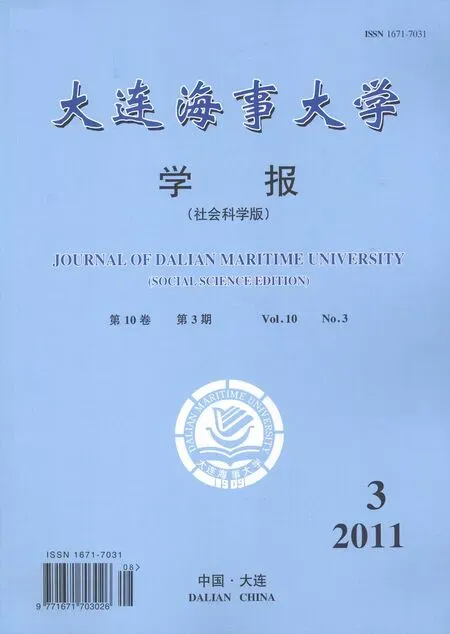论抗战文学中风景的物恋性
厉 梅
(大连海事大学 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辽宁 大连 116026)
论抗战文学中风景的物恋性
厉 梅
(大连海事大学 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辽宁 大连 116026)
抗战时期,日军的入侵给中国造成的灾难切断了中国历史的连续性.在这种创伤性的情境中,只有通过符号性的行动才能弥合现实的裂缝.物恋是对实证化的匮乏之物充满快感的认同.借助于物恋,抗战文学中的风景描写实证化了在战场的溃退面前遭受质疑的民族价值和信念.因此物恋性的风景,例如旷野、土地、国家等,成为人们的喉舌,传递着人们关于国危家难、寻找出路的想象.
抗战文学;风景;物恋;创伤性;匮乏;认同
大自然自从进入人们的审美视野之后,就化身为不同文学篇章中的风景描写,承载着不同的意义功能:或者如中国古典诗歌那样情景交融地传达人与自然的和谐,或者如西方批判现实主义那样让风景为人物和情节服务,又或者如后现代写作中通过风景的零度情感介入来显示自然在人类世界中的退位.风景描写从来都参与一定的文化建构活动,从而成为一定社会价值观念或文化身份意识的索引.具体到抗战时期,不同文体的文学作品中都存在着大量的风景描写.这些风景描写通过或隐喻或转喻的修辞使抗战时期的历史主体、民族美德和民族性格得以确立,发挥了抗战动员的作用.在风景的修辞中,从"此类事物"到"彼类事物",存在着一个半真实、半虚构的结构.对风景这一"此类事物"的固着,反映了人们对风景的物恋(fetishism)心理.这种物恋心理是风景在抗战时期扮演重要角色的原因之一,以下详论之.
一、三家言"物恋"
何谓"物恋"?物恋首先在物神崇拜的仪式中具有功能,指原始人对有神力的物品、物像加以膜拜.在19世纪,马克思借用这个词来谈商品拜物教,即他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通过商品的关系来体现的,因而是异化的.在19世纪末期,伊宾第一次将这个术语用于性行为,即性兴奋绝对依赖于某些特定对象的存在,这又被称为"恋物癖"."某些特定的对象"就是物恋对象,例如一只鞋子或内衣.在弗洛伊德和拉康那里,物恋或恋物癖获得了充分的精神分析学的意义.弗洛伊德认为,物恋来源于儿童对母亲的男根缺失的恐惧以及符号性替代,这种性倒错主要发生在男性之中.他所谓的物恋,就是"被想像为失去了或可能失去的某物的替代品……一个物恋者把自己害怕丧失或可能会丧失的那一部分的重要性解释为自己身外的匮乏,以多种方式在另一个躯体上(例如女性的头发、脚、乳房,等)重新找到,并赋予它们神奇的力量,因而使它们成为'物恋'的对象"[1]348.弗洛伊德的"物恋"涉及主体形成过程中的匮乏、替代和认同,拉康对此进行了阐发.
拉康对弗洛伊德的发展在于他将物恋在性行为中的运用引入到语言学的领域.拉康强调,应该清楚地辨识这种以男根为范例能指的隐喻修辞."物恋的对象和母亲的菲勒斯的同义只有在语言的转换中才可以理解,而不能进行视觉领域的模糊类推,例如将阴毛和软毛等同."[2]这样,拉康就将物恋和主体的形成联系起来.在此阶段,他保留了弗洛伊德的观点,即恋物癖多发生在男性之中,在女性中则极为少见.实际观察有力地支持了他的主体和阉割理论.拉康在1958年为物恋提供了颇有意思的新解,即阳具为异性恋的女性呈现了物恋的价值,引起了一系列有趣的问题.第一,它颠倒了弗洛伊德关于物恋的观点:物恋并不是对真实的阳具的符号性替代,而是阳具本身通过替代了母亲缺失的符号性的菲勒斯而成为物恋的对象.第二,它暗中破坏了同时被弗洛伊德和拉康所持有的宣称,即物恋在女性之中很少发生;如果阳具可以被视为一个物恋的对象,那么,物恋在女性之中要比男性之中普遍.[2]
拉康对物恋前后不一的说法一方面暗示了真相就在物质化的表面,另一方面暗示着对某种对象过度固着或物质化的冲动形成了一种泛拜物主义(拜物与物恋都是fetishism,意思也相似,只是经常被用于不同的场合,如经常会看到马克思的商品拜物教,或者心理学领域内的恋物癖或物恋.齐泽克关于拜物的叙述适用于物恋).当今的各个学说、意见均指责对方为拜物,齐泽克从这些争论中看到了某种理论价值,即造成拜物或物恋这一概念分歧的关键.所以齐泽克梳理了拜物的历史并作出了自己的界定.
齐泽克对拉康知之甚深,他认为:"拜物——客体的关键在于,它是在两种匮乏的交界点出现:主体自身的匮乏和他的大他者的匮乏.拉康的基本矛盾正在于此:在符号秩序内部(基于匮乏的不同关系的秩序),一个客体的确定性并不是在匮乏被填满时出现,而是正相反,在两种匮乏相交时出现.拜物同时作为他者的难以抵达的深度的代表和它的反面,即他者本身的匮乏的替代物('母亲的菲勒斯')发挥作用."[3]125也就是说,在物恋的前恋母情结中,主体在对母亲的认同和对想象的菲勒斯的认同之间游离,对母亲的认同源于主体自身的匮乏,对想象的菲勒斯的认同则源于大他者的匮乏,物恋实现了二者的短路.在物恋中,匮乏的替代物的存在使主体对阉割的否认成功了.这种成功的否认带给主体以快感.所以可以说,"在最本质的层面,拜物是一个遮蔽了他者的无能的极限经验的屏障"[3]126.齐泽克认为"埃及人的秘密对埃及人自己也是秘密"就是此经验的最佳体现."埃及人的秘密"包装了"埃及人本不知晓的秘密"这一"空无",从而对主体的凝视形成一种炫目的迷惑.也就是说,物恋将匮乏、不可能或者说"他者的难以抵达的深度"进行了实证化,并且对实证化的匮乏、不可能之物充满快感地认同.
二、抗战文学中的物恋性风景:旷野、土地、国家
在这一概念的烛照之下,很容易看出风景在抗战时期所扮演的角色.在抗战时期,日军一方面直接在沦陷区推进奴化教育,抹除中国人的民族记忆;另一方面,它给中国社会带来的各方面的灾难切断了中国历史本身的连续性,很多人质疑中国能否取得抗战的胜利,中国战场的节节溃退滋长着亡国灭种的情绪.在这种创伤性的情境中,只有通过符号性的行动才能弥合现实的裂缝,因而,意义、秩序必须围绕这个创伤性的内核建立起来.而要建立这种符号秩序,必须借助于某种物恋的对象将断裂的历史连续性填充起来.风景就充当了这种角色.风景是人的内在主体性的产物,由于主体的介入,风景成为虚假的"自在"表象,具有一种"客观"的主观性,传达着作者对于外部世界的视点和思路;同时,在这个表象之上,风景又被施加了陌生的精神维度,即风景及其修辞所构成的空间对峙将风景和它所表征的民族价值观念联系起来.也就是说,风景将民族价值观念进行了实证化和物质化,并且使人们对这些实证化的民族价值观念充满快感地认同.
不同的作家基于自身不同的生活道路、政治选择、审美趣味,对物恋对象的选择也是不一样的.
战争给中国描绘了一幅流亡图,因而旷野这个意象为很多作家所钟情.旷野以空间的无垠削弱了主体的归属感,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主体的内在性被挖掘出来.路翎笔下的知识分子就在旷野中"举起了他的整个的生命在呼唤着"[4].旷野中的人物如旷野本身一样充满了辩证,正如路翎所说,"我希望人们在批评他的缺点,憎恶他的罪恶的时候记着:他是因忠实和勇敢而致悲惨,并且是高贵的.他所看见的那个目标,正是我们中间的多数人因凭信无辜的教条和劳碌于微小的打算而失去的"[4].也就是说,旷野中的人物一方面体验着真正残酷的虚无与没有过去和未来的断裂,另一方面又不断地为众人所遗忘的理想而奔走不息.正是这种夹缝式的生存,定位了他们不容抹杀的主体性.艾青也写过旷野.在路翎那里,旷野是知识分子的吁天之所,留下的是奔走者的痕迹;而在艾青那里,旷野是静止的,是关于农村、农民的,是缺乏生命和生活的波澜的.在这片生机凋零的旷野中,希望在哪里,快乐在哪里?为什么作者会对这片旷野感到亲切?人在无意识之中并不觉得自己会死,因此,艾青的《旷野》设置了一个很明确的外在视点——"我",旷野中的一切都是属于"我"的视野中的物事."我思故我不在",在"我"和这个旷野的距离之外,作者对这无尽的贫穷、灾难、卑微的描写抒发了"无意识之我"的一种强烈的求生吁求.反过来说,意识是从对死亡的认识开始的,对旷野的第二人称的感叹暴露了那难以掩盖、不可遏止的死亡焦虑.因而这个趋死又求生的旷野悲哀而又旷达,辛苦而又贫穷,忧虑而又容忍,不平而又缄默,具有巨大的张力.程光炜在《艾青传》中提到,当艾青身处山川河流与密林中时,他意识到相对于无休无止的万物变化而言,个人的生死充满偶然和无意义.所以,这悲哀而又旷达、趋死而又求生的两面性的旷野,既让他感到困惑,又朦胧地体现了他轻生死而活在当下的意念.然而当下确实是贫困而悲哀的,如果说物恋是一个遮蔽了他者的无能的极限经验的屏障,那么,这个旷野的意象就以张力之网遮蔽了无休止的同一命运——很长时间以来的如现在这般的劳困、饥寒、疾病和死亡.这些无法编织进作者意念的"剩余"的存在,就成为作者刻骨铭心的怜悯的根源.
江村在《旷野的悒郁》中,写到了僵卧的褐色的田野和荒冷的村庄.一切青色的生命都被吞噬,枯朽的老人也几乎被压折了脊梁.旷野是忧郁的,那里的人们背负着苦难,被时间所遗忘.但他们仍然不忘编织希望,不管是几近暮年,还是他们的生活遭受了外国商品的冲击.在这些关于旷野的叙述中,总是存在着真实与虚构互补的叙述,即几乎看不到希望,但又不是彻底的绝望,作家们迷恋上了这最后一丝想象空间.
不仅旷野中的人在寻找归宿,抗战时期所有的中国人都在追问:什么才是实在和牢靠的?什么才是身体和心灵的归依?邹绛的《温暖的泥土》充满了尖锐的讽刺,作者用"狗在摇尾"比喻报纸上学者的宏文,用"狗在狂吠"比喻理论家的高谈阔论.但视觉和听觉都不足以给作者一个真实的感觉,真实对作者而言是匮乏的.作者的大他者也是匮乏的,因为作者只用了"这些都不真"这样一个否定的表述而没有直接肯定所指,所以,作者自身的确定性也就无从着落.为了形成自身的自足统一性,作者试图寻找这种匮乏的替代.作者找到了温暖的泥土,从后文"杂沓的脚步"以及"奔赴着黎明的世纪"可知,温暖的泥土指代的是边远地区的普通民众.在这里,通过物理学上的转喻以及触觉的真实可感性赋予后者以当仁不让的历史地位."在这关于'战争哲学'的沉思里,'土地'显然被赋予了一种崇高、神圣的意义.这是一种自然的联想,在中国与外国的神话传说,也即人的原始记忆里,'土地'就是与国家、民族、历史这些'永恒'的载体联结在一起,并因此给人以'归宿'感的.在面临'国土沦丧'的威胁的抗战时期,'土地'对于人们,既是'现实'的,同时又是'象征'的."[5]因而,此处的"温暖的泥土"作为两种匮乏相交后的具体物化,作为一个风景意象,成为一个物恋对象.黄万华指出了关于抗战时期的土地意象极为重要的一点,就是在臧克家、端木蕻良的笔下,土地被称为"海".这两个意象的结合,强化了其深邃、蕴藉,更易成为民族根本和归宿的能指.
与土地密切相关的是国家、民族.在陈独秀看来,"觉醒过来的自我,并不只是一个正在寻找国家的公民,而是一个潜在的爱国者,他渴望一个能够激起其情感的理想国家.一个不能激起爱国主义的国家,比一个没有任何感觉的公民更应当受到批判,因为只有一个值得去热爱、去牺牲,能够激起对民族之爱的国家里,自我意识才能觉醒"[6].那么,什么样的国家才值得人们去投入热情呢?徐迟在《中国的故乡》中认为,中国的故乡在西北,那他又是如何论证它的合理性的呢?因为那里既是一个文化的故乡,也是一个自然蕴藏丰富的故乡,那里有着无限的发展潜力:地面上的森林、地下的矿产、金矿、产驴的原野、产药材的山峰、煤矿、"塞北江南"的田地、产羔羊皮区、产马名区、雪水灌溉的沃壤、产石油的荒郊,这所有的一切都使西北成为中国的后备区、抗战的根据地.在这关于西北地区丰富矿藏的繁复的叙述中,不能不引入当时某些人对这种写法的反思.他们提出,这些可见的物质对一个民族来说并不是最主要的,最重要的问题在于人,在于政治和人事.反过来看,这种将人摈弃于环境之外的写作,将匮乏的文明中国的形象以自然资源来替代,就是一种最直接的物恋.
艾青在《他死在第二次》第六章中写到了田野.中国的农业文明的形式从来没有像在抗战时期那样得到这么明显的体现,松软的泥土、水田、耕牛、农妇以其对时代意识形态的契合成为能指"中国"最为显著的具象.也可以说,那种"这就是中国"的反应是对中国的物恋化的想象,这个"中国"从来就不是事实上的中国.但是在这种反应中存在着一种愿望,面对日寇的入侵造成的文化断裂,它是最后剩余的反抗,最终的身份认同.[1]350这种认同是坚决的,像诗中所说的,他知道他的过去、现在和未来都会由符号支配,但此时的他没有介意.他没有介意农夫没有看到他的善意的笑,更没有介意牺牲后的凄凉.
介意的是我们,艾青后来在谈到为什么创作这首诗时说:"《他死在第二次》是为'拿过锄头'的、爱土地而又不得不离开土地去当兵的人,英勇地战斗了又默默地牺牲了的人所引起的一种忧伤.这忧伤,是我向战争所提出的,要求答复与保证的疑问."[7]因为这首诗发表后,有人对艾青塑造的这个战士的形象颇多微词,所以艾青才作了上述说明.然而这不是最主要的,最主要的是要明了战争无法向任何人保证什么,因为战争存在的本身就意味着打破保证与承诺.战争是赤裸裸的实在界(the Real)的入侵,它阻断了意义的连续生成.除去战争对个体的无意义的消灭,个体的剩余意义就只有在与民族、国家认同的过程中才能得到实现.艾青对战争的控诉可以作为前事之鉴、后事之师,然而对当时的反侵略战争而言,唯有认同这一抗战使命.或者这个民族、国家令"他"感到陌生,甚至是不很满意,但他已经对人们所说的"这就是中国"印象深刻,"这就是中国"这一物恋的想象使他决然地重返战争,死在了第二次.这种生命的献祭"维系了他的向上,他的旷远",成为这首诗最为动人的力量.
另外,还有一种关于物恋的叙述:
古城,/我爱你!//古城,/我爱你;/虽然你那硬石板上移动着许多软脚.//虽然那些被饥饿烧得发狂的眼睛,/要拼命夺去行人手中的一块小饼.//……虽然这长街上/只有寂寞和阴暗的风景.//古城,我爱你,/你使我开始知道生活.[8]552
我在江滨独步,/黄昏在山野间徘徊,/因贪恋傍晚的景色,/不怕黑夜向我走来.//黑夜向我走来,/黑暗如一片大海,/如大海的黑暗,/会将我无声的掩埋.//那样我再不能看见含烟的柳色,/再不能看见金色的太阳,/再不能看见阵阵的归鸦,/再不能看见点点的帆樯.//但我甘愿黑夜将我埋葬,/因为我眼里可以映进灿灿的星光.[8]134
物恋的产生总是因为遭遇到一种创伤性的情境,这种创伤的瞬间闪过了实在界的身形.然而,实在界是不能捕捉的,因为与实在界的碰面会令人丧失所有的现实感.所以在以上两首诗中,就出现了以退为进的叙述:古城疯狂、寂寞、阴暗,黑夜会将我掩埋,使我看不到含烟的柳色、阵阵的归鸦、金色的太阳和点点的帆樯.这不祥的风景冲击着主体的现实屏障,如若不采取行动将会令人难以忍受,所以"我"选择了"爱"这古城和"甘愿黑夜将我埋葬".由于实在界总是被回溯性地建构,因而这些选择所填充的空洞位置就是实在界的容身之所,将这实在界隔离出来,就是将其不可能性实证化,从而完成物恋对象的确立.这种叙述存在于当时很多作品之中,形成了一种视死如归的豪迈与忧伤.
三、结 语
物恋是对不可能之物的实证化,是对匮乏的替代与认同.那么,是否风景成为物恋对象就只适用于抗战时期,还是所有的风景都是物恋对象?例如中国古典诗歌中的风景,"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等.成为物恋对象需要什么样的条件?一般来说,物恋的产生需要一种创伤性的情境,而古典诗歌的意境是和谐的.中国古典文学中的天人合一是诗人驾轻就熟的境界,主体会消融在风景之中.但是在物恋那里,主体始终面临着一种被阉割的恐惧,有一种无能的经验始终缠绕着它.在迫切需要民族认同的时刻,物恋的风景成为人们的喉舌,传递着人们关于国危家难、寻找出路的想象.
[1]张京媛.后殖民理论与文化批评[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2]EVANS D.An introductory dictionary of Lacanian psychoanalysis[M].London:Routledge,1996:64.
[3]斯拉沃热.齐泽克.幻想的瘟疫[M].胡雨谭,叶 肖,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
[4]杨 义.路翎研究资料[M].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1993:30.
[5]王晓明.批评空间的开创[M].上海:东方出版中心, 1998:250.
[6]费约翰.唤醒中国——国民革命中的政治、文化与阶级[M].李恭忠,李里峰,李 霞,等,译.北京:三联书店, 2004:133.
[7]海 涛,金 汉.艾青专集[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1982:168.
[8]许 迦.古城,我爱你[C]//臧克家.中国抗日战争时期大后方文学书系.第六编:诗歌.第一集.重庆:重庆出版社, 1989.
On fetishism of landscapes in
literature during Anti-Japanese War
LI Mei
(College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Dalian Maritime Univ.,Dalian 116026,China)
During Anti-Japanese War,the disasters brought by Japanese troops cut off the continuity of the Chinese history.In this traumatic situation,healing over the cracks of reality needs the symbolic actions.The fetishism means identifying the lack of the positivization with enjoyment.With the fetishism,the landscape description in literature during Anti-Japanese War positivized the suspected national values or brief in front of the retreat.So the landscapes,as the fetish,such as wilderness, earth,or the nation,etc.,became the mouthpiece to bear the imaginations about the way out of the national disaster.
literature during Anti-Japanese War;landscape;fetishism;traumatic;lack;identity
1671-7041(2011)03-0111-04
I206.6
A*
2010-12-28
厉 梅(1979-),女,山东日照人,博士,讲师;E-mail:lm-llm@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