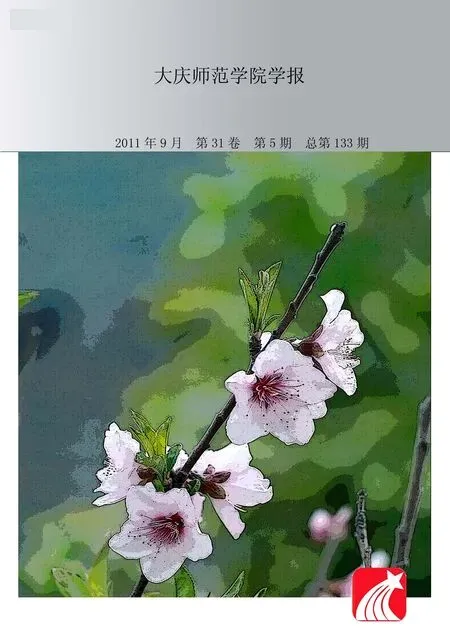黄河水患与清代河南吏治
吴小伦
(天津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天津 300387)
在清代,持续多发的黄河决溢成为河南所遭受的最严重的灾伤之一,史载黄河之害“惟豫省为甚”[1]卷33:825,河南之大政“首在河工”[2]卷10:15。黄河水患虽然是一种自然现象,但也与人事作为密切相关,譬如道光年间,东河总督栗毓美实心河务,不畏困难,“任事五年,河不为患”[3]卷16:626。这里就折射出一个关键性问题,即吏治的清浊,直接关系到各项治河赈灾措施的制定、施行及所能达到的实际效果。目前,学术界对此虽已有涉及,但均失之简略,对河患尤重的河南更是没有专文详述。鉴于此,本文拟以清代河南为研究对象,就黄河水患中的官员作为作一述论,以期从一个视角得出对当时河南吏治的客观认识。
一、清代黄河水患概况
清代河南境内的黄河水患非常严重,我们可以从以下两方面管窥一斑。第一,决溢次数多。关于这一点,胡思庸曾做过较为细致的研究。[4]54-57据统计[注]参见胡思庸《近代开封人民的苦难诗篇——介绍汴梁水灾纪略》(《中州今古》1983年第1期)一文的附录,在该文文末处,作者给出的河决次数为174次,但据笔者对表格的统计,河决次数为167次。:清代黄河共决溢167次,其中河南70次,约占总数的42%;而光绪之前,黄河共决溢133次,其中河南67次,约占总数的50%。由此可以看出河南河患的严重程度。光绪以来,连年的河决转移至山东境内,但考究转移之肇因,却恰恰来自于咸丰五年(1855)河南兰仪县(今兰考县)铜瓦厢处的河决,黄河不但自此结束了泛淮入海的历史,也把决溢带离了河南。
第二,决溢危害重。黄河决溢不仅吞噬人口,如道光二十一年(1841)开封河决,大溜经过村庄“有全村数百家不存一家者,有一家数十口不存一人者”[5]卷153:4028,还沙化、碱化土壤,恶化生态环境,如滑县黄河故道左右“半属沙碱草荒”[6]卷7:11,“其地沙碱、茅苇弥望皆是”[6]卷8:1。更突出的是数次河决的影响不止于河南一境,如道光二十一年(1841)开封河决波及“河南安徽两省共五府二十三州县”[7]卷359:482,两年后的中牟之决致使河南、安徽、江苏“三省灾黎,流离失所”[7]卷407:97,光绪十三年(1887)的郑州之决又使三省人民“荡析离居,极堪悯测”[8]2331,尤其后两次河决,均在一年后始合龙成功。黄河水患表现出发生频率高、破坏性强、持续时间长、影响面广等多重特点。
二、清代政府的作为
(一)积极地治河赈灾
为治理黄河,遏控决溢,清政府于顺治元年(1644)设立河道总督,令其“掌治河渠,以时疏浚堤防”[9]卷116:3341。此后逐渐形成了机构层次分明、官员设置完备的黄河河务管理体制,河工缘此成为一项非常重要的国家行为。但是,由于河南地依黄河,协济河工、赈恤灾民也是不可推卸的法定公务。职责所系,不少官员表现了积极应对的态度。
依照清代河工成例,河员专司治理,州县协济夫料。但实际上,在具体的操作过程中,州县对河务的参与程度远非“协济”二字那么简单。比如设置堤夫、堡夫,安澜时维修河干,决溢后抗洪抢险等工作。以封丘县为例,道光年间,每届伏汛时节,该县官员即派拨民夫为站堤夫,令其“各携锨筐席片,搭盖高铺,住宿堤顶,协同兵役昼夜巡守,一遇漫滩水涨,鸣锣为号,齐往抢护”[10]卷9:13。但是,黄河大堤绵延数千里,更多无工之处人迹罕至,仅有汛节堤夫是不够的,所以再于黄河沿岸广建堡房,设置堡夫,令其常年住守,“上下相应,远近互为声援”[11]卷5:21,这样可以及时发现问题,并以充足的劳力治黄河于决溢之先。地方官俨然成为了河务的主导官。非但如此,如果遇到料物不足或国家经费未至,河南各级政府又不得不多方筹措,因为工期尤其险工是不能够迁延的。如道光二十一年(1841)六月,河决开封,料物不足,巡抚牛鉴立派人赴“尉氏等三十六州县买办”[12]69。同年九月初,邹鸣鹤不得不勒令城内八家典商上缴“旧存官银十五万两”[12]72,以应对迫在眉睫的兴工。
不过,仅仅有以上这些作为还是远远不够的,夫役的遴派、料物的购备、经费的筹集只是为黄河的岁修与抢修做了前期的准备工作。所谓岁修,是指黄河安澜期间对以维修堤坝为主的相关河工的兴举。很明显,它为河务专属,非地方官职责所及。但部分沿黄州县还是尽己所能,积极修堤自卫。如虞城县,北濒大河,“恒恃堤以为卫”。康熙十七年(1678),境内遭受河患,主簿张允嘉亲筑堤防,“滨河堤成,一境获全”[13]卷4:11。雍正七年(1729),知县张元鉴再次择人修堤,“分任方隅,日夜趣工”[13]卷8:105,堤竣而邑安。所谓抢修,顾名思义是指黄河决溢期间的抢险工程。虽仍为河务专属,然面临堤溃邑没的危局,地方官员就必须协同抢修了。如乾隆三年(1738)九月,郑州境内黄河汹涌欲溃,知州张钺急率3000民夫昼夜督护,“内戗外筑,埽工坚好,得保无恙”[2]卷2:5。乾隆二十六年(1761),河溢柘城,知县胡天畀“督催民夫筑堤”[14]卷10:6三昼夜,大决未致。很明显,二者之中岁修最为重要。如果岁修及时,并且保证工程质量,那么黄河决溢的可能性就会大大降低,抢修工程自然随之减少。同时,如果岁修期间各类治河料物预备较足,也能为成功抢修提供必要的保障。河南地方官员的治河行为既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河务的不足,也给自己的属邑带来了安全与稳定。
如果说过多地参与治河有越职任事之嫌,那么赈恤灾民则是地方官员实实在在的份内之事了。黄河决溢后,田舍被淹,四处汪洋,灾民栖止无所,饔飧难继,政府之赈恤尤为重要。可以说,“灾黎得一日之赈,即度一日之命”[15]卷311:91。在这一层面上,河南地方官员多有可资赞写的惠行。
依照清代的荒政,在河患发生后,为了更好地实施救治,第一步便是迅速赶往灾区,厘定灾荒等级,而河南地方官员身处其中,自然能够在第一时间查勘上报。如嘉庆十八年(1813),睢州、宁陵一带因河决被淹,巡抚方寿畴立即派员飞赴灾区,“督率该州县委员亲赴被水各村庄,履勘明确,分别灾分轻重,户口多寡,逐一开列清单禀报,以凭奏办”[16]卷3:2。道光二年(1822)七月,河溢原武,武陟、汤阴等县间有被淹,巡抚姚祖立派官员仔细查勘,“分别被灾轻重情形,据实奏明办理”[5]卷58:1497。
堪灾的同时,救灾活动也迅速展开。由于灾区房屋倾圮,民无所栖,流离迫寒,殊为至虞,提供居所尤为急务。而水冲后,物资又异常匮乏,所以,广置“棚”屋成为地方官最快最佳的解决灾民居所的办法。如嘉庆十八年(1813),睢工漫溢,宁陵、睢州、商丘、柘城、鹿邑等州县居民均遭水淹,各地方官及时“搭盖席棚棲止”[16]卷7:2。道光二十三年(1843),河决中牟,地方官又“搭盖窝棚三百余座”[17]633。
房屋被冲,意味着仓庾尽毁;灾黎枵腹,生命更趋垂危。面对嗷嗷待哺之“棚”民,地方官又刻不容缓地散发食物。如嘉庆八年(1803)河决封丘后,该县之官即散放“一月口粮”[17]392。光绪二十二年(1896),滑县河决,训导谢泰阶“捐馍饼三千斤”[6]卷14:33,救助饥民。对于路程较远者,则设法送达,如嘉庆二十四年(1819),河溢河阴,居民被淹,知县蔡銮登“驾舟贮饼饵啖之”[18]卷14:8,多村之民赖以活。
但是,单纯的散发食物也存在问题:政府的库粮是否可以满足众多灾民所需?河决后,灾区处处是水,灾民是否有柴薪把食物加热或做熟?一个妥帖的办法刚好可以解决这两个难题,那就是设置粥厂,煮粥济民。河南各级官员非常重视这一“理想化”的赈灾方式。如乾隆二十六年(1761),河决柘城,知县胡天畀“用谷一万九千余石,煮粥散发贫民”[14]卷10:6。嘉庆十八年(1813),睢州、宁陵二处因河决淹浸,归德知府谢学崇发放政府存粮及各处所捐银谷,严令“赶紧多设粥厂,一体煮赈”[16]卷3:19。同时,巡抚方受畴派试用知县恽焯驰赴睢州粥厂,鼎力相助,并将“该州共设粥厂几处,何日开厂,大口每日给粥若干,小口每日给粥若干,男妇老幼共有若干,每日需米若干,有无遗漏”[16]卷4:10等情况密折回禀,确保煮赈顺利进行。
此外,河决后,一方面人畜大量淹毙,提供了疾疫爆发的土壤,另一方面食物、药品匮乏,饥馑导致灾民免疫力下降,缺药又使灾民投医无门,这就导致泛水过后,疾疫肆虐。防治措施自然势在必行。如乾隆四年(1739),河决归德,柘城典史对疫病者“饮以汤药”,使“民无亡者”[14]卷2:29。道光元年(1821),河溢柘城,境内大疫,县令周联登“刊方施药,所活甚众”[14]卷2:30。
以上这些灾中救助虽然缓解了灾民的燃眉之困,但并不能使其从灾伤的阴影中真正脱离出来。因为黄河泛水给灾区带去的是千疮百孔的社会局面,而要想医好这些创伤,官员们既需留意勘察,又要戮力解决。河南灾区的不少官员也做到了这一点。揆其要,概有如下四个方面:
其一,招民复业。河决后,灾民或背井离乡,乞食在外,或踯躅灾区,无以为生,生存境况非常艰难。国家赈济只能救民于一时,助其复业才能行长远之效。如顺治十一年(1654),封丘遭遇黄河水患,及至决口堵塞,知县余缙即“披荆棘,芟草莱”,“加意招徕,劝民复业”[19]4。顺治十八年(1661),知县屠粹忠莅任伊始,再次“遴土著,招流亡,多方挑除淤沙”,对于无耕具者,“借牛种,劝谕开垦”[19]5。
其二,开渠兴农。河决后,泥沙沉积,沟渠多淤,不利耕作,所以要广兴水利,多浚沟渠。如原武县,康熙间黄河决溢后,境内多淤,一遇霖潦,农田辄被水灾。乾隆二年(1737),知县吴文炘亲勘形势,“开南北两渠,暨官道渠,水乃通流,无沮洳之患矣”[20]卷2:4。中牟县也是如此。由于屡遭河患,沟渠多淤。乾隆十二年(1747),孙和相任知县后,躬履四境,相度地势,“或创或因,乘农隙募民修凿,计开渠四十七道,一律深通,民享其利”[21]。
其三,蠲缓钱粮。泛水过后,田禾淹毙,收入无望;地被沙压,沃野易瘠。不特当年之钱粮赋税难以筹集,如果田土持续沙瘠,灾民更无法承载此后数年国家正常的赋税征收。在这种情况下,“蠲缓”钱粮就显得非常重要了。“蠲缓”即蠲免与缓征。其中,蠲免是对灾区的钱粮赋税,按受灾程度订出等级,确定全部或者部分免除。如嘉庆八年(1803),河决封丘,被水村庄民欠之钱漕银谷“概予豁免”[17]393。嘉庆十七年(1812),李家楼漫口,虞城被淹十之二,夏邑十之六,永城十之七,其地丁钱粮“虞城豁免一年,夏邑二年,永城三年”[22]卷14:15,按照受灾等级区别免除。而缓征是对灾区的钱粮赋税实行延缓征收,分数年补征完毕。如道光元年(1821)七月,原武受黄水之灾,巡抚姚祖同奏请将所有本年应征钱漕“缓至来年麦后、秋后分别启征”[17]523。但由于缓征不是免征,这里也有一个缓征的时间和方法问题。巡抚姚祖同曾留心观察,发现“若以一年而完数年之欠,民力实有未逮”。道光二年(1822),他覆准将原武等十四州县“各灾村原缓至道光二年麦后应行启征之嘉庆二十三、四、五等年,并道光元年钱漕银谷等项,均请展缓至本年秋后为始,各按最先年分每年带征一年”[17]533。赋税的征免权归于并不知灾区实情的帝王,因此它的或征或免与灾区地方官员是否关心民瘼、据实力奏有很大的关系。
其四,调解田界纠纷。黄河徙道势必造成田界混乱,若遇不法民人或官吏借机强占,争执在所难免。如康熙年间,河阴境内黄河徙道,部分土地出现了“水在地南,地在水北”的情况,武陟县张洪略等人借机强夺新河道北部田地,引发了其与河阴庠生秦士升之争。知县申奇彩据实申诉后,经上宪及河阴、武陟两县官员历时两年的实地调查,最终还田于河阴,张洪略等人受到戒饬。[23]卷2:2又如巩县与温县,壤境相接,黄河屡徙,田界多争。乾隆三十年(1765),上宪亲勘田界,巩令李天墀与温令“争于上宪前,声色俱厉”。巩民恐其得罪诸官,自愿息讼,李天墀却说:“吾即得罪,不过左迁,岂忍恋一官使众民失业耶!”[24]卷11:59表现出了强烈的怀民情结。
(二)出现的舞弊问题
清代河工虽然取得了不俗的成就,且出现了诸如靳辅等彪炳史册的治河能臣,但河工中的腐败舞弊行为却始终是难以杜绝的大弊窦,尤其到了清中后期,“河工习气”甚至成为官员腐朽的代名词。这种贪腐之风也由河务官蔓延到河南官场之中。光绪四年(1878),御史孔宪谷在奏陈河南吏治积弊时说,“豫省官吏向染河工习气,竞商奢靡,所办公事,率多粉饰欺蒙,毫无实际”[8]604。舞弊伎俩也是各有不同。
如前所述,河员专任修防、州县协办夫料是清代河工的一大特色,但在实际运作过程中,一些州县官员却时常玩忽职守,漠然置之。乾隆八年(1743),河督白钟山即因此上奏乾隆帝,“府州县正印官每膜不相关,无同舟共济之情,掣肘误工,不一而足”[11]卷9:26。还有一些官员虽然投身河工,却敷衍应事,影响了工程质量。如道光元年(1821),内黄县丞詹大煃等在原阳县修筑一道越堤,但“完工甫及一年,遇有涨水,辄被刷塌”[5]卷57:1491。次年五月,黄河北岸长堤加帮土工及武陟马营坝增培遥格等堤工程完毕后,经河督严烺勘察,发现“河内县丞张士钰硪架无多”[5]卷57:1473。不唯州县官员如此,省级官员也有这样的表现。如道光二十一年(1841)河决开封,为保护城垣,巩县人王世隆献上了较为有效的“活坝式”[12]51。巡抚牛鉴颇善该法,命人依法办理。但仅仅数日,却被河营都司关思义、抚标中军尤渤强行停用。既然是巡抚下令置办,怎么会出现被停用而没有人追究停用的原因并及时恢复呢?牛鉴的玩忽敷衍不言自明。
另外,假借治河、横征暴敛也是河工中屡见不鲜的舞弊伎俩,道光帝在二十三年(1843)的上谕中就曾尖锐地指出部分官员借河工“或按亩科派,或择户捐摊”[5]卷85:2219的不法行为。河南一些地方官员也未能例外。就在道光帝发布该上谕的次年,林县政府即频加“河工料物”,愤怒的民众组织“联庄会”,进行反抗。道光二十八年(1848),孟县知县又加收“河堤土方折价”,民众以监生张来法为首,赴县署要求减免。[25]卷4:15个别贪官污吏没有因为皇帝的指责而有所收敛。
舞弊行为同样出现在赈恤过程中。一些不法官员以赈灾为幌子,伺机克扣公帑,私饱囊橐。比如冒赈侵赈。嘉庆十八年(1813),河溢兰阳,政府设厂煮赈,该处官员上报每日收养灾民5000余人,后经查实,“厂内领粥仅有五六百人”[16]卷5:11,九成的赈灾物资被其侵吞。道光二十一年(1841)十二月,陈留知县李公赴开封领取八箱赈恤银,却私侵三箱。[12]83又如滥用胥役。道光年间,金应麟曾上书说,“被灾地方穷民最苦,而豪棍最强;富户最忧,而吏胥最乐”[7]卷244:679。之所以出现这样的现象,是因为清代一些州县官宁将事委派于胥役,也不使用县丞、主簿等属僚,“其意以为丞薄尉易掣吾肘,而胥吏惟吾欲为”[26]卷22:2。这样,官役勾结、胥役滋弊就在所难免了。如嘉庆十八年(1813),睢州决溢,据参与赈务的蒋祥墀所奏,“胥役乡保彼此侵吞,饥民实在领赈者不过十分之四,胥役下乡登名造册,每名索大钱二三十文不等,穷民无处借挪,竟束手待毙。又于发签时多番刁难,致老弱拥挤仆弊,该役将口粮肥己”[16]卷2:31。对于胥役作弊,时人也有清醒的认识,并在治灾中尽力防弊。如道光二十一年(1841)六月,河决开封,生员王家勤等禀称“两厂放赈时以事出仓猝,户口难稽,地方官惟饬令地保散放赈票,地保不免藉端渔利,高下其手,并开写虚名,请人冒领,且书役更滋弊端,串通地保,多开虚名,冒领侵吞,在所不免”,为确保赈务真正实惠及民,“应请派绅士挨户清查,庶德遍灾黎,而经费亦不致虚靡”[12]59。而深忧此弊的嘉庆帝也曾要求各地督抚“饬令州县官严行约束,如有包揽把持等弊,立即查拿,按律严办,以除奸蠹”[27]卷308:87。但是,纵容胥役作弊的恰恰正是这些官员。因此,欲除其弊,必须实施深层次的吏治变革,而这又是当时牢固的政治体制所不能做到的。
三、结 语
清代对吏治的重视,可以从满清入关后两位帝王的言论中得以深切体会。顺治元年(1644)十月的上谕指出,“国之安危,全系官僚之贪廉”[28]卷9:94。继任的康熙帝不但重视吏治清廉,“朝廷致治,惟在端本澄源;臣子服官,首宜奉公杜弊”[29]卷90:1136,还对地方官提出了要求,“宜实心任事,洁已爱民,安辑地方,消弭盗贼,钱粮不得加派,刑名务期明允,赈济蠲免,必使民沾实惠,以副朕察吏安民之意”[29]卷45:594。上行而下效,最高统治者的强调和重视势必对官员群体的政风带来一定程度的积极影响。河南各级官员面对几近常态化的黄河水患,采取了一系列积极的措施,也取得了不俗的成效。可以说,如果没有这些官员系统性和持续性的治河赈灾行为,很多河决的恶劣影响会更加难以想象。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清代的河政腐败也与日俱增,尤其在和珅秉政后,“其任河督者,皆出其私门,先以巨万纳其帑库,然后许之任视事,故皆利水患充斥,借以侵蚀国帑。而朝中诸贵要,无不视河帅为外府,至竭天下府库之力,尚不足充其用”[30]卷7:25,从而养成“内外官吏贪墨之风”[31]卷34:239。文献记载虽不免有些夸大和珅贪腐对清代吏治之不良影响,但也折射出了当时的社会现实,即乾嘉更代之际成为清代吏治清浊的过渡期和分水岭。随着康乾盛世余晖的散尽,嘉道中衰阴霾的到来,吏治窳败已如流水东逝难以遏抑。河南处于这样的社会环境之中,其吏治亦概如此。不过,从文中所述可以看出,在为人乐道的前期吏治中,官员之贪腐也有发生,而在饱受诟病的后期吏治中,亦有廉吏出现,可谓清中含浊、浊中有清。所不同的是,随着后期“靡费罪小,节省罪大”[32]卷6:2等扭曲心理在官员中的弥漫,浊吏日益过渡为官员中的主流人群,使得河南虽在协济河工和赈恤灾民过程中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财力,却并不能真正收到预期的效果。清浊互蕴遂成为清代河南各级官员在黄河水患救治中所表现的吏治特点。
[参考文献]
[1]贺长龄.皇朝经世文编[M].北京:中华书局,1992.
[2]张钺.郑州志[Z].乾隆十三年刻本.
[3]陈康祺.郎潜纪闻二笔[M].北京:中华书局,1984.
[4]胡思庸.清代黄河决口次数与河南河患纪要表[J].中州今古,1983(3).
[5]武同举.再续行水金鉴[M].民国三十一年铅印本.
[6]马子宽.重修滑县志[Z].民国二十一年铅印本.
[7]清宣宗实录[M].北京:中华书局,1986.
[8]朱寿朋.光绪朝东华录[M].北京:中华书局,1958.
[9]赵尔巽.清史稿[M].北京:中华书局,1986.
[10]姚家望.封丘县续志[Z].民国二十六年铅印本.
[11]王荣搢.豫河续志[Z].民国十五年河南河务局铅印本.
[12]李景文.汴梁水灾纪略[M].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6.
[13]李淇.虞城县志[Z].光绪二十一年刻本.
[14]元淮.柘城县志[Z].光绪二十二年刻本.
[15]清高宗实录[M].北京:中华书局,1986.
[16]方受畴.抚豫恤灾录[M].嘉庆刻本.
[17]清代黄河流域洪涝档案史料[M].北京:中华书局,1993.
[18]高廷璋.河阴县志[Z].民国十三年石印本.
[19]王赐魁.封丘县志·县令[Z].民国二十六年铅印康熙十九年刻本.
[20]吴文炘.原武县志[Z].乾隆十二年刻本.
[21]肖德馨.中牟县志·人事志[Z].台北:成文出版社影印本,1968.
[22]杨景仁.筹济编[M].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本.
[23]申奇彩.河阴县志[Z].康熙三十年刻本.
[24]李述武.巩县志[Z].民国十二年铅印乾隆五十四年刻本.
[25]程有为,王天奖.河南通史[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5.
[26]葛士浚.皇朝经世文续编[M].近代中国史料丛刊本.
[27]清仁祖实录[M].北京:中华书局,1986.
[28]清世祖实录[M].北京:中华书局,1986.
[29]清圣祖实录[M].北京:中华书局,1986.
[30]昭梿.啸亭杂录[M].光绪年间上海申报丛刊铅印本.
[31]黄鸿寿.清史纪事本末[M].上海:上海书店,1986.
[32]魏源.魏默深文集·古微堂外集[M].宣统元年上海国学扶轮社铅印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