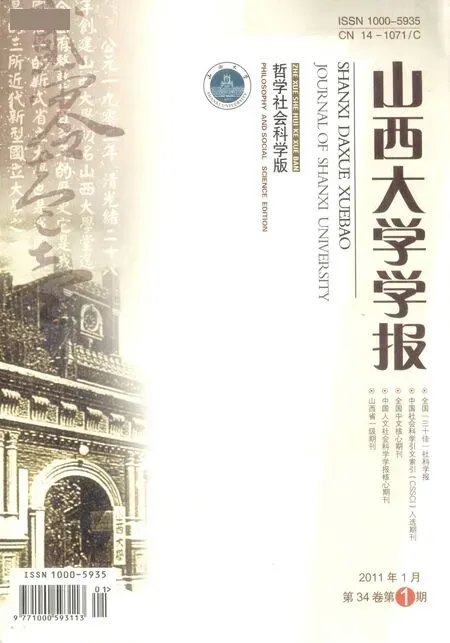近十年来成长小说中的日常生活叙事
龙慧萍
(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北京 100084)
在风靡一时的新写实小说、“70后”个体叙事退潮后,进入21世纪以来,小说创作中出现了新一轮关注日常生活的热潮,并且与近年来学术界对日常生活的理论讨论形成呼应。按照杰姆逊的说法,一种叙事立场或观念即是一种意识形态。那么,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在新时期文学中逐步占据主导地位的日常生活叙事,也正是中国社会转型期社会观念变化的某种风向标。
作为表现人的社会化过程的成长小说,必然关涉社会规范对特定个体进行的约束、引导和训诫,因而也就能最敏锐地体现社会意识形态的这一变化。近十年(2000-2009)间,将日常生活叙事与成长主题结合在一起的小说有池莉的《生活秀》(2000)、王安忆的《富萍》(2000)、池莉的《怀念声名狼藉的日子》(2001)、莫言的《四十一炮》(2003)、余华的《兄弟》(2005)、胡廷楣的《生逢一九六六》(2005)、王安忆的《启蒙时代》(2007)、林白的《致一九七五》(2007)等。如果说“十七年”文学中的主人公是完全没有个人私性的公共形象,那么90年代新写实和“70后”个体叙事中的人物,又完全是私性的,与历史和社会现实无涉。而在近年来的成长小说中,人物以及日常事件都被赋予了丰富的社会意义,从而取得了个体空间/公共空间、个体感受/时代氛围之间最为和谐的叙事效果。
一 从耽于梦想到归于庸常
在这些作品中,《富萍》、《启蒙时代》、《生逢一九六六》、《致一九七五》、《怀念声名狼藉的日子》以主人公六、七十年代的经历为素材,但在故事展开的过程中却刻意排除政治意识形态的影响,而是将六、七十年代作为一个笼统的成长背景来处理。主人公的成长过程与以往的成长故事——尤其是此前的“十七年”经典成长小说①一般指的是“谱歌巷”,即《红旗谱》、《青春之歌》、《三家巷》这几部作品。有很大的差别,体现出政治社会转化为市民社会时,温饱富足取代了昔日的英雄梦想,成长过程从耽于梦想到归于庸常这一历史性的转变。
这其中最典型的代表是《启蒙时代》。小说中的少年南昌因为父亲的身份而成为一个痛苦的、逃亡的“革命者”。这在客观上使得南昌能从抽象的“革命”概念转向对具体生活的感性体验。在南昌的五位“启蒙者”(陈卓然、“小老大”、嘉宝、阿明、高医生)中,“小老大”的影响无疑是决定性的。这个出身复杂、生活环境优渥的小知识分子,知识渊博,身体孱弱,情感颓废而带有诗意,对生命有独特的感悟。正如王安忆在访谈中谈到《启蒙时代》时所说的那样:“他(南昌)对世界的认识是感官化的,这对于教条主义也许可以成为一剂药,它让人有效地摆脱意识形态,让感性浮出水面”[1]。
显然,小老大的客厅在南昌的成长中有特殊重要的意义。这个客厅里永远是各色人物聚集的沙龙,他们无所不谈,跳芭蕾、听音乐、看电影,以维持精致的小市民的生活方式无言地对抗着时代的狂躁。在南昌进入“小老大”家的那一刻,一个丰富、细腻、可感的日常生活世界就在他的面前展开了。这个世界唤醒了南昌,使他与外部狂热意识逐渐分离。他不再满足所谓“革命”的空洞说教,在价值倾向上逐渐向市民靠拢。在经历了与珠珠、舒娅姐妹等女孩相处的市井生活体验,与嘉宝身体的亲密接触,以及由于嘉宝意外怀孕而寻求高医生的帮助,并得到其“光与真理”思想的启蒙等一系列事件后,南昌脱胎换骨,在蜕变中成长起来。
如果说《启蒙时代》完成了从“革命者”到“新市民”的华丽转身,《怀念声名狼藉的日子》中的主人公,则是南昌故事的“女性版本”。小说中的豆豆从对政治运动和两性关系都一无所知的懵懂状态到逐渐成熟,并毅然离开公社党委副书记关山,其选择的标准可以说是充满了世俗生活智慧:关山从第一次得到她的身体开始,每次事后都要独自享用她做的鸡蛋汤;而小瓦却在知道她与关山的关系后,仍然一如既往地给她准备热豆浆和豆腐脑。
将这部小说与《青春之歌》进行对比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豆豆和林道静一样,在人生失意的时候遇到了生命中的拯救者,却在后来的共同生活中逐渐发现拯救者的种种缺陷,并找到新的感情归宿。由于在成长的过程中,选择伴侣的问题其实也就是一个选择生活道路和生活方式的问题,因此,这个作品在一定程度上看起来就像是对《青春之歌》的解构——会过日子、会体贴人的小百姓战胜了党委副书记,女性的成长不再受到头上顶着政治光环的“克理斯玛”型人物的感召(这类人物在今天的成长小说中所遭遇的彻底挫败,在“十七年”文学中,几乎是不可想象的)。
林白的《致一九七五》与胡廷楣的《生逢一九六六》叙述的也都是“文革”少年的成长故事。同样,两部小说的命名都体现了作者试图用另一种方式把握那段历史的创作意图。显而易见,林白的命名有明确规避“文革”而突出70年代的意思,胡廷楣的命名则暗示着某种宿命的悲剧。
《致一九七五》的成长故事发生在广西的偏远小城,作为与北京、上海等截然不同的成长环境,凸显了它的地缘政治意义——天高皇帝远,革命到这里也就走了样。在乡村的日常生活中,一群青春少女的空洞的理想主义启蒙教育,无法转变成革命行动,反落实成为一系列充满世俗生活气息的事件:清扫粪屋、修理自行车、种蘑菇、学木工,都各有其趣。小说没有被时代阴影笼罩的悲苦压抑,反倒充满了青春成长中的冒险、猎奇、热情、懵懂、浪漫和叛逆,它们相互激荡,再加上林白特有的情绪化的追忆、感觉的狂想,与同类型作品相比,小说表现出罕见的某种抒情的、诗性的气质。
而《生逢一九六六》的故事又重新把我们带回上海这座历尽沧桑、拥有独特文化品位的大都市——作为“文革”少年成长的另一重要历史舞台,丰富精致的、物质性的日常生活构成了其文化的底色,这一点,在张爱玲30年代的“沪上市民传奇”中已成定式。事实上,上海这座城市的内涵经得起反复书写和琢磨。在前面提到过的《启蒙时代》中,南昌这样的“革命的后代”在开始就并不能融入其文化的中心(因为他们接受的是简单而且教条主义的阶级教育,将人和事划分成抽象的类别,家庭教育中没有提供人情世故的常识)。而在《生逢一九六六》中,上海的市井智慧和生存法则,包括小奸小恶,却是催生人物自我意识的酵母。
和王安忆一样,胡廷楣将文革中的青少年成长的故事放在上海拥挤嘈杂、各业混杂的石库门的市井社会里展开,使得小说的叙述拥有最具体的日常生活质感,体现出复杂的“市井社会的精神状态”[2]。尽管如此,与池莉、林白不同的是,胡廷楣的这部作品包含了某种更尖锐的东西,她更注重挖掘人物命运的日常性悲剧内涵,表现出将人物置于大时代的背景中又刻意悖反、别有怀抱的良苦用心。与以往很多文革题材的作品截然相反,她小说中主人公陈瑞平的成长悲剧是某种“渐变”,而非戏剧性的,没有大是大非的原则冲突,也没有对错之间的艰难抉择。即使是故事的最后,陈瑞平失去一切,蛰伏在家三天,完成了他的青春祭奠,第四天走出家门,生活仍然还要继续。或者正如王安忆所说,《生逢一九六六》是这几部作品中唯一的“俗世哀史”[2]。
作为“海派传人”,王安忆的大多数作品都可以归为“新上海市民故事”。在世纪之交,褪去了《长恨歌》的喧嚣华丽后,她选择了从扬州进入上海找生活的小姑娘富萍,讲述了她从一个乡下女孩一步步变成上海人的平凡故事。就这样,从“上海小姐”到扬州来的乡下妹头,再到“革命的后代”南昌,王安忆几乎把大上海所有人的成长故事都讲了一遍,并且在她的所有故事中,都有着丰富生动的日常起居、饮食男女的种种琐事。
在《富萍》中,与主人公的成长蜕变联系在一起的,全是些柴米油盐、鸡毛蒜皮的小事。尽管故事发生在“文革”前夕,但王安忆所还原的70年代成长环境是完全自在状态的民间日常生活,对可能作用于人物成长的一切意识形态因素剔除得更为彻底。这样的成长过程尽管平凡得像邻家的日子,但又决不平凡,因为正是无数个“富萍”的普通日常生活构成了上海这个浮华大都会的历史根基,上海的发展也就是日复一日、点点滴滴的日常生活的积累和演变。在这个意义上,王安忆的新上海市民故事与池莉的武汉市民传奇一样,都有着某种城与人以及时代共同成长的意味。
在“十七年”成长小说中,日常生活完全被遮蔽的局面,在此已然被完全扭转。在经典成长小说中,主人公最终都成为“英雄”或是脱胎换骨,成为坚定的革命战士,成长最终都达到了某个具体目标;而在这里,成长小说的结局则往往是开放式的,不确定的,主人公没有实现宏大叙事话语中的革命理想,而只是成为“那个个人”——一个平凡的人。
二 历史的欲望面孔
《四十一炮》、《兄弟》、《生活秀》等作品,虽然也是在描写日常生活的流程中展现人的成长经历,但很明显,与前面几部作品在表现人物成长时,刻意规避时代政治话语解构宏大叙事不同,由于侧重于表现改革开放以后的社会生活变化,这几部作品表现出某种与时代生活变化同步的态势——即表现时代如何进入人的成长过程,如何塑造人的主体。中国社会在近几十年里的变迁是极其巨大的,社会价值观念与生活方式的剧烈变化必将改变社会中每一个体的成长轨迹,甚至完全改变他们的命运,这就为成长小说提供了广阔的社会生活基础,其意义正如巴赫金所说,“时间进入人的内部,进入人物形象本身,极大地改变了人物命运及生活中一切因素所具有的意义。”[3]230而在一个世俗欲望得到充分肯定的物质时代,个体的成长轨迹必然会打上世俗欲望的烙印,这个时代的历史也就不可避免地拥有了一张欲望的面孔。
莫言的《四十一炮》以90年代初农村改革为背景,通过一个孩子的成长反映出了农村改革初期两种势力、两种观念的激烈冲突,以及人性的裂变,人们在是非标准、伦理道德上的混沌和迷惘。在大多数成长小说中,欲望是青春少年成长(认识自身)的一种引导,而莫言故事里的这个孩子直接就是欲望的化身,是一个无所顾忌、无所敬畏的新一代肉“神”,是一个时代欲望的象征。由于他对肉食的超乎寻常的强烈欲望被勤俭持家的母亲压抑,为了能吃到肉,吃好肉,他主动向父亲的仇人兰继祖示好,并发明“洗肉”的方法(这实际上是更高明的注水方法),进了他的肉联厂当车间主任。选择这样一个人物作为小说的主人公,显然能更深刻地揭示一个世风日下、物欲横流的时代在人的成长过程中的作用:罗小通身上藏污纳垢却又充满活力,他愚昧恶俗却偏能在时代潮流中如鱼得水,人物与其所处的时代正是以这样的方式互相诠释了对方,互相印证了各自的发展和变迁。
莫言以惯用的夸张、荒诞手法,将罗小通的成长/堕落与吃肉之间的关系表现得令人惊诧,且富于象征意味。“吃(猪)肉”——这一国人最简单也是最基本的口腹之欲,在此成为个体成长/异化以及全民成长/堕落的历史原动力,人的基本食欲如果不加规范便会诱发道德失范和异化。在这个意义上,《四十一炮》堪称新民族寓言,其对时代荒谬性的尖锐的批评自不待言。
如果说《四十一炮》的叙事焦点是“食”,那么《兄弟》的叙事焦点则是“色”。在当年那个用偷窥美女屁股的秘密换取三鲜面的李光头最终成为刘镇的垃圾大王,特别是他通过洋垃圾西装的倒卖而成为刘镇首富后,围绕他的生活展开的光怪陆离的纵欲“奇观”,如:做爱如同吃饭、垃圾西装、人造处女膜、隆乳霜等等,在今天这个对欲望的追逐无所不用其极,“只有想不到,没有做不到”的年代,既夸张荒诞,又无比真实。
所谓“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在这一点上,莫言和余华似有默契,两人都敏锐地捕捉到了“饮食”与“男女”等日常生活事件对于人的成长的意义,并通过它们折射出时代的本质方面。两部小说的叙事模式也颇有相似之处——主人公都是随着时代崛起、无所顾忌,在时代中如鱼得水的一类人,他们都经历了欲望遭压抑的少年,因此就有了成长后的纵欲狂欢,以及纵欲过度之后欲望的死灭。在故事的最后,罗小通没有了吃肉的本事,而李光头对女人也没有了任何兴趣。作为成长小说,如此结局,其训诫意味自然不言而喻。
和罗小通一样,《兄弟》中的李光头也是一个中国的特殊历史所铸就的怪胎,他的成长和发迹,充分展示了中国社会转型期所暴露出来的种种问题。因此,无论批评家指责《兄弟》中有多少页码是“屁股”连缀成的,有多少事件描述的是拖沓重复的“垃圾”,在长达40年的叙事跨度里,如此集中而夸张地在一个人物的成长经历中折射出时代从“禁欲”到“纵欲”,乃至“无欲”的巨变,就当代文学史来说,《兄弟》应该说是独一无二的。
池莉和王安忆一样,都是描写市民生活的行家,她笔下原汁原味的武汉市民生活,鲜活得甚至可以嗅得出油盐酱醋的味道,拥有与王安忆的“新上海”市民故事相似却又完全不同的质感与更为泼辣蓬勃的内在生命力。《生活秀》里的来双扬和她的鸭颈甚至成为武汉城市的一种标志。武汉这座散发着独特市民生活气息的城市也因此拥有了新时期成长地缘学的特殊意义。
来双扬小小年纪遭遇不幸,在她由15岁起独自承担家庭重担,到最终成为吉庆街的名人的成长过程中,迈出的至关重要的第一步既是被穿衣吃饭的基本生活需求逼出来的,又与老百姓的日常需求密切相关——为了养活弟妹,她大胆地把家里的煤球炉抬到人行道上,架起小铁锅卖起了油炸臭干子。当人们好奇地探出头,看着这令有关部门目瞪口呆的行为好久反应不过来时,来双扬已经烧起了吉庆街的第一把火。
《生活秀》的故事看起来比《四十一炮》和《兄弟》要朴实平易得多,但和这两部作品一样,主人公成长的最简单、最原始的驱动力,仍是解决基本温饱问题。主人公的成长也有基本一致的内在逻辑——对长期物质生活的贫乏和肉体欲望遭压抑的剧烈反弹。但略有不同的是,在池莉笔下为生存而奋斗的主人公那里,自身的温饱始终是第一需要和终极目标。来双扬是穷怕了,因此,她不愿、也不能在人生选择上出任何差错。如果“男女”之情可能威胁到“饮食”的安全,对她来说,那便成为可有可无,可以随时放弃的奢侈品。来双扬对待卓雄洲和年轻画家的态度表现出近乎残酷的冷静和实际,褪去了一切的玫瑰色梦想和理想主义激情,再一次体现了池莉小说中“不谈爱情”的一贯原则,以及市民生存法则和价值标准对理想主义的胜利。
在缺乏深度、价值判断缺失、道德立场暧昧、媚俗等问题上,评论界对《四十一炮》、《兄弟》、《生活秀》的恶评并不算少(当然以欲望叙事迎合大众口味的问题在以六、七十年代为背景的一些作品中也不同程度地存在),但无论如何,以日常生活中的食、色之欲为叙述的切入角度,来诠释一代人的成长和一个时代的历史,既是对80年代以来理想主义笼罩的单一宏大叙事的某种改写,也是把握时代本质特征的全新尝试,因而其反映现实生活的深度并不可轻易全盘否定。
三 救赎、迷失或沉沦——双刃剑
尽管对日常生活有不同定义,但毫无疑问,“衣食住行、饮食男女等以个体的肉体生命延续为宗旨的日常生活资料的获得与消费活动,是日常生活世界的最基本的层面”[4],其中,世俗的物质欲望和肉体欲望是非常重要的两个组成部分。在当代文学叙事中,它们先后遭遇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革命/政治话语以及80年代的理想主义的驱逐和压抑,然而,80年代中后期以来,在文学叙事(包括历史叙事)中处于“无名”状态的日常生活逐渐浮出历史地表,获得了在文学表现中的合法地位。
这也是近十年来的成长小说频频将目光投向六、七十年代资源与90年代以来的社会变革的主要原因。目前活跃于文坛的五、六十年代出生的作家群体(本文涉及的作家中只有余华出生于1960年,其余作家都是50年代出生),正是在六、七十年代的政治狂热氛围中度过了青少年时期,又遭逢了理想主义的80年代,对这两个时代都有比较深入的了解。他们反复地重写当年的成长故事,其用意正是对革命英雄主义和激进主义为代表的政治话语进行解构;而他们笔下以改革开放以来的时代巨变为背景的小说,无疑指向了对理想主义的质疑。
当然需要注意的是,在经过“新写实”和“70后”的两次冲击后,日常生活已经获得它在文学表现中相对独立的价值。但是,随着物质功利主义的流行,文学领域的日常生活叙事有逐渐丧失其最初的叛逆性与革命性,陷入零散化、碎片化的泥淖,并沦为商业性写作策略的危险。失去了革命的方向,成长是否就将迷失方向?消退了理想主义激情,叙事是否就会沉入欲望的深渊?
尽管本文所讨论的众多成长小说也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个体经验的碎片化、零散化,缺乏激情和理性深度、价值判断模糊等缺点,但就前面所提出的两个问题而言,它们交出的答卷还是基本令人满意的。
首先,将日常生活叙事融入成长过程,是以文学叙事把握历史发展的“常”与“变”之间关系的一种全新的尝试。
由于日常生活本身的重复性和自在性,将其引入成长叙事,就使后者摆脱了原来的纯粹精神主导的状态,变为物质性的、肉体的,同时也是重复性的,而这样的重复恰恰是历史发展的常态。王安忆在谈《富萍》时说,“在纷攘的时世替换中,其实常态的生活永不会变,常态里面有着简朴的和谐,它出于人性合理的需求而分配布局,产生力度,代代繁衍”[5],就充分体现了一个优秀作家对历史发展的“常”与“变”之间关系的深刻认识。
在《怀念声名狼藉的日子》中,小瓦战胜了关山的重大意义,并不止于精通组装自行车和收音机、会做豆腐、会过日子、会体贴人的小瓦战胜了党委副书记,而是在小说叙事中,反复出现的鸡蛋汤和豆腐脑这样充满生活气息的细节堂而皇之地进入了个体成长的历史性时刻,拥有了合法地位,并成为叙事的关节点。同样,在南昌的成长故事里,“小老大”客厅里的精致的玩意儿——尤其是在小说叙述中多次出现的那对玉雕小象,以及《致一九七五》里的拾牛屎和尝草(忆苦饭)等场面,也有同样的重要性。至于《四十一炮》里连篇累牍的吃肉场面,《兄弟》里面大段的性爱描写,也都自有其生活原材料的意义。在此,个体的生活感受和生命体验被置于首要的位置,一切成长的感悟、蜕变、抉择都有了具体可感的日常生活的底子。而在《青春之歌》这样的经典成长小说中,日常生活叙事在小说中明显地受到压制。一心追求进步的林道静因为“叫卢嘉川看见自己做这些琐细的家务劳动而感到羞怯”。她家里墙上吊了一盆翠绿的天冬草,书架上摆了个小小的精致古瓷花瓶,也受到批评:摆着这些资产阶级的玩意儿,是不够革命化的,无产阶级的革命战士是反对这些“玩物丧志”的东西的。
其次,正如列斐伏尔指出的那样,日常生活虽然作为微观方面显得平庸无奇,但“上层建筑时时刻刻都从日常生活和社会实践中产生着”[6]41,“关系的生产”(即日常生活)是“生产关系”的前提与基础。就此而言,人必须首先变成“日常的人”,然后才能变成“完全的人”。这也正是后革命时代,个体成长的新方向——不一定要成为英雄,而是要逐渐接近某种内心的成熟和个体的完满,从政治维度上的“单向度的人”,变成日常的人、丰富的人。在《启蒙时代》中,南昌的主体意识与革命话语分离而转向日常生活感受后,他的内心世界显然更为丰富生动了。
当然作品中大量的物质生活的描写有可能使成长过程显得支离破碎,从而湮灭主题,那么在成长目标整体性归于庸常后,对新市民的内涵和外延重新进行思考和定位,也许能帮助解决这一问题。针对当前成长小说中普遍存在的推崇市民价值观的倾向,我们也许应该考虑如何避免将市民塑造成“市侩”,而探讨其成长为现代意义上的“公民”的可能性。
最后,尽管从政治话语中挣脱的成长在摈弃了理想主义关怀后,有陷入身体欲望维度上“单向度”困境的危险,但肉体在几十年遭压抑后重新获得的发言权本来就来之不易,值得珍惜。这里珍惜的意思当然也包含着不可滥用。众所周知,人的食欲、性欲既是自然生理属性,又是历史文化与意识形态的产物。个体自我意识从懵懂到清晰的过程伴随着对身体本身的认识,当然也包括性意识的觉醒,在这个意义上,身体欲望对个体的成长具有相当的重要性。但如何揭示身体欲望与主人公成长及命运的关系,同时揭示特定历史阶段身体欲望如何实现自身,还需要深入思考。
更进一步说,与后革命时代“归于庸常”的成长目标相适应,在肯定“常”态生活价值的基础上,挖掘蕴藏在平庸中的深层心理结构与内在逻辑,是化平庸为神奇的可行之路。与社会学和文化研究领域采取消费者生产的战术操作观点①如米歇尔·德·塞托长期对日常生活实践进行研究,旨在找寻其中蕴含的独特逻辑(可参见其著作:《日常生活实践》,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来阐述平民大众沉默抵抗的生活诗学一样,文学作品或许可以尝试将艺术表现的视角探入大众日常生活中的那些细微平凡的环节,进而从中发掘和整合出某种整体化的、体系的挑战力量。就这一点而言,《致一九七五》中,走了样的“革命”就颇耐人寻味。通过对革命话语/实践进行剪切、拼贴和改装,“政治夜校”变成了粪屋、舂米房;到后来,粪屋里居然又办起了村办幼儿班,知青们领着一群拖着鼻涕的小孩在里面唱歌、嬉闹。“革命”徒留其表,似是而非,体现出与日常生活融为一体的青春狂想在时代高压下依旧可能拥有的飞翔姿态。
总而言之,就是要“用一种非平庸的看法来看平庸”[6]35。列斐伏尔在归纳出19世纪以降的失败和挫折、二元对立、奇迹这三大文学主题后,曾高度推崇波德莱尔的日常生活转向,赞扬他使奇迹题材见出了勃勃生机和原创精神的巨大贡献。在某种程度上,《四十一炮》、《兄弟》中反复出现的日常生活场景具有某种特定时代的个体所经历的欲望“奇观”的意味,与波德莱尔的“恶之花”一样,本就已经抵达了生活的本质,因而都有着批判时代的强大穿透力。而营造文学中的“奇观”的关键在于将日常生活中的事物、事件陌生化,从而通过对宏大叙事的批判,酝酿日常生活的革命。
将成长叙事从制造革命英雄与理想主义精英的轨道上拉回来,回归日常生活,已是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尽管在今天看来“日常生活启蒙”从“新写实”一路走来,很有可能走到另一个极端,被消费主义裹挟,成为另一种专制,但无论如何,在这一叙事转向已成定局后,如何继续挖掘日常生活的深层内涵,使普通和日常的讲述变得妙趣横生和意味深长,并同时抵达个体灵魂与时代症候的深处,才是最为重要的问题。或许也只有做到了这一点,才能真正有效地遏制新的消费主义专制的生成。
[1]钟红明,王安忆.《启蒙时代》:一代人的精神成长史[J].黄河文学,2007(5):20-24.
[2]王安忆.市井社会时间的性质与精神状态——《生逢一九六六》讲稿[J].当代作家评论,2008(1):107-111.
[3]巴赫金.小说理论[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
[4]常利兵.日常生活研究的理论与方法——对一种社会史研究的再思考[J].山西大学学报,2009(2):67-71.
[5]王安忆.近日创作谈——关于写作《富萍》[N].解放日报,2003-06-23(12).
[6]陈学明,等.让日常生活成为艺术品——列菲伏尔、赫勒论日常生活[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