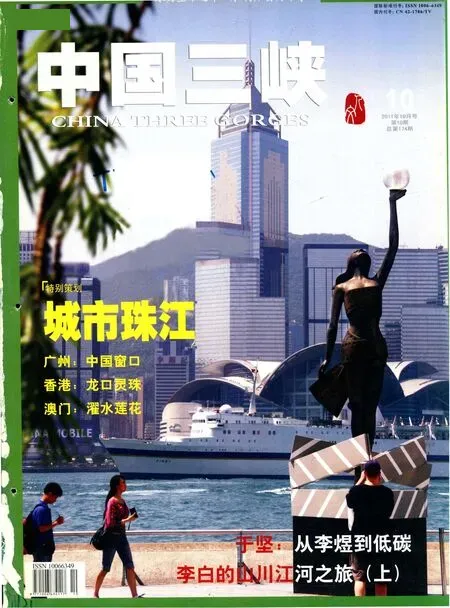三峡洪水题刻:大水肆虐的证据
文/黄晓东 编辑/罗婧奇
在长江上游和三峡地区留下的大量古代洪水题刻,是我们认识历史上的大洪水最直接、最珍贵的物证。题刻的文字都是在洪水淹没的“印痕”处留下的,它们描绘出一次次洪水的具体图像来。
近年来到三峡旅游,随处可以看到海拔135米和175米的水位标识牌,它在时时提醒人们,三峡工程二期截流蓄水后和三峡工程全部完工后,长江的水面将分别抬升至标示位置。我们将目睹三峡水面随着三峡工程的进展不断抬高的历史过程,欣赏不同阶段“高峡出平湖”的姿色。“135”、“175”这些枯燥的数字,已经成为决定当地百姓生存状态的重要标志。
如同猛兽一样的洪水一直是中华民族心中的一个“痛”,大禹治水的故事流传了几千年,表明我们的祖先是同治水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今天,现代“大禹”又在三峡修建水利工程,为人类造福。三峡工程最主要的目的之一是防洪,通过三峡大坝的削峰、错峰作用,以消除长江中下游严重洪水灾害的威胁,所以三峡工程是现代治水最伟大的工程。
今天的人们对洪水的记忆,最真切的莫过于1998年长江大洪水和“抗洪救灾”。洪水的泛滥再次引起全国人民的高度关注,抗洪救灾成为对中华民族的又一次严峻考验。而像那样滔天的洪水,在历史上不知曾泛滥过多少回。

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洪水题刻。
民间记录历史洪水的直接物证
长江流域水资源和水能资源的蕴藏量十分巨大,由于降水分布不均,洪、涝、旱等自然灾害时有发生,随着人类不断开发引起的环境变化,洪水威胁也日趋加重。长江上游、特别是三峡地区是洪水的多发区,生活在这里的人们一直感受着洪水的威胁,最早在汉代的史籍上已有对长江洪水的记载,从此以后,史不绝书。
在长江上游和三峡地区留下的大量古代洪水题刻,是我们认识历史上的大洪水最直接、最珍贵的物证。
古代洪水题刻镌刻在江岸的一定高度之上,虽然没有海拔高度的明确标示,但题刻的文字都是在洪水淹没的“印痕”处留下的。透过文字,我们可以了解到历史上洪水肆虐的情况,结合科学测量题刻的海拔高程的数据,完全可以描绘出一次次洪水的具体图像来。
据不完全统计,从公元227年至1948年间,长江上游发生的较大洪水有56个年份,其中留存至今的洪水题刻有23个年份,数百条洪水题刻记录,大多分布在涪陵、忠县、万县、秭归、宜昌等处。
三峡地区最早的洪水题刻时间为宋代绍兴二十三年(1153年),最近的洪水题刻为1948年。新中国成立后,沿江建立了多处水文站,开始科学地收集水文数据,人们才不再看重民间的洪水题刻标志。
洪水题刻或简明扼要,或生动活泼
三峡洪水题刻一般都是刻画在洪水漫过的山崖、石坡地、柱础、石桥、城门口等处。就目前发现的洪水题刻而言,一般为从右至左竖写,每行2~6字不等,大者长不过1.5米,宽为50~70厘米;小者长50~80厘米,宽为30~40厘米。大字有10余厘米,小字有3~4厘米。
题刻记事者一般初通文墨,也有下级官吏或僧道。文字字体亦庄亦随,题刻内容大都简明扼要,包括年代、水情等消息。描述洪水情况用“水作”、“水泛则至此”、“水界”、“水此”、“大水到此”、“水安(淹)在此处”等,有的题刻在洪水淹至的某处刻画“—”等记号,方便后人对当年洪水准确水位的认识。大部分题刻没有记号,只有文字描述,一般都以“水淹至此”处为洪水水位处,也是了解古代洪水情况的重要材料。
在洪水题刻信息中,也有较为生动的记录,如涪陵龙兴场洪水题刻:“水涨大江贯(灌)小溪,戊申曾涨与滩齐,迄今八十单三载,涨过旧痕十尺梯。观涨人题,庚午年(1870年)六月廿日,水涨至此。”这种用比较的方法记录洪水的情况,在题刻中不是孤例。

上:清同治九年(1870年)涪陵龙兴场洪水题刻。

下:清同治九年(1870年)忠县洪水题刻。
在三峡历史洪水中,水位最高的三次洪水记录为:宋代绍兴二十三年洪水题刻、南宋宝庆三年洪水题刻和清代同治九年洪水题刻。
史二道士祖孙的洪水题刻
公元1153年6月,忠县的一位道士望着浩浩荡荡的洪水,信笔写下了“绍兴二十三年癸酉六月二十六日,江水泛涨去耳。史二道士,吹篪书刻,以记岁月云耳”的题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史道士在感叹岁月的流逝如同浩荡的洪水的时候,也给后人留下了记录三峡洪水的重要信息。
这是已发现的记录三峡洪水的第一例石刻文字,这次洪水主要来源于沱江上、中游和嘉陵江水系的涪江流域,这一地区属四川盆地龙门山暴雨区范围。嘉陵江洪水到达重庆后,与长江、沱江洪水汇合,酿成特大洪水灾害。根据该题刻所处位置的测定,这次洪水将江面抬高至海拔158.47米,是长江上游干流历史上的第三特大洪水。可以想象,汹涌的洪水涨至这样的高度,会给当时的社会造成多大的损失。
“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住在江边的人对水有感情,对洪水的发生更是耿耿于怀。在忠县汪家院子里,就有800年前祖孙两人关于洪水的对话。
南宋宝庆三年(1227年),在绍兴二十三年史二道士题记的边上,史二道士的孙子史袭明道士又刻了一则洪水题记:“宝庆三年丁亥,去癸酉七十五年,水复旧痕,高三尺许。六月初十日,嗣孙道士史袭明书记。”
75年后,又一次特大洪水扑来,史二道士的孙子按照他祖父的办法,也将洪水记录在案,只是他没有关注时间、感叹人生,而是直面洪水,客观、冷静而准确地记录下这种自然现象。这次洪峰水位比公元1153年的洪水还要“高三尺许”,据测算,此次洪水的海拔高程为159.55米,仅次于1870年清代同治九年的大洪水。祖孙两人的记录,将洪水历史演变的轨迹保留了下来。
清代同治九年的特大洪水
重庆忠县是对洪水非常敏感的地方,自宋代以来,凡特大洪水几乎都有题刻记录。清代同治九年(1870年),忠县遭遇了历史上最大的洪水袭击,在城内顺河街土地庙,有“同治庚午六月中,大水至此”的题刻,据测量,题刻的海拔高度为162.16米。也就是说,这次洪水将长江水面抬升到海拔162米左右的高度。

绍兴二十三年(1153年)史二道士洪水题刻,右下为宝庆三年(1227年)史二道士之孙史袭明洪水题刻。
同治九年的特大洪水,波及地域最广,破坏最烈,受关注程度最高。记录的题刻有近200条,分布在合川、江北、巴县、涪陵、丰都、石柱、忠县、万县、云阳、奉节、宜昌等处,将这些题刻联系起来,更能形象地理解这次洪水的汹涌澎湃。题刻准确记录下洪水涨退的具体时间,并由此推断,这次洪水是双峰型洪水。
据史料得知,这次洪水“六月十三日开始涨水,雨很大,下了七天七夜,六月十七日……全城尽没。水到城隍庙门口,只涨不退,平了三天,二十日开始退水,退了十来天,退下去,第二次还回涨上街,又退下去。”
除了洪水题刻记录此次洪灾,在重庆涪陵区李渡镇周正伯家有专门记录这次洪水的“簿记”,这个记录更详细,可以补充洪水题刻简略的不足:“同治九年庚午岁六月十七日,涨大水,又落大雨,上涨情(齐)河麻井,还长(涨)情(齐)禹王宫、土地庙坎下米市街,水涨雷轰街土地庙当门,水安(淹)正街张丰玉当门盐站。十八日肖公庙水打去,十九日王爷庙水打去,二十二日退。大水以(已)过,生意好。”
在三峡洪水题刻中,清代洪水题刻特别引人注目,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六、七月间,岷江、沱江、嘉陵江流域暴雨集中,洪水猛涨,重庆至宜昌河段又遭暴雨袭击,与此同时,长江中、下游地区普降大雨,由此形成长江流域性洪灾,致使荆州城被淹。
道光二十年(1840年)八月下旬,暴雨笼罩岷江、沱江、涪江及嘉陵江流域,出现大面积洪水,在三峡地区形成较大的洪水,宜昌城进水。
咸丰十年(1860年)六、七月间,长江上游暴雨成灾,洪水进入重庆至宜昌河段与乌江洪水汇合,加之三峡地区的暴雨,水势汹涌,荆江两岸溃堤成灾。
最大的一次洪水还是前面说到的同治九年(1870年)特大洪水,重庆、巴县、长寿、涪陵、丰都、忠县、万县、云阳、奉节、巫山等县城大多被洪水冲淹,损失巨大。
位于西陵峡中的黄陵庙是一处洪水记录比较集中的地方,有多款题刻或碑记记载了清代的几次特大洪水,此外在庙中禹王殿内的楠木立柱上还保留着同治九年大水浸泡的痕迹,站在殿中仰望那清晰可辨的水痕,不由使人想起毛泽东的“人或为鱼鳖”的词句。
三峡洪水题刻的文化价值与科学价值
我们在洪水题刻文字中,还发现了一个有趣的语音现象。
在涪陵南沱乡明代嘉靖三十九年(1560年)的洪水题刻上有这样的话:“加靖三十九年,庚申年,水安在此处。”“加”为“嘉”之同音字,“安”为“淹”之意,为重庆地区的方言读音。
在重庆唐家沱的清代洪水题刻也有同样的记载:“大河水,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戊申,大水安此处。”在万县高峰乡也有同样的例子。今天,重庆人仍将淹字说成“安”字音。
这些例子说明,500年前,重庆方言的一些读音就固定下来并流传到今天,语言的形成需要很长的历史过程,一旦形成不会轻易改变。有人就想到,今天的重庆方言形成于什么时候,这些洪水题刻是否可以作为一个旁证。
三峡洪水题刻不仅仅具有重要的文物价值,而且对科学研究工作有极大的帮助,具有重要的科学价值。有关部门在制订长江流域规划以及葛洲坝、三峡水利枢纽工程的设计中都曾利用这些洪水题刻提供的历史上洪水情况作为参考。在三峡工程的文物保护中,有关部门制定了完备的保护方案,考虑到洪水题刻是某一时期反映某地区长江水位的记录,不宜搬迁,采取了就地保护的办法,并选择适当地点进行复制品展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