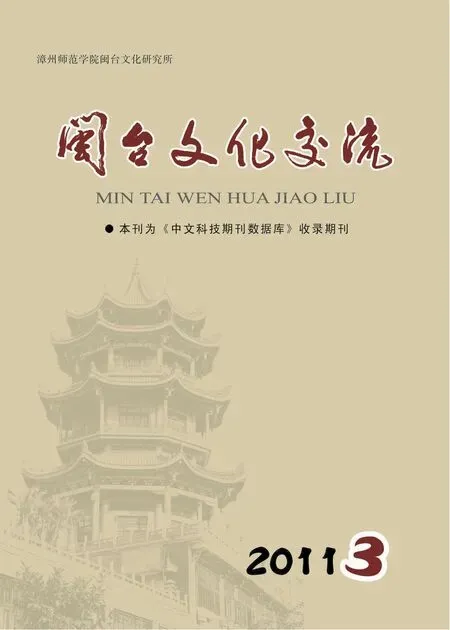杨骚流亡生活中的诗意与悲怆——读巴人散文《任生及其周围的一群》
杨西北
杨骚流亡生活中的诗意与悲怆——读巴人散文《任生及其周围的一群》
杨西北
《任生及其周围的一群》是巴人的散文回忆录,记叙了他与先父杨骚在1942年3月底到7月底在印尼一个荒僻的小岛上的流亡生活。这篇将近5万字的文章,是巴人1947年10月在香港花了一个星期的时间写出来的,极真实地展现了他们周围最底层的华侨苦难的生活图景,极生动地传递出作为文学家的杨骚和巴人细腻丰富的情感。许多年前我读它的时候,不止一遍地从心底里发出赞叹,为不少章节中自然流溢出来的诗意,为不少段落中平实然而是精当的评述。最近重读这篇有浓郁文学色彩的回忆录,再次悸动,当年的印象重新腾现,漫过心头。
一
巴人和杨骚住的山芭(即小村庄)叫“松芽生比”,位于小镇亚里附近一道河湾的尽头。亚里距萨拉班让市区有4个钟头的舢板路程,萨拉班让所在的小岛属苏门答腊省辽州。松芽生比在地图上是找不到的,他们在一个布满繁星的夜晚,乘坐舢版离开原居住地萨拉班让,天亮后才来到这个小村子。他们住在树胶林间一所白木板屋,同房东一家人在一起,房东叫任生,来自广西的客家人。巴人此时的身份是书店的小伙计,上海人;杨骚成了在新加坡开小店的生意人,同行的还有巴人的爱人刘岩(雷德容),她成了杨骚的妹妹,因为日本人攻占了新加坡,他们一家逃难到此。杨骚会讲闽南话,不易引起怀疑,有很多方便的地方。
住屋四周的树胶林由橡胶园和槟榔园组成,有小溪流穿过,水是血红色的(为何这般颜色,文中没有说明,可能是我在当知青时在深山烂泥田见过的铁锈水),简陋的冲凉房搭在溪流上,水直接从底下舀起,冲到身体,又流入小溪里,无比爽快。就是这样的水,巴人和杨骚还是认为,“比住在萨拉班让从井中打取黄色的咸水冲凉要不知舒服多少了。”
本来战乱中这些抗日分子为避免屠杀躲到这热带的丛蛮中,心绪应是惶惶然,可是偏不。附近河湾的高坡上,有一座废弃的硕莪(即西谷米)厂遗迹,有一架破残的绞硕莪的机器。他们竟然爱上了这个地方,这里似乎堆积着诗人般的灵感。每天傍晚,他们总要来这里坐坐。
“这土墩,自有它的诗情,前临潮水涨落的河湾,碇泊着任生的舢板和舴艇,而血红的溪流又从这里曾经有过水闸的高处奔泻而下。我们坐在那里,既可听溪水铿锵的流声,还可远望一片晚霞,照映苍黄的荒原。霞光是那样锦绣夺目,变幻无穷。荒原是那样迎风颤栗,凄切哀歌。如果这一晚,我们大家喝了点酒,那么东北流亡曲的歌声,又在败草丛中,槟榔树顶飞扬了。这真是无聊的感伤,多余的生命出现在像蚯蚓似地生活着的任生的土地上啊!而在任生听来,是否会说,我们是在为他那衰败的家庭,而唱出了招魂之曲呢?”
我完整地录下这段文字,是因为两次阅读到这些方块字,就沉浸在他们所感受的境地,弥漫出流落异国他乡的游子的怅惘,诅咒挑起战争的日本侵略者。
这样的日子实际上过得是不安稳的。杨骚同任生的叔父同一个房间,这个40多岁的阿叔过早衰老,脸如蟾蜍,皱纹密布,因疲惫而夜夜鼾声,杨骚则是因文人思维的活跃而在睡梦中时有呓语。巴人这样写来:“我们对房而睡,中隔前厅,常常可以听到他(阿叔)的鼾声如雷。它和老Y(杨骚,下同。)演说似的梦话,仿佛要赛个你高我低。我想,这怕是这两人生活的反映。一个是垂老的劳动农民的倦怠,一个是身体衰弱的诗人幻想的奔放,这就织成大鼾声与长梦话交奏的夜曲了。”在这逃亡生活中的漫漫长夜里,人的生理性的夜声成了可供欣赏的交响曲了。
在动荡的日子中,这几个不安分的文人仍想尽自己的一点责任。刘岩利用时间,教附近几个女孩子识字。来读书的女孩中有一个叫阿莲的,才17岁,“已显出成熟的征候”,“到了一切女孩神情恍惚,做事没耐心,爱串门子,像寻找什么失落的东西似的年龄。”杨骚单身一人,引起妇人们的注意。任生嫂想做媒,对杨骚说,这女子价格不太高,她母亲只要200叻币便可放手,年纪大些没关系。巴人夫妇也开玩笑说,阿莲来得这么勤,可都是为了你呀。打趣归打趣,巴人实际上这样认为:“老Y是诗人,灵魂的境界是深密的。一个缺少知识的女孩,怕不容易理解他。固然也有一些有特殊嗜好的诗人,即使家有好酒,却总爱在下雨天气,踏进下等酒寮,对着脸搽得像猴子屁股的女堂倌,细斟缓酌,感到别有诗情与风味。而老Y不是那样诗人。”这样的记叙,让人感到那怕在隐姓埋名的苦难中,生活的热望仍匍匐心中,这是否算别样诗意呢?
他们曾想过要开荒种菜,但是锄头使不到一个时辰,便抱怨这家伙太重,杨骚更是手上冒出了两个血泡,只好作罢。
但文人却有自己的风雅。杨骚在直落岛的小杂货店里买了两把德国斧头,“看来像是纯钢的,不大,打铸得极为灵便。斧口较阔而不厚,像黑煤似的发光。”有一天,杨骚炫耀般地请来任生和阿叔,取出让他们欣赏,两人赞叹不已。任生委婉地表达想买的意思,杨骚一听这话,“立刻从两人手中拿回斧头。依然各别用纸包好,合扎在一起,像母亲放孩子到摇篮里去似的,放回箱子去。关上箱子后,老Y不说一句话,静静地望着窗外的树梢和天空。看来在那斧头上有他的世界和天国。他非常之满足了。”
有意思的是这件事并没有这样了结。4个月后,巴人和杨骚要搬离松牙生比,任生正式向杨骚提出要买下这两把斧头,杨骚说:“早给朋友拿去了。”杨骚先离去,后来捎信给任生,让他将自己一口箱子带到亚里小镇。任生搬送这口箱子时,箱子没上锁,箱里也没多少东西,两把斧头在箱子里滚动,发出声响,这让任生是多么的失望。巴人写道:“4个多月来任生没有向我们要求过什么,这是为了他工作上的需要,对这市上难以买到的斧头有了热爱。但农人的爱和诗人的爱,现实的爱和幻想的爱,是像月亮和太阳,永不能会面的。”这样的描写不是充满着诗意吗?多年以后,杨骚病逝,巴人在《记杨骚》一文中重提此事,可见印象之深。
二
任生及其周围的一群,都来自唐山,有湖南、广西、广东、福建等地,他们的艰苦悲惨的耕耘生息,在作家的心灵打下悲怆的烙印。
有一对叫阿鲁和阿鲁嫂的夫妇,自广东海丰到这里有10多年,对生活心灰意冷,对家乡已感情淡漠。阿鲁嫂先后生下了11个孩子,除了留下一个7岁大的,都卖掉了。这一家是以出卖自己亲生孩子为主要谋生手段的。杨骚他们来不久以后,阿鲁又以140元的价格卖掉了一个刚出生的婴儿。任生说:“这在我们种田的,实在算是一种最好、最稳当的出产品。每年一个,拉平均,130元算,这对穷人家,也很可以了。一年的欠缺,就得填补过去。”初听到阿鲁这一种生活方式的秘密时,使他们的心“像受谁的铁椎的敲击,几乎碎裂。”后来甚至产生出一种十分矛盾的心态,常常为阿鲁祝福,因为世界大战一时是不会结束的,阿鲁的日子,也将越来越困难,只能祝福他们夫妇俩,在这苦难的年头里,年年养下一个孩子来,救活自己。如果不是流亡到松芽生比,作家或诗人们会有这样痛心的感受和违心的呼吁吗?这是南洋低层华人多么悲惨的生活状态。
任生周围的一群人,生活在几近与世隔绝的山芭中,他们艰辛的劳作着,维持着最低的几近原始人的生活标准。但他们又是活生生的人,有人的本能欲求,于是就出现了奇怪的人。任生家中有一个帮工叫阿龙,曾当过海员,是广东台山人。他每月给任生家砍运7船的柴火,便没有其他的事了,管吃住,但没工钱。阿龙每个月总有三四天处在颠狂的发病状态,有时不起床也不吃饭,认为不干活就不能白吃,有时脸色发青,看人就像要“咬断你的喉管似的”,呈现“原始人性欲冲动的可怕形象”。杨骚他们月尾送几元给他,算是柴钱,他立刻高兴地唱着歌,穿过林子,四五天不回来。任生嫂说,他是找马来婆去了。说他可以同马来婆又唱又跳,从黑夜到天亮,又接着下去,疯子一样地发泄。作家们认为,“这里,支配着男女关系的不是社会的道德律,而是生理的自然律。”因此,这一群人的关系也就产生了文中诸多的邻里故事,在文学家笔下繁衍开来都会是一篇篇有涵意的小说,仅现有勾勒出来的片断,仍会让人叹息不已。
文中任生的弟弟在砍柴时不慎自伤,失救至死。他的媳妇随任生的父亲分家另辟新村,杨骚曾去探访,回来时捎带回她一句问话:“我们房里那张铁床,现在是不是有人睡着呢?”引起这些流亡文人的感慨,这房和床现在由他们使用,这张床承载过这个不幸少妇的幸福和痛苦,让她系念于心,以至让他们生出自己是“掠夺者”的感觉。这个细节文中仅一带而过,谁敢说它不是尚未孕育的小说中最动人的情节。这样的细节在文中还有一些,充满苍凉和悲痛。
任生家已显现出颓败的模样,但杨骚从他父亲新开的山芭带回来的是一派新景象,令人赞叹。任生父亲这个70多岁的健壮老人,率领着一批人,仍在坚韧地组织着自己的垦殖事业。
流亡的文人无比感慨,“在这样山芭中住着的人们,就是这样大家回返到原始时代。而这一切原始的生活的表现,是那样自然,不勉强。每个人不抱多大的希望,只为某一时,或某一点的欲望,求得满足,就感到安慰了。年轻和年壮的要一杯咖啡,一杯酒或一次男女的接触,而年老的则要天国中一个灵魂的座席,一炷香火。这在他们看来都觉得是僭望,是越轨的行动,是不易达到目的的。……这是如何残酷的现实啊!”
他们深切感受到,在杨骚关于任生父亲垦殖的简单描述和任生旧芭中生活故事配合起来看,“就展开了一部分华侨农民,永远和命运斗争,又为命运所逼害,倒下去,又站起来;一部分人埋入地下去,一部分人又生下来;这里的土地干了,房屋倒了,那里的荆剌榛莽的原野又被焚烧起来,开辟出来,另建了一个新天地——这样的历史图画。”令人不禁为之惊心动魄。
《任生及其他周围的一群》中,有许多富有生活实感的片断,看似零碎,却颗颗是闪光的珍珠;有许多作家由衷发出的感叹,流动着诗意,布满悲怆,又蕴涵哲理,让人心房震动。这些片断和感叹在文中此落彼起,如颤动的丝线影影绰绰,又连为一线。
我没有一口气重读完这篇散文回忆录,我是想有时间慢慢咀嚼。我想起生活对作家的深远影响,这种影响对他们作品的丰厚滋养。有一篇文章说,巴人一直游走在政坛与文坛之间。我又想起新闻界前辈郑楚耘在一篇回忆杨骚的文章中讲起的往事。上世纪五十年代,巴人在北京请杨骚和郑楚耘在“全聚得”吃烤鸭,席间,杨骚几次三番地劝巴人辞去外交工作,回归文坛写作。这从一个侧面表明当年杨骚从海外归来,是下了多大的决心要重返文学队伍。可惜天不假以年,否则他将会留下更多的有关海外华侨题材作品的。
注:《任生及其周围的一群》1949年10月由上海海燕书店出版,1984年12月收入《印尼散记》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1997年9月收入《巴人文集》(回忆录卷)由宁波出版社出版。”
(作者系漳州市作协主席)
责编:李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