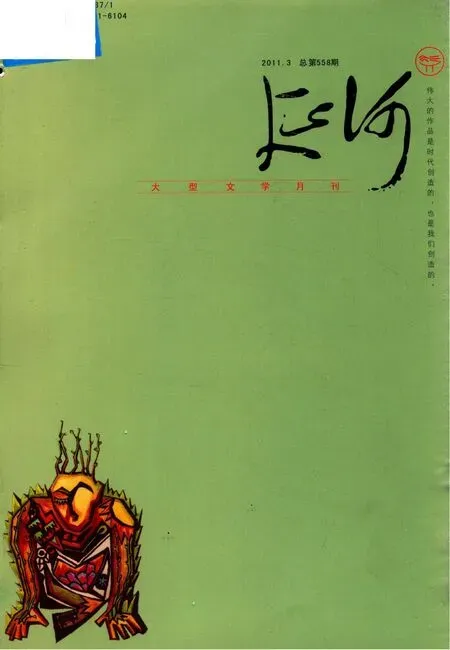一条路与一个人
一条路与一个人
作为武汉大学首届作家班的学生,离开那珞珈山下的可爱校园,不知不觉,二十年时间已经过去。这是整整一代人的时间。记忆中的校园生活,虽然有的仍栩栩如生活在脑子里,但大部份都已模糊。如果说有什么最值得我怀念的,大约只有一条路和一个人了。
一条路是校园里的樱花大道。
一个人便是当时的校长刘道玉。
每每听人夸赞,武汉大学是中国最美丽的校园。珞珈山蓊郁的林木,东湖里的粼粼波光,都是这所百年名校自家庭院中的风景。山环水绕,水碧山青,山中鸟语如珠,水中鸥影似梦。在这般景色中念书,实乃是三生修来的福气。
然而武大校园的最美之处,仍要算与珞珈山隔垅相望的樱花大道。大道在半山腰上,一侧为下坡,满眼的森森古树;一侧为上坡,坡上是百年前的古建筑,一长溜三层的石头房子。我们住校时,那些房子是女生宿舍。每当潇潇春雨,道上的樱花次递开放,这樱花不是可结红红果实的中国樱,而是日本的那种只会开花不会怀孕的嘉木。暖风穿过雨的缝隙走过这条道上,樱树怀春的幽梦就醒了。在你不经意时,它的枝头就骨突出几片花瓣。要不了几天,这道上枝柯交错,全敷了濛濛的一白,如月、如乳、如灿灿的晶片在诗中,如簇簇的蝴蝶在梦里。此时若在黄昏,从树下经过,偶尔抬头,看到花树之上的窗户里,正好有一位女生探出白皙的脸庞,与她的眼光倏然相碰,她报以莞尔。这时,你才确切地领会毛泽东的诗句“俏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的种种妙处。
八十年代中期的武汉大学,在高校教育的改革上,做出了几件敢为天下先的事,如“学分制”,学生自由选系、插班生制度等等。都是因材施教、惠及学人的善举。推行这些改革,刘校长功不可没。作家班正是插班生制度实行的产物。没有作家班,我不可能成为武大的学生。不是武大的学生,我虽然也可以去珞珈山畔看樱花,但仅仅只是一个游人而已。
记得第一次领到武汉大学的校徽时,我真是百感交集。皆因在过往求学历程中,我三考武大皆不获选。第一次是1974年,当时非考而让基层推荐,我下乡所在公社,推荐我上武大中文系,填表政审均通过,最后还是被刷下,原因是县上一位领导的儿子看中这个名额。第二次是1977年恢复高考,我报考志愿,本可填三个学校,但我第一志愿是武大中文系,第二志愿仍是,第三志愿还是。期以为志在必得,谁知误听流言而数学缺考。虽然语文成绩全县第一,终因交了一门白卷而名落孙山。第二年,我准备再考,谁知临近考试,我因急性阑尾穿孔入院治疗,一位工农兵学员为我开刀,他把我当成试验品,小手术弄成大手术。一个月后我出院,考期已过。于是者三,命运好象故意捉弄我,让我总不得跨进武汉大学的门槛。
兹后,我于1982年成为湖北作家协会的专业作家。1985年,刘校长决定在全国中青年作家中遴选人员试办首届作家班,我有幸符合条件而入选。就这样,我不但了却了多年的夙愿,更在刘校长“创新改变命运”的理念中,增强了开拓理想的信心。
去年九月份,刘校长的自传《一个大学校长的自白》出版。我应邀前往北京参加首发式,躬逢其盛后,在归汉的火车上,看了他的自白,许多校园往事便涌到心头。现在看来,刘校长在武大执政期间推行的种种改革,无疑都是正确的,并经得起时间的检验。辗转之间,夜不能寐,于是哼了两首七绝:
一自先生离职后,胸中扫尽是风烟。
梅花未老群芳妒,云水苍茫十七年。
漫言暮雪掩乡关,风雨鸡鸣兴未阑。
岁岁重阳公又至,还将热血化春蚕。
过了耳顺之年的刘校长,该到了重阳赏菊的时候了,但他的精神气儿,仍如当年当校长时那般旺盛、那般睿智。因此每次见到他,我都会产生于濛濛春雨中穿过簇簇樱花的感觉。
2006年9月1日草于南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