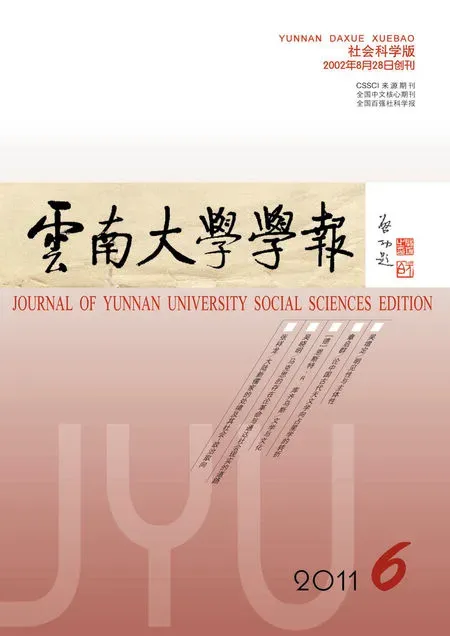论中国古代天文学向占星学的转折*
——秦汉思想聚变的缘起
章启群
[北京大学,北京 100871]
中国哲学
论中国古代天文学向占星学的转折*
——秦汉思想聚变的缘起
章启群
[北京大学,北京 100871]
中国;天文学;占星学;转折;秦汉思想
中国古代天文学在春秋末战国初发生了向占星学的根本转折。这一转折支配并影响了当时的中国思想、学术和政治。在汉代经学中,不但程度不同地羼杂了这种占星学与阴阳五行混合的思想,甚至在根本上受到了占星学观念的支配。其中,“观象于天,法类于地”的占星学思想成了《易传》的核心观念,而《春秋》公羊学大家董仲舒据此提出的天人感应学说,在中国历史上影响巨大而深远。由此可见,占星学对秦汉以后的中国思想、学说和政治所产生的影响是不可估量的。
一
对于中国古代占星学的出现、形成及其与天文学的关系问题,中国天文学史学界的权威们一直没有明确的界说,很多学者于是把中国上古天文学与占星学笼统地混淆在一起。陈遵妫先生说:
我国大概在商代以前,占星术就已经萌芽了。由于奴隶主阶级的提倡,占星术得到了迅速发展,商代的许多甲骨片就是占卜用的,其中有不少天象纪事,正是占星术发达的证明。古代史籍中常见的巫咸就是商代著名的占星家。到了周代,占星术不仅为统治阶级所把持,而且明显地在为其服务了。春秋时代占星术更为盛行,从《左传》及《国语》的记载,可以看到占星术在公元前七世纪及公元前六世纪的兴旺景象。占星术的基本内容是,凭着那时看来是反常或变异的天象,预言帝王或整个国家的休咎以及地面上灾祸的出现,从而尽了提出警告的责任,使之预先有所警戒或准备。[1](P194)
很明显,陈先生对古代占星学的界定非常模糊。甲骨文中的天象记录或星占,与当时的卜筮属于同一类事物,而占星学是运用星辰的运行规律指导人间行为,这是两回事。巫咸可能是商代的掌管天象的史官,与后来的占星家也不是一类。占星学的蓬勃发展是战国以后出现的,春秋以前基本上还没有占星学。
中国天文学史整理小组编著的《中国天文学史》则笼统地认为:“到了阶级社会,原始迷信和神话传说的成份却变成相当细致的占星学。”[2](P3)在这里,似乎是阶级社会的出现导致了中国古代占星学的形成。但全书没有论及占星学与天文学的异同和关系。
由此可见,现存仅有的两部最权威的《中国天文学史》对中国古代天文学与占星学的关系和界限没有论述。而其他一些相关著述也基本如此。例如,冯时先生说:
东西方的天文学在尚未摆脱神学影响的时代,都或多或少地染上了占星术的色彩。西方的占星术……认为,日月众星对人体具有的某种作用,如同铁在磁场中受到磁力作用一样,而中国人则更相信天人感应和天人相通……因此,中国的占星术并不像西方那样完全根据人出生时日月五星在星空中的位置来预卜人的一生命运,而是把各种奇异天象看做是天对人间祸福吉凶发出的吉兆和警告。显然,中国的占星术更多地为统治阶级所利用,这与中国天文学官营特点是密切相关的。[3](P69)
这里基本上把中国古代天文学与占星学混为一体,也没有描述它们的界限和历史发展的过程。
上述这些观点在中国天文学史学界长期流行,更值得关注的是,江晓原先生近期在此基础上又尖锐地提出了“政治天文学”的观点,他认为,中国古代天文学实质上始终就是占星学,并且主要不是为农业生产服务的:
诚如《汉书·艺文志》数术略“天文”类下所言:“天文者,序二十八宿,步五星日月,以纪吉凶之象,圣王所以参政也。”这里“天文”的性质判然可见,不折不扣,即今人所谓之占星学也。而与“农业生产”之类扯不上任何关系。历代官史中的《天文志》,皆为典型的占星学文献,这类文献最早的,在《史记》中名为《天官书》,天官者,天上星官所呈之象,即天象,尤见“天文”一词之原初遗意。今人用“天文”去对译西方astronomy一词,其实是大违“天文”的中文本意的。想像一下,大学的“天文系”,按照中文的本义是应该理解为“占星学系”的,这多么荒唐可笑
江晓原先生用汉字“天文”二字的本意来解析中国古代天文学与占星学的关系,认为中国天文学一诞生就是占星学,这就使上述各家观点更加鲜明而突出地展现出来。
中国上古原发形态的天文学是否就是占星学?或者说,中国上古原发形态的天文学与占星学是否混为一体?它们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厘清这个问题不仅对于推进中国古代科学史的研究,而且对于中国古代思想史的研究都是意义重大和十分必要的。
二
《汉书·艺文志》的确是用占星学思想来解释“天文”一词的含义的,*冯友兰先生对此作了区分:“‘序二十八宿,步五星日月’,是天文学;‘纪吉凶之象’,就是占星术了。”[5](P522)而《史记·天官书》和《汉书·天文志》的基本内容确实是占星学,但是,并不能由此断言《史记》、《汉书》之前的中国天文学也是占星学。例如,《夏小正》与《诗经·豳风·七月》是现存可靠的且具有代表性的上古天文学资料,它们可以帮助我们明晰上古天文学与占星学的关系。
《夏小正》现存于大戴《礼记》中,《隋书·经籍志》首次单行著录。经文只有463字,文义古奥,亦有错乱残缺。故《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云:“《小正》文句简奥,尤不易读。”在很长时间里,人们忽视了《夏小正》的价值。*据沈文倬先生研究,自汉至宋,《夏小正》只有卢辩的注。宋代有傅崧卿和金履祥的注释,清代形成整理《夏小正》为研究天文学动植物的专门科学,先后有二十多家。校勘以卢文(弨)黄丕烈、孙衍星、叶大壮最著名,注释有诸锦的《夏小正诂》、孔广森的《夏小正补注》、毕沅的《夏小正考注》、王聘珍的《夏小正解诂》、朱俊声的《夏小正补传》、王筠的《夏小正正义》等。[6](P1001~1002)而《夏小正》中具有夏代天文历法的资料,这一观点基本上已为学界共识。
孔子曾主张“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论语·卫灵公》)“夏时”就是夏代历法。《竹书纪年》语云:“帝禹夏后氏元年壬子,帝即位居冀,颁夏时于邦国。”这说明有一种“夏时”即夏历存在并流传。此外,甲骨卜辞出于商代中后期,对年月日与农事关系的记录已经相当精确、稳定。可以推论,在这种比较成型的历法之前应该有一种更原始、更简易的历法。夏历的存在应该是不容置疑的。
《礼记·礼运》记载:“孔子曰:我欲观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徵也,吾得夏时焉。”郑玄注:“得夏四时之书也。其存者有《小正》。”《史记·夏本纪》云:“孔子正夏时,学者多传《夏小正》云。”陈遵妫先生说:“《夏小正》相传是夏代的历法。……尽管这书作于西周至春秋末叶之间,也可能为春秋前期杞国人所作或春秋时居住在夏代领域沿用夏时者所作,但其中一部分确信是夏代流传下来的。”他认为,《夏小正》根据天象、物候、草木、鸟兽等自然现象,定季节、月份,还记有各月昏旦伏见南中的星象,并指明了初昏斗柄方向和时令的关系,这可能是后代每月斗建的起源。[1](P200)当代专治“三礼”的沈文倬先生认为,杞国是夏后裔,夏代的历法在传说中保留下来一些,到春秋时始被录成书是可能的,《夏小正》很可能保留了一些夏代的历法材料。因此,他说:“《夏小正》一书(就其经文言)应与《尚书》《诗经》一样,看作是我国最古的文献资料之一”。“只要有部分真实,仍不失为研究夏后氏的重要材料。”[6](P1002)李学勤先生也认为,由戴德最后编订的《夏小正》极可能依据夏代传下的历法。他说:“可见从晚周到汉代,人们都认为《夏小正》确与夏代有关。学者认为《夏小正》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具有丰富物候知识的著作,是合乎实际的。……其经文不会像一些学者所说的晚到战国时期。”[7](P212,222)*詹子庆先生说:《夏小正》是“我国现存的一部最古老的月令。它是按十二月顺序,详细地记载了大自然包括天上星宿、大地生物和与之相应发生的变化,形象地反映了上古先民对时令气候的认识”。[8](P32~33)
让我们节录其中一个月,直观地了解一下:
其中内容包括:天象(参则伏)、物候(摄桑、委杨、鸣鸠等)、气象(越有小旱)、农事(采识、妾子始蚕、祈麦实)、政事(颁冰)。由此可见,《夏小正》描绘了四季日月星辰的运行,并把天候物象与农业生产联系起来,通告什么时候适宜或不适宜何种农业劳作,与农政相关,像是农书。这一点正是它的主要内容和目的。清代学者王筠解释《夏小正》的“正”字,认为是“政之古文,非正朔之正”。[6](1001~1002)*当代学者在我国哈尼族的调查中发现了一种普遍流行的“十二月生产调”,“内容或简或繁,大体包括月份名称、各月的自然现象、农事经验、宗教活动等等。实际上起了生产百科全书的作用。在有些民族中几乎人人会说会唱。……这种生产调可以说是一种口头的历书。它给我们一个启示,大约整理成书于春秋的《夏小正》即由上古时代的十二月生产调脱胎而来。”[11](P7~8)而这一切与占星学或“政治天文学”无关。
再看《诗经·豳风·七月》(节选):
七月流火,
八月萑苇,
蚕月条桑,
取彼斧斨。
以伐远扬,
猗彼女桑。
七月鸣鵙,
八月载绩。
……
五月斯螽动股,
六月莎鸡振羽。
七月在野,
八月在宇,
九月在户,
十月蟋蟀入我床下。
作为中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诗经》不仅是诗歌史和文学史的宝藏,也是社会学和思想史的宝藏。《豳风·七月》的产生年代大约是公刘处豳的西周初期。*《汉书·地理志》:“公刘处豳……故豳诗言农桑衣食之本甚备。”颜师古注:“谓《七月》之诗。”这首民歌不仅描述了一年之中星辰运行的天象,记述了天象与季节农时的关系,几乎说到每个月具体的农事,还描述了劳动者生动鲜活的思想情感,包括春日里的欢快、秋收的喜悦、酒宴上的欢庆、肃穆的祭祀活动以及对统治者的抱怨和无奈,这是我们见到的最早的描述关于季节与农耕生活的可信文献。但它只是素朴地描写四季天象、物候和农家生活,与占星学或“政治天文学”也是无关的。
三
《夏小正》和《诗经·七月》没有涉及占星学并非偶然。
现存最早的中国古代天文观测资料,都是很单纯的天象资料,与占星学基本无关。例如,有关夏代的两条天文记录,第一是关于五星聚的:“禹时五星累累如贯珠,炳炳若联璧。”(《太平御览》卷七引《孝经·钩命诀》)据今日学者推算,在公元前1953年2月中旬至3月初,黎明时分的东方地平线上,土星、木星、水星、火星和金星排成一列。2月26日夜,五大行星之间的角距离小于4度。这是迄今五千年中最难得的一次五星聚(纬合宿),时间长达一个月。[12](P64~65)古人观此异常壮丽的天象,难以忘怀,将此记忆代代流传下来,但这只是一种纯粹的天象记录。
第二是关于仲康日食。《左传》昭公十七年引《夏书》云:“辰不集于房,瞽奏鼓,啬夫驰,庶人走。”今人考证得出,这次日食可能发生在洛阳地区的4个时间:公元前2043年10月3日,公元前2019年12月6日,公元前1970年11月5日,或公元前1961年10月26日。[13](80~81)此记载被认为是世界上最早的日食记录,除了认为日食是一种自然灾害以外,没有其他寓意。《史记·夏本纪》与古文《尚书·胤征》也记录了此次日食的事情,文字基本相同,但《尚书·胤征》语前多出“乃季秋月朔”一语。“辰”为日月会次之名,“房”是星宿名,“集”通“辑”,“瞽”是乐官,奏,进也。啬夫是小臣,汉代有上林啬夫。庶人即百役。意为:日月会次,不相和辑,而掩蚀于房。乐官击鼓,小臣奔忙,百姓奔走帮助祭祀。古人逢日食伐鼓用币救日。[14](P64)这与《春秋》鲁庄公二十五年、鲁庄公三十年、鲁文公十五年记有“鼓,用牲于社”一样,是古代对待日食的办法,就像大旱求雨的仪式一样,与占星学有本质区别。
据今人研究,在出土的甲骨文中,发现由“星”字组成的词有“其星”、“不(或毋)其星”、“大星”、“鸟星”、“新星”(或“新大星”)。“星”义或解为天晴,或解为星辰。殷墟甲骨文记载的月食有五次,这是定论。[15](P9~20)其中是否有日食的记载还在争论之中。[3](232~250)《诗经》、《春秋左传》、《国语》等记载的关于日食、月食的现象,基本为学界所认同。例如,《春秋》纪年自鲁隐公元年至鲁哀公十四年,共242年,记录日食37次。这是确实无疑的观测记录,其年月日基本相符。[16]其中有经无传26条。经文记载几乎都是“某月某日,日有食之”,只有鲁庄公二十五年、鲁庄公三十年、鲁文公十五年记有“鼓,用牲于社”。[17]这些记载基本表明,上古时期人们看待日食月食虽然也是灾异,但就像刮风下雨打雷下雪等一样,是一样的自然破坏力,这与战国以后的占星学思想具有本质的区别。现在已经发现了春秋战国以前的很多天象记录,包括日食、月食、太阳黑子、彗星、木星、恒星、新星甚至超新星,基本上属于单纯的天象记录。*据徐振韬、蒋窈窕先生研究:“1974-1977年,中国科学院、教育部和国家文物局的有关部门和学校,以及各省市的有关图书馆和博物馆等,大约一百多个单位和三百多人按计划对古代天象记录进行普查。查阅古籍总数高达15万卷,收集到的天象记录1万多条。其中包括太阳黑子、极光、陨石、日食、月食、流星、流星雨、彗星、新星和超新星、月掩行星、日月变色、异常曙暮光和雨灰等。1988年,以《中国古代天象记录总集》为名,由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12](P57)
这里还有一个有意思的现象:中国古代最早命名的星辰名称,都来自于生活中的用具及其相关事物、动物和神话传说,与占星学毫无关系。例如,营室(房屋)、壁(墙壁)、箕(簸箕)、毕(捕兔小网)、井、斗、定(锄类农具)等属于用具,牵牛、织女、参、商等属于神话传说。*《左传》昭公元年:“昔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閼伯,季曰实沈,居于旷林,不相能也,日寻干戈,以相征讨。后帝不臧,迁閼伯于商丘,主辰。商人是因,故辰为商星。迁实沈为大夏,主参,唐人是因,以服事夏、商。……故参为晋星。”《诗经》中出现的星宿有:火(心)、箕、斗、定(室、壁)、昴、毕、参、牛、女等,还用“天汉”指银河,用“启明”、“长庚”、“明星”指金星。《小雅·大东》:“维南有箕,不可以簸扬。维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浆”,直接把星辰与用具做了有意思的比较,反映了古人天真的心理状态。*现在某些地区还有“犁星”、“水车星”、“轱辘把星”、“南挂星”、“三枝浆星”等说法。[2](P42)二十八宿的名称,以及后来岁星纪年的十二次,例如,星纪、析木、大火、寿星、鹑尾、鹑火、鹑首、实沈、大梁、降娄、娵訾、玄枵,这些名称都没有占星学色彩。
这些情况说明,至少在春秋以前的中国天文学,其目的主要是为农业生产服务,表达了一种农耕社会的宇宙观,基本上没有受到占星学的影响,不属于“政治天文学”。*《诗经》中描绘天象的诗有不少,如前所述,其内容都是描述农耕生活与星辰的一般关系,唯《小雅·十月之交》不仅描绘了日食和月食,还有“日月告凶,不用其政”之说。我认为,不管这首诗写于何时,仅此一首诗决不能说明在那个时期系统的占星学理论已经建立。
四
中国上古天文学的性质是由农耕文明的社会性质决定的。
现代考古学证明,中国大约在一万多年前就出现了农业。[18](P31~34)农作物的播种、生长、收获需要适当的阳光、雨水和温度,因而必须与时令、物候等条件一致。于是,对节气和季节的认识是农业生产的先决条件。就像古代埃及人根据尼罗河水的涨落来决定历法一样,中国原发形态的农耕文明,决定了我们的先人必然由“观象授时”来制定历法,就是通过观察太阳、月亮尤其是星辰的运行规律等天象,来制定历法。因此,伴随着农耕文明的进步,中国古代天文学也自然地产生了。*古代人们传说,关于“观象授时”的历史是从三皇五帝开始的。《史记·历书》云:“黄帝考定星历,建立五行,起消息,正闰余,于是有天地神祗物类之官。”《尚书·尧典》云:帝尧“乃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时。”这种早熟的农耕文明无疑是决定早期中国天文学形态的根本因素。
在农业出现之前的远古人类的渔猎和采集生活中,日月星辰只有纪日和标识方向的功能。中国仰韶文明的彩陶上就有太阳纹、月亮纹、日晕纹、星座纹。新石器时代半坡遗址中的房屋就已经都有一定的朝向。到了农耕社会,太阳比月亮和其他星辰对生活就更重要了。山东大汶口遗址所出土的5800多年前的彩陶上刻有“旦”字的图案,意味着太阳的升起。《山海经·大荒南经》说“羲和者帝俊之妻,生十日”。《大荒西经》说“帝俊妻常羲,生月十有二”。《海外东经》说“汤谷上有扶桑,十日所浴……九日居下枝,一日居上枝”,等等,都可以解释为在十二个月中太阳和月亮升落的不同方位。在郑州大河村仰韶文化遗址所出土的一件复原陶钵的肩部,有十二个太阳图案,也可以作这样的解释。
但是,太阳光芒耀眼刺目,难以观测。月亮是地球的卫星,同属太阳系,月相的盈虚圆缺周期,大致为一个月的长短,不能明显地反映出季节的不同。因此,古人观测天象主要是观看星辰。由于中原地区四季分明,古人最早观测的星辰大概是北斗七星,也有人说是红色亮星大火,即心宿二,现在通称为天蝎座α星。据推算,公元前2400年左右,黄昏时在地平线上见到大火,正是春分前后的播种季节。此后白昼越来越长,进入农忙季节。[2](P10)殷商武丁时期,初昏时大火星在正南方的季节是仲夏之月,这与《尚书·尧典》记载的“日永星火,以正仲夏”是一致的。[15](P403)这说明大火星的观测历史确实远至上古。*庞朴:“二子(参、大火——引者)在一年里对于人们的关系,正如日月在一天里对于人们的关系一样。太阳在东方升起,开始了‘日’和劳动;太阳到西方落下(明月或早或迟代之而起),进入‘夕’和休息。一年的情景,刚好是一天的放大:大火在东方升起之时,开始了‘春’和劳动;大火到西方落下之后(代之而起的是参的东升),进入了‘秋’和休息。长期的这种实践,在人们头脑里形成了一个牢固的观念,时间上的‘春’天和空间上的东方、天上的大火星象和地上的东方方位,成了混沌一体而不可分离;有如人们一直习惯于把太阳和东方联系在一起那样。这正是原始思维的特点,它带有种种感性的色彩,有时更有幻想的成分。”[19](P132)春秋时期,“晋人用的是夏历,记史者用的是周历,彼此相差两个月。当时,周历虽然具有政治权威,而且在天象上有着更大的合理性,但脱离农事这一点,成了它的致命弱点,在生活中难以推行,更不用说取其他历而代之了。”[19](P134)
传说颛顼、尧时就有火正,负责观测大火,指导农事。《国语·楚语》云:“颛顼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属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属民。”《史记·历书》有同样的记述。《左传》襄公九年曰:“陶唐氏之火正閼伯居商丘,祀大火,而火纪时焉。”陶唐氏即帝尧,“火正”就是观测大火星的官员,即历象天文“观象授时”的官员。这些记载虽然只是传说,但也不应该完全是子虚乌有。夏商周三代设有天文官员,应该是很可靠的,西周称冯相氏、保章氏,还有执掌漏壶的挈壶氏。
因此,上古先民在描述天象和星辰的时候,总是与农耕生活内容相关联。《诗经·七月》起首句:“七月流火,九月授衣。”*张汝舟先生发现,中国上古天文学中的几个概念“中”、“流”、“伏”、“内(入、纳)”表明了不同月份中星宿在天际显示的不同位置和状态。例如:“昏火中”(《月令》六月记),“流火”(《诗经·七月》),“辰则伏”(《夏小正》八月记),“内火”(《夏小正》九月记)。[10](P16)意为:在七月的黄昏时,大火星开始由南偏西向下降行。它不仅表明当时的人们认识大火星,还表明这个星的运行状态与人们的日常生活密切相关。《夏小正》则把天象与农耕生活更直接地结合起来。例如:“五月,初昏大火中,种黍菽糜。”*据后人考察,《夏小正》的说法基本符合农事规律。宋黍升的《<夏小正>笺疏》曰:“五月中气黄道日躔柳十六度九分,昏之中星,当距日一百七度,日距心前一百一度二十分,故大火中。心中,种黍菽糜时也。……《尚书·考灵曜》云:‘主夏者,心星昏中,可以种黍’是也。又言菽者,《尚书·大传》云:‘主夏者,火星中,可以种黍菽。’又言糜者,《开元占经》引《神农书》云:‘大岁在四仲夏至,可以种糜。’此正夏至种糜之据也。”[6](P1001~1002)如果说《诗经·七月》只是一种民间歌谣,吟唱先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那么,《夏小正》则是一种历书的雏形,它的主要功能即是指导先民进行农业耕作和种植活动。
农耕生活决定着当时天文学的内容和性质,或者说决定着当时人们的宇宙观。《左传》昭公十七年记梓慎言曰:“夏数得天。”《逸周书·周月解》亦云:“夏数得天,百王所同。”“夏数”即是夏代历法,说明夏历比较适合农时、符合天象。因此,中国的历法一开始就不是单纯地纪日、纪月、纪年,每一天,每一月,都有具体的农事。这种历法可以说是“农时”的代名词,也就是后来的农书。对中国古代天文历法有精深研究的张汝舟先生说得很明确:
中国古代“天文”与“历法”是一回事,它的对象虽也是天文,这与西方天文学是一致的,但观察的目的却是“观象授时”,这与西方天文学又有所不同了。两者不应混淆,混淆是有害的。[10](P13)
由于“观象”是为了“授时”,因此,中国历法中的二十四节气的出现具有一种必然性。
根据现代天文学者的研究,夏代可能是用立杆测影法来计量年月日。夏历以冬至后两月为孟春,作一年之始。干支记日一轮正好两个月。在这个阶段,古人用肉眼观测容易见到的参、大火、北斗、织女等星象,看它们于日出日落前后在天空的方位,来确定月份和季节,再参照气象、自然景物和物象来制定历法。[20](P95)《夏小正》载:“正月,鞠则见,初昏参中,斗柄悬在下。”意为:黄昏时,参星正好在正南方的上空,北斗的斗柄又指在正下方,这就是正月。《夏小正》正月记“越有小旱”,四月记“越有大旱”,七月记“时有霖雨”,这些已经把直接影响农作物生长的重大气象情况记述出来了。《国语·周语中》云:“《夏令》曰:‘九月除道,十月成梁。’”表明了夏代历法与农业生产生活的密切关系。
殷商时代,甲骨文“众”字是指众人劳作。大规模的农业生产必须了解季节时令,因此,商代的天文历法已经相当发达。现存的殷墟甲骨文中有月、日、年字,甲骨卜辞每条都记有日期。记日用干支,甲骨文中有完整的干支表。*可能在盘庚迁殷(约前1300年)之前就已经采用干支纪日。《春秋》记载的第一次日食发生在鲁隐公三年(前720年)二月己巳日,这次日食已被证实日期准确。由此证明,从春秋一直到清宣统三年,干支纪日2600余年,没有一日差错。关于天干地支的起源,有的学者认为,天干与羲和生十个太阳的神话有关,地支与常羲生十二个月亮的神话有关。[21](P65)记月用数字一、二、三……。十二月为一年,闰月为十三月。季节有“春”“秋”,没有“冬”“夏”。甲骨文中有连续10天的气象记录,为当时世界之最。卜辞中有对风雨、阴晴、雷、霾、雪、虹、霞的记载,其中,关于风有分大风、小风、大骤风、大狂风的不同,而卜雨的卜辞数量最多,据统计共有344条。[15](P386)除“雨”、“乃雨”、“亦雨”、“帝令雨”、“不雨”等,也有“大雨”、“多雨”之分。另外,还有不少卜辞卜问“旱”、“立黍”(商王是否要亲自莅临视察种黍或种黍)、“受(帝授)年(成)”、“受禾”、“保(帝保佑)年”等,以及大量关于耕耘、收割、节气与农事活动的卜辞。*例如:“贞:帝不降大旱。九月。”(《合集》10167)“月一正曰食麦。”(《合集》24440)[15](P409~422)根据常玉芝的研究,“殷人将一年分为春、秋两季。春季相当于殷历的十月到三月,即夏历的二月到七月,即农作物的播种、生长时期;秋季相当于殷历的四月到九月,即夏历的八月到一月,即农作物的收获时期。”据此,“气象卜辞证明殷历岁末岁首的交接是在夏季;殷历的岁首一月是种黍和收麦之月,即相当于夏历五月;殷人以‘大火’(即心宿二)昏见南中的夏历五月为岁首,即殷正建午。但由于殷人尚处在观象授时的历史阶段,还没有掌握置闰的规律,或是建巳,或是建未。”[15](P425~426)*她的结论也完全证明了关于夏代建寅、商代建丑、周代建子的“三正说”只是汉儒的臆造,纯属子虚乌有。杨向奎先生的研究也表明,商代历法的岁首实际上是不固定的。他说:“我国早期历法中,虽然季节月名有基本固定的关系,但岁首有一定的摆动。因此认为:商代历法的岁首很可能在主要农作物收获前后的秋季,即建申、建酉,含今立秋至寒露、霜降三个月中,这不仅符合武丁纪月的月食考订,也能解释许多纪月与季节有密切关系的农事、气象卜辞。”[22](P244)张汝舟先生经过对比发现,《夏小正》、《诗经·七月》和《月令》皆用殷正,《尚书·尧典》用的是夏正。[10](P597~598)由此可见,殷代历法是以与农作物的生长、收获季节相符合为依据的。
《尚书·尧典》曰:“日中星鸟,以殷仲春;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宵中星虚,以殷仲秋;日短星昴,以正仲冬。”这里的仲春、仲夏、仲秋和仲冬,即是春分、夏至、秋分和冬至。也就是说,在黄昏的时候,星鸟(心宿一)正好出现在南方中天,就是春分,这时的昼夜长度相等;大火(心宿二)出现于南方中天就是夏至,这时的白昼时间最长;虚(虚宿一)出现于南方中天则为秋分,这时的昼夜长度相等;昴出现于南方中天则为冬至,这时的白昼时间最短。用四组恒星于黄昏时在正南方天空的出现来规定季节,而且知道这四气在仲春、仲夏、仲秋、仲冬月份之中,这大概是古人关于春夏秋冬四季星象的最早思想。[2](P11)*也有人认为“日中”、“日永”、“宵中”、“日短”指二分二至。[23](P50)有学者认为:“战国秦汉间的四季仲月初昏中星,据《礼记·月令》与《吕氏春秋》记载,是孤矢、亢宿、牛宿、壁宿。这是战国秦汉间的天文历法现象,当时人抬头即见,容不得任何人作伪。而《尧典》四中星却是星宿、大火、虚宿、昴宿,它与战国秦汉四中星相比,各星向西后退了大约三十度。……中间就要经过2152.5年,这正是帝尧到战国秦汉之间的年数。由此可知,《尧典》中的历法材料,一定就是当时的历法天文材料,而不是战国秦汉人的作伪。”[24](P24)竺可桢曾认为,《尧典》四仲中星是殷末周初时候的天象。还有人认为,四仲中星是公元前2100年左右的天象。[4](P58~59)据《左传》记载,我国最早的冬至时刻的测定,是在春秋时代鲁僖公五年(前655年)正月辛亥和鲁昭公二十年(前522年)二月己丑,是用圭表测定的。[25](P82)这种知识最晚在商代末期形成。因为甲骨文中就有用来描绘春天南方中天初昏时天象的鸟星。《尚书·尧典》载:“朞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闰月定四时成岁。”表明一年366日、“四时成岁”以及闰月的概念已经十分明确。
西周时不仅对年月日有明确区分,还用十二地支来计时,把一天分为十二个时辰。干支纪时是秦汉以后在古代的十二时辰的基础上建立的。大概在周以前就发明了计时的仪器漏壶。《诗经》有很多诗篇将星辰的出没与季节变化和农业生产生活结合起来,例如《豳风·七月》、《召南·小星》、《陈风·东门之杨》、《唐风·绸缪》、《郑风·女曰鸡鸣》等。周人对月亮盈亏变化的规律的认识也相当清楚,用“初吉”、“既生霸”、“既望”、“既死霸”来描述月相。有关月相记录的甲骨和青铜铭文很多,例如,牧簋铭文:“七年三月既生霸甲寅”。周代已经发明了用圭测影的方法,能确定冬至(正午日影最长)和夏至(正午日影最短)。此前只能利用昏旦中星以及北斗的斗柄指向来定季节,这说明人们已经能够将太阳的周年视运动与星空背景直接联系起来,认识回归年的精确长度,准确制定二分二至等重要节气。
周代的历法还能够定出朔日。《诗经·小雅·十月之交》载:“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丑……”据推算,这一天是周幽王六年十月初一,这是我国第一次明确记载日食的记录。周代还渐渐发现了二十八宿,即把沿着天球赤道和黄道附近的星象划分为28个部分,由间接参酌月亮在天空的位置来推定太阳的位置而设立。因为星象在四季出没的早晚是不同的,反映了太阳在天空的运动,于是,就可以通过测定月亮的位置以推断太阳在星宿中的位置,从而确定一年的季节。*二十八宿的说法在西周时期还没有完善。现已证明,这个体系至迟是在战国早期完善起来的。[10](P16)其中的部分星宿名称在《诗经》和《夏小正》中有记载。《周礼》中的《春官》、《秋官》中都有二十八宿之说。到《吕氏春秋·有始》才最早给出了自角至轸的全部名称。竺可桢、钱宝琮、夏鼐认为,建立二十八宿的目的是为了观测月亮运动。正如《吕氏春秋·圜道》所言:“月躔二十八宿,轸与角属,圆道也。月行于天,约二十七日又三分之一天而一周,约日旅一星,经二十七日余而复抵原星,故二十八为宿舍之数,以记月亮所在位置。”中国、印度、阿拉伯和古巴比伦都有二十八宿之说。陈遵妫和日本学者新城新藏认为中国起源最早,与四季相关。新城新藏说:“二十八宿是在中国周初或更早的时代所设定,而在春秋中期以后自中国传出,经由中亚细亚传于印度,更传入波斯、阿拉伯等地方。”印度古代分冬春夏雨秋露六季,现在还分寒暑雨三季,与二十八宿不配合。根据岁差的计算表明,距今3500年之前,冬至在虚,夏至在星(七星),春分在昴,秋分在房,天球赤道正好与二十八宿中大部分星宿的位置相符合,即二十八宿大部分处于赤道附近。后汉时代,我国黄道坐标概念才得以形成。[25](P70)
春秋时期,人们发现木星约十二年(实际是11.8年)绕天一周,便以木星每年所在的位置纪年,称岁星纪年(因此称木星为“岁星”,又名摄提、重华、应星、纪星)。*金木水火土五星中最先被人们认识的是木星。这可能与它在一年中被人们看到的时间很长而且明亮有关。有人认为:大约在公元前20世纪以前,人们就知道木星是颗行星,12年绕天一周。周初已经用推算木星的位置来占卜。[25](P74)用木星进行占卜是巫术,与后来的占星学具有本质的不同。占星术也不同于古代的天地日月之神的崇拜,与这些祭祀活动有根本区别。后来又用太岁纪年,即假想一个与木星运行速度相等、方向相反的行星“太岁”,以它每年所在的位置纪年。*东汉建武三十年(54年)以后用干支纪年。[21](P65)《左传》僖公五年记载,僖公于冬至那天登台观看云色,并说当时“凡分、至、启、闭,必书云物,为备故也”。分是春分、秋分,至是夏至、冬至,启是立春、立夏,闭是立秋、立冬,说明当时已经知道这八个节气了。《吕氏春秋·十二纪》明确在孟春、仲春、孟夏、仲夏、孟秋、仲秋、孟冬、仲冬八个月中,分别安插立春、日夜分、立夏、日长至、立秋、日夜分、立冬、日短至这八个节气,这是一年的二十四个节气中最重要的八个节气。春秋后期出现了四分历,回归年的长度为365.25日,并用19年7闰为闰周。这是世界上当时最精确的历法。[2](P23)
在这样的情况下,二十四节气的产生应是水到渠成。第一次把二十四节气全部列出是《淮南子·天文训》(公元139年),其次序与今天完全一致。但这不是最早的文本,因为《管子》、《吕氏春秋》已有二十四节气的大部分名称,战国古六历包含了节气概念,秦统一时制定的颛顼历把历元定在立春,也证明二十四节气产生在秦统一之前。此外,《夏小正》中的节气有启蛰(惊蛰)、夏至、冬至。《逸周书·时训解》所记二十四节气,次序与今亦完全相同。这些可以说明,它的出现远在汉代之先。[26](P583)
二十四节气,即从冬至日开始,将一回归年等分为二十四分,以反映太阳在黄道上视运动的二十四个特定位置,从而反映出气候变化的情况。这是根据太阳的运行变化制定的,与月亮运行无关。这种特殊的历法,不仅表明了古人观测天体视野的广阔,更重要的是反映了农业生产在古人心目中的优先地位。因为二十四节气最根本的用处和意义是在农业生产方面。二十四节气是上古中国历法思想最典型、最集中的体现。中国早期的宇宙观和哲学意识也就自然生长于其中。正因为如此,明末清初的顾炎武《日知录》云:
三代以上,人人皆知天文。“七月流火”,农夫之辞也;“三星在户”,妇人之语也;“月离于毕”,戍卒之作也;“龙尾伏辰”,儿童之谣也。
中国早期历法的这种根本性质贯穿在整个中国古代社会,同时也决定了古代任何帝王在试图通过历法强调自己的统治理念时,都不能无视这种根本性质。因此,上古的重农思想与皇权意识在历法中似乎是一体的。许倬云先生认为:“古代文献资料中,‘藉’是与农业有关的行事,其来源可能甚早。《夏小正》中的藉,列在正月,可算是农事之始。”[27](P283~284)*占星学出现以后,这种思想有了改变,比较一下可以看出其中的变化。“藉”也见于金文铭辞中。《国语·周语上》有王室藉礼的详细说明:
先时(立春前)九日,太史告稷曰:“自今至于初吉(二月朔日),阳气俱蒸,土膏其动。弗震弗渝,脉其满眚,榖乃不殖。”稷以告王曰:“史帅阳官以命我司事曰:‘距今九日,土其俱动,王袛祓,监农不易。’”王乃使司徒咸戒公卿、百吏、庶民,司空除壇于藉,命农大夫咸戒农用。先时(立春前)五日,瞽告有协风至,王即斋宫,百官御事,各即其斋三日。王乃淳濯饗醴,及期,鬱人荐鬯,牺人荐醴,王祼鬯,饗醴乃行,百吏、庶民毕从。及藉,后稷鉴之,膳夫、农正陈藉礼,太史赞王,王敬从之。王耕一墢,班三之,庶民终于千亩。其后稷省功,太史监之;司徒省民,太史监之;毕,宰夫陈饗,膳宰监之,膳夫赞王,王歆大牢,班尝之,庶人终食。
另外,《诗·豳风·七月》云:“三之日于耜,四之日举趾。”这可能不仅记载单纯的下田工作,也可能指涉初耕的仪礼。最后的“跻彼公堂”就是祭祀和飨礼。《诗经》中的《小雅·甫田》、《小雅·大田》、《周颂·载芟》、《周颂·良耜》、《周颂·臣工》和《周颂·噫嘻》等都描写田间生活,包括王公大臣。统治者不仅认识到不违农时,而且在农忙时采取措施保护耕作、不兴土工、不作师旅,庶民“不冠弁、娶妻、嫁女、享祀”等。[26](P594)这个传统一直延续到清末,贯穿了整个中国封建社会的始终。
五
中国上古天文学的主要目的是指导农耕生活,但《史记·天官书》、《汉书·天文志》为何成为了占星学?我认为大约从春秋末战国初开始,中国天文学发生了一个根本转折:即从“治历明时”走向“占星祈禳”,试图用天象反映人间社会的等级制度,论证人间帝王统治的合法性。因此,这期间的天文学把星叫做“星官”,凡星都是“官”。《史记·天官书》唐司马贞《索隐》曰:“星座有尊卑,若人之有官曹列位,故曰天官。”这就在“四象”之后出现了“分野”、“三垣”的说法。占星学由此应运而生。
“四象”是把二十八宿分为四组,并以动物形象名之,故曰四“象”,即东方苍龙、西方白虎、南方朱雀、北方玄武(龟)。人们发现,每组星象确实与以之称名的动物很像。有人认为,《尚书·尧典》关于四仲中星的说明,产生了把周天恒星分为四群以分别表示春夏秋冬四季星象的思想。因此,人们很容易想像,“春分前后初昏时当朱雀升到南方中天(上中天)时,苍龙的房宿正处于东方的地平线附近;白虎的昴宿正处于西方的地平线附近;而龟蛇的虚宿正处于地平线下与朱雀的七星相对的北方(下中天)。这是就定东、西、南、北四个方位的由来,它是以古代春分前后初昏时的星象为依据的。”[25](P66)可以看出,“四象”说还属于比较纯粹的天文学,与占星学没有明显的关系。陈遵妫先生认为,“四象”的出现应在二十八宿之前。因为角、心、尾就是东方苍龙的龙角、龙心和龙尾。“四象”的名称来源可能更早。[28](P330)*《礼记·礼运》曰:“麟凤龟龙,谓之四灵。”《十三经注疏》云:“前朱雀而后玄武,左青龙而右白虎。”后来把麒麟换为白虎,有人称与孔子作《春秋》到获麟为止相关。“麟为周亡天下之异。”所以,后人以山兽之君“虎”代替。《礼运》孔疏引:“龙东方也,虎西方也,凤南方也,龟北方也,麟中央也。”西方为白虎,麟在中央。湖北随县的曾侯乙墓(前433年左右)中有一漆器箱盖,会有二十八宿图案,东方绘有青龙,西方绘有麟。可见在汉代麟才换成白虎,而二十八宿在当时已是很普遍的知识,“四象”的知识可能还会更早。
“分野”是用天上的列宿对应地上的封国。《左传·昭公元年》所说的高辛氏长子閼伯迁于商丘,主辰,故辰为商星,次子实沈迁于大夏,主参,故参为晋星。由此可见,星辰与地域已有关联。后来共有十二分野之说,几乎每一列国对应天上一个星宿。这个观念一般认为出现在二十八宿之后。*徐振韬、蒋窈窕先生认为,十二次分野大概是在战国时代形成的。[12](P20)《周礼·春官·保章氏》曰:“以星土辨九州之地所封,封域皆有分星,以观妖祥。”由此可见,分野已经与占星有关。
如果说“四象”中有苍龙、麟、凤等神话中的动物,这实质上还是关于天象的纯粹描述,“分野”把星辰和地域联系起来,表明了一种天人生活同构的雏形,而“三垣”则完全反映了统治阶级的观念。“三垣”即紫薇垣、太薇垣、天市垣,把位于二十八宿以内的恒星分为三大块。紫薇垣是天上皇宫的意思,其中有帝星、帝后星、群妃星、三公星、太子星等;太薇是天上政府的意思,有将星、相星、诸侯星;天市是天上都市的意思,有主管秤权交易和商人的宦者星、宗正星、宗人星、客星等。紫薇垣和天市垣见于《开元占经》辑录的《石氏星经》,大约出现于战国时代。太薇垣初见于唐初的《玄象诗》。[29]这即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名副其实的占星学,或者也可以说“政治天文学”。
在当时的天文学中,以甘德、石申、巫咸三大学派影响最大。
传说巫咸是殷代大臣,史载的《巫咸星经》为我国最早的星表,据说含33座共144星,但原本亡佚,后世存本列齐、赵国名,显然属于伪托。有人认为,西周巫咸学派为宋国司星继承,巫咸祒(字子韦)是其代表,《庄子·天运》中有“巫咸祒”,即是证明。[25](P58)甘德活动于战国时期,或为楚人,或为鲁人,作《天文占星》八卷,亡佚。石申是魏国司星,开封人,活动约在前4世纪战国中期,作《天文》八卷,但早已亡佚。虽然甘德和石申的原著亡佚,但从《史记》、《汉书》和引文中可知一二。后人拾遗补阙,把石申的《天文》与甘德的《天文星占》合并,该书在宋代称《甘石星经》,又名《星经》,托名为“汉甘公、石申著”,始见于晁公武《郡斋读书志》的著录,曾收入《道藏》,题名为《通占大象历呈经》,流传至今,是一部对天文研究有很高的科学价值的文献。
从本质上说,此时的天文学家已成为占星家。虽然他们掌握了丰富的天文学知识,但他们是用天象知识为各国国君服务,实际上就是运用占星学来服务于各国国君,因此,天文学在性质上发生了根本转变。占星内容涉及到用兵、立嗣、农桑、祭祀等众多国家大事。例如,《左传》襄公二十八年记载,梓慎发现当年的岁星应在星纪,却到了玄枵(实际是由于木星运行的误差所至),这即是春行夏令,由此,他预言郑国和宋国要发生饥荒。据《国语·晋语四》载,晋国史官董因根据天象预测重耳可以成功继承君位。《国语·周语下》还说到武王伐纣的天象有利,故能成功。汉代《淮南子·兵略》也说到这件事,其实都是附会。
占星家最关注的天象,首先是日食、月食和彗星这些历来被认为是不祥的天象。日食这时已经被占星学家说得玄乎其玄。据《开元占经》记载:“甘氏曰:‘日始出而蚀,是谓无明,齐、越受兵,一曰亡地。’甘氏曰:‘日中而蚀,荆魏受兵,一曰亡地,海兵大起。’甘氏曰:‘日将入而蚀,大人出兵,赵燕当之,近期三月,远期三年。’”[30](P132)只要出现日食,都与兵灾和亡国失地有关。
此外就是关于五星的运行状况。金木水火土五星,又被称为五纬,与东南西北中的方位相连,这些观念都应该在阴阳五行说之后产生。前述之夏代关于五星相聚的记录没有这些说法。《汉书·天文志》云:“古历五星之推,亡逆行者,至甘氏、石氏《经》,以荧惑、太白为有逆行。夫历者,正行也。古人有言曰:‘天下太平,五星循度,亡有逆行。日不食朔,月不食望。’……甘、石氏见其常然,因以为纪,皆非正行也。”这说明甘德、石申对五星规律的观测有着重要发现,同时,他们关于五星的占辞也很多。例如:
甘氏曰:“五星主兵,太白为主。五星主谷,岁星为主。五星主旱,荧惑为主。五星主土,填星为主。五星主水,辰星为主。五星木土以逆为凶,火以钩已为凶,金以出入不时为凶,水以不效为凶。五凶并见,其年必恶。”
石氏曰:“五星不失行,则年谷丰昌。”
石氏曰:“五星行二十八舍星七寸以内者及宿者,其国君死。五星舍二十八宿,王者诛除其国。五星犯合宿中间星,其坐者在国中,犯南为男,犯北为女,东为少,西为老。五星逆行去宿虽非七寸内而守之者,其国君被诛刑死,顺而留之,疾病死。”*见《开元占经》卷十八。[30](P142,144~145)另:马王堆出土的西汉帛书《五星占》和《云气星象杂占》表明,当时对五星会合周期的了解已经相当准确。其中,《五星占》包括占文和表格共6千多字。[18](P350)
占星家们把五星的运行状况看作国家兴亡的预兆,后来史家经常以此附会。为了给刘汉王朝罩上神秘色彩,《汉书·高帝纪上》云:“元年冬十月,五星聚于东井,沛公至霸上。”现代天文学证实,这次五星聚合的天象发生在第二年五月,属故意捏造。《史记·天官书》亦云:“汉之兴,五星聚于东井。”《史记·张耳陈余列传》仍说此事:“汉王之入关,五星聚东井。东井者,秦分也,先至必霸。楚虽强,后必属汉。”由此可见,王朝更替的合法性要获得占星学的证明。1995年,在新疆民丰县尼雅遗址的一座东汉至魏晋墓葬中出土了一件色彩鲜艳的五色织锦,上绣“五星出东方利中国”。长沙马王堆出土的帛书《五星占》保留了秦汉之际关于五星的占星学宝贵资料。*徐振韬、蒋窈窕:《五星聚合与夏商周年代研究》附录二“中国古代五星会聚记录”,统计了远古至清乾隆六十年各种史籍关于五星聚合的记载,其中很多是当作祥瑞。
这种情况到了战国末期就很严重了。秦始皇的阿房宫就是按照天上的星象建造的。而《月令》是按天象给天子设计每月移动的住处。由此可见,占星学对当时的政治生活和学术思想产生了巨大冲击。
六
春秋战国之际,中国天文学界为什么出现了这样的现象?《史记·历书》云:
幽、厉之后,周世微,陪臣执政,史不记时,君不告朔,故畴人子弟分散,或在诸夏,或在夷狄……
《汉书·律历志》所载与此略同:
三代既没,五伯之末史官丧纪,畴人子弟分散,或在夷狄……
这就是说,东周以降,天文历算学者从周王室分散外流。各国诸侯却因争夺称霸,招揽人才。这是中国古代天文学向占星学转折的一个重要条件和原因。然而,在周王室的天文学人才散入各诸侯国的时候,占星学为什么会蓬勃兴起呢?我们还必须回到上古先民的原始自然崇拜和巫术活动中来考察这个问题。
鉴于中国文明的特点,“观象授时”的史官应该自古有之。然而,在早期先民的原始崇拜和巫术活动中,观天象与原始崇拜和巫术不是完全无关的。现有资料证明,用龟甲、牛骨作占卜材料早在新石器时代就有。《史记·龟策列传》云,“三代”以上的占卜不可记,三代以下皆以卜筮以决疑。占卜之人称史、卜、祝。殷商甲骨文中的“贞人”即占卜者,是具有巫史双重身份的人。贞人可能还懂医术,掌握文字,有丰富的社会知识。*而在我国的部分少数民族中,用骨、木、竹等占卜延至近代。[31](P2,146)1973年,在藁城台西商代遗址发现植物种子三十余枚,其中有桃仁和郁李仁,是治病的药物。灸、刺和按摩的治病方法已经存在。上古刺即用石针,殷商时应是青铜针。“殷高宗武丁一朝,五十九年之间殷人之病,凡有头、眼、耳、口、牙、舌、喉、鼻、腹、足、趾、尿、产、妇、小儿、传染等十六种,具备今日之内、外、脑、眼、耳、鼻、喉、牙、泌尿、产妇、小儿、传染诸科。”[32](P308,314)在这些古代巫术中就有一种星占的活动。《国语·楚语》曰:颛顼“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属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属民,使复旧常,无相侵渎,是谓绝地天通。”这里是说,让重和黎分别负责天上星辰和地上人民的事务,不让老百姓直接和天上星辰交往、沟通。意思是把上天的意志垄断起来,不让老百姓知道。这表明了古代先民有关于星辰的崇拜和巫术等祭祀活动。
上古先民对待水旱灾害和疾病瘟疫,只能用巫术祛除。这些巫术有傩、雩、禜、酺等。*金景芳先生说:“用傩、雩、禜、酺的办法来对待水旱疾疫,虽然最早只见于周代文献,但不能即认为是周人创始,它也应有长远的历史,在这里保存着原始时代‘魔术’的遗迹。”[33](P58)其中,禜是一种对星神的祭祀活动,可能与星占有关。《礼记·祭法》云:“幽宗,祭星也。”郑玄注:“宗皆当为禜,字之误也。幽禜,星坛也。星以昏始见,禜之言营也。”《周礼·春官·大祝》云:“掌六祈,以同鬼神亓(礻)……四曰禜……”《左传》昭公元年云:“山川之神,则水旱疠疫之灾于是乎禜之;日月星辰之神,则雪霜风雨之不时,于是乎禜之。”(子产语)《左传》哀公六年云:“是岁也,有云如众赤鸟,夹日以飞三日。楚子使问诸周大史,周大史曰:‘其当王身乎!若禜之,可移于令尹、司马。’王曰:‘除腹心之疾,而置诸股肱,何益?不榖不有大过,天其夭诸?有罪受罚,又焉移之?’遂弗禜。”(楚昭王语)杜注:“禜,禳祭。”这些资料说明,禜可能是一种与星占相关的巫术。
甲骨文中也有关于星占的记载。如前文所述,在出土的甲骨文中,发现由“星”字组成的词有“其星”、“不(或毋)其星”、“大星”、“鸟星”、“新星”(或“新大星”)。其意义一是指天晴,一是指星辰。殷墟甲骨文记载的月食有五次,这是定论。[15](P9~20)这说明殷人对这些特殊天象的关注和解释,其中不乏星占的思想和观念。
同时,《易经》和《诗经》中亦可发现星占的资料。例如,《离卦》九三爻辞曰:“日昃之离,不鼓缶而歌,则大耋之嗟,凶。”“日昃”指太阳偏西。“日昃之离”的意思是:太阳在西方附丽于天空,不久将落下,如同人之暮年,故要击鼓缶而歌。而高亨《周易大传今注》曰:“离,读为螭。”即螭龙,云气形成龙,谓之霓。螭、霓一声之转。其意思是:太阳偏西时有霓出现在天空,是个凶兆,老年人悲叹,故击鼓缶歌唱禳解之。《丰》卦辞曰:“亨,王假之,勿优,宜日中。”六二爻辞曰:“丰其蔀,日中见斗,住得疑疾,有孚,发若吉。”九四爻辞曰:“丰其蔀,日中见斗,遇其夷主,吉。”“日中”是正午。“斗”即北斗。卦辞的意思是:祭祀仪式可在正午举行,不必忧虑。这也是从天象看吉凶。*闻一多对《乾》卦进行研究,认为乾卦整体是北斗星的表征,各爻是东宫苍龙所代表的龙马,拉着帝车在天空运行。《睽》卦上九爻辞:“睽孤,见豕负涂,载鬼一车,先张之狐,后说之狐,匪寇婚媾,往遇雨则吉。”[34](P3)
《易经》还有用月亮卜筮吉凶的。《小畜》上九爻辞曰:“既雨既处,尚德载。妇贞厉。月几望,君子征凶。”“月几望”就是月既望,为月满过后的月象,月望后至下弦前的一段日子。这是因为古人视月食不祥。已知月食必发生在望,望日在十五前后发生。因此,他们把月望作为可能的凶日。望后就没有月食,比较安全。《归妹》六五爻辞曰:“帝乙归妹,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月几望,吉。”出家时在月几望,即月望之后,因此吉。《中孚》六四爻辞曰:“月几望,马匹亡,无咎。”月既望时,马匹丢失,但无咎。[34](P3~5)《诗·小雅·十月之交》不仅描绘了日食和月食,还有“日月告凶,不用其政”之说,也是把日食和月食看作不祥的天象。
上古这些原始崇拜和巫术活动,具有深厚的社会土壤和广泛的应用范围,与人们的日常生活不可分割,因此成为一种文化和观念深深扎根于人们的意识中。西周以后,有所谓周公“制礼作乐”之说,人们逐渐崇尚理性,因此,这些上古时期的星占遂与其他巫术一样式微。但孔子说过:“鳯鸟不至,河不出图,吾已矣夫。”(《论语·子罕》)听说“西狩获麟”,令他悲愤、感慨不已。一方面说明,即使像孔子这样伟大的思想家对这些远古的宗教、巫术也深信不疑;另一方面也说明,这些原始崇拜和巫术像一股潜流,仍然涌动在当时的社会生活之中。到了春秋战国之际,诸侯争霸,这些本来潜伏在社会生活底层的原始遗存被一些“畴人子弟”重新整理起来,与日渐发达的天文学知识相结合,从而形成了占星学的大气候,对当时的政治、思想和学术产生了重大影响。因此,原始的宗教崇拜和星占巫术可能是占星学兴盛的一个源头。五星聚合、日月食和彗星等都是奇异的天象,容易引起人们的附会和猜测。
应该特别强调的是,这些星占活动原来只是原始巫术活动的一种,与占星学无关。它只是给后来的天文学家以启示和灵感,天文学家运用新的天文学知识对这些特殊的天象进行解释,从而形成占星学。
中国古代天文学向占星学的转折,不仅是中国古代天文学的重大变革,也是中国古代思想史上的一件大事。我认为,这个事件与邹衍的阴阳五行学说的出现之关系密不可分,并以此为标志。[35]
七
《国语·周语下》记载了伶州鸠叙述周朝姬氏的祸福与星相的运行关系,并涉及上古五帝,这基本属于传说。但其中说到武王伐纣的天象有利故能成功的事迹,因此留下了可以考证的空间。
武王伐纣的史实究竟如何?是否符合伶州鸠的描述?通过对相关史籍中关于武王伐纣的记述与伶州鸠的描述进行比较,就可以看到占星学发展的清晰轨迹。
(伶州鸠)曰:“昔武王伐殷,岁在鹑火,月在天驷,日在析木之津,辰在斗柄,星在天鼋。星与日辰之位,皆在北维。颛顼之所建也,帝喾受之。我姬氏出自天鼋,及析木者,有建星及牵牛焉,则我皇妣大姜之侄伯陵之后,逄公之所凭神也。岁之所在,则我有周之分野也。月之所在,辰马农祥也。我大祖后稷之所经纬也,王欲合是五位三所而用之。自鹑及驷七列。南北之揆七同,凡人神以数合之,以声昭之。数合声和,然后可同也。故以七同其数,而以律和其声,于是乎有七律。”(《周语下》)
“岁在鹑火,月在天驷,日在析木之津,辰在斗柄,星在天鼋。星与日辰之位,皆在北维”都是占星学内容。伶州鸠说的“岁”指岁星,意即岁星当空,利于征伐。这个故事被后来的学者经常引用,《战国策·赵二》载张仪语云:“愿以甲子之日合战,以正殷纣之事。”汉代《淮南子·兵略》曰:“武王伐纣,东面而迎岁,至汜而水,至共头而坠,彗星出而授殷人其柄。”
武王伐商的时间一直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重要问题。在现存的相关史料中,一个最重要的证据是1976年出土于陕西临潼的一件西周早期的青铜器利簋,又名武王征商簋。此器现收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簋腹内底铸有极为宝贵的铭文,共4行32字:
珷征商唯甲子朝岁鼎克闻夙有商辛未王在管师锡又事利金用作檀公宝尊彝
一般解读为:武王征伐商纣,甲子日早晨,岁星当头,贞卜能克,灭亡了商。辛未日武王在阑地,赏赐青铜给右史利,用作制造檀公宝尊彝。
这段铭文的重要意义在于印证了《尚书·牧誓》、《逸周书·世俘》及《史记·周本纪》等古代文献中关于武王伐纣在甲子日的记载,与史书文字几乎完全吻合。右史利因参与克商之役受赐而作此器,时间又是在武王克商后的第八天,故利簋是现存最早的一件西周青铜器,可以说是这场中国古代史上划时代变革的现场记录。然而,铭文所说的甲子日凌晨岁星当头宜于征伐,这只是一种星占,是占卜的一种,与龟占、卜筮属于一类,而非后来的占星学。上节我们对此区分作了详细论述,因此与伶州鸠所说的含义完全不同。
尤其值得引起我们进一步讨论的是,把铭文中的“岁”解读为“岁星”,是以张政烺先生为代表的学者的观点,虽然这种解释影响广泛,但疑难很多。第一,“岁”在甲骨和西周金文中当作岁星的解释至今未见,故难成立。第二,把“岁”释为岁星,接下来的“鼎”就要训为“丁”,义为“当”,意即“岁星当其位”,而“鼎”字这种解释在钟鼎彝器中也没有例证,难以成立。
因此,有人认为,把铭文中的“岁”解读为岁星是不能成立的。而如果把“岁”释为“岁祭”,可能更符合铭文原义。因为,第一,从甲骨到金文,用“岁”作岁祭的例证不可胜数。第二,把“岁”解读为岁祭,“鼎”则可训为“贞”,王国维认为贞鼎二字“自古通用”。这样解释文义既有训诂证据,符合文法,非常通畅,又符合早期史书的记载。[36]*黄德宽教授认为,“岁”应解释为岁祭。岁祭由史官利主持,得大吉。武王克商之后,作为对祭祀史官的奖励,赐他铸簋以志。这种解释非常符合情理。而按照思想史发展的逻辑来说,我也认为这里的“岁”应该是“岁祭”,而不是“岁星”。如果我们把铭文“岁”释为“岁祭”,原文应读为:
珷征商,唯甲子朝,岁,鼎(贞):克闻(昏),夙有商。辛未,王在管师,锡(赐)又(右)事(史)利金,用作檀公宝尊彝。
大意为:武王征伐商纣,在甲子日早晨,岁祭,贞卜黄昏时能克,遂灭亡了商。辛未日武王在管师,(因占卜有功)赏赐青铜给右史利,用作制造檀公宝尊彝。
这里依然未见与占星学有丝毫关系。
更值得注意的是,上述史籍中都没有提及“岁星当空”之说:
时甲子昧爽,王朝至于商郊牧野,乃誓。(《尚书·牧誓》)
越若来二月既死魄,越五日甲子,朝至,接于商,则咸刘商王纣,执天恶臣百人。(《逸周书·世俘》)
二月甲子昧爽,王朝至于商郊牧野,乃誓。(《史记·周本纪》)
对比原始的资料,所谓“岁星当空”应是空穴来风。即使对占星学极为崇信的司马迁在《史记·周本纪》中也没有提及。
上述两种解释都说明,利簋铭文中没有占星学的内容。由此可以得出两点结论:
第一,伶州鸠的说法只能是后来者臆造的。这也恰好证明,占星学家为了宣扬他们的学说,采取了对上古历史进行占星学的篡改和虚构的事实。因此,《史记·天官书》和《汉书·艺文志》所述的上古占星学和占星家的历史也完全属于虚构。*1996年国家启动了夏商周断代工程,历史学、考古学、天文学和物理学家们通过分析研究史料、对相关遗物进行碳14测定,同时根据天文现象推算等艰苦细致的考证研究之后,得出武王克商的确切年代是公元前1046年1月20日,而这一天正是甲子日。但其天文依据仍然把利簋铭文“岁”释为岁星,并采用《周语》伶洲鸠“岁在鹑火”的说法,因此留下了巨大疑问,令人质疑。[13](P44~49)
第二,至少在伶州鸠说话时的春秋晚期,即周景王二十三年(昭公二十年,公元前522年),占星学已经大行其道,成为流行观念了。*此外,伶州鸠在叙述了武王伐纣的天象之后,接着说周朝得天象的依据是“颛顼之所建也,帝喾受之。我姬氏出自天鼋,及析木者,有建星及牵牛焉,则我皇妣大姜之侄伯陵之后,逄公之所凭神也”。基本上与早期传说混为一体了。这样的叙述在《国语》中并不少见。例如,《楚语》云:颛顼“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属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属民,使复旧常,无相侵渎,是谓绝地天通”。这也是记载了一种古代传说。由此可证,《国语》的很多文字成文较晚,所记人物很多是后人补记,不可全信。
八
从《左传》、《国语》等典籍的记载中,我们可以看到从星占巫术到占星学的一些发展轨迹。《左传》中涉及天象与占星学内容的资料如下:
春,无冰。梓慎曰:“今兹宋、郑其饥乎?岁在星纪,而淫于玄枵。以有时灾,阴不堪阳。蛇乘龙,龙,宋、郑之星也。宋、郑必饥。玄枵,虚中也。枵,耗名也。土虚而民耗,不饥何为?”(襄公二十八年)
夏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晋侯问于士文伯曰:“谁将当日食?”对曰:“鲁、卫恶之。卫大,鲁小。”(昭公七年)
史赵曰:“陈,颛顼之族也。岁在鹑火,是以卒灭,陈将如之。今在析水之津,犹将复由。”(昭公八年)
夏四月,陈灾。郑裨竈曰:“五年陈将复封,封五十二年而遂亡。”子产问其故。对曰:“陈,水属也;火,水妃也。而楚所相也。今火出而火陈,逐楚而建陈也。妃以五成,故曰五年,岁五及鹑火,而后陈卒亡,楚克有之,天之道也。故曰五十二年。”(昭公九年)
春,王正月,有星出于婺女。郑裨灶言于子产曰:“七月戊子,晋君将死。”(昭公十年)
冬,有星孛于大辰,西及汉。申须曰:“彗所以除旧布新也。天事恒象,今除于火,火出必布焉。诸侯其有火灾乎?”梓慎曰:“……若火作,其四国当之,在宋卫陈郑乎!……”郑裨灶言于子产曰:“……若我用瓘斝玉瓒,郑必不火。”(昭公十七年)
(梓慎)曰:“二至二分,日有食之,不为灾。日月之行也,分,同道也;至,相过也。其他月则为灾,阳不克也,故常为水。”(昭公二十一年)
夏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梓慎曰:“将水。”昭子曰:“旱也。日过分而阳犹不克,克必甚,能无旱乎?……”(昭公二十四年)
(史墨)曰:“六年及此月也,吴其入郢乎,终亦弗克。入郢必以长庚,日月在辰尾。庚午之日,日始有谪。火胜金,故弗克。”(昭公三十一年)
夏,吴伐越。……史墨曰:“不及四十年。越其有吴乎!越得岁(指木星)而吴伐之,必受其凶。”(昭公三十二年)[17]
《春秋》一书纪事长达241年。《左传》纪事至鲁哀公二十七年,前后共计254年。笔者大略统计,《左传》真正提到占星学内容的只有上述十处。其中,昭公十七年记申须对彗星出现的解释语“天事恒象”,即天的意志一定要通过天象表达出来,是引起后来学界极为关注的思想,为众多学者经常引用。《左传》提到的占星家有梓慎、士文伯、史赵、郑裨竈、史墨等人。从《左传》可以看出,与占星学相关的内容最早出现在鲁襄公二十八年,在鲁昭公以后才开始进入人们的视域之中,引起人们的关注,但还没有形成强势。
《国语》与占星学相关的内容如下:
范蠡曰:“人事必将与天地相参,然后乃可以成功。”“臣闻古之善用兵者,(嬴)【赢】缩以为常,四时以为纪,无过天极,究数而止。天道皇皇,日月以为常,明者以为法,微者则是行。阳至而阴,阴至而阳;日困而还,月盈而匡。古之善用兵者,因天地之常,与之俱行。后则用阴,先则用阳;近则用柔,远则用刚。后无阴蔽,先无阳察,用人无艺,往从其所。刚(柔)【彊】以御,阳节不尽,不死其野。彼来从我,固守勿与。若将与之,必因天地之灾,又观其民之饥饱劳逸以参之。尽其阳节、盈吾阴节而夺之。宜为人客,刚彊而力疾;阳节不尽,轻而不可取。宜为人主,安徐而重固;阴节不尽,柔而不可迫。凡陈之道,设右以为牝,益左以为牡,蚤晏无失,必顺天道,周旋无究。”“圣人之功,时为之庸。得时不成,天有还形。天节不远,五年复反,小凶则近,大凶则远。”(《越语下》)
内史过归,以告王曰:“……夫天事恒象,任重享大者必速及……”(《周语上》)
(单子)曰:“夫辰角见而雨毕,天根见而水涸,本见而草木节解,驷见而陨霜,火见而清风戒寒。故先王之教曰:‘雨毕而除道,水涸而成梁,草木节解而备藏,陨霜而冬裘具,清风至而修城郭宫室。’故《夏令》曰:‘九月除道,十月成梁。’其时儆曰:‘收而场功,偫而畚梮,营室之中,土功其始。火之初见,期于司里。’此先王所以不用财贿,而广施德于天下者也。”(《周语中》)
(单襄公)曰:“……天六地五,数之常也。经之以天,纬之以地。经纬不爽,文之象也。”(《周语下》)
献公问于卜偃曰:“攻虢何月也?”对曰:“童谣有之曰:‘丙之晨,龙尾伏辰,均服振振,取虢之旗。鹑之贲贲,天策焞焞,火中成军,虢公其奔!’火中而旦,其九月十月之交乎?”(《晋语二》)
子犯曰:“……天事必象,十有二年,必获此土。”(《晋语四》)
姜曰:“……吾闻晋之始封也,岁在大火,阏伯之星也,实纪商人。商之饗国三十一王。瞽史之纪曰:‘唐叔之世,将如商数。’”(《晋语四》)
(董因)曰:“岁在大梁,将集天行。元年始受,实沈之星也。实沈之墟,晋人是居,所以兴也。今君当之,无不济矣。君之行也,岁在大火,阏伯之星也,是谓大辰。辰以成善,后稷是相,唐叔以封。瞽史记曰:嗣续其祖,如榖之滋,必有晋国。”(《晋语四》)
《国语》所涉及的占星学内容谨录于此,加上节所述《周语下》共十处。*《周语上》记:“幽王二年,西周三川皆震。伯阳父曰:‘周将亡矣!夫天地之气,不失其序;若过其序,民乱之也。阳伏而不能出,阴迫而不能烝,于是有地震。今三川实震,是阳失其所而镇阴也。阳失而在阴,川源必塞;源塞,国必亡。夫水土演而民用也。水土无所演,民乏财用,不亡何待?昔伊、洛竭而夏亡,河竭而商亡。今周德若二代之季矣,其川源又塞,塞必竭。夫国必依山川,山崩川竭,亡之征也。夫天之所弃,不过其纪。’是岁也,三川竭,岐山崩。十一年,幽王乃灭,周乃东迁。”在这里,伯阳父用阴阳二气失调来解释地震的原因,也不属于占星学。但这里的情况却与《左传》大不相同,一是占星学思想比较成熟,二是出现年代比较早。此外,《周语上》亦有“天事恒象”之说,与《左传》昭公十七年申须所言完全一样,《晋语四》还有“天事必象”之说。
在《左传》和《国语》中同时记录了“天事恒象”这个术语,表明这样的术语应该有一个共同来源,同时也表明这个术语已经进入了人们的日常生活,人们对之耳熟能详,随时运用,因此,这个术语实则已经是一个成语。这个成语的出现也恰好证明,占星学的观念在这个时期已经流行。《左传》记载这个术语的年代是昭公十七年(公元前525年)。而《国语》记载的说话人内史过是周惠王(前679~前655)、襄王(公元前654~前620)时人,子犯是晋文公(公元前639~前630)时人,比《左传》的年代早一百年以上。《左传》与《国语》的记载年代相差一个多世纪,因此很难同时为真。参照伶州鸠所述武王伐纣的时间,即周景王二十三年(昭公二十年,公元前522年),《左传》记录这个术语的时间(昭公十七年,公元前525年)应该是可靠的。也就是说,大约在昭公十七年的时候,占星学的观念已经比较流行了。据此我们可以判断,早于这个时间的其他关于占星学的说法,基本上都是后人杜撰的,纯属附会。
《左传》全名《春秋左氏传》,其作者一般被认为是与孔子同时代的左丘明。《国语》被《汉书·艺文志》称为《春秋外传》,司马迁又说:“左丘失明,阙有《国语》。”因此,汉唐以降都认为《左传》和《国语》的作者为同一人,即左丘明。近代学者对此说置疑,认为《国语》可能是当时各国史乘的原始记录。笔者无意于对此问题追根究底,但通过以上辨析,说明《左传》与《国语》的作者是同一人的可能性很小,成书的年代也可能属于不同时期。
从甲骨文关于“星”的卜辞,到《诗经·七月》(包括《小雅·十月之交》),以及《夏小正》,再到《左传》、《国语》,这些文献资料都比较清晰地展示了中国古代天文学向占星学转变的大致发展轨迹。
九
上文大略论证了在春秋末战国初发生的中国天文学向占星学的根本转折。通过了解这个转折,我们不仅可以知道中国古代天文学与占星学的基本界限,同时还会发现上古思想发展的一个重要轨迹,更为重要的是,我们还可以由此探索这种思想史的转变对当时中国学术的影响。
战国以降的这种与阴阳五行说合为一体的占星学在汉代达到全盛。司马谈在《论六家之要指》中把阴阳家列为六家之首,称之以“阴阳四时、八位、十二度、二十四节各有教令”,“大祥而众忌讳”。司马迁对盛行的占星学作了总论性质的概括,《史记·天官书》则是最早的全面而系统地描述全天星官的著作,也可谓集占星学之大成。《汉书·天文志》开篇曰:
凡天文在图籍昭昭可知者,经星常宿中外官凡百一十八名,积数七百八十三星,皆有州国官宫物类之象。其伏见蚤晚,邪正存亡,虚实阔陿,及五星所行,合散犯守,陵历斗食,彗孛飞流,日月薄食,晕适背穴,抱珥(工虫)蜺,迅雷风祅,怪云变气:此皆阴阳之精,其本在地,而上发于天者也。政失于此,则变见于彼,犹景之象形,郷之应声。是以明君睹之而寤,饬身正事,思其咎谢,则祸除而福至,自然之符也。
《汉书》还首立《五行志》,专载五行灾异,例如日食、月食、地震等,以及天人感应。在战国列国纷争、风云变幻的局面中,占星学应运而生以后,一个《月令》这样新型的天人模式就被构建出来了。尽管如此,司马迁还是把《天官书》和《历书》区分开来,这表明占星与历法之间仍然是有区别的。
自此以后,中国古代的占星学异常繁荣。《隋书·经籍志》所载天文书共97部,675卷;历书100部,263卷。今日出土的汉代帛书即有《五星占》之类。这些天文书实质上与占星学已成一体,其著述繁富,可见一斑。
我们发现,经过汉人整理的古代典籍,有些明显地留下了这种占星学和阴阳五行学说的深深印记。汉代经学中不但程度不同地羼杂了这种占星学与阴阳五行混合的思想,甚至在根本上受到了占星学观念的支配,其中,“观象于天,法类于地”的占星学思想甚至成为了《易传》的核心观念,而《春秋》公羊学大家董仲舒,把先秦儒学与阴阳五行学说结合起来,提出了天人感应学说,其在中国历史上影响巨大而深远。由此可见,占星学对秦汉以后的中国思想、学说和政治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
但是,思想界反对这种占星学的声音从来不绝于耳,当时的代表人物为荀子和王充。荀子说:“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星坠、木鸣,国人皆恐。曰:是何也?曰:无何也,是天地之变,阴阳之化,物之罕至者也,怪之可也,而畏之非也。夫日月之有蚀,风雨之不时,怪星之党见,是无世而不常有之。”(《荀子·天论篇》)王充的《论衡》对日食、月食作了专门讨论,把“阴阳符验”、“天人感应”之类斥之为“虚妄”。这些思想观点应该是上古中国朴素天文学思想的延续,非常难能可贵。这些思想家与占星学理论的冲突交锋,构成了中国古代思想史发展的另一条重要线索。
应该说明的是,即使出现了中国古代天文学向占星学的转折,占星学思想甚至成为了当时的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但天文学的观测、计算,以及据此推算建立的历法,仍然具有科学的意义,始终没有断绝,一直相对独立地发展。它与占星学的合流,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也表现出不同的比重。自汉至唐、宋,占星学大行其道,天文学只是内嵌于其中,成为它的附庸或手段。宋明以降,占星学式微,天文学又日渐崛起,成为其中的主流。中国古代天文学与占星学之间的这种相互依存又相对独立的关系,源自各个历史时期社会政治与科学发展的内在张力,它们在相互交错中发展、演进,经历了两千年的历史发展,直至清末中国帝制的结束。西学东进之后,这种状况得到了彻底的改变,近、现代中国学者完全剔除了古代天文学中占星学的思想内容,建立了与西方科学一体的中国现代天文学,占星学终于成为了历史。
[1]陈遵妫.中国天文学史(第一册)[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
[2]中国天文学史整理小组.中国天文学史[M].北京:科学出版社,1981.
[3]冯时.中国天文考古学[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
[4]江晓原.占星学与传统文化[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5]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第二册)[M].三松堂全集(第八卷)[C].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
[6]沈文倬.菿闇文存[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
[7]李学勤.《夏小正》新证[A].李学勤.古文献丛论[M].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
[8]詹子庆.夏史与夏代文明[M].上海: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7.
[9][清]王聘珍.夏小正第四十七[A].大戴礼记解诂[M].北京:中华书局,1983.
[10]张汝舟.二毋室古代天文历法论丛[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7.
[11]邵望平,卢央.天文学起源初探[A].中国天文学史文集(第二集)[C].北京:科学出版社,1981.
[12]徐振韬,蒋窈窕.五星聚合与夏商周年代研究[M].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6.
[13]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夏商周断代工程1996-2000年阶段成果报告(简本)[M].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0.
[14]蔡沈.书经集传[M].北京:中国书店,1994.
[15]常玉芝.殷商历法研究[M].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8.
[16]张培瑜.《春秋》、《诗经》日食和有关问题[A].中国天文学史文集(第三集)[C].北京:科学出版社,1984
[17]杨伯峻.春秋左传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1.
[18]袁行霈等主编.中华文明史第一卷[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19]“火历”续探[A].中国文化(第一集)[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4.
[20]殷玮璋,曹淑琴.中国远古暨三代科技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21]黄金贵主编.中国古代文化会要[M].杭州:西泠印社出版社,2007.
[22]杨向奎.宗周社会与礼乐文明[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
[23]徐传武.中国古代天文历法[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6.
[24]郑慧生.星学宝典——天官历书与中国文化[M].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1998.
[25]申先甲.中国春秋战国科技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26]白寿彝.中国通史(第三卷·上册)[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
[27]许倬云.西周史[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1.
[28]陈遵妫.中国天文学史(第二册)[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
[29]郑慧生.认星识历——古代天文历法初步[M].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6.
[30]刘韶军.古代占星术注评[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1992.
[31]孟世凯.商史与商代文明[M].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07.
[32]胡厚宣,胡振宇.殷商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33]金景芳.先秦思想史讲义[M].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7.
[34]卢央.易学与天文学[M].北京:中国书店,2003.
[35]章启群.两汉经学观念与占星学思想——邹衍学说的思想史意义探幽[J].哲学研究,2009,(1).
[36]吴伟.利簋铭文再释[J].文博,2009,(3).
B992.2
A
1671-7511(2011)06-0042-16
2010-08-02
章启群,男,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 我在《〈月令〉思想纵议——兼议中国古代天文学向占星学的转折》一文中,曾论及中国古代天文学向占星学的转折这一问题,后来又收集到一些相关资料,特别是几个重要的证据,促进了我对这一问题的进一步思考。由于这是一个涉及中国古代思想史、科学史的重大问题,本文的缺漏和不足之处在所难免。但由此在更深的层面上探求中国古代思想和科学发展的真正历程,亦不失为学界一大幸事。故希望各界同仁不吝赐教,以推动对这一问题的深入研究,从而得出真理性的结论。为了论证的完整统一,原来文章中的材料也一并使用,特此说明。
■责任编辑/陆继萍
——南县中小学生天文学认知度现状调查研究
- 云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的其它文章
- 论( 托名) 狄奥尼修斯《神秘神学》的神秘神学
- 论春秋时期的代理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