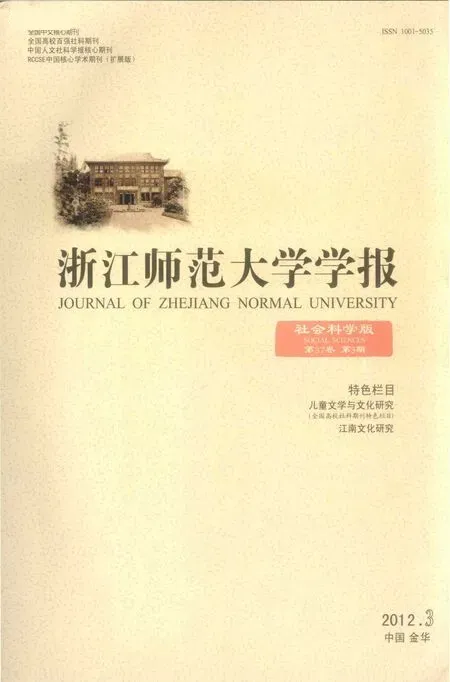由“启蒙”到“学术”
——20世纪初北京大学图书馆功能之演变*
方俊琦
(浙江师范大学图书馆,浙江 金华 321004)
大学是学术研究的重要阵地,而图书馆则是大学学术研究的文献中心。晚清以降,在西方图书馆理念刺激下,传统学校藏书楼逐渐转变为近代大学图书馆,其功能从译介西方新思潮的文化启蒙中心,逐渐演变为单纯的学术服务机构,对我国学术发展和高等教育都产生过深远影响。
由京师大学堂藏书楼发展而来的北大图书馆,与北京大学一同成长。20世纪初,北大图书馆不仅是“借书所”,更是“研究室”,含有教育的性质;新文化运动中,它作为开放的社会教育机构,成为新思想传播和社会启蒙的重要阵地;至30年代,随着高等教育的发展,现代体制化学术对图书馆建设提出更高要求,从而使其成为继新式学会及研究院所之外的重要学术重镇。
一、从藏书楼到图书馆
1898年京师大学堂初立,校内附设译书局,开始购置中外书籍,但仅供编译之用。1902年正月,恢复被义和团运动中断的大学,乃设藏书楼,陆续调取江浙鄂粤湘等省官书局各种书籍,并购入中西新旧书籍藏之。①是为北大图书馆之始基。
1903年,管理大学堂事务大臣张百熙奏请吏部,分发湖北试用道梅光曦派充藏书楼提调,“查学堂开学以来,该道创办藏书楼事宜,悉心经理,渐有端绪”。②是年,大学堂先后派人赴南方采办书籍,其中1903年江苏省送书696部、图歌12张;浙江省送书73种,计406部;湖南省送书78部。③这些图书中,汉文书籍甚多。1904年,由外务部领到图书集成一部,并接受巴陵方氏大宗书籍捐赠(约银一万二千二百两),其中多有由日本佐伯文库等收回之珍本。④以上图书构成了善本特藏的基础。
1904年,《奏定学堂章程》规定大学堂内设分科大学堂。京师大学堂遵照奏定章程设立图书馆,将藏书楼改称图书馆(楼额仍沿藏书楼之名),广置中外各种图书以备学生参考之用。本年,管学大臣张百熙续订《京师大学堂图书馆章程》,并制定“借取章程”、“借还书、预借及毁损赔偿”等制度,大学堂图书馆管理走向规范化。1903至1904年,大学堂译书局购买外国书籍850卷,内容涉及医学、自然科学、农学、数学、地理、历史、语言、文学、游记、哲学、心理学、经济学等几乎所有西学门类。⑤
1910年,第一任京师大学堂图书馆经理官王诵熙主持编纂《大学堂图书馆汉文图书草目》,记载图书编目和排架的方法,著录中、日文图书8000余种。[1]5光绪末年,大学堂图书馆藏书数有较快增长,新学书籍尤甚,“兹据洋教习函称:数学、物理、动物、教育、历史五科书籍,共一百八十五部,二百二十三本,已交本学堂藏书楼收存”。⑥
1912年,京师大学堂图书馆改称北京大学图书部。国内外学者捐赠书籍较多,其中有周慕西博士、日本板谷男爵、英国亚当士教授、黄树因讲师所捐中西文书籍约3000余册。[2]
到1917年底,北大图书馆已有藏书147190册,其中中文137260册,日文1580册,西方文8350册,中外杂志120种,是当时国内藏书较多的图书馆之一。[1]5-6经过 30 多年的发展,至 1934年图书馆共有藏书20余万册,其中中文约15万余册,西文约5万余册,所藏中文书籍中,善本书籍甚多,多为海内各大藏书家所未见之珍本,至为名贵。1935年1月18日《京报》报道:北大图书馆每年购书经费约九千元,阅览人每日平均约三百人。馆藏书:中文书129972册,西文书44306册,日文书2710册,地图160册3947幅,杂志按期到馆200余种。[3]西文藏书增长尤速。由旧时“皆为贵族所专有,仅绝少数人始得阅读”之藏书楼,转换为“平民谋便利而设图书馆,则最近数十年学制革新以后始有之”。[4]59
图书馆走向现代化,除拥有相当数量的藏书外,尚需科学的管理体制与制度。在大学堂藏书楼成立初期,缺乏明确的发展目标、规划及业务工作条例,原有的读者借阅规则也基本是一纸空文。直到李大钊出任图书馆长时,这种状况才有了较大的改观。1918年5月,李大钊亲自制定《国立北京大学总务处图书部试行条例》,共13条,明确规定图书馆的组织系统和工作任务,其内容涉及图书馆各个业务部门和各项工作,并提出了详细的职责分工和要求。该条例于1920年5月7日正式提交北京大学第二次图书委员会讨论通过并付诸实行。⑦北大图书馆各项业务工作由此走上了制度化。
图书部原有管理、阅览、理书、书目编订四个室,以及讲义收发室和缮写室。这些机构的设置不能很好地体现出大学图书馆的特点,同时也无法适应日益增长变化的读者需求。1920年5月,图书馆在李大钊的主持下进行了重大机构调整。调整后设主任一员,下辖事务员、书记员若干;馆中设登录、编目、购置、典藏四课,并附设打字处、装订处。职员约20人。⑧对于北大图书馆来说,这是具有重大意义的改革,是其迈向现代大学图书馆的关键一步。
二、新思潮激荡的场所
新文化运动中,作为开放的社会教育机构,北大图书馆推动了新思想的传播和社会启蒙事业。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推动下,伴随印刷技术的快速发展,以及西方图书馆理论和方法的传入,以北大图书馆为主要代表的一批新型图书馆开始成长。1917年初,甫任校长的蔡元培对北京大学进行了重大改革,使北大成为新旧思潮斗争和新文化传播的阵地。北大图书馆作为大学的工作重心之一,亦开始了新的转折,发挥了作为社会启蒙机构的功能,这其中有蔡元培与李大钊的重要贡献。
蔡元培早年就提倡“自由读书”的精神。他在国外读书期间,目睹西方先进的图书馆后,便立志于中国图书馆的建设。1912年,蔡元培任教育总长,拟定了教育方针七项计划,明确提出“对于大学校图书馆等未完成者,皆渐图结束前局,而于一定期间内,为革新之起点”。[5]他把大学图书馆看作是整个教育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自就任校长,即以扩充北大图书馆、博物馆、试验室为先务”,[6]特任李大钊为图书馆长。“李氏本为社会学专家,对于增进文化事业,昕夕筹思,不遗余力,接办以后,第一步即从整理着手,凡编制目录,改良收藏及陈列诸事,无不积极进行。”[7]
为充分发挥图书馆的教育职能,李大钊借鉴欧美日等国图书馆的管理经验,把图书馆设想成一个现代学习中心,可以为任何市民和机构提供用户服务,以更好地发挥其启蒙教育功能。他提出,大学图书馆不仅是“借书所”,更是“研究室”,它“含有教育的性质”。[8]为节省无谓的手续和浪费的时间,给阅览提供一种便利,北大图书馆由闭架改为开架,即由“文库式阅览”转变为“开架式借阅”,并同时增加副本,摒弃了“守书人”式的办馆方法,工作人员由书籍资料的监护者改变为信息提供者。
为将图书馆办成“教育机关”和学术性的机构,李大钊还极力主张在图书馆中聘用文化层次较高的“助教式”的工作人员。“美国某大学设立了助教制度,以前只有一个教师,现在增添了许多助教,这些助教不必上讲堂授课,只在图书馆里搜罗书籍供学生参考。这种制度有两层利益,一层可以消除师生间的隔阂,一层可以鼓励研究的兴趣。”[9]167在他的提倡下,1920 年 9 月,北大图书馆开始聘用大学毕业生任助教,馆内高层次文化人员占了全馆职员总数的近二分之一。到1922年9月,图书馆有工作人员21人,其中助教6人。
蔡元培一贯倡导“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思想。李大钊也主张各国文化和图书应当互相取长补短,理应达到“兼容互需”而不应有所偏废。“兼容互需”成为北大图书馆藏书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针,对于当时提倡各种新思潮、新学说的书刊,北大图书馆都予以收藏;与此同时,对于所谓的“旧”书籍,图书馆也不予偏废,仍然尽力搜集并馆藏。
为了弥补订购方式的不足,图书馆利用征求、捐献、交换等多种方式收集书刊,收到了很好的成效。《北京大学日刊》上各种书刊的征求启事和有关捐书鸣谢不断刊登,图书馆募捐书刊一时成为风气。到1920年,北大图书馆藏书已达到162031册,其中中文图书123651册,西、日文图书19826册;订购杂志近600种,中外报纸40种左右。从图书增长量来看,从1918年到1922年以来,图书馆藏书平均每年增长近万册。此时北大图书馆的藏书数量居大学图书馆第一位、全国图书馆第三位。[10]531920年5月,北大图书委员会召开了第一次会议,通过了“预算案内之添购图书费应定为每年六万元”的决议,⑨至此北大图书馆有了固定的购书经费,积极践行蔡元培的“为研究学问计,最普遍的是图书馆”的办学思想。⑩
为更有效地改善读者服务的工作,北大图书馆实行的第一个举措就是大幅度地延长开馆时间。调整后的图书馆开放时间每天达11.5小时,每周达80.5小时,而且延长开放主要针对可以借阅书刊的阅览室。此外,图书馆还延长了暑期开馆时间,为那些想利用暑期阅览书籍的读者服务。[11]这一决策反映了北大图书馆从以藏书为中心转移为以传播新思潮、启蒙教育、服务读者为中心的重要变化,也从侧面体现了这一阶段北大图书馆对其启蒙教育功能发挥的重视。
“图书馆和教育有密切的关系,和社会教育更有关系”。[9]168以蔡元培、李大钊等为首的新文化派,把图书馆作为传播新思想、启蒙大众的阵地,认为图书馆本来就应该是面向社会民众、面向青年、面向劳工。尤其是在这些人群聚集的地方,必须设有适当的图书馆或报馆,以供阅览。同时,基于这种认识,他们还主张图书馆应该一律公开且不收取费用。《申报》曾报道,北大“职员学生两方面热心教育之士,现拟扩张图书馆事业,以为普及平民教育之计,特建设通信图书馆一所,意在以通信方法,使各地有志读书者得以少量金钱,阅览多数书报”,[11]增进他们知识,使他们能自己觉悟,以达改良社会之目的。“五四”运动高举民主与科学的旗帜,是一次伟大的启蒙运动。而大学图书馆作为宣传新思想、传播新文化的阵地,在社会教育中也发挥了积极作用。
三、现代学术研究中心
图书馆之必须完备,为谋吾国学术之独立与发展之先决步骤,此理至为显明。[6]各国大学之设备,无不以图书馆占重要部分,其所以增进学生知识之效能,比之教师尤为伟大,盖欲修精深之学业,无不可无丰富之修养,若仅恃讲堂授课,有讲义笔记数小册,所得实属甚微,是以图书馆有文化宝库之喻,非无由也。[12]可见,图书馆事业对学术研究的重要性,时人已有清醒认识。
北洋政府时期,中国政治极端黑暗,整个教育文化事业十分艰难,北大图书馆也陷入了危困和停滞境地。1929年8月,在北大师生的共同努力下,北大校名恢复,1930年12月蒋梦麟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主持校政后的蒋梦麟,“是很想把这个新的北大图书馆完全放在一种新的组织和新的效率之上,——简单说,就是要‘美国化’它。此意无可非议,因为我们深信图书馆是以美国的为世界第一。”[13]63在一系列的改革中,北大图书馆的地位得到恢复并有所提高和加强。
20世纪30年代,国民党政府发动的“文化围剿”和文化专制主义政策,影响了馆藏中进步书刊的收藏和流通,致使北大图书馆中的进步书刊减少,引起了广大读者的强烈不满。时任图书馆长毛准出面否定北大图书馆有查禁进步书刊的行为。他曾在《北京大学周刊》上发表言论说,凡是对青年思想有害无益的书籍是绝对不购买的,但用于研究学术所必有的书籍则不会因为避嫌而不买。不难看出,北大图书馆能够从学术研究的立场出发,不避嫌疑加以收藏,其图书馆的学术研究功能开始逐步走上重要地位。
20世纪30年代初到1937年抗战爆发前的这段时期,北大图书馆进入了相对稳定、繁荣发展的阶段,取得了较大成就与进步。从新馆建成到各项业务工作建设的加强,再到蒋梦麟亲任馆长的重大举措,显示出北大开始重视青年学生学术研究能力的培养,逐步将北大图书馆发展成为现代学术研究的中心。
1.新建图书馆舍,创造良好阅览环境
因经费短缺,长期以来,北大图书馆馆舍空间过小,阅览参考不便,教职工和学生借阅图书很难按时归还,有些书刊甚至出现在校外旧书摊出售,造成藏书严重流失。因此,北大图书馆急需一座宽敞、实用、安全的馆舍。
在复校后拟定的《发展北大计划大纲》中,图书馆的建设置于重要工作首位,拟筹集60万元建设新馆舍,以全校经费的五分之一用于购置图书仪器。与此同时,毛准任馆长之后,为解燃眉之急,首先与校长蒋梦麟积极筹划和实施了图书馆向松公府新址的搬迁工作。到1935年8月新馆落成,北大图书馆又步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图书馆舍的较大改善,使许多读者改变了不愿意坐图书馆的习气,大家开始喜欢新的读书场所。据记载,当时北大有些学生更加愿意到图书馆学习,哪怕是上课时间。从此,图书馆的学术研究功能开始逐渐被放大,师生也开始把图书馆作为现代学术研究的重要场所。
2.调整组织机构,改进书刊分类编目
新馆落成以后,图书馆在组织机构方面做出了较大调整。首先,调整管理人员,选拔图书馆专业人员任馆长。鉴于毛准“是一个没有‘美国化’的人,办这个新图书馆,确很不相宜”,蒋梦麟颇为此事焦虑。“最近我虽没有和他细谈,但我知道他有改组图书馆的计划,想向北平图书馆借一位专学图书馆管理的人来,做这番改革的事。此人大概是严文郁君居多”。[13]636其次,内部机构由四课调整成为五股,分别为:事务股,主管文书和杂务;购贮股,主管书刊的采购和登录;中文编目股,掌管中、日文书籍的分类编目;西文编目股,掌管西文书籍的分类编目;阅览股,掌管书库、阅览室及借阅事宜。[10]75馆长、主任和各股股长构成了馆务委员会,适应了图书馆工作情况的变化,促使图书馆成为一个有效整体,对北大图书馆的建设起到了良好的促进作用。
在书刊的分类编目上,图书馆也做出了较大改进。其中,中文分类编目采用皮高品编制的《中国十进分类法》,书次号使用著者号,采用王云五的四角号码编制法。西文编目在采用《杜威十进分类法》的基础上也做出了改进和完善,对西文书进行了突击整理编目,基本上解决了其大量积存的问题。同时中西文分类编目都制定了详尽的编目条例,中文30条,西文14条,体现了较高的业务水平和正规化的程度。[3]分类编目的改进也从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学术研究领域区域化,是图书馆走向现代学术中心不容忽视的举措。
3.改进藏书采访方法,增加藏书数量
由各学系主任和教授提供采购书单是北大图书馆的采访传统。在这个传统的基础上,图书馆制定了采访工作条例,使得原来随意性很大的书刊采访逐渐正规化且制度化。期刊采访采用补购缺期期刊、交换重复期刊的方式,避免了以往的混乱状况。
20世纪30年代,北大图书馆馆藏图书有了较快增长。1935年,馆藏图书已达到250293册,比一年前增长了1万余册,其中中文书170415册,日文书12275册,西文书67603册,另有中外杂志400余种,中外报纸30余种。1936年,北大图书馆购入“马氏藏书”,其中包括小说、戏曲等俗文学作品。“马氏藏书”至今保存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善本书库。[10]74北大图书馆因此成为馆藏丰富的图书馆之一。对于藏书的调整,主要是采取全校藏书集中收藏的方针,为方便管理和读者使用提供了有利条件。在此基础上,北大图书馆效仿美国大学图书馆,设立了研究室,“上下各二层,层各十二间,每间宽三公尺,深四公尺半,为教授研究工作处”。主要为各系教师提供专业研究之用。⑪
至此,北大图书馆的学术功能得到大幅度提高,为其后来走向现代学术中心做了充足的铺垫。正如蔡元培所指出的:“图书关系学术至为密切。承先哲之余绪,开后来之涂辙,体用咸备,细大不遗,实惟图书是赖。集多数图书于一处,予民众以阅览之便利,辅助文化进步,实惟图书馆之功。”[4]58
注释:
①⑧参见《北京大学日刊》(1920年12月17日)关于北大图书馆的相关介绍。
②参见《大学堂为藏书楼提调给咨回省事咨呈吏部》,载于《北京大学综合档案》全宗一·卷29(一)。
③参见《有关省府向大学堂送运借书》,载于《北京大学综合档案》全宗一·卷36、卷135。
④参见《光绪二十九至三十年大学堂译书局购买西国书籍报销清册》,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学部·财经·卷217。
⑤参见《本馆述略》,载于《北大图书部月刊》,1929年第1期。
⑥参见《大学堂为购办书籍事呈学务大臣文》,载于《北京大学综合档案》全宗一·卷135。
⑦参见《国立北京大学总务处图书部试行条例》,载于《北京大学日刊》,1920年5月10日。
⑨参见《图书委员会致校长之报告书》,载于《北京大学日刊》,1920年5月10日。
⑩参见蔡元培:《北京大学一九二二年开学日演说词》,载于《北京大学日刊》,1922年10月6日。
⑪参见沈肃:《本馆建筑概况》,载于《北京大学周刊》,1935年6月29日。
[1]陈源蒸,张树华,毕世栋.中国图书馆百年纪事:1840-2000[M].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
[2]北京大学校史研究室.北京大学史料:第1卷[M].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3:465.
[3]介绍北大图书馆过去与现在[N].北平晨报,1934-09-30.
[4]蔡元培.韦棣华来华服务三十年纪念[M]//蔡元培全集:第七卷.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
[5]蔡元培.向参议院宣布政见之演说[M]//蔡元培教育论著选.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12.
[6]北京大学留美同学会为北大图书馆募捐通启[N].晨报,1921-09-16.
[7]北大图书馆之现在及将来[N].申报,1920-08-15.
[8]李大钊.李大钊文集(下)[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167
[9]李大钊.在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图书馆二周年纪念会演说辞[M]//李大钊文集(下).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10]吴晞.北京大学图书馆九十年记略[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
[11]野云.北京大学图书馆消息[N].申报,1920-07-20.
[12]野云.北大筹备图书馆之计划[N].申报,1920-07-05.
[13]胡适.胡适书信集(中)[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