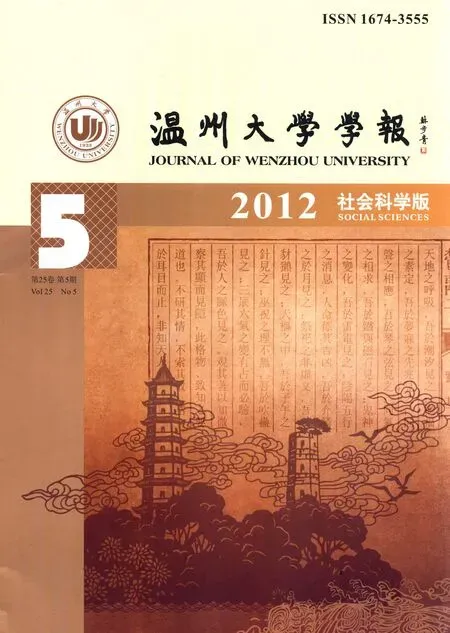敦煌西汉金山国政权性质及其立国举措成败析论
段锐超
(郑州大学历史学院,河南郑州 450001)
敦煌西汉金山国政权性质及其立国举措成败析论
段锐超
(郑州大学历史学院,河南郑州 450001)
敦煌张氏归义军政权的第三代统治者张承奉,在唐朝已经灭亡、外患方殷的形势下,在原地方政权基础上于910年建立起具有高度独立性的西汉金山国政权,使原来一直奉唐正朔的张氏政权由此蜕变为割据性独立政权。其立国之举虽不乏民众基础,但加剧了与周边政权特别是甘州回鹘政权关系的紧张。此举道义上的欠缺和策略上的失误,暴露出统治者为了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离心倾向,但不能完全否认其自存自保的现实意义,而上层及民众中普遍存在的中原情结,表露出敦煌地方与中原血脉相连的精神实质,这正是汉民族文化认同的巨大张力和国家统一必然性的反映,也是西汉金山国政权特殊性的典型表现。
敦煌;敦煌文书;西汉金山国;归义军;张承奉
敦煌西汉金山国政权是张氏归义军政权的第三代统治者张承奉所建立的政权。虽然史书记载寥寥,但幸赖 1900年敦煌文书的发现,其事迹终于没有被湮没。迄今为止,学术界关于敦煌西汉金山国政权的研究不多,并且观点各异。如李正宇、颜廷亮充分肯定了张承奉立国的正义性[1-2]。杨宝玉、吴丽娱则认为立国是张承奉未为其政权找到合理定位时回应回鹘逼迫及周边少数族威胁的应激之举,而后梁政权的局促乏力促成了金山国的建立[3]。有些学者则指责其立国之举是“割据称帝”[4]。本文主要借助敦煌文书并结合相关史籍,寻绎西汉金山国的建国背景和战略意图,剖析其政权的构成及性质,考述其内外矛盾和斗争,并总结其立国成败的原因。
一、张承奉建国称帝的时代和地域背景
从公元755年起,安史之乱和接踵而至的藩镇之祸使唐王朝边防空虚、无力西顾。成为孤城的敦煌在被吐蕃围困数年后,终因得不到朝廷救援而于贞元二年(786年)陷落。此后六十余年间,包括敦煌在内的河西、陇右人民处在吐蕃奴隶主贵族的统治下[5]1839,东望王师,汉心不改:“牧羊驱马虽戎服,白发丹心尽汉臣。”[6]但唐朝廷无力完成收复西北失地的重任,这一夙愿却由敦煌人民自己完成了。宣宗大中二年(848年),沙州大族张议潮趁吐蕃内乱,率领受压迫的汉羌等各族人民一举驱逐吐蕃,收复瓜沙(瓜州与沙州的合称),奏捷长安,继而收复肃、甘、伊和凉等州,六郡山河,宛然而旧,朝野欢腾:“凉州声韵喜参差”[7]。
大中五年(851年),唐置归义军于沙州,以张议潮为节度使,多民族联合的地方政权得到朝廷承认。但归义军与唐朝廷之间存在潜在矛盾,而其政权内部也存在激烈的权力之争。张议潮仗节归唐后,掌握实权的张议潮之侄张淮深在兵变中被杀,此后由张淮深的叔伯兄弟张淮鼎秉政。不久,重病的张淮鼎把儿子张承奉托付于张议潮女婿、沙州刺史索勋,但索勋自立为节度使并得到朝廷认可。张议潮第十四女(史失其名,可称张氏,凉州司马李明振之妻)发动兵变杀死索勋一家,复立张承奉,但她的三个儿子李弘愿、李弘定和李弘谏掌握实权并排挤走张承奉,这又导致河西大族倒李扶张,使张承奉终于获得实权。
从乾宁二年(895年)直到天复末年(904年),张承奉一直奉唐正朔,维系了唐朝力量在河西地区的存在和河西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天祐年间,朱温挟天子而令诸侯,各地节度使裂土称雄,唐王朝名存实亡。起初张承奉仍守臣节,S.5747《天复五年归义军节度使祭风伯文》称:“归义节度、沙瓜伊西管内观察处置押蕃等使、金紫光禄大夫、检校司空兼御史大夫南阳张公以牲牢之奠敢昭告于风伯神。”①转引自: 荣新江.归义军史研究[M].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6: 94.张公是张承奉,南阳郡开国公是他承袭的张氏封爵。这件文书的纪年是天复五年五月五日。昭宗天复年号用了四年,文书所谓天复五年当为天祐二年(905年),当年敦煌仍在沿用天复年号。归义军政权沿用被朱温杀害的唐昭宗天复年号,不用朱温所操纵的昭宣帝天祐年号,一定程度上表明了对唐王朝的忠诚。
907年唐朝灭亡。张承奉于910年建西汉金山国,自称白衣天子[8]。《旧五代史·吐蕃传》和《新五代史·吐蕃传》对此有相同的记载:“沙州,梁开平中,有节度使张奉,自号‘金山白衣天子’。”[5]1840,[9]这是正史仅有的关于西汉金山国的史事。另外宋代邵雍《皇极经世书》卷六有“张奉以沙州乱”数字②转引自: 杨宝玉.金山国建立时间再议[J].敦煌学辑刊, 2008, (4): 44-52.,这种贬斥的记述应该与当时后梁政府闻讯后的态度有关。
二、西汉金山国政权的核心构成及立国基础
位于河西走廊西端、具有重要战略位置的敦煌自秦汉时期起即是“华戎所交,一都会也”[10],是中西文化交汇和民族融合的前沿,进入并定居于敦煌的粟特人为数不少。吐蕃攻陷敦煌前后,原来集中居住于敦煌从化乡的粟特人逃散于各方。以从化乡之粟特聚落的消失为契机,留在敦煌的粟特人与汉人杂居通婚、交往共事,多种途径综合作用的结果,促成了这些粟特人的汉化[11]。在收复瓜沙的斗争中,势力较大的粟特人是张议潮的重要支持力量。敦煌其他少数民族的汉化状况应该与粟特人相似。张议潮收复瓜沙后创建的归义军政权是一个蕃汉联合政权,许多高级官职由粟特人担任,节度副使、粟特人安景旻是昭武九姓的代表。部落使阎英达则代表吐谷浑、通颊等势力。敦煌的主要对立面是甘州回鹘,其次是吐蕃。在针对共同敌人的斗争中,敦煌各民族加深了团结。敦煌本地民族融合的深入和民族认同的发展是西汉金山国立国的民众基础。
至910年西汉金山国建立,离848年敦煌被收复已经过去了半个多世纪,粟特人及其他敦煌少数族人的汉化程度更深,因此此时的西汉金山国已经演变为一个汉族色彩更加浓厚的政权,而且西汉金山国的主要将相中汉人的比例更大。金山国宰相、吏部尚书兼御史大夫张文彻对张承奉的支持可以追溯到张淮深秉政时期。据S.1156《光启三年(887年)沙州进奏院上本使状》载:张淮深遣使赴长安求取节度使实授时,在唐政府态度不明的情况下,宋闰盈等力主坚持,而张文彻等则认为“仆射(指张淮深)有甚功劳,觅他旌节”[12],打退堂鼓。可知张文彻不是张淮深的支持者,而是张淮鼎、张承奉一方的支持者和张承奉建国称帝的坚定拥戴者。张文彻无疑是汉人,金山国的许多文件出于张文彻之手,可能还是金山国皇室宗亲。
P.3633《龙泉神剑歌》中提及的浑鹞子、阴舍人(或即阴仁贵)、宋中丞、张舍人、阴仁贵、张西豹等无疑都是汉人[13]149-151。其中的张舍人即“累历三朝”[14]的张安左。但张承奉无疑也得到了汉化少数民族官僚的有力支持。
国相、衙前都押衙罗通达是金山国的主要将领和支持者。罗为吐火罗姓,也是汉姓,是敦煌地方的重要姓氏。P.3633《七言诗三首》有“毅勇番生罗俊诚”[15]一语,所以罗通达更可能是汉化中亚人。P.2594+P.2864《白雀歌》中有“罗公挺拨摧凶敌,按剑先登浑舍人”等语[16]146。S.4654《罗通达邈真赞并序》称颂罗通达“英高国相之班,宠奖股肱之美”及伐楼兰、击回鹘的战功[17]。根据P.3633《辛未年(911年)七月沙州耆寿百姓等一万人上回鹘天可汗状》[18]154和S.4654《罗通达邈真赞并序》,甘州回鹘围攻敦煌危急时,张承奉又派罗通达赴南蕃请兵。P.3633《龙泉神剑歌》中“今朝一日罗公至,拗起红旌似跃尘”[13]151指军民期望罗通达能够率众击败甘州回鹘。
三、西汉金山国的周边形势及其与周边政权的关系
张议潮时期是归义军疆域最广、力量最强的时期,据有瓜、沙、肃、甘、伊、凉六州。从张淮深时期起,归义军力量转衰,疆域日蹙。西州、甘州都被回鹘控制,肃州被龙家占据,凉州因有甘、肃二州相隔,实际上也已脱离了控制,并受到嗢末的威胁。所以张承奉时期虽云“继五凉之中兴,拥八州之胜地”[16]145,实际上辖境已缩至二州八镇一小块地区,而且被甘州、西州两大回鹘政权拑制。为求生存,金山国建立前后与各政权修好并进行贸易,又不得不进行一系列战争。
根据P.2594+P.2864《白雀歌》和S.4654《罗通达邈真赞并序》等敦煌文书的记载,张承奉称金山王后,曾以罗通达为统帅征伐楼兰,以恢复与于阗的交通。楼兰,即汉之鄯善,当时建有璨微这一少数民族政权。罗通达伐楼兰回军之际,又北上进攻伊州的回鹘。“还乃于阗路阻,璨微艰危,骁雄点一千精□(兵),天佑顺盈,神军佐胜。……回剑征西,伊吾弥扫。”[17]
金山国建立前,甘州回鹘多次进犯敦煌。如S.3905《唐天复元年(901年)辛酉岁十一月十八日金光明寺造窟上梁文》提到回鹘曾经焚烧了金光明寺等处:“猃狁(指回鹘)狼心犯塞,焚烧香阁摧残。”[19]张承奉建国称帝后,甘州回鹘立刻作出反应,对金山国发动更大规模的进攻,张承奉予以反击。P.3633《龙泉神剑歌》表达了对战胜来犯的甘州回鹘的信心:“我帝威雄人未知,叱吒风云自有时;祁连山下留名迹,破却甘州必不迟。”[13]149
但是,连年争战使得国弱民苦,金山国对甘州回鹘的进攻已经难以抵御,“沿路州镇,逦迤破散,死者骨埋□□,生者分离异土。号哭之声不绝,怨恨之气冲天”[18]153。回鹘兵临城下,张承奉不得已与其订立城下之盟,以沙州百姓的名义上书回鹘可汗,约为父子之国,“可汗是父,天子是子”[18]153。西汉金山国和白衣天子降格为“西汉燉煌国”和“燉煌王”。随着张承奉去世,张氏政权灭亡。后梁乾化四年(914年),沙州大族、兵马留后曹议金废燉煌国,去燉煌王号,恢复归义军称号,自称归义军节度使,入贡后唐,并获得后唐庄宗的正式封授。
四、西汉金山国立国的战略意图及其与中原政权的关系
作为孤悬边陲、受到钳制的地方政权,归义军政权曾经孤忠守边,有功于唐。王冀青认为归义军终唐之世均忠于唐室、奉唐正朔[20],其说法未必符合史实。907年唐亡后,张承奉着手建立西汉金山国。荣新江认为张承奉于910年始建国称帝[8]。至于后梁政权对待张承奉建立西汉金山国这一行为的态度,正史无明文,《皇极经世书》记述“张奉以沙州乱”,如果作者邵雍采用的是原始记录,则可以说明消息传到中原后,官方对张承奉策划自立的行为并不认同。
西汉金山国名称中的“西汉”意为西部汉人之国。“西”为所居方位,“汉”言民族属性。金山即今阿尔金山,当时称金鞍山,敦煌人认为“东有三危大圣,西有金鞍毒龙”[18]154。至于张承奉自称“白衣天子”,李正宇认为:根据五行观念,西方属金,其色白,中央属土,金生于土,故土为金之母,“张承奉自退一隅,以西部为职司之所,其尊崇中央之意甚明”[2]。
甘州回鹘政权的建立基本割断了敦煌与河西东部地区以及与中原政权的联系。颜廷亮认为张承奉自称“金山王”之举发生在甘州回鹘政权建立后不久,甘州回鹘政权对敦煌地区的严重威胁要求张承奉采取非常措施[1]。李正宇认为,统一河西,建立以汉人为主的安定之区,是张承奉祖孙三代之志,金山国的建立,就是在唐末中原多故,河西失控的形势下,归义军领导人重整河西之志的集中体现,其矛头一开始就是对准回鹘、吐蕃等周围民族的[2]。二人观点相似,均强调了张承奉面临的客观形势以及建国称帝的明确的战略意图。在唐朝已经灭亡、篡唐自立的朱温无力西顾的情况下,要张承奉继续孤忠亡唐或者效忠朱温,都不合情理,而周围各种势力的威胁又使他必须尽早凝聚和调动力量准备反击。
毋庸讳言,张承奉立国无力也无意与中原王朝分庭抗礼,他首先要解决的是敦煌面临的现实威胁。其国号本身仍然体现出对中原政权和汉族历史文化的认同,透露出以所立之国为中原政权在西陲的一部分、以中原为宗主的意思。在依靠中原政权无望,而“六戎交臂必须平”[16]146的特殊形势下,立国称帝更可能是为了避免敦煌陷于回鹘或吐蕃,加强内部团结,调动内部积极性,保持孤军奋战的敦煌汉民族的独立性和自主性,保卫汉人一代代赖以生存和极其热爱的家园。所以这一举措实质上是一种自救自卫措施,当时做出这种选择不无合理性和正当性。
S.4276《管内三军百姓奏请表》是由粟特人、左都押衙安怀恩代表敦煌军民的上表,前半部主要是歌颂张议潮驱逐吐蕃势力,收复失地,随后任职长安,子孙相继任节度使之事:如“伏静河湟,虏逐戎蕃”,“遂乃束身归阙,宠秩统军”,“尔后子孙相继,七十余年,秉节龙沙”等[21]。郑炳林认为S.4276《管内三军百姓奏请表》很可能是在金山国建立后以百姓名义上给当时后梁政权的奏表的草稿,上奏的目的是得到其承认和支持,并提请后梁册封张承奉为西汉金山国王[22]。敦煌文书P.3518v《张保山邈真赞》中有对张保山晋见中原皇帝的记述:“效壮节得顺君情,念依(衣)冠而入贡。路无阻滞,亲入九重。上悦帝心,转加宠袟(秩),得授左散骑常侍兼御史大夫。回骑西还,荐兹劳绩,当佥(迁)左马步都虞侯(候)。”[23]仍称中原统治者为“帝”,可见张保山此行的目的就是奉表请求后梁册封。这更说明西汉金山国政权对中央政权的认同和向心力及对统一的维护和追求仍然存在。文件中中原情结和桑梓之情的交织,充分说明西汉金山国的“汉民族的独立意识和对中原王朝的精忠之情”[24]这种宝贵精神实质犹在。
但是张氏归义军政权原本就具有的独立性和分离性随着唐室的衰败和中原军阀的崛起,越来越明显。归义军政权有与河北藩镇相同的一面,而西汉金山国有与五代时期的割据政权相同的一面,它们对朝廷并非绝对忠诚、始终如一。中央政府对其不能完全放心也不是毫无根据的,但在鞭长莫及、无法进行有效管理的情况下,承认现状和拖延待变也是一种无奈的策略。而金山国立国后表现出的“横截河西作一家”[13]149、“奉为我拓西金山王,永作西垂之主”[25]这样的独立性及恢复归义军全盛时期领土的愿望与张议潮逐蕃归唐的性质已经大不相同。除非其最终指向是统一,但西汉金山国政权显然是没有这种气魄与实力的。
五、西汉金山国政权的特殊性及立国成败的历史意义
西汉金山国政权既具有割据政权或独立政权的共性,但相对于其他割据政权或独立政权,又具有明显的特殊性。张承奉面临的形势要比当时割据称雄的南北各政权复杂。鉴于这种特殊状况,把西汉金山国与一般意义上的独立或割据势力如当时割据称雄的南方各政权区别开来是必要的。西汉金山国政权与十六国时期的李暠西凉政权有一定的相似之处,其性质复杂又过之。
如前所述,西汉金山国的建立,部分实现了其立国的战略企图,取得了对外反击的一些战果。敦煌本地的粟特等民族的汉化和民族融合的深入为西汉金山国的建立奠定了民众基础。敦煌民众的中原情结又反映出中华民族巨大的向心力与凝聚力。张氏政权的建立和发展,客观上实现了中原政权在敦煌地区的力量存在,而且一定程度上适应了当地民众的需要,维护了他们的利益和民族感情,使较为先进的汉文化传统没有被淹没,对保护先进文化和先进生产力功不可没,并为敦煌地区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当然,这也是与中原王朝以往的支持分不开的。
但是,我们必须看到另一面。在节度使一职还未得到朝廷正式任命的情况下,在S.4470《唐乾宁二年(895年)三月归义军节度使张承奉副使李弘愿回向疏》[26]中,只是归义军节度副使的张承奉,其具衔已为“归义军节度使”,表明像张淮深一样,在被正式授任之前,张承奉已自称节度使了,这表明归义军政权具有某种程度的僭越性。张承奉的做法等于斩断了获得中原王朝从道义上和实质上支持的可能性,他不是放远目光、韬光养晦,而是高扬西汉金山国独立旗帜,暴露出“定疆广宇”[13]149的战略企图,反而一定程度上激化了民族矛盾,孤立了自己,从道义上和策略上来说都是一种错误。西汉金山国时期的民族关系远不如其后曹议金时代和谐就是明证。
西汉金山国虽然存在的时间短暂,但它绝不是一闪而过的流星。它的建立,深刻地影响了这一地区的政治局势及历史走向,通过深入挖掘其立国举措的成败得失,可以更好地理解这一地区及相邻地区的民族关系发展变化的历史根源和历史脉络。
[1]颜廷亮.敦煌西汉金山国考述[M].兰州: 甘肃人民出版社, 2009: 5.
[2]李正宇.关于金山国和燉煌国建国的几个问题[J].西北史地, 1987, (2): 63-75.
[3]杨宝玉, 吴丽娱.梁唐之际敦煌地方政权与中央关系研究: 以归义军入贡活动为中心[J].敦煌学辑刊, 2010,(2): 65-76.
[4]贺世哲, 孙修身.《瓜沙曹氏年表补正》之补正[J].甘肃师大学报, 1980, (1): 72-81.
[5]薛居正.旧五代史[M].北京: 中华书局, 1976.
[6]杜牧.河湟[C]//彭定求.全唐诗.北京: 中华书局, 1999: 599.
[7]杜牧.郡斋独酌[C]//彭定求.全唐诗.北京: 中华书局, 1999: 5983.
[8]荣新江.金山国史辨证[C]//钱伯城.中华文史论丛: 第50辑.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2: 77.
[9]欧阳修.新五代史[M].北京: 中华书局, 1974: 915.
[10]范晔.后汉书[M].北京: 中华书局, 1965: 3521.
[11]陆庆夫.唐宋间敦煌粟特人之汉化[J].历史研究, 1996, (6): 25-34.
[12]佚名.S.1156光启三年(887年)沙州进奏院上本使状[C]//唐耕耦, 陆宏基.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 第四辑.北京: 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 1990: 371.
[13]佚名.P.3633龙泉神剑歌[C]//颜廷亮, 校录.敦煌西汉金山国考述.兰州: 甘肃人民出版社, 2009.
[14]佚名.P.3541张安左生前邈真赞并序[C]//颜廷亮, 校录.敦煌西汉金山国考述.兰州: 甘肃人民出版社, 2009:
162-163.
[15]佚名.P.3633七言诗三首[C]//颜廷亮.敦煌西汉金山国考述.兰州: 甘肃人民出版社, 2009: 156.
[16]佚名.P.2594+ P.2864白雀歌[C]//颜廷亮.敦煌西汉金山国考述.兰州: 甘肃人民出版社, 2009.
[17]佚名.S.4654罗通达邈真赞并序[C]//郑炳林.敦煌碑铭赞辑释.兰州: 甘肃教育出版社, 1992: 337.
[18]佚名.P.3633辛未年(911)七月沙州耆寿百姓等一万人上回鹘天可汗状[C]//颜廷亮.敦煌西汉金山国考述.兰州: 甘肃人民出版社, 2009.
[19]佚名.S.3905唐天复元年(901)辛酉岁十一月十八日金光明寺造窟上梁文[C]//郑炳林.敦煌碑铭赞辑释.兰州: 甘肃教育出版社, 1992: 438.
[20]王冀青.有关金山国史的几个问题[J].敦煌学辑刊, 1982, (总3): 44-50.
[21]佚名.S.4276管内三军百姓奏请表[C]//唐耕耦, 陆宏基.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 第四辑.北京: 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 1990: 186.
[22]郑炳林.唐五代敦煌的粟特人与归义军政权[C]//郑炳林.敦煌归义军史专题研究.兰州: 兰州大学出版社,1997: 400-432.
[23]佚名.P.3518v张保山邈真赞[C]//郑炳林.敦煌碑铭赞辑释.兰州: 甘肃教育出版社, 1992: 506.
[24]邵文实.敦煌边塞文学研究[M].兰州: 甘肃教育出版社, 2007: 77.
[25]佚名.P.4044+P.3999修文坊巷社再缉上祖兰若标画两廊大圣功德赞并序[C]//颜廷亮.敦煌西汉金山国考述.兰州: 甘肃人民出版社, 2009: 192-193.
[26]佚名.S.4470唐乾宁二年(895年)三月归义军节度使张承奉副使李弘愿回向疏[C]//唐耕耦 , 陆宏基.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 第三辑.北京: 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 1990: 84.
Analysis on Nature of Regime of Dunhuang Western Hans’ Jinshan Kingdom and Lessons of Its Founding
DUAN Ruichao
(School of History, Zhengzhou University, Zhengzhou, China 450001)
Based on original local regime, Zhang Chengfeng, the third-generation ruler of the Guiyi Jun (the army that stand up for justice) of local regime of Dunhuang Zhang Family, founded the Western Hans’Jinshan Kingdom regime with high degree of independence in the situation of ruin of the Tang Dynasty and serious foreign aggression in 910 A D.The founding of the regime stood for the changing of Zhang Family regime from the regime obeying the Tang Dynasty to an independent separationist regime.Although the founding of the regime had its public acceptation, the founding had increased the tense relationships between Zhang Family regime and surrounding regimes, especially with Ganzhou Uighur regime.Despite the fact that the deficiencies in morality aspect and faults in strategy aspect of the founding disclosed a tendency of rulers’purpose of maximizing their own interests, the practical importance of protecting their rights and control could not be totally overlooked.And the Central Plains Complex (commonly existed among upper classes and public) reflected the essential spirit that Dunhuang and the Central Plains are as close to each other as flesh and blood, which also both demonstrated the great cohesion of cultural identity of Han nationality and the necessity of national unity and precisely reflected the particularity of the regime.
Dunhuang; Dunhuang Document; Western Hans’ Jinshan Kingdom; Guiyi Jun; Zhang Chengfeng
K234.1
A
1674-3555(2012)05-00024-06
10.3875/j.issn.1674-3555.2012.05.004 本文的PDF文件可以从xuebao.wzu.edu.cn获得
(编辑:朱青海)
2011-11-07
段锐超(1970- ),男,山西临汾人,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魏晋南北朝隋唐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