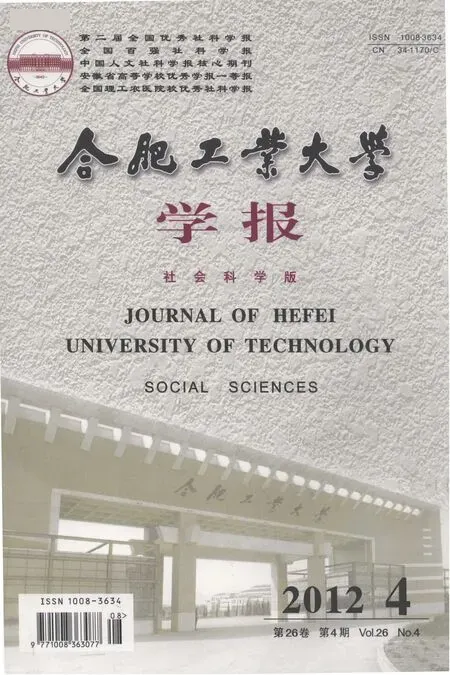古希腊先哲们对幸福的运思
王增智
(海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海口 571158)
古希腊先哲们对幸福的运思
王增智
(海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海口 571158)
“好生活”需要“好世界”。前苏格拉底哲学家们对外部实际生活世界的认知有限,因而将幸福视为神谕在人间的展开。不论在当时的哲学还是文学悲剧中,宿命论是一种主题。苏格拉底通过对“好东西”这一概念的分析,将诸神的幸福从理念上拉回到人间,从而揭开了人类可以自主追逐幸福的序幕。
幸福;故事;悲剧;苏格拉底的转向
作为伦理学范畴的幸福理念始于古希腊的梭伦,而体现梭伦幸福观主要内容的则是很多人耳熟能详的一则故事。虽然只是一则故事,但体现了古希腊人关于幸福的一般看法:一种宿命论的悲剧幸福观。这主要源于古希腊人外部生活境遇的不确定性和不可捉摸性。当进入到“古典时期”(公元前五至四世纪四十年代)后,先哲们开始从本体论转向认识论,思想被拉回到人自身,人类开始反思。这时,基于命定的悲剧幸福观在苏格拉底的对话中悄然发生了某种变化:他试图将幸福阐释为人类的一种自主追求,尽管这种追求几经转折后只有哲学家或爱智慧者才能享有,但其毕竟开启了关于世俗幸福的言说。另外,古希腊人关于幸福的隐喻除了哲学或伦理学之外,作为文学的悲剧也是其重要载体。基于这种思路,本文从如下三个方面展开。
一、故事原型及中外的不同解读
普鲁塔克的《希腊罗马名人传》之《梭伦传》和希罗多德的《历史》中都记载有关于梭伦幸福观的一则故事。其梗概如下:
吕底亚国王克洛伊索斯邀请梭伦访问萨尔迪斯(当时吕底亚王国的首府),并向他展示了自己拥有的巨大财富。然后,克洛伊索斯神气地发问:“梭伦,我知道你作为哲学家的声名,也知道你游历天下见多识广,能告诉我,你所遇见的最幸福的人是谁吗?”克洛伊索斯以为梭伦一定会回答自己是最幸福的人,然而,梭伦的回答却让他始料不及:“雅典的特勒斯是最幸福的人,因为他生活在一个管理得很好的城邦里,膝下有一群既勇敢又善良的儿子;他也看到了健康的孙儿们的诞生,并且在享受了一个人在正常情况下所能有的幸福生活之后,为雅典抵御埃勒西斯而光荣献身,人们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葬礼,并且心怀感激地纪念他。”听了梭伦的回答,克洛伊索斯便迫不及待地问道:“除了特勒斯之外,还有谁是最幸福的人呢?”他以为这第二的位置总该轮到自己了吧。然而,梭伦却说;“是阿尔哥斯城邦的克列欧比斯和比顿。因为这两个年轻人曾双双在赛会上获胜。当他们的母亲要乘车到五英里外的赫拉神庙参加节日庆典时,由于拉车的牛未能及时从野外回来,他们就自己拖车。庆典中所有的人都为这两个年轻人的力量喝彩,并纷纷向他们的母亲道贺。母亲喜不自胜,祈求女神赐予她的儿子人类所能有的最大福分。结果,祈求应验了。祭祀和宴饮之后,两个小伙子在神庙中沉睡,这时女神把他们召进了天国。”听了梭伦的回答,克洛伊索斯恼火极了,他说:“雅典的客人啊!为什么您把我的幸福这样不放在眼里,竟认为我的幸福还不如一个普通人重要呢?”梭伦说:“在一个人活着的日子里,其中的每一天都会有与以往不同的事情发生,所以,在一个人死前,你无法断定他这一生是否幸福;而你作为尊贵的国王所认为的幸福,其实并不是真正的幸福。真正的幸福是充满智慧地享受你所拥有的人生财富和荣誉,而你现在所拥有的感觉,只不过是眼下的一种被权力所装饰的虚荣,是一种对占有欲一时的满足罢了。”之后,克洛伊索斯把这个不注重当前幸福的“大傻瓜”梭伦送走了[1]14-16。
但是,在欲望的驱使下,克洛伊索斯先失去儿子,后在希波战争中被居鲁士俘获并处以火刑,而就在火焰舔着克洛伊索斯双脚的时候,克洛伊索斯终于体悟了梭伦的话——“活着的人没有一个是幸福的”。他对天大喊梭伦的名字,并向居鲁士道出了缘由。就在这时,“一直是晴朗并平静无风的天空上,乌云集合起来,刮起了暴风并下了豪雨,而火焰便给熄灭了。”克洛伊索斯获救了[1]44-45。
我国学者冯俊科认为这是梭伦从政治生活的视角阐释自己的幸福观:“最有财富的人并不幸福”、“幸福并不在于自己生存并享用荣华富贵,而在于为城邦和他人的利益而献身,从而获得人们的赞誉”,即“从物质和精神两个方面来考察幸福”和“幸福在于善始善终”等。而美国学者达林·麦马翁将这个故事纳入到整个古希腊文化中进行考量,认为这是幸福的悲剧。因为在古希腊人的世界里,“人类的目标总是经常受到各种不可预知的神秘力量的威胁,整个世界都是由命运或者诸神支配的,苦难无处不在,不确定性更是伴随着日常的生活经验。”而泰洛斯、克列欧毕斯和比顿在其有生之年英勇地“克服了生命中的苦难,且在他们人生最光荣的时刻荣耀地死去。”[2]在此,达林·麦马翁实际上将梭伦的幸福观上升为那个时代的一般性看法,特别是死亡对于幸福的意义:在一个充斥着不确定性和不可捉摸性的生活境遇中,神往往不过是叫许多人看到了幸福的一个影子,随后便把他们推上了毁灭的道路,所以只有死亡才能定格整个人生的幸福。在古希腊的传统秩序中,克洛伊索斯的“当前幸福”不过是昙花一现的“幸运”,抑或是“幸福的一个影子”。在一个人类不可能支配自己命运的世界里,以为自己可以拥有幸福是一种自大傲慢的表现,这种傲慢挑战了神威,从而必遭神的惩罚。这就是克洛伊索斯的命运。
在哲学史上,命运是米利都学派时代(与梭伦所处的时代大致相同)探讨的一个主题。泰勒斯将万物的“始基”归为水,而水的悄无声息地流动蕴含了万物命运变化的不可捉摸性。阿那克西曼德则直接将“始基”表述为“无定形”,这实际上进一步强化了命运的不确定性和不可捉摸性。他说:“万物由之产生的东西,万物又消灭而复归于它,这是命运规定了的。因为万物在时间的秩序中不公正,所以受到惩罚,并且彼此互相补足。”[3]7阿那克西美尼认为“万物的‘始基’是‘无定形’的空气”,保留了其老师的“无定形”。从这些命题可以看出,尽管“始基”概念确定了世界的统一性、确定性,但对“始基”的界定又无不打上某种神秘的烙印。这正如黄克剑教授所言:“哲学在它的滥觞期是负着浓重得多的宗教情愫的,阿那克西曼德和阿那克西美尼都不否认神的存在,他们或者认为被肯定为始基的‘无定形’或‘空气’就是神灵,或者认为遍在的神灵总不外于始基而为始基所笼罩。”[4]尽管如此,就米利都学派基于经验通过对宇宙本源的探索来试图打破自荷马史诗和赫西俄德《神谱》构建起来的传统秩序而言,其意义重大。正如希尔贝克和伊耶所言:自此,“宇宙——哪怕是最远的角落,都是可以用人类思想来穿破的。”因此,“没有任何东西是神秘的、不可理解的。”[5]这是直接对神谕的反对。之后,毕达哥拉斯的“数”使早期神话秩序进一步解体。同时,他提出的二元对立理念被赫拉克利特吸收后,基于逻各斯,开创了辩证思维方式。当然,赫拉克利特的“一切皆流,无物常驻”观点也蕴涵对命运之不可捉摸的无奈情愫。由此可以看出,尽管先哲们试图突破神谕传统,但最终还是被传统所笼罩。这一点在古希腊悲剧中体现得尤为明显。
二、“凡间的人没有一个幸福的”[6]——古希腊人的悲剧幸福观
罗念生先生认为,“古希腊人把他们所不能解释的种种遭遇统统归之于命运。”[7]7命运对古希腊人而言是不可捉摸的东西,但又是一种真实的存在。而以存在和不可捉摸性为特征的命运观是古希腊悲剧的主题,这一主题在“悲剧冲突”中得到极力彰显。所谓“悲剧冲突”即是主人公在一种极端情境下被迫在两种对立又彼此正确的价值选项中做出抉择的行为。如阿伽门农、俄狄浦斯和美狄亚,他们既被诸神追猎,又遭到家族的诅咒,最终只能任由命运摆布。“悲剧冲突”在古希腊人那里实际上蕴含了一种多神教,且诸神又都是正确的,诸神之间的冲突转化为人自身的冲突。因此,不论凡人选择哪种价值都会以牺牲另一种价值为代价,悲剧没有圆满的结局,这就是其内涵。
在埃斯库罗斯的《俄瑞斯忒亚》中,主人公阿伽门农面临着抉择:按照神谕把自己的女儿献祭或放弃对特洛伊的战争。在鱼和熊掌不可兼得的情况下,阿伽门农选择了前者,而这又埋下了女儿母亲的复仇计划,致使阿伽门农最终没有逃脱被复仇的惩罚。正如剧中歌队所唱:“凡人的命运啊!在顺利的时候,一点阴影就会引起变化;一旦时运不佳,只需用润湿的海绵一抹,就可以把图画抹掉。”“哪一个凡人能够夸口说,他生来是和厄运绝缘的呢?”[7]240剧中无奈的伤感同样是剧作者的情愫:“凡人没有一个能逃离,我们永远躲避不了这种悲惨的命运。”[7]28人成了诸神的玩偶。
在索福克勒斯的《俄狄浦斯王》中,当瘟疫笼罩着忒拜城,根据神谕,必须找出杀死拉伊俄斯的凶手即他本人时,合唱队道出了命运不可逃避的可怕性:“那神示刚从帕耳那索斯山上响亮地发出来,叫我们四处寻找那没有被发现的罪人。他像公牛一样凶猛,在荒林中、石穴里流浪,凄凄惨惨地独自前进,想避开大地中央发出的神示,那神示永远灵验,永远在他头上盘旋。”[7]358这种表达既凸显了神对人的权威,又内涵了一种人存在的境遇:遭受无数痛苦是命定的,在神面前无处藏身,且不受时空限制。
欧里庇得斯在《美狄亚》中的直白则进一步揭示了神对人的支配性地位:“宙斯高座在俄林波斯分配一切的命运,神明总是做出许多料想不到的事情。凡是我们所期望的往往不能实现,而我们所期望不到的,神明却有办法。”[8]在这种不可捉摸的人生境遇中,“顺其自然”也许是一种明智选择。而这恰恰印证了古希腊人不能自主追求的悲剧幸福观,更深层次地体现了古希腊人与社会和自然环境的冲突——人受必然性的支配及无奈。
悲剧中所揭示的不可改变、无法逃避的神谕、命运及其导致的惩罚和禁忌,自梭伦时代就已生成并逐渐固化为一种社会想象形式。正因为如此,索福克勒斯在《俄狄浦斯王》结尾处说:“当我们等着瞧那最末的日子的时候,不要说一个凡人是幸福的,在他还没有跨过生命的界限,还没有得到痛苦的解脱之前。”[7]387这呼应了梭伦在回答克洛伊索斯时所讲的话。希罗多德与索福克勒斯是同时代的人,历史和悲剧以思想观念的形式再现了叙事者的人生悲怀。
在悲剧世界里,人的行为总是受到不可名状的限制,苦难是不可避免的,即使有幸得到幸福也是诸神的恩惠,人在此境中的存在是被动的适应过程。这就是悲剧的困境。尽管诸神之间也有冲突,有时还很激烈,但在支配凡人这点上却是惊人地一致,凡人的自主选择在诸神那里就是挑战其权威的傲慢自大。因此,克洛伊索斯的遭遇和巴比通天塔(《旧约·创世纪》第11章)最终没有建成是一个主题的不同表达。
古希腊人的现实生活中同样充满着“悲剧冲突”——选择或放弃某些价值准则。好人做坏事是情境所逼,是生存的真实。这实际上蕴含了古希腊人的生存悖论:追寻存在的意义和神谕下追寻的无意义。“一方面是对人类存在的被动性以及他们在自然界中的主动性的一种原始感觉,以及对这种被动性的憎恨与愤怒;另一方面是我们理性的活动使人类的存在合理化,从而拯救了我们人类的生存——理性必须要拯救人类的生存,否则那种生存就是无意义的生存。”[9]3正基于此,悲剧试图通过“冲突”来揭示实践生活中选择的局限性,从而在生活可能性的基础上探索人类的生存意义。从这个角度来说,悲剧不是展示给观众解决“悲剧冲突”的办法,而是通过提出问题的方式来反思人类存在的实景,进而开启一种新的探索实践生活的方式:减少选择,从而减少“悲剧冲突”的发生。
三、“有谁不希望在世上生活的好呢?”[10]11——苏格拉底的转向
在苏格拉底之前,古希腊哲学家们研究的中心领域是自然界,其核心任务是探求世界的本源;智者学派从语言哲学开启了哲学研究的转向,但具有相对主义的不彻底性;苏格拉底在与智者们的辩论中彻底完成了将哲学从自然转到人类事物,即转到伦理-政治哲学。正因为此,罗马著名演说家西塞罗说:“是苏格拉底第一个将哲学从天上召唤下来,使它立足于城邦并将它引入家庭之中,促使它研究生活、伦理、善和恶。”[11]苏格拉底究竟是怎样将哲学从天上拉回到人间的呢?
首先,苏格拉底转变了自己的研究方向:从自然科学转到人类事物。在《斐多篇》中苏格拉底这样陈述自己的研究转向:“年轻的时候,我对那门被称作自然科学的学问有着极大的热情”,但也极度困惑。正在此时,阿那克萨戈拉的“心灵产生秩序”使我兴奋不已,并终于“在阿那克萨戈拉那里我找到了一位完全符合自己心意的关于原因问题的权威。”[12]18色洛芬在《回忆苏格拉底》中这样评介自己老师的研究转向:“因为他并不像其他大多数哲学家那样,辩论事物的本性,推想智者们所称的宇宙是怎样产生的,天上所有的物体是通过什么必然规律而形成的。相反,他总是力图证明那些宁愿思考这类题目的人是愚妄的。”[13]4关于这类的哲学家,苏格拉底诘问道:“是不是像那些学会了人们所运用的技艺的人们那样,他们希望为了他们自己,或是为了他们所愿意的人们而把他们所学会的技艺付诸实践,同样,那些研究天上事物的人,当他们发现万物是凭着什么规律实现的以后,也希望能够制造出风、雨、不同的节令以及他们自己可能想望的任何东西,还是他们并没有这类的希望,而是仅以知道这一类事物是怎样发生的为满足呢?”[13]5这是两种不同的研究目的。纳斯鲍姆认为:“技艺就是把人类智慧审慎地应用于周围世界,从而得到对运气的一些控制,技艺与需要的管理、预期以及对未来偶然性的控制都相关。用技艺来指导生活的人面对新的环境总有先见之明,具有一些系统的思考,对外物有控制能力,从而就能从容面对新的处境,消除对外界的盲目依赖。”[9]124将“技艺”用于实际生活就是实践。苏格拉底正是通过将神谕的不可捉摸性转换为人类通过“技艺”,从而“实践”来理解和掌握具体的生存形式,进而实现了自己的研究转向。
第二,确立一种关于“好生活”的规范性洞见。在《欧绪德谟篇》中,苏格拉底首先将追求幸福视为人的一种天性,即“有谁不希望在世上生活得好呢?”苏格拉底认为克洛伊索斯追求自己的幸福是一种崇高的探索,并列举了诸如富裕、健康、俊美、出身、权力、荣誉、节制、正直、勇敢、智慧(运气)等等的“好的东西”。但并不是只要拥有了这些东西就能够过“好的生活”,因为“一个人要幸福不仅必须拥有这些好东西,而且也必须使用它们,否则就不可能由于拥有这些东西而得到好处。”[10]14而且还必须是“正确的使用”,错误的使用将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这里的关键在于:正确使用得到的好处——能促进幸福或善。而要想正确使用就必须以知识为导向:“知识在各种行业中不仅给人类提供好运,而且还产生好的行动。”[10]14-15因此,“凡有智慧在场之处,无论是谁,只要拥有智慧就不要智慧以外的别的好运。”[10]14-15苏格拉底这种“借助概念分析,我们能获得有关情境和应当做什么的真理。这一方法,同时适用于对真实事态的知识和对价值目标的洞见,洞见到什么是正当和善,什么是我们应该做的。”[5]43由此可以看出苏格拉底向我们展示了一个追求幸福生活的途径:拥有一些好东西,并在知识的指引下正确地使用,以促进善的目的性。更为重要的是,苏格拉底还将幸福分类为:个人幸福和国家幸福。在《申辩篇》中,苏格拉底说:“因为我把自己所有的时间都花在试探和劝导你们上,不论老少,你们首要的、第一位的关注不是你们的身体或职业,而是你们灵魂的最高幸福。我每到一处便告诉人们,财富不会带来美德(善),但是美德(善)会带来财富和其他各种幸福,既有个人的幸福,又有国家的幸福。”[12]18这里的国家幸福是指“好世界”。苏格拉底在此还同时强调了“善”是幸福的源泉。
第三,如何才能获得“好生活”,即获得“好生活”的方法问题。苏格拉底的幸福观由两方面构成:好的生活环境——国家政治的善;一个人是否具有享受好生活的条件,如:德性、正义、勇敢等品格。在国家政治环境既定的情况下,个人追求“好生活”只能通过“认识你自己”来完成。而“认识你自己”在某种程度上又与“要自制”同义;“要自制”实质上就是反省。因此,他说:“人知道自己便会享受许多幸福,对于自己有错误的认识便要遭受许多祸害?因为知道自己的人,会知道什么事情是适合他们的,并会辨别他们所能做的事情与他们所不能做的事情;而由于做他们知道怎样去做的事情,于是便替自己获得自己所需要的东西,并且事事亨通顺遂,同时由于禁绝做自己所不知道的事情,便可以过活得没有罪过,并避免成为倒霉不幸的人。”[14]由此看出,认识了自己就会产生一种自律,这种自律会将我们引入幸福,回避不幸。达到自律的人也就是苏格拉底所说的有德之人,有德之人也就是幸福之人。而“认识你自己”就是要不断完善你自己的德性,从而促使你达至幸福之境。
综观之,苏格拉底将古希腊人祈求的神谕转换为通过完善人类自己的德性获得幸福。也就是说,当幸福不再被视为神谕在世俗里的展开,而被看作为人追求善的一种天性时,希腊人的幸福观发生了改变。黑格尔在《哲学史讲演录》中这样提及了苏格拉底的转向:“拿人自己的自我意识,拿每一个人的思维的普遍意识来代替神谕,——这乃是一个变革。”[15]一句话:幸福不是神的恩赐,而是人的自我追求,一种反思性的自我追求。
[1]希罗多德.历史(上)[M].王以铸,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2](美)达林.麦马翁.幸福的历史[M].施忠连,徐志跃,译.上海三联书店,2011:14-15.
[3]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教研室.古希腊罗马哲学[M].北京:三联书店,1957.
[4]黄克剑.从“命运”到“境界”——苏格拉底前后古希腊哲学命意辨正[J].哲学研究,1996,(2):
[5](挪)G·希尔贝克,N·伊耶.西方哲学史——从古希腊到二十世纪[M].童世骏,郁振华,刘 进,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
[6]欧里庇得斯.美狄亚[C]//古希腊悲剧喜剧全集.张竹明,王焕生,译.南京:凤凰出版传媒集团、译林出版社,2007:516.
[7]罗念生.罗念生全集(第2卷)[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
[8]罗念生.罗念生全集(第3卷)[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127.
[9](美)玛莎·纳斯鲍姆.善的脆弱性——古希腊悲剧和哲学中的运气与伦理[M].徐向东,陆 萌,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7.
[10]柏拉图.柏拉图全集(第2卷)[M].王晓朝,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
[11]叶秀山,王树人.西方哲学史(第2卷)[C]//古代希腊与罗马哲学.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472.
[12]柏拉图.柏拉图全集(第1卷)[M].王晓朝,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
[13]色洛芬.回忆苏格拉底[M].吴永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
[14]周辅成.西方伦理学名著选辑(上)[M].北京:商务印书馆,1964:63-64.
[15](德)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2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60:96.
Analysis of Ancient Greek Philosophers'View on Happiness
WANG Zeng-zhi
(School of Marxism,Hainan Normal University,Haikou 571158,China)
“Good life”requires“good world”.The Pre-Socratic philosophers had to bear the fate of their elusive external real life world,so they regarded the happiness as the commencement of the oracle in the world.Whether in the philosophy or literary tragedy at that time,the fatalism was a theme.Socrates,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he concept of“good stuff”,pulled the concept of happiness of the gods back to the earth,thus opening aprelude to the autonomic chase of happiness by human beings.
happiness;story;tragedy;Socrates'steering
B502.1
A
1008-3634(2012)04-0007-05
2012-06-07
王增智(1973-),男,湖北随州人,副教授,博士。
(责任编辑 蒋涛涌)
——评《当代中国青年幸福观及其培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