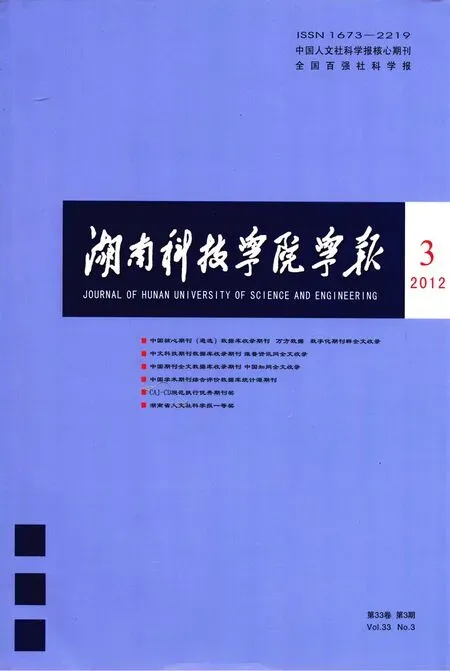鲁迅童话译介中的启蒙思想
郑奕
(福建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福建 福州 350108)
在鲁迅的精神世界里,有一种来自域外的“童声”,那就是他终其一生从事的童话译介。在这种“童声”的背后,隐含着鲁迅深刻的启蒙思想,以及对当代中国人“国民性”的批判和反思。在这里,我们试图通过对鲁迅童话译介问题的深入探讨,研究探讨童话译介与鲁迅启蒙思想的内在关系。
一童话译介作为“立人”之道:一种启蒙的视角
鲁迅的“立人”思想,最早形成于1907年写的《文化偏至论》中“立人”思想的形成,他说:“是故将生存两间,角逐列国是务,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若其道术,乃必尊个性而张精神。”[1]P57此后,以“立人”为核心的启蒙思想,就贯穿在鲁迅一生的文学创作和学术探索中。而对于“孩子”的关注,则是其中最为重要的内容之一。从鲁迅在白话小说《狂人日记》中喊出“救救孩子”开始,在鲁迅的文学创作中就反复出现“孩子”的形象;而关于西方童话的译介,则是鲁迅关注“孩子”的另一种途径,也是其启蒙思想的重要体现。
当然,关于鲁迅启蒙思想的研究,几十年来一直是鲁迅研究领域的热点话题,而从鲁迅的文学译介方面入手探讨这一问题,也已经不是新鲜的话题了。早在20世纪80年代,著名学者许怀中先生就在《鲁迅早期译介外国文学与“立人”思想的启蒙》一文中,对这一问题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论述。在许怀中看来,鲁迅早年在日本留学时期,介绍西方的“摩罗派”,是以启蒙主义思想为发轫的,其目的是为“立人”。在这篇文章中,许怀中着重研究了鲁迅的“科学小说的翻译”,并以此作为鲁迅为启蒙进行译介的论据。可惜的是在这篇论文中,鲁迅关于童话的译介,并没有被提及。[2]即使是在迄今未的鲁迅研究中,关于鲁迅童话译介中的启蒙思想研究,仍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毫无疑问,鲁迅不仅是中国新文学的奠基者,也是中国现代童话艺术的拓荒者。因为鲁迅的一生中不仅翻译介绍了大量优秀的外国童话,而且在童话艺术的文学批评、理论研究等方面都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3]那么,如何从启蒙的角度理解鲁迅的童话译介及其意义,对我们更深入地了解鲁迅的思想及其文学创作,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
从某种意义上说,童话译介是鲁迅终其一生的重要事业和活动。 早在1909年,他与周作人合译的《域外小说集》,就包括王尔德的童话《快乐王子》;1922年,他翻译了俄国童话家爱罗先珂的作品 13篇和童话剧《桃色的云》;1926年,他翻译了荷兰作家望·蔼覃的童话《小约翰》;1929年,他翻译了匈牙利作家至尔·妙伦系列童话集《小彼得》;1934至1935年,他先后翻译了苏联作家班台莱耶夫的中篇童话《表》和高尔基的《俄罗斯的童话》。1935年,鲁迅在写给萧军萧红的一封信中说:“前几天的病,也许是赶译童话的缘故,十天里赶译了四万多字,以现在的体力,好象不能支持了。但童话却已译成了……”1936年,鲁迅走到了自己生命的终点!由此可见,童话译介在鲁迅的生命中占据了极其重要的分量。
在鲁迅看来,“童年的情形,便是将来的命运。”鲁迅把少年儿童的命运和国家民族的前途联系起来,并把改造社会的希望寄托在年轻一代的身上。鲁迅曾引用日本儿童作家桢本楠郎的话说:“旧的作品中,虽有古时候的感觉、感情、情绪和生活,而像现代的、新的孩子那样,以新的眼睛和新的耳朵,来观察和倾听动物、植物和人类的世界者,却是没有的。为了新的孩子们,是一定要给他新作品,使他向着变化不停的新世界,不断地发荣滋长的”。[1](第10卷)P395在这里,所谓的“新作品”,正是童话。在鲁迅看来,童话蕴含着当时西方先进的思想和人类共同的智慧,对儿童的成长具有重要的引导和启迪作用。由此,鲁迅把童话的译介当作“救救孩子”的重要手段之一,而这也是他实践自身“启蒙”思想的重要方式和手段
二童话启蒙方式的转变:从“直译”到“意译”
在鲁迅的翻译生涯中,人们常常发现一个问题,鲁迅常常在“直译”与“意译”两种不同的话语表达方式中摇摆。这似乎是一个令人难于理解的问题。有些学者仅仅将其归结为翻译内容的不同,而没有进行深层次的探讨。事实上,在鲁迅关于“直译”与“意译”两种不同的话语表达方式背后,隐含着一种对“启蒙”方式的执着追求和实践。
我们知道,对于翻译,鲁迅最初是主张“直译”的。他对翻译的这种主张,早在日本留学时期就确立了。鲁迅曾经在致增田涉的信中说:“《域外小说集》发行于一九0七或一九0八年,我与周作人还在日本东京。当时中国流行林琴南古文翻译的外国小况,文章确实很好,但误译很多。我们对此感到不满,想加以纠正,才干起来的。”由于林琴南自己不懂外文,因此他在翻译外国小说时,只能靠懂外文的助手帮助,然后加以自己的文笔转译而成。这便与原著在内容和风格上有所差异,甚至完全偏离原著的意思。鲁迅对此“感到不满”,他认为凡是翻译,在“动笔之前,就先得解决一个问题:竭力使之归化,还是尽量保存洋气呢?”[4]P475这里的“归化”,就是所谓的“意译”,鲁迅认为这种译法只是“貌合神离,从严辨别起来,它算不得翻译。”而“保存洋气”,就是努力使译作保存“异国的情调,”“保存着原作的丰姿”就是所谓的“直译”。在鲁迅看来,“直译”既忠实于原作,又能比较可靠地将原作的内容和风格介绍给读者,是一种严肃而又认真的态度。
关于翻译的“直译”与“意译”问题,鲁迅甚至与梁实秋等人的发生了一场论战。梁实秋在一篇题为《论鲁迅先生的“硬译”》的文章中严厉地批评道:“……其文法之艰涩,句法之繁复,简直读起来比读天书还难……”而赵景深则在《论翻译》一文中说:“译得错不错是第二个问题,最要紧的是译得顺不顺。倘若译得一点也不错,而文字格里格达,吉里吉八,拖拖拉拉一长串,要折断人家的嗓子,其害处当甚于误译。”对此,鲁迅总结道:“在这一个多年之中,拼死命攻击硬译的名人,已经有了三代:首先是祖师梁实秋教授,其次是徒弟赵景深教授,最近就来了徒孙杨晋豪大学生。但这三代之中,却要算赵教授的主张最为明白而且彻底了,那精义是——‘与其信而不顺,不如顺而不信’”。但鲁迅依然坚持自己的主张,他认为:“译得‘信而不顺’的至多不过看不懂,想一想也许能懂,译得‘顺而不信’的却令人迷误,怎样想也不会懂,如果好像已经懂得,那么你正是入了迷途了。”[1](第4卷)P342如果仅仅是单纯地看待这场论战,我们或许会认为是文人之间的纠葛或者是基于对翻译的不同理解。但如果深入追究的话,其中却隐含着对西方思想理解方式和传播方式的不同认识。对于近代中国来说,面对纷繁复杂的外来思想,国人往往无法直接阅读原文,只能依靠译者的转达进行理解。但是,由于部分翻译者由于水平问题,对西方学者的著作和思想不能准确把握,或者有意地扭曲,往往导致读者对西方启蒙思想的误读和理解的偏颇。这种现象对于当时处于混沌复杂状态的中国思想界而言,是一个需要认真对待的问题。而鲁迅显然很敏感地关注到这一问题,这也是他执着坚持“直译”的原因。
应该说,在鲁迅一生的翻译事业中,都努力地遵循着“直译”的主张,然而他的童话译介却是一个例外。在鲁迅译介童话的过程中,我们惊奇地发现,他所运用并且反复强调的翻译方法却是自己坚决反对的“意译”。他在《小彼得·序言》中说:凡学习外国文字的,“开手就翻译童话,却很有些不相宜的地方,因为每容易拘泥原文,不敢意译,令读者看得费力”[5]P84。言外之意,为了不令读者看得费力可以大胆地意译。他对童话翻译的这种态度,与其弟周作人颇为相似。周作人说:“我所主张的翻译法是信而兼达的直译,这其实也可以叫作意译”,“童话的翻译或者比直译还可以自由一点。”[6]P87显然,鲁迅对童话翻译的这种态度,与他一贯的翻译主张是相矛盾的。那么,是什么使一向以性格倔强著称的鲁迅改变他一贯的主张呢?这是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
从客观上说,儿童毕竟不同于成人,他们的生活经验较少,知识面相对狭窄,掌握的词汇远不及成人丰富。这便决定了儿童对文学作品有着特殊的需求。而鲁迅对儿童的这种心理特征是有深入研究的。1913年至1914年,他曾先后翻译过日本心理学家上野阳一的几篇论文:《艺术玩赏之教育》、《社会教育与趣味》、《儿童之好奇心》、《儿童观念界之研究》等。这些论文对儿童的心理特征有着精辟的论述,并且根据儿童的心理特征提出了一系列关于儿童教育的主张。这无疑对鲁迅的思想产生了很大的启发和影响。此后,他自己也写了—些关于儿童教育的文章,如《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我们怎样教育儿童》等等。正是基于对儿童心理的深入了解,鲁迅说:“孩子的世界,与成人截然不同;倘不先行理解,一味蛮做,便大碍于孩子的发达。所以一切设施,都应该以孩子为本位。”[1](第1卷)P135这里所说的“一切设施”,当然应该包括为儿童所翻译的童话在内,这也是鲁迅在童话译介中的真实体验。他在童话《池边》的译者附记里说,“可惜中国文是急促的文,话也是急促的话,最不宜于译童话;我又没有才力,至少也减了原作的从容与美的一半了。”在《鱼的悲哀》译后附记里说:“然而这一篇(鱼的悲哀》)是最须用天真灿熳的口吻的作品,而中国话又最不易做天真灿熳的文章,我先前搁笔的原因就在此。”在《桃色的云》序里说:“日本语原是很能优婉的,而著者又善于捉住他的美点和特长,这就使我很失了传达的能力。”关于苏联作家L·班台莱耶夫的中篇童话《表》,鲁迅在《译者的话》中也曾自述其在用字上遇到的苦衷:“想不用什么难字,给十岁上下的孩子也可以看。但是一开译,可就立刻碰到了钉子了,孩子的话,我知道得太少,不够达出原文的意思来,因此仍然译得不三不四。”
以上的这些话,虽难免有鲁迅的自谦这词,但也说明了他在翻译时确实遇到很多困难。在这里,如何应用“急促的中国文”去翻译“最须用天灿熳的口吻”的童话,并且要用“近于儿童的简单的语言”,“给十岁上下的孩子也可以看”,无疑是鲁迅在童话译介中需要解决的问题。在这里,如何以最合适的方式,达到真正的“启蒙”效果,对于鲁迅而言,已经超越了翻译的话语表达本身。可以说,鲁迅在童话翻译上的这种转变,恰恰是其探索“启蒙”方式的一种实践。
三童话译介与文学创作:启蒙的国民性批判
鲁迅的一生始终对童话艺术保持着浓厚兴趣,并在童话艺术的翻译介绍和理论倡导上都作出了重要的贡献。鲁迅最初翻译的童话是俄国童话家爱罗先珂的作品,对此,他说:“不过要传播被虐待者的苦痛的呼声和激发国人对于强权者的憎恶和愤怒而已。”[1]9(第1卷)P224
1921年,爱罗先珂因参加五一国际劳动节纪念活动,被日本当局以宣传危险思想嫌疑的罪名驱遂出境。在出境前遭到殴打和凌辱,受到非人的折磨,这引起日本文化界人士的愤慨,纷纷著文抗议。鲁迅对爱罗先珂的悲惨遭遇也十分关注和同情,并开始翻译介绍他的作品。后来,爱罗先珂来到北京,就借住鲁迅家中,两人交往更加密切了。在爱罗先珂的作品里,鲁迅深深地体会到一种“无所不爱,然而不得所爱的悲哀”。(《爱罗先珂童话集·序》)对于爱罗先珂来说,“看见别个捉去被杀的事,在我,是比自己被杀更苦恼哩”,还常常“为了非他族类的不幸者而叹息。”然而,在严酷的现实面前,爱罗先珂这种“无所不爱”的思想破灭了,他所得到的只是“不得所爱的悲哀”。在爱罗先珂的童话《小鸡的悲剧》里,这种“悲哀”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小鸡的热烈的爱遭到了无情的冷漠,甚至它的死也无法惊动麻木冷酷的被爱者,换来的只是嘲弄,这是何等的悲哀!
鲁迅对此是深有同感的。他年轻时救国救民的满腔赤子之情,却在严酷黑暗的现实中四处碰壁,而国民的麻木愚蠢,甚至使他绝望了。这种“无所不爱,然而不得所爱的悲哀”,同样浸透了鲁迅的心灵。在鲁迅的小说《鸭的喜剧》里,鲁迅用类似于童话的笔触生动地揭示了无所不爱和不得所爱的矛盾。《鸭的喜剧》作于1922年10月,以爱罗先珂正北京的生活为题材:爱罗先珂喜欢蝌蚪,又喜欢小鸭,于是便把它们一起养在池塘里,结果,小鸭吃光了小蝌蚪,“无所不爱”的思想在这里碰了壁。“无所不爱就必定不得所爱”,这是鲁迅和爱罗先珂的共同感受。如果说,《鸭的喜剧》这个题目是与爱罗先珂同年6月在北京所作的童话《小鸡的悲剧》相对应的话,那么,这更是两颗饱受到创伤的心灵在内心深处彼此的呼应和理解。
从这里我们可以发现,鲁迅与爱罗先珂这位外国的童话?作家,在创作意象上有着共同的选择,用以表达他们相似的思想情感。而更为明显的则是鲁迅所翻译的爱罗先珂童话《狭的笼》。鲁迅在《爱罗先珂童话集·序》里说:“依我的主见选译的是《狭的笼》、《池边》、《雕住的心》、《春的梦》,此外便是照着作者的希望而译的了。”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主见,正式鲁迅对自身“启蒙”思想及其效果的反思和探索,其中包含着对国民思想麻木状态的批判。
鲁迅的文学创作不仅在“意象”上借鉴了童话译介的内容,在文学创作的形式上同样也有所借鉴。作者采取了“梦的形式”,却在其中装进了一个“童话”即“人与狗的对话。”从狗的身上,我们明显地看到了童话的物性特征,也就是拟人化以后的狗,仍然具有原来物的特性:不知道分别铜和银、布和绸、官和民、主和奴……,然而作者又是巧妙通过“狗”的口中道出了这些特征。这不仅符合童话的逻辑性,而且表现出童话独特的象征性。在童话艺术中,童话的幻想无论如何新奇,它的主人公不论是飞禽走兽,或者草木虫鱼,这些“主人公”的一切活动都与现实生活有着密切的联系。[7]P122在现实生活中,人们通常指斥狗是势利的动物,本文却巧妙地通过狗的“愧不如人”的驳诘,揭示出比狗更为势利。童话形象有时又常常是某社会观念的象征,不过这种观念已经被人格化,赋予了生命和个性,成为童话中的角色并与其他人物一起打交道。从这个意义上说,《狗的驳诘》具有更广泛的象征意义,甚至是人类某种性格特征的绝妙写照,其中同样反映了鲁迅对启蒙后果的批判与反思。
从鲁迅在20世纪初喊出“救救孩子”算起,如今已过百年,但在今天“救救孩子”依然是一个沉重而现实的话题。当今的中国儿童教育所存在的种种问题,仍然令人难于回避。尽管作为先驱者的鲁迅早已离去,但在鲁迅的精神世界里,那种纯粹、真诚的域外“童声”依然存在,并且仍然有着积极的启发作用。
[1]鲁迅.鲁迅全集(第1卷)[C].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2]许怀中.鲁迅早期译介外国文学与“立人”思想的启蒙[J].厦门大学学报,1986,(3):1-8.
[3]张向东.“救救孩子”还是“救救父亲”?——从鲁迅小说中“孩子”命运看其对启蒙和自我启蒙的思考[J].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4):563-567.
[4]鲁迅.鲁迅自选集[C].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1990.
[5]蒋风,潘颂德.鲁迅论儿童读物[C].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3.
[6]蒋风.中国儿童文学大系·理论(一)[C].太原:希望出版社,1988.
[7]郭大森,高帆.中外童话大观·童话的象征性[C].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