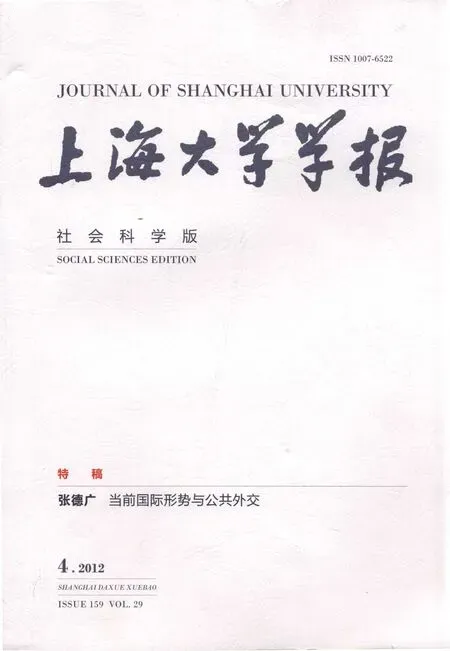试论清代弹词的文体分化过程及其特点
盛志梅
(天津师范大学 文学院,天津 300387)
一、“文体分化”概念的界定及相关问题的说明
谈弹词的文体分化问题,就要首先界定一下什么是“文体分化”。这里用到了一些“文学文体学”的知识。在西方,1908年,塞偕哀所著的《文体学与理论语言学》出版以后,文体学便作为一门新型的学科问世了。他们认为,文学文体作为作品语言的存在体,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体裁归类问题,它还有更多的涵义,包括以“体”来表述作家的个性风格、流派或时代风格特征等。《大英不列颠百科全书》是这样为“文体学”定义的:文体学是研究被认为能产生表达或文学风格的语言方式(如修辞和句法类型等)的理论。这个定义恰与中国古代文论中关于“郊寒岛瘦”、“建安风骨”等的理论研究有些不谋而合,只不过后者比较形象化一些罢了。“文学文体学”中的“文体”有狭义和广义之分。从语言学的角度说,文学文体是狭义的“文体”,而广义的“文体”则指包括口语体、书面体等在内的各类文体。①本文关于西方文学文体学的相关理论,均参考张毅著《文学文体概说》一书。
本文所用的“文体分化”概念即是在广义分类基础上的狭义概念,也即作为口语体的弹词文学和书写体的弹词文学表现在叙事和代言两种写作手段上的文体的分化、成长过程。简单一点说,即是代言体弹词和叙事体弹词在书场和书斋两个发生地、传播场的文体分化、成长过程。为了论述的方便,以弹词的发生地为标志,将弹词分为书场弹词和书斋弹词,前者是艺人在书场表演的口语体弹词,后者则是文人在书斋创作的书写体弹词。不论是书场弹词还是书斋弹词,都存在着叙事体和代言体两种叙事模式的消长过程。①“叙事体”,是指具有小说叙述特征的叙事模式;“代言体”则是指具有戏剧表演倾向或者戏剧叙述特征的叙事模式。
清代以前,不论是艺人创作的书场弹词,还是文人创作的案头弹词,大都是以第三人称的叙事模式出现的。因此,从弹词发展的历史来看,叙事是弹词的本来面目,代言则是新生事物。弹词的“文体分化”即是指代言体弹词从弹词叙事中分化、成长起来,与叙事体弹词并驾齐驱,成为弹词文学的两种主要的叙事模式的过程。就清代弹词的发展而言,文体分化构成了其历史演变的主线。具体说来,清代弹词的文体分化发生在两个不同的领域——书场、书斋。在这两个领域里,文体分化各自表现出了不同的发展内容。书场中,代言体弹词得到了迅猛的发展,相应地,原先占主体的叙事体弹词则渐渐萎缩;在书斋、闺阁里,不论是文人(包括闺阁才人)的创作还是阅读,叙事体弹词都逐渐成为主流,而代言体弹词的创作和消费却日渐消歇。
清代弹词文体的分化过程是以代言体弹词的逐步成熟为标志的。因此,我们以代言体弹词的产生、成熟阶段为主,②虽然书场代言体的出现要比书斋代言体弹词早许多,但从整个历史发展进程来看,两者的成长阶段基本一致,这为文章的阐述提供了很大方便,我们可以在同一个时间段里同时分析两种代言体弹词的发展状况,从而在整体上把握弹词文体分化的阶段性特征。参考叙事体弹词的案头化线索,将清代弹词的文体分化过程分为初期、中期、完成期三个阶段。为了简洁起见,我们在阐述分析时,只关注不同领域里占主导地位的弹词文体的变化,也即,对书场弹词而言,代言体弹词的出现、成长是主要的;对从书斋里产生又主要用于阅读的案头弹词,将主要关注叙事体弹词的成长、成熟过程。
二、文体分化初期——书场弹词代言体萌芽的出现
据资料记载,早在明代万历、崇祯年间,代言体书场弹词就出现了。秦淮墨客所编的《陶真选粹乐府红珊集》,选录了当时流行的说唱陶真若干种,其中的乐曲用了南北曲,人物有了角色的划分,与清朝初年有曲牌的弹词很相似。代言体弹词首先在书场中出现,这主要是因为弹词的演唱形式本身蕴涵着代言的因素,当艺人以局外人的身份讲故事时,会不自觉地模仿故事中人物的言语行动,以求惟妙惟肖的效果。随着演出经验的积累以及书场弹词消费市场的日益扩大,艺人们为了满足听众不断求新的娱乐心理,他们不断地吸收其他文艺样式的表演因子,在唱腔、表演上大量借用了杂剧、传奇或山歌小调的曲牌、套路甚至表演程式,久而久之,就形成了具有戏剧表演特征的叙事模式。
书场代言体弹词最初出现在明代,很长时期内一直是缓慢发展,在资料记载中罕见代言体的踪影,大部分的讲唱还是以叙事体为主。直至乾隆中叶,书场上才出现了专门善唱某种角色的名家。李斗《扬州画舫录》卷十一有关于“唱口”的记载:
元人唱口,元气漓淋,直与唐诗宋词争衡,今惟臧晋叔编百种行于世。而晋叔所改四梦,是孟浪之举。近时以叶广平唱口为最,著纳书楹曲谱,为世所宗,其余无足数也。清唱以外净老生为大喉咙,生旦词曲为小喉咙,扬州刘鲁瞻工小喉咙,为刘派……其唱口小喉咙,扬州唯此一人。大喉咙以蒋铁琴、沈湄二人为最,为蒋、沈二派。蒋本镇江人,居扬州,以北曲胜……沈以南曲胜。……其次陈恺元一人,……唱口在蒋、沈之间。此扬州大喉咙也。苏州张九思为韦兰谷之徒,精熟九宫,三弦为第一手,小喉咙最佳……[1]这里的“唱口”即是清代早期对民间弹词的称呼。“大喉咙”、“小喉咙”是指弹词演唱中人物角色的唱腔特色,净、末、老生等角色唱腔粗犷,乃云“大喉咙”,生、旦等角色唱腔细腻婉约,则云“小喉咙”。从上面所记看,此时的弹词演唱已经有了确切的角色划分,可以确定说唱艺人已经能“起角色”了,只不过是“清唱”,没有舞台动作。同一时期的说唱过录本也能证明此时书场弹词的戏曲化趋势。在乾隆年间出版的《玉蜻蜓》、《倭袍传》、《珍珠塔》等民间唱本中,都有了生、旦、净、丑等角色分工,但大多数还是叙事与代言杂用。总结起来,这个时期书场弹词的“代言体”特点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其一,人物上场基本都套用杂剧、传奇的套路,有[引]、[白]、[唱]三段,(或用词、诗、白、唱模式)由人物自道来历,如《倭袍传》第一回唐上杰出场:
[点绛唇]辅国何宜导君,仁义休谈利,进宝册,异论佞党,趋避。
诗曰:幼年熟读五车书,得志匡君绰有余。但憾寡诛存谦仄,逢君之辈未全除。
外白:老夫唐上杰,表字从玉,湖广荆州府支江县人氏……
唱:老夫勤学幼年间,磨砺工夫赖圣贤。入阁已来将五载,进贤远佞我居先……①[清]海兰涛撰《绣像倭袍传》,乾隆54年(1789)刻本。
人物上场的戏剧化、程式化是代言体弹词不同于叙事体的最明显标志。凡代言体弹词,其人物出场,基本上都是“自报家门”。而叙事体弹词则无角色划分,开篇先唱(念)诗,然后入正文。如郎瑛《七修类稿》卷二十二所云:“闾阎陶真之本之起,亦曰:‘太祖太宗真宗帝,四祖仁宗有道君。’”当然有的小型弹词也许没有这样的套话,但也不是如代言体那样简洁的,如《茶碗记》第一回:“若问此人家何住,自然道起本家门。家住扬州江都县,洛阳桥下是家门。”因此,相比之下,代言体弹词的开头要简洁得多,同时也亲切得多,无形之中就拉近了与听众的心理距离,与叙事体弹词比较起来,效果当然要好一些。
其二,说白的角色区别。清初的代言体弹词在人物说白上也与戏剧表演一样,有一个“尊卑贵贱”之分。凡是主要人物如生、旦、净、外等角色,说白皆用官话;那些次要人物,或出身低微、职业低贱、品行低下的角色,诸如贴、丑、末、付之类,其说白皆用方言土语,大多用苏白。既符合人物身份,又起到插科打诨的喜剧效果。如《玉蜻蜓》第二回“遇侠”:
(净白)哈哈哈,妙呵。果是大邦胜景,月夕花朝好,叫俺观不尽春光烂漫,看不完水秀山青。吓吓,行了半日,不觉到有些疲倦了,不免觅一酒家,小饮一回,……呔,酒保,可有美酒?(丑白)客人,小店只有好酒,吃得啥个鬼酒?(净白)呔,俺原道美酒,谁说鬼酒?(丑白)介末,客人是山西口气,更兼故一嘴胡子遮住子故张阔口,酒保一时听差了,请里势坐。……①见《新刻玉蜻蜓》,同治12年(1873)刻本。
这个体例在以后的代言体弹词中一直沿用下来,成为弹词叙事戏曲化的又一标志。
其三,说书艺人叙事身份的变化。在叙事体弹词中,说唱者以第三人称、全知视角叙述故事;在代言体弹词里,说书人一个人唱一台戏。当他扮演故事中的生、旦、净、丑诸角色时,其叙事语气、叙事视角是限知的,第一人称的。原来在叙事体中的叙事主体变成了局外的旁观者或者故事中人物的影子,只对故事的发展进行必要的解说,说唱者既是当事人,又是旁观者,一边表演一边评论。如《芙蓉洞》第二回“游殿”:②见[清]陈遇乾著《芙蓉洞全传》,道光元年(1821)刻本。
唱:昨见俏尼心挂牵,回家一夜未曾眠。左思右想无计策,立不安来坐不宁。将书撇,叹连连,只得假作烧香到庵边,一见俏尼如得宝,只要与她做个并豆莲,不想去为官。你道书痴颠不颠。(这是剧情解说)
……
表:金大老官勒朵三师太床沿浪一坐,一个懒腰一伸,到困子下去哉。
贴:阿呀,大爷,贫尼床上睡不得哪。
生:怕什么呢?
(这是扮作当事人在表演)
唱:贵升做事果然刁,恶唷,什么东西钦痛了腰……(这里前半句是解说评论,后半句又是扮作当事人在表演了)
也有部分情节已经实现了叙事身份的消解,说唱者完全模仿戏剧叙事,一个人虚拟生、旦、净、丑诸角色,现场表演,如《玉蜻蜓》第一回“踏春”:
(丑白)大爷,沈三爷来哉。(小生引)相逢谈笑友,畅叙往来人。(小生白)大哥,请了。(生白)三弟,请了,请坐。(小生白)有坐。(生白)文宣,看茶。(丑白)是哉。(生白)吓,三弟,为何连日不晤?莫非公冗分烦麽?(唱)近来小弟却清闲,懒把纷纭家事牵。独坐聊斋惟寂寞,抛书午梦意留连。(生白)为何不来走走?(唱)只因兄长乍乘鸾,谈心促膝磐交欢。恐其扰乱新婚赋,相隔云山一假缘。(生白)君兄休得取笑。(唱)古云识性可同居,莫逆情关意自如。虽只是时人不识琴中曲,今日里既遇知音何用词。(小生白)贵兄,小弟此来原是有意。……
人物的行动完全是戏剧化的舞台表演,说唱者的任务既单一又很繁重,单一是指他只要将各种角色按戏剧的模式表演出来即可,不需要在讲解者和表演者之间来回变换身份了,说其任务繁重,是指说唱艺人一个人要模拟很多角色,甚至要会不同的乡谈土语,以增加人物的真实性和故事的趣味性。这样听众听书犹如看了一场折子戏,自然比那单调的叙事体唱书要热闹得多,但对说唱艺人来说,则要求说、学、逗、唱、表,样样精通才行。当然,此时这样成熟的“代言体”只能在作品中部分出现,大部分还是代言、叙事混杂在一起的。
书斋代言体弹词萌芽于康熙、雍正时心铁道人著的《梅花梦》。在作品中,作者引进了“传奇的开场煞尾”样式,从而开代言体弹词创作之先声。在小说的开头曾有一段颇为自得的开场白,显示着这种文体的“新生儿”身份:
这一部说是演义,又夹歌谣,说是传奇,复多议论。无腔无板,分明是七字句盲词了。但自来盲词,从来没见有像传奇的开场煞尾,仿演义的说古谈今。况且口气或顺或断,回数或短或长,竟是封神传上姜太公骑的一只马(四)不相,殊觉杂凑无章,不成体例。……故此在下自创一个从来未有的格局,以记叙行文,用声诗作曲,有似弹词,却非俗调……今日开此法门,久而久之,也就成得体例了。
在这部“似传奇又似演义”的“马(四)不相”作品里,作者尝试着在开头结尾用了传奇的写法。开头用了[临江仙]、[前腔]、[蝶恋花][玉楼春]等曲牌词调,结尾用了[北新水令]、[南步步娇]、[北折桂枝]等南北杂剧的曲牌、词调。另外,大概是受了传奇角色分唱的启发,对人物角色、唱白作了区分,标明[张唱]、[秦唱]、[苏白](乞儿)等。除了这两点以外,全书唱词大都用七字句,唱词后面附有说白,没有“表”,说书人基本是以局外人身份在讲故事,因此,《梅花梦》充其量只是一部有着代言体倾向的书斋弹词,其主体还是“以记叙行文,用声诗作曲”的叙事体。但这些体式上的变革已经启发了代言体弹词的创作灵感,在其以后的发展过程中,逐渐向戏剧的表演程式靠近,慢慢形成了弹词叙事体制的另一大类——代言体弹词。
三、文体分化中期——代言体弹词成熟、叙事体弹词案头化完成
嘉庆、道光年间,弹词体裁出现了明显的分流倾向:一方面是书场代言体弹词越来越讲究演出的舞台效果,不但人物分角色,而且在表演程式上也开始戏曲化。另一方面是书斋叙事体弹词向小说靠拢,越来越脱离说唱文学的环境束缚,向韵文体小说的方向发展。总的来看,这两个方面的作品与前一阶段相比,取得了较大的进展。
先说书场代言体弹词的演出。乾嘉之际,花部兴起,昆曲衰落,戏曲演员为生活所迫,纷纷加入到弹词说唱的行列中来,所以很自然地把戏曲的唱腔风格也带了进来,从而加速了弹词说唱的戏曲化。这个时期出现的“响档”大都与戏曲渊源很深,像弹词前四家之首的陈遇乾,本为造诣很深的昆曲艺人,后改唱弹词,其唱腔深沉苍凉,有浓厚的昆曲味,人称“吟叹调”,是后来弹词说唱者必学的唱腔之一。再如节奏舒缓、旋律委婉的俞调,是与马调并肩的弹词主要唱腔,也是吸取昆剧南曲中的某些唱法,继而糅合一些皮簧戏生旦的曲调发展而成的。其唱腔柔婉、静细、情韵双绝,适合于女性角色,宜表现深闺佳人之哀怨、惆怅、悲凄之情。花部的兴起使得人们对民歌小调更加青睐,书场弹词当然会紧跟时尚风气,加之江南尤其是弹词演唱发源地苏州,素来是吴歌、小调的渊薮之地,弹词艺人纷纷将民间小曲唱腔及时加入到自己的书艺之中,如陈的学生毛菖佩就吸收了民间小曲[东乡调]、[滩簧调]等唱腔,创造了慢弹快唱、似说似唱、低回曲折的毛调。同治年间名满江南的弹词家马如飞创造的“马调”,就是在毛调的基础上吸收其他唱腔改造而成的,而且成为清代书场弹词后期的主要唱腔。戏曲和小调唱腔的加入,更进一步加快了弹词戏曲化的进程。
除艺人的演唱实践外,这个时期书斋代言体弹词创作也达到高峰,其创作势头甚至超过叙事体弹词。书斋代言体弹词的作者多为男性,新作迭出,题材多样,风格不一,已经远远高出前代同类弹词的艺术水平。书斋代言体弹词的案头化开始趋向成熟,但总体艺术成就还是赶不上叙事体弹词。归纳起来,这个时期的书斋代言体弹词的总体特征有如下几点:
其一,文体意识增强。代言体弹词的创作、改编开始有了明显的文体意识,一些作者注意到戏曲演出与代言体弹词叙事的不同,并以准理论的方式在书中阐释,如《燕子笺弹词》中澹园氏就曾一再说明“说书不同唱戏”,在最后一回,作者即从戏剧与弹词文体形式的不同来说明自己的修改理由:
明公!您却又错了!这说书不同唱戏,戏是扮与人看,即如安禄山的始末,不过换了几回行头,打了几阵锣鼓,从后台里提出颗首级,又早已经完了戏了。若是说书,便必须要一节一节还他个实在,又加上渲染,那听的才色动眉飞。所以这位编书的,按据正史,采摭传奇,重新与他装点起来,才成几回上等的好书。那缪家都喜吃酒,醉死了真是好死。那斋夫痛恨恶人,作了官也是个好官。那阮大铖只讲排场,不讲文法,所以后来都没个照应。这都还算小事。若论那个梅香,虽不是要紧的角色,却毕竟没有罪过,若要教他把包裹交与那个驼婆子,也还有个活便的方法,怎便就置之于死呢?
在作者看来,弹词、戏曲两者虽然都是代言体,但弹词毕竟是静态的非立体的说唱,而不似戏曲的动态表演,所以在改编时要注意体裁特点。这些意见都是很在行的,也可看作是成熟期的代言体弹词创作理论。
另外,在一些代言体弹词中,作者特别注意营造戏曲的诗意化舞台气氛,如《四香缘》第一回京报、别母:
老旦白:为娘的还有一句要紧之言,你须牢记。
母唱:倘然得有安身处,早寄鱼书慰母愁。
生白:孩儿谨记。
老旦白:去罢。
唱:此去杨生一径行,老夫人倚户看分明。
唱:越行越远难相见,恨杀那松林隔得深。
白:望不见了,待我闭上柴门进去罢。
唱:孤令令独自回内室,冷清清越想越伤心。哭泣泣割去心头肉,从此焦愁有万分。
这一段极力摹写老母依依别子的眷眷之情。“越行越远难相见,恨杀那松林隔得深”,让人想起《西厢记》的长亭送别,明显是借鉴过来的。有的弹词在结尾时甚至模仿戏曲的演出形式,如《梅花韵》卷十第四十二回的结尾用了戏曲里常用的“集唐句”:“(外)人间祸福本无凭,(生)怎奈群生□□深。(旦)若肯回头离苦海,(合)化生草木本长春”——以此来总结主旨并宣告结束。乍看去,与戏剧的舞台谢幕毫无二致。
其二,文人参与弹词的创作、改编活动频繁,代言体弹词的文学艺术水平普遍提高。
这个时期进行代言体弹词创作的作者大都有很高的文学素养,像改编《燕子笺》的澹园氏,创作《拱璧缘》的陆怡安,改编创作《蕴香丸》,《梅花韵》的佚名文人等,都是文采很好、自视颇高的“才子”,其作品的书卷气很浓。代言体弹词在他们手中基本已经案头化了,可读性很强,但不适合演唱。这些文人创作、改编弹词的动机很单纯,或为遣闷兼寓胸怀,如《燕子笺弹词》;或借笔墨以陶情,如《四香缘》;或借盲词而驱落寞,如自叙传式弹词《拱璧缘》;也有以教化众生为己任、专为“挽回风气”“教忠教孝”而作的,如《梅花韵》、《蕴香丸》等。这些书斋代言体弹词所涉及的题材特别广泛,有借历史事件以抒胸怀的《燕子笺》弹词,有写儿女英雄锄奸护国、婚姻有成的《四香缘》、《梅花韵》,有写才子佳人的《三笑新编》、《拱璧缘》等。在这些小说中,以才子佳人类的弹词最发达,小说中“才子”痴情者居多,好象形成了一个塑造“痴情种子”的风气,像《拱璧缘》里的俞笙香、《蕴香丸》里是路韵兰、《三笑新编》里的唐寅等都是著名的情痴,就连《义妖传》(顾光祖改编)里的许仙也变得有几分多情起来,不再是以前书场说唱中的那个胆小怕死、出卖妻子的负心汉形象了。
文人参与代言体弹词的创作,在形象内涵、作品意境、题材挖掘、审美意趣等方面都比艺人的努力高出很多;文学价值的突出使书斋代言体弹词超越了书场过录本,可以作为一个单独的文学种类来供人阅读。从现存清代弹词书目来看,书斋代言体弹词的创作至此已达到高峰。之后,文人就很少进行这种体裁的创作了。但受弹词说唱戏曲化的影响,弹词代言体的形式已经被听众和读者所接受,以至于在民国初年,人们印象中的“正正式式的弹词小说”,都是“与传奇曲本一样,要出角色,有说白,有表白,有上场,有下场,一折一折的要分做若干折”,而且“摛文藻词”,文雅得让“说书先生拿了,反而不便弹唱”。①见《满江红弹词·敬告阅者》。从弹词发展的历史看,这显然是“后来居上”了——把书斋代言体弹词奉为正宗,而大部分的书斋叙事体弹词则被归为“非正式”的弹词小说,与清初弹词以叙事体为主流的局面完全相反了。
再看这个时期叙事体弹词的状况。此时的叙事体弹词创作也已经达到高潮,作者多为女性,比较著名的弹词小说家有侯芝、邱心如、郑澹若、李桂玉等。几乎每一部作品都是这些女才子们呕心沥血、戛戛独造的结晶,是她们独立的人格精神和内心世界的真实写照。像侯芝,不仅把陈端生的《再生缘》批评一遍,提出了31条批评建议,而且加以改编、续写,名之为《金闺杰》,后来,又因不满于孟丽君的“无君无父”,反其意而作《再造天》。邱心如不满于《再生缘》的不重纲常,“翻其意”而作《笔生花》,此二者的创作,使以《再生缘》为核心的系列篇全部完成,从而成为清代弹词史上一道耀眼的风景线。郑澹若厌恶充斥男欢女爱的“文字流殃”,要作一篇解铃文章,以补“文字之过”,所作《梦影缘》以酸冷、空灵的笔调描写十二花神的尘世经历,追求的是至性真情的精神生活。其文“华缛相尚,造语独工”,与一般弹词花团锦簇、情语旖旎的风格迥然有别,使弹词之体,为之一变。李桂玉的《榴花梦》“翻新述旧”,用唐代的兴衰来影射清王朝的腐败,以“梦”为依托,通过“寓意寄情”的手法,抒发她的补天愿望。整个作品围绕桂恒魁的“百年事业”,作者写了桂、桓、梅、罗四大家族的英雄业绩,杂以宫廷、外藩的政治风云、军事纠葛。全书集清代叙事体弹词之大成,举域内域外、宫廷民间之巨细;纳兴亡感慨、英雄儿女之精粹,人物众多,情节繁杂,七字韵语,一气到底,真可谓纵横捭阖,气势磅礴,后来者无出其右。《榴花梦》的出现,标志着长篇叙事弹词已经达到了巅峰时期。这个时期,代表清代弹词成就的主要作家、作品都已出现了,其总体艺术成就远远超过前代同类作品,书斋叙事体弹词的案头化至此基本完成。
四、文体分化完成——书场弹词日趋戏曲化、书斋弹词叙事体复兴
咸丰、同治年间,内忧外患,社会动荡不安,弹词的演出和创作都受到了很大的影响。文人创作呈现萧条局面,不论是叙事体,还是代言体,均乏善可称,书斋弹词进入了低谷期。与此同时,书场代言体弹词却空前繁荣。
由于说唱派系的形成,听众形成了固定的欣赏标准。听众的这种保守倾向,使弹词艺人们说书每每以得其师真传为高。为了生存,艺人们的注意力大多都转向了对说唱技术的追求。许多人都是因一技之长而在书场走红的,如王石泉融合马调、俞调于一体的“雨夹雪”、赵湘舟的大套琵琶、“水底翻”俞调,在当时都大受欢迎。自咸丰年间至清末,弹词演唱更加戏曲化。相应地,书场弹词的代言体特征也就日渐明显,并成为主流。至清代末年,人们对弹词说唱的叙事体已经很陌生了,反“而以角色登场者为正格”。(《同心栀·序》)①[清]程瞻庐著《同心栀弹词》,民国8年(1919)商务印书馆铅印。这个时期书场里不起角色的说书已经很少了(同治年间的四大家之首马如飞说书不起角色),大多数弹词艺人对说书技艺的追求都集中在戏曲化的模仿上。像清代评弹后四家之一王石泉,书艺受昆曲影响比较大,演唱中采用昆曲道白形式和表演程式,形成独特的风格,说表官白、私白分得很清,使角色说白、叙事说白相辅相成。张福田善起角色,暮年时所扮年轻丫鬟仍俊俏生动。谢少泉书艺借鉴、吸收京剧、昆曲说白、唱腔、手面、身段,起角色如《三笑》中的唐伯虎、祝枝山等人,均有独到之处,人称“谢派三笑”,被誉为“书坛状元”。朱耀庭说表灵活,表演各种小人物惟妙惟肖,起《双珠凤》中的陆九皋、倪卖婆、来富、秋菊等尤具特色。有“活九皋”、“活来富”之誉。
尽管这个时期艺人的代言体弹词说唱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受弹词表演的行业竞争、书场受众的保守倾向等因素的制约,使他们过于讲究书艺而忽略了文本创作,书场弹词最终由文本、说唱并重的文学种类逐渐蜕化为一门演唱艺术。书场弹词文学的这种结局与口头传承文学灭亡的过程颇有相似之处。“当歌手把书面的歌看成是固定的东西,并试图一字一句地去学歌的话,那么,固定文本的力量,以及记忆技巧的力量,将会阻碍其口头创作的能力。……这是口头传承可能死亡的最普遍的形式之一;口头的死亡并非在书写被采用之时,而是在出版的歌本流传于歌手中间之时。”[2]书场弹词由一个口语体的文学种类逐渐蜕化为一门表演艺术,也最终难逃“死亡”的命运。
光绪之后,书斋弹词出现了转机,但主要是叙事体弹词的复兴,代言体弹词创作基本停滞。光绪二十六年之前,弹词创作以反省总结以往得失为特色,作家们都力求脱落窠臼,有所超越、创新。其中周颖芳觉察到弹词小说果报循环之不经,结合自身之遭遇,毅然砍斫小说《说岳全传》而成弹词《精忠传》,去掉迷信冤报之说,弘扬精忠刚直之气,岳飞故事由此面目一新;《凤双飞》,一反过去弹词以两性婚姻、恋情为主线的作法,掉转笔头以同性之恋为主,异性之欢为副,其主旨依然劝善惩恶、教忠教孝;《娱萱草》,反感于旧式弹词才子佳人、落难成祥、状元及第、桂子兰孙之侥幸矫情,搜寻经史之逸闻,融以瑰丽之想象,以亲情为重心,于虚无飘渺之中结撰出一篇合情合理的大文章;《四云亭》,有感于国事日衰之现实,伤时忧世,欲抒木兰之高志,借黄梁之梦以泄其悲郁绝望之情。题材、情节虽旧,风骨颇奇。这些作品在题材、布局、角度等的选择、挖掘上都比以往的弹词有所改进。相对于咸丰、同治时期的低谷期,是令人眼界一新之举。只可惜韶光难驻,这个短暂的繁荣局面不过是末期弹词的回光返照而已。清代传统弹词创作自此一振之后瞬即消歇,文人创作进入时事弹词阶段。受“小说界革命”的影响,“开智谲谏”、“改良女子社会”是这一时期时事弹词创作的两大主题,代表作有《庚子国变弹词》、《精卫石》等。由于过于注重文学的社会功利性,教化功能成为创作的唯一追求,两种文体的弹词都化入时代小说的行列,作品的艺术水平普遍不高,其叙事形式上的差别也就无足轻重了。这时期的弹词最终淹没于小说革命的喧嚣之中,也意味着清代案头化弹词的终结。
小 结
弹词发展至清代末年,叙事体已经成为书斋弹词的主要形式,而代言体则被接受为书场弹词演唱的“正格”。两种叙事模式的弹词各自找到了适宜的生存空间,文体分化最终完成。纵观中国古代文学史,这样的过程不独弹词有之,与之有“血缘”关系的诸宫调文体也有类似的演变历程。诸宫调的文体存在着一个由“词体”到“曲体”的变化过程。诸宫调最早的音乐体制基本上是以“一曲独用”(如《张协状元》“副末开场”)或者“一曲带尾”(如《刘知远诸宫调》)居多,在形式上,这些用来唱的散词与宋词无异,都采用分片的格式,被称为“词体”诸宫调。随着诸宫调文体的逐渐成熟,音乐体制越来越复杂,“一曲独用”的形式很少见了,“一曲带尾”、“多曲带尾”成为主要的音乐组织形式,说唱过程中的唱词逐渐多了起来,到了元代王伯成的《天宝遗事诸宫调》,唱词多到与杂剧难辨真假的地步。现存六十套曲词中,竟然“有了象一折杂剧那样长的接连十几个牌子”,“不象说书人的口吻,就有被疑为白朴《游月官》的第一折的可能”。①赵景深《天宝遗事诸宫调辑逸》前言。诸宫调发展到元末,已经完全“曲化”,且被认为是“院本”典范了,②明沈德符在《顾曲杂言》中说:金章宗时,董解元《西厢》尚是院本模范。在元末已无人能按谱唱演者,况后世乎?甚至有人在家乐中按照戏曲的表演程式,“分诸色目而递歌之”。③焦循《剧说》卷二引《笔谈》所记:董解元《西厢记》,曾见之。卢兵部许,一人援弦,数人合座,分诸色目而递歌之,谓之“磨唱”。卢氏盛歌舞,然一见后无继者。赵长白云:“一人自唱。非也!”杂剧由元代的场上之曲逐渐演变为清代文人的案头之曲,乃至出现了像嵇永仁《续牢骚》那样个人独白式的独幕剧,同样也经历了一个文体分化的过程。综上,我们可以这样认识弹词文体分化的理论价值:作为一种文化存在方式,文体分化的过程就是文学种类全部内涵升华、成长的过程。作为社会文化整体的一部分,文学文体总是随着整个文化由低层次向高层次进化,由幼稚、粗糙到精致、成熟和不断完善的。这不仅外在地体现在文学体裁的逐渐丰富与成熟及作家风格的变异上,更在文体内部构成上体现出来:越是发展到文学种类的成熟期,文学文体从生存中所获得的涵义也就越丰富。因此,清代弹词的文体分化是弹词作为一种文学文体成长的必然选择。[3]
[1]李斗.扬州画舫录[M].北京:中华书局,1960.
[2]阿尔伯特·贝茨.故事的歌手[M].北京:中华书局,2004.
[3]张毅.文学文体概说[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41.
——苏州光裕书场现状调查与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