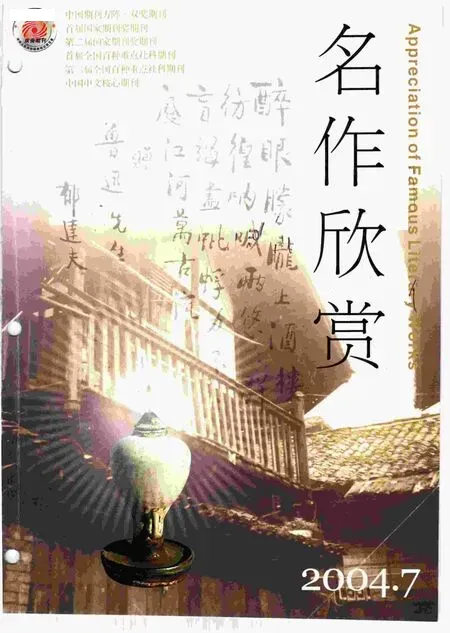吕叔湘先生的底色(上)
/ 江苏_姜广平
作 者:姜广平,作家,文学评论家,教育学者。
有一种观点认为,叶圣陶语文观的核心思想是“语文是工具”,也即著名的“工具论”,以及与此相关的“阅读中心论”,并认为:叶老的“工具论”,以“应需”为目的,在国民文化素质普遍较低的特定时代,对于推动社会进步、普及提高民族文化素养,有着巨大的意义。问题是,后来吕叔湘、张志公等先生,把叶老的思想进一步“发扬光大”,终于使之成为语文教育界占统治地位的思想。
细细思量这种说法,似乎当代语文为何遭遇“少、慢、差、费”,责任并不在应该承担此责任的主事者,倒反像是吕叔湘这样的大师在推波助澜、上下其手似的。“罪责”都应归于吕叔湘等先生。
实在,这是没有看到本质的一面。究其原因,是没有看到吕叔湘先生的价值与意义。
从语法角度切入语文教学
吕叔湘小叶圣陶整整十岁。照理,吕叔湘是真正的后来者,然而,要看到的是,吕叔湘与叶圣陶之间,其实并无真正的师承关系。纵使有所谓的师承关系,长江后浪推前浪,青出于蓝,也应该是一种必然。当然,这样表述显然不符合历史事实。因为,吕叔湘其实与叶圣陶很不相同,吕叔湘是一个游走于两个世界的大师。即便是与叶圣陶相近的这一世界,吕叔湘也与叶圣陶有着很大的不同,也就是说,吕叔湘的底色,与叶圣陶是很不相同的。底色不同,也就决定了行为方式的不同。
当然,这两个人,在语文教育中的地位与影响都是巨大的。只不过,客观上说,吕叔湘的很多影响是被遮蔽了。
所以,如果我们能清醒地认识到这两人的差别,我们更应该确立吕叔湘在语文教育中的地位与作用。然而,历史有时候就这样阴差阳错。历史有时候跟人开的玩笑,实在也巨大了点。
只不过,这次,历史是与中国语文教育开了一个大大的玩笑。
也就是说,如果是吕叔湘主导中国语文,以吕叔湘的治学方式、教育思想为中国语文开道,可能,情形便会有大的不同。
当然,历史不能假设。中国语文沦落至此,是我们现在所必须面对的。而我的另一层意思是,吕叔湘既没有像叶圣陶那样走到中国语文教育的前台,也就没有为语文教育承担恶谥的责任。
然而,却有人对吕叔湘如此错误地定论。实在有失厚道与公允。
如果我们算一笔细账的话,那么便会发现,在叶圣陶主导语文界时,吕叔湘正在努力形成自己的知识体系、学问结构。这时候的吕叔湘似乎与叶圣陶,其实正行走在不同的道路上。
我的意思是,叶圣陶与吕叔湘,在学问研究上,可能有交叉地带,但两人的角度、境界、思维方式与研究风格,则不可同日而语了。如果说两人走到了一起,也应该是两人都有了相当的影响后,才成为莫逆的。
按照叶兆言的记述,吕叔湘与叶圣陶是过从甚密的朋友:“……几次见到他和祖父聊天,腔调都很接近苏州话。或许因为他曾在苏州生活过,或许因为治语言学,有很强的语言能力,我一直误以为他是苏州人。”(叶兆言:《吕叔湘》,《万象》2002年第12期)
但如果细细推敲,我们发现:吕叔湘大学时代主修外国文学,大学毕业后,主要是作为中学英文教员身份出现的。1938年因抗战爆发,他从英国牛津大学人类学系、伦敦大学图书馆学科肄业,回国后任云南大学文史系副教授。在云南大学任教期间,他发表了他的第一篇有关汉语语法的文章,从此他走上了语言研究的道路,并进而成为语文教育方面的专家。
也就是说,吕叔湘是从文法(语法)角度切入中国语文教学的。而这一条线索,我们现在大致可以进行这样的梳理:
我国汉语语法研究从马建忠的《马氏文通》至黎锦熙的《新著国语文法》属草创阶段。这一时期汉语语法界深感模仿拉丁语法或英语语法弊端很多,于是“努力寻求中国文法的特点”成了当时的呼声。其后,《中国文法要略》作为吕叔湘先生前期代表性的语法学著作,也是他的成名之作,迎来了中国文法建设的黄金时期。《中国文法要略》的出版令人耳目一新,在理论和方法上作出了许多贡献。该书构建了以动词为中心的句法模型,提出并研究了汉语语法结构之间的变换关系,以语义为纲全面描写汉语句法。全书就文言与文言、白话与白话、文言与白话、汉语与英语、古今汉语等进行多角度的“对比”。《中国文法要略》精细的描写,理论上的博大精深,开拓创新,对以后的汉语语法研究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此后,吕叔湘先生的研究重点是汉语语法。《中国文法要略》之后,又出版了《语法修辞讲话》(与朱德熙合著)、《汉语语法分析问题》、《汉语语法论文集(增订本)》等。吕叔湘先生参与撰述并审订了《现代汉语语法讲话》,直接参加了“暂拟汉语教学语法系统”的制订工作。吕叔湘先生是我国最具社会影响的词典《现代汉语词典》的前期主编和我国第一部语法词典《现代汉语八百词》的主编。这些著作引例宏富,分析精当,在汉语语法体系建设以及理论和方法上都具有开创意义,成为半个多世纪以来我国现代汉语语法研究最有影响的重要成果。吕叔湘先生也因此成为我国近代汉语研究的拓荒者和奠基人。从上世纪40年代开始发表的专题论文到80年代出版的《近代汉语指代词》(江蓝生补)代表了吕叔湘先生在近代汉语研究方面的总体成就,不仅填补了白话语法研究的空白,而且具有方法论上的示范作用。
如果再往前推,出生于1904年的吕叔湘,在其中学时代,很可能是叶圣陶那个被称为人生派的文学研究会中诸多作家的忠实读者。也就是说,吕叔湘中学时代,可能受到叶圣陶等作家的影响。然而,大量关于吕叔湘先生的文章记载中,并无这方面的资料可以佐证。
1904年12月24日,吕叔湘出生在江苏省丹阳县城内新桥西街柴家弄,在兄弟中排行第三。父亲吕东如经商,家境较富裕。吕叔湘幼年时在县城的一所私塾读书,1915年,考入丹阳县高等小学。这是该县最早的一所高等小学,校址坐落在县城白云街中段,现在是丹阳实验小学。吕叔湘入学的这年,学校增开了英语课。
1922年,吕叔湘中学毕业,以优异的成绩考取国立东南大学外国文学系(后改为外国语文系)。根据当时学校的制度,除本专业课程外,还必须在文科和理科的几组课程中选修若干学分,如中文、历史、物理、化学、地学、生物学、心理学等课程。这也是他在后来能形成自己的两个世界的重要原因。
吕叔湘学生时代的兴趣在文学方面,对语言方面如语音、会话等并不十分重视。后来到中学教英文,需要语音、语法方面的知识,就边教边补。吕叔湘于1926年从南京国立东南大学毕业,到家乡刚刚创办了一年的丹阳县立中学教一个班英文。当时只有两个班,校长陈湘圃自己教了一个班的英文。吕叔湘教学任务不足,陈湘圃让他兼教国文文法。吕叔湘以《马氏文通》为教材,开始钻研中国文法。可以说,这时候的吕叔湘始关注中国语言问题,并开始了一个语言大师、语文教育家的文化之旅。
但这里要看到一点,在吕叔湘,显然并没有将成为语言大师和语文教育家作为自己的发展目标。或者说,这时候的吕叔湘,究竟将来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心中并无十分明晰的方向。
我们且看其后的情况:
1928年,江苏省丹阳县中发展不佳,校内矛盾丛生,主事者吕凤子(著名画家、教育家,吕叔湘堂兄)等请何其宽担任县中校长,希望能缓和矛盾。何其宽又把吕叔湘请回来担任教务主任。另外又从外地请来几位有学问有经验的教师,一时间,教师阵容整齐,学校气象为之一新。但情形只维持了一个学期,何其宽便又不得不辞职回到杭州去教书,吕叔湘也辞职去安徽省第五中学教书,暑假后仍到苏州中学任教。此后的七年,吕叔湘一直在苏州中学任教。在苏州中学,吕叔湘除教学任务以外,还担任学校图书馆馆长一职。正是在苏州中学期间,吕叔湘研读了丹麦学者叶斯柏森的《语法哲学》等语言学名著,为以后走上语言学研究的道路打下了基础。在苏州中学,吕叔湘是高中英语教员。这段时间,吕叔湘除教学外,还参加《高中英文选》(中华书局出版)的编注工作。前后译出《人类学》《初民社会》《文明与野蛮》三种,分别由商务印书馆和生活书店出版。
关于吕叔湘在苏州中学的情形,我们从杨荫榆的有关轶事中也能获知一二。
1935年5月,江苏省教育厅厅长周佛海,派他日本的同学、省督学王亦文(字骏声)到苏州中学视察。这次视察在苏州中学史上,以苛细、挑剔、偏袒、不公著称,有关督察报告,都在当地报纸上刊出。就是在这次视察中,杨荫榆被勒令退职,揭开了杨荫榆大战王骏声的序幕,杨荫榆前后四次上书教育厅,逼王骏声引咎辞职。最后,杨荫榆被苏州中学辞退,再也无法在教育界立足,王骏声改任镇江中学校长。当时,吕叔湘先生也正在苏州中学,任高二的英文教师。在王骏声提交的视察报告中,吕叔湘先生倒甚得好评,其中对吕叔湘上课教法好,英文习作也分量最多持肯定态度。
吕叔湘,原名湘,字叔湘,以字行。1935年,他已经三十一岁了,在苏州中学教书有年,甚得好评。这年暑假,吕叔湘参加了现任教育机关服务人员留学考试。
据《苏州明报》1935年9月3日报道:江苏省留学生考试揭晓录取吕湘、刘诒谨二名。
这里的“吕湘”就是吕叔湘,此时他已过而立之年。虽然这个公费留学不过两年,且是进修性质,但吕叔湘还是作出了这样的选择。吕叔湘在英国先后入牛津大学和伦敦大学,学习人类学和图书馆学,这一经历,改变了他一生的人生走向。
明确地说,在此之前,吕叔湘只是基础教育界的教员,然而留学归国作为一个转折点,使吕叔湘成为大学教员,并从此开始了他与语文教育的结缘。
1937年,抗日战争已开始,吕叔湘没有等三年期满,提前于1938年初回国。当时江苏已沦陷,吕叔湘家人流亡到湖南,吕叔湘与家人会合后,转道云南,在云南大学文史系任副教授,教英语。在云南大学,他和施蛰存同事相得甚欢。施蛰存约他给《今日评论》周刊写文章。
其时,吕叔湘看到朱自清先生写的一篇文章说,每个句子总要有一个主词,觉得这种说法不全面。于是在经过深入思考后,写出了《中国话里的主词及其他》。
这就是吕叔湘先生的第一篇有关汉语语法的文章,通过这篇文章,吕叔湘结识了朱自清先生。
其后,也就是1939年暑假后,云南大学文史系给吕叔湘加了一门中国文法。其时,王力先生正在西南联大讲授“中国现代语法”,王力先生的讲义印出来后,吕叔湘借来一份参考。吕叔湘本想就阅读与教学中的一些问题请教王力的,可王力先生休假期间住在河内从事汉越语的研究。吕叔湘痛惜失去向王力求教的机会。一年后,也即1940年暑假后,吕叔湘离开昆明,迁居成都,任华西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研究员。
吕叔湘与王力的真正合作,就这样被推到了四十年之后的《中学教学语法系统提要》。
吕叔湘的第一篇研究论文是《释您、俺、咱、喒,附论们字》,这是针对胡适和王静如的文章写的,他们说“们”是从“俺、您、喒”的韵尾-m变来的,吕叔湘发现这个结论恰好把历史的演变颠倒了,引许多材料证明先有“们”字。“俺”是“我们”的合音,“您”是“你们”的合音,“喒”是“咱们”的合音。此后他接着发表《说汉语第三身代词》(英文)、《论“毋”与“勿”》等论文,其中有好几篇是研究近代汉语(即早期白话)的,开辟了汉语语法研究的一块处女地,代表作有《释〈景德灯录〉中“在、著”二助词》等。
1942年,吕叔湘离开华西大学,改任金陵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研究员。同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他的《中国文法要略》上卷(中、下卷出版于1944年)。这是我国语法学史上的开创性著作之一。吕叔湘的这一著作比起比他大了四岁的王力先生的《中国现代语法》(1943)、《中国语法理论》(1944)以及《中国语法纲要》(1946)等著作,发表时间都要早。
“工具论”辩
吕叔湘的另一个世界,在叶兆言先生的那篇文章里有过描述:
在学问的路子上,俞(指俞平伯——引者注)是出世的,吕是入世的。俞活得像个艺术家,吕更像个有社会责任感的人文学者。只要举几本吕叔湘年轻时翻译的著作就足以说明问题,譬如罗伯特·路威的《文明和野蛮》和《初民社会》,又譬如80年代末期为劳伦斯的《沙漠革命记》写的题记,在这篇字数不多的文章中,他非常清晰地介绍了中东冲突的根源……
笔者如此引述,不过是想说,吕叔湘与叶圣陶,在学问之道上其实是完全不同的两种人。他们可能研究同一个问题,但出发点不同,过程不同。只不过是后来才在语文教育上有了交集。我们的三老中的其他人,有没有吕叔湘先生的这样的世界?其他努力想成为第四老与第五老的人,又何尝能像吕叔湘先生在语言学之外有一个更为广阔的文化世界?
有人认为:中国的语文教育之所以积重难返,原因之一是“语言学家介入语文教育太多”(王丽:《重新确立教育终极目标》,《北京文学》1998年第7期。文章引述的观点来自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童庆炳)。持论者认为,这些语言学家,在语言学界的地位和贡献是不可否认的,但对中国语文教育的影响,有时候是负面的。持论者为何如此持论,只不过是因为语言学家是研究语言的,而语言是一种工具。所以,他们得出的结论就是语言学家如果介入了语文教育,就一定会持语文的工具论。
如此推论,似乎非常符合逻辑。当然,是否符合逻辑,还真的得问问金岳霖们。当然,如此持论者倘或有人去金岳霖先生处问道,似乎又会得出一个高论:什么是逻辑?逻辑学不就是一个典型的工具吗?那么,金岳霖先生一定是一个典型的工具论者。
研究工具,对工具着迷,是不是就一定持工具论?这是一定要甄别的一个问题。还有,这样的工具,与语文的工具,是不是就是一回事?再有,这里的工具,是不是一定导致持论者所谓的“工具至上导致的恶果是急功近利,是应试教育?”
如果这样看工具论,那么,我们又如何理解格律大师杜甫及其惊人的诗歌天才呢?杜甫老来渐于声律细,晚年的杰作《登岳阳楼》与《登高》,于不动声色中,全篇对仗,声律圆润,然而遣词造句却恰如诗人所期待的“语不惊人死不休”。杜甫可谓工具大师矣!杜甫亦可谓语言大师也!
至于刚刚提及的金岳霖,如果以工具论或工具本身论及这位先生,则金先生应为天下第一无趣之人。然而,在西南联大,金岳霖的逻辑课,却一直人满为患。至于金先生的爱情,则更为感人,自始至终都以最高的理智驾驭自己的感情,他终生未娶,爱了林徽因一生。
可见,以语言学家身份而必然应该受到工具论之讥,实在,是一种武断。语文教学的“少、慢、差、费”状态,吕叔湘本人也深切于心。我们又怎么能将此过失放在吕叔湘的头上?
持上述之论者,还引许慎、段玉裁、赵元任等为例,认为语言学家并不是语言大师。
说到语言大师时,我们想到的也是文学家,如庄周、司马迁、韩愈、曹雪芹、鲁迅,而不是语言学家许慎、段玉裁、马建忠和赵元任,因为这些语言学家虽然有丰富的语言学知识,但他们在语文运用上却大大不如文学家。因此他们可以是语言学大师,而不是语言大师。
(唐晓敏:《北师大版高中语文教材主编童庆炳的语文教育思想》。转引自作者博客http://blog.tianya.cn/blogger/post_read.asp?BlogID=1921717&Post ID=16271988)
也许,说及许慎与马建忠,人们可以这样看。但是,段玉裁和赵元任的例子,可能就有点偏颇了。
段玉裁博览群书,著述宏富,由经学以治小学。昔人论之:根基充实,深得体要。著有《六书音均表》《诗经小学》《古文尚书撰异》《周礼汉读考》《仪礼汉读考》《汲古阁说文订》《说文解字注》及《经韵楼集》等书,可谓集语言与文化于一体。
而于1892年11月3日生于天津的赵元任,从小就显露出语言天才,各种方言一学就会。于西方音乐也非常精通。刘半农《教我如何不想她》如果没有赵元任作曲,是否还能在“五四”时期广为流传,可能就成了一个未知数。赵元任十七岁考取留学美国的官费生,在康奈尔大学主修数学,选修物理、音乐。1914年获数学学士学位后,1915年入哈佛大学主修哲学并继续选修音乐,1920年赵元任回国执教清华学校的物理、数学和心理学课程,同年冬曾为英国著名哲学家罗素(B.Russel l)来华讲学担任翻译。赵元任与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被人称为清华国学院四大导师,今人如此枉论赵元任,真不知是真无知还是真无聊。
何况,吕叔湘的语言学治学,不但严谨,也注重趣味。我们从他的《错字小议》《论“基本属实”》《语言的演变》即可发现这一点。其文风一如杜甫的不动声色,但细细掂量,却犹如静水流深,大波若平,非寻常之人可以识得此中真趣。
《错字小议》对报刊上错别字的现象进行了罗列分析,于平实、幽默的文风中,能让人体会到一个语言大师的细腻与亲切。而《语言的演变》则更有趣味了,为了表达“语言如世界上万事万物一样都永远在那儿运动、变化、发展”这一观点,吕叔湘作了直接论述:“语言的变化,短时间内不容易觉察,日子长了就显出来了。”但随即便来了一个比方:“比如宋朝的朱熹,他曾经给《论语》作过注解,可是假如当孔子正在跟颜回、子路他们谈话的时候,朱熹闯了进去,管保他们在讲什么,他是一句也听不懂的。”比方之贴切、生动,是一方面,同时,又立即把这里面的问题全面剖析了出来。这就足见吕叔湘先生的功力与趣味。
吕叔湘之真趣,还可以从一件事看出来。
1986年10月14日至18日,在北京西山第四次现代汉语语法学术讨论会上,吕叔湘讲了话,主要是推荐一篇《光明日报》上报道杨振宁教授谈要研究活的物理学的文章。他抑扬顿挫地朗读了报道的全文。与会的四十多名中年同志和三十多名列席旁听的青年同志领悟了吕叔湘先生这番话的深刻含意:搞语言学也应该追求新的、活的、与现实直接发生关系的东西。吕叔湘引杨振宁的话:“一个青年人应该将他的大部分时间用于解决简单的实际问题,偶然做一些难的问题,而不应该专一处理深奥的根本问题。”
有谁能想到,在这样一次学术讨论会上,吕叔湘并没有像平常那样拿个学术报告,照本宣科,而是另出机杼,心裁别出,最后拿杨振宁的话来为其学术报告作结。
从这一件事,我们是否能想到另一点:在吕叔湘看来,语言研究的最高境界,语文教学的最高境界,恰恰如陆游所言:“汝果欲学诗,功夫在诗外。”语文学习最重要的方法,在于执教者本人或语文教育理论研究家本人,需要构建起自身的两个世界。这样,一个人的知识结构,才构成了一种相互回望与对话的可能。有了这种相互回望与对话的可能后,语文修养才会与一个人的另一半形成一种相得益彰的效果。
而吕叔湘如此通人,则已经形成了自己的两个世界。即便是在语言学领域,吕叔湘也仍然是将汉语言研究与英语研究都做到了极致的程度。
然而,恰恰是吕叔湘这样的大师,却被人认为是语文教育的扼杀者,我为此不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