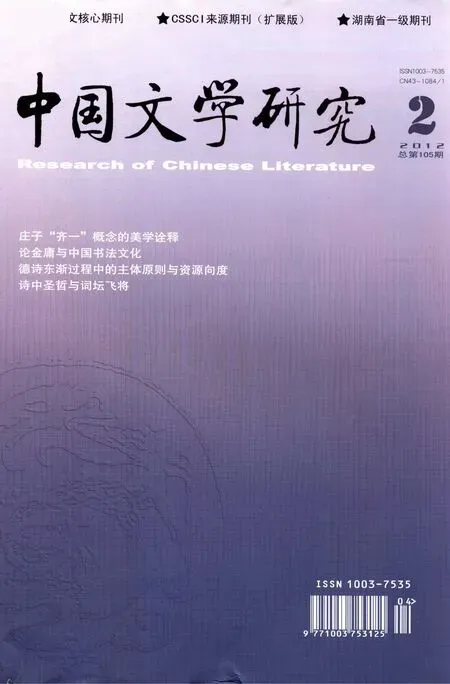海外华文文学有别于中国文学的特质
——以海外新移民文学为例
[澳]庄伟杰
(华侨大学华文学院 福建 厦门 361021)
当我们把审美文化镜头 对准包括中国(大陆)文学在内的整个华文文学世界缓缓扫描时,一道道属于散居海外各地的华文文学风景线组成的文化景观,就会清晰地凸现在我们面前。参与构筑这个华文文学海外景观的诗人、作家则如星星之火,燎原于浩淼的星空,无论在北半球的欧美加、还是南十字星座下的澳纽,无论在西方的星辰月色、还是东方的文化星空。海外华文作家们犹如星光缤纷闪烁于辽阔的天幕,或以诗情画意让母(汉)语芬芳在回家的路上。尽管他们的文学成就宛若春兰秋菊,在艺术风格上也是争奇斗妍,但他们笔下的故国想象或异域风光的动人描述,仍然有着其共同的底色,潜藏其中的中华情结则在他们的文本世界中一脉相承。在某种意义上,又与中国本土文学共同汇合成气象万千的“大中华”文学图景。
然而,海外华文文学毕竟有别于中国本土文学,盖其源在于其生成于异质文化语境中,即两者所处的文化背景、地理位置、作家自身身份等因素而形成差异性。由于空间位移所带来的深层文化原因,海外作家们所呈现的文本世界潜隐着诸多层面的各自不同的价值取向和美学观念。如果我们仅以单一的文化眼光去加以审视,就难以感知和把握其中丰富而复杂的文化内涵。或者我们只是以求“同”多于探“异”来理解阐释,同样无法破解海外华文文学自身已然形成的话语谱系。众多的迹象表明,海外华文文学中“异”的文化特质所构成的文学世界异彩纷呈,尤为值得我们关注和思考。遗憾的是,国内批评界和学术界长期以来对海外华文作家、学者在推动中华文化文学走向世界的作用,往往未能深入而全面地给予足够的重视。“事实上,在海外华文作家作品中呈现出来的那种文化的‘混杂性’,在客观上已成为当前世界文学进程中的一道独特的‘风景线’,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全球化语境中出现的文化文学的多样性。因为这些作品是介于两种文化之间的,有母体文化的特征,也有‘异’的文化质素,可与本土文化文学对话,也融合有某些世界性的‘话语’,有可能跻身于世界移民文学的大潮中,有助于中华文化文学走向世界。”〔1〕(P4-5)海外华文文学色彩多样的文学文本,有着诸多值得我们观照的理论问题。只要我们进行新的理论阐释和探讨,或在相互参照中,就可能发现海外华文文学和中国本土文学两者之间,除了有某些文学共相和作为文学自身的特殊规律外,由于华族文化向外位移和流散于域外之后的创造性转换和重建,在文学形态和审美书写等方面具有自己独特的、有别中国本土文学的新质。基于以上思考,我们不妨以海外新移民文学为例,从共时态的横向关联上,就海外华文文学有别于中国本土文学的特质或因素加以对照探析,并寻找出其中带有启示性的价值意义。
特质之一:具备故土与新土的双重经验,尤其是域外经验,对生命和生存体验拥有更多层面的深切理解并格外动情,视野更见开阔,作品呈现出带有独特情调的另类色彩。
随着时间的推移,大部分新移民作家在海外接受到不同文化意识的浸染,感受到不同的审美体验,审美价值取向自然也逐渐发生变化。其表现视野较之中国同期作家更为开阔,这与作家自身的生命和个体生存体验有关。因为新移民作家出国前大多在中国接受过良好教育,或已走向社会,拥有一份较为理想的职业,皆具备一定的人生阅历和生活积累,即对母国的人情世态几乎了如指掌。他们曾经拥有的经历,像一条河流不只是横陈于自己的身旁,其实也流进了身体,注入了血脉似的。一旦跨疆越域,落脚到另一个新的陌生的空间,犹如在浪峰与波谷之间航行,心灵的投影,在其间或起伏转折,或推波助澜,既有激情的浪花,也有理性的堤岸。这种特定境遇中凝聚的人生经验,比起同期国内作家来说,显得更为沧桑、逼仄,也更辽远。他们心灵绵延的长线在异域阳光下晃动,而梦想似是悬舞于岁月的长空。于是,个体生存境况、文化碰撞摩擦、思想情绪波动,在一路走向幽深中将时间浸泡,将空间更多地延展。这些都是国内作家所难以体验到的。尽管经验并不是什么神秘的东西,但人在域外,特定的经验对于这些华文作家却如个人心灵的漂流融入历史长河的潮汐之中。这种经验并不一定有固定的形式,甚至不必讲究任何形式,也能滋生出心灵的长度。更多的时候,这种经验像万物生长时暗藏的念想,悄然注入每个人的生命韵律,进入每个人的精神境地。它比现实更梦想一些也更沉重一些,它比梦想更现实一些也更朦胧一些。于是新移民作家对生命、对生存、对梦想的体味拥有更多层面的深切理解,现形于色,现态于行。当经验以母语的形式不断从心灵里漫溢出来,或者可以将人们引领到广阔的新天地,或者可以让我们看见到那遥远的去处。像高行健、卢新华、杨炼、北岛、严歌苓、虹影、桑烨、刘索拉、祖慰、林湄、陈河、李彦等等作家,本来在国内已有着相当丰富的人生历炼,也有过高质量的作品问世。流散于海外之后,即便时过境迁,但多少况味,连同过去的一切在心灵里留下的痕迹,便成为一种记忆,无论是欣慰或苦恼、还是微笑或疼痛,无形中都折射出自己难以忘怀的一段心灵史和命运史,也是对人类文明进程的一种形象反映和凝视。严歌苓曾这样说过:“侥幸我有这样远离故土的机会,像一个生命的移植——将自己连根拔起,再往一片新土上栽植,而在新土扎根之前,这个生命的全部根须是裸露的,像是裸露着的全部神经,因此我自然是惊人地敏感。伤痛也好,慰藉也好,都在这敏感中夸张了,在夸张中形成强烈的形象和故事”。〔2〕(340)加之海外经验让作家们有机会将昨天与今天、过去与现在、祖籍国与移民国、东方与西方的方方面面形成比照、加以审视。他们一路走来,栉沐欧风美雨,品尝月缺星寒,涌动过念的起伏,闪烁过梦的幻灭,不禁五味迸出,声色俱下。其写作资源更为丰厚,题材选择更为多元,驾驭技巧更为从容,只要注入深沉的思考和独到的眼光,铺展的文字所架构的文本就显得更有厚度和纵深感,自然给人留下更多值得深思和再造想象的空间。如严歌苓的《无出路咖啡馆》、《女房东》、《人寰》等多部长、中、短篇小说,一直在海外新移民文学领域独领风骚,她以经验叙事方式创造性地推出一系列史与诗的张力营造的佳构,标志着新移民文学有着和中国本土文学相同而又有别的文学精神和质地。张翎的《雁过藻溪》、《望月》、《交错的彼岸》、《邮购新娘》等作品,无论是题材的拓展、还是心灵追寻的指向,无论是交错于原乡与异乡之间、还是对一代人命运的理性思考,不仅具有深刻的认识价值和审美价值,而且蕴含深远的文化意义。
海外新移民文学之所以形成了自身独特的价值形态和文化风貌,源自于“生命移植”的文化撞击和丰富体悟,源自于站在中西文化语境交接地带的反观和深思。对此,美国华文作家沈宁如是感触:“在对作品题材的选择上,海外华文作家更愿意表现家庭生活,个人性格等题材”,不像中国作家习惯于“重大历史题材,或色情题材,清官反贪题材,名利追求成功题材等”;而“在对故事的表达上,海外华文文学作品,大多保持较传统的结构和叙述方式”,中国作家则喜欢“超现代形式,不点标点,故意消除时序等”;“在语言的运用上,海外华文作家会喜欢更真实,更轻松,更日常,更幽默的文字”,中国作家则喜欢“一本正经,死板面孔,大话空话等等。”〔3〕(P212)相形之下,海外华文文学作品(优秀的)往往呈现出带有独特情调的另类色彩而有别于中国文学及中国意识。比如新移民文学里所表现的独特异国情调,展现了西方“他者”的基本面貌,为当代文学提供了富有说服力的西方形象的文本。可见,由于长时间受居住国文化氛围和生活气息,包括社会思潮、经济体制及政治气候等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尤其是西方多元文化政策的自由与宽容,特别是随着写作主体审美体验的转变,驱使海外华文作家的文学书写和文化精神得以成为一种独立自足的艺术存在。
特质之二:置身异域,中西两种思维方式的碰撞与交融,华文作家看待事物、思考人生和关注问题的视角更趋开放和冷静,海外华文文学日渐凸显出一种新品格。
无庸讳言,海外华文文学和中国本土文学有着千丝万缕的“割不断,理还乱”的文化血脉关联,即同文同种的族群意识,文学观念和思维方式同样延续和传承了“五四”新文学的传统,还有作家内心一脉相通的文化意识诉求等等。但空间位移带来了社会环境的不同,华洋文化的交融混杂以及审美价值和文化身份的恍然转变,使得新移民作家的写作行为转化成文学的移植,因为移民不仅是身体或生命移植,也是文化的移植。跨出国门,置身异域,浪迹天涯,眼界开阔,身处多元文化、东西方文明碰撞的交汇点上,可以广览博采世界各种不同民族文化的精华来滋养、丰富和完善自己,具有生物学上的“杂交”优势。于是,立足于两种或多种文化的交叉边缘地带,在非母语的国度用母语来表达自身的文化诉求和精神寄托,“带着超越者的冷静,观看身旁的风云翻卷”。〔4〕(P80)其明显的优势一旦体现在创作中,让华文作家看待事物、思考人生和关注问题的视角更趋开放和冷静,这是同一时期国内作家有所或缺的。正因为如此,才诞生了像高行健的《灵山》这样的扛鼎之作,同时也产生了一些颇为深刻清醒且富有哲思性的重量级文本。例如,荷兰华文女作家林湄的长篇巨著《天望》,内蕴诸多生存况味和生命意味,其中在对待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上,其文本更为重视人的个体价值对于自然的理性超越。女作家以人类自身的生存处境与自然天体的相互交织来叩询文明及寻求生命意义之所在。她视宇宙人生为认知存在的对象,企冀在宇宙之外寻找能超越存在的主体。她笔下的主人公弗来得,在贪婪和物欲、冷漠和恐怖的现实中,视金钱为粪土,坚守“人的最高特性是神性”,并渴求对上帝的虔诚和对人类的博爱去拯救世界,争取天国的大奖。而其来自中国的妻子荣微云,身居异域,即便衣食无忧,依然怀着生为渔家女时的神祗信仰,确信保佑她平安幸福的是海神。她需要有一个安定的家,一种实实在在的生活。这是不同民族的思维方式所体现出的文化差异性和特殊性使然——
从宏观上讲,在对待“人”与“自然”关系问题上,东方人认为宇宙是有情有理的,“人”与“自然”有天人合一的感应。西方人则将“自然”作为认知的对象,希望在“自然”之外寻找一个超越存在的本体。在对待心灵的问题上,东方人重内而轻外,着重人的“性情”和“情理”,人无“性”无“情”不可为人,强调“心”的作用和自省自足,认为“心”与世界本原或本体相通,不需要外找,注重情理的超越,主张自我完善自我实现。西方人则重视“知性”和“理性”,强调“力”的作用,力求运用科学技术,“探知”外在世界,达到“认识”的超越。〔5〕(P2-3)
置身异域的边缘作家,中西两种思维方式的碰撞与交融,其视野里的人事风景别有洞天,于是对待事物、思考人生和关注对象的视角,往往与中国本土作家有所区别。林湄笔下的主人公弗来得是通过传道济世的方式来完善自我人生的,哪怕现实世界中的科技文明进步与社会的堕落和人性的贪婪并不协调。这是对人类心灵知性的探寻,显然与中国文学中自我完善由内而外的认知不同,是对东方文化中‘人’与‘自然’天人合一的超越。或者说,作家在关注东西方文化冲突、碰撞、相互接纳和融合的同时,更注重对现代人灵魂的窥探,即人的精神归属问题。因此,“从她的小说中我们不仅看到了欧洲的异国风情,看到高度发达的现代文明社会中的影影绰绰,看到离井背乡的生灵的血与泪,更主要的,在她所展开的生活图景和命运波澜中,我们更感受到一种理性的呼唤,一种充满爱和体恤的情感的冲击。这种高远的创作意向,显示了华文文学的一种新品格,也给今天国内文坛一种新的启示。”〔6〕
海外新移民作家表现中西两种文化的碰撞和交融的作品不胜枚举。具有相当代表性的还有王小平的小说《刮痧》。它同样向我们传递这种信息提供了一种别出心裁的“证词”。小说围绕给生病的孩子刮痧是否构成对孩子的伤害这一焦点展开,反映了一个让生活在美国的男女主人公撕心裂肺,面临着家离人散局面的故事。情节的冲突,东西文化的隔膜,情感心理的震荡,说明新移民走出国门之后,带着自身文化的思想观念、价值判断、思维方式和生活习俗等文化特征和民族烙印,走向异域的全新生活与文化环境中,必然会与这一新的环境发生多层面的冲突。但文化的特殊性并没有因为碰撞交流而消失,反而沿着各自的轨迹不断向前伸展。引人深思的同时,触发了我们对不同文化做出更为深入的思考,或以一份宽容的心态,尊重差异,寻求沟通。
特质之三:面对国家政治、文化身份和自我认同的观念及在理解上发生质的转变,华文作家的整体心态更为自由,作品中既有自觉的“世界公民”意识,又有强烈的纪实性或自传性色彩。
在后殖民理论家萨义德看来,移民身份本身的属性就决定了他们无论是从现实经历的角度、还是从文化心理的角度,相对于居住国文化来说都有一种异质性。这种由东方移民身份而导致的文化上的“异质性”,本身处于一种“他者”的地位。“他者”作为“本土”的对应物,所强调的是客体、异已、国外、特殊性、片断、差异等特质,以显示其外在于“本土”的身份。新移民文学从本质上可看成是一种跨越文化经验的流散性写作,由于人在海外的生存境遇和个体心理状态不一,加之身份认同和文化属性的问题始终悬搁着,对事物的感受不尽相同。随着新移民逐渐获得所在国国籍,作家们会从中西文化夹缝里的新移民心态的表现,转向对生命本身价值的探寻。
然而,在中西文化的界限日趋模糊的今天,要真正把握新移民的“自我”的本质和共性似乎变得越来越不可能。对他们而言,“自我”与“中国人”、“中国文化”固然有着深刻的联系,但其实质更多地显示为中西文化、传统与现实关系之间持续不断的互动、对话和调整。尤其是随着时间的嬗变,新移民在经济状况和社会地位获得提升之后,逐步融入居住国的本土文化,种族观念会越来越趋淡薄,并对“自我”和与自己关系一度最为亲近的文化传统给予重新审视和认识。一方面他们自觉地寻求生活的多元和变化,另一方面又企冀寻找一个可以诗意安居的精神家园。此外,随着新移民作家对生活的体验日渐丰富和深刻,他们关注视角的投向更为广阔,或从眼前返向过去、或由外在走向内心纵深处开掘,得以超越国家、政治、种族和文化的界限,对具有普遍意义的人性展开深入的思考和表现,摆脱了最初的肤浅和浮躁,重新赋予文学以人文关怀和深度模式,并对自己的文化身份有了更为理性的认知,“世界性”也随着生活方式的改变,悄然地走向他们的意识深处,从而以更加开放的眼光和文化理念,以及更具包容性的胸怀对人类共同的命运加以关注和表现。这种带有世界性的文学具有独特的价值,是介于两种或多种文化之间的文学书写,在本土与他者、看与被看之间,以其另类特征而跻身于世界移民文学大潮中。诚如霍米·巴巴所言:“最真的眼睛现在也许属于移民的双重视界(double vision)”。我们从石小克的《美国公民》、《基因之战》等小说中,可以看到新移民在经历了多元文化价值观的较量与碰撞、排斥与吸引、融汇与扬弃的过程中,具有更加开放的文化理念和更为活跃的文化因子,从而生成更强的文化适应性。这种自觉的“世界公民”意识和生存经验,在严力、严歌苓、哈金、小楂、薛海翔等作家的文本里同样有着大量的尝试。《北美漂流》中的杨帆就时常以“世界公民”来定位自我。她跨国纵情游历,超越种族与人际,热衷于能够超越局部视野的文化混杂,以此来理解或观看现代社会里人类与个体生命存在的意义。这种“世界性”文化视野的确立,让新移民作家透过跨文化语境来构造笔下异国的故事。对于这种情形的认知和表达,是同期内中国本土作家所难以获得的,也是当代新移民作家比起他们同在海外的前辈华文作家最为突出的特色之一。
诚如任何事物的发展都会经历不同的历史阶段一样,初到海外的华文作家似乎特别善于将自己或他人的生活经历以小说文本的形式反映出来,让读者分享自己的人生经验或在海外挣扎求存的经历感受和某段心路历程。这种在不同程度上带有自传色彩的作品,尽管良莠不齐,却不乏精彩厚重之作。其实,中外举凡名篇名著,特别是作家的代表作或成名作,大多带有自传性色彩。“写作无论什么形式,都带有自传的性质。”因而,“写来写去,总离不开自己;自己,自己,从哲学从诗性找到根据,并以此自慰。”〔7〕(P1-2)当我们在共时态中作横向观察,就会发现,海外新移民作家中带有自传色彩或纪实叙事的作品堪称铺天盖地,这是同期内的中国文坛甚为鲜见的一种“奇观”。即便是写故国生活题材的作品,也注入诸多自传性元素。最具代表性的有高行健的《一个人的圣经》、严歌苓的《一个女人的史诗》和《穗子物语》、虹影的《饥饿的女儿》、闵安琪的《红杜鹃》、张戎的《鸿:三代中国女人的故事》等作品,他(她)们要么写自己曾经拥有的过去,要么写家族的历史,个人性、倾诉性、经验性成为其显著特色。至于纪实性写作,所占的比例则多不胜数。如旅居美国的沈宁,多数作品是纪实之作,《美国十五年——我如何闯入美国主流社会》、《战争地带——目击美国中小学》、钱宁的《留学美国,一个时代的故事》,等等。这些作品,重新释放了大写的“人”的生命能量,修正过于强大乃至于膨胀的国家话语对个人空间的挤压,使新移民文学成为一种个人话语占上风的叙事模式。其价值取向,我们不妨理解为他们试图在跨文化时空语境中,对于自我意识和个人价值的重构。
特质之四:不同历史境遇与文化语境构筑的“文学场”不尽相同。海外华文文学属于边缘性的第三文化空间,既对中国文化传统进行深刻反思和批判性重建,又为我们带来了一种新的叙事语言空间。
不同历史境遇与文化语境所构筑的“文学场”是不尽相同、各有千秋的。或许,存在(在场)的就有其合理性。海外华人所建构的文学场,自有其本身的文学文化价值。借助流散写作和流散现象来加以观照,我们可以从一些优秀作家的文本世界里读出不同的滋味。因为在海外华人作家那里,笔下更多的是展示以华人生活为题材的文学图景。这种流散(写作),驱使华人作家们用中国文学传统、尤其是五四以来的新文学传统来唤醒自己的汉语创造力,从而在海外的“旅行”中再造了(re-in-vented)一个和海外(居住国)紧密相连的“文化中国”,即再造了一个自己心目中向往的精神家园。
如果说,我们把海外华文文学当成为独立于中华文化母体之外的边缘性另类文学场域,并称之为“第三文化空间”有其充分的自足性和合理性的话,那么,同是用汉语书写的海外华文文学,既不属于所在国的主流文学,又不同于本土原创的中国文学,而应是在超越了语言、族群、宗教、社会和国家体制后的多元混合体。以此推论,海外华文文学存在的重要意义,乃是其与中国本土作家书写的当代文学之间存在着本质异同,呈现出一种“前连互动”的互文式的对应和关联。从这个角度讲,海外华人作家的域外经验以及所构筑的文学场——第三文化空间,的确在他们的写作中显示出自身的文学特性和独到的影响力。从知识谱系中的文学地形图上,将其置于和中国本土文学的联系比较,起码有两大方面值得我们注意。
一是对中国文化传统的深刻反思和批判性重建。海外华文文学对中国文学传统(古典美学)的继承是显而易见的,无论是新移民文学中那种漂泊异域、心系故土的中国情结所体现的流浪意识,还是所表现的异国情调,乃至提供的大量中西关系的隐喻方式。但新移民文学又有不同于古典诗学的另一面,其自我放逐的流浪意识体现在作为文化边缘人的文化认同危机。俨如一方双面镜,新移民文学使中西方文化“镜像”得以映现,内蕴诸多丰富的文化信息和意味。对此,旅美女学者陈瑞琳以在场者的姿态发表过看法:
近20年的北美华文文学,带给人们的震撼首先是海外移民作家面对西方异质文化及自己的母体文化所做的精神挑战。加华作家中更以近年来蜚声文坛的“新移民作家”的创作显得声势凌厉而浩大。他们的一个突出精神特征就是勇于在远隔本土文化的“离心”状态中重新思考华文文学存在的意义,并能够在自觉的双重“突围”中重新辨认自己的文化身份,同时在“超越乡愁”的高度上来寻找自己新的创作理想。纵观北美近20年来的海外新移民文学创作,先是由“移植”的痛苦,演绎出“回归”的渴望,再由“离散”的凌绝,走向“反思”的“超越”,这样一条清晰的精神轨迹在加拿大的新移民作家群中得到了生动而充实的体现。〔8〕
由于面对着来自两大文化的挑战,一方面是新移民作家的特殊知识结构及其在国内成长的历程,对文化传统的批判意识已内化为一种经验或精神觉醒;另一方面是他们置身于异质土壤接受着另一种文化的洗礼,对身后传统的反思追问,为他们带来重新认识自我和认识世界的契机。我们从卢新华的《紫禁女》、严力的《母语的遭遇》、严歌苓的《扶桑》、查建英的《丛林下的冰河》、曹桂林的《北京人在纽约》、鲁鸣的《背道而驰》等作品中均能或多或少地看到新移民作家对中国文化传统进行批判和反思的态度,《紫禁女》则海外新移民文学提供了一个富有独特性的隐喻文本。“紫禁女”石玉这个人物形象身上,有着太多的象征意味和丰沛的再造想象空间。从紫禁城(封闭而古老)挣脱出来寻机打开自己走向世界(开放而独立),主人公的个体悲剧命运也是一个民族集体遭受的命运悲剧之象征。作家卢新华较之于同时代的反思文学作家站得更高,看得更远,想得更深。他透过跨文化的眼光去观照和检视中国文化传统,融入自己在中西方积淀的切身感受和体悟,以其独有的视角和敏锐的触须,隐约传达出一种历史的纵深感和沉重感,反映了新一代华人移民从艰难跋涉到走向自我解放与拯救、提升与发展的曲折过程。这部交织着浓厚意味的生命悲痛和文化情怀的沉郁之作,在某种程度上,是对中国当代反思文学的超越。
二是为我们带来了一种新的叙事语言空间。对于那些有着思想深度和审美高度的作家而言,创造并拥有自己的语言空间或话语方式,为读者带来再造艺术想象的空间,无疑的是一个作家思想艺术臻达于成熟的标志。海外华文作家的跨文化经验、世界性视野和融合中西两种文化理念的思维方式,常常让呈现的文本在形式上营造出一系列新的质素。因此,只要继承中国古典审美意蕴的精华,又灵动地吸收西方现代文化的营养,就有可能构成一种让东方神韵和西方现代意识交相并举的独特美学风貌。
海外新移民作家语言叙事空间的形成,主要体现在文本叙事策略与个性化话语的形成,充分反映了人在海外经历的跨文化经验,表明他们因空间位移之后,带来了新视角和新观念所引发的对世界进行重新思考的可能。针对海外华语写作,严歌苓深有感触地说:“既游离于母语主流,又处于别族文化的边缘。游牧部落自古至今是从不被别族文化彻底认同,因此从不被异种文化彻底同化的。但它又不可能不被寄居地的文化所感染,从而出现自己的更新和演变,以求得最适当的生存形式。这里生存形式决定我们在文学中的表达风格,决定我们的语言——带有异国风情的中国语言。”〔9〕(P109)我们只要透过海外新移民文学中的女性自我书写,就不难发现,她们的笔下大多把中国女性命运的发生、发展和改变的过程,置之于不同文化的互动链中,让丰富而复杂的历史风貌得以多角度、立体式的呈现。要么以一种“我手写我心”式的原创性文风,要么以独具的慧眼与角度以及非凡的表达,形成为或繁富与简约、或素朴与瑰丽、或平淡与性灵、或现代与古雅等相互交揉的叙述方式和多重转换。这种跨地域、跨时空、跨语境的自我书写所营造的话语空间,可谓是家园之外的家园书写,是在异质空间里的东方冥想,甚至罩上一层梦幻般的神秘和悲情化的诗意色彩,从而构成为时空的重合、分裂、交错,既扩大了叙事空间,又深化了主题意蕴。如张辛欣自传体小说《青春遗址》、张戎《鸿——三代中国女人的故事》、杨瑞《吃蜘蛛的人:一份关于文革的个人记忆》、虹影《饥饿的女儿》、钟丽思《顽童的时代》、王小慧《我的视觉日记》、曹明华《世纪末在美国》等都是颇具代表性的文本。严歌苓的书写文本所呈现的那些淡雅柔和、淳朴委婉与异国风情的东方神秘并举的叙事方式堪称领异风骚。在《母亲与小鱼》与《失落的版图——告别母亲》中,以一种融入叙事而不着痕迹的笔法状写人生,表面看起来自由松散,如同信马由缰,一路走来却铺展一幅幅人性的画卷。如此体悟精妙之笔,既绵密细腻又步步为营,在一种开放却不露痕迹的语言环境中,探寻作为个体存在的多种可能性,蕴含着现代人的价值选择与精神取向的多样化。
可见,新移民作家那些带有纪实性的自我书写和融入自身的生命体验所营造的文本结构,是一种坚执的、有背景的、可验证性的生命过程的舒缓铺展。生存境遇、个体生命、双重视界等所构成的语言文化,一旦通过分裂或互否,就能达到新的有机组合。这种文化策略,乃是试图通过个人的声音打通中国与世界的阻隔关系,让文学成为一种重要的文化交流渠道。确切地说,是让自身固有的文化融入异质的因素,促使其在革新和变化中日渐丰盈,同时寻机向西方主流文化输送新鲜的思想表达。从写作视角来看,乃是以人类性的文化大视野,把个人忏悔意识和民族自省意识加以清醒的展示,开创性地对个人心灵自省、成长道路追寻、家族隐私披露和民族精神拷问等维度,进行历史的包括人的精神领域的一系列探究和反思的书写方式,为中国当代纪实性写作提供一个有力的参照。而个性化的生存观念和个性化的生命历程,需要个性化的叙事方式。体现在个性化话语风格的形成上,则与中国大陆纪实文学中的“大合唱式”的同声共音模式不同,其在叙事方式上更新了中国本土纪实性书写的话语模式,拓展出富有个人性和个性化的新的审美表现形态,为我们打造出另一种新的语言叙事空间。
值得一提的是,新移民作家尚有另一与中国本土作家明显不同的优势,即双语写作并行。德国汉学家顾彬批评中国当代作家不懂外语的劣势,这观点固然值得商榷。但一个作家,如果能凭借其语言优势,游刃有余地穿行在双语或双重文化两个世界之间,肯定利大于弊。我们从老一代的林语堂、张爱玲等身上、从新移民作家中的高行健、严歌苓、李彦等那里可以看出,拥有了至少精通两种语言能力所带来的某种优势是不言而喻的。
无论从何种角度出发来审视海外华文文学、尤其是新移民文学,都是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文学生长空间,也是当代华语文学研究中一个重要的生长点。从新移民作家所生产的大量文学作品,我们不仅看到了一个内容和风格多样化创作群体的成长,而且发现了其写作带来的有别于本土中国文学的特质等态势。作为一种在跨文化语境中出现的历史性文学现象,新移民文学并非不能诞生大作家。在世界文坛上,历史已为我们诞生了索尔仁尼琴、康拉德、奈保尔、纳博科夫、昆德拉等响亮的名字,并留下了他们各自独特的声音。事实表明,一个作家未必只有固定在自己母语中才能写出好作品,在异国非母语的环境中用母语从事写作并不阻碍伟大作家的登场。相反的,不同语言环境和文化氛围常常触发作家们对自己母体文化产生新的想象和新的思考方式,让身处边缘的作家拥有更多可资利用的创作资源。对于海外华文文学而言,新移民文学的浪潮方兴未艾。大批的海外作家, 在坚守文学的同时其实就是坚守精神家园。他们的创作则丰富了整个华人文学世界。“移民作家的鲜明特色正是体现在他们游走在两种文化的边界,在社会责任与艺术诉求之间、在忠诚与背叛、抵达与回归的矛盾中挣扎徘徊。而我们的传统文学和评论,多是在固定的山川下写人事的沧桑变化,海外的作家却是要面对山川土地的巨变来写人的坚守,这显然是一个巨大的挑战。”〔10〕(P26)即集中体现在跨国写作对传统写作的“挑战”。其拥有的机遇、潜力和亮点,恰恰是海外华文文学提供给中国本土文学最有价值的思考,也为新世纪全球性文化时空和电子传媒时代的文学创作与批评提供了一个鲜明的参照。
〔1〕饶芃子.海外华文文学研究的新视点——海外华文文学的比较文学意义〔A〕.世界华文文学的新世纪——第十四届世界华文文学国际研讨会论文选〔C〕.吉林大学出版社,2006.
〔2〕严歌苓.少女小渔·后记〔A〕.洞房·少女小渔〔C〕.春风文艺出版社,1998.
〔3〕(美)沈宁.海外华文文学创作比较和分类研究初探〔A〕.多元文化语境中的华文文学——第十三届世界华文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C〕.山东文艺出版社,2004.
〔4〕陈瑞琳.横看成岭侧成峰——北美新移民文学散论〔M〕.成都时代出版社,2006.
〔5〕林湄.边缘作家视野里的风景〔A〕.天望〔M〕.长江文艺出版社,2004.
〔6〕陈美兰.“抬起头来,为大地创造意义”——读长篇小说《天望》〔J〕.文艺报,2006年4月15日.
〔7〕蔡其矫.流浪汉的品性——庄伟杰诗集《精神放逐》序〔J〕.精神放逐〔M〕.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4.
〔8〕陈瑞琳.“离散”后的“超越”——论北美新移民作家的文化心态〔J〕.华文文学,2007.
〔9〕严歌苓.中国文学的游牧民族·波西米亚楼〔M〕.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2001.
〔10〕陈瑞琳.北美草原上温柔的骑手——悦读林楠的《彼岸时光》〔A〕.彼岸时光〔M〕.香港大世界出版公司,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