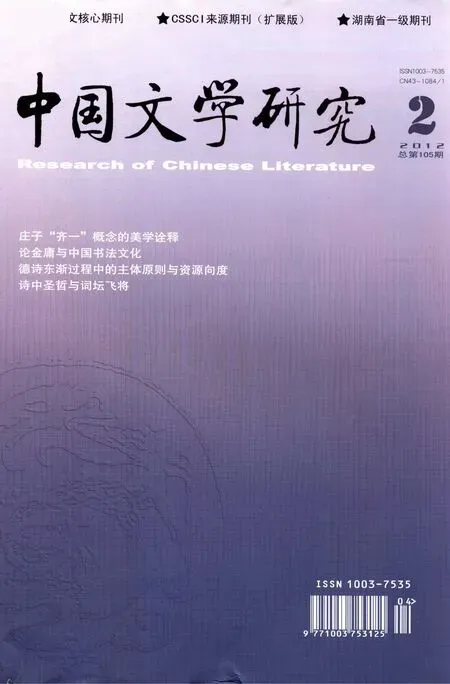“残损”之维:戴望舒诗歌另类意象解析
张文刚
(湖南文理学院学报编辑部 湖南 常德 415000)
作为“雨巷诗人”戴望舒,人们更多的是只看到他诗歌美丽和寂寞的一面,感受那种纯净的抒情气息和风格,领悟因爱情的吟唱带来的朦胧诗意和向往,而对于他诗歌河床中的另一类意象以及由此带来的斑驳的色彩和深沉的内涵缺乏必要的解读和分析。有别于“雨巷”式意象的典雅和悠长的韵味,戴望舒诗歌中的“残损”类意象以其现实的残缺感和心灵的伤痛感,更逼近生活的真实和心灵的真实,更具有现代色彩。这是戴望舒诗歌中值得引起我们注意并加以剖析的一类诗歌意象,惟其这样,我们才能找到和还原一个完整的诗人戴望舒,也才能体味作为现代派诗人戴望舒其诗歌文本的丰富内涵和艺术感染力。
一
戴望舒诗歌中的“残损”类意象主要有三类:自然类残损意象、人生类残损意象和社会类残损意象。
自然类残损意象主要体现在戴望舒的早期诗歌创作中。在戴望舒早期诗歌的锦词妙句中,处处可见残月、残阳、残叶、枯枝、残碑断碣这一类意象,就连《雨巷》这样纯美得近于天上仙乐的诗歌,在“油纸伞”的背后也隐现着“颓的篱墙”;而有些诗歌就干脆在题目中贴上“残损”的标签:《残花的泪》、《残叶之歌》……翻开他前期的诗作,映入我们眼帘的,几乎全是泣哭的残月、寂寞的古园、幽暗的树林、微茫的山径、抛残的泪珠和青色的魂灵,这些词汇所构成的意象无不反映了戴望舒前期创作心态中的烦忧苦恼意识之深重。“我们细读他前期诗作,可以明显地感到戴望舒对现实人生充满了苦恼和失望,并企望在自造的幻觉中为破碎的生活寻求一个新的支点。”〔1〕(P326)这类抒情意象在戴望舒的诗作中,多半是一种“点缀式”、“镶嵌式”的意象结构,亦即在写景抒情的过程中,因情赋景,借景写情,随意而恰到好处地穿插一些自然意象的残片和断章,借其破碎、枯槁和黯淡的一面以抒发和营造一种失意、苦闷乃至悲凉的情绪和氛围。
人生类残损意象则直指生命的存在和感受。当遭遇爱情的失意、婚姻的波折和社会的动荡时,诗人就把先前赋予自然万物以残损之形的眼光挪移到人自身,写人的生命的破碎、凋残和精神的痛苦。在戴望舒的诗作中随手可拈来这样的诗句:“我的唇已枯,我的眼已枯,/我呼吸着火焰,我听见幽灵低诉”(《Spleen》);“泪珠儿已抛残,/只剩了悲思”(《生涯》);“它存在在喝了一半的酒瓶上,/在撕碎的往日的诗稿上”(《我底记忆》);“我说,我是担忧着怕老去,/怕这些记忆凋残了,/一片一片地,像花一样;/只留着垂枯的枝条,孤独地”(《老之将至》)。那首短小而充满智性的诗作《白蝴蝶》,看起来表现的是一个完美的意象——蝴蝶,实际上在这个完美意象的翅翼下,包含着大的残缺和不完美。那只小小的白蝴蝶,“翻开了空白之页,/合上了空白之页”,在“开”与“合”之间,隐含着人生的大通脱、大智慧:生命不就是那只“白蝴蝶”吗?变幻不定、飘忽无常、空虚寂寞,种种不完美不就拼成了人生残缺的图景吗?荣格说,一件伟大的艺术作品就像是一场梦,它并不给人以解说或提示,但以其幻象标示着一种诗意的存在〔2〕。这首《白蝴蝶》虽谈不上是“伟大的艺术作品”,但包含着令人遐想和咀嚼的诗性内容。被视为戴望舒的代表作之一的《断指》,在对生命的审视中具有了更丰富、更切实的人生内涵。这首诗用“他者”的眼光,既表现了“断指”和“爱情”的牵连:“‘为我保存着这可笑又可怜的/恋爱的纪念吧……’”;同时又将“断指”与“革命”联系起来:“这断指上还染着油墨底痕迹,/是赤色的,是可爱的,光辉的赤色的”。“断指”储存着爱情的悲哀的记忆,更浸染着现实的风云和革命者的人格光辉。正因为这样,在诗人看来,“断指”就成为了人生的“珍品”,因而残损的生命就成为了生命走向完美和崇高的一种激励:“每当为了一件琐事而颓丧的时候,我会说:/‘好,让我拿出那个玻璃瓶来吧。’”这首诗歌在写实的基础上加进了个人的生命体验和感悟,因而显得格外真切和动人。难怪艾青称赞《断指》是戴望舒“在抗战前所写的诗中最有现实意义的一首诗”〔3〕(P3);孙玉石也认为:“比起《雨巷》的惆怅迷茫来,《断指》则展示了诗人另一番内心世界的景象。这里没有彷徨者的苦闷,而别有一种在宁静中激励自己奋斗的情怀。”〔4〕(P65)这首诗虽然涉及到人生的社会意义,但还保留着爱情的神秘面纱和朦胧意绪,有一种试图融爱情和革命于一体的写作冲动,显然带有一种过渡的性质。到后来《元日祝福》、《我用残损的手掌》等诗作的出现,诗人则在对生命的注目中融进了更多的社会内涵和现实意义。
社会类残损意象可以把《元日祝福》视作一个起点。这首诗创作于1939年的元旦日。可以说这是戴望舒第一次把目光聚焦于苦难的土地:“血染的土地,焦裂的土地,/更坚强的生命将从而滋长。”显然,《元日祝福》是戴望舒诗歌创作的转折点。诗人把“生命”和“土地”联系在一起,从过去对“残损”的生命的怜悯、追怀转而对“焦裂”的土地的审视、哭诉,并把生命的命脉和土地的生存、民族的自由解放融为一体,从而超越了简单的对生命的叩问和对社会的抽象的抒情。“写这样的诗,对望舒来说,真是一个了不起的变化。我们在他的诗中发现了‘人民’、‘自由’、‘解放’等等的字眼了。”〔3〕(P3)“……诗人戴望舒同他的伤痕累累的祖国,同他的满目疮痍的民族,同他的饱经忧患的同胞一起,迎来了1939年的元旦。……我们的诗人从时代的良心出发,以更加阔大的胸怀向着广袤的祖国母土,向着广大的中华同胞,吟诵着出自肺腑的《元日祝福》。”〔4〕(P209)
当诗人身陷囹圄写下《狱中题壁》的时候,诗人已经完全超越了个人的苦难和不幸,做好了用“伤残”乃至牺牲迎接新生活的思想准备:“当你们回来,从泥土/掘起他伤损的肢体,/用你们胜利的欢呼/把他的灵魂高高扬起……”和《断指》相比,与人的生命牵连的神秘爱情以及由此带来的小小悲欢退隐了,诗人完全把生命交给了“泥土”和“山峰”,交给了现实的苦役和对未来所怀抱的“美梦”,生命的篇章由此得到了改写和升华。到著名诗篇《我用残损的手掌》,则完全主客融合,诗人把生命的残损、心灵的疼痛和祖国山河的破碎、民族的苦难紧紧联系在一起,完成了诗歌境界的拓展和飞升。因而这首诗被孙玉石称之为“抗战诗中不朽的名篇”。在诗人生命的最后岁月,他曾多次向听众朗诵这首诗作,足以见出这首诗歌在他整个诗歌作品中的地位。
由上面的分析可见,在戴望舒的数量不多的诗歌作品中,“残损”类意象不仅构成了一道特殊的审美景观,而且其自身也有一个内涵扩大和转换的过程。诗人从把苦闷寂寞的情绪投射到自然外物之上,赋予自然以“残损”之姿态和“忧郁”之情状,到凝望生命,进入到生命的残缺和疼痛,彰显生命的意蕴和方向,再到将生命的敏锐感受和社会现实的风云变换紧紧联系在一起,这一线索既表现了诗歌境界的丰富和拓展,更表现了诗人人格的锤炼和精神境界的提升。“残损”的酒杯,置于20世纪初期杯盘狼藉的桌面上,漫溢出来的是诗人寂寞、挣扎和奋进的心声,是生命由破碎臻于完整、由黯淡转入光辉的缕缕韵律,是生命个体逐渐融入社会和民族命运的倾诉和呐喊。
二
任何审美意象的反复呈现都是有因可寻的。戴望舒诗歌中大量“残损”类意象的出现并非诗人一时兴之所至,而是有着诗人自身生理、心理、情感以及社会和文学思潮等多种因素的影响,正是这些因素相互渗透从而内化为一种审美思维和艺术眼光,引导着诗人的意象选择和营构。
第一,在身体的病残面前,诗人借“残损”类意象惺惺相惜以释放内心的忧郁和痛苦。据有关资料记载,戴望舒童年时染上了天花,虽经细心关照和治疗,病愈后却在脸上留下了瘢痕,这给他的童年乃至一生都蒙上了阴影。“这场纯粹生理上的不幸,很快就在小伙伴们的嘲笑声中内化为心理上的创伤,诗人后来维持一生的忧郁的根源就在这里,即使是在成名以后,敏感而自卑的气质也无法改变。”〔5〕(P6)这里对“忧郁的根源”的分析不免有些绝对,但却从生理的角度指出了戴望舒忧郁气质形成的原因之一。另一个方面,戴望舒还患有哮喘症,并因此而过早地离开了人世:“同时他常年患着哮喘症,也就是他一生不幸的根源。”〔5〕(P8)虽然戴望舒有着魁梧的身材,潇洒的风度,有着一个抒情诗人的浪漫多情,有着美丽与忧郁的文字所成就的“雨巷诗人”的头衔和美誉,但身体的病残势必影响到他的心理和人格的形成,影响到他对自然和人生的态度。在诗歌《我的素描》中他这样表达:“我是寂寞的生物”,“我是青春和衰老的集合体,/我有健康的身体和病的心”。青春和衰老、温存和胆怯、谈笑和沉默、健康和病残纠结在一起,构成了一个自信而又自卑、奔放而又内敛的戴望舒。这种气质和心理性格的形成,不仅影响了他对诗歌意象的选择,更影响了他对生活的态度,包括他对爱情的态度。他那种极度渴望爱情而又不能、不敢表白的矛盾心理,给他带来了更甚于身体上的缺陷所带来的忧郁和痛苦。“真的,我是一个寂寞的夜行人,/而且又是一个可怜的单恋者。”(《单恋者》)一旦人的身体上的缺陷导致心理上的变异,必然生活就会被改写,包括他所从事的艺术。于是,因残生残,以残写残,就成为了戴望舒艺术构思和艺术表达中的一种自然而然的现象。
第二,在爱情和婚姻的残缺面前,诗人借“残损”类意象宣泄心底“沉哀”的感情。戴望舒短暂的一生写下了数量不多但美若珍珠的诗篇,他是快乐而幸福的;可是在爱情和婚姻的诗行中,他却步履艰难,甚至章法凌乱。列维·斯特劳斯说,两性关系是人类社会的深层语法。由于戴望舒个性中的弱点,导致他的家庭中的“语法”常常不顺,终而阻塞不通。从施绛年、穆丽娟到杨静,三位年轻漂亮的女性,围绕着他,给他带来了爱情的滋润和诗歌的灵感,但最终又都绝情地离开了他。正如他在《雨巷》中所写的:“在雨的哀曲里,/消了她的颜色,/散了她的芬芳,/消散了,甚至她的/太息般的眼光,/她丁香般的惆怅。”有学者指出,戴望舒在诗歌中四次使用“沉哀”一词,两次是施绛年给他的,两次是穆丽娟给他的。〔6〕(P164)这“沉哀”,应该说就是“残损”的琴弦所弹奏出来的伤痛之音。爱而不得的遗憾,得而复失的苦闷,失而再失的无奈,爱情和婚姻这个双面镜,一损又损,一破再破,在刺伤他多情而敏锐的心灵的同时,也无疑散落为他诗歌中无处不在的“残损”的艺术意象,散射着忧郁而寂寞的光。“而这里,鲜红并寂静得/与你的嘴唇一样的枫林间,/虽然残秋的风还未来到,/但我已经从你的缄默里,/觉出了它的寒冷。”(《款步二》)这首小诗,用“残”作结,从“残秋”而至“残心”——“寒冷”就是戴望舒爱情婚姻的琴弦上演奏出来的“沉哀”的音符。
第三,在山河破碎的社会现实面前,诗人借“残损”类意象表达对国家、民族命运的忧思。20世纪20年代末期到30年代初期,“从黑茫茫的雾,/到黑茫茫的雾”(《夜行者》),社会环境的窒息带给诗人戴望舒的是一种压抑、苦闷的思想情绪,诗人在相对封闭的个人生活的圈子里,更多地沉湎于爱情的悲欢和对人生前途的寂寞的守望中,于是见月月残,观花花谢,一双忧郁悲切的眼睛打量着世界的荒芜和内心的苍凉。待到1935年戴望舒从法国游学归来,及至目睹抗日的烽火,山河破碎、民族危亡的现实使诗人渐次从爱情“小曲”的“音的小灵魂”、“香的小灵魂”中走出来,把山河的破碎和自身的残损、祖国的伤痛和个人的命运联系在一起,有如深山涓涓溪流的爱情吟咏之作也逐渐被饱含民族忧患意识的血泪之声所替代,“残月的泪”、“残花的泪”被“残损的手掌”上的“血和泥”所置换。而在40年代初,流落到香港的戴望舒被关进日军的监狱,诗人更是以一种生命的切身感受从那“黑暗潮湿的土牢”领略了现实的残酷,继而在“梦”的世界里打开了通向“胜利”的窗子。吕进指出,戴望舒的诗集《灾难的岁月》的写作正是中国多灾多难的岁月,所以“其中的作品与以前的诗相比有更开阔的意识,对国家、民族命运的关注代替了对个人迷茫、失望情绪的表达”。〔7〕(P321)有人认为,30年代是戴望舒思想最为复杂的时期,他也一度摇摆于无产阶级革命和自由主义道路之间。直到外族入侵、民族危亡的惨痛时刻,他才感觉到这个“大政治”的意义,才起来作文化上的抗战,才向往解放区。“作为一个文化人,他不再把文学尤其是诗歌当作另外一种人生,而是使自己的诗歌汇入时代抗战的主旋律中”〔8〕(P129)。正是社会现实的巨变促使诗人把目光投向巨变的社会现实,克服内心里的“摇摆”,走出精神的“迷茫”,在家残国破的惨痛现实面前,举起自己“残损的手掌”,在“残损的手掌”里紧紧攥着祖国和人民的大哀大痛、大期待和大呼唤。也正是从这里,显示了一个文化人的胸襟、风骨和殷殷爱国之情。
第四,在20世纪初的诗歌“荒原”冲击波面前,诗人借“残损”类意象表达自己对人生、宇宙和社会的体味与感受。作为现代派诗人,显然戴望舒上承浪漫主义诗派和新月诗派的精神余绪,并带有象征派诗人李金发诗歌的某些艺术痕迹。而发生在中国20世纪初期的诗歌,处在一种开放的文学视野里,曾经广泛接受了世界文学潮流特别是西方现代主义诗歌的影响。20世纪初期即传入中国的T·S·艾略特及其诗歌代表作《荒原》,作为一种“冲击波”曾影响了那个时代的许多诗人。孙玉石在他的相关论述中列举了不少诗人的名字,如闻一多、徐志摩、孙大雨、卞之琳、何其芳等,并着重提到戴望舒,指出他的《深闭的园子》、《致萤火》等诗作,“是‘荒原’意识在中国诗人心头的回声,是经过艺术过滤之后的意象凝聚与创造”〔9〕(P219)。这是通过一些具体的诗歌作品或诗句来指认中国诗人所接受的西方现代诗潮的影响,特别是那种已经中国化了的“荒原”意识的影响。而当我们从诗歌意象入手,梳理出戴望舒诗歌中的“残损”类意象的时候,就会发现,戴望舒接受“荒原”意识的影响并非仅仅通过个别的字词或诗句表达出来,更是把“荒原”意识内化为一种审美思维方式和艺术表达方式。确切地说,戴望舒是将“荒原”意识转化为“残损”意识,通过“残损”类意象表达其对人生和社会的独特体味与感受。戴望舒对“荒原”意识的这种接受和转换是有其现实土壤和心理基础的。戴望舒和他同时代的诗人,他们生活的现实离“五四”时代那样理想的氛围愈来愈遥远了,“大革命失败后破败荒凉的中国社会现实裸露无遗地呈现于诗人面前。幻灭感和绝望感占据了许多青年的心。这种现实和心理激起的对于社会、人生与宇宙的思考,同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T·S·艾略特代表的现代主义诗潮中弥漫的虚无思想和绝望情绪有了相通之处”〔9〕(P216)。另一方面,如前所述,戴望舒自身的身体缺陷、婚恋阴影等所导致的自卑心理和忧郁气质也更契合“荒原”意识的精神内核。所以戴望舒接受“荒原”意识并在诗歌中用“残损”类意象来表达自己的感受和思考就是顺理成章的了。
三
“残损”类意象的大量运用,使戴望舒的诗歌呈现出一种更为丰富的艺术形态和更为坚实硬朗的质地,因而摈弃了早期诗歌单一的抒情风格和清浅的歌唱,开始走向诗艺的综合和内涵的丰盈。
“残损”类意象的大量引入,在对自然、社会现实的生命感受和象征表达中,超越了纯浪漫主义的抒情风格和纯象征诗派的玄奥与晦涩,使戴望舒的诗歌开始出现一种融写实、抒情和象征于一体的诗美景观。早期浪漫主义诗歌中的“天上的市街”、“夜晚的明月”以及种种风花雪月的缠绵的歌唱,在戴望舒的笔下,大都演变为“荒芜的园子”、“残月的泪”和风花雪月的哀婉的咏叹。“残损”类抒情意象的大量出现,犹如在昔日浪漫的抒情河流中抛下一块又一块破碎而尖锐的石头,固然也溅起美丽的浪花,但诗歌的指掌已触摸到坚实的泥土,在抒情河道的内部展开了一个更加真实、更加丰富和更加沉郁的诗性宇宙。即使是写爱情,戴望舒的抒情笔法也迥异于徐志摩的轻灵和烂漫,那沾着“油墨”的“断指”在诗人伤痛的追忆和祭奠中显示出生命的重量,完全没有了徐志摩“我轻轻地招一招手,不带走一片云彩”的那种人生的洒脱。尽管戴望舒很明显地受到徐志摩、闻一多等新月派诗人诗风的影响,但在对意象的选用方面,徐志摩主要选取的是“雪花”、“明月”一类轻盈明丽的意象,表达自己的梦和理想情怀,闻一多主要选取“死水”、“烂果”等意象抒发自己对现实的咒诅和愤激之情,而戴望舒则把自己对人生和现实的感怀和忧患更集中地通过“残损”类意象来表达,在“黑茫茫的雾”的世界里,一边抚摸着伤残和疼痛,一边渴望着介入现实、改变现实。
戴望舒笔下“残损”类意象也并非完全写实,并非完全是某种情绪的客观对应和投射,在有的时候已经虚拟化,成为某种象征的诗性表达。这一点在他40年代的诗作中体现得尤为明显。《狱中题壁》中的“掘起他伤损的肢体”一句,是为了表达诗人在残酷的现实处境中的宁死不屈和人格坚守。更不用说,在诗歌《我用残损的手掌》中,“残损的手掌”不能作具形的理解,而是战争背景下祖国山河的微型缩影和掌上地图,是民族伤痛和个人命运水乳交融的象征化表达。这是在写实的基础上的象征,不是那种飘渺虚幻不知所云的象征,因而我们能真切地把握其所蕴涵的意义。
戴望舒的诗歌综合了浪漫的抒情、现实的描写和象征的表达等多种艺术手段,这对新诗早期毫无节制的浪漫抒情风格和晦涩难懂的象征派诗风是一种矫正,从而使戴望舒成为30年代现代派诗人的领军人物。正如苏珊娜·贝尔纳所说:“对戴望舒这类诗人而言,诗歌首先是对客观世界的再创造,通过再创世界,给予读者以新的形象和感觉。正如法国诗人兰波一样:他既不认为做诗时要达到‘意识紊乱’的地步,而又要把幻想作为伴侣、轴心和依据。这种梦幻不断与现实交融,并超越甚至压倒了现实,诗歌创作就存在于这种辩证关系中。”〔10〕(P65)
戴望舒诗歌“残损”类意象的大量运用,使其所要表达的诗意既具有了生命的感觉,又被赋予了社会的内涵。“残损”是人的一种生命化的感觉,它来自于人对外界以及人对自身的敏锐的感应和感受;生命、自然、历史以及社会现实在这里被打通,并得以渗透和融合为一种生命的触须、生命的状态和生命的疼痛,因而自然、社会现实被赋予生命之情状,生命亦被赋予社会历史之内涵。在戴望舒的笔下,残花、残月、残阳,乃至于残破的山河、焦裂的土地,以及人生命方面的诸如断指、伤残的身体等等,都是诗人精心选用的审美意象,按照诗人内心的旨趣和指令一一呈现,传达出一种感时伤世的情怀,一种生命的大悲悯、大忧患与大疼痛。当诗人描写“残损”类客体意象时,将客观事物生命化、情态化,赋予物象一种生命的感觉和气息;而描写“残损”类主体意象时,将生命社会化、现实化,赋予生命一种深厚的意蕴。这可以戴望舒的经典之作《我用残损的手掌》为例来说明。“残损的手掌”是诗人个人的生命写照,也是广大受难同胞的生命写照;生命的“残损”来自祖国大地的“残损”:“这一角已变成灰烬,/那一角只是血和泥”,可见个人的生命和祖国的命运是二而一的存在,祖国存则个人存,祖国损则生命损。这是社会意识、民族意识的一种生命化表达、疼痛化表达,也是生命的一种最富有时代感和现实感的表达。比起那些直抒胸臆的“政治诗歌”、“抗战诗歌”更增添了生命的感性力量和艺术的感染力量,比起那些单纯轻灵的“生命歌唱”更增添了宽阔的视野和厚重的笔力。在这里,诗歌所传达的情绪既是内敛的,又是外溢的,既是个人的,又是普遍的,如T·S·艾略特所说的那样,诗人追求诗歌达到“把一个人的成分都溶混于非个人的和普遍之中”,且变得更丰富,更完全,因为“变得更不是自己就更成为自己”〔11〕
诗人藉“残损”类意象还表达了对理想世界的追求,对另一种生活的热切向往。诗人描写残破之景象和残损之生命,这并非其写作的目的,作为一个才情横溢富于想象的抒情诗人,他所要到达的决不是眼前之所见,残破之景象和残损之生命只是他漂流在抒情的海洋里顺手拣起的残楫断帆,他所要真正抵达的是一个更远的地方,是一个美的世界、爱的世界、梦的世界,是一个日月齐辉的光明世界。因此,拨开“残损”的花叶,拂去手掌上的“血和泥”,我们看到的是诗人所向往、所钟情的爱情的宇宙、生活的乐园、梦幻的世界和光明的胜境。在那里,有花繁叶满的“五月的园子”,有充满泥土芳香的“家乡的小园”,有沉浸在“而我是你,/因而我是我”的爱情甜蜜中所带来的生命的美妙、惬意和完整,有“自己成一个宇宙”而乐在其中的自由、快乐和烂漫,有作为爱的见证的闲花野草、流水白云,有纯朴如清泉、自然若垂柳的恋爱中的“村姑”……特别是戴望舒一再写到“梦”,这个“梦”就是超越了人生的局限和社会的束缚而到达的一种理想境界。《寻梦者》一诗虽然强调了过程的漫长和艰难,但诗人坚信“梦会开出花来的,/梦会开出娇妍的花来的”。当然,梦境是和残酷的现实相伴随的:“于是我的梦是静静地来了,/但却载着沉重的昔日”(《秋天的梦》);“采撷黑色大眼睛的凝视/去织最绮丽的梦网!/手指所触的地方:/火凝作冰焰,/花幻为枯枝”(《灯》)。这种矛盾和对抗,更衬托出了现实的沉重,也更显示出了梦境的珍贵。
在戴望舒的笔下,实际上存在两个世界:残损之世界与完美之世界。这两个世界或互渗互融,彼此衬托,或在一个世界的背后隐含着另外一个世界。因为“残损”,“完美”才显得弥足珍贵;因为“完美”,“残损”才必将为人所抛弃和远离。二者是辩证统一的。当然在戴望舒的诗歌创作中,对“完美”的表达有一个从朦胧、抽象到清晰、具体的演进过程。早期的诗歌,诗人在“残损”的背后所寻觅的主要是爱情的完美、个人生活的美满;随着社会生活的急遽变化,随着诗人个人宁静生活的被打破,诗人在“残损”的背后,把目光投向了灵魂得到升华的“山峰”和心灵得以安放的“远方”。与“残损”相伴随的“完美”,也随着“残损”类意象内涵的拓展而丰富着、提升着自身的含义。这一点在《狱中题壁》、特别是在《我用残损的手掌》中得到了极好的体现。“然后把他的白骨放在山峰,/曝着太阳,沐着飘风,/在那暗黑潮湿的土牢,/这曾是他惟一的梦。”(《狱中题壁》)在这里,“山峰”就是一种“完美”,就是诗人梦想的天堂和人生期望达到的高度,诗人表达了肉体残损乃至消亡之后的一种至上的追求,一种超越人生苦难和家国不幸的心灵梦想。在《我用残损的手掌》一诗中,当诗人用“残损的手掌”摸索“广大的土地”之后,在“手指沾了血和灰,手掌沾了阴暗”之后,突然急转直下,把手掌伸入那遥远而光明的一角:“只有那辽远的一角依然完整,/温暖,明朗,坚固而蓬勃生春。/……因为只有那里是太阳,是春,/将驱逐阴暗,带来苏生,/因为只有那里我们不像牲口一样活,/蝼蚁一样死……那里,永恒的中国!”至此,戴望舒的诗歌在含着血泪的歌唱中,进入了一个最高音,进入了一个把个人命运粘附在祖国命运之中的阔大的境界和完美的梦境,在“残损”的背后,开掘出了一份具有社会意义的“完美”,一份永恒的“情结”。
〔1〕龙泉明.中国新诗流变论〔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
〔2〕卡·古·荣格.陈焘宇,译.心理学和文学〔M〕//戴维·洛奇编.二十世纪文学评论(上册).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
〔3〕艾青.戴望舒诗集·序〔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
〔4〕孙玉石,主编.戴望舒名作欣赏〔M〕.北京:中国和平出版社,1993.
〔5〕刘保昌.戴望舒传〔M〕.武汉:崇文书局,2007.
〔6〕王文彬.中西诗学交汇中的戴望舒〔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
〔7〕吕进,主编.文化转型与中国新诗〔M〕重庆:重庆出版社,2000.
〔8〕杨四平.20世纪中国新诗主流〔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4.
〔9〕孙玉石.中国现代诗歌艺术〔M〕.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7.
〔10〕转引自江弱水.中西同步与位移——现代诗人论丛〔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
〔11〕T·S·艾略特.诗与宣传〔J〕.周煦良,译.新诗,193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