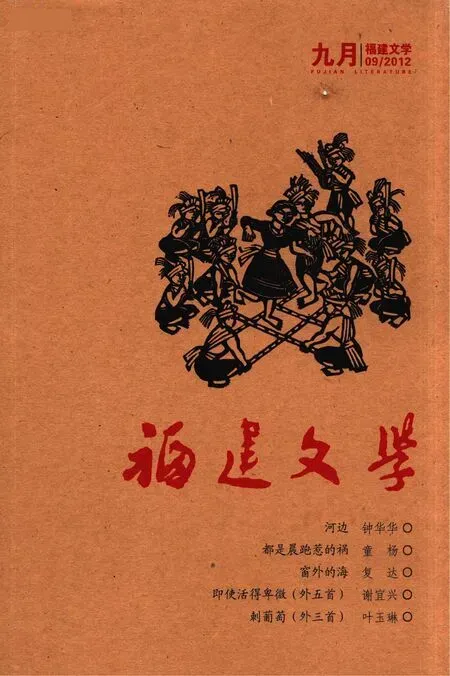在革命繁星中灼灼其华——汤银钗纪事
钟兆云
在革命繁星中灼灼其华
——汤银钗纪事
钟兆云
“纪念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70周年”征文
引 子
相传,天与地脱离混沌之时,人与星便有了遥远的关联,一颗星即为一个人。是故民谚云:“天上一颗星,地上一个丁。”
远远地观望,它们的力量是如此微弱:有时,弥漫天际的星辰齐齐向地面投射的是渺不足道的微光;有时,万丈光辉下,生为万物之灵长的人界却笼罩在黑暗之中。令人欣慰的是,光明终究要穿越并撕裂阴霾,耀眼人寰。
乾坤含疮痍,忧虞何时毕?二十世纪初百孔千疮的古老中华,满地斗争接连不断,在理想与血腥中竖起了闪着金光的铁锤和镰刀,仿佛是附在旗帜上的最亮星辰;旗下集结着被称作共产党的人,一个丁一个丁地汇成群,死者无悔,化为天上星,生者后继,不遗余力地发出革命和真理之光,连着天上星,坚信能点亮光明。
汤银钗便是有这么个信仰的人。自古揭竿革命、铁血报国者,多须眉和“白衣冠冕”,而目不识丁的“红装翠袖”竟也心怀主义,且百折不回,满门忠烈,堪称天地绝响。
初遇星火
二十世纪初的宁德虎贝乡中洋里村,黎庶饔飧不继,艰辛备尝。一天清晨,阳光还在云中打滚,几声犬吠隆隆升起,断断续续地,争先恐后地,像极了一场沸腾的唠嗑。汤银钗和丈夫叶世妥携孩子们穿梭于吠声中,踏上了通往霍童的弯曲山路。这一年,白色恐怖正黑压压地笼罩着闽东。
在盘旋的路上,远远就可见着霍童。从地形上来讲,它象一块眉黛敛秋波般的小盆地,水流直通沿海商埠,山路依稀可通。便利的交通让这巴“大掌”一揽,成了周宁、屏南、宁德三县的物资集散地和转运站,人来人往,熙熙攘攘。
霍童于汤银钗,是亲切而温暖的地方。自1888年出生于此,她在这度过了十五个春秋,直至嫁到相隔不远的中洋里。婚后,夫妻恩爱有加,相继哺育了五个儿子。如今,汤银钗带着一家老小来把娘家还,一来可摆脱中洋里村漫长的农闲来霍童打打短工,二来也可锻炼尚在成长的孩子们。一家人的生活算是暂时有了安定。
可时局却不安定,国民党掀起“清党”的血雨腥风,拍倒了一大批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听闻这些穿透青砖黑瓦的消息时,汤银钗——不明局势的农家女还是云里雾里,让她茅塞顿开的是四弟汤昌满。
1932年,随着以抗租、抗债、抗捐、抗税、抗粮为内容的“五抗”斗争席卷闽东大地,四弟与二哥、三哥的行踪变得高深莫测起来,汤银钗决计伺机行动探个究竟。这一探,就从四弟身上探出了把驳壳枪。原来,汤昌满早就加入了共产党,二哥、三哥也都是共产党员,他们立志要和他们的同志推翻反动黑暗统治,建立没有剥削的社会。
这些动人心扉的话触动了汤银钗最柔软的心底,她霍然流露出兴奋而庄重的神情,出头之日终有盼了!她睁大双眼,紧紧握住四弟的手:“我要加入你们革命,跟共产党走!”
“其实,组织上已把你当作自己人了,这些天让你看门、望风,就是对你的信任啊!”汤昌满反握着姐姐的手,热情洋溢地说。
人生就像天气,变幻莫测得很。上一秒还是局外人,下一秒已成局内人,初任地下交通员的汤银钗忙着执行任务。周而复始中,她很快就体验到了从未有过的神圣的使命感,且又迎来了一项任务,无从想到的是这竟然编织了一段“母子”传奇。
1932年10月,窗外,水银色的月光倾洒着院落。四弟领来了一位清秀腼腆的小伙子,叫“小叶”,要暂寄姐姐家,千叮万嘱要照顾好。汤银钗瞧了一眼,看他与自家的娃年龄相仿,还是个孩子,就毫不犹豫地应承下来。
这“小叶”不简单,他就是日后大名鼎鼎的开国上将、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叶飞。时年18的他虽然青涩,却是中共福州中心市委特派员,一个有勇有谋、满心要创建新社会的革命者。他白天在革命中颠簸,晚上与汤家的娃们同吃同睡,像极了亲兄弟。身边的天伦之乐,也使汤银钗的心填满了欣慰。
只是没多久,“小叶”就负伤了,伤的是关键的脚部,连骨头都裸露出来了。如何让他尽快恢复?汤银钗不停思索着这个问题,为此还打听到一个偏方,赶紧和老伴上山采来草药,她还拿了量米的竹筒向村里村外尚在哺乳的妇女讨奶水,调和中草药细心地给他敷上。“小叶”这才有了好转,重回组织为革命播火。
汤银钗与“小叶”的母子情缘似乎难斩。一段时间后,再次受伤的“小叶”又被抬进了汤家。所不同的是,这时的“小叶”已与颜阿兰组织发动了霍童暴动,创建了闽东工农游击武装。伤口就是敌人“围剿”时所创,特别严重,需要调养好些时日。汤银钗看着“小叶”受此大难,有些激动更有些心疼,这孩子为了革命,真是连小命都不想要了!
天气渐冷,多了些哆嗦,寒风四起,躺在床上的“小叶”直打冷战。汤银钗二话不说,把家中仅有的一条旧棉被盖到他身上:“好好养伤,别着凉了。”
“我不能要,这可是仅有的一床被子啊。”“小叶”努力起身,眼中闪着坚毅的光芒。
“你是革命的希望,不能因此而倒下,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汤银钗一把按下“小叶”的肩膀,把棉被严严实实地给他捂上。
那个冬天,汤家几口人仅用破棕衣和稻草覆着身体过夜。那个冬天,汤银钗几乎目不交睫,坚持上山采集中草药,为“小叶”敷药;坚持亲自下锅,为“小叶”端茶喂饭;时时还得望风,在风吹草动中辨别敌情。经过汤银钗两个来月亲如生母般的细心照料,“小叶”的腿部伤口逐渐愈合了,又生龙活虎起来。
患难见真情,如此情真意切的积蓄,汤银钗与叶飞的人生彼此都享用不完了。时隔多年,身居高位的叶飞还是亲切地称汤银钗为“妈妈”,彼此间交往密切,其乐融融。
赴汤蹈火
1934年2月,崭新的闽东苏维埃政府成立了,中洋里地下党支部也正式成立,还兼带着数支游击队。鉴于此,需要一名可靠的交通员,传递情报,沟通联络,工作极重要,风险性极高。汤银钗不假思索地接受了重任,还把自家的破屋摇变为秘密联络站。
地下交通奔波劳累,对汤银钗这样的小脚女人而言,绝非易事,但她咬牙坚持着。即使遇上豺狼嗥叫,或老蛇挡道,也不退缩。地下交通险象环生,得有些小聪明、“小把戏”才行,或用米汤密写情报,或用石子绑住信件遇险可丢,实在不行,干脆把重要信件塞在月经带里。有几回,汤银钗照常躲过了劫难,却被自身落下的病给打倒了。
那是1936年七月的一天,天气燥热,眼瞅着就要下一场大雨。距中洋里村五里路的莲花心,是游击队活动的据点,正处于被敌人“围剿”的喘息期。时间刻不容缓,身为交通员,年近五旬的汤银钗受命马上把情报送达。
五里山路!倾盆大雨!漆黑一片!那晚的雨水与敌人一样不怀好意,把汤银钗的高烧因子给诱发了出来。但她不顾难受直奔据点,看到带病站岗的儿子叶伯安,口中直蹦一句话:“赶快转移,敌人明天就要进攻过来了!”
说这话时,汤银钗已然快撑不住了。正当大伙手忙脚乱地打包物品时,她终于烫得昏厥倒地。
“不能丢下汤妈妈,再苦再累也要抬着随队转移!”队员们轮流背着她,深一脚浅一脚地安全转移到山深林密、地势险要的梅坑山。
转移告捷,高烧却一直狂噬着汤银钗……几个日夜下来,汤银钗的病终见起色。闲不住的她,又为大伙儿缝缝补补、挖野菜、烧水做饭,照顾伤员,唱山歌为大家解闷、鼓劲。大家的心里都是暖洋洋的。在大山深处,充盈血丝的一双双眼球凝聚起来更像是一轮朝阳,点亮了冉冉升起的希望。
地火日夜运行,革命顽强进行。血染的红花从天降:二哥汤昌坂为革命牺牲;四弟汤昌满跟着叶飞北上抗日,在著名的繁昌保卫战中壮烈捐躯;闽东游击队数十人被国民党一○七师在霍童诱杀,被剖腹掏心,割首示众……当然,雨后春笋般的好消息更是鼓舞人心:汤银钗的三儿子叶伯安当上了游击队负责人,最小的儿子叶隆双当上了地下党支部宣传委员,并担任贫农团副团长;时任华东野战军一纵一师政委的阮英平,受派回了福建担任中共闽浙赣省委常委、军事部长和闽东地委书记,闽东的革命又涨潮了。
敌人沉不住气了,全力搜寻“围剿”游击队。1948年早春二月的一天,荷枪实弹的国民党保安五团踏着凌乱的脚步将中洋里村重重包围起来。此时的汤家只剩下卧床不起的叶世妥,被连拖带拽到了村口,因为坚守妻儿的隐藏地,在敌人歇斯底里的咆哮声中被推入坑中活埋。没拿住汤银钗和游击队,敌人就烧毁了她和几位革命群众的房子,还把中洋里男女老少七八十号人押到乡公所,并枪杀一人,威逼利诱,要他们交出汤银钗。
已安全转移的汤银钗获悉情况,义愤填膺,既然已经搭上了老伴,为何还要滥杀无辜的百姓?绝不能因我个人再赔上村民的性命!花甲之年的小脚女人义无反顾地踏上了“飞蛾扑火”之路。
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这就是汤银钗给革命交出的答卷。当她一脸汗水出现在乡公所时,中洋里众乡亲一阵哗动,敌人也是一阵哗动:这个送上门找死的女共匪,原来不过是个老太婆!
敌营长像卸下重担似地大呼一口气:“来啊,把她给我绑起来!”
面对着黑洞洞的枪口,汤银钗并不挣扎,昂首挺胸地被敌人反绑着押走。
她在中洋里留下了一个巾帼豪情的女杰背影,在浓重的夜幕里熠熠生辉。
浴火重生
到了“虎山”后,汤银钗被折磨得遍体鳞伤,鲜血淋漓,死去活来。敌人把她倒吊在屋梁上,硬生生地吊断了她的两根手指。她咬紧牙关,任由敌人打得皮开肉绽,依然是只字不吐。
墙上、地上、身上,全是新鲜的和凝固的血迹。暗室中袅袅升起鲜血的腥味,沉重得让人透不过气来。让敌人傻眼的是,这些沉重丝毫动摇不了她的意志。
动摇的只是敌人的耐性,他们终于沉不住气了,敌营长亲自出马,想用软办法骗取口供:“你这几天受苦,我很同情你,只要说出你儿子带的游击队在哪里,保证放你回家,再送你三十担稻谷。你儿子那,我会派人和他联系,跟我们合作,不仅能保证他的人身安全,还可保证他升官发财。”
她斩钉截铁地回答:“不知道!”
敌营长黔驴技穷,上前揪住她的衣襟吼叫:“你的儿子和游击队究竟在哪里?”
汤银钗坚定地说:“凡是人眼看得到的地方,都有红军游击队!”
敌营长的眼神刹时凝结了一团肃杀之气,丧心病狂的他,从旁操起一把寒光闪闪的刺刀向汤银钗乱舞。汤银钗像一尊淡定的女神,眼眨也不眨。
“嚓”的一声,刺刀从她的头上落下。她本能地一偏头,刀锋削在左嘴角,再斜划到左胸前,乳房被剜去半片,还连着皮,欲掉未掉,而锋利的刺刀还在屠夫的狂叫声中、亮闪的光中挥舞,肆虐着柔弱的肉体。
钻心的疼痛,鲜血像喷泉般倾泻,那殷红的液体被簇拥成一条弯曲的红河,侵蚀着阴森的暗室。那是怎样一个震撼心扉的画面!
敌营长冷眼漠视,心生毒计,挥手让人把她抬进乡公所对面的牛栏。他要看看她的儿子和游击队会不会前来解救。他设下埋伏,伺机来个瓮中捉鳖。
消息传到山上,游击队员们个个摩拳擦掌,争着要下山解救英勇的汤妈妈,但被叶伯安拦下了。知母莫若子,他提醒大家这是敌人设下的圈套。
两天两夜过去了,敌人见歹计未成,又见她几无声息,失望之余,就地扔弃,任其自生自灭。
敌兵撤走了。
第三天下午,对面乡公所保长的小老婆起床梳头时,看到牛栏里有人在动,还有一个微弱的声音游丝般传来:“妹子,你借我一把剪刀来。”原来是“女共匪”复活了,一身血迹爬了起来。
保长小老婆明白了,拿了把做鞋底的剪刀和两个包子,看看四周无人,便大胆走过去。汤银钗和着嘴唇上的血咽下两个包子后,有了点力气,接过剪刀,一咬牙,“咔嚓”一声就把胸口那块血淋淋连着大半片乳房的皮肉给剪断了。鲜血跟着撕心裂肺的疼痛一起涌来,她咬紧牙根,尽量不哼一声。
夜幕来临,汤银钗连走带爬,拖着沉重的身子,向中洋里挪动。一步,一步,每挪动一步,就要流一滴血。群众发现了,游击队发现了,连忙合力抬着她上了山。
多么坚强的革命妈妈,多么顽强的生命力啊!看到她体无完肤,联想到她遭的罪,再硬的汉子也忍不住哭了。
汤银钗苏醒时,已是几天后的事了,她听到了一个个兴奋而关切的声音:“娘啊,你终于睁开眼了!”“汤妈妈,你真是革命的好妈妈!”
她环顾四周,积攒着力气,说出的第一句话竟是:“中洋里的乡亲们没事吧?”
时光不紧不慢地流着,汤银钗在精心照料下渐渐脱离了危险。但还没等伤口痊愈,她又舍身忘我地奔忙在革命的战线上,上山送信,下山筹粮。对丹心赤忱的她来说,当好一名交通员,为革命多做事,最大限度地贡献自己的力量,才是最重要的。
“敌人虽然摧残了我的躯体,但我的信念和革命意志,是任何人也摧毁不了的!”她常常豪迈地说。
凤凰在战火洗礼中重生,羽翼更是俊秀美丽,神采夺目!
薪尽火传
汤银钗是合格的“革命妈妈”。
五星红旗在天安门上空高高飘扬时,汤银钗已是六十开外的人了,但革命毅力依然不减当年。她总认为自己只是沧海中的一粟,所做的贡献实在是太小太小,希望能在有生之年多为革命发一份光和热。她热情又周到地接待一批又一批进村工作的干部;她奔走呼号,带领乡亲们完成国家的各项任务,宁德县(现蕉城区)第一个互助组就在中洋里。在福建省第一届英模代表会上,叶飞亲自把闪闪勋章挂在了她被敌人剜去了半个乳房、伤痕累累的胸前,动情地称她为“革命妈妈”。尔后,汤银钗上北京,见到了日思夜想的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
胜利来之不易,重在教育后人!汤银钗常用“发扬革命传统,争取更大光荣”,来勉励村里的老少妇孺努力发展生产,建设好新家园;以翻身不能忘本、永葆革命青春,来教育自己的子女和周边乡亲。
到省城开会时,她经常与当年的“小叶”、已是省委书记和省长的叶飞唠唠家常,连自个的七十寿诞都在叶飞家温馨度过;看到自家的娃因为革命而耽搁婚事,她积极奔走为儿做红娘,以使“革命自有后来人”;“文革”狂飙起,继叶飞之后,担任副县长的儿子叶伯安等坚定的革命者转眼都成了“反革命”,她却始终相信他们,坚信乌云遮不住太阳。爱唱革命歌曲的她,临终前仍轻哼着那首“打破旧世界,建立苏维埃,朱毛啊领导无产者……”她还把自己的勋章用红布包了一层又一层,放在儿子、媳妇手心,叮嘱他们要跟党走,要为百姓做事,薪尽火传。
春回大地后,叶飞曾不止一次地回忆闽东的峥嵘岁月,深情叙说汤银钗一家为革命所做的奉献。得知汤银钗的孙女已是大学领导,叶飞欣慰地称之为“红色第三代”。
青山依旧在,红旗永不落。汤银钗这个平凡的名字,已成革命繁星中的一颗,在灿烂的天空闪烁,照耀着地上的一个丁又一个丁。新的世纪,她的精神依旧在人间流传,在她的红色后代的血液中流淌。
责任编辑 林 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