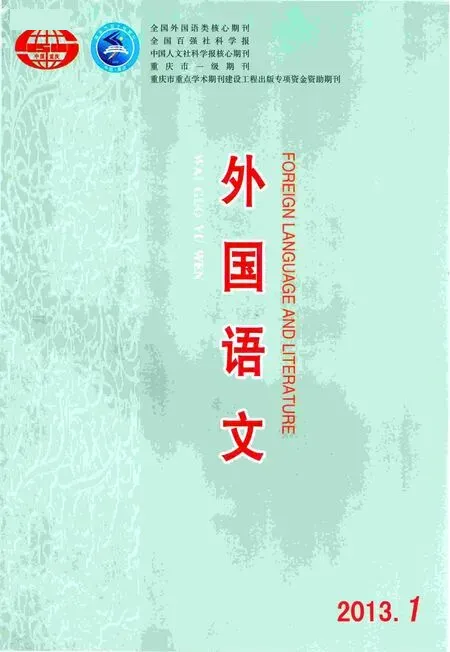多元系统理论视角下的中国文学“走出去”模式
罗清月
(四川外国语大学 翻译学院,重庆 400031)
1.引言
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中国文化与世界交流的迫切性不言而喻,中国文学“走出去”的文化策略应运而生,并不断得到关注和呼吁,中国在这一时期对外翻译工作,其规模是任何时代都无法达到的,比如启动了“中国当代文学百部精品译介工程”、“中国文学海外传播工程”等中国文学“走出去”的项目。但与此同时却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作家刘震云认为:“中国文学还没有走向世界,但是世界文学却已经走向中国了”,无疑展露出中国当前文学译入与译出巨大差距的担忧。因为“与中国对外贸易‘出超’相比,中国的对外文化交流和传播则是严重‘入超’,两者之间存在着巨大的文化赤字”。从多元系统的角度来看,相对于强势的西方文化,在世界大多元系统中,中国文化多元系统在其中处于边缘位置(张南峰,2004:56)。弱势文化译入强势文化必然面对巨大的阻力,因为文化交流具有自身的规律与趋势:“交流总的趋势通常是高势能向低势能辐射,从‘强势’文化向‘弱势’文化流动”(廖七一,2012:5),而由中国学者策动的中国文学“走出去”带有明显的“逆向交流”的性质。元代著名杂剧《赵氏孤儿》在法国的经典化过程,寒山诗在美国掀起的热潮无疑是第三世界文学涌入主流文学领域的成功典范,根据多元系统理论对其进行分析,探索并发现现象背后的原因和规律,可为中国文学“走出去”的模式提供启示。
2.多元系统理论概述
20世纪70年代,以色列学者伊塔马·埃文-佐哈尔(Itama Even-Zohar)提出了多元系统理论(Polysystem Theory),并在1978出版的《历史讲学论文集》(Papers in Historical Poetics)中得到体现。佐哈尔从俄国形式主义、结构主义、一般系统理论与文化符号学等中汲取了积极因素,该理论核心内容就是把“各种社会符号现象,具体地说是各种由符号支配的人类交际形式,如语言、文学、经济、政治、意识形态等,视为系统而非由各不相干的元素组成的混合体。这些系统并非单一的系统,而是由若干个不同的系统组成的系统;这些系统各有不同的行为,却又互相依存,并作为一个有组织的整体而运作”(佐哈尔,2002:19)。文学本身即为一个多元系统,有“经典的”、“非经典的”、“中央的”与“边缘的”、“一级活动”与“二级活动”等之分。其中,翻译文学被视为文学多元系统中的子系统,它在文学的多元系统中的地位并非一成不变,通过无休止的斗争,“整体内的各个系统会不断地发生变化:处于中心的系统可能被驱逐到边缘,而处于边缘的系统可能攻占中心位置”(谢天振,2003:60)。佐哈尔认为,在以下三种情形下,翻译作品可以起到革新的作用(属于一级模式),促进新的形式库的建立。而所谓形式库,意谓支配文本制作的一切规律和元素(可能是单个的元素或者整体的模式)的集成体。这三种情形是:(a)当文学依然“幼嫩”尚未定形时;(b)文学在更大的文学系统中处于边缘或“弱势”地位时;(c)文学系统出现真空、危机或者转折点时。(1978:24-25;1990:47)实际上,一个系统的行为模式,有时与它在多元系统中的位置有关。例如翻译文学,翻译策略的选择是由它在文学多元系统中的地位决定的。它处于中心时,往往参与创造一级模式,不惜打破本国的传统规范;处于边缘时,则常常套用本国文学中现成的二级模式。前者的翻译策略着重译文的“充分性”,后者则着重“可接受性”(张南峰,2002:19)。
3.《赵氏孤儿》与“寒山诗”对外译介经典化过程的多元系统视角分析
3.1 《赵氏孤儿》在法国的译介与传播
18世纪起中国戏剧开始传播到欧洲,而当中传播最广、影响最深的首推元代剧作家纪群祥的《赵氏孤儿》,并构成了18世纪欧洲“中国热”的文化景观。这部元杂剧在国外的经典化过程,无疑是边缘文学步入主流文学领域的一个成功案例。
最早翻译《赵氏孤儿》的是法国耶稣会传教士马若瑟(Joseph Maria de Premare),但马若瑟将其翻译成法语时进行了节译,作为主动译入的译者,他首要考虑必然是译入语文化的“可接受性”,他对节译的解释无疑表露了这样的考虑:
中国人完全不像我们那样在喜剧和悲剧之间做出明确区别……中国人的悲剧和喜剧中都掺和一些唱词。……有些戏剧中的唱词很难听懂,尤其是对欧洲人来说更为困难。因为其中充斥着我们根本不习惯的隐喻和矫揉造作的内容。
(转引自吕世生,2012:66)
实际上,在译入之初,《赵氏孤儿》位处边缘,马若瑟的节译和删减可被视为对本国文学中现成的二级模式的套用,也可以说“充分性”通常出现在从强势文学系统向弱势文学系统传播的翻译过程中,这是多元系统相互间活动的规律。
其实,译文还是将原剧的故事框架和基本面貌保留了下来。此后,该译文相继被巴黎的《法国西时报》(Mercure de France)、《水星杂志》选载。不久后,《中华帝国志》(也译成《中国通志》)的编辑也在发表这篇剧本时介绍这部中国戏剧,并盛赞该剧的道德及寓教于乐的审美价值。经欧洲颇具影响力的该杂志刊载后,《赵氏孤儿》由此开始在欧洲各国传播开来。若文本翻译还只是激发了西方文化对该剧的兴趣,马若瑟的删节“属于文本形态的调适,其意义仅限于满足18世纪西方对中国文化的猎奇心理”(吕世生,2012:66),然而要得到西方文化认同,顺利迈进西方文学的中心领域并完全融入西方文化,该剧经历的第二阶级“文本改写”才真正地推动了《赵氏孤儿》与目的文化的融合。最为影响深远的是法国思想家、文学家伏尔泰(Voltaire)以该剧为基础所改编的全新剧本《中国孤儿》(L’Orphelin de la Chine),并把“文本的立意由家族之争上升为文明与野蛮之争”,“源语文本意在‘善恶有报’,改写本意在‘扬善融恶’,突出仁爱,强调和解”(同上)。显然,改编本的文本立意得以深化,其道德力量得到了增强。伏尔泰改变源文本立意的改写,着眼于目的语的文本接受,实现了源文本与目的语文化的融汇升华,因为“18世纪的法国,启蒙主义大行其道,作为引领启蒙主义运动的思想家伏尔泰极力高扬理性大旗,回归理性成为他的终极思想诉求……因此,《赵氏孤儿》原文本中‘扬善惩恶’的文本立意上升为其《中国孤儿》中的‘扬善融恶’则是其理性主义思想的自然流露”(同上)。由此,伏尔泰改编后的《中国孤儿》获得了目的语受众的积极反响。
事实上,伏尔泰的改写中产生了其立意冲突的情节——成吉思汗与爱达米的爱情。“但这种调适非但没有影响文本的广泛接受,或许还是引发观众兴趣的重要情节。其原因在于这种爱情叙事是西方英雄剧的惯常模式,满足了西方文本受众的美学期待。”(同上:67)
因此对于《赵氏孤儿》的翻译与改写创造的译介成功,有学者总结到,“《赵氏孤儿》的异国情调满足了其时西方社会萌动勃发的对中国文化的好奇心”(钱林森,1998:118),这可谓体现了时机性,并且“其中的中国传统道德蕴含了西方社会向往的政治理想及道德规范”(沙日娜,2011:113;Williams,2000:221),这一点是意识形态的契合。总之,中国文学“走进”西方语境,以目的语规范进行调适是获得接受的重要条件。
3.2 “寒山诗”在美国的经典化过程
在中国唐代诗歌中名不见经传的诗僧寒山,却演绎了中国文学的“边缘文本”、“边缘诗人”步入西方文学“中心”与“经典”殿堂、经典建构的传奇。美国翻译家赤松 (Red Pine)颇有感触地说到:“如果中国的文学评论家要为自己国家过去的最伟大诗人举行一次茶会的话,寒山可能不会在众多被邀请之列。然而受邀的那些诗人却与中国的庙宇和祭坛无缘,但寒山的画像却能被供奉于众多神仙与菩萨当中。在韩国和日本,寒山也受到了相同的礼遇。当杰克·凯鲁亚克(Jack Kerouac)1958年将《法丐》(The Dharma Bums)题献给寒山时,寒山还成了西方那一代人的护佑天使”(Pine,2000:3)。在中国文学对外译介的历史上,在故国文学中“被边缘化”,而在美国翻译文学中被“经典化”,“寒山诗”的经典建构过程拥有深入探讨的价值。
首先将寒山诗译入英语世界的是阿瑟·韦利(Arthur Waley),其27首译诗发表在《相遇》(Encounter)第3卷第3期。继此之后,美国垮掉派诗人加里·斯奈德(Gary Snyder)开启了寒山诗在美国的传播。首先,斯奈德在六画廊(Six Gallery)诗歌朗诵会上朗诵了自己英译的寒山诗,作为旧金山文艺复兴运动序幕的此次朗诵会,为寒山诗迈步经典的殿堂奠定了基础。他的24首寒山译诗首先刊载在垮掉派作家的宣传阵地《常春藤评论》(Evergreen Review)上,继而在1961年,斯奈德译诗由于被美国学者托马斯·帕金森(Thomas Parkinson)编辑的《“垮掉一代”论集》(A Casebook on the Beat)收录,并由纽约的托马斯·克罗维尔出版公司(Thomas Y.Crowell Company)出版,因为“这部论集是较早真实反映‘垮掉一代’生活与创作的资料来源,所以在学术界有较好的口碑,其卓越的史料价值也深得学术界的认可。因此,在研究‘垮掉一代’和五六十年代的美国社会文化方面,它一直是很核心的研究材料”(周晓琳、胡安江,2008:127),因而斯奈德的译诗也就得到了更大范围的传播和接受。1965年,他的译诗又被选入“美国著名比较文学教授白芝(Cyril Birch)编辑的《中国文学选集》(Anthology of Chinese Literature:from Early Times to the Fourteenth Century),标志着寒山诗经典化在文学史意义上的正式确定”(区鉷、胡安江,2008:20)。随后,寒山诗全译本的出现,并全面进入美国各大文学选集和东亚文学的大学课堂,被编入教材,华生(Burton Watson)、赤松等学者的相继翻译,以寒山为题的博士论文的出现,至此,寒山诗已从故国的“边缘化”到译入国的“经典化”完成了一个华丽的转变。
从多元系统理论视角看来,寒山诗的成功“经典化”在于把握住了一个良好的时机。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美国暴露出了各种尖锐的问题,“垮掉派”的一代寻求着反传统、反主流的方式进行抵抗。在轰轰烈烈的“垮掉运动”的背景下,“在当时的语境下,斯奈德笔下的寒山——这位唐代诗人、疯癫的山之隐者——变成了一位‘垮掉’英雄(a beat hero)和反文化的先锋”(Kern,1996:237)。同时由于当时的美国社会历经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本土的文学多元系统正处于一个相对‘边缘’与‘弱势’的状态。因此,翻译文学的中心地位得以凸显,许多一流的诗人、作家与学者都纷纷投身翻译事业,积极参与构建新的文学规范”(胡安江,2011:198)。寒山诗正是迎合了目标语文化语境中主流意识形态的变迁,把握住了美国文学多元系统中的一次“边缘期”,并且寒山诗的“情调和60年代‘垮掉的一代’的心态及至整个现代西方文学的追求有某种投契之除”(黄鸣奋,1997:158),符合当时译入语文化背景下的读者心理和期待,成功地从“边缘系统”攻占到“中心位置”,在美国文学多元系统中起到了革新的作用,挺进“经典”行列。
4.多元系统理论下中国文学“走出去”的启示
从《赵氏孤儿》到“寒山诗”在对外译介的成功经典化,无疑两者都体现了一些共同点:翻译时机的把握,并且两者均为国外译者的主动译入,对译入语文化的意识形态、读者的接受效果有更切身的体察。因而,由我国主动发起并进行的中国文学“走出去”,更应敏锐地观察译入语文学多元系统,洞悉其系统内部的变化与发展,把握译入时机,了解读者的期待与诉求,顺应多元系统活动的归律,发挥译入语译者的作用,寻求中西合作的方式,以达到最大的译入效果,为“边缘文学”系统迈向中心系统打通渠道。
而近年来,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对外译介也出现了一大突破,即英国的中国文学学者和翻译家蓝诗玲(Julia Lovell)成功地将鲁迅、张爱玲等作家引入了西方文艺界影响最大的“企鹅经典”(Penguin Classics)。其中蓝诗玲对翻译的内外部环境的认识,对文本的选择,对策略的选取是其译作成功译介的条件。谈到对鲁迅作品的翻译,蓝诗玲认为“鲁迅代表了一个‘愤怒、灼热的中国形象’,任何一个想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人都无法跳过鲁迅。他像英国大文豪狄更斯一样,备受尊崇却在今天有点受到冷落”①http://cnmedia.org/?p=300,此后她还在《卫报》发文指出“如果想了解中国人的这种绝望情绪,就应该去读鲁迅的小说……20世纪中国文学的世界性并不输给英国或美国文学”②http://www.guardian.co.uk/books/2010/jun/12/rereading-julia-lovell-lu-xun。这些言论无疑会改善译入语读者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理解。再谈翻译策略,佐哈尔认为一个系统的行为模式,有时与它在多元系统中的位置有关,即翻译策略的选择要以文学在多元系统中的地位为考量。而认识到翻译文学在英语文学多元系统中位处边缘,蓝诗玲的翻译策略突出“可接受性”,“寻求英美文学经典形式库中现成的表达法,将原作引向读者,便于读者理解和接受”(覃江华,2010:118)。随着这些译作刊行于“企鹅经典”,标志着中国现当代文学在所处的世界文学多元系统中,开始从边缘往中心迈步了。
5.结语
通过运用多元系统理论对翻译文学在译入语文化中的成功接受案例进行的客观描述,带给我们多重思考。透过多元系统理论,文学的成功译介远非只是原文与译文间的等值问题,而在上述的情况下更是远非如此,翻译研究走上了文化研究的道路,背后的诸多文化因素开始得到揭示。“中心”与“边缘”的位置进行着永无休止的更替,中国文学“走出去”要顺应多元系统活动归律,探求译入语多元系统中的变化与发展,寻求译介契机,拓展译者模式,深刻认识翻译的对内对外环境,顺应语言转换在多元系统中的规律,寻找中国文学“走出去”的最理想可行的模式。
[1]Even-Zohar,Itamar.Papers in Historical Papers[C].Tel Aviv:Porter Institute for Poetics and Semiotics,1978.
[2]Even-Zohar,Itamar.The Position of Translated Literature within the Literary Polysystem[J].Poetics Today,199(1):45-51.
[3]Kern,Robert.Seeing the World Without Language,Orientalism,Modernism and the American Poem[M].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6.
[4]Lovell,Julia.China’s Conscience[EB/OL].[2012 - 12- 20].http://www.guardian.co.uk/books/2010/jun/12/rereading-julia-lovell-lu-xun.
[5]Pine,Red.The Collected Songs of Cold Mountain[M].Port Townsend:Copper Canyon Press,2000.
[6]Williams,Dave.Misreading Chinese Character:Image of the Chinese in Euro America Drama to 1925[C]//Asia Thought and Cultures.New York:Peter Lang,2000.
[7]埃文-佐哈尔.多元系统论[J].张南峰,译.中国翻译,2002(4):19-25.
[8]胡安江.寒山诗:文本旅行与经典建构[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1.
[9]黄鸣奋.英语世界中国古典文学之传播[M].上海:学林出版社,1997.
[10]李梓新.Julia Lovell:把鲁迅和张爱玲带进“企鹅经典”[EB/OL].[2012-12-20].http://cnmedia.org/?p=300.
[11]廖七一.文化典籍的外译与接受语境[J].东方翻译,2012(4):4-8.
[12]吕世生.元剧《赵氏孤儿》翻译与改写的文化调适[J].中国翻译,2012(4):65-69.
[13]区鉷,胡安江.文本旅行与经典建构——寒山诗在美国翻译文学中的经典化[J].中国翻译,2008(3):20-25.
[14]钱林森.纪君祥的《赵氏孤儿》与伏尔泰的《中国孤儿》[J].文艺研究,1988(2):117-129.
[15]覃江华.英国汉学家蓝诗玲翻译观论[J].长沙理工大学学报,2010(5):117-121.
[16]莎日娜.《赵氏孤儿》跨文化传播现象考察[J].国际关系学院学报,2011(2):111-115.
[17]谢天振.多元系统理论:翻译研究领域的拓展[J].外国语,2004(4):59-66.
[18]张南峰.中西译学批评[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
[19]周晓琳,胡安江.寒山诗在美国的传布与接受[J].西南政法大学学报,2008(2):125-1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