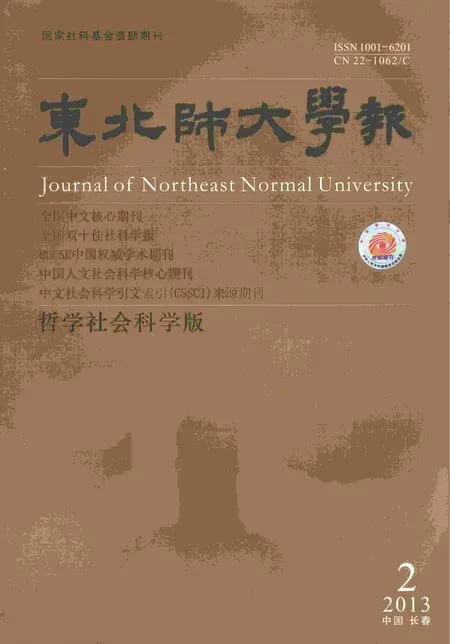明代婢女政策与法规的演进及社会内涵
王雪萍
(黑龙江大学 明清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黑龙江 哈尔滨150080)
对明代社会的历史性变迁,可以从多重角度加以诠释,国家有关婢女政策与法规的演进也是其中之一。婢女政策与法规制定和运行的背后涉及明代国家政治、管理思想以及社会矛盾的嬗变,因此,它是一个具有牵动性的议题。目前,尚未有关于明代国家婢女政策与法规演进的专门性研究成果,相关研究虽有涉猎,但因研究的主旨所限,都没有做更深入地探讨①参见牛建强:《明代奴仆与社会》,《史学月刊》,2002年第4期;樊树志:《明清的奴仆与奴仆化佃农》,《学术月刊》,1983年第4期;郑定,闵冬芳:《“良贱之别”与社会演进——略论唐宋明清时期的贱民及其法律地位的演变》,《金陵法律评论》,2003年秋季卷。。鉴于此,本文尝试以朱元璋婢女政策及由此凝结的明代婢女法规发轫,再延展至明朝其他诸帝,进而揭示有明一代婢女政策与法规的演进特征及社会内涵,希望能对明代社会变迁的整体研究有所裨益。
一、明太祖时期婢女政策与法规基本原则的设定
明太祖时期的婢女政策是围绕国家政治稳定而展开的。朱元璋从缓和阶级矛盾为着眼点,立足于扩大国家名义下的劳动力数量,削减豪绅集团对国家人力资源的垄断,采取政治强力干预手段推行婢女政策。此种思想与朱元璋在明初的其他政治治理思想一脉相承。明太祖的婢女政策亦上升为明代的法律规定,体现在该时期修订的《大明律》有关婢女条文中。这些政策、法规对后世明朝诸帝影响非常大,一度成为他们处理有关婢女问题的行事范本,故明太祖婢女政策的诸多层面值得深入探究。总体上看,它主要包括两大方面:一方面,采取各项手段坚决抑制社会上婢女数量的增长;另一方面,极力维护良贱等级秩序,对婢女的僭越行为予以严厉打击。
(一)坚决推行抑婢政策
在明朝尚未正式建立之前,朱元璋的抑婢思想就已存在。在元末战争期间,朱元璋的队伍就曾经掠夺了大量的婢女。对此,他做出“还婢与民”的举措。据《太祖实录》载:“(朱元璋)召诸将谓曰:‘比诸军自滁来,多虏人妻女,使民夫妇离散,军无纪律,何以安众?凡军中所得妇女,当悉还之。’明日,聚城中男子及所掠妇女于州治前,至则令妇女居内,男子列门外两旁,纵妇女相继出。令之日,果夫妇相认而去,非夫妇无妄识。于是夫妇皆相携而往,室家得完,人民大悦。”[1]卷2,乙未春正月戊午朔尽管这项“还婢与民”的举措有战时收买人心,巩固政权的目的,但由此体现的抑婢思想在明朝建立之初得到了很好的延续。
明朝建立伊始,明太祖对社会上存在的庞大婢女人群依然保持高度关注,为此不断颁布诏敕加以遏制。洪武五年诏告天下:“曩者兵乱,人民流散,因 而 为 人 奴 隶 者,即 日 放还。”[1]卷73,洪武五年三月戊辰稍后,对社会上的蓄婢现象进行限制,普通庶民之家严禁蓄养奴婢,“有存养奴婢者,杖一百,即放从良”[2]45。还规定了功臣及品官之家使用奴婢的数量:公侯家奴婢数不过20人,一品官员不过12人,二品官员不过10人,三品官员不 过 8 人[3]卷56,官员仪从。为 表 抑 婢 的 决心,朱元璋对那些始终跟随自己征战的有功之臣违例蓄婢的行为也同样决不姑息。如明初功臣赵庸,功劳很高,本应封公,“以在应昌私纳奴婢,不得封公,封南雄侯”[4]3807。又如,明初功臣开济,为明太祖所信任,但其骄纵无行,“役甥女为婢,事发,下狱”[4]3978。值得注意的是,此时使用奴婢数量的规定更多的是一种限制行为,旨在约束功臣及品官之家,督促他们放还多余的婢女。可见,明初千方百计促使奴婢放良,以增加社会劳动力。
为了使抑制蓄婢政策尽快显现实效,明太祖还辅以其他相关保障性措施。其一,官府出面收赎那些因为自然灾害而被迫卖身为婢的女性。如洪武五年,在陕西、山西、河南等地都进行了一系列的收赎行为:“军民先因饥荒逃移,将妻妾子女典卖与人者,许典卖之家首告,准给原价赎取归宗;其无主及愿留者听之。”[5]卷20,户口考·奴婢附从“实录”记载观之,此类收赎行为持续有序地进行着:“洪武十九年夏四月甲辰,诏:‘河南府州县民,因水患而典卖男女者,官为收赎。女子十二岁以上者不在收赎之限。若男女之年,虽非嫁娶之时,而自愿为婚者,听。’”[1]卷177,洪武十九年夏四月甲辰及至同年“(八月)庚子,河南布政使司奏:收赎开封等府,民间典卖男女凡二百七十四口,计钞一千九百六十余锭”[1]卷179,洪武十九年八月庚子。收赎年限定在12岁以下,表明此条针对的主要是典卖子女为奴婢的,因为结合后面嫁娶内容来看,超过12岁以上的男女多以婚嫁为名,若官家收赎就有干涉平民婚姻之嫌。其二,制定法律打击各类卖婢牟利的行为。洪武时期颁布的《大明律》记载:“凡收留人家迷失子女,不送官司,而卖为奴婢者,杖一百,徒三年……若得迷失奴婢而卖者,各减良人罪一等……若收留在逃子女而卖为奴婢者,杖九十,徒二年半……若得在逃奴婢而卖者,各减良人罪一等。其被卖在逃之人,又各减一等……若冒认良人为奴婢者,杖一百,徒三年……冒认他人奴婢者,杖一百。”[2]45类似的法律颇多,兹不赘叙。
不仅如此,明太祖朱元璋还采取递进式策略保证抑婢政策的推行。鉴于蓄婢行为已经成为明代社会的一种生活习惯,倘若实行“一刀切”式的激进改革,即无论上至皇室下至庶民都禁止蓄婢行为的话,必然影响国家抑婢政策的推行,甚至导致此政策的夭折。所以,明太祖非常巧妙地从限制蓄婢种类、范围方面,采取递进方式来保证抑婢政策的出台。
在限制蓄婢范围方面,明太祖划定的限婢范围不断缩小。明初国家把蓄婢作为功臣、官员的特权,且不限制他们的蓄婢数量,而只单纯禁止庶民蓄婢。如明太祖在洪武五年昭告天下,那些因势孤力弱和贫穷等因素导致不能自存,转而投靠“庶民之家为奴”的人,“诏书到日,即放从良,毋得羁留强令为奴婢,亦不得收养。违者依律论罪,仍没其家人口,分给功臣为奴驱使。功臣及有官之家不在此限”[6]卷2,劝兴礼俗诏。但到洪武二十四年就规定了公、侯、一品至三品官员蓄婢数目的最高值:公侯家奴婢数不过20人,一品官员不过12人,二品官员不过10人,三品官员不过8人[3]卷56,官员仪从。这表明明太祖限制蓄婢的范围在不断收缩。在限制蓄婢种类方面,明太祖的限制范围由私婢开始,慢慢扩及到官婢。从洪武五年的昭告内容看,明太祖禁止庶民的蓄婢行为。从良家女子沦为婢女的缘由来看,都是因贫穷、势单而不得不投靠,说明这些婢女都是通过买卖方式购得的,也就是通常所说的私婢。可见,明太祖在洪武五年时禁止庶民蓄婢的种类当属私婢无疑。而明太祖对功臣、官员们蓄养私婢的行为不做限定,自然给他们的官婢赏赐也不会做任何的限定。但到洪武二十四年对功臣、一品到三品官员使用婢女数量却做了限定。这些限定婢女数目针对的是皇帝给赐的官婢。
(二)明确婢女的贱民身份
明太祖通过各种途径再次明确婢女卑贱的身份属性。怎样让这群卑贱之人与芸芸众生相区别呢?在此方面,明太祖作了一系列努力,“太祖尝命儒臣历考旧章,上自朝廷,下至臣庶,冠婚丧祭之仪,服舍器用之制,各有等差,著为条格,书成,赐命《礼制集要》”[7]96。其中,服制是当时用来区分等级的外在表现。明初对分属于不同等级身份的人们的着装加以限制,以实现“望其服,而知贵贱;覩其用,而明等威”[8]76的目的。《明太祖实录》记载:“婢使人等绾高顶髻,用绢布夹领,长襖长裙。小婢使绾双髻,用长袖短衣长裙。制曰可。”[1]卷73,洪武五年三月乙亥,[4]1650朱 元璋的意图是在服饰方面,婢女着装“不可与主人相疑,所以正名分而尊其主也”[9]548。在见面礼节方面,洪武二十六年朱元璋规定:“凡民间子孙、弟侄、甥婿见尊长,生徒见其师,奴婢见家长,久别行四拜礼,近别行揖礼。”[4]1428这些显性差异规定使婢女这一卑贱群体更容易被人们识别,其贱民身份进一步被凸显出来。
与此同时,明太祖也着意固化主婢之间的尊卑关系。他从理顺社会各个阶层秩序和巩固统治阶级地位的角度着眼,推行了较为周全、一致的法律条令,使主婢高低、贵贱等级更为清楚。首先,婢女不能打骂、谋杀主人及家属,否则都要给予各等级的惩罚。成书于洪武时期的《大明律》规定:“凡奴婢骂家长者,绞。骂家长之期亲及外祖父母者,杖八十,徒三年。大功,杖八十;小功,杖七十;缌麻,杖六十。”[2]170法律对婢女殴打家长及亲属行为的处罚更严厉,规定:“凡奴婢殴家长者,皆斩;杀者,皆凌迟处死;过失杀者,绞;伤者,杖一百,流三千里。若殴家长之期亲及外祖父母者,绞;伤者,皆斩;过失杀者,减殴罪二等;伤者,又减一等;故杀者,皆凌迟处死。”[2]162其次,婢女为主人容隐则免于处罚,以遵循家内长幼之序。规定:“凡同居,若大功以上亲及外祖父母、外孙妻之父母、女婿,若孙之妇夫之兄弟及兄弟妻有罪相为容隐。奴婢、雇工人为家长隐者,皆勿论。若漏泄其事及通报消息,致令罪人隐匿逃避者,亦不坐。”[2]18-19与之相通,婢女不能告发主人,否则视为犯罪[2]177。最后,不许婢女背主逃跑与私嫁,“若婢背家长在逃者,杖八十。因而改嫁者,杖一百,给还家长”[2]61。
另外,明太祖朱元璋亦强化平民与婢女之间的良贱关系。在社会层面上,明太祖遵循良贱有别,良高于贱的原则,围绕平民与婢女的良贱身份制定了各种法律规范。如关于良贱之间发生冲突的处理办法,《大明律》中《良贱相殴》条规定:“凡奴婢殴良人者,加凡人一等。致笃疾者,绞;死者,斩。其良人殴伤他人奴婢者,减凡人一等。若死及故杀者,绞……若殴缌麻、小功亲奴婢,非折伤勿论。至折伤以上各减杀伤凡人奴婢罪二等,大功减三等,至死者,杖一百,徒三年。故杀者,绞。过失杀者,各勿论。”[2]162另外,《良贱为婚姻》条也开列了婢女违法婚姻的处理方法。规定:“凡家长与奴娶良人女为妻者,杖八十,女家减一等,不知者不坐。其奴自娶者,罪亦如之。家长知情者减二等。因而入籍为奴婢者,杖一百,若妄以奴婢为良人而与良人为夫妻者,杖九十,各离异改正。”[2]62从上述贯彻明太祖婢女政策的系列法律规定中不难发现,明代法律严格地区别了婢女的贱民身份,并按照有别于良人的标准对婢女的违法行为分别实施不同程度的惩罚。
二、明后世诸帝婢女政策与法规的变通与调整
明太祖时期的婢女政策和法规为有明一代国家规范婢女群体奠定了基本原则,其后的明代诸帝对这些基本原则的把握基本不差,并没有公然地违背。特别是在婢女法律上,由于其具有稳定性而被始终遵守。但是,后世诸帝的婢女政策因需要与社会相适应,故与明太祖时期有程度不等的差异。如这些后世诸帝尽管仍然保持控制婢女数量过多增长的自觉性,最起码这种自觉意识在皇帝个人身上还有清晰显现。然而在推行抑婢政策时却明显不如明太祖时期那样强硬。再有,随着社会经济状况的好转,为了顺应社会各阶级对婢女需求数量的增加,后世诸帝把婢女政策重心放在注重提升婢女对自身职责的个人认同度、表彰杰出婢女事迹上。
(一)明成祖朱棣婢女政策所具有的宗教性色彩
明成祖朱棣行事风格颇类其父,对洪武时期的抑婢政策也奉行得比较认真。但与明太祖不同的是,明成祖在推行婢女政策时,更加注意大量使用宗教信仰的神秘力量来增加其政策的规范效果。明成祖朱棣将宗教中的果报论应用到其婢女政策中,明显例证便是他撰写了一部名为《为善阴陟》的书。他在序中称:“朕惟天人之理一而已矣。书惟天阴陟下民。盖为天之默相,保佑于冥冥之中,俾得以享其利益,有莫知其然而然者,此天之阴陟也。人之敷德施惠,不求人知而无责报之心者,亦曰阴陟。人之阴陟固无预于天,而天报之者其应如响。尝愽观古人,身致显荣,庆流后裔,芳声伟烈,传之千万世,与天地相为悠久者,未有不由阴陟所致。”[10]序从序言中看,明成祖规劝世人行善之意图非常明显。其中有六则故事是关于婢女的,篇目分别为:《弘敬延寿》、《范宰择嫁》、《禹钧行善》、《查道倾囊》、《公亮与钱》、《王令嫁孤》,其故事内容大都为主人公因各种机缘巧合遇到了良家女、官家女沦为婢女,而不忍驱役之,终获善报的事情。在每个故事结束之后,明成祖都会作一番评论。如在《弘敬延寿》中,他称:“人之寿夭贫富,虽曰前定。然能存心忠厚,济人利物,念念不忘。至其阴功善行,积累既深,感动于天地神明,则夭者可寿,贫者可富。前定之说有时而不可必矣。若刘弘敬者,家虽富而不刻取于人,乐善好施而不望报,其心之所存可知矣。及闻相者大期将至之言,乃安于命分,遽为身后之计。因买婢之事,而仁慈恻怛之心,惕然著见,使流离颠困之女,得配良人,其心宁有所希冀哉!一旦感之于梦寐,形之于气色,于是寿延二纪,富及三代之言,不爽毫发。世之有志于为善者,观此宜益加劝矣。”并有诗云:“家富非因刻众成,大期将至莫逃生。只将一念存忠厚,即感天教福寿并。名家有女困流亡,弘敬慈心特感伤。择配良人阴德厚,寿延二纪子孙昌。”[10]卷4其他的故事内容与评论大致类此。明成祖大篇幅地记录这样的故事,其最终欲强调的就在于“无他,止将婢作甥女嫁之”、“不忍以贵为贱”以及“因买婢之事,而仁慈恻怛之心,惕然著见,使流离颠困之女,得配良人,其心宁有所希冀哉”。这些话语意在向众人宣扬,生活中随处都能为自己及子孙积累阴德,像不蓄养婢女这样很容易为人做到的事情,也会积阴德,这实际上与其政治层面的抑婢政策互为表里。
(二)明代其他诸帝婢女政策的变化
面对社会现实中的庶民蓄养婢女现象以及婢女数量不断膨胀之现状,明代皇位继承者们非常清楚地意识到,为了维护国家的安定团结,他们不可能像自己的老祖宗那样对社会的蓄婢行为进行强制性的约束,因而转向怀柔和疏导。朱棣将宗教中的因果报应说作为一种手段纳入婢女规范范畴,就是婢女政策变化的体现。除此之外,明后期其他诸帝还将婢女政策的重心转向缓和主婢矛盾,避免其升级,并倡导“主婢之义”上。
具体表现为:其一,官赎婢女措施的继续推行。史载:“虞谦字伯益,金坛人也。洪武乙亥由太学生擢刑部山东司郎,中升杭州知府。永乐初,召为大理寺左少卿,寻升左副都御使,命巡视淮扬旱灾。至则疏民所苦,请发廪赈贷,官为赎还所卖男女为奴婢者。”[11]卷29,虞谦宣德时期,下旨官赎于旱灾中所卖男女为奴婢者[12]卷26,宣德二年三月壬子。神宗时期也有救赎灾民的政策[13]卷277,万历二十二年九月庚辰。其二,规范宗室征选婢女之相关事宜。明宣宗时期,统治者对社会层面驱使婢女的态度还很谨慎,因担心臣官们的“烦言”,而希望宗室对采买婢女事宜需慎重,这表明统治集团对蓄婢于良民的行为还很自律。“实录”载:“宣德元年夏四月辛未,秦王志均奏已择陕西都指挥张麟女为婚,所少使女个人欲于军民之家选用。上复书曰:‘择婚已定,当卜日发册。使女若选于民间,或非其所愿,必致烦言。西安护卫军家女子必有愿入官者,宜访求,酬之以直,但不宜抑取以失其心。’”[12]卷16,宣德元年夏四月辛未宣宗虽允许秦王征婢,但他对征婢方式的细节却百般嘱咐,其一是必须给费用,其二不能强征。宣宗对当时社会上蓄婢风气以及引起的民怨有所了解,不支持但也无能为力,只能希望宗室本身能够做到合乎规范才好。英宗也对宗室征选婢女的行为进行了相应的约束①参见《明英宗实录》卷44“正统三年秋七月壬寅”条;卷51“正统四年二月辛酉”条;卷85“正统六年十一月辛亥”条;卷102“正统八年三月戊辰”条;卷110“正统八年十一月庚申”条;卷136“正统十年十二月癸亥”条;卷139“正统十一年三月庚午”条;卷196“景泰元年九月辛酉”条;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室影印本,1967年版。。明英宗复辟后,宗室所用婢女数量庞大,为避免引起公议,镇国将军钟镒为求自保,而自愿放归府内多余的婢女来向皇帝邀宠[14]卷279,天顺元年六月丙申。其三,打击那些在社会产生恶劣影响的虐婢事件。如明代宗时期,鼓励御史弹劾犯官收“义女”为妾违例之事宜[14]卷218,景泰三年秋七月戊戌。明宪宗时期,官员邓夕因虐婢而被罢官[15]卷5。正德时期,皇帝亦严惩滥杀婢女的官员。如当时的刑部主事陈良翰妻程氏虐杀婢女数人,“东厂廉得其事,并良翰俱下锦衣卫狱。拷讯得实。都察院覆议。程氏穷凶极惨,比拟故杀律斩。良翰纵妻为恶,谪戍边卫。上从其议”[16]卷104,正德八年九月丁丑。明宪宗时期,皇帝亦严惩了滥杀婢女的礼部致仕左侍郎杨宣之妻王氏[17]卷289,成化二十三年夏四月癸酉。其四,整肃与婢女相关的事宜。明代宗时期,经过刑部官员讨论,决定保留主人告“义女”不孝之罪名。“景泰元年二月丙戌,刑部署郎中王概言:‘旧例,告义子女、义女、义孙妾子、前妻前夫之子不孝者,必审其四邻,盖恐挟私冤抑也。其义子女又必验其年岁,如过房在十五岁前曾受义父母鞠养,则坐以不孝;不然,但以雇工人殴骂家长律坐之。比奉诏尽革条例,臣以为此便不宜去。’从之。”[14]卷189,景泰元年二月丙戌明英宗时期,对宗室成员家内因奸婢引发的矛盾进行处理与训诫。如“正统六年秋七月己酉,代王桂宠其侍女荣花、菊花,妃徐氏妬之,粪其鼻口,漆其身成癞。已而,傅药溃烂之,复潜令卫卒阴仲谦诱之亡去。大同府官以闻,上命王妃勿问,仲谦付佥都御史罗亨信治之,狱成坐杖,命杖讫发甘肃充军。仍赦谕王:‘自今宜严肃内外,以正家法,凡有当行之事,悉令世孙奉行,不许妃嫔干预。’”[14]卷81,正统六年秋七月己酉英宗时期,对明太祖时期“奸义男妇”条令进行重新认定。史载:“正统三年十一月丙戌,民有收义女为妾者,法司论奸。大理寺评事王亮奏请行勘:原卖与媒合人果系义女,罪之如律。若通房使女收为妾,而立约明白,两相愿者,不治罪、不离异。从之,遂著为令。”[14]卷48,正统三年十一月丙戌“正统十三年六月己未,刑部尚书金濂奏:‘奸义男妇者,洪武永乐以来,有论依奸子孙之妇应斩,有论依奸妻前夫之女应徒者,情犯相同,议拟不一,伏乞圣断,永为遵守。’三法司奉诏议:‘亲男与义男情有亲疏,若将奸义男妇与奸亲男妇同罪,亲疏之情不分。今后有犯前罪者,宜比奸妻前夫之女徒罪科断。’上曰:‘通奸者准拟徒,其男与妇仍断还本宗;强奸者处斩。’”[14]卷167,正统十三年六月己未其五,明后期诸帝倾向于引导婢女重视自身职责,并树立此方面的婢女典范。出于维护主婢秩序的目的,明代特别注重发挥婢女典范们的榜样作用。像朱元璋的得力大将花云之侍儿孙氏因护主有功,至明武宗时期被封号立祠[18]卷9,正德十六年十二月戊戌。花云将军的侍儿孙氏救主之事发生在明初,但在历经150年之后,明武宗又将孙氏重新加封授予殊荣,其榜示目的不言而喻。再如,明神宗时期还主张旌表婢女盛儿殉主的行为[13]卷194,万历十六年正月丁酉。上述种种举措皆反映了明代政府大力推崇那些能够蹈行“主婢之义”的婢女们。
在上面提及的明后期诸帝对婢女政策的变通中,有四个地方需要注意:其一,明太祖时期由官府出面的“还婢以民”的抑婢政策,至宣德以后转变为旱涝灾荒时期政府的赈灾慈善之举。其二,明太祖时期对宗室、功臣、高官蓄婢行为的严禁政策,在英宗时期尚可看到,《英宗实录》中还反复记载了皇帝对宗室蓄婢违例情况的训诫与劝导,之后的皇帝在此方面几乎没有花费什么心思,太祖时期对社会统治阶级上层社会的遏制方针就此沦为空文。其三,皇帝对社会中的虐婢、杀婢等违法事件的处理,不是一种经常性的状态,并且其本身带有一定的“仪式性”,这就如同皇帝每年中的“祭天”、“励农”仪式,只是表明了一种意愿,而非国家利器。皇帝对虐婢、杀婢的偶尔严厉的处理意见亦如此,通过个案的处理与宣扬,表明了皇帝希望约束主家的违法行为,但由于缺乏必要的、强有力的、社会制度化的措施,其结果微乎其微。其四,明中后期的婢女政策由初期的抑制转为疏导与维持。这是顺应明代婢女数量膨胀趋势之举。因为明代国家政府的管理机器已经无法有效控制婢女数量增加的势头,只好倾向于怀柔政策,表现为倡导“主婢之义”,营造主婢良好互动之社会氛围,以减少主婢矛盾,达到维护社会稳定之根本目的。
三、明代婢女政策与法规演化的社会内涵
纵观有明一代,明太祖有关国家婢女政策与法规尽管在形式上被后世明代诸帝所坚持,但在婢女政策的重心和方式上还是存在差异。明成祖朱棣在推行婢女政策上,更加注意大量使用宗教信仰的神秘力量,通过积阴德、讲果报的宣传,增加其政策的规范效果。这也反映出明太祖以后诸帝在推行抑婢政策时已经从强硬走向了柔性。虽然明太祖以后还能看到皇帝对社会中虐婢、杀婢等极端违法事件的处理,但已不是一种经常性的状态。在明英宗以前,皇帝尚能对宗室蓄婢违例情况进行训诫与劝导,之后就鲜有发现。明太祖时期对社会蓄婢行为的严禁政策事实上已经不存在了,而代之以疏导手段。也即国家极力提升婢女群体对自身职责的个人认同度,表彰杰出婢女事迹,倡导主婢之义,旨在营造主婢良好互动之社会氛围。明代国家婢女政策从严禁走向怀柔,由强制转为疏导,其背后是社会上婢女数量的逆向增长,蓄婢阶层的渐趋广泛以及对蓄婢特权的普遍僭越。
明太祖采取的抑婢政策,不仅出于小农经济下对生产力的维护和社会的稳定,也是极力保持社会等级秩序,从而达到“别贵贱、正名分”的目的。但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有关婢女的法规便不断被冲破。仅从人们着装上说,已让人“上下无辨”[13]卷51,万历四年六月辛卯,无从知晓其身份。朱镛就曾对此进行批评:“近数十年来,士习民心渐失其初,虽家诗书而户礼乐,然趋富贵而厌贫贱……侈繁华,则曳缟而游,良贱几于莫辨。礼逾于僭,皆无芒刺,服恣不衷,身忘灾逮。”[19]39赵鸿赐也称:“司马温公,清修寡欲,家无曳绮之妾,而婢仆之禁甚严。一日有客自轮盘隙中见一婢蓬首垢面,疙瘦如鬼,不觉警叹,乃知前辈治家严内外之分如此。愚谓近日缙绅之家婢仆皆曳绮阑入,亦足羞矣。”[20]卷1上述婢女曳缟、曳绮,缟、曳都是丝织品,是上等阶层所用,婢女身份为贱民,穿丝织品服装与其身份不符。不仅如此,按规定婢女应穿青色衣服,故常被称为“青衣”,但在此时婢女着装艳丽却较为常见。叶梦珠曾讲道:“婢女出使非大红里衣不华”[21]卷8。《金瓶梅》中有一段潘金莲假扮丫鬟时的服装描写,“(金莲)寻了一套大红织金袄儿,下着翠蓝缎子裙:要妆丫头,哄月娘众人耍子”[22]549。
不仅奴婢的穿着、起居违礼越制,对奴婢数量的限制也流于形式。尽管明初朱元璋对社会上的蓄婢现象进行了限制,要求普通庶民之家严禁蓄养奴婢,并规定功臣及品官之家使用奴婢的数量,但这些规定后来在社会中日趋衰微,起不到约束作用。据《孝宗实录》记载,弘治元年“在京各驸马、皇亲及天下王府并王亲仪宾之家,蓄养奴婢、家人之类,比之旧制,或多逾十倍”[23]卷19,弘治元年十月乙未。为更加清楚地说明当时违例蓄婢之现象,现以镇国将军钟镒为例。“天顺元年六月丙申,庆成恭僖王庶长子镇国将军钟镒奏:父存日,所选寡妇及买使女入府使用数多,今父薨,禄米截日住支,供给不敷。且妇人无人管束,皆有依亲之愿。除年老无归者,臣自行养瞻,欲将少壮有依者给亲完聚,俾无幽滞。上览奏称善,从之。”[14]卷279,天顺元年六月丙申正是这个钟镒在英宗时期还主动上请减少自家婢女数目,而至孝宗初年则因滥占使女、多子、冒支禄米而遭到官员非议。《湧幢小品》对此有专门记载:“庆成王钟镒,谥荣惠,晋恭王之曾孙也。弘治五年八月,山西巡抚杨澄等奏王子女至九十四人,恐其人有收养异姓之弊。且为子镇国将军奇□等增年,冒支禄米,乞下礼部议处,并乞限各郡王以下,妾媵之数。礼部查勘覆奏,谓王子女俱王妃、夫人并宫人、室女所生,别无违礙,其冒支禄米,法宜追征还官。得旨。王子女既无违礙,其支勿论,冒支禄米,不必追征。准作以后年分该支之数。法司原奏,有不许滥收子女事例,仍行各王府知会。自郡王以下,妾媵多少之数,再会官定议以闻。礼部复会议覆奏,谓郡王自正妃外,妾媵不得过四人,各将军不得过三人,中尉不得过二人,从之,著为令。王后生子至百人,俱成长,又皆隆准。自封长子外,余九十九人,并封镇国将军。今本府数至二千余人,他府有止二三十人者。”[24]卷21,多子从朱国祯的记述可知钟镒的子女竟有一百位之多,试想倘若负责侍奉每位子女的婢女数量为2—4人①《明孝宗实录》卷26,弘治元年六月丙午,规定“晋府庶人使婢四人”。进而结合《明武宗实录》卷8的相关内容:弘治十八年十二月甲戌,“凤阳高墙庶人(即犯罪的皇家子弟——作者注)使女止许一二人”。可以说,2~4人的婢女数量还都是戴罪之人的待遇,其他清白皇家子弟所拥有的婢女数量只能比此数值要高,也许会高许多。,100位王子将有几百个婢女,况且这还是最低数值,扩而想之,这还仅仅是负责照顾子女的婢女数量,其他诸人如王妃、夫人等主人身边的婢女数量也不会小,加起来,钟镒府上的婢女数量实在庞大得惊人!从钟镒天顺元年(1457)上奏皇上削减婢女至弘治五年(1492)遭官员弹劾,这短短的33年间其家婢女数目成几十倍增长,可看做明代社会婢女数量膨胀之缩影,也是明初抑制良家女子为婢女政策之失利。
更为出格的是,从弘治时期开始,明宗室子弟竟有为自己的宠婢向皇帝“为请祭祀”。“弘治五年十二月甲辰,赵王见灂乞封其宫人罗氏为夫人,礼部复奏于例不合,不允。”[23]卷70,弘治五年十二月甲辰上行下效,有些官员也敢向皇帝撒谎,为婢请祭。如“天顺四年六月庚戌,彭城伯张瑾初收其妻朱氏从嫁婢为妾。婢死,自称次妻,上章乞祭祀,礼部以无例格之。至是,为校尉所觉,六科十三道劾举其罪,下都察院,狱具当徒。”[14]卷316,天顺四年六月庚戌尽管这样的请封没有被获准,但上至宗室下至官员的为婢请封之举,却说明明太祖时期的婢女政策在当时社会上的失利状况。在这一良贱混淆、等级秩序备受冲击的历史背景下,明代诸帝关于婢女政策与法规的调整就是一种顺应社会变迁的历史性选择。
明初国家限婢政策逐步走向消解存在基础性动因,这就是明代经济与社会的蓬勃发展,使拥有财力蓄婢的阶层不断扩大,进而拉动社会上对婢女的强大需求。但除此之外,国家秩序与社会秩序固有的矛盾和冲突亦是关键所在。朱元璋的限婢政策有明初政治稳定的考量,同时也来源于其农业立国思维。农本政策的出发点是促使劳动力与土地的结合,而社会上奴婢的大量存在妨碍了劳动力的归农。故朱元璋限婢政策的目的是规范国家秩序,包括国家的经济秩序、政治秩序。虽然朱元璋在规范国家秩序中,对良贱等级尊卑的社会秩序采取了维护政策,然而他却将蓄婢作为一种特权限定在政治高层范围,对社会上大多数阶层的蓄婢行为加以禁止。这实际上是国家秩序对社会秩序的干预。为了实现设想的国家蓄婢秩序,朱元璋采取了法制化、强控制的手段,要求社会蓄婢秩序与其保持高度的一致。对于破坏国家蓄婢秩序的任何社会势力,国家都采取严格防范、严厉打击的措施。然而,随着经济与社会的发展,朱元璋时期实行国家限婢政策的社会环境在变化,社会上蓄婢需求逐步扩大,自发蓄婢秩序的因子也在逐步增强,社会也要求国家蓄婢秩序的松动和调整。但明太祖朱元璋婢女政策作为祖制或祖训无法改变,这导致了一方面明代国家婢女基本政策的愈加僵化,另一方面是社会秩序与国家秩序的日益背离。如何解决在规范婢女群体问题上,国家秩序与社会秩序的冲突成为明太祖以后诸帝面临的现实问题。由此不难理解,明太祖以后诸帝在表面遵从明初刚性限婢政策的同时,更多地表现出处理具体社会蓄婢秩序的弹性。这既是对明初国家蓄婢政策的变通,也是对明太祖以后日益凸显的社会蓄婢秩序的暗和。
[1]明太祖实录[M].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室影印本,1967.
[2]大明律,怀效锋校[M].沈阳:辽沈书社,1990.
[3]李东阳.明会典[M].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4]张廷玉.明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4.
[5]王圻.续文献通考[M].万历三十年(1602)松江府刊本.
[6]皇明诏令[M].嘉靖二十七年(1548)浙江布政使司刻本.
[7]余继登.典故纪闻[M].北京:中华书局,1981.
[8]张瀚.松窗梦语[M].北京:中华书局,1997.
[9]瞿式耜.媿林漫录[M].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
[10]朱棣.为善阴骘[M].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
[11]过庭训.本朝分省人物考[M].明天启刻本.
[12]明宣宗实录[M].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室影印本,1967.
[13]明神宗帝实录[M].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室影印本,1967.
[14]明英宗实录[M].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室影印本,1967.
[15]戴冠.濯缨亭笔记[M].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
[16]明武宗实录[M].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室影印本,1967.
[17]明宪宗实录[M].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室影印本,1967.
[18]明世宗实录[M].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室影印本,1967.
[19]崇武所城志[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7.
[20]赵鸿赐.无甚高论[M].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
[21]叶梦珠.阅世编[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22]秦修容.金瓶梅:会评会校本[M].北京:中华书局,1998.
[23]明孝宗实录[M].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室影印本,1967.
[24]朱国祯.湧幢小品[M].明天启二年(1622)刻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