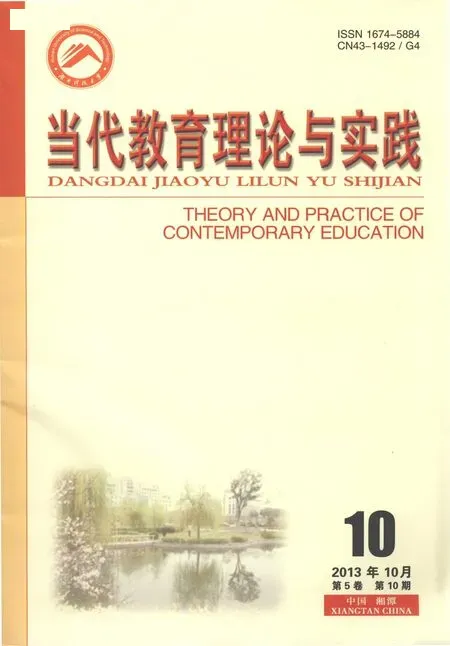哈姆莱特形象在中国的成长①
张吉轶,姚天问
(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湖南长沙410000)
在我国文学界浮现出性格各异、血肉丰满的异国形象,不懈追求的浮士德、疯癫惧怕的狂人、英勇好战的阿基琉斯等,这些他者形象通过各种传播方式被我们知晓,或多或少地打上本土色彩,入乡随俗而被我们接受,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们笔下所塑造的自我形象。对于这些他者形象,在接受过程中,我们进行了再创造,在不同时期,或者同一时期不同学者的作品中,具备乌托邦色彩来表达对于本国的希冀和叹息,或是染上意识形态的色彩来认同自我的价值。在这众多异国形象当中,莎士比亚《哈姆莱特》戏剧中的主人公哈姆莱特形象具有人物饱满、性格丰富的特点,自传入中国以来,学界对该形象的探讨一直津津乐道,产生着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同时印证了中国各时期的社会百态。
一 哈姆莱特在中国的异国形象
比较文学中的他者形象,即异国形象,包含乌托邦和意识形态两种模式。所谓乌托邦模式,即塑造一个异国形象进行自我批判,把这个并非真实的异国形象作为一种异己力量来质疑现存秩序,期望对自身文化传统和社会现实进行修正和调整。而意识形态模式的异国形象,是“按本社会模式,完全用本社会的话语重塑出的异国形象。从注视者主体立场讲,它是要维护和保存本国现实。”[1]用自身文化的优势去蔑视异域文化,以加强自身文化的认同感和凝聚力。总之,异国形象的塑造者把自我意识和灵魂注入其中,通过异国形象来诉求自我的理想、欲求,诉说自身的焦虑、恐惧,因而异国形象具有表达“他者”和言说“自我”的双重功能。
19世纪中叶,莎士比亚的名字由西方的传教士带到了中国,自此在东方这座大舞台上便不断演绎着缠绵悱恻、悲壮雄丽的故事,其中《哈姆莱特》成为中国观众最熟知的作品。20世纪50年代后,哈姆莱特的形象俨然成为在莎剧众多形象中,被研究得最多,争论得最激烈的他者形象。
50年代后中国对莎士比亚的哈姆莱特形象的认识研究,李伟民先生将其分为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中国莎学引进苏联莎学,强调莎士比亚及其作品和艺术形象,包括哈姆莱特的人民性、阶级性。第二阶段:莎士比亚具有时代先进性和人民性,哈姆莱特是人文主义者的典型形象。第三阶段:莎士比亚创作体现了人文主义思想,但哈姆莱特并不是人文主义者,他的理想也不是人文主义理想。本文将分别解读这三个阶段哈姆莱特在中国作为他者形象的表现及其成因和影响[2]。
二 乌托邦模式的哈姆莱特形象
(一)乌托邦模式的哈姆莱特形象的表现
中国莎学学者对哈姆莱特形象的认识,以及由此而来的中国社会对其的看法,在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由具有人民性到具有人文主义者理想,都描绘上了乌托邦色彩。
最初的理论认识来自20世纪五六十年代前苏联莎学学者,阿尼克斯特的《论莎士比亚的悲剧〈哈姆莱特〉》是苏联对《哈姆莱特》评价的经典之作,他认为“哈姆莱特是个人文主义者”,“是一场解放人类的光荣战斗中的一员战士”,而之所以他不能找到“改造世界的现实途径和自己身上的其他弱点,是因为时代条件所局限”[3]。他的观点使得哈姆莱特的形象在我国社会中开始被普遍认定为一个人文主义者,甚至时至今日。
在第一个阶段,中国学界认为哈姆莱特的形象具有人民性和阶级性。
在国内对《哈姆莱特》评价的奠基人卞之琳先生,1956年发表了《论〈哈姆雷特〉》,文中分析了哈姆莱特作为“人文主义战士”的形象。卞之琳先生认为哈姆莱特“简直可以说是莎士比亚自己的灵魂,‘时代的灵魂’”,“非常突出而生动地表现了当时的先进人物,为了人类的美好理想,与人民利益相一致的,反抗社会罪恶的斗争精神,斗争里显示出的人道的光辉”[4]。这成为中国《哈姆莱特》评价长期的主导思想。
在第二阶段,中国学界对于莎学的认识仍然有沿袭苏联观点的成分,但相对阶级性而言更加倾向于人文主义理想的特点。
1979年出版的《欧洲文学史》认为哈姆莱特是一个典型的人文主义思想家,同时莎士比亚也注入了自己的理想,“作为人文主义者——新兴资产阶级进步思想家,他具有美好的理想和善良的愿望,他看到封建社会衰亡、资本主义兴起这一历史转折时期的种种矛盾……认为有责任改变这种状况”[5]。人们仍然普遍认为哈姆莱特就是人文主义者的代表,是莎士比亚的传声筒,这种上升到理论上的认识和第一阶段的一样,依旧具有乌托邦色彩。
(二)乌托邦模式的哈姆莱特形象的成因及其社会效应
中国莎学在这两个阶段主要是受到了前苏联莎学观点的影响,结合当时国内外的社会政治环境,形成了对于哈姆莱特形象的阶段性认识。
第一阶段,结合国内自身情况,20世纪五六十年代,新中国刚刚成立,反右倾活动如火如荼,而具有左的阶级理论思想的苏联莎学恰巧成为国内莎学界效仿的对象,研究的视角在莎作中的社会矛盾和阶级关系,重点在揭示莎剧对封建势力和资产阶级的揭露与批判,莎士比亚及其作品,尤其是哈姆莱特的形象,具有中国学界和社会上寄托对新中国美好期许的乌托邦色彩,人们希望像哈姆莱特那样与恶势力对抗,重整乾坤。
到了第二阶段,20世纪七八十年代,随着文革结束和改革开放展现的新面貌,与苏联在政治上关系走向全面对抗时期,国内莎学开始试图离开苏联这个老师。中国莎学取得了长足发展,中国学者们意识到第一阶段马克思主义莎评的研究方法缺乏辩证的观点,带有那个时代特定的色彩,开始摆脱阶级性这个观点。七八十年代正值新的经济体系建立,全国各地蓬勃发展时期。而哈姆莱特在威登堡大学就读的背景,使哈姆莱特仅仅是穿着中古丹麦王子的华丽服装,而具有了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思想正是当时国内学界和社会所需要的,是人们所殷切期盼的,从而在这个阶段中国莎学认为,哈姆莱特体现了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者的典型形象,这也是中国学界和社会用他者的形象来寄托对于自身的期许,哈姆莱特这个人文主义者的形象依旧具有了强烈的乌托邦色彩。
这种对异国形象具有乌托邦色彩的认识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苏联阿尼克斯特的莎学理论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成为中国学者研究莎作的指导书,苏联莎评成为指导中国莎学研究者解析莎作的有力武器,甚至是成为大学外国文学和莎士比亚课程讲授的参考书。这种影响不仅从20世纪二三十年代引进苏联莎评以来影响着中国对于莎作的解读和对哈姆莱特形象的理解,而且50年代后又历经五六十年,到21世纪还在潜移默化地通过各种途径对学习者们传输着“哈姆莱特就是人文主义者的思想”。苏联莎评的影响如此深远而广泛,中国莎学在第二阶段有意识地摆脱却仍然无意识地沿袭着传统观点,可想而知,具有人文主义思想的在中国的乌托邦模式的哈姆莱特形象,不只在中国过去、现在产生着影响,在未来也将发挥一定的作用。
三 意识形态模式的哈姆莱特形象
(一)意识形态模式的哈姆莱特形象的表现
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学界对于莎士比亚的哈姆莱特形象的认识进入了第三阶段。国内莎学界开始认为莎士比亚创作体现了人文主义思想,但哈姆莱特并不是人文主义者,他的理想也不是人文主义理想。笔者认为这样的哈姆莱特形象开始摆脱了乌托邦模式,逐渐转变到了意识形态模式上来。
1984年陶冶我先生发表了《“哈姆雷特想要改造现实”说辨惑》一文,对准枪头反驳了阿尼克斯特认为的把哈姆莱特“重整乾坤”理解为“改造现实”的说法,从剧本文本着手,论证了“重整乾坤”即是为父报仇、夺回王位,认为哈姆莱特并非理想的认为主义者的典型[6]。其后1985年叶舒宪先生发表《从哈姆雷特的延宕看莎士比亚思想中的封建意识》,1986年,高万隆先生发表《哈姆莱特是人文主义思想家吗》,认为“那种先从‘哈姆莱特是人文主义思想家’这一既定概念出发,而后从剧本中找根据的批评,只能图解、割裂甚至歪曲原作中的艺术形象。”[7]从丛先生发表《论哈姆莱特并非人文主义者》等等,表明国内莎学研究者们开始旗帜鲜明地质疑哈姆莱特这个形象所含有的人文主义理想的成分,“我们说哈姆莱特不是人文主义者,并不意味着否定莎士比亚是一个人文主义者的典型代表,也不意味着否定《哈姆莱特》一剧具有明显的人文主义倾向。”[8]
第三个阶段,在中国莎学者们看来,哈姆莱特不再是人文主义者的形象,不再只关注莎作的社会矛盾和阶级关系,就片面地认为哈姆莱特的形象也具有阶级性、人民性,和符合社会发展需要的人文主义色彩,而是开始探讨哈姆莱特悲剧的各种成因,在此过程中,逐渐辩证地分析哈姆莱特的形象。他一开始是快乐的王子,而后遇到变故,在挫折面前变得延宕,从而没有完成重整乾坤的任务。国内莎学界对其悲剧探讨出多种成因,有性格说、有环境说、有人与社会关系说等等,这些探讨,都将之前寄托着自身期许的乌托邦色彩的哈姆莱特形象,拉回到现实中来,王子不再只是拥有着人文主义就非常快乐的,受困难阻挡,受信仰徘徊,这样的凡人形象,甚至不符合人们自身创造新社会的愿望,于是对于哈姆莱特悲剧的种种探究当中,逐渐形成了对于其形象定位的意识形态模式。通过这种探因,诉说着人们自身对困难的焦虑、恐惧,从而将言说哈姆莱特这个他者形象的乌托邦模式转变成为诉说自我的意识形态模式上来。
(二)意识形态模式的哈姆莱特形象的成因及其社会效应
随着时代的发展和改革开放进程的推进,中国的国际地位在软实力和硬实力上都在以令人咋舌的速度提高,在文化上的话语权也逐渐凸显,西方以往的霸权主义也随之受到怀疑,并不是所有的西方经典就是能符合国情,促进国内文学及其他方面发展的,中国在接受异国形象的同时,更注重促进国内文学的发展,并将中国文学走出去,使得人们对于哈姆莱特形象上并不是以往那样带有盲目的乌托邦色彩了。另一方面,一些研究者对于以往的莎学研究中掺杂的过多的政治因素和意识形态理念进行了考察,有意识地避免苏联模式带给国内莎学界的影响,对哈姆莱特形象进行客观全面而深入的解构,并引入国际上否定哈姆莱特形象的观点进行参考。在深入研究的过程,进而发现主人公悲剧的多种因素,破除了以往对形象的简单一刀切的认识,乌托邦色彩逐渐淡化,意识形态模式的形象定位开始出现。
对于事物的认识不可能不随时代的发展而一陈不变,打破常规,摆脱传统,勇于革新,都是有利于事物和社会发展的。中国莎学界对哈姆莱特形象的认识能主动突破苏联莎评观点和国内传统看法的强势主导背景,是推进莎学研究的重要一步,是对异国形象的独到认识,是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成果,是对摒弃过去讲话思维方式、理论研究模式的重大举措,是我国学界独立发言的重要标志,是摆脱西方文化优势地位追求平等的有力迈进。
四 结 语
莎士比亚历来是国内外学界研究的重点,而《哈姆莱特》更是代表作品。莎士比亚在作品中倾注了人文主义思想,而对于哈姆莱特的形象是否是人文主义者众说纷纭,国际学界400多年里一直有崇哈派和否哈派之争,而在中国20世纪形成莎学以来,是以苏联莎学的传统崇哈派观点为主,具有强烈的乌托邦色彩,直到七八十年代,由于多方面因素,国内莎学出现了否哈派的声音,哈姆莱特在中国的形象开始由乌托邦模式向意识形态模式发生转变,这是中国对于异国形象研究前进的重大一步,中国莎学将以平等的姿态,对话于西方优秀文化,相互促进人类文化的交流,互相欣赏、增益,以求共同发展繁荣。而哈姆莱特形象在中国的成长历程正可以映射出人们在接受异国形象时,本国的传统和现状的各个方面对其接受过程产生了重大影响,而研究者们只有认清这些社会历史情况才能更好地认识到异国形象对文学及其社会的发展存在的重要意义。
[1]曹顺庆.比较文学论[M].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2002.
[2]李伟民.从人民性到人文主义再到对二者的否定[J].重庆大学学报(社科版),2004(1).
[3]A·阿尼克斯特.论莎士比亚的悲剧《哈姆莱特》[C]//杨周翰.莎士比亚评论汇编(下).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
[4]卞之琳.莎士比亚悲剧论痕[M].北京:三联书店,1989.
[5]杨周翰,吴达元,赵萝蕤.欧洲文学史(上)[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
[6]陶冶我.哈姆雷特“改造现实”说辨惑[J].温州师院学报,1984(2).
[7]高万隆.哈姆莱特是人文主义思想家吗[J].山东师大学报,1986(4).
[8]从 丛.论哈姆莱特并非人文主义者[J].河北大学学报,198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