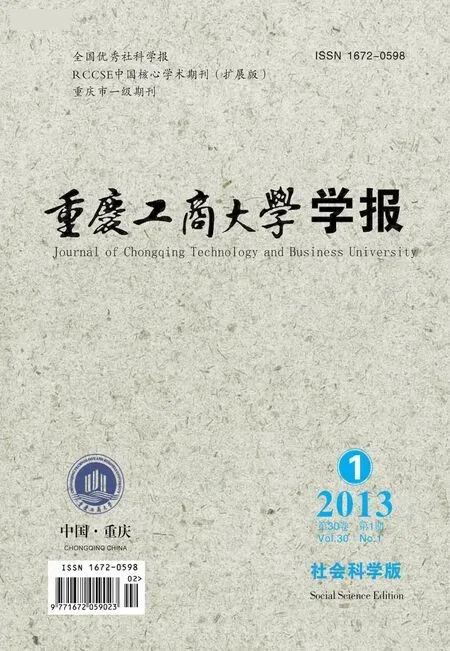席慕蓉诗歌的民族个性及其影响*
一、席慕蓉的成长背景
席慕蓉蒙古名穆伦·席连勃(一作“木润·席连帛”,为音译使用不同汉字的差异),曾使用“漠蓉”“萧瑞”等笔名。席慕蓉1943年农历10月15日生于重庆西郊金刚坡(今沙坪坝区歌乐山中),金刚坡抗战期间为国民政府官僚及中央大学教职员等住地,郭沫若任厅长的国防部三厅文化工作委员会也在金刚坡,参加三厅工作的田汉、阳翰生、冯乃超、傅抱石、李可染等曾居于此。抗战胜利后席慕蓉随父母辗转南京、香港,1954年迁至台湾定居,1964-1966年到比利时布鲁塞尔皇家艺术学院进修,曾任新竹师范学院美术科副教授、教授。
席慕蓉生活在典型的蒙古家庭,朝夕相处的父母、外祖母都是蒙古族人,外祖母全名宝尔吉特光濂公主,属于吐默特部落,成吉思汗嫡系子孙。蒙古家庭有一个传统,从小在家里父母都会告诉很多部族规矩、有关家族的历史。在席慕蓉成长、生活的家中,爸爸妈妈都说蒙语,外祖母也鼓励席慕蓉说蒙语,这是有利于蒙古民族文化传承的环境。“据说,在我很小的时候,本来是会说蒙古话的,虽然只是简单的字句,发音却很标准,也很流利。……家里有客人来时,我就会笑眯眯地站出来,唱几首蒙古歌给远离家乡的叔叔伯伯听。”(席慕蓉《飘蓬》)不过随着年龄增长,在家的时间毕竟不及在学校和所处南方汉文化大环境的活动多,所以席慕蓉说,“长大了以后的我,却什么都记不起来,也什么都说不出来了”(《飘蓬》)。但从小在家里接受的蒙古文化的熏陶,还是铭记在心灵深处。1989年8月1日台湾地区公教人员赴内地正式解禁,8月20日席慕蓉就到达“父亲的草原上”,“我第一次见到故乡的时候,我是没有记忆的。我没有任何印象,我有的是所有我的父母、外婆给我的讲述、我的想象。然而当我第一次踏上蒙古高原,真正见到草原的景象,我觉得我见过,在梦里我见过!”[1]席慕蓉丈夫刘海北说,在最初和她交往的时候,发现她最具北国气质——是就是,不是就不是,从心到口是一条平坦笔直的大道,没有一丝拐弯抹角。[2]可以判断,虽然席慕蓉并没有出生于蒙古高原,没有成长、生活于草原大漠,由于蒙古文化自身强有力的延续性,通过席慕蓉父母、外祖母等从小全面的教育,得到非常确定的有效传承。
有的学者认为席慕蓉受到蒙、汉、欧三种文化影响,但席慕蓉在欧洲学习时间较短,且主要学习美术技艺,其留学期间的生活范围也主要在中国留学生中间,从她的诗歌来看,欧美文化的影响并不显著。蒙古民族的血统、蒙古民族性格与文化,以及长期受汉民族文化的熏染,相当程度影响了她的生活和创作。质朴、粗犷、豪迈的草原游牧文化基因与深厚的汉文化交融、互补,形成了适度的审美“距离”,构成具有艺术魅力的“陌生化”效果及独特的新鲜风格。
二、席慕蓉诗歌的民族个性
1981年席慕蓉第1部诗集《七里香》出版,1983年第2部诗集《无怨的青春》出版,这两部诗集出版后均在极短时间内多次再版,确立了席慕蓉在台湾地区的影响和地位。1986年席慕蓉诗集开始在中国内地正式出版,也在很短时间内多次再版,进一步扩大了席慕蓉的影响。读者在接受席慕蓉诗歌的时候,一般并不注意其中的民族特性,这当然和席慕蓉出生于南方、生活于南方、接受汉文化熏陶有着密切的联系。不过,读者还是感觉到席慕蓉诗歌中具有一些与众不同的元素,这些元素带来了新鲜甚至略带神秘的艺术体验。这些新元素的构成是比较复杂的,民族特性则是其中不应忽视的要素。席慕蓉诗歌具有典型的蒙古民族的生存特征、独特个性与文化心理。例如:
就这样一直走下去吧/ 不许流泪不许回头/ 在英雄的传记里/ 我们从来不说/ 他的软弱和忧愁
就这样一直走下去吧/ 在风沙的路上/ 要护住心中那点燃着的盼望/ 若是遇到族人聚居的地方/ 就当作是家乡 (《祖训》)
蒙古民族因为游牧而迁徙不定,要不断寻找新的牧场,即使熟悉的牧场也不能保证没有被其他部族抢先到达或占领。辽阔的草原缺乏天然遮蔽,易受恶劣气候、外族侵扰等许多不确定因素的剧烈影响,一次巨大的自然灾害或者外敌入侵都可能改变一个部族的命运。因而,他们对未来抱有强烈的不确定性。所以,蒙古民族的文学艺术一方面表现蒙古高原的辽阔博大,蒙古人民的勇敢无畏,又往往呈现一种苍凉乃至悲壮的韵味,蒙古族的马头琴声,蒙古民族的歌声,大多也有这些特征。这种苍凉、悲壮,加上席慕蓉父母从蒙古高原迁徙南方,随国民政府从重庆到南京,辗转香港再到台湾定居的“漂泊”经历的强化作用,以及生活的汉民族文化环境及南国风情的影响,在她的笔下转为或显或隐的哀愁、低回。例如:“像日里夜里的流水/ 是山上海上的月光/ 反复地来 反复地去// 让我柔弱的心/ 始终在盼望 始终/ 找不到栖身的地方”(席慕蓉《此刻之后》)“找不到栖身的地方”这样的感觉,以及在她的爱情诗篇里也经常写到的迷惘不定的情绪,应该是游牧民族漂泊不定生活的文化存留。“流浪”是席慕蓉诗文中出现频度很高的词之一,仅《七里香》《无怨的青春》等早期的6部诗文集中就出现35次。迁移不定的生活特性,经过长期积淀,就会形成一种缺乏确定性、稳定性甚至安全感的“流浪者”意识。
有一部分研究者不解席慕蓉事业、爱情、生活一帆风顺,何以她的诗篇总有淡淡的哀愁,甚至认为不过是为赋新诗强说愁。兹举一例,“现实生活中的席慕蓉是一个极其幸运的女子……我发现席慕蓉在玩弄人生的同时,呈现出一种装腔作势的忸怩之态。作为贵夫人的席慕蓉,时不时在自己的幸福与喜悦里,掺进一些淡淡的悲伤,以及自己的矫情与造作来骗取读者的信任与眼泪,以故作高深的忧伤与悲苦来装饰自己平淡无奇的日常生活。”[3]类似评价不少。这些基本上都忽视了席慕蓉身上的蒙古民族的特殊基因及其早年漂泊经历的强化作用。民族的基因根植于民族文化心理的深层,即使在一帆风顺的环境里也不会消解,它强烈地参与或影响席慕蓉风格的形成。由此形成的不确定、哀愁、低回,贯穿于席慕蓉的几乎所有作品。这些由于民族个性与文化心理等形成的特质,是席慕蓉诗歌具有鲜明民族特性的有力证据。
值得注意的在于,蒙古民族特质、家庭的文化传承,以及幼年、少年时期南方的辗转漂泊,长期在南方的生活环境,促进了南、北文化对席慕蓉的交替影响。影响到创作,席慕蓉诗歌不是“一丝不差”的蒙古文学风格,而是以蒙古文化心理为基因或者深层元素,同时融入她的“漂泊”体验、所生活的南方汉文化元素,形成极具魅力的当代风格:抒情细腻、形式精致而不柔弱或过分艳丽,深沉含蓄、低回宛转,又兼具质朴自然及源自北方草原的辽阔悠远。席慕蓉诗歌风格明显熔铸南北诗风之长,而避免了南北诗风的不足,如南方的太过柔弱艳丽、北方的相对简单粗糙。
在席慕蓉诗歌中占大多数,表面看来并没有直接采用蒙古民族题材的作品中,其实都可以发现这些民族的深层元素。这里就席慕蓉质朴自然的态度作一些分析。她的《无怨的青春》组诗前面有一段小序:“若不得不分离,也要好好地说声再见,也要在心里存着感谢,感谢他给了你一份记忆。”这基本上可以代表席慕蓉数量不少的爱情诗的基本风格。这种风格和汉民族许多爱情诗极为强烈的爱憎感情是有显著区别的,如汉乐府:“上邪,我欲与君相知,长命无绝衰。山无棱,江水为竭,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乃敢与君绝。”(《上邪》)“闻君有它心,拉杂摧烧之。摧烧之,当风扬其灰。从今以往,勿复相思。相思与君绝!”(《有所思》)再如明代民歌:“要分离除非是天做了地;要分离除非是东做了西;要分离除非是官做了吏。你要分时分不得我,我要离时离不得你。”(《挂枝儿·欢部·分离》)文人诗歌如元稹“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李商隐“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等,可为中国汉民族爱情诗基本思想的代表,具有极端的强烈性,甚至极端的单一、不可改变性。席慕蓉的爱情诗却明显具有新的元素,例如《一棵开花的树》:
如何让你遇见我/ 在我最美丽的时刻 为这/ 我已在佛前 求了五百年/ 求他让我们结一段尘缘
佛于是把我化作一棵树/ 长在你必经的路旁/ 阳光下慎重地开满了花/ 朵朵都是我前世的盼望
当你走近 请你细听/ 那颤抖的叶是我等待的热情/ 而当你终于无视地走过/ 在你身后落了一地的/ 朋友啊 那不是花瓣/ 是我凋零的心
“求了五百年”的爱因为“无视”而凋零,当然是锥心的痛,但是如果与汉民族类似诗篇比较,就可以发现诗中并没有极强烈或极端的反应,感情要“平静”或“温和”得多。如果结合张承志《黑骏马》描写蒙古族老奶奶、索米娅对待类似感情的态度,就可以进一步理解这些新元素形成的民族学因素。北方民族,尤其是“极北”地区的民族,环境相对恶劣,四季变化更为剧烈,生存、适应、延续在一个民族的文化中占有更重要的位置,起伏变化剧烈的环境大概也使北方民族的内心更为强韧,迁徙不定、随遇而安的生存方式造就了北方民族更强的适应性,唯一、不可改变等这些更多来自于安土重迁的农耕社会的带有极端性的思维本来就少于中原或南方民族。它们表现在文学创作中,形成北方民族文学或者带有北方民族深层质素的文学独特的风格。席慕蓉的《禅意(之二)》也具有代表性:“当一切都已过去/ 我知道 我会/ 慢慢地将你忘记// 心上的重担卸落/ 请你 请你原谅我/ 生命原是要// 不断地受伤和不断地复原/ ……生活原来可以/ 这样的安宁和美丽。”这种很强的“复原”能力,和蒙古民族很强烈的顺应自然等思想也有关。
还可以注意到,具有蒙古民族特色的事象或意象在席慕蓉诗歌中出现的频度不低,这也成为席慕蓉诗的显著特征之一。蒙古民族是一个马背上的民族,“马”“草原”“风沙”“大漠”“鹰”等,都是蒙古民族的典型事象,积淀了很深的蒙古文化心理。在席慕蓉笔下,“马”“草原”“风沙”出现的频率尤其高,大致统计席慕蓉《七里香》《无怨的青春》《时光九篇》《有一首歌》《河流之歌》《在那遥远的地方》等6部比较有代表性的诗集或诗文合集,“马”出现超过100次,“草原”出现近70次,“风沙”出现超过30次(“风”出现近200次,“沙”出现超过80次)。此外,“大漠”“阴山”“塞外”“鹰”“箭”等在席慕蓉诗歌中也多见,且具有北方塞外特征的意象在一些诗篇中“集群性”出现,构成具有地域特征的意境。即使席慕蓉描写都市现代生活的诗篇,也出人意料地运用具有塞外特征的意象:
路是河流/ 速度是喧哗/ 我的车是一支孤独的箭/ 射向猎猎的风沙 (《高速公路的下午》)
“箭”“风沙”具有典型的北方游牧民族的特征。席慕蓉驾车行进在中国南方雨水充沛、植被良好的台湾的高速路上,应不至于黄沙漫天,“孤独的箭”“猎猎的风沙”其实都是蒙古民族文化基因的存留,它们鲜活的存在于席慕蓉内心,自然而然地,或者潜意识地,进入了创作的视域。这里要指出,除了作为蒙古族诗人的席慕蓉,还没有,恐怕也不大可能看见其他民族诗人的诗歌创作采用这样新鲜的意象组合。席慕蓉的爱情诗也具有新鲜的表达风格,意象组合同样很有特色:
只为 不能长在落雪的地方/ 终我一生 无法说出那个盼望/ 我是一棵被移植的针叶木/ 亲爱的 你是那极北的/ 冬日的故土 (《四季》)
“针叶木”是中国北方或高寒地区生长的植物,“针叶”是为了减少水分和能量的损失,南方由于阳光充足、气候湿润则多为阔叶木。以“被移植的针叶木”来喻示席慕蓉北方蒙古民族血缘而生活于南方的经历,并以“极北的冬日的故土”这样的意象组合来表达分离、思念、回归的渴望,不但具有浓郁的北国特征,也十分切合席慕蓉的感情历程。同样,除了作为蒙古族诗人的席慕蓉,还没有看见其他民族诗人的诗歌创作采用这样新鲜的意象组合表达类似主题。汉民族诗歌表现分离、不舍等主题最常用的意象是“杨柳”,在席慕蓉诗篇中不但出现数量相对较少,而且通常并不用于表现典型的“分离”主题。我们再以当代两位著名汉族女诗人舒婷、傅天琳描写分离等主题的手法来作一个比较。舒婷描写分离多用“站台”“汽笛”“分岔的路”等,具有现代城市文明、工业文明的特征,“分岔的路”还具有传统汉诗的特点,如唐代王勃描写“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傅天琳描写分离则用“机场”“海港”“团圆饭”等,同样具有现代城市文明、工业文明的特征,“团圆饭”具有鲜明的汉民族色彩。通过比较,不但可以发现席慕蓉表达方式与南方汉族诗人的差异,而且可以确认其创新力度更大,形成显著的、也更具魅力的“陌生化”效果。可以说,席慕蓉带有北方游牧民族色彩的事象与新鲜的意象组合,已经在某种意义上丰富了中国文学的表现方式,同时也使中国文学呈现出某些崭新的当代风格。
值得注意的还有席慕蓉诗歌的艺术形式。她的300余篇诗歌中极少无韵诗,例如:
荷叶在风里翻飞/ 像母亲今天的衣裳/ 荷花温柔地送来/ 她衣褶里的暗香
而我的母亲仍然不快乐/ 只有我知道是什么缘故/ 唉/ 美丽的母亲啊/ 你总不能因为它不叫做玄武你就不爱这湖(《植物园》)
统计席慕蓉3部早期诗集《七里香》《无怨的青春》《时光九篇》,按比较严格的标准来衡量,完全的无韵诗不到10篇,约占这3部诗集173篇诗的4%,96%为有韵诗,除少部分外(约5%),大多(超过90%)用韵密集,语言的乐音效果显著。这在“废韵”思潮盛行的当代诗人中并不多见,也值得反思。为何席慕蓉在众声喧哗中有一份固执的坚守?笔者认为受草原游牧文化与传统诗学“中和”理论的双重影响可能是值得注意的因素。草原游牧文化有一个重要思想是强调与自然力量和谐相处。席慕蓉说,“游牧文化的萨满教的中心思想是和谐”。[4]“和谐”的核心是相通、相容,协调关系、互相适应使之达到最佳状态,包括人与自然、人与人,以及各种构成要素之间的协调、和谐;同时要避免过度、偏激、怪异,这往往会破坏各要素之间的稳定协调关系。游牧文化的和谐思想与传统哲学“天人合一”及传统诗学的“中和”思想在方向上具有一致性。中国传统诗学的“中和”思想支持了包括唐诗宋词在内的中国古典诗歌的繁荣,但由于近现代以来对传统文化的批判性反思,以及当代某些思潮的影响,受到明显削弱。席慕蓉承袭的草原游牧文化的和谐思想由于与传统诗学“中和”理论的一致性则得到某种“强化”,因而不易改变或随波逐流。席慕蓉诗歌表达感情注重适度,不追求偏激、怪异或者歇斯底里的发泄,不管是意象的选用,还是意境的营造,抑或感情的表达,都以追求“和谐”为目的。形式上则趋于精致,重视音韵调配,这同样也是以追求更“和谐”为目的。
三、席慕蓉现象的思考
《七里香》是席慕蓉第1部诗集,1981年7月出版后在台湾引起极大轰动,1个月之内再版,半年之内再版7次,“席慕蓉这个名字在台湾出版商眼中迅速成为利润的代名词”[5],随后《无怨的青春》等多部诗集陆续出版。大陆诗人沙鸥描述了席慕蓉诗集在中国大陆传播的基本情况:“以花城出版社出版的两集为例,《七里香》从1987年2月到1989年11月,仅两年零九个月,印刷14次,累计印数达51万余册;《无怨的青春》从1987年9月到1989年11月,仅两年零两个月,印刷15次,印数50万余册。另有些出版社还出版了席慕蓉诗集多种。”[6]到2004年,席慕蓉诗集销量“最保守的估计是500万册”[7]。席慕蓉诗歌在中国内地和台湾地区同时获得巨大影响且历久不衰,已经具有超过30年的持续不断的影响力,绝非如一些评论者所说的“流行”而已。这是因为一般意义的“流行”有一个典型或本质的特征是时间很短,通常不会超过几年,长期影响则必须具有内在品质的支撑。超过30年的影响,而且极可能还将继续拥有数量不少的读者,意味着席慕蓉诗有可能进入另一个意义层面。如果从500万册巨大销量来判断,席慕蓉不但是当代辐射最广、影响最大的蒙古族诗人,从某种意义上也是当代全球有影响力的诗人之一。从印度到欧美,我们目前都没有发现诗集总发行量超过席慕蓉诗集的。
进入当代,诗歌艺术的黄金时代似乎已经远去。甚至有人认为诗歌是农耕时代的艺术,进入工业化时代、后工业化时代、信息化时代之后,小说、影视艺术等取代诗歌成为主要的大众艺术是必然趋势,诗歌必将成为点缀性的“花边文学”。不过,笔者以为,这种对诗歌的看法不止悲观,而且是单一的线性思维。每一种重要艺术都有其特殊的表现能力,这些表现力与魅力会因为时代变迁发生一些变化,却不会因为某种“时代”到来而消亡。小说、影视等叙事艺术并不能完全满足读者丰富、多向的审美兴趣和要求。诗歌具有更集中、更有力也更精巧的抒情特性,与小说、影视等叙事艺术并不“同质”,所以不具备互相取代的逻辑理由,因为“取代”的前提是“同质”和多余,即如果诗也属“叙事”艺术,则它可能被更大型的小说、影视等取代。实际的情形是,小说、影视往往需要插入“诗”或“歌”来塑造人物、推动情节发展,在影视艺术中,主题曲、插曲几乎是必不可少的,这可证明抒情艺术与叙事艺术是一种互补关系而非互相排斥、互相替代的关系。中国新诗的一支,即流行歌曲的歌词——《诗三百》中的相当一部分就是这类“诗”,其艺术水平尤其是接受、传播的广泛性显示的生命力很值得关注。从“歌”的高度接受,可以注意到“诗”的厚实基础及其未来。这是正诗歌必将与人类共存,并将在某些时期或周期性地出人意料地繁荣的原因。当一个民族情绪高昂或处于某些关键时期,抒情文学往往率先受到关注。在社会发展的相对平稳期,繁荣的社会环境及传播媒介的有效支持,则为大型叙事艺术提供了发展空间。诗歌艺术在人类早期率先发展,和当时社会组织、传媒相对不发达,小说、戏曲、影视等艺术对传媒、都市化水平等依赖度较高有关,诗歌艺术以其相对轻巧灵活,创作与传播“成本”相对“低廉”率先适应人类早期及“农耕时代”,而非只能适应于早期与“农耕时代”。当代宏观环境固然十分有利于小说、影视艺术的发展,其实也为诗歌艺术带来了新的机遇。席慕蓉诗歌发行500万册以上何尝没有强大的现代出版、流通及各种媒介的巨大效应。席慕蓉诗发行500万册提供的不止是接受者不需要诗歌艺术、诗歌艺术必将衰落的重要反证,也提醒现代诗人,回归艺术本原、提升诗艺、抓住机遇才是更重要的问题。
[参考文献]
[1]涵柔,汤斌.席慕蓉本色[J].中国女性(Women of China中文海外版,2003(7):60-64.
[2]刘海北.家有“名妻”席慕蓉[J].视野,2006(9):52-53.
[3]孙生民.重读席慕蓉[J].文学自由谈,1990(4):158-160.
[4]宋燕.席慕蓉:原乡路上的行吟[N].燕赵都市报,2009-5-31.
[5]张业松.拆碎七宝楼台——席慕蓉诗境界说[J].当代作家评论,1992(4):115-123.
[6]沙鸥.有感于“席慕蓉现象”[J].当代文坛,1990(5):40-41.
[7]李冰.席慕蓉:诗集销了500万册[R].北京娱乐信报,2004-6-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