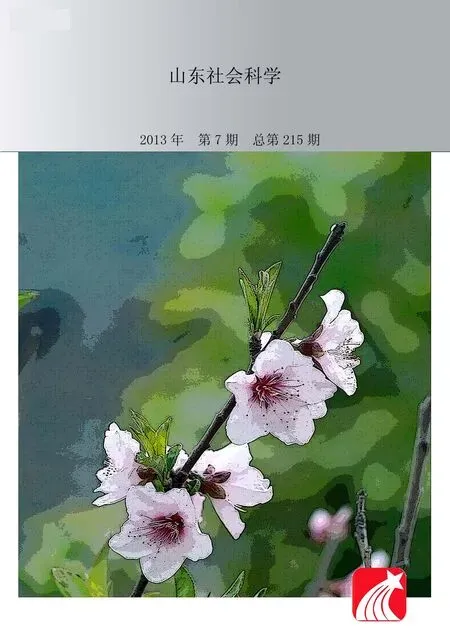从“私民”到“公民”:网络空间主体的公共性转向
常晋芳
(中国人民大学 哲学院,北京 100872)
1994年4月,中国实现了与互联网的全功能连接,进入网络时代。经过十多年的高速发展,中国网络空间具有越来越强的公共性意义,成为当代中国公共空间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极大地推动着中国的民主政治进程,对于公民的有序政治参与、公共权力的监督、公共事业的发展、公共精神的培育、促进社会和谐、实现社会公正都具有积极意义。从“私民”到“公民”,从“小众”到“大众”,从私人性到公共性,是网络空间主体——网民发展的最重要走向。在论证这一观点前,先来辨析几个核心概念。
一、主要概念辨析
(一)公共空间与网络空间
公共空间又称公共领域(public sphere),是一些西方学者首先提出的。汉娜·阿伦特认为,“公共领域是为个性而保留的,它是人们能够显示出真我风采以及具有不可替代性的唯一一块地方。正是为了这个机会,并且出于对国家(它使每个人都可能有这种机会)的热爱,使得每个人都或多或少地愿意分担司法、防务以及公共事务管理的责任。”注[德]汉娜·阿伦特:《人的条件》,竺乾威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82页。哈贝马斯认为,公共领域是“政治权力之外,作为民主政治基本条件的公民自由讨论公共事务,参与政治的活动空间。”注[德]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曹卫东等译,学林出版社1990年版,第35页。这些学者主要从社会政治角度定义“公共领域”或“公共空间”。笔者认为,公共空间是在由公共权力构成的国家政治空间、由生产关系构成的经济空间与由家庭和私人关系构成的私人空间之外的社会空间。公共空间的主体是公民,核心内容是公民对公共事务的参与、表达、监督和运作,以及在其中形成的公共秩序、公共精神和公共价值。
“网络空间(cyberspace)”最早见于1984年威廉·吉布森的科幻小说《新浪漫者》,作者描写了一个由计算机所构筑的虚拟世界。迈克尔·海姆认为“网络空间表示一种再现的或人工的世界,一个由我们的系统所产生的信息和我们反馈到系统中的信息所构成的世界。”注[美]迈克尔·海姆:《从界面到网络空间:虚拟实在的形而上学》,金吾伦、刘钢译,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79页。笔者认为,网络空间是指以信息网络为技术平台,存在物理空间之上的虚拟空间。网络空间在传统哲学的物质——精神二分法的基础上,创造了“第三空间”,类似于波普尔所说的“世界3”。网络空间是最具当代意义的公共空间,具有虚拟性、全球性、中介性和公共性的特性。
(二)公共性
公共性是网络空间的核心特性之一。不同学者从不同角度对其做不同解释:或定义为个体的公共性权利和共同体的公共权力;[注]刘圣中:《从私人性到公共性》,《东方论坛》2003年第1期。或定义为公共组织、公共权力、公共事务、公共物品、公共服务、公共利益等事物所具有的公有性(非私有性)、共享性(非排他性)和共同性(非差异性);[注]王保树、邱本:《经济法与社会公共性论纲》,《西北政法学院学报》2000年第3期。或提出公共性的几个层次:是一个社会范畴,它根植于人的社会本性;是一个历史范畴,它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中获得其实质内容和表现形式;是一个政治范畴,主要表现为公共权力的内容及其合法性的主要来源;是一个文化范畴,文化体系决定着公共性的内容和形式。[注]郭湛主编:《社会公共性研究》,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71-76页。笔者认为,公共性概念在哲学上源于个性与共性的关系,现实层面源于个人与群体(私与公)的关系,指主体与主体间、主体与客体间存在的共有性、共享性和共同性。
(三)“私民”与“公民”
所谓“私民”,是指以个人取向为主导的民众,其言论和行为以关注和满足个人或小群体的利益、情感、意志为主要目的。所谓“小众”与之基本同义。
法律意义上的公民,是指具有一国国籍的人。政治和社会意义上的公民是指积极参与公共事务、监督公共权力、享有公共权利、承担公共义务的独立个人。所谓“大众”在此意义上与公民基本同义。
所谓网络公民,就是现实社会中的公民在网络中的存在和延伸。
二、网民从“私民”到“公民”转变的具体表现
(一)网民身份的大众化、全民化
中国网络发展的早期,网民是社会公众中数量很少、身份很特殊、代表性很低的群体。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1997年10月发布的第1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我国上网用户数62万。性别结构:男性87.7%,女性12.3%;年龄结构:21-35岁占78.5%;地区结构:北京、上海、广东三地占52.3%;职业结构:计算机业、教育、科研共占52.3%;文化结构:大本占49.6%(第二次的数据,第一次无此项目)。[注]数据来源:http://www.cnnic.com.cn,下文中有关CNNIC的调查数据均来自该网站。可见,早期中国网民具有明显的群体特征:以男性、21-35岁、大专以上学历、来自经济文化发达地区为主。
随着互联网的迅速发展,中国网民的群体特征逐渐弱化,在性别、年龄、学历、职业、地区等方面越来越趋向于普通民众结构。中国网民已经逐步进入大众化、全民化阶段,在全体公民中的代表性越来越高。据最近一次CNNIC的调查,截至2012年6月底,中国网民数为5.38亿,普及率达39.9%,超过世界平均水平。2012年3月,国家发改委等七部门研究制定了《关于下一代互联网“十二五”发展建设的意见》,提出“十二五”期间,我国互联网普及率达到45%以上,一个全民上网的时代正在来临。
(二)网民对公共事务的参与和对公共权力的监督——网络舆论
网民与其他社会群体相比,具有更强的正义感、社会责任感和平民意识。网民不断超越个人和小群体利益,越来越多地参与公共事务、表达公共诉求。网民从私人性向公共性转变是一个不断量变导致质变的过程。在完成这一转变后,我们可以说,网民就是网络公民的简称。
1998年印尼排华事件、1999年北约轰炸中国驻南联盟使馆事件、2001年中美南海撞机事件都引发了早期网民参与公共事务的高潮。而初步完成这一转变的标志是2003年的两大网络事件。一是孙志刚事件。2003年3月,湖北青年孙志刚在广州因无暂住证被收容,在收容所被殴打致死。此事引发传统媒体和网络媒体的怒潮,6月20日,国务院新颁布的《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取消强制收容,改为自愿救助。孙志刚事件是网络舆论和网民自下而上地影响社会政治进程的开始。二是国家领导人开始关注网络舆论。2003年4月,时任国家主席胡锦涛在广州对一位参与防治SARS的医生说,“你的建议非常好,我在网上已经看到了。”国家最高领导层自上而下地关注网络舆论,与网络舆论自下而上的力量相结合,标志着国家权力、网络舆论和普通网民之间的沟通渠道开始建立。2007年后,中央政治局多次开会讨论网络文化建设和网络管理问题,网络公共空间的建设和管理已经成为社会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
(三)网民参与公共事务的主要方式
网络新闻评论。在多数网络新闻网站的新闻下面,网民可以跟贴评论,尽管其中也存在一些“水军”恶意评论以及一些违反法律法规道德的言论,但总体而言,可以看到最真实最原生态的网络民意。
网络论坛和社区。时政类、社会类、思想类论坛是网民发表公共言论、参与公共事务的主要方式之一。尽管近年来政府对其监管越来越严格,但其自由度和开放度仍是传统媒体无法比拟的。
博客(blog),意为网络日志,是个人记录和表达自己感情和思想的私人空间。现在,越来越多的博客从自娱自乐转向关注公共问题,从私人空间演变成公共空间。
微博,即微博客(Micro Blog)的简称,学者陈永东把微博定义为“一种基于关注机制分享简短内容的广播式的社交网络平台”,并认为其具有“简短式记载、平等式交流、裂变式传播、碎片式呈现、即时式搜索及开放式群聊”等特点。[注]陈永东:《微博开放平台再开放些》,《网络导报》2011年4月21日。博客和微博降低了发表言论的门槛,打破了思想文化的垄断,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每个人都可以是一个没有执照的电视台”,[注][美]尼葛洛庞帝:《数字化生存》,胡泳、范海燕译,海南出版社1997年版,第205页。每个人都可以成为微薄而强大的自媒体。中国的微博发展时间短但速度很快。2009年8月份中国最大的门户网站新浪网推出“新浪微博”,成为中文门户网站中的第一家。截至2012年6月底,中国微博用户数达到2.74亿,网民使用率为50.9%。
总之,“中国的网站十分注重为网民提供发表言论的服务,约80%的网站提供电子公告服务。中国现有上百万个论坛,2.2亿个博客用户,据抽样统计,每天人们通过论坛、新闻评论、博客等渠道发表的言论达300多万条,超过66%的中国网民经常在网上发表言论,就各种话题进行讨论,充分表达思想观点和利益诉求。”[注]《中国互联网状况》白皮书,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0-06/08/c_12195221.htm。
(四)网络公民的主体分化
网民并不是铁板一块,而是多元主体的集合,根据不同标准可以分为很多派别。如根据政治立场可分为左(极左和中左)、中、右(中右和极右)派,根据思想和价值观可分为马克思主义、自由主义、保守主义、民族主义、传统本位主义、全盘西化论等,还有“五毛党”、“美分党”、“七字党”、“自干五”、“辟谣党”、“网络特务”等独特群体。可以说,现实社会中存在的各种政治和价值观派别都能在网络空间中找到,而且更加聚集、更加鲜明、更加激烈。网民的多元化是否与网民的公共性有矛盾?是否会损害网络公共秩序和公共利益?凯斯·桑斯坦对此有所质疑,他批评网络空间易出现“群体极化”现象,“网络对于许多人而言,正是极端主义的温床,因为志同道合的人可以在网上轻易且频繁地沟通,但听不到不同的看法。”[注][美]凯斯·桑斯坦:《网络共和国》,黄维明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51页。
笔者认为,网民的多元化与公共性并不矛盾。网民正是建立在个体自由和多元差异基础上的公民群体。真正的网络空间并不是同质的网民发出同样的声音,而是异质的网民发出不同的声音。网络空间中的价值分化和极端化会不会消解网络空间公共性,关键在于每个人和利益群体是否都有平等、自由、充分的表达和交流机会。
三、网民从“私民”到“公民”转变的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1994—2002年):自发的私人化阶段。这一时期,网民属于“另类”、“边缘”和“小众”,不但数量少、代表性低,行为模式和价值观比较“另类”。据CNNIC的统计,早期网民上网的主要目的是获取信息、交友、休闲娱乐,较少关注公共事务、参与公共讨论。即使有部分网民对公共事务有强烈的关注和参与,其影响和效果也很有限。这一时期,社会公众对于网民和网络的态度呈现两极分化。有人对于网络推动社会变革的积极进步意义评价过高,而对社会变革的复杂性认识不足;有人对于网络的公共性意义评价过低,或漠视而放任自流,或仇视而一味封堵,或对网络前景悲观。
第二阶段(2003—2006年):公私混杂的阶段。随着互联网的迅猛发展和对社会空间的持续渗透,网民和网络舆论的力量日益强大,社会影响日益显著,网络公共事件频繁出现。其中既有抨击社会不公、揭露官员腐败、维护弱势利益等正面现象,如2003年孙志刚案、刘涌案、2006年华南新城业主被打案;也有恶意炒作、“网络暴民”、“哄客”等负面现象,如“木子美”;还有出于正义目的而对个人隐私的侵犯,如“铜须门”事件、“虐猫女”事件等。这种混杂的现象最典型地体现在“人肉搜索”[注]“人肉搜索”,指网民通过网络与非网络方式对特定对象进行的信息搜索。笔者不赞同“人肉搜索”一词,因为按其本义可称为“网民搜索”或“人工搜索”,叫“人肉”既不恰当也有歧义。中。人肉搜索既可以用来进行网络舆论监督,也可以用来宣泄私愤、侵犯他人隐私。
第三阶段(2007—2010年):初步的公民化阶段。这一时期,网民和网络舆论的主流进入初步的公民化阶段,即参与公共事务,监督公共权力,还原事件真相,维护大众利益。
2007年,网络空间“出现了多元的意见领袖和理性的意见表达。在网民的意见交流中,理性的声音成为主导力量,网民们表达意见的方式也更加理性化。同时,传统媒体与网络媒体的舆论互动又为网络舆论的公正性和理性提供了保障。”[注]李卓钧、朱智红:《从2007年网络公共事件看网络舆论的新变化》,《东南传播》2008年第7期。陕西农民周正龙拍了张华南虎照引发了网民的广泛质疑,“打虎派”网民运用科学理性方法揭开了事件的真相;厦门市民用“散步”方式反对破坏生态环境的PX项目,最终取得胜利;传统媒体与网络舆论相结合,共同声讨山西“黑砖窑”中的奴工现象;在聂树斌案彭宇案许霆案背后,面对司法的不公,每一个公民都要摸一摸自己发凉的脊背。
2008年是中国与世界大事频发的一年。在南方雪灾、5·12汶川大地震等天灾的悲情中,在三鹿毒奶粉、襄汾溃坝、瓮安“俯卧撑”等人祸的反思中,在对分裂势力和反华闹剧的愤怒中,在北京奥运会的喜悦中,网民表现出前所未有的激情、正义、团结、理性、爱心,网民的公共意识和公共素质大幅提升。2008年,中国网络公民完成了成人礼。
2009年以来的网络空间更加精彩纷呈,尽管不乏“你妈妈喊你回家吃饭”的无聊和“凤姐”、“犀利哥”的炒作,但其主旋律无疑是网络监督和网络民主,如在南京周久耕“天价烟”事件、“李刚门”事件、云南“躲猫猫”事件、“跨省追捕”事件、湖北邓玉娇事件、“转基因主粮”争论、富士康“13连跳”等网络公共事件中,网民求真相、督权力、维权利、守良知,促进着教育医疗住房、暴力拆迁、劳资矛盾、官员腐败、司法不公、食品安全等社会问题的讨论和解决。网络监督的力度、广度和效果都持续提高,有人戏称网络是“网络纪委”,网民是“一亿个包公”,在“网络纪委”和“一亿个包公”的全方位、全天候监督下,一切腐败人物和行为都无所遁形。
2008年后,网民和网络舆论已经从“沉默的大多数”的边缘变成社会舆论的主流。从正面看,“在网络监督中,网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得到很大程度的实现,主体意识日益崛起,主体地位日渐形成。在主动参与到社会事务的过程中,网民通过网络观念的激荡,借助网络中理性知识分子的示范,掌握了民主政治的相关常识,迅速成长为了‘网络公民’。”[注]叶雷、温睿:《从网络暴民、网络哄客到网络公民——2009网络公共事件透视》,《社会观察》2009年第12期。从负面看,当前中国的社会矛盾日益激化,两极分化到了危险边缘,网络起到了“减压器”、“缓冲剂”和“安全阀”的作用,如果没有网络的作用,这些社会矛盾会导致更严重的后果。
国务院新闻办2010年6月8日发布的《中国互联网状况》白皮书正式确认了互联网的舆论监督作用:“中国政府积极创造条件让人民监督政府,十分重视互联网的监督作用,对人们通过互联网反映的问题,要求各级政府及时调查解决,并向公众反馈处理结果。”[注]《中国互联网状况》白皮书,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0-06/08/c_12195221.htm。
第四阶段(2011年至今):真正的公民化阶段。这一时期网络公共空间的最突出表现就是微博的异军突起。微博由于其主体的平民性、内容简洁、传播速度快、范围广、裂变式传播等特点,迅速成为普通网民传播公共信息、表达公共诉求、参与公共事务、监督公共权力的最佳平台。
2011年,郭美美事件、7·23动车事故、药家鑫案、校车事故等社会公共事件都借助微博等网络媒体得以传播、争论和解决。活跃的微博用户具有强烈的公民意识,这部分具有公民意识的民众一方面满足了公民社会的条件之一,另一方面又有助于社会制度环境的完善,推进了公共领域的构建。[注]刘环环:《“微民主”或“伪民主”:微博的外部图景与内部控制》,2012年安徽大学硕士论文。
2012年,以微博为代表的网络空间对社会公共事务的介入和影响达到白热化程度,呈现出范围广、程度深、争论分化严重、正负效应俱强等特点,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影响到国家政治、社会和文化,官方、管理者、经营者、各种权力或资本利益集团、普通网民在网络空间中的利益和价值观冲突日益激烈。
年初的方韩大战引发网民的混战,各方对作家和媒体的操守、价值观、法律和道德底线展开深入而激烈的讨论,在推倒一个人造“青年意见领袖”后,更值得反思的是当代中国文化中真实和诚信的稀缺;对党的十八大新领导集体的高度期待反映了网民对中国未来前途的高度关注和责任感、使命感;陆续爆出的各种“表哥”、“表叔”、“房叔”等腐败的人和事,既表明网络的强大反腐监督能力,也反映了正规渠道反腐倡廉的不给力;对奥运金牌、中国人首获诺贝尔奖的相对淡定反映了中国网民越来越成熟的大国观;“中国好声音”、“江南style”和电影“泰囧”的火热表明草根网民与所谓“精英”在文化价值观上的对立;“航母style”的火热表达了普通网民对航母、舰载机、航天、深潜、北斗等中国在国防和高科技领域取得的新成就的欣喜和自豪;“中国梦”的流行更是从上到下的中国人都可以有的“最大公约数”,尽管梦的内容迥然不同。
四、网络公民和网络空间的问题与矛盾
在看到网络公民和网络空间的正面价值和积极成效的同时,也应当承认,网络公民中存在许多成长中的问题,主要表现在:
第一,网民的公民意识和公民素质有待进一步提高。网民中还存在低俗化、极端化、泛意识形态化、泛娱乐化倾向。泛意识形态化指部分网民的言行,不讲真理,不讲道德和法律,不讲是非对错善恶美丑,唯意识形态是从,唯立场是从,“只站队,不站对”,把一些严谨认真的讨论引向意识形态化的斗争;泛娱乐化是指丧失了公民精神和社会责任感,把一切事物庸俗化、娱乐化,结果浪费自由空间,消解公民责任,矮化社会价值,其后果就是尼尔·波兹曼所说的“娱乐至死”。
第二,网民的言论自由与社会规范之间的矛盾日趋复杂和尖锐,网络舆论的监管和规范有待进一步完善。如何更好地处理自由与规范、个人表达与公共利益、舆论监督和保护隐私、批评监督和造谣污蔑、“疏”与“堵”的关系,如何更好地处理普通网民、网络监管者、经营者、各利益群体在权、责、利上的矛盾,营造和谐共生的网络空间,将是未来网络发展乃至整个社会发展的关键环节之一。近期,国家在这方面推出一些重要法规,如《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加强网络信息保护的决定》,但这些法规政策能否得到合法合理公正严格的执行,还有待实践的检验。
第三,网络舆论监督的深度、广度有限,没有常态化机制,更多地局限于对个别事件的监督,还缺乏对更根本性、普遍性问题的反思和监督。网络反腐“刑不上大夫”,也很难避免被某些利益集团利用来“定向性”打击对手,成为利益集团斗争的工具。
第四,政府对网民和网络舆论的态度有待进一步端正,政府进行网络监管和处理网络公共事件的能力有待进一步提升。有些政府部门和官员对网民和网络舆论不够宽容和开放,或漠视,或压制,或封杀,损害了政府的公信力和网民参与公共事务的积极性,具体方法上,该软的不软——对不同意见滥用监管手段,该硬的不硬——对触犯道德和法律底线的言行立场不清、态度不明、执法不严。
第五,各种社会利益集团,特别是资本和特权利益集团对网络空间的渗透、影响和控制日益加深,严重影响公共利益和公共价值的实现。甚至有些特殊利益集团滥用有限的言论自由空间,利用一些社会不公现象和群体性事件,配合国外反华势力,造谣惹众,煽风点火,宣扬歪理邪说,动摇国本、政本。
五、结语
尽管还存在着诸多问题,我们坚信,网络空间和网络公民拥有光明的未来。网络空间将成为公共空间的主流和常态,网络公民将成为公民的主体,网络政治将成为民主政治的常态化形式。“在中国这样的公共领域并不发达的国家,互联网可能成为普通公民抵制信息垄断和发出声音的唯一出口;在大多数时候,这并不会导致突破性的变化,但是,它显示了公民通过共有媒体影响政治的一些重要方式。共有媒体也许不能一夜之间改变那些根深蒂固的非民主行为,但是却能够令公众在政治过程中的作用发生变化,把政治话语带进公民的日常生活体验,改变人们对控制、自由与创造的认识,以便他们能够自由地动员集体智能提高治理水平。”[注]胡泳:《众声喧哗:网络时代的个人表达与公共讨论》,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334页。网络空间和网络公民的进一步成长和发展,将为中国的国家富强、民族复兴、社会和谐、文化繁荣和人民幸福做出更大的不可替代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