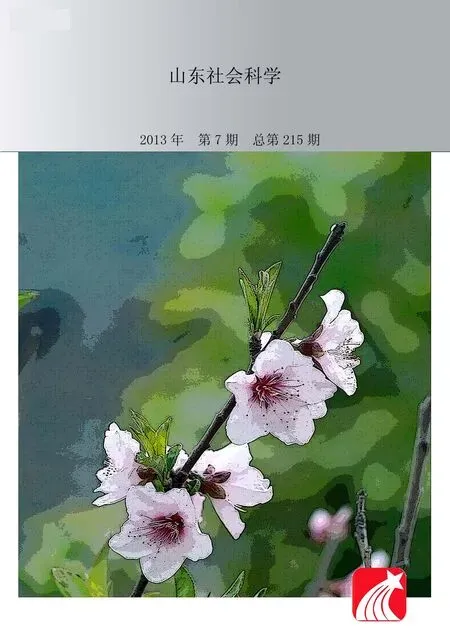从纯洁的情到世俗的爱
——现代通俗小说的言情主题
司新丽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文化与传播学院,北京 100070)
现代通俗小说所塑造的充满悲剧色彩的世俗之爱的言情主题,是从民初哀情小说叙述的满载幻想色彩的纯洁之情开始的。
一、情爱的空中楼阁
从1912年前后到五四文学革命发生,出现了以徐枕亚和苏曼殊的小说为代表的哀情小说,这些小说以哀伤的情感、纯洁的恋情为主,这些小说之所以受到读者深切的喜爱,与当时的社会背景密不可分。辛亥革命后,传统的婚姻制度已经动摇,“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做法已经不合时宜,“门当户对”也逐渐失去它的效力。代之而起的是新的才子佳人追求婚姻自由,追求的愿望是美好的,但传统礼教壁垒森严,有着美好愿望的青年男女无法逃离最终的灾难,美好真挚的情感无法如愿以偿。徐枕亚的《玉梨魂》就是当时哀情小说的代表作。
《玉梨魂》写的是英俊的小学教师何梦霞,寄住在崔家并做寡妇白梨影儿子的家庭教师,与白梨影发生了一场令人肝肠寸断的精神恋爱,最终则以白梨影、何梦霞和白梨影的小姑子崔筠倩的死亡悲剧作为结局。徐枕亚们所构建的情爱到底是一种怎样的情感?是现实中感天动地的真正爱情还是建立在空中楼阁中的情爱?对于民初的哀情小说,孔庆东认为:“他们已经把爱情上升到人生意义的最高点。在他们的心目中,纯洁、坚贞的爱情,价值高于一切,可以为之牺牲生命和一切现世的幸福。”①孔庆东:《1921 谁主沉浮》,山东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87页。这种观点极大地拔高了民初言情小说的价值。事实上,他们对爱情的追逐只是停留在虚空的充满了想象色彩的精神层面,一旦碰到现实却显得那样苍白无力,哪怕是逾越封建礼教一步,他们都无能为力。这一时期小说突出了一种哀情,极其浓郁的哀情淡化了政治、社会等因素,政治和社会因素只能退到后台成为小说的一种背景,而情愫急剧增加。民初的哀情小说确实如同佘小杰所写:“一个最突出的特点,就是把一个‘情’字,渲染到了极点。而且到处是‘情天恨海’……”②佘小杰:《中国现代社会言情小说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7页。在中国文学史上民初的哀情小说对于男女情感的渲染和表现超越其他任何历史时期的言情小说,但无论如何渲染这种缠绵悱恻的爱情,终究对传统的封建礼教无法逾越。《玉梨魂》中的白梨影虽然敢于涉足情海,渴望突破传统的封建礼教,但始终是战战兢兢、发乎情、止于礼,宁死也没有勇气争取。陈平原对此有过精当的分析:“民初新小说家特别强调‘言情之正’。所谓‘言情之正’,说到底一句话,就是‘发乎情止乎礼义’。”①陈平原:《陈平原小说史论集》中册,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820页。五四时期新文学作家批评鸳鸯蝴蝶派是“诲淫”,这是一种不正确的理解。其实民初的言情小说不是淫荡,而是过于圣洁。这些言情小说不但没有任何性欲的描述,甚至连不太正经的挑逗都没有,只是一种柏拉图式的精神恋爱。正是这样朦朦胧胧的对爱情的追求,这种心动而又完全没有超越礼数的男女之情,这种内心非常渴念但又没有肉体接触的男女情爱,最符合那个时代读者的审美心理和阅读期待。《玉梨魂》中的白梨影意识不到爱情是人的合理追求,才把自己作为“未亡人”的恋爱看成是命中注定。尽管她渴望得到爱,但又恐惧接受它,对爱情的痴情和对封建礼教的虔诚构成了她内心极大的矛盾,在临死之前还认为这段情史是一个污点。内心的渴望和躲闪强烈地冲击着她,她也从来没有真正踏实地拥有和享受过真切的爱情。小说传达给读者的感觉虽然是一种令人感动得掉泪的真诚的爱情,但小说中的主人公所感受的则是一种爱的痛苦。刘扬体认为:“以自戕方式履践爱情誓言,视爱情价值高于一切的行为,在人格力量与情感愿望上都具有了向现代爱情迈进的前趋性。”②王晓初:《中国现代文学的多重视野》,新星出版社2006年版,第31页。这种为情爱而殉情的方式,相对于现实而言是软弱的,但毕竟用生命为代价向传统的伦理观念和封建礼教发出了有限的挑战。这种悲剧发生的原因在于人物内心的矛盾冲突,这种冲突表现为他们对封建礼教的信奉和对不被礼教所容忍的爱情的执着之间的巨大冲突。爱情本来是一种很美好的、激励人、让人沉浸和享受愉悦的感情,而导致悲剧出现的原因在于爱情遭遇了封建礼教的阻拦和扼杀。男女主人公的痛苦源于内心对爱的渴望和对封建礼教不敢越雷池一步的恪守心理之间的激烈冲突。最终结局是此种情爱的空中楼阁构成了一个眼泪的世界,吴双热在《余之妻》序中说:“如是于此知说部之感人最深,实足以启发固有之真性情者也。惟哀情之作鵖多,苟得而尽读之者,不将走入泪世界耶。”情爱的空中楼阁的悲剧中充斥着男女主人公因情感不能实现的无限哀伤,哀伤和忧愁几乎成了小说主人公的性格特征。
《玉梨魂》悲剧的制造者是深藏于人心中而又无法抗拒的传统封建礼教,吴双热的《孽冤镜》、李定夷的《閗玉怨》中悲剧的酿成都是因主人公内心无法超越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封建礼教。《孽冤镜》中的人物因炽热情爱的燃烧和封建礼教的阻挡相撞而疯狂地自我毁灭,足以让人扼腕流涕。世家子弟王可青在摆脱了第一次痛苦的包办婚姻后遇到才高貌美的薛环娘,两情相悦,欣然订婚,但却遭遇了父亲的阻拦并被迫与素娘成婚,环娘得知消息后撞墙而死,最后王可青也自缢于环娘的坟前。《閗玉怨》讲述了男女主人公刘绮斋与史霞卿一见钟情,私定婚约,但遭到家长阻挠,史霞卿在被逼嫁给一个纨绔子弟时选择了以死抗争。后来双方父母答应了他们的婚事,传来的却是刘绮斋轮船失事的消息,史霞卿以死殉情,刘绮斋被人救活后回到了家中也绝尘而去。同样的悲剧还发生在苏曼殊的《断鸿零雁记》、周瘦鹃的《恨不相逢未嫁时》等小说中,这些小说写的都是情感的悲欢离合,不管情意如何缠绵与深厚,最后都是非死即散,即使活下来也是惆怅满腹、饮恨终生。这类小说注重的是忧郁和绝望的感伤美,男女之间的情爱成为空中楼阁,这也就注定了情爱成为悲剧的宿命。文茜认为民初的哀情小说所写的两性情爱“逐渐远离物质的和社会的因素而内化到两性的精神世界”,并认为“男女主人公从此开始在两性情爱的世界里痛苦的纠缠”③文茜:《论清末民初言情小说的主题形态与观念转变》,《中国文学研究》2009年第2期。。
二、情爱的社会话语
汤哲声说:“人的感情是具有社会性的,小说表现的感情能够打动人,还需要厚实的社会生活的支撑”④汤哲声:《中国现代通俗小说流变史》,重庆出版社1999年版,第93页。。言情小说从《红楼梦》到清末民初,一直是“言情”有余、表现社会不足,言情小说的变种(狭邪小说)仅限于秦楼楚馆,民初的哀情小说则只注重言情的纯粹性,甚至于把男女情爱推至空中楼阁,只是一味遵从“发乎情,止乎礼义”。继晚清狭邪小说、民初哀情小说之后将社会和言情两个主题结合起来,超出当时政治或言情两大模式的是李涵秋的《广陵潮》,其成为社会言情小说的开山之作。《广陵潮》所描述的情爱不同于才子佳人相敬如宾的模式,也不同于鸳鸯蝴蝶般卿卿我我的缠绵,而是在对情爱的描述中始终坚持对社会的刻画和揭示。但社会小说和言情小说的紧密结合在小说《广陵潮》中体现得并不完美,佘小杰说:“《广陵潮》作为社会言情小说,并不仅仅是社会内容和言情因素的结合,更应该说是社会小说和言情小说两种小说类型的结合。”⑤佘小杰:《中国现代社会言情小说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5页。但“这两种小说的结合,在《广陵潮》中,尚未达到盐溶于水的程度,而是像油与水的结合,很多地方是互相游离的”①佘小杰:《中国现代社会言情小说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6页。。真正把社会和言情紧密联系起来,并获得了很高成就的是张恨水,特别是他1929年写作的《啼笑因缘》更具有代表性。
狭邪小说是言情小说的一种特殊现象,研究社会言情小说时需要讨论社会狭邪小说。民国之前狭邪小说言情的成分更浓郁一些,民国时期狭邪小说的代表作家有何海鸣、毕倚虹和周天籁等,代表作品有:何海鸣的《十丈京尘》、《倡门红泪》、《老琴师》,毕倚虹的《人间地狱》、《北里婴儿》,周天籁的《亭子间嫂嫂》。②范伯群:《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史》上册,江苏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60页。这些作品描写的青楼爱情与晚清所写的青楼爱情不一样,不再是风光旖旎的两情相悦,更多的是控诉情感的被扼杀,痛陈情感归宿的飘渺无依,写出了社会的黑暗,人道主义成为其非常重要的思想主题。通过言情表达出更广阔的社会话语,从而深化了言情的意义。比如何海鸣的《老琴师》写老琴师收了一个十二三岁的非常有天赋的女徒弟阿媛,阿媛有天然的美丽和真诚,老琴师非常喜欢她,把毕生的才艺都传授给了她,但是一年后老鸨却把出落得更美丽的她献给了一个出价最高的军阀,一夜之间,这个集艺术美和身体美于一体的女孩便失去了贞操和甜美的声音,最终老琴师因无法拯救这个女孩而扔掉胡琴下落不明。其中所写的嫖客和妓女之间的感情都是毁灭与被毁灭的关系,正如范伯群所说:“这是一篇描写真善美被毁灭的哀歌,是一篇金钱肆意残害艺术的血泪控诉,也是一曲老琴师用生命去抗争那些蔑视人的尊严的恶势力的颂歌。”③范伯群:《中国现代通俗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86页。再比如,毕倚虹1922年出版的短篇名作《北里婴儿》写雏妓蕙娟中了嫖客的圈套怀了孕,老鸨则因为蕙娟丧失初夜权损失了一大笔钱而狠狠折磨她,让她挺大肚子给客人唱曲,等她生下孩子后让人抱走孩子,后来又迫使她与孩子姐弟相称,最后孩子死去,蕙娟去看他时硬被叫去陪客人。这是一个深刻的悲剧,妓女和嫖客之间仅仅是情爱被欺骗和肉体被占有的关系,孩子的死从某种意义上宣告了一切的荒诞和虚无,老鸨的深层参与和残忍无情表达了作者对这个社会的控诉。蕙娟的痛苦无助、孩子的凄惨死亡、老鸨的贪婪狠毒以及嫖客的欺骗和肉欲把传统妓女和嫖客之间的情爱撕裂得粉碎,这就是男女情爱社会话语的真诚表达。嫖客和妓女之间情爱的社会话语更生动的体现是1938年周天籁的《亭子间嫂嫂》,不但表达了对黑暗社会的控诉,更表达了一种人道主义的精神。汤哲声说:“在‘风光’与‘善良’的对比中,小说写出了顾秀珍的本性在生活的压迫下的扭曲,把矛头指向了社会。”④汤哲声:《中国现代通俗小说流变史》,重庆出版社1999年版,第113页。现代狭邪小说中表达男女情爱的方式更加社会化,把这种特类男女情感与社会大环境相融,透过男女情爱的社会话语表达了更深刻的思想和对这样的情爱关系的一种深刻同情,传达了人道主义的精神,从而使男女情爱的社会话语具有了更强的现实性和穿透力。
真正表达男女情爱社会话语的作品当属张恨水的社会言情小说以及20 世纪40年代秦瘦鸥的《秋海棠》。汤哲声认为张恨水的《啼笑因缘》标志着社会言情小说的正式产生。⑤汤哲声:《中国现代通俗小说流变史》,重庆出版社1999年版,第116页。汤哲声说:“1930年张恨水的《啼笑因缘》出现在文坛,标志着言情小说和社会小说的合流和社会言情小说的正式产生。”社会言情小说的真正产生同样标志着男女情爱社会话语的正式诞生。男女情爱社会话语的表达使男女之间的情爱更具有现实性,已经彻底脱离空中楼阁般的存在方式,在其中道出了男女情爱存在的本质,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啼笑因缘》所描述的故事非常曲折,讲述的是主人公樊家树与三个女性之间的多层情爱关系。小说的男主人公樊家树是一个非常普通的从南方到北京来考试的青年人,他邂逅了唱大鼓书的女孩沈凤喜,由于樊家树听沈凤喜唱完大鼓书后给了一块大洋,沈凤喜便怀着感激之心与樊家树交往,但当军阀刘德柱用更多的金钱引诱沈凤喜时,她便对其投怀送抱,但樊家树依然爱着凤喜。侠客秀姑一直在帮助并暗恋着樊家树,但因误会并未走到一起。而另一长相酷似沈凤喜的富家小姐何丽娜也一直喜欢樊家树,但家树因为她的奢华而拒绝了,后来凤喜受刘德柱的折磨而致疯,何丽娜放弃奢华的生活到西山学佛,最后在秀姑的促成下樊家树和何丽娜走到了一起。言情的社会话语一方面道出了男女情爱的悲剧,另一方面蕴藏在情爱悲剧中的原因就是作品向世人展示的社会话语,两个方面相互交融,相互使对方的内涵更丰富、更深刻。毫无疑问,这是一场男女情爱的悲剧,虽然作者在小说结尾用“家树万分难过之余,觉得还有这样一个知己,握了她的手,就也破涕为笑了”⑥张恨水:《啼笑因缘》,团结出版社2003年版,第407页。这样的语句作为结尾,或许给了读者不少温润的感觉,但是情爱的悲剧依然深深压在读者的心头。从张恨水笔下的男女情爱悲剧发生的原因可以看出,男女情爱这种被民初哀情小说家描述成纯粹的近乎于柏拉图精神恋爱的状态完全被张恨水打破了,张恨水不仅把社会各层次因素掺入男女情爱中,更重要的是不再写才子佳人和嫖客妓女这类特殊的人群,而是把笔锋转向了一般小市民,当然也触及上层有钱人及军阀,包括侠义人士。把男女情爱从狭窄的二人世界扩展到整个社会层面,无疑男女情爱就会产生极强的社会话语性,同时在相对全面的社会话语中男女情爱更符合现实、更曲折。情爱的社会话语,既能反映作为社会人的本质和观念,更能折射复杂的社会景观。
沿着《啼笑因缘》的创作道路写作,并有一定创新的是20 世纪40年代秦瘦鸥创作的《秋海棠》。1941年出版的《秋海棠》相比《啼笑因缘》同样有军阀、戏子和姨太太,都掺杂了一点武侠因素,其创新在于反映社会生活的面大大扩展了。《秋海棠》所反映的爱已经成为在抗战的大环境下人生存的一部分,并成为一种生存的责任,它通过写两性的情爱关系反映了更广阔和更深刻的社会内容,而且两性之间的情感更让读者感觉悲壮。《秋海棠》采用新式章节形式给读者描述了一个不像戏子的戏子秋海棠和一个不像姨太太的姨太太罗湘绮之间美丽和凄惨的故事。汤哲声认为这部小说通过写超越于婚姻模式、不受婚姻约束的一对真正相爱的恋人之间的爱情,来展示“美的结合、美的破碎、美的韧性和美的毁灭”①汤哲声:《中国现代通俗小说流变史》,重庆出版社1999年版,第121页。。这部小说中男女真诚的情爱彻底打破了民初哀情小说没有肉欲的纯情,梅宝的出生证明了灵与肉的结合才是真正的男女之情。让人羡慕和尊敬的男女情爱被袁宝藩破坏和毁灭,更是一场让人扼腕的悲剧。当灵与肉结合的男女真诚情爱被社会黑暗势力所扼杀,而男女情爱又作为一种美好情感被赞扬,那么扼杀它的社会黑暗势力一定遭受唾弃和指责。男女情爱和社会现实结合得如此完美,男女情爱的社会话语因此充分展现,从而圆满地完成了言情小说社会话语的表达。
三、情爱的畸形世俗化
言情小说所表达的主题除了圣洁的空中楼阁般的纯情、与社会紧密联系的社会话语外,还有一种不被世人接受却被津津乐道或感叹的情感,即畸形世俗化的情爱。代表作品为刘云若和张爱玲的小说。
刘云若曾被称为“天津张恨水”,但是“如果说张恨水的小说风格得中和之美,那么刘云若的小说则以诡奇取胜。他们两个‘一正一奇’,双星闪耀,使民国通俗小说星光长明。”②张元卿:《刘云若论》,载《民国北派通俗小说论丛》第一辑,山西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113页。从刘云若的第一部长篇《春风回梦记》起,就在向读者讲述着非正常的男女情爱故事,多数是婚姻内的三角恋爱。婚姻的三角情感是一种世俗客观存在,因为它的不合常情而往往以悲剧结束,在非正常的三角情感中,人的感情都不能正常完全地表达,因此人的心灵备受折磨和扭曲。《春风回梦记》讲述了一个凄婉动人的情爱悲剧。卖唱女郎如莲和富家公子陆惊寰相思多年,如莲为了能和陆惊寰经常接近竟卖身妓院。陆惊寰在新婚之夜竟然抛下新娘与如莲约会,后来当陆惊寰把如莲娶回家时,如莲旋即气绝,陆妻也同时病殁。20 世纪40年代引起巨大轰动的刘云若的《旧巷斜阳》讲述的是出身社会下层的贫家妇女璞玉因为丈夫是失明的残疾人,又要照顾两个未成年的孩子,只好去餐馆做女招待,偶遇王小二后顿生知己之感,她痛苦徘徊在丈夫与情人之间,丈夫发现隐情后离家出走,王小二也因自责离开。后来因为巧合,璞玉与王小二结为夫妇,但好景不长,王小二因仕途受牵连亡命天涯。《红杏出墙记》写铁路职员林白萍一天深夜回家,为了让妻子惊喜而悄悄潜入家门,结果却发现妻子和自己的好友同床共寝,林白萍万分痛苦离家出走,妻子黎芷华内心忏悔追寻丈夫,在这个过程中,引出了一系列的男女人物,这些男女之间发生了错综复杂的恋情,但最后都是死结。小说中的主人公也不例外,最终都以悲剧结尾,林白萍跳水自杀,黎芷华坠楼身亡。范伯群认为刘云若的《红杏出墙记》写作目的在于“为了认识一个大千世界,认识大千世界中的‘畸情’以及许多书中的‘至性人’”③范伯群:《中国现代通俗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458页。。其实,这部小说写的是“精神之爱与生理欲望的矛盾,清醒的理智与无可救药的沉沦的冲突,恩爱、悔恨和善恶生死交战”④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44页。。综上所述,刘云若的小说主要表达的就是情爱的畸形世俗化,即写世俗中存在于婚姻内的三角情爱关系,因受道德的约束不被社会所接受而以悲剧结束。
刘云若小说的主题由言情的畸形世俗化所构成,其实是由“爱情”、“苦难”和“彷徨”三个母体交织在一起构成的。张元卿认为刘云若“通过三角恋爱中人物的犹豫不决,表现爱的苦闷和彷徨;用‘爱情’表现‘彷徨’的深刻,同时又用‘彷徨’揭示‘爱情’的破碎的必然;通过面对‘爱情’的‘彷徨’表现‘苦难’,同时又通过‘苦难’透视‘彷徨’的深层原因”①张元卿:《刘云若论》,载《民国北派通俗小说论丛》第一辑,山西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104页。。总之,从刘云若的作品中可见的都是婚姻内世俗社会中平凡男女畸形的情爱三角关系。相对于张恨水擅长写世族大家和中上流社会,刘云若更善于写市井人家和中下流社会,因此刘云若的小说所述男女情爱更具有世俗化倾向。汤哲声认为:“张恨水写的是情与社会恶势力的冲突,把批判的矛头指向不合理的社会。刘云若则写情和理的冲突,它引发的是人们对现有情理关系的思考。”②汤哲声:《中国现代通俗小说流变史》,重庆出版社1999年版,第124页。男女情爱之间三角般的畸形世俗化最终以出走或死亡结束,虽然其中表达了男女至真至纯的真感情未必存在于婚姻内,但男女情爱是一个社会化的问题,因此必然有一种社会道德的约束力量。男女两性情感表达的虽然是一种社会言语,但当表达违背社会话语的常态时必然是一种畸形,畸形的男女情爱很难按照世俗社会的存在法则正常存在和发展。
类似的畸形男女情爱在张爱玲笔下处处可见。张爱玲小说把传奇性、世俗化和生活化较好结合在一起。张爱玲凭着对世俗情感的独特感知,把空虚和压抑的命题更多地写进了她的文本世界,常常写爱的缺席所带来的畸情,因此她的小说是阴郁冷色的。她的小说虽是写小市民的男女之情,向读者展示的却是对人生悲剧性的体验,不是宣泄,而是一种苍凉的启示,用张爱玲自己的话说:“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虱子。”③张爱玲:《天才梦》,载《张爱玲散文全编》,浙江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3页。张爱玲的小说创作主要在上海沦陷时期,因这个特殊的历史阶段以及张爱玲特殊的生活环境和个性使其小说具有强烈畸形世俗化倾向。张爱玲小说结集成集,最后命名为《传奇》有一定道理,关照其小说就会发现一个异趣的情感世界,即对纯情的解构和冷观。《沉香屑·第一炉香》中的薇龙嫁给了乔琪后,等于把自己给卖了,因为她“整天忙着,不是替乔琪弄钱,就是替梁太太弄人”。《心经》写女儿对父亲产生了情人般的感情,让人的心灵感到极大的震撼。张爱玲在《自己的文章》里曾说:“在我的小说里,除了《金锁记》里的曹七巧,全是些不彻底的人物。”《金锁记》讲述的是麻油店铺的女儿曹七巧因为金钱嫁给姜家残废人,处处受到排挤,她的金钱也处处遭人算计,她千方百计保住了自己的金钱,但是她一生却没有任何真正的爱情,这个漫长的拥有金钱而缺乏男女情爱的过程使曹七巧情感扭曲、心理变态,黄金劈死了她的爱情,而她则又用自己的不幸劈杀了自己一双儿女的幸福,特别是女儿因为恋爱而戒掉鸦片后,她还要在儿子长白宴请童世舫的席间演出令人毛骨悚然的一幕:“长白道:‘妹妹呢?来了客,也不帮着张罗张罗。’七巧道:‘她再抽两筒就下来了。’世舫吃了一惊,睁眼望着她。七巧忙解释道:‘这孩子就苦在先天不足,下地就得给喷烟。后来也是为了病,抽上了这东西。小姐家,够多不方便哪!也不是没戒过,身子又娇,又是由着性儿惯了的,说丢,哪儿就丢得掉呀?戒戒抽抽,这也有十年了。’……”一个母亲竟然有预谋地坦然扼杀自己女儿的幸福,让人心灵震撼恐惧之余禁不住产生厌恶,厌恶之余也会升起怜悯之感。通过曹七巧不幸的一生,可见作者展示给世人的男女情爱畸形世俗化注定是一场无法挽回的悲剧。总之,张爱玲小说写出了男女之间特殊境遇之下的世俗的畸形情感,这种世俗的畸形情感营造了一幅幅感伤而苍凉的画面,总能让人扼腕长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