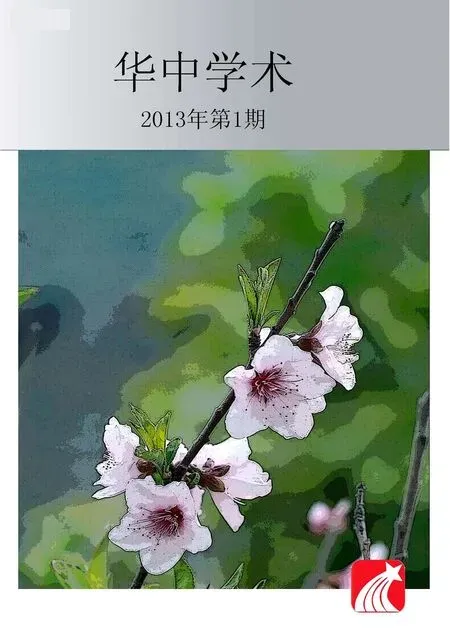魏泰其人考略
李晓晖
(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湖北武汉,430079)
魏泰,字道辅,号汉上丈人、临汉隐居。北宋襄阳人。生卒年不详。大致生活在北宋中后期。《宋史》无传。关于他的生平事迹,仅零散见于少数文献,且多存疑义。本文试图对其家世、生平等略加考辨。
一、魏泰家世及生卒年考
魏泰的家世,今已不甚明了。根据魏泰《东轩笔录》卷12云:“余为儿童时,尝闻祖母集庆郡太守陈夫人言。”[1]“集庆郡太守”,当为“集庆郡太君”。如宋代孙觉《陈襄墓志铭》云:“公姓陈氏,讳襄,字述古。其先光州固始人,五代时王氏入闽,因随家焉。今为福州侯官县古灵人。(中略)父讳象,台州黄岩县尉,累赠尚书兵部侍郎。母黄氏,永嘉县太君。继母王氏,集庆郡太君。”[2]显然魏泰祖母与陈襄继母同样接受的是“集庆郡太君”赠封之号。宋代张镃《仕学规范》卷29引《东轩笔录》此条,文字稍有节略,云:“余为儿童时尝闻祖母集庆郡夫人言。”[3]江少虞《宋朝事实类苑》卷53“忠孝节义·钟离君”条引《东轩笔录》此句亦节略同上[4]。皆可证“太守”当作“太君”。
据现存文献记载,魏泰一生不曾为官,当然不可能为其祖母博得朝廷封号。故其祖母的封号,当与其父祖辈之仕宦有关。由此我们可以推测魏泰出生于襄阳的一个官宦世家。另外我们从其祖母陈夫人能讲述南唐旧事,以及米芾《画史》载魏泰收藏有南唐徐熙的名画等多种书画艺术精品[5],或可推测其先祖曾出仕南唐,或与南唐有较深的渊源。
魏泰的姐姐魏玩,为曾布之妻,是北宋著名女词人,有《鲁国夫人词》。前人对魏夫人词的评价很高。朱熹曾将魏夫人与李清照并提:“本朝妇人能文,只有李易安与魏夫人。”[6]如此才女,在当时的文化环境下,只可能出身于与李清照家庭类似的书香门第。魏家居襄阳,曾家居南丰,魏玩与曾布的婚姻也可能与先辈的交往有关,这也从侧面证明当时魏、曾两家门第相当。
魏玩、魏泰的生卒年均不详。魏玩生年或当与曾布相近而略晚,曾布生于宋仁宗景祐三年(1036年),由此推测魏玩、魏泰的生年当在此后。
魏泰《东轩笔录》卷15有云:“余为儿童时,见端溪砚有三种,曰岩石,曰西坑,曰后历。(中略)西坑砚三当岩石之一,后历砚五当西坑之一,则其品价相悬可知矣。自三十年前,见士大夫言亦得端溪岩石砚者,予观之,皆西坑石也。迩来士大夫所收者,又皆后历石也。岂惟世无岩石,虽西坑者亦不可得而见矣。”[7]又据魏泰《东轩笔录序》云:“思少时力学尚友,游于公卿间,其绪言余论者有补于聪明者,虽老矣,尚班班可记,因丛摭成书。呜呼!事固有善恶,然吾未尝敢致意于其间。姑录其实以示子孙而已。”所署作时为“元祐九年之上元日”[8]。元祐九年(1094年)四月改元绍圣元年(1094年),以此上推三十年,即治平元年(1064年),即西坑砚尚多时;再上推十年,即至和元年(1054年),或当魏泰所云儿童之时。由此推之,魏泰的生年当在庆历四年(1044年)左右。与前据曾布、魏玩之生年所作推测,正可相合。
据南宋祝穆撰、祝洙增订《方舆胜览》卷32载:“魏泰,襄阳人。章子厚欲官之,拂袖还家。”[9]又明代李贤等纂修《大明一统志》“襄阳府·人物”条记载:“魏泰,襄阳人,崇观间章惇欲官之,竟拂袖还家,善文章,著《临汉隐居集》二十卷,又著《东轩笔录》十五卷,尝赋襄阳形胜,识者伟之。”[10]《大明一统志》所谓“崇观间”,实不可信。据《宋史·徽宗本纪》及《名臣碑传琬琰集·章丞相惇传》,可知章惇自元符三年(1100年)九月罢相出知越州,其后不断被贬,于崇宁元年(1102年)责授舒州团练副使、睦州居住,次年徙越州居住,又徙湖州,崇宁四年(1105年)十一月卒[11]。大观年号更在崇宁以后,可见崇宁、大观间,章惇不可能“欲官”魏泰。若如《方舆胜览》所言,“章惇欲官之”实有其事,则当在绍圣、元符间。
据李廌《济南集》卷1《岑使君牧襄阳受代还朝某同赵德麟谢公定潘仲宝皆饯于八叠驿酒中以西王母所谓山川悠远白云自出相期不老尚能复来各人分四字为韵以送之某分得相期不老》、卷2《从德邻至邓城访魏道辅故居怀道符》、《廌寓龙兴仁王佛舍德麟公定道辅仲宝携酒肴纳凉联句十六韵》、卷3《赵令畤德麟作襄阳从事丁丑季冬出行南山三邑某同谢公定曾仲成潘仲宝携酒自大悲寺登舟过岘山宿鹿门明日复自岘首目送缘绝壁而往上船山下相与酌酒而去德麟赋诗次韵和之》等诗[12],可知魏泰在绍圣四年丁丑(1097年)前后与岑象求、赵令畤、李廌等交往、唱酬颇为密切,时岑象求任襄州知州、赵令畤任州从事。
据明人曹学佺撰《蜀中广记》卷23载:“碑目云:《万州虚鉴真人赞》,朝请大夫知襄州军州兼管内劝农事提举房随郢州兵马巡检公事柱国借紫岑象求撰文,阳翟李廌书丹,南京进士戚逵题额,奉议郎权知万州军州兼管内劝农事武骑尉赐绯借紫盖休景立石于元符元年。”[13]可知元符元年戊寅(1098年)岑象求尚在襄州任。
由以上考辨,我们可以判定,在绍圣、元符间魏泰尚活跃于诗坛、文坛。
二、魏泰困顿场屋考
魏泰早年曾数举进士,颇不得志。
张知甫《可书》“白殭”条云:“魏泰数举进士不利。荆公戏云:‘眼下有臣卧蚕者贵,如文潞公有之而为相。公亦有而未遇也,岂非白殭者乎!’”[14]张知甫生活在北宋、南宋之交。据《可书》“种张庄”条(此条文字内容又见周煇《清波别志》卷下,文字小异。周煇注明文献来源为元祐《实录·张问传》)[15],其祖父为张问,字昌言。又据《可书》“村夫背上奇物”条称“仆顷在京师因干出南薰门”[16],可知张知甫于北宋宣和年间(1119—1125)尝为官于京师。张问为襄阳人,《宋史》有传。据孔凡礼先生考,张问卒于元祐二年(1087年)十月,享年七十五[17]。可知张问与魏泰为同乡,年辈当长于魏泰。张知甫《可书》所载魏泰事可能得闻于父祖或乡里长老。由此可知魏泰曾多次举进士不售。
又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12引《桐江诗话》云:“魏道辅泰,襄阳人,元祐名士也。与王介甫兄弟最相厚。仆初以谓有隐德,不仕,及试院中,因上请主文,道辅恃才豪纵,不能忍一时之忿,殴主文几死,坐是不许取应。”[18]这段文字又见史容注山谷诗。《山谷外集诗注》卷11《和答魏道辅寄怀十首》,史容注“酒阑豪气在,尚欲椎肥牛”句称:“《桐江诗话》云:‘魏道辅与王介甫兄弟最相厚,试院中,因上请,恃才豪纵,殴主文几死,坐是不许取应。’”[19]史注所引文字较前《苕溪渔隐丛话》所引简略。其实,二书所引皆为节略之文,文意颇有难晓处,惜原书已佚,无从校阅。
不过根据此则《桐江诗话》,我们推测魏泰这次殴打考官,一方面是因为“恃才豪纵”,另一方面也可能因为不满考官的轻视,同时还可能是把举场多次不售的怨气一次发泄出来,所以“不能忍一时之忿”而大打出手,竟然“殴主文几死”。其结果可想而知,魏泰此番“动粗”,断送了自己的功名前程。由此看来,魏泰后来隐居不仕,不仅仅是出于隐逸高怀,也是出于不得已的选择。
据上引张知甫《可书》所载,王安石竟拿魏泰数举进士不利来开玩笑以及《山谷外集诗注》卷11《次韵道辅双岭见寄三迭》题下史容注云:“和答魏道辅等凡四诗,今考三诗皆言徐德占,而永乐之祸,乃元丰五年九月,今置之五年,庶与诗合。”黄庭坚此诗有云:“明如九井璜,美如三危露。贞观魏公孙,今来功名误。儿时汉南柳,摇落伤岁暮。时不与我谋,羲和促天步。生涯鱼吹沫,文彩豹藏雾。人言壶公老,渠但未得趣。饮酒入壶中,茫然失巾屦。时不与我谋,今君向何处。”对魏泰充满了赞美与惋惜,言其功名无成,退隐江湖。山谷此诗作时,必在魏泰“殴主文几死,坐是不许取应”以后。郑永晓《黄庭坚年谱新编》于黄庭坚与魏泰唱和诗有详细考订,亦赞同史容注,定为元丰五年(1082年)作[20]。因此,我们可以推测魏泰最后一次参加科举考试的时间,当在元丰五年(1082年)九月以前。
三、魏泰仗势横行考
魏泰在历史上似乎名声颇不好,大略与前文所叙“殴主文几死”的科场案无关,实与见载正史的“规占公田案”有关。
《宋史》卷319《欧阳修传》附其中子欧阳棐事迹有云:“修卒,(棐)代草遗表,神宗读而爱之,意修自作也。服除,始为审官主簿,累迁职方员外郎、知襄州。曾布执政,其妇兄魏泰倚声势来居襄,规占公私田园,强市民货,郡县莫敢谁何。至是,指州门东偏官邸废址为天荒,请之。吏具成牍至,棐曰:‘孰谓州门之东偏而有天荒乎?’却之。众共白曰:‘泰横于汉南久,今求地而缓与之,且不可,而又可却耶?’棐竟持不与。泰怒,谮于布,徙知潞州,旋又罢去。元符末,还朝。历吏部、右司二郎中,以直秘阁知蔡州。”[21]
这段文字,实有不少令人疑惑不明处。如欧阳棐“累迁职方员外郎、知襄州”的时间?曾布任执政与魏泰倚声势居襄是否有关系?欧阳棐“徙知潞州,旋又罢去”,是否为曾布因魏泰私事而打击报复?
值得庆幸的是,《宋史》中所载欧阳棐事迹的文献来源,尚完整流传下来。《欧阳文忠集》附录四,载有南宋淳熙间洪迈等所修《四朝国史》欧阳修本传,传后亦附其中子欧阳棐事迹,其文有云:
修薨,(棐)代草遗表,神宗读而爱之,意修自作也。免丧,始为审官主簿官制局详检官太常博士主客考功员外郎。(中略)元祐初,以集贤校理为著作郎、判登闻鼓院,复徙职方礼部员外郎、知襄州。曾布执政,其妇兄魏泰恃声势,来居襄,规占公私田园,强市买,与民争利,郡县莫敢谁何。至是,指州门东偏官邸废址为天荒而请之。吏具成牍至,棐曰:“孰谓州门之东偏而有天荒乎?”却之。众共白曰:“泰横于汉南久,今求地而缓与之且不可,而又可却邪?”棐竟持不与。泰怒,谮于布,徙之潞州,旋又罢去,夺校理。元符末,还朝。历吏部右司二郎中,以直秘阁知蔡州。[22]
比较可知,《宋史》中所载欧阳棐事迹文字,实由《四朝国史》节写而成。
《四朝国史》所载欧阳棐事迹文字,又主要取材于毕仲游《欧阳叔弼传》,该传全文具见《西台集》卷6,今摘引相关部分如下:
哲宗即位,(棐)为秘书省著作郎、充修实录检讨。叔弼甫曰:“古虽不讳嫌名,而今日为官称,则不可以不讳也。”乃辞不就职,而更为集贤校理、判登闻鼓院。后入省为职方礼部二员外郎。(中略)章公子厚入相,叔弼甫数请外,乃以朝散郎秘阁校理、知襄州。有魏泰者,曾公子宣卫国夫人之兄也,居襄二十年,倚子宣之重,以传食于汉南。虽为布衣,州郡以倅贰之礼接之,犹慊不怿。多规占公私田园,强市买,与民争利,前后无复谁何者。于是,以州门之东偏楼店官废址为天荒而请之,上下弥缝为成书,然后示叔弼甫,叔弼甫曰:“孰谓州门之东偏而有天荒可请乎?”却之。州官上下更谓叔弼甫曰:“泰横于汉南日久,未易裁也。彼请地而迟与之且不可,况终却之乎?”叔弼甫曰:“天荒地野,泰请之。州门之左,以门左之地为天荒售人,非政也。惮泰而诬天荒之令,非法也。”泰闻之怒,诉于转运司,下其诉于州。叔弼甫终持不与,泰由是诉叔弼甫于子宣矣。襄罢,以朝请郎知潞州。潞罢,乃禠所帖校理还吏选,继降官二等。元符三年,始复以朝散郎还朝,为尚书吏部郎中,迁右司郎中。请外,遂以朝奉大夫直秘阁知蔡州。[23]
由于史书篇幅的限制,以及后来史官出于对欧阳棐的同情和对曾布等新党的痛恨,从《四朝国史》到《宋史》,节录毕仲游《欧阳叔弼传》文字愈加简约,从而给后人了解魏泰“规占公田案”始末增添了不少误会。
欧阳棐“累迁职方员外郎、知襄州”的时间,据《宋史》所叙“服除,始为审官主簿,累迁职方员外郎、知襄州”,很容易让人误会是在宋神宗朝(按:《大清一统志》卷271“襄阳府二”载历代宦守有云:“欧阳棐,修子,神宗时知襄州。”[24]即因《宋史》而误);据《四朝国史》所叙“元祐初,以集贤校理为著作郎、判登闻鼓院,复徙职方礼部员外郎、知襄州”,又容易让人误会是在元祐初年。其实据毕仲游文所叙:“章公子厚入相,叔弼甫数请外,乃以朝散郎秘阁校理、知襄州。”可知欧阳棐出知襄州,乃在章惇以后。
据《宋史·哲宗本纪》载绍圣元年(1094年)四月,“壬戌,以资政殿学士章惇为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郞”[25]。又绍圣二年(1095年)四月,“戊辰,诏职事官罢带职,朝请大夫以下勿分左右,易集贤院学士为集贤殿修撰,直集贤院为直秘阁,集贤殿校理为秘阁校理”[26]。结合《宋史》所载章惇入相时间,以及改集贤殿校理为秘阁校理的时间,与毕仲游所叙,可以推知,欧阳棐以朝散郎秘阁校理、出知襄州当在绍圣二年(1095年)四月以后。
下面我们来讨论曾布任执政与魏泰倚声势居襄是否有关系。据《宋史》所叙“曾布执政,其妇兄魏泰倚声势来居襄,规占公私田园,强市民货,郡县莫敢谁何”。与《四朝国史》所叙相同。而毕仲游所叙比二史首尾更详。
比较三文,二史所载显然有误。魏泰并非自“曾布执政”以后“倚声势来居襄”。魏泰本为襄阳人,非乘曾布之势忽从外地迁来。“曾布执政,其妇兄魏泰恃声势,来居襄”,一语并不见毕仲游文,乃为《四朝国史》所添加而为《宋史》所袭用。毕仲游文已明言此前魏泰已“居襄二十年”(按:其实,若从魏泰父祖辈算起,居襄阳的时间远不止二十年),方可与后文所谓“泰横于汉南日久”相照应。若如二史所谓魏泰乃乘曾布之势忽从外地迁来,则前后自相矛盾。
曾布初任“执政”的时间,据《宋史·哲宗本纪》载绍圣元年(1094年)六月,“癸未,以翰林学士承旨曾布同知枢密院事”[27]。“同知枢密院事”,也简称“同知院”,在宋代也通称“执政官”(按:曾巩《隆平集》云:“以参知政事、枢密使、副知院、同知院、签书院事,并为执政官。”)。可知曾布初任“执政”,比章惇拜相的时间尚晚三个月左右。至绍圣二年(1095年)欧阳棐知襄州时,曾布居“执政”位尚不到一年的时间,即使魏泰也曾借姐夫曾布之势,但也不至如毕仲游所说“居襄二十年,倚子宣之重”。因为曾布在熙宁、元丰间因与王安石、吕惠卿不和,颇受打压;至元祐间旧党当政,亦受排挤,故久在地方任职;至绍圣元年(1094年)始进入政权核心。即使有地方官因忌惮曾布,或想拍曾布的马屁而巴结魏泰,也当是近年之事,而不当是“二十年”以来如此。其实,毕仲游此文叙魏泰事,颇多夸饰之辞,如“传食于汉南”、“州郡以倅贰之礼接之,犹慊不怿”、“多规占公私田园,强市买,与民争利,前后无复谁何者”,都属莫须有的罪名,颇让人怀疑其真实性。
我们还需要进一步考查欧阳棐“徙知潞州,旋又罢去”,是否为曾布因魏泰私事而打击报复?魏泰“规占公田案”始末,毕仲游之文叙述已详:魏泰“以州门之东偏楼店官废址为天荒而请之,上下弥缝为成书”,但为州守欧阳棐所拒;魏泰不服,于是上“诉于转运司”;转运司复将诉状批转本州处理,而州守欧阳棐“终持不与”。可见欧阳棐坚持原则,于魏泰毫不假借,故魏泰最终输了这场官司。
魏泰“规占公田案”,还有一个尾声。《四朝国史》云:“棐竟持不与。泰怒,谮于布,徙之潞州,旋又罢去,夺校理。”《宋史》亦云:“棐竟持不与。泰怒,谮于布,徙知潞州,旋又罢去。”共谓此后魏泰谮诉于曾布,曾布遂肆行报复,欧阳棐不久被调离到潞州,又不久被曾布罢官。
二史所叙的“尾声”当然与毕仲游文有关。不过细味毕仲游此节文字:“叔弼甫终持不与,泰由是诉叔弼甫于子宣矣。襄罢,以朝请郎知潞州。潞罢,乃禠所帖校理还吏选,继降官二等。元符三年,始复以朝散郎还朝。”实与二史所叙颇有差别。
毕文所谓“泰由是诉叔弼甫于子宣矣”,实乃揣测之辞,难以落实;但二史则已完全坐实。所谓“襄罢,以朝请郎知潞州”,从行文来看,已是另起一段,叙述欧阳棐的另一段潞州仕历;欧阳棐很可能是襄阳任职期满后,改任潞州。所谓“潞罢,乃禠所帖校理还吏选,继降官二等”,很可能与魏泰案毫无关系。毕仲游文叙欧阳棐襄州、潞州仕历,并没有“旋又罢去”的说法,此四字实为《四朝国史》所添。前文已考明欧阳棐知襄州在绍圣二年(1095年)四月以后;至元符元年戊寅(1098年)岑象求已在知襄州任上,很可能岑象求就是欧阳棐的接任者。欧阳棐襄州任后,接任潞州,毕仲游文已载其至元符三年(1100年)始还朝。从绍圣二年(1095年)至元符三年(1100年),其间约五年左右,时间并不算很短。当然也完全可能欧阳棐襄州之任的时间长于潞州之任,但潞州之任被“禠所帖校理还吏选,继降官二等”,可能与魏泰案毫无关联。
总之,因毕仲游《欧阳叔弼传》“叔弼甫终持不与”以下行文,一者因有疑似之辞,一者因与前事相接太紧而又文字过于简略,容易让人产生曾布肆行报复、欧阳棐因此而被罢官的误解。《四朝国史》正因误读而扭曲事实,《宋史》则袭用《四朝国史》而未作深考。
我们今天来看这场官司,当然欧阳棐坚持原则、不畏权贵,值得肯定。但如果放到宋代历史环境中,可能类似魏泰的这种做法也颇常见。如元丰四年(1081年)二月,苏轼贬黄州时,老友马正卿哀其贫,为之于郡中请得故营地数十亩,苏轼将这块地称作“东坡”,后自号“东坡居士”即缘于此(《苏轼诗集》卷21《东坡八首并叙》);次年二月,又于“东坡”之旁得废圃,筑“雪堂”(《苏轼文集》卷12《雪堂记》)。毕仲游之文已载魏泰所请之地为“州门之东偏楼店官废址”,实与苏轼所得之“故营地”、“废圃”类似。苏轼请荒废之地的做法,历来无异议。何以魏泰此举深受指责?值得我们思考。从前文考察魏泰在绍圣、元符间,与欧阳棐的继任者岑象求,以及州从事赵令畤、名士李廌等人的密切交往活动来看,魏泰的恶名未必如毕仲游文所叙那般败坏。
其实,若从更深层的历史大背景来探讨,这场简单的民事纠纷被诸史纷纷转录,有更重要的政治原因。曾布在《宋史》中被列入《奸臣传》,曾布为魏泰的姐夫,曝光魏泰之丑,更是为了曝光曾布之恶。欧阳棐为欧阳修之子,乃名臣之后,又曾被列入《元祐党籍》,遭受打击;又有才士毕仲游为其作传,又为洪迈《四朝国史》引用,故魏泰的恶名,俨成定谳;一桩贪图小便宜而未遂的小案件,被放大成了新旧两党斗争的大事件。
南宋时期也不乏史学家能超越党争的局限,以实事求是的精神撰写史著。王称的《东都事略》、李焘的《续资治通鉴长编》都载录了不少与欧阳棐相关的史事。
《东都事略》卷72《欧阳修传》后附有《欧阳棐传》,今摘录相关部分如下:“修卒,始仕,为审官院主簿,迁太常博士。哲宗即位,为著作郎,(中略)章惇入相,棐以秘阁校理知襄州;又知潞州,坐元祐党夺校理。元符三年还朝,为吏部郎中,迁右司郎中。请外,以直秘阁知蔡州,复系元祐党镌直秘阁,罢。”[28]显然,《东都事略》未简单将欧阳棐在潞州任上遭夺职、降官,视为曾布替妻弟魏泰“申冤报仇”而肆意打击报复,而是归结为“坐元祐党夺校理”。
欧阳棐在元祐时期,官职屡有升迁,当时即颇为言官刘安世所攻击,甚至有“五鬼”之称。哲宗亲政以后,政治气候发生了逆转,元祐大臣及亲信多被清算。欧阳棐于章惇入相以后,数请外任,正是不自安于朝。他在绍圣间能以朝散郎秘阁校理、知襄州,应该说与遭打击迫害的苏轼、黄庭坚、张耒等相比,是非常幸运的。至元符初,欧阳棐在潞州任上,终因受元祐党牵连而被责处。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503哲宗元符元年(1098年)冬十月癸卯载:“诏朝请郎、秘阁校理、权知潞州欧阳棐落职,送吏部与合入差遣。以元祐权臣迷国之际,棐朋附大奸,每希进用,故有是责。”[29]该条后附注有李焘考异文,摘录毕仲游《欧阳棐传》。《续资治通鉴长编》正文不用毕仲游之说,说明李焘与王称认识一致,并不认为欧阳棐遭夺职、降官,是曾布替魏泰报睚眦之怨。
不仅《续资治通鉴长编》未载曾布对欧阳棐实行打击报复,反而载有曾布为欧阳棐向哲宗说情一段文字。《续资治通鉴长编》卷506哲宗元符二年(1099年)二月庚辰载云:“是日欧阳棐朝见,上目之,语曾布曰:‘此元祐五鬼。’布曰:‘亦闻有此名。元祐附丽,必亦有之。治郡亦常才,然欧阳修之子,登进士第。修于英宗定策之际最有功。章惇尝言,韩琦既以英宗判宗正,有建立之意,然未敢启口。一日与修议定,修见仁宗,便言英宗不立为皇子,则事未定。仁宗熟视修,久之不言,众为之战栗。仁宗徐曰:‘当如此。’琦与修等遂乞降诏,许之。当是时不易出此语,此功不可忘。’上矍然曰:‘诚不易启口。’布曰:‘此功为发明者少。’上颔之。”[30]曾布所对答哲宗之语,显然不以“鬼”视欧阳棐,且特别称颂欧阳修功德,意在劝哲宗对欧阳棐网开一面。
曾布在绍圣、元符间的为政是非,不是本文讨论的内容。本文只是指出,所谓魏泰案之余波,曾布因魏泰谮言对欧阳棐实行打击报复之事,实属欧阳棐或毕仲游个人揣测之辞,不可深信。
注释:
[1](宋)魏泰撰,李裕民点校:《东轩笔录》卷十二,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138页。
[2](宋)陈襄:《古灵集》卷二十五附录,四库全书本。
[3](宋)张镃:《仕学规范》卷二十九,四库全书本。
[4](宋)江少虞:《宋朝事实类苑》卷五十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693—694页。
[5](宋)米芾:《画史》,《全宋笔记》第二编第四册,郑州:大象出版社,2008年,第282页。
[6](宋)黎靖德编,王星贤点校:《朱子语类·论文下》第8册,卷一百四十,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3332页。
[7](宋)魏泰撰,李裕民点校:《东轩笔录》卷十五,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168页。
[8](宋)魏泰撰,李裕民点校:《东轩笔录》,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1页。
[9](宋)祝穆撰,祝洙增订:《方舆胜览》卷三十二,北京:中华书局,2003年,第579页。
[10](明)李贤等纂修:《大明一统志》卷六十,西安:三秦出版社,1990年,第925页。另见(明)凌迪知《万姓统谱》卷九十四:“魏泰,襄阳人,崇观间章惇欲官之,竟弗就还家,善文章,著《临汉隐居集》三十卷,又著《东轩笔录》十五卷,尝赋襄阳形胜,识者伟之。”中国谱牒研究会、山西社科院家谱资料研究中心、巴蜀书社联合编纂:《中华族谱集成》第2册,成都:巴蜀书社,1995年,第361页。
[11](宋)杜大珪编:《名臣碑传琬琰集》下集卷十八,四库全书本。
[12]傅璇琮等主编,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编:《全宋诗》,第20册卷1200至1202,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13564、13582、13586、13593、13599页。
[13](明)曹学佺撰:《蜀中广记》卷二十三,四库全书本。
[14](宋)张知甫撰,孔凡礼点校:《可书》,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405页。
[15]朱易安等主编:《全宋笔记》第五编第九册,郑州:大象出版社,2008年,第179页。
[16](宋)张知甫撰,孔凡礼点校:《可书》,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426页。
[17](宋)张知甫撰,孔凡礼点校:《可书》,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387页。
[18](宋)胡仔纂集,廖德明校点:《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十二,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第78页。
[19](宋)黄庭坚撰,(宋)任渊、史容、史季温注,刘尚荣校点:《黄庭坚诗集注》,北京:中华书局,2003年,第1161页。
[20]郑永晓:《黄庭坚年谱新编》,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7年,第130页。
[21](元)脱脱等撰:《欧阳修列传》附《欧阳棐传》,《宋史》第30册《列传》卷三百一十九,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10382页。
[22](宋)欧阳修撰:《欧阳文忠集》附录四,北京:中国书店,第1369页。
[23](宋)毕仲游:《欧阳叔弼传》,《西台集》第2册卷六,王云五主编:《丛书集成初编》本,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年,第86、87页。
[24](清)康熙:《大清一统志》卷二百七十一襄阳府二,四库全书本。
[25](元)脱脱等撰:《宋史》卷十八,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340页。
[26](元)脱脱等撰:《宋史》卷十八,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342页。
[27](元)脱脱等撰:《宋史》卷十八,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341页。
[28](宋)王称撰:《东都事略》卷七十二《欧阳修传》附《欧阳棐传》,光绪九年(1883年)淮南书局重刊本。
[29](宋)李焘撰:《续资治通鉴长编》卷503,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11989页。
[30](宋)李焘撰:《续资治通鉴长编》卷506,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1205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