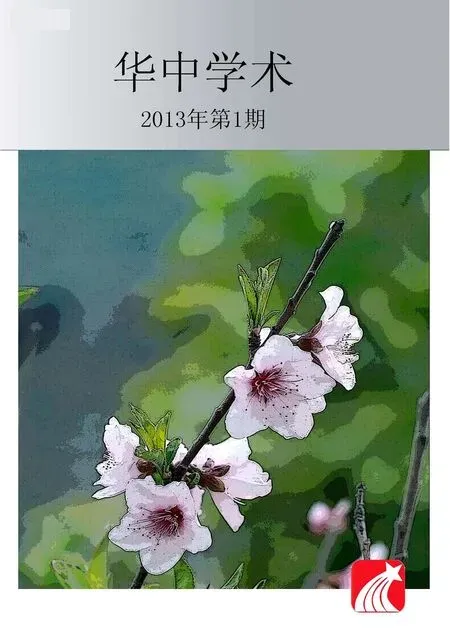北宋书学推重杨凝式之原因探略
张家壮 郑 薇
(南京艺术学院博士后流动站,江苏南京,210000;福建师范大学协和学院,福建福州,350007)
北宋书学推重杨凝式之原因探略
张家壮 郑 薇
(南京艺术学院博士后流动站,江苏南京,210000;福建师范大学协和学院,福建福州,350007)
宋代书学能于唐人之后另辟新境,与宋人对五代杨凝式书法的接受与阐释具有密切关系。本文在动态分析杨凝式其人其书的基础上,对北宋书学推重杨凝式的原因进行了深入探讨。指出杨凝式以其创新书风,让宋人在唐书法度已臻极致的情形下看到新变尚意的曙光;在文化转型所引发的文艺思潮的变革中,杨凝式的新变正好契合了新时代文化转型的要求。
杨凝式 尚意 宋代书风
杨凝式是五代诗人、书法家。《旧五代史·杨凝式传》有云:“凝式长于歌诗,善于笔札。”[1]《新五代史·杨涉传》亦云:“子凝式,有文词,善笔札。”[2]皆于其文学与书法成就并举。但随着北宋文学与书学的发展,杨凝式逐渐转变为主要以书法成就而备受宋人瞩目。北宋欧阳修、王安石、苏轼、黄庭坚等人均对杨凝式书推崇有加,他们的书法也正是在杨凝式所开示的道路上拓步前行的。近人李瑞清曾说,“杨景度为由唐入宋一枢纽”[3]。本文试图将杨凝式放置于唐宋这一文化转型期的大语境中,对其人其书作动态分析,由此观照杨氏在北宋的接受史,探讨北宋书学特别推重杨凝式的深层原因。
一
在苏、黄的众多书论、题跋中,往往将颜、杨并提。颜、杨对宋代书学的意义,值得我们作更深的体会。台静农《书道由唐入宋的枢纽人物杨凝式》认为,“二王”之后是颜鲁公,鲁公之后是杨凝式,这是苏、黄自己认为的书学系统[4]。苏、黄所标举的这一书学系统,无疑借鉴了当时已为主流话语的“道统”、“文统”之说,对北宋书学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颜真卿在书学史上的崇高地位在唐代实已确立,而杨凝式的地位则主要由苏、黄所标举的这一“书统”而提升至与颜真卿并称。苏、黄之所以如此推重杨凝式,很重要的原因,即杨凝式的书法有“二王”逸气。然逸气由何而来呢?我们可以先从杨凝式得与魏晋人异代相感的生存处境中求之。
五代的丧乱使文士的命运恶化,这一点与魏晋之际士人们的遭遇颇相似。《资治通鉴》卷265就记载着朱全忠以“衣冠浮薄之徒紊乱纲纪”为由大肆杀戮文人。文人生存环境实与六朝相似。不惟是环境,自我意识的又一次凸显,也呈现出与六朝传统具有某些呼应。不过,晋人在沉酣中,“向外发现了自然,向内发现了自己的深情”,人格上越发高蹈和独立,始终维持门阀氏族的优越感与脱俗的风貌;而唐末五代士人的群体人格却发生了剧烈的质变,据张兴武《五代作家的人格与诗格》分析,质变具体表现为士大夫缺乏节操意识,朝秦暮楚的特性不断发展,趋时应命成为时代普遍的心声,生成以满足名利渴求为目的的仕宦人格[5]。因此,在五代士人的自我意识中膨胀的主要是“名利”二字,正如张乔《题古观》所云:“莫如为名利,归踏五陵尘。”同为乱世,何以有如此巨大的差异?其实,这正是士族文化向世俗地主文化滑落难以避免的趋势。中晚唐以后,寒门庶族队伍不断壮大,他们介入社会上层,不断削弱了士族的力量,并逐渐取而代之,同时他们自身的俗气也裹挟而入,加之都市经济的发展,士人对市井俗气及相应的奢靡生活表现出浓厚的兴趣,沉湎酒色、醉入花间成为唐末五代士人在乱世震荡下的重要生活方式。世道愈乱,奢糜之风愈烈。
与同时期的士人比较而言,杨凝式可谓遗世独立。杨凝式之父杨涉是唐哀宗朝宰相,朱温篡唐时,杨涉送传国玺。对此,杨凝式曾以大义之言谏阻其父,杨涉闻言惊骇不已。陶岳《五代史补》卷一“杨凝式佯狂”条有云:“时太祖(朱温)恐唐室大臣不利于己,往往阴使人来采访群议,缙绅之士,及祸甚众。(杨)涉常不自保,忽闻凝式言,大骇曰:‘汝灭吾族!’于是神色沮丧者数日。凝式恐事泄,即日佯狂。时人谓之杨风子。”[6]类似的记载还有不少,足见佯狂一事对杨凝式甚为重要。这让我们很自然地想到了阮籍——一位魏晋风度的典型的代表。而所谓“魏晋风度,名士风流”,决不仅仅是外表潇洒风流,更在于隐藏其后的深沉忧患。杨凝式度越时辈,他与魏晋间人异代相感之处可谓多矣。他虽历仕各朝,却屡屡托以心疾罢去。传统儒士守道的恒心与波云诡谲、不断更替的新兴政权,使得杨凝式在世俗生活里始终面临着难以解救的矛盾。同时代的文人,或因彻底绝望而遁迹出世,或泯灭理想而醉入花间,相较而言,杨凝式的人生态度则显得十分沉重,他在徘徊、抗争中承受创伤,又在创伤中获得精神的涅槃。惟其如此,他的佯狂才具有真正深刻的内容,更重要的是,它还赋予杨凝式非同一般的艺术感觉。
或许从这个角度去思考,我们能更多地体悟到杨凝式苦痛人生的积极意义:外在的现实苦难已经转化为内在的审美自觉,他于深沉的忧患意识中磨砺感觉,积孕作为艺术核心的美与真的力量。杨凝式以狂者的姿态处世而不为流俗所左右,虚静使其神情专注、用志不分,保证审美、创作活动的有效深入;丰富的现实经验和巨大的人格潜力化为艺术潜在格调与风貌,同时也保持了人格的尊严与独立。
苏、黄推重杨凝式,同时还与杨凝式的书法追求清莹的境界有关。杨凝式遗留的墨迹中以笔札、题跋为多。《韭花帖》正是其简札代表作。《宣和书谱》将其书体定为楷书[7],从该帖用笔的主体笔法看是有道理的。同时它又有“五代兰亭”的美誉,这缘于该帖闲适、潇洒的体貌给欣赏者带来的感动。杨凝式虽欲在表现笔法和意境上追觅《兰亭序》的遗踪,但它的用笔显然比《兰亭序》沉着,隐没了《兰亭序》的轻盈之美,显得凝练浑成,可知其有受颜真卿沾溉的痕迹。然而单纯承载传统,不足使之成为艺术经典。因此,在究源探流作逆向考察之际,还应着眼于该帖更高的美学相位。这件作品具有中国古代书家审美追求的普遍意义——追求一个清莹的境界。清莹之美成为一种审美价值,诗人也罢,画家也罢,书家也罢,都推赏清莹的境界,咏写清莹的意境。《韭花帖》映衬了作者崇尚空明、澄澈、高清的书法观念,也含蕴着书家十分典型的清洁感和脱俗风貌,涤除了唐末以来的芜鄙之气。《韭花帖》的内容是构成清莹、简净格调的原因之一。杨凝式带着欣悦与满足,平和落墨,发而为书,初非经意而意在笔中,恍然有带露折花的新鲜与真切。作者在人命危浅、朝不虑夕的时代里,却向人们展示了生活极其温情平和的一面。作为楷书的《韭花帖》深具清腴简奥的韵致,已悄然消解唐以来楷书尚法俨然的传统。书贵适意的理想,已是呼之欲出,尚意的足音已隐然可闻。
二
将宋人“尚意”书风之滥觞,仅仅落实于《韭花帖》一件作品,难免让人觉得武断。其实,杨凝式对北宋书坛的影响是整体的,下文就杨凝式何以成为北宋书风的发轫者展开进一步的讨论。
在“斯文终有愧于古”的宋初[8],书风大抵汲取前朝余润,尚未足以自立,这一点前人之述详备,不需赘言。但有一点往往容易被人忽略,即宋初书风不仅带着唐末以来的衰芜之气,且仍以追求法度与功力为善。当时名家徐铉善作篆书,就颇以暮年所得“喎匾法”为豪[9]。朱长文《续书断》“王著”条云:“初,太宗临书,尝有宸翰,遗中使示著,著曰:‘未尽善也。’上益勉于临学。他日又示著,著如前对,中使责之,著曰:‘天子初锐精毫墨,遽而称能,则不复进矣。’久之,复示著,曰:‘功已著矣,非臣所及也。’”[10]“勉于临学”是宋太宗著于“功”的重要渠道,在王著看来,功既著则书法之能事也毕,大有“山登绝顶”之意。就是这位自称王羲之后人的王著,据《负暄野录》所载其书取法虞世南[11];后来翰林院书体,“全然规摹王著”[12],由是“盛唐之旧法,粲然可见”[13]。
值得注意的是,在此之前已动摇、衍化唐法,书风自出机杼的杨凝式并未引起宋初书法家的格外关注,更没有树为典型的迹象。此中有其道理。盖宋初借以代替武人政治的文治基础尚未形成,也就是说,作为这一新兴政权主体的世俗地主知识分子尚未掌权,且宋初人士多不读书,文艺既非他们精力之所专注,更无非常之才能使其自立。宋初书坛,如这里所分析,落入唐人窠臼也就不足为怪。由此亦可知书法艺术的发展虽总体上呈循序递进之规律,仍不免时有辗转回旋,书法史的复杂性于此可见一斑。这诚然是宋代书坛的遗憾,就个人言之,它更是杨凝式“未能合唱于属于自己的时代的个人悲剧”。
幸得悲剧并未延续太久。首先是欧阳修对杨凝式的认可[14],接着王安石书继其踵武[15],苏轼、黄庭坚对杨凝式推崇尤甚,这一点读《东坡题跋》、《山谷题跋》在在可见。以上诸位皆是北宋文化之重镇,于今重温他们的相关言论,不但可以看出杨凝式对于他们的重要性,而且颇能明了他们于书学上的期待之所在,也正是因了这种期待,杨凝式才得以进入他们选择的视野。苏轼云:
颜鲁公书,雄秀独出,一变古法,如杜子美诗,格力天纵,奄有汉、魏、晋、宋以来风流,后之作者,殆难复措手。柳少师书,本出于颜,而能自出新意,一字百金,非虚语也。——《书唐氏六家书后》[16]
我们对上引材料稍事辨析,便可推见苏轼对书学的态度。面对唐法盛极难继的局面,要避免拾人唾余,傍人门户,惟有变法出新,因而苏轼有如上之论。苏轼的看法在当时极具代表性。台静农先生也认为杨凝式之所以能成为影响北宋第一等人物,正因为凝式书的“自出新意”[17]。然而,杨凝式书的“新意”究竟出在哪里?还需要我们作更具体的探讨。
上文曾说到晚唐以来世俗地主日渐取代门阀士族的事实,至此,我们有必要就这一事实所引发的文艺思潮的重大革命作进一步的说明。李泽厚《美的历程》“韵外之致”一章有至为深入的阐述。“世俗地主知识分子既关心政治,热衷仕途而又不感兴趣或不得不退出和躲避”的矛盾性格,从中唐的萌芽而逐渐分化,经由晚唐、五代到北宋沉淀,一面为建立封建宗法一体化而努力,另一面则“对现实世俗的沉浸和感叹倒日益成了文艺的真正主题和对象”,于是“人的心情意绪成了艺术和美学的主题”[18]。《韭花帖》正是这一思潮鼓荡下的产物。如前所论,它的舒闲容与之态,展现着杨凝式简静自足的意绪。此外,述养生之道的《神仙起居法》用笔漫不经心,有如“散僧入圣”;跋高士画迹兼怀其人的《卢鸿草堂十志图跋》,浑厚朴茂,极见沉潜肃然之意;在炎炎夏日里写就的《夏热帖》,则超逸俊爽,凡此都一一展示了杨凝式在不同情境下的不同心境。换言之,不同心境激发下的创作,又何情不恣,何变可限?这是杨凝式书迹面目众多的关键,真可谓“适意无异逍遥游”,由迹入神,求实得真。无论是题壁时的“似若发狂”,还是写《韭花帖》时的简静自足,我们都惊叹于杨凝式遇境即就的创作灵感,同时也从中感受到他极其强烈的自我抒写意识。也正是这一意识的凸显,使杨凝式更易与晋人交感,也就不难理解其书“脱然都无风尘气似二王者”。
这一风格合乎苏、黄等人的书学理想。苏轼说:
自颜、柳氏没,笔法衰绝,加以唐末丧乱,人物凋落磨灭,五代文采风流,扫地尽矣。独杨公凝式笔迹雄杰,有二王、颜、柳之余,此真可谓书之豪杰,不为时世所汩没者。——《评杨氏所藏欧蔡书》[19]
黄庭坚则云:
余尝论及右军父子翰墨中逸气,破坏于欧、虞、褚、薛,及徐浩、沈传师,几于扫地;惟颜尚书、杨少师尚有仿佛。——《跋东坡帖后》[20]
学书要须胸中有道义,又广之以圣哲之学,书乃可贵。若其灵府无程,政使笔墨不减元常、逸少,只是俗人耳。——《书缯卷后》[21]
苏、黄的书学理论以“二王”为准则,但并不囿于成法,突出其对逸气的推崇,反对俗化。讲求脱俗、追求雅化,是北宋人自觉的文化行为。自中唐以来,世俗地主阶级逐渐壮大,将其固有的俗气带入其参与的文化建设,造成文化趋俗的倾向,至唐末、五代,俗化趋于极端;随着北宋政权的建立,他们通过科举大量涌入官僚机构,成为统治阶级,“官僚化本身要求世俗地主知识化,向历史索取本阶级的文化遗产。这就有了雅化的要求”[22]。雅化在北宋全方位、多渠道地进行着。具体到书坛,苏、黄等人在这样的文化进程中所构筑的书学理论自然就十分强调对意趣、气韵的追求:苏轼“我书意造本无法,点画信手烦推求”(《石苍舒醉墨堂》)[23];黄庭坚“蓄书者能以韵观之,当得仿佛”(《题绛本法帖》)[24];米芾“意足我自足,放笔一戏空”(《答绍彭书来论晋帖误字》)等等[25],总之,不是法度、笔墨本身,而是人的精神内蕴成为衡量书学的首要的尺度,这完全适应世俗地主阶级雅化的要求。只有精神内蕴的深度厚积,才可发挥艺术的无限可能。在这样的旨趣观照下,被宋初人冷落的杨凝式就自然而然受到了重视。当然不只是理论的赞誉,创作上也自觉接受其影响。米芾《书史》就记载着王安石学杨凝式的事实[26]。苏轼《跋王荆公书》曰:“仆书尽意作之似蔡君谟,稍得意似杨风子,更放似言法华。”[27]黄庭坚也说苏轼书有颜、杨气骨[28],还说自已曾得杨凝式诗草而日临数纸[29]。流传下来的作品如苏轼的《寒食诗帖》以一种沉着奔放的笔调来写其风雨料峭的贬滴生涯;而黄庭坚的《跋黄州寒食诗》则在率意驰逐中处处流露着一个知音者的自负;他如米芾的《虹县诗卷》、《多景楼诗帖》,蔡襄的《陶生帖》、《脚气帖》……不必一一具言。皆居法不泥,心手双畅,追求意趣、雅韵。
从杨凝式到苏、黄诸人,其间雅称“梅妻鹤子”的林逋在书史上的特殊意义也不容忽视。《林逋诗书》是这位隐居诗人少数墨迹中的最显著者。前面说到《韭花帖》用笔简洁凝练,布局疏朗有致。这种风格,《林逋诗书》庶几近之。若仅限于此,谈不上什么进步。可贵之处在于“师其辞”且兼“师其意”。林逋以其清矍的品性构筑《林逋诗书》清逸劲峭的书风,抒写一个隐居者幽寂清苦的情怀:“先生可是绝俗人,神清骨冷无由俗。”(苏轼《书和靖林处士诗后》)[30]林逋度越于宋初衰陋书风之外,与杨凝式上下相衔,成为杨凝式与苏、黄等北宋名家之间重要的传薪火者。
三
最后,我们再探讨一下杨凝式在“韵”、“法”、“意”之间的取舍。殷荪《论杨凝式》一文曾称杨凝式为“中国书法史上能够放开胆量写字的文人书家中之第一人”[31],是否为第一,姑且不论,但就杨凝式借笔墨以浇胸中块垒,以书写心而言,此说是确当的。欧、虞、褚、薛作为唐初楷书四大家,他们的作品尽是庙堂丰碑,典重肃穆,雍容华贵,虽然也取法魏晋,却只是取“法”而舍了晋人的“韵”了。张怀瓘说:“若逸气纵横,则羲谢于献。”[32]可就是这个以章草未能宏逸,劝其父改体的王献之,却被看重“节之于中和,不系于浮放”(《帝京篇序》)的唐太宗视作隆冬枯树、严家饿隶。可见,注重“逸气”的宋人与“尚法”的唐人取向的差异。直到张旭《古诗四帖》、怀素《自叙帖》、颜真卿《祭侄文稿》、《争坐位帖》的率性纵横,才又算是放开写字了。所以,黄山谷又云:“盖自二王后,能臻书法之妙者,惟张长史与鲁公二人,其后杨少师颇得仿佛。”(《题颜鲁公帖》)[33]然而无论张旭、怀素还是颜真卿,都未将这种以书法抒写心情意绪的意识贯彻其书法创作之始终,惟有杨凝式能全然遵循自己的渴望,远离那被人走过的道路,以其特殊的“且吟且书,笔与神会”的创作风格,成就一种即将成为新时代风尚的书风。
与强烈的自我抒写意识相应的是作品形式的变化。杨凝式的作品多为书札,摒弃了唐代书坛所青睐的皇皇巨制。黄庭坚曾以“下笔便到乌丝栏”称誉杨凝式的超逸,而“乌丝栏”就是书札之一种。作品形式虽不是构成书风的本质所在,但也颇可说明问题。书札即兴的特质最宜于表现“人的心情意绪”,也最为文人书家“功夫在书外”的审美意识所认同。根据曹宝麟《中国书法史·宋辽金卷》“宋辽金书法史大事年表”的作品编年[34],可知北宋中后期书坛涌现出大量的诗札、尺牍、题跋,而此时正是“尚意”书风勃兴的时期。这类作品乃是研究书学者所公认的“尚意”书风的代表形式。可见,杨凝式“善作书札”的一面经苏轼、黄庭坚等人的发扬,已成为一时的风尚。这里,也许存在着模仿的成分,但毋庸置疑,它更多的是新审美思潮、新书风推动下的自然认可与接纳。
综上所论,杨凝式成为书道由唐入宋的枢纽人物,究其原因,就在于杨凝式不但以其创新书风让宋人在唐书法度已盛极难继的情形下看到新的曙光,而且在文化转型所引发的文艺思潮的变革中,在宋人追求雅化的目的中,契合了时代的要求。
注释:
[1] (宋)薛居正等撰:《旧五代史》卷128,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第1684页。
[2] (宋)欧阳修撰:《新五代史》卷35,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377页。
[3] 台静农:《台静农论文集》,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361页。
[4] 台静农:《台静农论文集》,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358页。
[5] 张兴武撰:《五代作家的人格与诗格》,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第11页。
[6] (宋)陶岳撰:《五代史补》卷1,四库全书本。
[7] 《宣和书谱》卷19,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440页。
[8] (宋)苏轼撰,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卷10,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316页。
[9] 《宣和书谱》卷2,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67页。
[10] 上海书画出版社编:《历代书法论文选·续书断》,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年,第348页。
[11] 上海书画出版社编:《历代书法论文选·负暄野录》,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年,第378页。
[12] (宋)黄庭坚撰:《山谷题跋》卷5,丛书集成初编本。
[13] (宋)苏轼撰:《东坡题跋》卷4,丛书集成初编本。
[14] 参见(宋)欧阳修:《欧阳文忠集·集古录跋尾》卷10《杨凝式题名》,北京:中国书店1986年影印世界书局本,第1369页。
[15] 参见(宋)黄庭坚撰,刘琳等校点:《黄庭坚全集·正集》卷26,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684页。
[16] (宋)苏轼撰,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卷69,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2206页。
[17] 台静农:《台静农论文集》,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359页。
[18] 李泽厚:《美的历程》,北京:文物出版社,1981年,第153页。
[19] (宋)苏轼撰,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卷69,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2187页。
[20] (宋)黄庭坚撰,刘琳等校点:《黄庭坚全集·正集》卷28,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776页。
[21] (宋)黄庭坚撰,刘琳等校点:《黄庭坚全集·正集》卷26,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674页。
[22] 参见林继中撰:《文化建构文学史纲——中唐到北宋》,西安:三秦出版社,1994年,第66页。
[23] (宋)苏轼撰,孔凡礼点校:《苏轼诗集》卷6,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236页。
[24] (宋)黄庭坚撰,刘琳等校点:《黄庭坚全集·正集》卷28,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750页。
[25] (宋)米芾撰:《宝晋英光集》卷3,四库全书本。
[26] (宋)米芾撰:《书史》,《全宋笔记》第二编第四册,郑州:大象出版社,2008年,第247页。
[27] (宋)苏轼撰,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卷69,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2179页。
[28] (宋)黄庭坚撰,刘琳等校点:《黄庭坚全集·正集》卷28《跋东坡帖后》,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776页。
[29] (宋)黄庭坚撰,刘琳等校点:《黄庭坚全集·正集》卷28《题杨凝式诗碑》,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756页。
[30] (宋)苏轼撰,孔凡礼点校:《苏轼诗集》卷25,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1344页。
[31] 殷荪:《论杨凝式》,《书法研究》1990年第3期,第11页。
[32] 上海书画出版社编:《历代书法论文选·书断》,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年,第164页。
[33] (宋)黄庭坚撰,刘琳等校点:《黄庭坚全集·正集》卷28,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758页。
[34] 曹宝麟:《中国书法史·宋辽金卷》附录,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