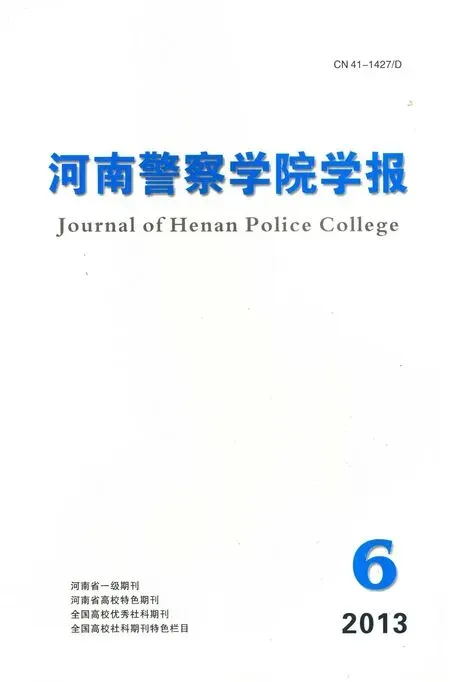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社区与社区警务
谭羚雁,于 群
(中国刑事警察学院,辽宁沈阳110854)
引言
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斯蒂格利茨认为,影响21世纪整个人类社会进程的有两件大事:一是由美国引领的科技革命,二是中国的城市化。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深入,中国经济在过去30年里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尤其是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加入世贸组织以来,中国城市数量、城市人口、城市化率的快速发展远远超过了全世界的预期。右边所示图表一组数据更直观地印证了中国社会所经历的城市化转型。
从图表所呈现的数据来看,中国城市化发展的速度之快是毋庸置疑的。根据最新统计资料显示,2011年中国城市化率首次突破50%。无可争辩的是,中国社会仅仅用30年左右的时间走完了西方国家花费近百年才完成的城市化进程。
何为城市化?一般来讲,城市化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指的是“工业革命以来,农村变为城市的复杂过程,即生产力进步所引起的人们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以及价值观念的转变过程,具体反映在人口聚集、经济发展、城区扩展、基础设施和社会服务改善、生活质量提升等方面。”[2]在2012年10月召开的第六届中国CEO年会②中国CEO年会自2007年诞生至今,已成功举办了六届,并形成了独特的品牌和价值资源。年会一直强调国际化特色,每年邀请全球最具影响力的管理大师到会,将最新、最前沿的管理理念带到中国,与中国的企业家们进行思想碰撞。上,国务院参事室研究员、国家统计局总经济师姚景源认为,“中国的许多问题都需要通过城市化来解决,城市化将是未来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然而,随着城市化越来越受到关注,一些不同的声音开始出现。越来越多的学者意识到城市化或许是充满迷惑性的“陷阱”。清华大学经济学研究所博士后杨伟鲁提出,“我们需要对‘虚高’或‘过度’城市化保持高度警惕”。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经济学家吴敬琏则将中国城市化的快速发展称为“摊大饼”模式,指的是城市建设以同心圆方式不断向外蔓延。这种描述实际上是在批判当今城市发展处于一种盲目、无序的扩张状态。

图1 1979年以来中国的城市化率①作者根据《2011中国统计年鉴》的相关数据统计汇总。
中国的城市化是喜是忧?该问题恐怕在长期一段时间内难以形成定论,但不容忽视的是快速城市化引发了各种复杂难解的城市秩序与社区管理问题。本文选取社区作为问题分析的出发点,把视角聚焦于中国城市化进程影响下的社区发展与社区警务,重新审视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社区警务所面临的发展困境与成因。为单位制度的空间表现形式,并具有强烈的居住——工作综合体特征。”[4]改革开放后,随着社会成员对单位依赖的不断减弱,社会成员大多搬离单位社区,开始涌入其他新型社区。三是城中村。“从居住形态上看,城中村是急剧城市化过程中原农村居住区域、人员和社会关系等就地保留下来,并被纳入城市范畴的局部社区;从社会关系上看,城中村仍以地缘关系和血缘关系为基础,并没有机会参与新的城市经济分工和产业布局。”[5]四是城乡结合部的边缘社区。从区位空间角度看,城乡结合部是“一种城市与乡村互相结合的特殊经济地理单元。该社区类型是不断蔓延和变迁的动态变化区域,具有鲜明的空间结构形态上的过渡性、经济结构与管理体制的二元型、人口构成的多样性以及经济社会发展的动态性等特征”[6]。五是新型房地产物业管理型社区。随着住房商品化的不断发展,社会成员在居住地域和空间选择上更具有自主性,该类型社区是人们通过自主选择住房区域而随机集结形成的新型社群。

图2 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社区类型及位置分布图①作者根据李东泉、蓝志勇论文《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社区发展的思考》中的相关资料修改整理。
一、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社区分类
1887年,德国社会学家滕尼斯在他的《社区与社会》一书中首次提出了社区概念,社区被看做是与社会相对的概念。滕尼斯认为社区好比是“简单的村落”,而社会相当于“超载的城市”。北京大学公共服务与社会管理研究中心丁元竹教授认为,“对于中国社会来说,社区建设象征着改革开放以来的巨大进步;社区建设的发展不仅是城市生活的基础,也昭示着一个国家的文明与成熟;社区因而也逐渐成为消化改革带来的各种社会问题的重要场所,如失业、老年护理、早期儿童保育、残疾人护理、公共安全甚至是环境保护等”[3]。随着我国城市化发展与转型的不断加速,城市社区发展逐渐呈现出类型多元化与结构复杂化的特征。
吴缚龙最早在1992年撰写的《中国城市社区的类型及其特质》一文中对城市社区进行了四种类型的划分,即传统式街坊社区、单一式单位社区、混合式综合社区、演替式边缘社区。在此划分基础上,结合蓝志勇、张鸿雁等学者的观点,我国城市化进程中社区类型可归纳为以下五种:一是旧城社区。即传统的城市街区,通常处于城市的中心位置与核心地段,周边公共服务配套设施完备,并拥有众多的文化保护区、新兴商业区和传统遗留区。二是单位社区。改革开放前的中国,社会成员通过隶属于一定的单位获取相应的资源与服务保障。“单位社区成
二、不同社区类型背景下社区警务面临的发展困境
当前,社区警务已成为西方最为流行的警务模式之一,并向诸多亚洲国家蔓延②Mike Brogden 在一篇题为《转型社会的社区警务》的论文中描述了一种现象,即“警务输出”或“警务移植”,指的是随着全球化影响的不断加深,欧美国家的社区警务理念逐步向处于过渡转型阶段的发展中国家渗透。作者指出,社区警务在输出过程中虽有成功案例,但也不可避免地存在水土不服问题,因此警务移植需要认真考虑“警务输入”对象的政治、经济、文化等特殊国情。。然而,社区类型多元化与结构复杂化使得社区警务工作困难重重,社区警务的理论构想与实践困境形成了难以协调的冲突。
冲突一:社区类型多元化给社区警务工作带来的挑战
理论层面,社区警务将着眼点投放到社区,强调解决社区问题,促进社区发展,旨在提高社区居民的幸福指数,不再把犯罪率下降看做是唯一的衡量标准。然而在实践层面,受不断扩张蔓延的城市化影响,不同类型社区存在形态各异的矛盾冲突,社区警务工作需因“区”而异,社区警务策略需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如今旧城社区的拆迁和重建已成为城市发展和社区建设的重要内容。旧城社区通常处于城市的核心地段,居民往往因旧城居住环境的便利和对旧环境的依赖,对旧城拆迁存在抗拒心理。城市郊区的土地征用和房屋拆迁问题也因城市化的扩张变得日益突出。由此,城市拆迁中维护社会治安秩序的警察执法活动与一些居民的拒拆行为经常成为矛盾和冲突的焦点。另外,在快速城市化的影响下,城中村、城乡结合部的边缘社区已成为外来流动人口的常住居住地,大量外来人口或外来闲散人员的涌入加大了社区发展的承载负荷,加剧了社区警务的工作难度。如暂住人口同籍聚居问题、出租屋或网吧等外来人口聚集场所内发生的治安事件使得社会治安形势更加严峻和复杂。单位社区内,随着越来越多的社区居民搬离原住所,留下的大多是失业人员以及老弱群体,社区民警在履行执法职责的同时要投入相当的精力用于关心和帮助困难群众,加强基层警务工作,化解各种社会矛盾。而对于新型房地产物业管理型社区,社区内居民大多是具有稳定工作的中青年群体,由于受教育水平、收入情况、价值观等的影响,他们往往更关注社区环境的改善以及社区民警的责任程度等。综上,不同类型社区存在形态各异的社区问题,警务工作与困难呈现出若干差异性。当然,上述各种矛盾冲突可能会同时交织于某一类型社区的警务工作中,对社区民警工作提出了更大的要求与挑战。

表2 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社区分类与社区警务①作 者根据李东泉、蓝志勇论文《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社区发展的思考》中的相关资料修改整理。
冲突二:社区警务工作中社区因素的缺失
早在19世纪初伦敦大都市警察建立的时候,罗伯特·皮尔就提出“警察即公众,公众即警察”的著名观点,这可以看做是社区警务的早期思想萌芽。理论层面,社区警务强调社区福祉需要警察与社区居民共同创造,其核心思想在于社区民警与社区居民之间积极互动,通过建立合作关系,共同维护社区治安秩序。因此,社区警务除了关注警察在社区发展上的履职,更要求社区居民对社区治安有较强的社区认同感、归属感和责任感,同时要求社区居民能够积极参与社区警务工作,形成对社区民警的高度信任和支持。然而实践层面上,不同类型社区在社区认知度、社区参与度以及对警察的信任度上呈现出差异性,社区警务工作难度加大。
一是社区认知度。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教授沃尔多夫认为,“社区认知不仅包括社区居民对其居住环境、邻里关系感情的认知与理解程度,而且还包括社区居民对其居住生活质量的满意度评价”。以黎熙元教授对广州旧城区、城中村、商品住宅区三类社区的数据采集为例,通过对五项问题②五个问题分别是“社区建设我也出了一份力”、“参与社区事务是每个社区成员的职责和义务”、“社区组织的活动对我的发展有较大作用”、“我会尽可能参加社区里的选举活动”、“我很关心报纸和电视对我们社区的报道”。的调查测量发现,“城中村社区居民的社区认同度最高,商品住宅区居民的社区认同度则略高于旧城区居民”[7]。袁振龙博士分别从“社区意识”、“社区凝聚力”、“社区依恋度”三个角度对北京市城乡结合部的A、B两个社区进行了调查,结果显示,“除了在社区意识上B社区高于A社区外,社区凝聚力和社区依恋度指数A社区明显高于B社区,而且对社区治安状况的评价A社区也高于B社区。因此得出结论:社区认同与社区治安存在正相关性,社区认同度越高,社区居民对社区公共事务更感兴趣,更愿意为社区贡献更多力量,社区治安也就越好”[8]。
二是社区参与度。社区参与也包含两层含义,“一是社区邻里间的社会交往,这是有利于邻里形成相互支持与信任的基础层面;二是社区居民的行为承诺,即社区居民愿意为社区问题的解决与秩序的维护贡献自己的力量”[9],而不是以一个免费“搭便车”行为者出现的。同样以黎熙元教授在广州三类社区进行的社区参与指标测量数据为例,“刚刚进入城市行政制度改造和城市生活圈的城中村居民的社区参与程度最高,而商品住宅区居民的社区参与程度最低。”[10]同上,袁振龙博士在测量北京城乡结合部A、B两个社区的参与度对社区治安的影响作用时,则从“社会参与”与“政治参与”两个维度进行了分析。研究结果显示,“A社区的社会活动参与较为积极,社区组织较为多样,但政治参与相对较弱,不够活跃;与A社区相比,B社区社会性参与不积极,政治参与则基本接近零;社区参与与社区治安同样成正相关性”[11]。从总体上看,尽管A社区在社区参与度上明显高于B社区,然而两个社区的政治参与要明显弱于社会参与。
三是社区对警察的信任度。美国西南德州大学刑事司法系主任昆特·舍曼教授指出,“社区对警察的信任对社区警务来说是最核心的”。相关研究表明,“公众对警察的信任能够提高警察效率以及警察行为的合法性,当公众认为警察合法或认为警察值得信任时,公众选择与警察合作以提升效率的可能性也大大增加”。[12]郭春甫博士分别对重庆市的A、B两个社区开展了对警察的信任度调查。A社区以老城区为主,属于合作式社区类型,行动者在社区警务网络中的地位和关系相关平等;B社区以城郊结合部为主,属于行政主导型社区类型,行动者在社区警务网络中缺少互动。信任度测量形成了六个等级量表:“完全相信、比较相信、一般、不太相信、很不相信、不知道”。比较发现,“两个社区在对警察信任度上存在明显差异。A社区对警察的信任指数偏高;但同时两个社区对警察的‘一般信任度’较为明显,‘不太相信’或‘很不相信’仍占一定比例;而且两个社区普遍更愿意信任官方警务行动者,对于私人成立、以营利为目的的保安服务公司,信任度指数最低。”[13]
三、社区警务发展中的社会资本弱化
何为社会资本?法国学者布迪厄最早在20世纪70年代从微观视角提出了社会资本概念,即个体拥有的可以有效利用的网络关系幅度或社会资本量。1988年美国社会学家科尔曼继续在微观层面上指出个体的社会资本拥有量与以下三要素成正比:个人参加的社会团体数量、个人的社会网规模和异质性程度、个人从社会网络摄取资源的能力。之后,美国学者帕特南从宏观层面把社会资本定义为“社会组织中的信任、规范、网络等要素,它们可以通过促进合作的行动而提高社会的效率”[14]。微观与宏观定义的共通之处在于两者都强调:首先,社会资本是一种利于个体与组织发展的有效性资源;其次,社会资本是能够容纳多元行动主体(包括个体、家庭、社区及其他社会组织)且主体间关系交错的社会网络;最后,社会资本的本质内核是基于规范、信任及网络而形成的相互合作。从以上三方面看,社会资本的基本内涵正契合了社区警务的实践需求,即关注警察与社区多元化警务主体的沟通与协作,而且这种合作关系需要建立在良好的社区规范、社区信任及社区网络基础之上。关于社会资本与社区警务的关系问题,西方学者已有相关研究。如,Kristin M.Ferguson& Charles H.Mindel(2007)运用社会资本理论分析了美国达拉斯社区的犯罪恐惧问题;Nathan W.Pino(2001)认为社会资本概念是测量社区警务策略实施有效性的有力工具;Alejandro Portes(1998)指出,社会资本有利于警察权威的维护;Jason D.Scott(2002)论证了社会资本与社区警务的相关性,并提出社会资本发展越良好的社区,居民对警察的信任与合作程度越高;Mark E.Correia(2000)研究认为,社区警务的作用发挥需要依赖社区环境,即社区因素(社会资本)对社区警务的影响要超出警察因素的影响作用。
就中国当前城市化背景下的社区与社区警务问题,社会资本理论提供了一种全新的思维视角与分析逻辑,即快速扩张的中国城市化引起社区社会资本的下降,从而导致社会警务中社区因素的缺失。

图3 中国城市化、社会资本、社区警务三者之间的关系逻辑
关系逻辑一:城市化引起社会资本的弱化
德国社会学家滕尼斯早就提出过对城市化的疑虑。他认为,城市化过程实质上是从小社区(Gemeinschaft)转变为大社会(Gesellschaft)的过程。“小社区里居民相互熟识,就如同村落似的家庭生活,简单、亲切、私密、内敛,有共同的语言、生活习俗以及强烈的认同感和归属感;而在大社会中,城市化伴生的种种现代文明使得原有的亲密关系变得离散,个人不再包容而是极端自利,邻里之间因过度封闭独立而丧失了联系纽带。”[15]滕尼斯甚至认为这是“社会的病态”,也有学者将其看做是“现代性的压榨”。城市化进程中社会资本的弱化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一是社区制度规范由“有序”走向“失范”,具体体现为:城市化进程中,原有社区文化传统受到破坏,原有社区规范逐渐丧失约束力,然而新的社区服务制度、社区居民公约、社区志愿者管理制度、社区成员代表会议制度等社区文明尚未建立健全,而且未能得到公众的认可和接受。二是社区网络的封闭性导致社区空间的“隔离”、“分割”或“孤立”。这种社区空间的极化现象主要归因于城市化所带来的旧城区的衰落和新城区的繁荣,社区网络对外来群体的排斥性日益增强,穷人社区与富人社区的分割界限异常清晰,社区网络关系打上了“区域性”烙印。三是城市社区人口异质性增强,“陌生人”关系状态有碍社区信任的形成。随着城市化进程中外来人口的不断涌入,城市社区原有居民往往视外来群体为影响社区安全的不安定因素,而且认为这些外来群体侵占了社区资源,影响了自身的生活质量。这种不容纳的心理或行为状态导致邻里间关系越来越疏远,彼此间的信任度越来越低。
关系逻辑二:社会资本弱化导致社区警务中社区因素的缺失
所谓社区因素的缺失,是指社区制度失范、社区网络封闭、社区信任的“陌生人”状态破坏了社区警务所需的社区文化基础。警察与社区是社区警务的两个根本要素,社区居民对社区的认知、参与社区事务的积极性以及对社区民警的信任和支持是社区要素的重要内容。城市化进程中的社会资本弱化使得社区警务异变为警察单方面的事务,淡化了社区的责任性和主动参与性。对此,西方学者的两个观点值得我们深思。观点一:在社区警务事务中,社区因素的影响作用要远远大于警察因素。有学者进行了“社区警务中警察因素与社区因素的重要性比较”[16]研究,认为社区警务的有效运行更多依赖社区环境要素。观点二:“橱窗装饰”[17](window dressing)的观点。所谓“橱窗装饰”,是指警惕社区警务异变为改善警民关系或提升政府形象的面子工程。有学者认为,社区警务的运行实务实际反映出“警务哲学”(philosophical policing)与“警务实践”(tactical policing)的冲突。“警务哲学”即皮尔提出的“公众即警察,警察即公众”原则,而警务实践中却很难践行警务哲学理念,理想架构演变成改善政府政治形象的“虚晃”。
[1]牛文元.中国新型城市化报告2012[M].北京:科学出版社,2012:11.
[2][4]李东泉,蓝志勇.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社区发展的思考[J].公共管理学报,2012,(1).
[3]Ding Yuan-zhu.Community building in China:issues and directions[J].Social Sciences in China,Vol.XXIX,No.1,2008.
[5]深圳市社会科学院课题组.深圳城中村的现状、问题与对策研究[J].南方论坛,2004,(3).
[6]范晓光.现状及其超越:城郊结合部研究的文献综述[J].江汉论坛,2008,(9).
[7][10]黎熙元,陈福平.社区辩论:转型期中国城市社区的形态转变[J].社会学研究,2008,(2).
[8]袁振龙.社区认同与社区治安——从社会资本理论视角出发的实证研究[J].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4).
[9]Rachael A.Woldoff.The effects of local stressors on neighborhood attachment[J].Social Forces,Vol.81,No.1,2002.
[11]袁振龙.社区参与和社区治安——从社会资本理论视角出发的实证研究[J].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4).
[12]Andrew Goldsmith.Police reform and the problem of trust[J].Theoretical Criminology,Vol.9,No.4,2005.
[13]郭春甫.社区警务网络中的信任分布及影响——以重庆市为例[J].重庆行政(公共论坛),2012,(3).
[14]Robert D.Putnam.Tuning in,tuning out:the strange disappearance of social capital in America[J].Political Science and Politics,Vol.28,No.4,1995.
[15]蓝志勇,李东泉.社区发展是社会管理创新与和谐城市建设的重要基础[J].中国行政管理.2011,(10).
[16]Mark E.Correia.Citizen involvement:how community factors affect progressive policing[J].Police Executive Research Forum,2000.
[17]Vic W.Bumphust,Larry K.Gaines,Curt R.Blakely.Citizen police academies:observing goals,objectives,and recent trends[J].American Journal of Criminal Justice,Vol.24 No.1,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