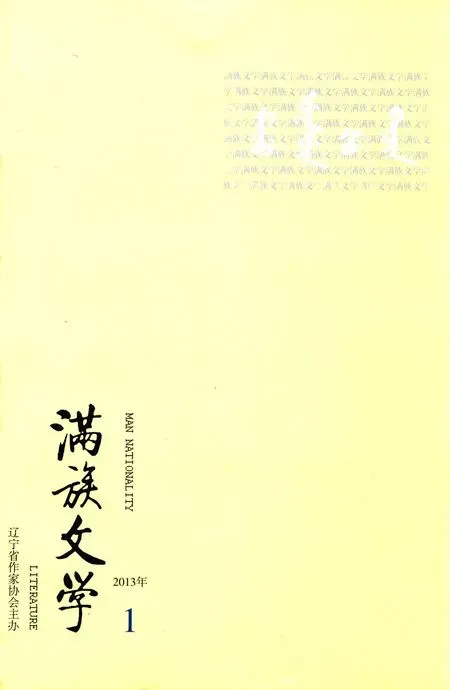心 经
石 杰
一
太爷爷死的那天,天上炸着轮好大好大的白太阳。
太爷爷把碗筷一撂,就对围坐在院心饭桌边尚未吃完午饭的家人和两个临时雇来的伙计说:“走走!都去!下晌儿把这片园子的梨摘下来,赶天黑装好,明儿顶着卯星进城,准他妈的能抢个好价儿!”太爷爷话音未落就先担起副空筐子走了。正午的阳光把他高高大大的身子缩成个小小的侏儒在地上晃着,两个筐子身前身后忙忙地摆动。
伙计和二太爷爷随后赶到时,太爷爷已经软软地躺在地上,身旁的一大摊血红得刺眼,像一朵盛开的硕大的红牡丹;脸却白得像天上炸着的那轮白太阳。
不远处有根胳膊粗细的断枝,枝头上,一嘟噜梨青青地挂着。
此后几年的时光里,太奶奶一直这样说:“俺当家的是为那嘟噜梨蛋子死的呀。”
二太爷爷就说:“是啊是啊,也怪,那嘟噜梨蛋子咋就没摔掉呢?”
太爷爷那年四十四岁。
太奶奶七天七夜哭号不休。第八天,浑身上下收拾利索,约了人打牌去了。
太奶奶那时怀着三个月的身孕。
太爷爷一死,家里没了管事的,主事的担子就落在了奶奶的肩上。奶奶那年二十四岁,二十四岁是女人的黄金岁月。奶奶有着高挑的身材、美丽的脸蛋,肩膀和屁股圆溜溜的,乌黑的大簪挽在头上,走起路来春风荡柳一般。只是那鼓鼓的胸脯,却用一条白布带子勒得紧紧的,像一块木板板。
“三七”那天晚上,天空墨蓝。奶奶把正房西间的大炕扫得干干净净,将玻璃瓶做成的煤油灯添了油,剪了灯芯,屋子里便黄澄澄地十分明亮。奶奶把全家人都召集到西屋里,只少了太奶奶一个。太奶奶到八里外的娘家村去打牌,十天半月的不回来是常事。
奶奶半倚半靠在地当央那张黑得发亮的老八仙桌上,立着的一条腿便显得格外修长。她用圆润好听的声音说:“爹这一走,扔下咱老小五口,实指望娘能收收心,可这几天你们也看见了。狗子呢,油瓶倒了都不扶的,可这日子总得过不是?往后呢,里边的事俺张罗着,外边就靠二叔叔了。”轻轻地咳了一声,乌黑的眸子静静地看住二太爷爷,土墙上映出半个美丽的剪影。
二太爷爷从屋角的模糊处收回目光,忙忙地说:“你看你看,赶着鸭子上架咧,你二叔叔是那拿事的人么?狗儿媳妇,你行咧,往后,这个家就靠你咧。唉,狗儿他不中用噢,啊——哈,俺可得回去睡喽。”一个大哈欠带出两点泪光,慢慢地下了炕,拐着左腿要回东厢房。
奶奶站直了身子,盯着二太爷爷在门口暗影处弯着的背,正了颜色说:“二叔叔既有这话,俺就多张罗着,俺还是爹活着时那句话,有活儿大伙干,有饭大伙吃。可有一宗,这钱得由俺经管着。要是由着娘的性子耍去,只怕是全家人都得喝西北风呢。”
二太爷爷的腿在外间门槛上绊了一下,哼哼唧唧地出去了。
一阵风从门开处刮进来,灯火猛地摇晃了一下。
爷爷不知什么时候靠在炕角睡着了,涎水从嘴边流到炕上,手里抓着几根秫节。
三爷爷一拳砸在炕沿上:“娘那个×,嫂,往后你只管在家张罗着,外头有俺老三呢,看哪个龟孙子敢欺负咱!”
奶奶低了头,两颗泪珠从那好看的眸子里滚落下来。
太阳从西山顶上红着脸儿躲下去了,晚霞铺得红一块紫一块的。
羊倌吹着口哨响着鞭儿从南山坡上快快乐乐地走下来,前面是一群雪白的羊。
屋后不远处的坟地里忽然传来太奶奶扯着嗓子的哭号声:“当家的呀,你咋就狠心走了呀,扔下俺孤儿寡妇的让人家欺负啊……你五斗谷子换来个狐狸精,这家业可是你用命挣来的呀……”声音断断续续地飘散着,房前屋后的,荡得人心慌。
爷爷在檐下石阶上玩秫节,忽然抬起脸痴痴地说:“姐,你听,娘在哭,娘为啥哭哩?”
奶奶站在院心冷冷地看着西天边上的火烧云,头也不回地对身后打扫院子的三爷爷说:“三儿,天怕是要变了,你去场上把梨盖盖,俺去羊倌那把羊接回来。”
三爷爷就放下扫帚,扛起两捆席子,大步流星地走了。
天色迅速地暗淡下来,院里的一切渐渐模糊。二太爷爷的东厢房里,传出醉酒人硬硬着舌头的唱:
东屋点灯东屋亮啊
西屋不点灯黑咕隆咚
墙上定个橛子梆梆紧哪
拔下来是个大窟窿
二
奶奶是十岁那年被太爷爷用五斗谷子换来的。
那天夜里,太爷爷正在看梨人的小棚子里半躺半卧地吸旱烟,隐约听得一阵窸窸窣窣的响声。太爷爷就悄没声地提上鞋,循着声音,蹑手蹑脚地走过去。冷不防一只腿被人抱住了,脚边响起一个女孩儿的尖叫:“爹!快跑!快跑啊!”不远处的一个黑影子跑了几步又折回来,咕咚一声跪在地上:“她大爷,俺屋里的快不行了,俺想给她请个大夫,俺是实在没有路了……闺女,还不快给人家跪下!”
女孩儿跪下了,不时偷觑太爷爷的脸,星光下看得出眉眼端正,太爷爷不由得消了几分火气:
“几岁了?”
“十岁。”
“属鸡的?”
“嗯,俺娘说,是金鸡。”
太爷爷暗自掐算了一下,不禁心头一动。他慢慢装上一袋烟,蹲下来,吸着,火星在暗夜里一闪一闪。末了,磕磕烟袋锅子,对那男人说:“俺看你这闺女满招人喜欢呢,眼下你也是难。俺有个儿子,小闺女一岁,属相对路。说话是糊涂点儿,性子可是再好不过的。你要是愿意呢,咱俩做个儿女亲家,俺这你先拿去五斗谷子。治病打紧,是不是?”两眼看住那个男人。
男人犹豫着,拿不定主意了,女孩儿却叫起来:“爹,俺愿意!俺要给娘治病!”男人的眼里就流了泪。
那时候太爷爷刚落成这座石头大院,奶奶走进院子时阳光和煦。
爷爷坐在檐下石阶上玩秫节,一道涎水在阳光里闪闪地亮,硕大的头上顶着几根黄黄的毛发。
太爷爷说:“下了三天雨,可巧今儿就晴了,狗儿他命不错呀。”
太奶奶正靠着门框用榆皮水抹头,眼睛一剜一剜地说:“瞧这丫头怪有主意的样子,谁敢保狗儿他日后不受老婆的气?”就让爷爷和三爷爷叫奶奶“姐”。
爷爷抬脸嘻嘻地笑着,涎水流到胸前的衣服上,样子傻呵呵的;六岁的三爷爷就在院心跳着叫着:“小媳妇,推磨子,黑了天,尿裤子。”
山里的光阴过得快,一晃儿奶奶就十六岁了,十六岁的奶奶已经出落成个水灵灵的大姑娘。太奶奶斜着奶奶挺挺的胸和圆圆的臀,对太爷爷说:“该给狗儿圆房了。”
那时爷爷刚刚过完十五岁生日,十五岁的人像个娃娃似的,晚上不敢一个人上茅房。
入夜,正房西间里,一灯如豆。炕上放着两条崭新的麻花被子。窗缝里有风吹进来,灯火便忽左忽右地摇曳。
爷爷着一件簇新的蓝布褂子,笑嘻嘻地在炕沿上玩秫节。奶奶把两个被窝并排挨在一起,低声说:“狗子,往后别叫俺姐了。”
“那,叫啥?”爷爷认真地睁大了眼。
“叫……叫秀儿。”
“秀儿?嘻嘻,不好听,不好听。”爷爷使劲晃着脑袋,“俺叫姐,俺愿意叫姐。”
奶奶坐在被子上,对着灯火发了阵子呆,听见院里太奶奶干干地咳嗽,就脱了衣服钻进被里,说:“狗子……进来。”
爷爷高兴了,上炕脱衣,口袋里掉出一块鹅卵石。奶奶捡起来,趴在枕头上,细细地把玩那石头上的花纹。纹络走着弯儿,一圈又一圈的,缠绕着,如指头上的斗。
院子里再次响起太奶奶的干咳,奶奶就吹熄了灯,把赤条条的爷爷拽进被窝,说:“狗子,你身上咋这么凉?”
爷爷不说话,鸡爪般的手抓住奶奶的乳房嘻嘻笑。
奶奶身上一阵燥热,心慌慌地说:“狗子,那阵儿娘把你叫到她屋咋说的?你要不听她的,娘明儿又得骂俺。”
爷爷仰头想了一会儿,瘦瘦的身子紧贴在奶奶肉乎乎的身上,头扎进腋窝,片刻,呼吸渐渐均匀起来。
鹅卵石滑到奶奶的身子底下,凉凉硬硬的一块。
月光清虚虚地洒满了窗纸,满世界已经没有声息。只剩了墙角的一对蟋蟀,一长一短,捉对儿地叫。
这年腊月,太奶奶产下一个死婴。
第二年春天,奶奶为三爷爷娶了媳妇。
三爷爷结婚那天风和日丽,村里人多来贺喜帮忙。酒席间,大门外乱哄哄地吵闹起来。原来,灶间的一个小伙子去当街的柴垛旁抱柴火,却见一蓬头垢面的老头在柴垛背后拉屎。小伙子说:“你这人真不知好歹,人家办喜事,拉屎也不看看地方?”
老头抓把茅柴揩了屁股,提着满是补丁的裤子,慢吞吞站起身来。自称是算命的,路过此地,观天相,看地脉,算命打卦,无所不能。
小伙子不信:“那你算算这家新媳妇日后生男生女?”
老头不言,低眉阖眼咕咕噜噜了一会儿,睁了眼叫道:“不得了,不得了,这家日后要出高人哩。”又以手搭额,望了一会儿大院上空,骇然变色,说:“这家房顶上罩着晦气,不日定有大祸临头。”
围观的人听了,也不在意,皆以为是胡说八道,一哄赶走了。
三奶奶人极清秀,细眉细眼地耐人看。更兼性情温柔,因此,阖家上下无不喜欢。那时三奶奶的肚子已经大起来,常常笨着腰身,拿着婴儿的活计,到奶奶的房中边做边说话。三奶奶有一手好针线,肚兜上绣着的花鸟如真的一般。
奶奶说:“三妹好福气呀,进门儿不到一年就有了儿子,哪像俺,都七八年了……唉,老了可靠哪一个?”声音凄楚楚的。
三奶奶就笑着说:“看嫂说的,哪好就是个儿子呢?是个赔钱货也说不定。”
奶奶说:“老人们常说酸男辣女,你这阵子爱吃酸的,准是个男娃呢。”目光在三奶奶的肚子上馋馋地一瞥,又怯怯地闪开。
三奶奶忙说:“嫂,俺的娃还不就是你的娃?再说你又不是七老八十了,日后生下十个八个也说不定呢。”说得奶奶噗嗤一笑,又愁苦了脸色说:“三妹你别哄俺开心了,俺这话也就是和你说,你大哥他哪像个男人啊?这么些年了,弄得俺也灰了心。”说罢,长叹一声。
三奶奶不由得红了脸。
日子就这样在平静中慢慢地流过去。不知不觉太爷爷已经去世三年。
太奶奶依旧时常在外边打牌,没大输也没大赢。
二太爷爷每日抱着老酒壶,在东厢房里喝得烂醉。
爷爷除了让人指使着做些看猪撵狗的事儿,就坐在檐下石阶上玩秫节。
三奶奶的儿子已经满院蹒跚。三奶奶一边洗衣做针线,一边看着儿子呀呀学步,脸上露出满足的笑。
只有奶奶和三爷爷,没黑没白地扑在果园里。家里紧缩开支又买下了一片苹果园。奶奶说:“等这片园子再收上几年,咱的家产在村里也就数得着了。”
三爷爷发狠说:“到那时,就再盖他几间大瓦房!”
太阳滚到了西山顶上,羊倌的口哨声和着鞭声在南山脚下响起来。
奶奶扬起红扑扑的脸,看看太阳,说:“哟,没经意就到了这时辰。三儿,你把家什扛回去,俺去把咱的羊接回来。”不等三爷爷答话,踩着轻快的步子下了坡。晚霞映在奶奶的身上,奶奶的背影很是好看。
三
二太爷爷有两件宝贝,一个是大肚子老酒壶,锡皮的;一个是小巧玲珑的白瓷酒盅。酒壶上满是污垢,已经脏得辨不清颜色了;酒盅却总是擦得锃亮。盅底上凸起半个浅褐色的玻璃球,倒上酒,下面便现出一张女人的头像。女人卷曲着长长的头发,无声地笑着,很年轻很妩媚的样子。酒波荡漾,秋波荡漾,二太爷爷就醉成了一滩泥。
二太爷爷年轻时在一家酒店当学徒,与店主的独生女儿相好。店主极贪,不甘心女儿嫁个穷光蛋,非要未来的女婿一夜间拿出一锭白银。二太爷爷年轻气盛,一怒之下,揣着仅有的一点儿积蓄进了赌场。天亮前垂头丧气地回到酒店时,店主把捆好的行李扔给了他。二太爷爷一言不发地走到酒缸边,咕嘟嘟饮了半瓢冷酒,扔了瓢,把一个死去的伙计留给他的老锡壶挂在腰上,背着行李,晃晃悠悠地出了门。半路上从崖畔滚下去,跌断了一条腿,从此走路拐呀拐的。二太爷爷从行李卷里发现了这个酒盅,知道是店主女儿给他的诀别之物,流下两行热泪。从此后,酒壶和酒盅就伴了他二十多年。
二太爷爷不提年轻时的事,仿佛他不曾有过年轻的时候。家里人也不提。二太爷爷几乎把所有的钱都买了酒,一个人在小屋子里慢慢地喝,奶奶看不惯二太爷爷这副样子,常常阴着脸,二太爷爷却似浑然不觉。
这天后晌,天气出奇的热,人们都在家里歇伏。
奶奶去村里剪鞋样了。
三奶奶的儿子在屋里睡觉。
三奶奶一边做针线,一边给儿子轰蝇子。
爷爷在檐下石阶上玩秫节。
三奶奶的儿子一觉醒来,哭着闹着要吃酸枣。三奶奶哄不住,只好牵着儿子的手上了南山坡。
南山坡的背后有一道沟,沟边上长满了酸枣棵子。三奶奶和儿子穿过果园来到沟边,就见沟底羊儿安闲地吃草,却不见羊倌的身影。三奶奶记得沟里的一个凹凹处酸枣棵子茂盛,就拉着儿子的手往沟里走。一只大大的花蚂蚱扑棱一下飞出草丛,儿子乐了:“娘,花蚂蚱,俺要在这逮花蚂蚱!”兴冲冲甩开了娘的手。三奶奶便一人朝沟里走去。
凹凹旁不远处的草丛被人践踏过了,一棵小小的山杏子树上,挂着一根鞭子和一件白布褂。三奶奶以为羊倌在凹凹里贪睡,刚想走开,却听见羊倌小声儿说话:
“你总束着它干啥呀?”
是女人的声音:“不干啥,俺愿意这样,俺想忘了俺是个女人呢。”
“解开让俺看看吧?”
不一会儿,一条白布带子卷曲着挂在酸枣棵子上。
三奶奶吓得几乎没了脉,转身急急地来到沟边,拽着儿子的手就走。儿子说娘俺不走俺在这逮花蚂蚱。三奶奶小声儿说快走沟里有条眼镜蛇。儿子就边走边回头看蛇追过来没有。
奶奶直到晚饭前才回来,走了一头一身的汗,说这天真热呢,人家非让多坐一会儿不可。三奶奶就说大热天的家里也没什么事。奶奶看住三奶奶说:“三妹,你这脸色咋这么不自在?”三奶奶的儿子不等娘说话就说娘看见一条眼镜蛇娘吓坏了。三奶奶忙拿话岔过去。
太阳火辣辣的,满院子里金光灿烂。
爷爷拿着一把秫节在石阶上睡着了。
二太爷爷醉倒在东厢房里。
一只要抱窝的老母鸡拴在院子里的桃树上,绕来绕去咕咕地叫。
两条狗卧在门前空地上耷拉着舌头喘。
果园里,土地晒得泛出了热气。两条蛇缠在一起,扭得惬意。三爷爷初看时心里快活,后来兴起,弯腰摸了块石头狠狠地砸去。恰中要害处,挣扎了一会儿,散开身子,双双不动了。三爷爷就将死蛇碎尸万段,在树底下挖了个坑,埋了,心想今年这树的果子准又大又甜。
入夜,三奶奶忍耐不住,把白天的事悄悄告诉了三爷爷。三爷爷听罢火起,呼地坐起身,披衣下炕,要毁了羊倌那狗日的。三奶奶就急得流眼泪:“好人呐,这事又不在俺身上,你干啥这么急哩?你若露出半点口风,就先杀了俺吧。”心里后悔说出来。温存了半天,三爷爷的火气才消了些,却一夜间翻来倒去地睡不着。
秋后,奶奶的身子显了出来。太奶奶狐疑的目光老是在奶奶的肚皮上走,又盯住爷爷。说:“狗儿媳妇,俺看你这身板儿不利索呢。”
奶奶说:“是啊,娘,四个月了。”
太奶奶说:“咋就没听你提起过?”
奶奶说:“娘忙,俺也忙,也就没顾得上对娘说。”
太奶奶斜着眼睛问:“你这肚里当真是狗儿的骨血?”
奶奶正了脸色说:“娘,这话你可要讲清楚,这孩子不是狗子的是谁的?”
太奶奶一时语塞,把爷爷拽到她屋里:“狗儿,娘知道你老实,你当娘的面说,这孩子果真是你的?”
爷爷素来有些怕太奶奶,这会儿不知太奶奶为何生气,只是痴着眼,张着嘴,口水流出一尺长。太奶奶又问了些更直白的话,爷爷却结结巴巴地说得不清不楚,气得太奶奶一巴掌扇过去:“俺咋就养了你这个废物!”又叫过三奶奶问。三奶奶心儿跳得通通的,眼皮也不敢抬起来,嘴里自然说不知道。太奶奶自此不常在外边住,小心留意,却也没发现什么,心里倒游移不定了。
太阳又一次从东山后出来。
羊倌吹着口哨,响着鞭儿,赶着羊群朝南山坡爬去。
奶奶一家人围着桌子吃早饭。
三爷爷嚼得下巴骨咯吧咯吧响,恨恨地说:“这羊倌,可恶着哩,明儿把咱的羊赶回来!”
奶奶说:“赶回来谁放哩?”
三爷爷说:“让二叔叔和哥放!”
太奶奶沉了脸:“你二叔叔那腿脚,能行?”
二太爷爷忙说:“行咧行咧。”
奶奶也就不再言语。过后装做无意地问三奶奶:“三儿咋这么恨羊倌呢?”
三奶奶措手不及,红了脸。
那时候二太爷爷刚五十出头,已经衰老得厉害了。腰钩钩着,一只腿拐呀拐的,走起路来很是艰难。到了山上,把羊自由自在地一撒,就舒舒服服地仰在那向阳的石头上了。从腰里解下老酒壶,一口一口地咂着。每逢喝得醉眼朦胧,就连声地唤:“狗儿,狗儿。”爷爷就到他身边坐下,口袋里满是大大小小的石头子。
二太爷爷眯缝着眼,对着太阳唠唠叨叨:“咳,要说这人哪,咱家在你太爷爷手里那是穷掉了底儿。那年山东闹大旱,六个月没见一滴雨。你太爷爷一个箩筐挑着你爷爷,一个箩筐挑着破烂家当,和你奶奶俩逃荒到了这块地面。到你爷爷这一辈,咱好歹也算有了几棵果树和二亩地,咳,不算富裕吧,也糊得上嘴了。你爷爷实指望着这个家大发,起五更爬半夜的,哪曾想年轻轻的就得了痨病。咳,生生是累的呀!你爷爷临死,一手拉着你爹,一手拉着俺,上气不接下气地说:‘儿啊,爹是完了,就看你们……’”声音变了,泪水从浑浊的眼里流下来,扭了脸,掩饰着,大声地咯痰。甩了把鼻涕又接着说:“你爹真是好样的,干起活来一头牛也抵不过,硬是攒下了这几坡园子啊。可谁知就、就走了呢?从那么高的树上,为了那几个梨蛋子?要说也怪,那嘟噜梨咋就没摔掉呢?你个傻小子是没见哪,你爹那脸煞白煞白的,眼睛睁得老大,不甘心呐,可不甘心又能咋着?……”
爷爷嘻嘻地笑着,似懂非懂,一条粘粘的涎水流到石板上。几只蚂蚁迅速地爬过来,嗅了嗅,又掉头而去。爷爷忽然指着脚旁的两只叫起来:“二叔叔你看,俩蚂蚁粘在一起哩!”
二太爷爷乜斜着眼醉咧咧地笑:“嘿嘿,你这傻小子哟”,一边朝自家的方向望了望。什么也没看见,却见两只羊在不远处交合。二爷爷就一仰脖,把壶底的酒咕噜噜倒进喉咙里,嘴里含糊不清地说:“这黑子啊,咋昨儿和大白,今儿又和二白?不像这人,你娘她只能和你爹,你媳妇就只能守着你。嘿嘿。”
太阳就快落下去了,余晖给山坡罩上了一片温馨。爷爷把羊儿追得满坡乱跑,二太爷爷在山坡上睡成了一个大字。
四
春天里,奶奶产下一个男婴。
分娩的头天夜里,奶奶正在炕上睡着,隐约听得炕沿下吱吱吱吱地作响。奶奶小心地擦着火柴,探头往下一看,一条粗而长的花蛇正沿着墙根摇曳前行。奶奶素来怕蛇,刚想叫人弄出去,那蛇却抬起头来,眼中露出顾盼哀怜之意。相视良久,蛇竟顺着炕墙爬上炕来。奶奶怕伤了腹中的胎儿,急以手护之,蛇却躲开腹部,辗转嬉戏,温存备至。倏忽醒来,哪有蛇的影子?下身却已经湿了一片。方知是梦,不觉红了脸。转身一看,夜色中爷爷口角流涎睡得正酣。
那孩子生得出奇的顺利。奶奶从果园回来,放下一捆干枝说:“三妹,俺这肚子咋有些不舒坦?”腆着身子进了屋。三奶奶刚从西厢房出来,就听奶奶“哎哟”一声,紧跟着就是婴儿的啼哭。
婴儿满月那天天气出奇的热。贺喜的人们脱了夹袄在院里吃饭,说这天简直不像是春天。奶奶在屋里仔细听着外边的动静,闹哄哄里就听人们说昨夜羊倌家失了火。那火真大呀,旺得少见,直烧得片瓦不留,连大门口的柴垛都烧了个干干净净。只是那羊倌,不知死活。羊倌是个单身汉,靠给村里人放羊度日子,人们就都感叹羊倌的命苦。
奶奶在屋里听傻了眼,当天午后便高烧不止。直烧得口角起泡,昏昏沉沉。人们说大概是开窗开门受了风寒,请来邻村的老中医,又到处去寻童子尿。折腾了一天一夜,才醒过来,却从此没了奶水,只好一口口嚼饭滤汁喂那嗷嗷待哺的婴儿。
不久后,人们就传说羊倌的旧宅闹鬼,有人半夜里听见女人哽哽咽咽地哭。还有一次,一个赌钱人夜间经过此处,看见一个黑影子在废墟里转来转去,看体态像个年轻女人。直吓得赌钱人头皮发炸,一步紧一步,慌忙逃去。老人们便叹息说:“羊倌怕是成了阴间的鬼了。”
这天中午,烈日当头。奶奶在院心桃树下洗衣服,奶奶的儿子在旁边的地上爬。不一会儿,太奶奶从大门外进来了,慌慌张张地瞥了那孩子一眼,匆匆走进东屋,插上了门。奶奶心里好生奇怪,趁着晾衣服的当儿,隔着窗子偷偷往屋里瞅。就见太奶奶正掀开柜子盖,好像往里放什么东西。
午后,太奶奶又出去了。奶奶放心不下,见家里人都在午睡,就悄悄进了太奶奶的屋。柜子锁上了,一把大铜锁守得牢。奶奶正想去炕席底下找钥匙,西厢房里响起三奶奶的咳嗽声,便急忙退了出来。
这天夜里,奶奶睡得正香,突然浑身一激灵,醒了。张眼四顾,屋里漆黑一片,却散着一股香味儿,隐约听得外间屋有说话声儿。奶奶看了看熟睡的丈夫和儿子,悄悄下了炕,小心贴近屋门,一只眼从门缝看出去,只见三点香火映着厨房里太爷爷的灵位,太奶奶正跪在地上,披头散发的,喃喃低语:“当家的,今儿是你的冥寿,俺从马神婆那讨来了这道符,你要是有灵呢,就收了它,看看狗儿屋里这孩子可是咱李家的后?若是,你保佑他长大成人;若不是呢,就灭了他,灭了他!”说得咬牙切齿的。奶奶打了个大冷颤,身子险些跌倒。就见一团火光燃起,忽高忽低的,映着太奶奶扭曲的脸。
奶奶悄没声儿地回到炕上,抱紧儿子,一头一身的冷汗。自此,无论走到哪里,儿子不离半步。这样子又过了半年,不见出什么事,一颗心倒渐渐地定了下来。眸子里是两块冰,脸上却常常挂着笑。
这一年收成特别好,然而土匪闹得厉害,看园人常常在夜间被绑了票。不看吧,又有人偷,一夜间丢个百八十斤是少的。不少人家捱不到果子熟就卖了。
奶奶看着满园半青不红的苹果,沉吟着说:“三儿,明儿咱也卖了吧?”
三爷爷说:“这样卖,亏哩。”
奶奶说:“远近就剩咱这一片,丢也丢光了,咋办?”眼睛看着三爷爷。
三爷爷就将一块土坷垃踢个粉碎,恨恨地说:“俺来看着,不信他土匪龟儿子敢把俺咋样哩!”三爷爷回到家,就从柜子后边抽出大刀片子,哗哗嚓、哗哗嚓,在磨石上蹭得锃亮,也不听三奶奶的劝阻,当晚便搬到园子里的窝棚去了。
那时候,奶奶的儿子已经满了一周岁。这孩子乖巧得很,会帮二太爷爷捉虱子,帮爷爷捡秫节,帮奶奶到鸡窝里取蛋。奶奶自然欢喜不尽,想自己晚年定是个有福之人;又盼儿子福大命大,便取名福儿。只是福儿不知怎么养成了一种怪毛病,每逢夜半子时必要去院心撒尿,一边用手指着房子上空叫:“娘!娘!房顶上有个大红圈圈儿!”奶奶顺着福儿指的方向看,却什么也看不见。
这天半夜,福儿又闹着去院心撒尿。奶奶抱着福儿,刚要拉厨房门栓,门却是虚掩着的。奶奶心里好生奇怪,记得昨晚临睡前插上的,怎么开了呢?莫非记差了不成?院子里黑漆漆的,二太爷爷的房里却隐约有点儿动静。奶奶将福儿送回屋里,哄睡了,蹑手蹑脚地到了二太爷爷的窗下,方格子窗里正透出粗重的喘息。奶奶一愣,轻轻舔破一块窗户纸,黑忽忽的小屋里,两个暗影正叠合在炕上,虫儿般蠕动……
奶奶轻手轻脚地回了自己的房,黑暗中脸上挂了一丝冷笑。
第二天早晨是个阴天,三奶奶照例早早起来做好了饭。饭桌上,奶奶刚端起碗来,忽然想起什么似地说:“昨夜里倒真把俺吓了一跳。半夜抱福儿出来撒尿,门栓不知怎么没插。”笑笑,扒了口饭。
太奶奶说:“是睡前忘关了吧?”目光在奶奶的脸上扫。
奶奶说:“ 想必是吧。”又说:“ 娘,俺看你这几天身子骨好像不大好,俺想过去睡呢,夜里也好有个人照应。”
太奶奶一边扒饭一边说:“不用,俺一个人惯了,多了人反倒睡不着。”
奶奶又说:“娘一个人睡不嫌孤单得慌?要不就叫三妹过去吧。”
太奶奶就有些变了脸色:“不用不用!俺一个人睡得安稳,俺倒天天担心你那屋进了贼呐。你也把你那东西收紧点儿,别让贼摸了去。”
二太爷爷紫涨了脸,低着头,闷声扒饭。
三奶奶的儿子哭着要吃鸡蛋,太奶奶就骂:“再哭,看俺不撕烂你那张嘴!”
晚上,天阴得狠。大块的云团从天上滚过,云层里响着一阵阵闷雷。
奶奶招呼家里人早早睡下,说这两天外边风声紧,别点灯熬油地招惹胡子。
三奶奶打发儿子先睡了,看着窗外坐了一会儿,心里不静,就摸黑到奶奶的屋里来:“嫂,不知咋着,俺这心里闹得厉害。”
奶奶正哄福儿睡觉,看着昏暗中三奶奶的身影:“三妹是担心园子那边吧?过几天咱就摘。”
“俺这眼皮子也跳得厉害。”
“左眼跳财右眼跳祸,你这是跳财呢。”
东屋里,太奶奶那边早没了声息。
东厢房里的二太爷爷哼哼了几句什么,也睡了。
村里不时传来几声狗吠。
突然,西坡方向传来一声清脆的枪响,顷刻间电闪雷鸣天黑如墨。片刻的死寂后,东屋里就先传出了太奶奶的嚎啕。全家人都听出枪声来自苹果园方向,不知怎么回事,战战兢兢地聚到了一起。三奶奶就拉着儿子在太爷爷的灵位前跪下,头磕得山响。
这天夜里,三爷爷在苹果园的小窝棚里照例磨了一阵大刀片子,黑暗中,刀刃闪着烁烁寒光。三爷爷如同酷暑中喝了碗井拔凉水,心里好不惬意。刚刚仰在行李上点着了烟袋锅,忽然想起已经一连几夜没回家了。念头一起,身上不觉一阵燥热。想这天阴欲雨,偷梨人今夜怕不会来,便要收了刀回去。忽然听见一阵脚步声由远而近,伴着两个人的说话声儿。一个说:“这小子家里可是有俩的,不知能不能白他妈的走这一趟?”另一个“嘘”了一声:“小心,别让他听见跑了。”三爷爷就提着刀轻轻地闪到窝棚外的一棵老树后。黑暗中,一高一矮两个人影儿正快步朝窝棚走来。三爷爷看准了前边拿枪的那个,“嘿呀”大叫一声,端刀刺去。后边那个见了,扭头就跑。三爷爷见地上躺着的这个还在挣扎,又双手握住刀柄,嘿嘿怪叫着往下扎,胡匪“嗷”地一声,浑身猛一抽搐,子弹从枪口射了出去。三爷爷应声倒地,神智却还清醒。此时,果园上空雷声滚滚,电光烁烁,两道闪电交叉着,刺出一片血光。三爷爷瞬间里竟想起了那两条埋在地下的蛇。
三爷爷从果园里被抬回来时已经奄奄一息了。初升的太阳照在他浑身是血的身上,一张脸白得和纸一样,三奶奶就哭得死过去好几次。到了后晌,三爷爷竟好像缓过来了,能倚着被子坐起来,两眼光光地发亮。二太爷爷说怕是回光返照哩。三奶奶忍住泪,把那独苗苗儿子叫到跟前,那孩子却害怕,不敢靠近。三爷爷就攥住儿子的手定定地看着,眼里似有泪光。再看时,目光散了。
那时刻天上炸着轮大大的白太阳,院子里一片哭声和钉棺材的叮叮当当响。爷爷坐在石阶上拿着秫节看着进进出出的人说三弟咋就死了呢?太奶奶哭得呼天抢地。二太爷爷在小屋里灌着老酒,终于醉倒了。
几天后,村里人又在传说羊倌旧宅的废墟闹鬼。有人夜里看见那女鬼在废墟上坐着,第二天,废墟上还留下了一堆纸灰。纸灰被一阵旋风裹着,旋得老高、老远,一直旋到山凹凹里去了。
五
三爷爷死了,家里似乎冷清了许多。太奶奶依然出去耍牌。二太爷爷依然喝得醉眼迷离。爷爷依然在檐下石阶上玩秫节。三奶奶除了洗衣做饭,就整日把自己关在西厢房里。果园里全靠奶奶一人张罗着。
时光不知不觉地流逝,福儿长到了六岁,三奶奶的儿子也已经十岁了。三奶奶的儿子不大听话,时常惹是生非,让人抓破了手脸回来;福儿却乖顺得很,然而不得太奶奶的喜欢。太奶奶背着奶奶骂他野种,赌牌赢了钱就给三奶奶的儿子买好东西吃。福儿不哭不叫,仿佛没事一般,受了委屈也不告诉娘。
瓢泼大雨连着下了三天三夜,这一天天气陡然转晴。夜里,福儿又出去撒尿,回屋时,奶奶便仔细插好了门。约莫过了半个时辰,隐约听得房门“吱呀”一响。奶奶坐起身,见爷爷和福儿都睡得熟,便轻轻下炕,蹑手蹑脚地到了东厢房窗下,从窗纸的一处破洞看进去,见两个人影已叠做一处。奶奶思忖片刻,悄悄到西厢房前叩响了三奶奶的窗棂。三奶奶披着衣服刚出房门,就被奶奶拉到了东厢房窗下,只听屋里有叽叽咕咕的说话声。
太奶奶的声音:“又喝多了?”
二太爷爷没有说话。
太奶奶的声音:“总灌你那猫尿。”
二太爷爷笑嘻嘻地:“酒好啊,喝了酒,俺就尽想好事喽。”
紧接着是一阵呱唧呱唧的响声,扑——,似乎枕头掉到了地上,然后是一阵粗重的喘息。三奶奶早软了腿脚,要回屋去,却迈不动步子。屋内的喘息渐渐平静下来,静了片刻,又听太奶奶说:“老二啊,这两天俺尽梦见你哥那死鬼哩,瞪着眼看俺。俺想莫非这事让他知道啦?俺不怕。他活着时还不尽冷着俺?就知道干活,睡得像个死猪似的,不像你……”又是一阵呱唧呱唧的声音。三奶奶的身子早抖成了一团,“啪啦”一声,碰掉了窗台上的什么东西,屋里立刻一片死寂。
第二天仍然是个大晴天,天上炸着轮大大的白太阳,无数的小白太阳就炸在地面的水洼里。太奶奶一大早就不见了人影。爷爷、福儿和三奶奶的儿子在院子里踩水玩。三奶奶推说头痛没出来。二太爷爷只在饭桌上露了一下面,胡乱扒拉一碗,回屋了。
奶奶站在房门口,久久地眯缝着眼,看着天上的那轮白太阳,慢慢走到东厢房窗外说:“二叔叔,今天是俺娘的生日哩,你老人家去接她回来吧。”
二太爷爷嗫嚅着说:“她的生日她不记得?等她自个回来。”
奶奶说:“俺娘赌上瘾了什么不忘了呢?”
二太爷爷就懒懒地坐起身,懒懒地换上水鞋,把酒壶往腰带上一挂,拐着腿走出门去。
外边是个太阳的世界,二太爷爷在门口停了停,仰头看天,眯着挂了眵目糊的眼。
天过晌了,二太爷爷没有回来。
太阳快落了,二太爷爷还没回来。
夜色慢慢地降临了,四周的群山也模糊了身影。奶奶站在檐下台阶上剔牙缝儿,三奶奶踮着小脚从大门外进来,说:“看不见呢,嫂。二叔叔不会有什么事吧?”
奶奶说:“十几里路的光景,能出什么事呢?”
三奶奶的眼皮就跳了一夜。
第三天又是个响晴天气,地面的水也干了许多。早饭后,奶奶叫了正和福儿耍着的爷爷,对刷碗的三奶奶说俺去看看,拾掇了一下,上了路。
通往太奶奶娘家村的路虽不算远,中间却要经过一段水塘。二米宽的路面只剩了蛇身似的一条,两边的塘埂若隐若现。奶奶走出了一头一身的汗,想寻个地方解手,忽然发现远远的前方有团黑糊糊的东西。急奔过去,好像是个人,头朝下扎进了水塘。再近,看清了黑袄黑裤和挂在腰间的老酒壶。爷爷就嘻嘻地笑了:“这不是二叔叔吗?二叔叔咋睡到这儿来啦?”急忙翻转过来,瘦脸泡得肿胀苍白。奶奶去附近村里寻了担架,抬回家时太阳已经上了头顶。太奶奶一直让鼓乐吹了三天三夜,自己披麻戴孝地守在灵前,眼窝干干的,没掉一滴泪。那时候正是摘梨的紧要关头,熟透的果子就掉了一地。
二太爷爷灵柩下葬的当天夜里,奶奶连日劳顿,睡梦正酣,隐约听见东厢房里传来二太爷爷硬硬着舌头的歌声。奶奶想二叔叔不是死了吗?怎么这歌声真真切切?再听,歌声没了,东屋里却传出太奶奶似哭似笑的声音:“老二啦,你个狠心的,甩甩袖子走喽!俺知道你是咋死的,你是为了俺哪。老三没了,你也没了,剩下俺个孤老婆子还活个啥劲哩?你慢走,等等俺,俺这就跟了你去……她不让俺活好,俺也不让她活好……老二啦……”奶奶静静地听着,黑暗中铁青了脸。拽过被子蒙住头,翻身睡去。
不知过了多久,恍惚间太奶奶款款地走了进来,笑眯眯地坐在炕边。
奶奶说:“娘有事么?”
太奶奶也不急,也不恼,轻声细语地说:“俺来取你的魂儿啊。”
奶奶急欲分辩,惶急中却发不出一点儿声音。惊醒来,一头一身的冷汗。仔细忆及梦中的情形,再难入睡,就坐起身来,披衣下炕,打开屋门走出去。冷不防被漆黑的灶间里一个软绵绵的东西撞了头,伸手一摸,“啊”的一声不省了人事。家里人急忙围拢过来,昏黄的灯光里,太奶奶头脸光光地悬在梁上,一根舌头伸得老长。急解下,身子尚温热,却没了脉。
那时候正是午夜时分,福儿一个人到院子里撒尿,一边叫:“娘!娘!房顶上有个大红圈圈!”
三奶奶哭着说:“福儿,都啥时候了,还不快过来看看你娘?”
福儿就把尿尿到了裤子上。
自此,奶奶的病一日重似一日,虽有三奶奶端汤送水的悉心照料,终不见轻。白天似睡非睡的,倒还安静;夜里简直就合不得眼。一会儿说太奶奶要来取她的魂,一会儿又说二太爷爷来了,穿着黑棉袄,正醉倒在东厢房的土炕上。那盏煤油灯一宿一宿的不敢熄灭,铁片子做的灯罩上烟灰就积了厚厚一层。巫医郎中的请了个遍,钱财水似的流出去,人却瘦得皮包骨头。三奶奶一个人支撑不住,家境就渐渐地衰败下去。奶奶自知大势已去,坚决不再请医吃药。三奶奶知道这里再住不得,就趁奶奶清醒时,商量了,卖了太爷爷留下的这座老宅,择一僻静的山凹凹,另盖起三间茅草房。
新房落成那天奶奶的精神特别好,一大早就起来了,让福儿扶着,在老房的院子里慢慢地走,说这日子过得可真快呵娘在这里一晃儿住了二十多年了娘进这院时比你大不了多少。你爹他是个不会疼人的,娘想家了夜里就猫在被窝偷偷地哭。一眨眼都是快死的人哩人咋就活得这么快?福儿说娘你不要这么说,明儿咱搬到新屋里去,娘的病就会好起来的,娘不要急。奶奶就说是啊是啊娘怎么会死呢娘还要住住新房是不是?一边就翘着脚跟朝西望。福儿说娘你看什么呢?奶奶说没看什么娘就是看看。三奶奶在灶间喊福儿还不快扶你娘进来?娘俩这才慢慢地进了屋。
早饭时,奶奶竟比平日多吃了半碗,说这萝卜丝炒得可真好吃。吃完了就靠在行李上,看三奶奶扫地,收拾屋子,一边要了梳子,对着镜子慢慢地梳头。
三奶奶说:“嫂,你今儿刚刚见好,可千万别累着了。”
奶奶说:“不打紧的,俺觉着今儿精神蛮好呢。三妹你把俺那身新衣裳找出来,俺这身上也该换换了。”三奶奶偷眼看奶奶,未见异常,以为她是要换新房了,高兴,心儿也就放下了大半。
那一天是个响晴天,天上炸着轮大大的白太阳。三奶奶蹬着石头在墙头晾了一会儿萝卜干,回屋时,奶奶正在柜里翻找什么东西。
三奶奶说:“嫂,你咋自个下了地?你要啥,俺给你找。”
奶奶慢慢地说:“俺想看看西坡那片园子的地契。”
三奶奶的心里咯噔一下。那园子早已经卖了,钱,盖了新房。旧宅的买主非要等交房那天才肯付钱,不卖园子,新房拿什么盖呢?这话自然不敢对奶奶讲,只好强笑着说:“地契放得好好的,嫂还信不过俺?”
奶奶这才不再坚持。
爷爷拿着秫节走进来,看见奶奶穿了新衣,流着涎水嘻嘻地笑。奶奶让爷爷坐到身边,柔声说:“狗子,你看俺今儿可还利索?”
爷爷笑嘻嘻地说:“利索,姐今儿好看哩。”一边动手去摸奶奶的衣襟。涎水流到衣襟上,白白亮亮的一条。
三奶奶见状,悄悄地退了出去。
奶奶定定地看着爷爷痴呆的眼,想说什么又没有说,好一会儿才幽幽地叹了口气:“狗子,俺这一走,家里就指望你和三妹了,你千万别只顾玩秫节,也帮三妹干点儿活。羊是没了,你要帮她侍弄好园子……”
爷爷用袖子擦了下鼻涕,脏脏的手比划着:“姐,俺会刨园子,俺有劲,俺能刨起个大土块!”
福儿在窗外连声叫:“娘你看啊,俺逮住一只花蝴蝶!”
奶奶就把脸转向窗户这边来。
傍晌午时,奶奶却有些吃紧了,闭着眼,只是一口接一口地喘气,三奶奶的心就缩成了一团,心想怕是捱不过午后了。奶奶却又睁开眼来,看着窗外慢慢地说:“娘,你来了?”三奶奶见奶奶说得真真的,不由得也看看窗外。窗外一片阳光,风丝也无,窗台上的一排花盆却哗啦啦一齐碎在了台阶上。奶奶喘息着说:“娘,别急……再容俺一会儿……”声音低得几乎听不见了。渐渐地,那气息成了一缕游丝,只是不断。三奶奶看得心痛,哭着把福儿拉到自己的身边:“嫂,你要是挂着福儿,就放心去吧。”奶奶突然间明亮了眼睛,神情专注地候着什么。只听得一阵飒飒的风声,一股大旋风从院门口旋转而入,急转的风柱裹着柴草、枯叶,尘土飞扬,风柱里夹着悠扬的口哨声。奶奶的眼睛猛地一亮,随即黯淡下去,断了气息。
那时刻天上炸着轮大大的白太阳,爷爷一个人坐在院子的阳光里哀哀地哭。
奶奶下葬的当天夜里,一家人正在堂屋灵前寂寞地坐着,忽然院里红光一闪,顷刻间东西厢房火光四起。全家人都知道是胡子来烧房了,屏着气息,声儿不敢出。火势直到鸡叫头遍才渐渐弱去,隐约听得二太爷爷在东厢房里唱:
东屋点灯东屋亮啊
西屋不点灯黑咕隆咚
墙上定个橛子梆梆紧哪
拔下来是个大窟窿
声音似哭似笑,悲凉哀婉,全家人听得毛骨悚然。
六
光阴照旧静静地流逝,日出日落,月缺月圆。
若干年后,山凹凹僻静处的三间茅草房院里时常坐着一白须老翁和一白发老妇。老翁在檐下石阶上玩秫节,老妇在院心树荫下纺棉花。
若干年后,远近传说着莲花寺里出了个道行高超的和尚,可解人危苦,度人困厄。和尚时常在寺里讲经,听过的人都说,法师是要我们心里清明、安静。只是这和尚有个怪癖,每逢夜半,必要去院心撒尿。
老翁老妇皆享尽天年,无疾而终。
和尚活了九九八十一岁。临终之际,拈一枯败莲花微笑,安坐而逝。
——读申平小小说《头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