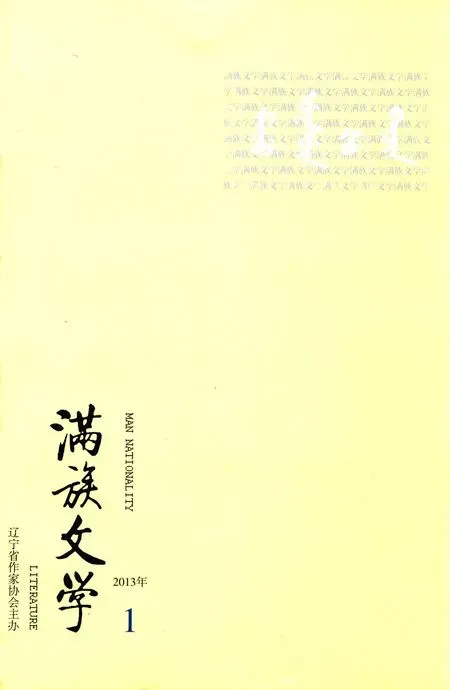回 家
康志刚
汽车一直往北走,来春看到了那条名曰石津灌渠(一条石家庄至天津的人工河,据说向天津供水)的小河沟。它从西面逶迤而来,又向东南方延伸而去,看不到头也看不到尾。河水呈淡绿色反射着鳞鳞波光,有两三个人在专注地垂钓,仿佛天塌下来也不去理会的。这条河是市区和市郊的分界线,再往前就是那个以梨花而闻名的肖家营村了。
然而,从前的田野上,如今伫立起大片的楼房;街道两边的店铺多了起来,挤挤挨挨、花里胡哨得让人目眩。行人和汽车也比几年前多出好多倍,哪里还有一点市郊的影子呢?完全成了省城的一部分。只有路西那家热电厂,差不多还是老样子,那两个高大巍峨的烟囱依然吐着乳白色的烟气,它们野心勃勃,像要把万里晴空给漂白似的。
“啧,才几年工夫呀,这里全变样了!”一个略带沙哑的声音从来春身边传过来,是小顺子大发感叹。来春点点头,却舍不得把目光从窗口移开。在里面呆久了,外面的一切都变得那么陌生而新鲜,像上帝创造的新世界。街道,以及在街道上行走的人、汽车,都因为漫天的阳光而生动起来,成为一幅富有动感的图画,也证实着这个世界完全是由太阳来点亮。
见他半天不吱声,小顺子将手伸进上衣兜儿,旋即,一枝“黄山”伸到他鼻子前:“来,老哥,解解闷吧。”
来春接了。在这个时刻,也许抽烟是一种非常不错的事儿。他在两种情况下喜欢抽烟,而且一根接一根地抽。一种是心里无比烦闷和焦躁时,另一种则完全相反,是遇到了什么舒心事儿让他兴奋难耐。今天的情形当然属于前者。
他刚吸了两口,就从前边传来司机毫不客气的制止声:“吸烟的乘客请把烟熄灭!车上不许吸烟!”
来春的手像烫着似的抖一下。何止是手,他的脸上乃至全身也像淋了开水,他一抬手将烟扔出窗外。小顺子也俯身将烟头用脚踩了,两人都像听话的小学生。来春抬头向大家笑笑,以示歉意,又赶紧将目光移向窗外。他非常敏感,害怕和人们的目光相撞,当他走出劳改场大门,重新置身于这个光怪陆离的世界时,就有了这种感觉。
汽车不疾不徐地在马路上行驶,上车和下车的人,鱼贯般地进进出出,车门开了又关,关了又开,无休无止。终于到了肖家营村,村西和村北各有一个站点,下车的是几位头发染成黄色和红色的小伙子,看样子像乡下来打工的。然后,汽车就顺着北外环向东驶去。可以看到梨花了,来春想。(肖家营地处滹沱河南岸,村北的河滩地上广植梨树,每到春暖花开,都要举办梨花节,盛况空前)。五年了,他都无缘欣赏梨花的芳容。他家院里就有一棵老梨树,是他出生那年爷爷亲手栽种的,为了让他一长大就能吃到甜梨。每年春天那一树的繁花,让他感到春天是那样的具体,具体得触手可摸。仿佛春天就是梨花,梨花就等于春天。今天,他却很失望,马路两旁依然是一个挨一个的店铺,店铺遮住了梨花的丽影。有乘客也伸长脖子向外眺望,但很快,眼里的期望熄灭了。春天在哪里呢?是现代都市,阻隔了人们和大自然的交流和亲近?来春困惑着,又沮丧不已。他对梨花那么在意,是因为在里面呆得太久了吧?五年,只是人生长河里的一瞬,然而,却在他心里划下了一道深深的印痕。汽车依然一辆挨一辆地驶过,只是,大货车明显多起来。
“操,咋这么慢?”小顺子嘟囔了一句,“瞧这样,没有俩小时甭想到俺们县。哎呀,咋这么多车哩?”一脸的不耐烦。因为是邻县,他和来春口音非常接近,只是个别字的尾音要往下拖一些,在来春听来就有些“侉”。他的话立刻引起了旁边几位乘客的注意,纷纷将目光射向他,眼尖的人,已瞥见他左胳膊上绣的那只深蓝色老鹰,还有他光亮的脑袋(他是那种梆子头,理成光头后格外滑稽而扎眼),挨他站着的那位穿戴时尚的中年女土,忙扭转身子往旁边靠了靠,下意识地将手里的小坤包朝怀里拢了拢,脸上流露出了戒备和鄙夷。
来春扭转头,瞥小顺子一眼,无奈地咂咂嘴。虽说从今天开始,他俩就是自由人了,和汽车上任何一个人一样都是共和国公民,是平等的。而且,也都脱下囚衣,换上了崭新的T恤,是前两天管教人员帮他们从外面买的。但他们的光脑壳儿,又不得不让来春心里头发虚。唉,这个小顺子,咋就一点不知道避讳呢?还是那个德性,大大咧咧的对什么都不在乎。再说,在里面呆好几年了,还差这么一会儿吗?你急什么呀?他在心里怨怼着小顺子,但,马上又理解了他。理解了,心里又不免滋生出一丝怅惘和伤感。自己要像小顺子这样该多好。而他呢,既盼着从里面出来,又害怕回家。不回家又能到哪儿呢?莫非,去南京找兰兰?
这种左右为难的痛苦,油煎火烧般地折磨着他,让他几乎快要身心俱焚。因而他盼着车开慢些,再慢些,当初,他不是就因为不想呆在家里,才做出那让他悔恨终生的傻事吗?
这么胡乱地想着,来春的脸越发的阴郁,凝重,像冬天快要下雪的天空。
“唉,我说老哥呀,一会儿就见到嫂子了吧?”小顺子的嘴巴总是闲不住,他歪着膀子凑近来春,从那双鬼精的小疤瘌眼里射出了一股子嘎气。他不明白,为什么一说回家,来春就愁眉不展。他应该高兴才对呀。
来春“嗯”了一声,不置可否。心里却很感激小顺子,明白他是让自己开心。小顺子是因为打架和抢劫进来的。人常说多行不义必自毙,那一次,他和他那帮小兄弟在镇上喝酒,从饭店出来,小顺子朝迎面开来的一辆小车扔酒瓶子,耍横(在酒精的作用下他真以为这个世界就数他大了),也该着他栽,偏巧,那是县公安局副局长的车。于是新账旧账一起算,才被抓进来了。虽说乡派出所长是他铁哥们,更是他的“靠山”,平时没少在一起喝酒,打麻将,当然,在麻将桌上,小顺子总是输多赢少。但在这关健时刻,人家却把自己头上的乌纱帽看得比什么都重要,自然是丢卒保车毫不含糊。在里面,他依然是“头儿”,也称“狱霸”。只要是人扎堆儿的地方,就有“头儿”。监舍也概莫能外。但他惟独对来春好,说和他对脾气。每当他那帮小兄弟给他送来烟和茶,他少不得让来春品尝。来春也透过他的“嘎”,看到了几分侠义,对朋友掏肝掏肺的,一百一。这也正是他可爱的一面。这人呵,本来就是个复杂的动物,很难简单地说是好人还是坏人。
看来春的脸依然绷着,小顺子又打趣道:“好呀,今晚上让嫂子好好服侍服侍,咱可是当了好几年和尚——”他忽然打住,没有像在里面那样天马行空口无遮拦。在里面,他谈得最多的就是女人,也就是男人和女人那点事儿。也难怪,正值青春壮年,作为一个男人,他们突然中止了那种属于人本能的生活,而且又是好几年,任谁也是不好受的,像是打二茬子光棍,似乎比失去自由还要难捱。何况,在外面时小顺子身边总不乏美女相伴,他说,都是她们主动对他投怀送抱的,这也是他向人炫耀的资本。小顺子年岁不大,可讲起这个来却是个行家,他那沙哑的嗓音,还有几分市侩气的笑,仿佛最适合说这种话题。
如今,他们终于熬到头了,就要回归那种真正属于男人的生活之中了。他俩是一起被释放,坐的又是同一趟车,小顺子回家要经过来春他们县。他们先是坐公交到市里长途汽车站,然后再一起搭上开往县里的长途车。是的,他俩非常有缘。
如今坐车很方便,来春认为没有必要让家人来市里接他,早两天他就给父亲打了电话。小顺子则有另一种安排:“嘿,那帮家伙!本来要来市里接我,我说,你们干嘛费这个劲儿呀,一帮人,跟打狼似的。我又没少胳膊没少腿的,我要自个儿回去,咋来的咋回去!他们倒听话,只是,非要给我摆接风宴,在我们县最豪华的饭店,金星!我不赞成,这是干嘛呢,给我过喜事儿呀?他们说,还真是过喜事儿哩。还说,吃过饭,就带我去洗浴城泡澡,再找小姐按摩,再——嘿,说要让我好好解解馋,说这几年委屈我了,大头小头都委屈了!哈哈,你看我这帮弟兄,真拿他们没办法呀!不过嘛,酒可以喝,但那种事儿咱不能干!刚从里面出来,得规矩点了。”小顺子说完笑了笑,他的笑里透着喜悦,也有一点显摆。
来春却看不惯他那帮朋友的做法,太张狂!嘛事儿呀,也值得这么大张旗鼓地庆贺?多么光彩是不是?哎,如今的人真有意思呀。然而,他又不得不为小顺子有那么一帮贴心贴肺的朋友而高兴。他这一辈子,也值了!
来春也喜欢交朋友,这一点和小顺子是相通的。甚至,说他把朋成看得和生命同等重要,也不算过份。他是尝到了交朋友好处的。当初,如果没有朋友帮忙,他在村里怎么能当上电工呢?他们村紧临一条省级公路,因为交通方便,村里人办厂子的极多,有家具厂、板材厂、养殖场,电工自然就成了香饽饽——都离不开电。
就是因为朋友,香梅和他闹翻的。来春的交往圈子主要是电工,本村的电工,还有外村的电工,他们常常是兴之所致,吆三喝四地去其中一家,无论到谁家,都少不得好酒好菜一番招待,闹腾得越欢,这家人越有面子。刚开始,香梅还是有耐心的,给客人倒茶递烟,下厨房做菜,忙得不亦乐乎,客人满意,来春也有面子。只是,时间长了,她脸上再难露出笑模样儿。她是个喜欢清静的人。“看你们这帮狐朋狗友,一来了就喝酒,一喝就喝个醉蛋,又是往屋地上吐痰,又是擤鼻涕,烦死个人!”客人前脚走,她后脚就发脾气,嗓门子又大,丝毫不担心让客人听到。其实她说得过份了,人家往地上吐痰不假,并没有擤鼻涕。她一发怒,说了过头话,还不觉得解恨,又说:“喝,喝,就喝不死你们?挣这几个猴钱儿,还不够你这么糟害哩!”起初,来春还强压住心里的火气,向她耐心解释:干我们这个,没有交际咋行呢?他在村里没什么背景,之所以能捞到这个肥差,完全是凭了朋友的关系。因为在村里根基不牢靠,如果他不和工友们打成一片,人们就会排挤他,他休想再干下去!香梅却根本不买他的账,说她本来干一天活儿了,回来不但要喂猪喂鸡,还得洗衣做饭,哪有心思和精力再侍候他们,真是烦死个人!来春也试图让自己理解她,原谅她。然而,他又做不到:“你是成心不让我干了!”他以为凭这个理由,可以让她改变态度。他想错了,这个倔强而不肯服输的女人,不但没有一点悔意,反而越发恼羞成怒,说,不干就不干,挣那几个猴钱,把我也搭进去呀,我亏不亏!她话说得噎人,嘴角上还挂一丝冷笑。不,简直是狞笑,是把对方战胜后的快意和幸灾乐祸。谁说生活中没有敌人呢,有时夫妻两人,无意中成为不共戴天的敌人。
这之后,他和她开始了长时间的对峙。来春依然带朋友来家里,他不能因为香梅,让自己在朋友面前失掉面子。香梅呢,依然对客人爱理不理,有时还甩个脸子。其实,如果不干电工,来春也不会饿肚子的,他不是那种吃一锅屙一炕的松包,随便做个生意,日子比别人也差不到哪去。只是,他在村里就没有了面子。他把面子看得比什么都重要!看香梅没有改变的意思,来春就提出离婚。是真离,不是吓唬她。她死活不肯。离不成婚,来春就不愿意在家里呆,开始和工友们去城里的舞厅玩。在那里,他结识了兰兰。兰兰以南方女人特有的伶俐和柔媚,不但迷倒了和她接触过的所有男人,也把来春迷住了,迷得神魄颠倒。终天有一天,他脑子一热,携带着收村民的八万元电费,带兰兰离开歌厅,开始了他们的“浪漫”旅程。他们先后去过西安、南京和杭州。他们对人生没有什么明确目标,快活一天是一天,每天除了游玩,就是呆在旅店里缠绵,享受那种生理上的快感。除此之外,什么也不想,仿佛世上只有他们两人。来春这样做其实还有另一层意思,以此来报复香梅,并且逼迫她和自己离婚。他的愿望最终没有实现,当他和兰兰再从杭州赶往上海时,在出站口被认出来。作为全国通缉的逃犯,他上了互联网,于是一把锃亮的手铐将他的双手牢牢铐住。
顶多还有四十来分钟,汽车就开进他们县城。当然,香梅不会去汽车站接他的。也许父亲和弟弟会等在那里。他们村离县城只有二十里,又不堵车,眨眼间就会到家的。他想,自己可以先回去看看父母,然后,再思谋下一步如何走。当然,父母绝不会让他再离开家的,他们不是一直都在反对他和香梅离婚吗?可他的命运还是握在自己手里的。只是,有一个问题一直在困扰着他:香梅为什么就不肯和他离婚呢?他终究没有想明白。
“老哥,车到山前必有路,干嘛不能吃口饭呀,你咋还为这个发愁?想开点吧。”
小顺子的话,让来春心里既感到温暖,又让他陷入另一种痛苦之中。是啊,他回去干什么呢?对于这个问题,他在里面不止一次地琢磨过,但一直也没有琢磨出个结果。其实,那实在是因为有香梅的影子在干扰他的思维。问题是,他回去后总要干点事儿的。他还要生活,还要养家,而且,还要偿还,偿还他和兰兰挥霍殆净的乡亲们那八万块电费,那是他们的血汗钱啊。一想到这个,他的脸上就像着了火,恨不得再掴自己俩嘴巴子——当他把那八万块钱挥霍净光,似从睡梦中清醒过来时,他就伸手打了自己俩耳光。
他回答小顺子:“没错,车到山前必有路,反正得想法儿挣钱吃饭。”他把那个“钱”字咬得非常重,也非常狠。
小顺子点点头说,那倒是,那倒是。你看这个世道,还不是钱的天下!又说:“我回去呀,不能再干那个了。再干那个,谁也对不住。对不住爸妈,对不住俺老婆子,更对不住咱王队长!”王队长就是负责他们那个班的管教干部。在里面,他们统称管教干部为“队长”,狱警为“班长”。王队长是个大胖子,性情温和得像个老大妈,对他们关心备至。一想起王队长,来春心里一热,说,对,不能再干那损事儿了,再干,谁也对不住。小顺子说:“我呀,我要把我们村北那个加油站盘下来。我哥们儿已经和主家谈好了,别人至少八万,我五万就能拿下。”见来春不解地望着他,小顺子又一挤眼睛,笑笑:“嘿,咱一不逼人家,二不抢人家,是人家自己乐意。哎,老哥,你知道这是为嘛呢?”来春摇头:“不晓得。”
“这就是字号呗。我的字号出去了,没法儿的事儿!”小顺子说完,先哈哈大笑,紧接着又无奈地摇头,而那难于压抑的得意,让他下巴上那几根黑里泛黄的胡子也跟着颤了几颤。
是不是就因为小顺子在里面呆过,人们才越发惧怕他,把他当作个人物?这个世道呵,怎么变成了这个样子呢?来春在心里感叹。
“要不,老哥跟我干吧?我那帮小兄弟干嘛的都有。随便给你个活儿,也能让你吃口饱饭!比你干电工差不到哪去。”
小顺子说这个时,他的目光是真诚的,里面跳跃着热情的火苗。来春心里一热,嘿,这家伙,真够义气!没错,他的确把自己当作了好弟兄。他何尝不想跟他去干呢?因为,他实在不愿回到那个家啊,确切地说,是不愿见到香梅。
“老哥,咋样,想好了没有?要不,还是先跟我回去吧,咱今个儿好好喝几杯,我的接风酒不也是你的接风酒吗?”
来春愣一下,他想不到小顺子会向他发出邀请。他从内心里感激他的好意,认为这也不失于一个好办法,可以缓解他面临两难选择的痛苦。但他又不想去凑那个热闹,没那个心情。那热闹只属于小顺子。何况,他最终还是要做出选择的。
见他迟迟不做回应,小顺子朝他眨眨眼:“这有嘛不好意思的,晚上再往家赶呗,这么近,反正又不影响和嫂子——”
他摇摇头,说:“不是不好意思,我心里烦,哪有那个心思?”说着,却不敢看小顺子那双热情的眼睛,因为从里面喷出的火,非常容易将他溶化。不然,小顺子哪有那么多铁哥们儿,又哪来那么大的号召力呢。他忙将目光移向了窗外,路边的花草、树木像画片似的向后退去,形成一条流淌的河,那何尝不是时光遁逝的影子呢。然而在来春看来,退去的速度还是太快了。他愿意让它慢下来,再慢下来,就像这个飞快的人心浮躁的时代。只有慢下来,才能拉长他回家的时间。
再往前走,马路两边依然有高楼、商店,但明显比先前稀少了。行人也少了。这一切迹象都表明,汽车已经驶出市区了。但依然看不到庄稼地。在没有楼房和店铺的地方,栽种着花木和草坪。枝头缀满绿叶,草坪绿光浮动,在这川流不息的马路边上,让人多少还能感受到一缕大自然的气息。
小顺子终于闭上了嘴巴。他是在想那场即将到来的接风酒宴。他的小兄弟们点什么菜,喝什么酒。当然,这根本不用他操心,他们非常清楚他的口味,自然会让他大快朵颐,满足他那委屈已久的肠胃和味蕾。
汽车终于驶出市区,田野出现在他们眼前,麦田里绿波摇曳,蜂飞蝶舞,一股清新的气息透过窗口吹进车里。只是,这让人赏心悦目的麦田,却让两边的店铺切割得支离破碎。正是这些各色的店铺,已将县城和省城连在了一起,让人难觅田野的广袤和辽阔。车上的人少了许多。
终于,“X县汽车站”几个漆红大字,映进了人们的眼帘。
“老哥,你下吧。抽个空儿,一定去我家看看,可记好了?”小顺子和他告别,从那双小疤瘌眼里,流露出一丝恋恋不舍。
来春用力点点头,低声说:“好吧,抽空一定去看看你。我咋能忘了你呢?这一辈子也忘不了。”他说得有些动情,眼角早已发湿了。他狠劲地咽口吐沫,让自己冷静。是的,他们可是在一起呆了好几年的狱友啊,那是他们人生中一段最不堪回首最难捱的时光,惺惺相惜,这种特殊经历让他们难舍难分。
汽车缓缓地进站了。透过候车室的大玻璃窗,来春突然瞥见了一个熟悉的身影。他身子一激棱,像触了电。再仔细辨认,没错,正是他最不想见到的女人——香梅!五年不见,香梅比五年前憔悴多了。身上那件浅红色的长袖褂子,也让他感到眼熟,忽然想起,这件衣服她穿了好几年了。但看得出,她今天还是刻意打扮了一番的,新烫了头发,脸上也搽了粉子,却掩不住额头上那几条深深的皱褶。她的神色里,依然透出一种执拗和倔强。来春像让人扎了一刀,正是她的这种执拗和倔强,将他击败了呀。此刻,她正伸着脖子朝这里张望,她的身边,站着他们的女儿文文。文文也长高了一大截儿,已经成为一个大姑娘了。他赶忙扭转了头,他害怕她们看到他。
他的屁股没有离开座位,当车门嘭地关上时,小顺子惊诧地望着他。来春无奈地一笑,强作镇静,第一次对小顺子撒了谎:“下一站吧,那里好搭上回家的车,方便。”
这个仓促间编织的理由有些荒唐,小顺子竟然没有丝毫的怀疑。他说,好呀,那咱们还能再做会伴儿!
汽车很快驶出车站,顺着107国道继续向北驶去。来春的心,也随着车轮的转动不停地翻滚着。刚才的一幕,大大地出乎了他的料想。他问自己,你应该怎么办?你不回去,又能到哪里去?要不,对小顺子道出自己的苦衷,先去他那里呆上几天,然后,再给南京的兰兰打电话,告诉他自己出来了。其实,前些天他早写信将这一消息告诉了兰兰,只是,没有告诉她具体时间。很快,兰兰就给他回了信,她在信中说,她非常高兴他重获自由,她一直都在盼着这一天的到来,她也一直都在等他出来。他进去以后,她来监狱探望过他一次。待他判刑到了劳改场,她又来过一次。每一次,都给他带了许多好吃的,有南京板鸭,薰鱼,还有日常用品,每一次,都不忘给他带一条烟。她的处境还不错,先是在一家超市打工,去年,和一位女友合伙开了一家美容院,那是真正的美容,不再干那种龌龊的事情了。她要洗心革面,靠自己的手艺吃饭。她在信的末尾写道:待他出来后,如果他还爱她,他可来南京,和他们一起经营这家美容店(已和女友商量好了),或者,他们干脆把这个店买下来。如果不再爱她,那也没关系,来电话告诉她一声即可,他们好聚好散,各走各的阳关道,谁也不再干涉谁。
这的确是一个很不错的出路,如果他真的去南京,不难想象,他未来的生活一定会富足和幸福的,他还可以非常轻松地还清村里那八万元电费。兰兰是个非常能干的女孩子,她相信她的能力和诚意。
有了这个想法,他就将目光投向小顺子。小顺子如果是个细心的人,就会发现来春眼里流露出的妥协。“小顺子——”来春轻轻叫了一声。小顺子闻声扭过头,惊奇地望向他,眨眨眼:“咋了,老哥?”他忽然又打消了那个念头,忙说:“没事儿,我是说,咱哥俩真是有缘。”小顺子嘿嘿一笑:“老哥说得没错,真是缘分。”似有些动容,又说,“老哥,别回去就把老弟忘了。嘛时候有空儿,一定去我那儿一趟。咱哥俩儿放开肚皮喝,咱喝个够!”说着,两双手握到了一起。是来春先伸出手,小顺子赶忙握住了,握得很紧,生生地疼。
他真的在城北口那一站下了车。兰兰的身影忽地又浮现在他眼前,不过,她不再那么温柔可爱了。他走进高墙的大门,兰兰是有责任的。她怎么就没有责任呢?如果,当初她得知他在她身上挥霍的是全村乡亲的电费,对他进行一番规劝和警告,那么,他自会悬崖勒马回头是岸的,不至于一步一步地滑向罪恶的深渊。她被他的出手阔绰打动了,并且沉腼其中。是呀,金钱真好,可以让她得到想要的一切东西,包括高级化妆品,高档衣服,还有各种美味。她本来是个歌厅小姐,为了钱,不惜出卖自己的肉体和灵魂,在她眼里,钱就是钱,就是让人来花的,用现代的说法就是用来消费的。因此,她才不管这钱的来路呢。刚开始,是来春让她花,到后来,她竟然主动向他索要了。
如今,自己成了一文不名的穷光蛋,再去找她,她真的还会像信上所说的那样爱他吗?来春开始想这个问题了。他不得不这样去想。他又看到了她用他的钱,去商场消费时的那种贪婪——盯在某一件高档物品上,目光久久不愿离去,那双亮晶晶的眼睛似要从眼窝里探出来。这样想着,来春的脊背上顿时像浇了一盆冷水,禁不住抖动了一下身子。这个曾让来春痴迷和倾倒的女人,霎时间,摇身变为聊斋里媚人的狐仙,正张着猩红的大嘴,欲将他无情地吞噬。
他拦了一辆西去的公交车。当车门打开的一刹那,他一步就迈了上去,丝毫没有迟疑。他要给他们母女一个惊喜,失望后的惊喜才更是惊喜。他可以找个理由来搪塞她,说自己从省城直接雇车回家的。
他还想,人这一辈子,其实都是在还债,为还债而活着。有的债务,是不能用金钱来还清的,那是心债!
而心债是要用心来偿还的。
他们家的院落很大,足有半亩地。终于,他又看到了久违的梨花,雪一样白的梨花直晃他的眼睛。突然,一缕袭人的清香钻进他的鼻孔。梨花还有香气?从前,他只知道赏花,哪去理会这些一身素装的小精灵竟然还散发出沁人的芳香?
“来春,咱们分手吧。文文长大了。”香梅站在梨树下,对他说,“那时候我不答应你,是为了文文,现在,我为了我自己。”
“不能改了?”
“就这么定了!我要和他结婚。”
“他是谁?”
“我还是先不告诉你吧?不过,你和他认识。要是没有他,这几年我连死的心都有了。幸亏有他照料我们。这回,你可满足了吧?”
来春张了张口,像噎住了似的说不出话来。他痛苦地闭上了眼睛。
文文是个哑巴,刚过十八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