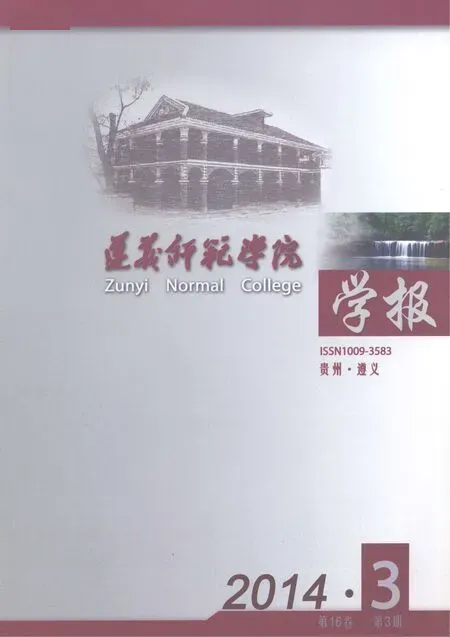红军长征时的遵义——《红军长征记》中红军对遵义的记述
颜永强
(遵义师范学院,贵州遵义563002)
《红军长征记》是记载长征历史的最早文献,它是由长征的亲历者执笔,由中国共产党组织的群众性集体写作,由于写作的时间是在长征后不久,书中所记录之事,都是写作者的亲身经历,因此其史料价值就比后来的一些回忆文献要高。1942年出版时,编者有这样的话:“本书的写作,系在一九三六年,编成于一九三七年二月,当许多作者在回忆这些历史事实时,仍处于国内战争的前线,因此,在写作时所用的语句,在今天看来自然有些不妥。这次付印,目的在供作参考及保存史料,故仍依本来面目,一字未改。”美国学者沈津在为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所出版的《红军长征记》一书的序中也说“执笔者写作的时间,离长征胜利仅有数月,途经之事,记忆如昨,历历在目。执笔者多半是拿枪杆子的,是向来不懂得所谓写文章,只是在枪林弹雨中学会作文字的人们,他们的文字技巧平常,但他们能以朴素的文字来写他们所经历的伟大的现实,故粗糙质朴、没有怎么加工的文字,不仅是可爱,而且必然是非常可贵的。因此,这本书对于研究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长征史来说,确实提供了第一手的资料,是一部珍贵的、重要的历史文献。”这部重要的历史文献中,有相当的篇目记述了红军在遵义的活动情况,不仅对解放军军史、长征史研究有着重要意义,对遵义地方研究也有着重要价值。
一、记录了红军进驻遵义市的历史场景
《红军长征记》记录红军从北渡乌江进入遵义到南渡乌江离开遵义,中间记录了“遵义十天”、“向赤水前进”、“会师遵义”、“邓萍牺牲”、“再占遵义”、“扩红”、“遭遇轰炸”、“过茅台”等一系列事件,将红军在遵义的主要活动线路和遭遇战斗的大致情况展示出来,尤其难得的是对红军长征中的衣食住行、吃喝拉撒等具体行动和生活状况有清晰的记录,如何涤宙《长征日记》中记录的遵义“确实不坏,大街上的铺子一间挨一间,只是比较大的铺子,家家门口挂了‘溃兵抢劫暂停营业’的牌子,从被刨坏的门板里,还看见柜台里零乱狼藉的模样,似乎要我们替他向王家烈算帐的神气。”“到川黔饭店,因为过早未开张,同掌柜商量,掌柜很客气,让我们上楼到雅座,代我们点了他们的拿手菜辣子鸡丁,醋熘鱼,血花汤等六七个菜,一边同我们谈着王家烈的苛捐杂税,弄得商人没法做买卖。”“今天开群众大会,成立遵义革命委员会……大会场在中学校的操场,人挤满了偌大的一个足球场。委员会产生了,一个红军里的遵义小同志也当了选,接着是朱毛的演说,群众今天才真正看见朱毛的庐山真面,‘毛泽东原来是个白面书生。’有的群众说,原来他以为朱毛一定是国民党所画的那样青面獠牙的,那末今天也许是个小小失望。大会结束,台上宣布遵义学生与红军比赛篮球。”“土城街上遍挂红旗,到处贴满了欢迎红军的标语。街上一堆一堆的人,踱来踱去,看传单,听讲演,大家睁着眼睛打量我们的全身,显示得特别自然、亲热,仿佛把我们看作‘王者之师’;但却也奇怪,似乎我们也和普通人一样,并没有一些特殊样子。”(谭政《向赤水前进》)《红军长征记》将红军进入遵义看到的情形,进入遵义后红军的活动,老百姓对红军的态度等全面的观察记录在案。作为作者行军中的日记,并非是为记录而记录,因此特别的真切,与后来长征叙述中的“层累的堆积”(顾颉刚语)不同,极大地丰富了红军长征的细节,使红军长征这一伟大的历史事件得到了更为鲜活、详细的呈现,也使人们看到长征时期遵义人民的生活状况及其对红军、王家烈地方军阀部队、国民党中央军等不同的态度。
二、记录了长征时期遵义人民的生活状况
贵州山多,河流湍急,过去曾有“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人无三分银”的说法,其地形地貌决定了经济不发达。红军长征决定放弃北过长江,转兵贵州,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国民党的中央军对这块贫瘠的土地防守薄弱。遵义位于云贵高原的边缘,在贵州虽然是第二大城市,但人民的贫困程度仍然非常之高,《红军长征记》的不少篇目,都提到了一般贫民缺衣少食,如张山震《瓮安之役》记载的一个事例:“‘红军先生沾个光,讨个钱儿,我们是干人儿。’咦!这是什么一回事呢?使我好不惊奇,原来是一个骨瘦如柴、脸似周仓样的青年男子与两个十八岁的姑娘,裤也未穿。难道是不穿裤打破封建吗?我怀疑地追问着。某同志回答道:不是呵!他们是可怜的穷人,靠挖煤赚饭吃,所以满脸都是黑,弄到几块钱又被王家烈苛捐抽去了。”雪枫《娄山关前后》也提到“十八岁的大姑娘没有裤子穿,五六十岁的老头子,屁股总是露着半边。”曙霞的《小茅屋》也写到“小茅屋,矮茅屋,入门要低头,睡卧难伸足,起风檐欲飞,雨来漏满屋。门前野草迷山径,屋后荒山暴白骨!绕屋凄凉无所有,旦暮但闻小儿哭。寒冬聚围小煤炉,火焰常灼小儿肤,茅屋梁上少包谷,家人下体多无裤!借问贫穷何至此?苛捐杂税如狼虎!兄弟流离爹娘死,卖儿鬻女偿不足。”从这些描述中,我们可以看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期贵州人民的生活状况,住不避雨、食不果腹、体无衣蔽,挣扎于社会的最底层,在恶劣的自然环境下,还会遭受苛捐杂税的盘剥。这些贫苦百姓,天然地有着对穷苦人的同情,有着对革命的向往,因此红军这支穷人的队伍能在此辗转立足、得以发展,与此密不可分。在李月波《我失联络》中的老百姓,虽然“六人吃饭,家无寸土,在此租人家的地要还租,一年不够一年吃,真不得了,难以养活一家人,也是没法子。”但是面对着失去联络、遭到围追堵截的红军战士,仍然是论辈认亲,帮助打听消息,带路送往部队。甚而至于“随便喊一声:‘当红军来哟!’壮年们就会跟着走的。那个时候,每个团一天总要扩大百儿八十个新战士来的。”(雪枫《娄山关前后》)
三、记录遵义的部分风物民情
红军进入遵义是在旧历一九三四年的腊月,他们在辗转中迎来了一九三五年的春节,但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红军战士看到的是“旧历正月初一,家家户户闭着了门,路上并无行人。”(李月波《我失联络》)“我”受着围追堵截的东藏西躲被发现后,“那民团队长手拿着一枝盒子枪,站在大门边,叫我快出去。……因为是正月初一日,讲封建,不能在人家家里用枪打死人。”这里记述的景况,正是缺衣少食的遵义人之风俗:不希望外人在家中过年,认为那样会把家吃穷。但如果来了,人民也不会驱赶。即便是抓人,也忌讳新年时在别人家中发生不愉快的事。这样的风物民情,在《红军长征记》中很多,涉及到方方面面,如对遵义城市建筑格局的记载:“遵义要算贵州第一号城市,街店相当繁荣,居民稠密,有新城老城之别,隔乌江有二十多里,直通大马路”(舒同《遵义追击》);如对遵义当时路况记载:“名字是马路,实在蹩脚得很,黏重的黄土,没有什么碎石或炭屑的培壅,受到雨水的冲洗,车轮的硬轧,一个窝洼,一个水坑,实在不容易下足,因此在五六天的贵州马路上,二路纵队行军,也成了问题。大家都想拣没有障碍的路间走,而障碍又偏偏不断的出现,于是纠纷就来了,我碰了你的手,他踏了他的脚,担子横过来横过去,拦住了两旁人不能前进”(莫休《一天——再占遵义城》);如对遵义人吸食鸦片陋习的记载:“大人们要鸦片烟的心比要其他东西的还要切,搜出来的三罐鸦片,分了两罐,一枝烟枪,转眼就不见了。”(何涤宙《遵义日记》)如对茅台酒的记载:“‘义成老烧房’是一座很阔绰的西式房子,里面摆着每只可装二十担水的大口缸,装满异香扑鼻的真正茅台酒,此外,封着口的酒缸,大约在一百缸以上;已经装好瓶子的,约有几千瓶,空瓶在后面院子内堆的像山一样”(熊伯涛《茅台酒》)等等。风物是人们对地域特色的事物最直接、最清晰的感受,在《红军长征记》的只言片语中,我们看到了1935年红军长征时期遵义人民的日常生活风貌,反映出国民党统治时期军阀割据、战乱不堪、民不聊生的社会生活特征。
四、记述了遵义部分山川河流的地形地貌
进入遵义,首先要跨过乌江,“乌江自古称天险,两岸壁陡,水深流急,不能通船,很难过渡。”“江面宽约二百五十米,流速每秒一米八,南岸要下十华里壁陡的石山,才能至江边,北岸又要上十华里之陡山,才是通遵桐的大道。渡口东西两旁、两岸都是悬崖绝壁。站在沿边一望,碧绿的江水,黑黑的石山,真所谓天险乌江!”(刘亚楼《渡乌江》)“乌江水深不可测,水势急流,有白鹅浑,水很轻,鹅毛也要沉入水底。”“乌江毕竟是天险!河的两岸是矗入云际的高山,山路也是崎岖难走,兼之河之对岸,还有王家烈的军队修了野战工事堡垒,控制着渡河点,扼阻我军。”(艾平《红四师强渡乌江的故事》)对乌江的记录,红军着重突出了它的险峻,及其水文特征的“水深不可测,流速也很大”,由此突出渡江的难度,“有利于敌人的扼守,不利于我们的渡河。”(艾平:《手榴弹打坍了一营敌人》)对娄山的记录,除险峻外,还记录了其人文景观:“娄山关雄踞娄山山脉的最高峰。关上茅屋两间,石碑一通,上书“娄山关”三个大字。周围山峰,峰峰如剑,万丈矗立,插入云霄。中间是十步一弯、八步一拐的汽车路。这种地势,真所谓‘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右翼的山,一律是悬崖绝壁;中间马路,敌人火力封锁了;左翼的山,虽然无路,然而还可以爬。先派一个坚强而又机动的连,由最左翼迂回到娄山关之敌的侧右背。主力则夺取可以瞰制娄山关的点金山。点金山之高、之尖、之陡、之大、之不易攀登,是足以使敌人有恃而无恐的。”(雪枫《娄山关前后》)红军在这样的环境中与敌人作战,其艰难险阻可想而知。不管是“云裹着山,山划破了云”的娄山关,还是“红花岗附近的密林高山,”或者遵义周围“错杂的矮山”,这样的环境不仅是红军长征时期辗转战斗于黔北、最终跳出敌人包围圈的活动空间,也是遵义人民世世代代生存的空间。在天堑变通途的今天,这些记录不仅强化了我们对红军长征的艰难困苦的直观感受,也对我们了解遵义的区域空间和特殊的地理现象有着重要意义。它告诉我们这种特殊的地域环境,对生活于兹的人类社会及其历史发展有着怎样的决定性的影响和制约,这种影响和制约,不仅在军事上、经济上、文化上,也有可能在人格生成、个性特征等方面都会留下一定的烙印。
五、记录了红军两次进遵义的气候情况
人们常说,一件事情的成功,靠的是天时地利人和。红军长征过遵义时,正是寒冬腊月。遵义的冬天,寒风刺骨,凝冻溜滑,给长时间的野外行军会带来极大的不便,更何况还要过湍急的乌江、赤水河。刘亚楼在《渡乌江》中就有这样的描述:“八个勇士虽然过去了,但交由他们游水时拉过去的准备架桥的一条粗草绳却因水宽流急以及身受寒冷刺激已无力气,无法拉得过去。……其中一个同志赤身冻了两点多钟,因受冷过度,无力游回,中流光荣牺牲。第一次强渡,遂告无效。”红军进入遵义时,其气候特征是“密云微雨,冷风冰水,”“江水浩浩、冷风袭袭,”“漆黑的夜,不辨咫尺”,红军在“残暴的北风”中忍冻过夜、架桥,这是怎样一项艰巨的任务啊!但红军在这样的环境下不但架起了浮桥,而且还在“大雾笼罩下隐蔽地接近了城乡,仅费了三发子弹,驱逐了他的一个小哨。”严寒的气候,给红军进入遵义带来了巨大的阻碍,也充分显示了“红军不怕远征难”的英雄气概。红军第二次进遵义城时,是“在一个阳光炎热的下午,”“太阳投下它那不着边际的光圈,被覆山岭树梢和鲜艳诱人的白的赭紫的罂粟花,绘出一幅美妙绝伦的春景画。润温的泥土被蒸得浮出秋云一般的轻雾,夹杂着窒人的怪味儿,人们都在迅捷地轮番两腿迈进。”(莫休《一天——再占遵义城》)以后,“在刚上山头的太阳光照耀下,在这无数群众的欢送与希望下,数万个红色战士,便沿着马路迈步前进了”。(小朋《残酷的轰炸》)而当他们再次往赤水河方向运动时,“可恨的天气在黄昏时下起大雨来了。”(熊伯涛《茅台酒》)忽冷忽热的贵州气候,“彻夜冷风刺骨”或“被太阳晒得满头流汗,”(艾平《第二次占领遵义城》)给行军的人们会带来多少灾难?这些叙述中虽然没有对气候环境的变化与红军活动的关系进行记录,但恶劣的气候曾给红军带来巨大的伤亡和牺牲是肯定的。
梳理《红军长征记》对遵义的相关记载,一方面是寻求遵义区域环境与红色文化的生成的密切联系。遵义是革命老区,它以红军长征在这里召开的“遵义会议”而名闻遐迩,是红军长征途中经过的最大的城镇。在这里,红军进城时受到到盛大欢迎,红军将士得到了大量捐赠的御寒衣物,队伍得到了补充,5000余优秀儿女踊跃参加了红军;因此,除了“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的遵义会议之外,这片土地给当年的红军留下了深刻的记忆,因此,《红军长征记》中有十多篇文章专门记述了在遵义活动的方方面面。在众多的红军战士的客观记录中,我们看到了他们对这片土地的悲悯和感激,在这片土地上的坚韧和激战,血与火、云和月都深深地烙印在红军战士的心底。我们深信,一个地区的光荣,总是与他的历史密不可分。另一方面,我们看到,这些客观而真切的记述,生动地展示了遵义人民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生活状况,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为我们研究地方史提供了形象的史料。我们可以将这些历史记录和地方研究连贯起来,考察社会的发展与变迁,将长征史的研究与地方文化研究紧密结合,深入挖掘长征文化的内涵,拓展长征文化的外延,更清晰地把握红色文化在不同地域中显示出的特点、形式,从而“深刻了解过去、全面把握现在、正确创造未来。”
[1]红军长征记[EB/OL].http://qw.duxiu.com/getPage?sw=%A1%B6%BA%EC%BE%FC%B3%A4%D5%F7%BC%C7%A1%B7,2013-12-23.
[2]张爱萍.从遵义到大渡河——张爱萍将军的革命回忆录[M].北京:作家出版社,19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