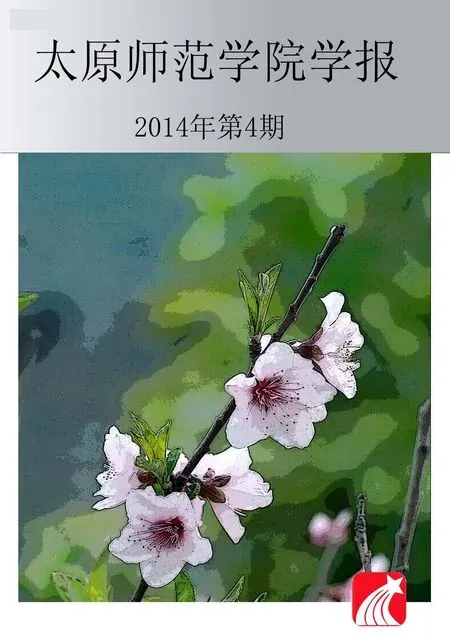论我国法院对我国民间对日索赔案件的管辖权
梁 樑
(四川大学 法学院, 四川 成都 610225)
论我国法院对我国民间对日索赔案件的管辖权
梁 樑
(四川大学 法学院, 四川 成都 610225)
中国民间对日索赔路途艰辛,在众多的对日索赔案件中终审无一胜诉,仅有四件和解,其余均以败诉告终。事实上对日索赔的诉讼全部在日本国内或美国展开,已成为追求正义和保障人权的巨大障碍,寻求对该类案件的我国国内诉讼已成为当务之急,并且是具备坚实的现实基础和法理依据的。
国内诉讼;管辖权;对日索赔
对日民间索赔是指针对日本二战期间发动的侵华战争致中国无辜平民受损,受害者以自然人身份而提起的要求日本政府或日本企业承担侵权所致的民事赔偿责任之诉。[1]日本二战期间在中国犯下了累累罪行,遗留的大量炸弹和化学武器,强制“慰安妇”,强掳/奴役中国劳工等问题至今仍严重伤害着中国人民的感情,为此众多中国受害者向日本国内以及美国等法院提起了赔偿诉讼,但基本都因国家无答责,国家主权豁免等国际法原则而导致败诉。尤其是2007年日本最高法院在西松建设案的终审判决中,认定中国公民个人的索赔权利在《中日联合声明》中已被放弃,使得对日民间索赔在日本法院得到公正判决的道路已被封死。尽管有众多学者认为这样的理由是勉强的,是日方寻求政治庇护的伎俩,但也使我们清楚地看到,寻求对日索赔的日本国内诉讼的胜诉就如同要求一个对自己的罪犯父亲奉若神明的儿子承认自己父亲的错误,并代替父亲承担相应责任一般,可能性几乎为零。而再看美国方面,美日两国间有着剪不断理还乱的政治因素。作为战略同盟,日本是美国远东战略的重要棋子。同时,两国在二战期间有许多相互牵制的索赔事件,比如有日本对美国的偷袭珍珠港事件,而美国则有对日本的广岛和长崎两颗原子弹。所以,完全为了自身利益,美国法院也不可能作出对日索赔案件的胜诉判决。而这样的现实状况就使得我们必须寻求新的途径,即对日索赔的国内诉讼。而在正式讨论该种诉讼的管辖权问题前,笔者认为须先对以下两方面问题予以解决:
一、对日索赔国内诉讼的先决条件
(一)原告享有国内诉讼个人请求权的依据
我国受害者对日提起的索赔依据是海牙《陆战法规和惯例公约》的第三条,该条规定:违反前述规则条款的交战方,在损害发生时,应对损害负赔偿责任,交战方对组成其军队的人员的一切行为负责。[2]日本法院认为该条是不承认战争受害者的个人请求权的,因此中国受害者向日本法院提起的诉讼应当由国家间的条约和外交途径来解决。对此解释需要弄清下述问题:战争后的赔偿有两种,一种是战败国对战胜国的国家间赔偿,称为战争赔偿,另一种则是战败国因对战胜国平民及其财产造成损失而进行的赔偿,称为受害赔偿。战争赔偿与受害赔偿在法律性质上不同,主要体现在赔偿的对象、赔偿的原因以及赔偿的方式等方面。就前者而言是一个纯粹的国际公法范畴的问题,而对于后者则不然。这是基于受害赔偿的复杂性得出的。中国民间的对日索赔是基于日本在二战期间的战争违法行为而引发的侵权赔偿责任,日本的这一国际侵权行为既违反了国际公法的规定,同时也违反了我国国内法的规定,对于前者的赔偿而言是属于国际公法赔偿的问题,而对于后者则是一个国际私法范畴的赔偿责任问题,因而我们得出受害赔偿(即中国民间对日索赔)是一个兼具国际公法与国际私法性质的赔偿问题。不同的法律性质必将决定原被告双方不同的法律关系,同时也会决定赔偿问题上个人请求权的有无、获得、存续并进而根据请求内容来确定相关的准据法。而反观日本法院在认定个人请求权有无时只考虑战争赔偿的国际公法性质,而完全不考虑受害赔偿中的国际私法性质,进而得出中国受害者个人无诉权的结论是牵强的。
从个人索赔权的国际实践角度看,1919年的《凡尔赛和约》第231条就已经规定作为战败国的德国及其同盟国必须对参战各国及其国民的一切损失和损害承担赔偿责任,从这一点我们看出,原先宽泛的战争赔偿已经区分为具体的国家间战争赔偿与国家和个人间的受害赔偿。同时就德国的实际做法而言,其在1953年同西方盟国签订的《伦敦债务协定》,1956年制定的《赔偿受纳粹迫害者联邦补偿法》和《为纳粹受害者赔偿联邦还债法》等都表明了个体索赔权的成立以及受害者方从战败国处获得实体救济的先例,甚至就日本自身而言,其与前苏联在1956年签订的《日本国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共同宣言》中也区分了战争索赔与受害索赔,因此我们可以认定个体索赔权与国家索赔权是两个均获得国际社会普遍认可的权利,两者共同存在并互不干扰。
日本的侵华战争除造成中国大量军人的伤亡这一直接影响外,还产生许多其他的非直接影响,譬如奴役劳工、屠杀平民、强制慰安妇等等,这些恶劣的故意行为对中国受害者的生命、健康、精神、财产乃至对外部的环境等都造成了极大的损害,而基于此产生的赔偿请求权是典型的私权利范畴,这些权利不因个人是否是国际法主体而受到丝毫的影响。因而也从一个角度证明了受害者对日索赔国内诉讼请求权的成立。
(二)国家有答责的依据
“国家无答责”是日本明治政府时期确立的,指的是当国家公职人员在行使职权过程中因自身违法行为而造成侵权损害时,受害者只能追究该公职人员个人的法律责任,而不能据此追究国家或公法人的责任,从而使国家得以免除其责任。这是日本在极端扩张这一国家政策下确立的对国家主权豁免原则和军国主义的宣扬,但其自身又是存在矛盾的。
日本虽在明治政府时期确立了“国家无答责”原则,但是随着君主主权逐渐被人民主权所取代,1946年的《人间宣言》以及《日本国宪法》中均已经否定了“国家无答责”,第二年出台的《国家赔偿法》亦贯彻了这一原则,也正是基于此使得日本法院在对待中国受害者的赔偿诉讼时作出了不同的判决,有的基于对历史问题的不正视支持了“国家无答责”,有的则基于对法律的遵从而否定了“国家无答责”,这样的结果本身就是自相矛盾且滑稽可笑的,如掩耳盗铃一般。
首先,就支持“国家无答责”的法院而言,他们所给出的理由是“法不溯及既往”,即相关的赔偿诉讼针对的是《国家赔偿法》生效前发生的国家行为,因而在认定事实时应当依据当时的法律作出判断,但是问题在于日本战前并不存在有关国家责任豁免的任何明确的法律规定,而仅仅是一些判例,而就作为大陆法系的日本而言,判例并不是其法律渊源,因而即使是辩称依据当时法律作出判断仍然是缺乏实体法依据的。
其次,日本所主张的“国家无答责”并非是日本作为国际法主体而享有的对国家主权的豁免,而是仅针对其本国国民而言的对公权力造成损害时的免责。从国民国籍而言,一方是日本国民,一方是中国国民,国籍不同不能适用。从具体行为而言,日本政府在中国实施的是所谓的杀光、烧光、抢光的“三光政策”,这是明显的违法行为,这样的法理基础是没有理由应用到日本对华的侵略战争上来的。
最后,“国家无答责”本身存在法理缺陷,1907年《海牙公约》宣言说明:在颁布更完整的战争法规之前,缔约各国认为有必要声明,即凡属其通过的规章中所没有包括的情况,居民和交战者仍应受国际法原则的保护和管辖,因为这些原则是来源于文明国家间制定的惯例、人道主义法规和公众良知的要求。该公约于1908年对日生效,表明《海牙公约》对日本是具有约束力的,再看日本在侵华战争甚至对整个亚洲国家战争中的种种行为,已经远远违背了《海牙公约》的有关规定,这也证明了“国家无答责”本身的错误。
二、我国法院对日索赔诉讼具有管辖权的相关问题
解决了上述两方面问题后,我们得以继续对我国法院是否对我国民间对日索赔案件具有管辖权进行进一步探讨,对此需要考虑以下三方面的问题:
(一)关于管辖适用原则问题
我国民事诉讼法在管辖问题上确立了“原告就被告”这一一般原则,倘若从这一点出发,那么基于涉案的日本政府或日本企业因为不在我国,因而我国法院不具有对其的管辖权。但是这一原则只是具有普适用,并非全适性,我国对一些特殊案件还确立了不同的管辖原则。日本对华的侵略战争是一种侵权行为,对于侵权行为的诉讼,是由侵权行为地法院进行管辖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条的规定,这一原则同样适用于涉外民事案件,我国司法实践中将侵权行为地扩大解释为行为发生地和结果发生地,而这两地中无论行为地还是结果地都是在中国发生的,所以据此认定我国法院具备管辖权是符合我国立法规定的。同时除我国之外,世界各国对于侵权行为之债也都规定了由侵权行为地法院管辖的原则,因此这也是符合国际惯例的,并非我国的一厢情愿或一家之言。
在此类案件由我国法院管辖的基础上,应当适用法院地法。这里的法院地法即我国法律,此结果会带来一些利好。如重要证据的保全,实现国际法上的公平正义原则,抚慰受害者的心灵等作用,因此由我国法院对此类案件进行管辖是既有法律依据又有益处的。
(二)关于法律溯及力问题
按照民事法律当中的侵权行为来认定我国法院具有管辖权,就必须考虑民事法律的适用期间,然而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日起,我国从战争侵权行为的发生到受害者的索赔起诉实际经历了两种法律体系的更迭,起初是中华民国制定的《中华民国民法》(1931年实施),之后即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有学者依据“法不溯及既往”的原则认为,既然战争导致的侵权行为发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那么对日索赔所依据的法律自然应当是当时的法律,同时1918年中华民国颁布的《法律适用条例》第二十五条:“关于因不法行为发生之债权,依行为地法。但依中国法不认为不法者,不适用之。”以及1927年的《法律适用条例草案》第二十六条:“因不法行为发生之债权,依行为地法。但依中国法不认为不法者,前项不法行为之损害赔偿及其他处分,以中国法律认可者为限。”也表明对日索赔选择在中国审理是有法律依据的。由此来看,似乎此种观点是可以被接受的。然而法律作为统治阶级的工具,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因此两个阶级性质完全不同的法律中的前者(《中华民国民法》)是不可能被沿用的,并且我国也于1949年2月发布了《关于废除国民党的六法全书与确定解放区的司法原则的指示》。笔者认为,这一方面是对旧的资产阶级性质法律体系的全盘否定,更是为对日索赔民事法律的适用提供了原则,即特殊情况下法律的溯及既往。法律的指引、预测等作用要求法律不溯及既往,但是这并非必然,相反,世界上许多国家均认为法律规范的效力可以有条件地适用于既往行为,即“有利追溯”。将对日索赔适用我国现行民事法律来处理,是既符合当前法律,又对相关各方面均有利的,因而应当按此处理。
(三)关于诉讼时效问题
按照1987年1月1日起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的规定,受害人可在二年诉讼时效期间内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这里的二年请求权的行使须具备三个条件:一是受害人知道损害;二是受害人知道责任承担人;三是请求权得以行使。前两点无须赘述,对于第三点而言,2004年福冈高等法院的判决认为,中国受害者请求权行使的起算点自中国的出入境管理法允许个人因私出国的1986年2月1日始,如果按此计算,那么至1988年2月1日止,中国受害者的诉讼请求权将消灭,这显然是不合理的。导致这一问题出现的原因在于请求权的行使有两方面的限制:一是事实上的障碍,这表现在中日双方在战争结束前敌对状态的持续以及之后外交、政治等各方面的原因。二是法律上的障碍,这体现在双方1972年的《中日联合声明》上,因为在这一声明中双方对战争赔偿的性质以及范围上有分歧,故在法律上导致了请求权行使的不能。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九条规定了诉讼中止的情形:“在诉讼时效期间的最后六个月内,因不可抗力或者其他障碍不能行使请求权的,诉讼时效中止。从中止时效的原因消除之日起,诉讼时效期间继续计算。”因此按照此条规定,因为请求权的障碍始终存在,因而中国受害者可以援引此条以解决请求权消灭的难题。
三、结语
民间对日索赔并非简单的法律上的诉讼问题,而是一个牵涉到更多的关于历史、政治、外交以及民族情感等复杂问题的大融合,中国受害者之所以矢志不渝地追求以诉讼的方式来实现自身的利益,关键并不在于希望借此能够获得多少经济上的补偿,我们甚至可以毫不夸张地认定受害者所追求的仅仅是一个公正的判决,一个精神上的慰藉,一个日本政府对历史问题的忏悔。而对判决的执行而言,实际上就是一个被告基于真诚悔过后的顺理成章的行为。然而现实状况是日本政府一再歪曲历史,伤害全世界人民的情感。日本法院虽然没有拒绝司法管辖,但是寻找各种理由不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因此由我国法院对相关案件进行管辖已成为一条必然的探索之路,而这需要整个社会的共同努力。在二战结束已近七十年之际,在受害者权利依旧没有得到保障,战争对他们所造成的创伤依旧没有愈合之时,我国法院肩负着重大的历史使命。
[1]郑文琳.对日民间索赔国内诉讼的法理基础及其法律适用——以“重庆大轰炸”案为例[J].甘肃社会科学,2012(1).
[2]王军杰,申莉萍.驳日本拒绝中国民间索赔的两个理由——兼评中国民间对日索赔18年诉讼实践[J].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4).
On Jurisdiction on the Part of Chinese Court on China's Civil Claim Cases for Compensation against Japan
LIANG Liang
(Law School,Sichuan University,Chengdu610225,China)
China's numerous civil claim cases for compensation against Japan face difficulties with none winning record from final judgments,and only four ended in reconciliation.The fact that all such lawsuits have been judged in Japan or USA has become an enormous barrier for seeking justice and guaranteeing human rights.Seeking litigation of such cases in China has become an urgent affair and it has sound realistic basis and legal basis.
litigation in China;jurisdiction;claim for compensation against Japan
1672-2035(2014)04-0049-03
D997.3;D925.1
A
2014-02-24
梁 樑(1987-),男,山西交城人,四川大学法学院在读研究生。
【责任编辑 张 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