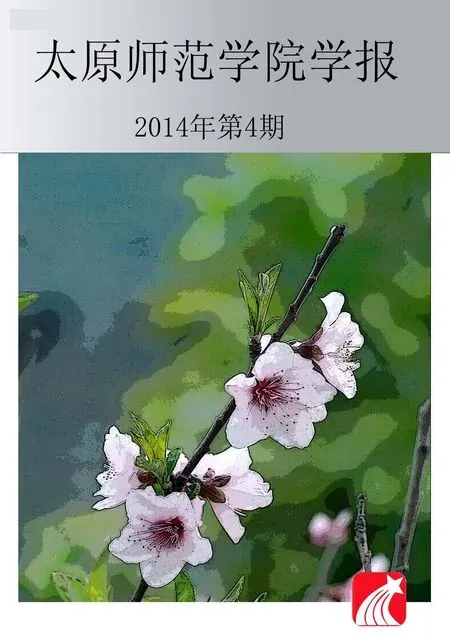大晟府词人“依月用律”考辨
(嘉兴学院 文法学院, 浙江 嘉兴 314000)
大晟府词人“依月用律”之说乃为史传所出,本为大晟府乐制的组成部分之一,但经夏承焘先生研究后,治宋词者均以言“依月用律”为讳,甚者踵事增华,将先生商榷之语增衍为崭绝之言。如:“至‘依月用律’及用中管为调,乃雅乐律法,隋唐以来,从未施诸燕乐。徽宗虽以律吕易诸乐名,然大晟诸人,仍未以月律入燕乐。……是知《钦定词谱》以月律分类,实属不伦。”(《唐宋词论丛·承教录》附录罗蔗园语)[1]233“大晟府的‘依月用律’,是当时人和后代人所津津乐道的,被看作是它的一大创造和贡献,但今人夏先生经过研究指出:宋词因为不能用四十八调中的三十五中管调,故不可能‘依月用律’,‘依月用律’之说,本出大晟诸人附会古乐……不足信也”[2]38,则把“宋词不用中管调”及不能“依月用律”之说进一步推向绝对化。其实,夏先生并未完全否定“依月用律”说。如:“雅言(万俟咏)与清真(周邦彦)同官大晟府,尝奉旨依月用律,月进一曲,其必非盲填如杨、陈可知矣。”(《唐宋字声之演变》)[1]77“宋词不用中管调,以管短一半则声高一倍,不易吹奏。今所见惟万俟咏《春草碧》一首中用中管高中(宫),盖咏在大晟府时依功令‘依月用律’之作。”(《〈白石道人歌曲〉校律》)[1]359-360“以予所知,今存宋人词中,其确用中管,且确为‘依月用律’,惟有仅见之一首,即万俟雅言(咏)之《春草碧》是。”(《词律三义》)[1]10即指出大晟府词人曾经依“月律”撰词,万俟咏《春草碧》即为其中一首。考之原说,夏先生《词律三义》虽立“宋词不依月用律”及“宋词不用中管调,故不能‘依月用律’”二条,但却以“以予考之,亦不尽然”的措辞委婉而出,非全然否定。事实上,“宋词不用中管调”,乃沈曾植氏即已疑之,云:“中管五调,宋世俗乐所无,独太常雅乐有之。”[3]3614夏先生尝以此问张尔田氏,张氏对以“宋词非不用中管,特用之者少耳”,先生允为“妙解”(《词律三义》)[1]8-9。故沈曾植俗乐不用“中管”之说,时人赞成者颇少。夏先生指出“宋词不用中管调”的同时,又指出万俟咏《春草碧》“确用中管”,为典型的大晟府“依月用律”之作。
“依月用律”是否施诸燕乐,大晟府词人是否依“月律”撰词,宋词是否存在“依月用律”现象,这些问题久经讨论仍未得到解决。有感于此,笔者不吝浅陋略作考辨,敬请批评指正。
一、“依月用律”徽宗朝之前即已用于燕乐
“依月用律”为古乐理论,然自载记以来,演奏实践或用或不用。宋人兴复古乐,有叹于虽有“月律”而乐工“止用黄钟一宫”的现状,“依月用律”逐渐施用于演奏实际。盖自真宗咸平四年起,至仁宗皇祐年间,“依月用律”逐渐施用于祭享郊庙、明堂等演奏实际。*据《宋史·乐志一》(浙江古籍出版社1998年影印百衲本),宋真宗咸平四年,太常寺言每祭享郊庙乐工止奏黄钟宫一调,乞随月转律。又据《宋史·乐志二》,宋仁宗皇祐二年五月,礼仪使言明堂所用乐皆当随月用律;七月,月律各从其音以为曲。可见,自真宗咸平四年起,至仁宗皇祐年间,“依月用律”逐渐施用于祭享郊庙、明堂等演奏实际。今据相关史料,考得“依月用律”在徽宗之前即已施用于燕乐。《玉海》卷一○六:
唐末旧声皆尽,惟大角传三曲。其鼓吹四曲,用教坊新声。车驾出入,奏《导引》及《降仙台》。警严,奏《六州》、《十二时》,皆随月用宫。[4]796-797
又《文献通考·乐考二十》:
国朝惟大角传三曲而已,其鼓吹四曲,悉用教坊新声。车驾出入,奏《导引》及《降仙台》。警严,奏《六州》、《十二时》,皆随月用宫。[5]1291
所谓“随月用宫”,亦即“依月用律”。《文献通考·乐考十六》:“(熙宁)十年,南郊,皇帝归青城,用《降仙台》一曲。”[5]1263《文献通考·乐考二十》:“熙宁亲郊,导引还青城,增《降仙台》曲。”[5]1291知至迟在熙宁十年“依月用律”即已施用于鼓吹乐。又据《玉海》卷一○六:
仁宗定雅乐,并及鼓吹,且谓“警严一奏,不应再用其曲”(减《导引》二曲)。亲制《奉禋歌》以备三迭。又诏聂冠卿、李照造词配声,下太常肄之。是年郊祀用焉。景祐二年八月辛酉,御制警严曲,名曰《振容歌》。十月乙卯,改《奉禋》。皇祐二年,享明堂,御制《合宫歌》(用[黄钟宫])。[4]797
《文献通考·乐考二十》:
仁宗既定雅乐,并及鼓吹。且谓“警严一奏,不应再用其曲”。亲制《奉禋歌》,以备三迭。又诏聂冠卿、李照造辞以配声,下本局歌之。是年郊祀,遂用焉。皇祐亲飨明堂,御制《合宫歌》。[5]1291
其中皇祐二年享明堂《合宫歌》所用[黄钟宫],正名为[无射之宫]。《景祐乐髓新经》:“[无射之宫]为[黄钟宫]。”(《宋史·律历志四》)[6]197《补笔谈》卷上:“[无射宫],今为[黄钟宫]。”[7]868此为九月之律,正好是“享明堂”之月律。据此可以推知,大约在仁宗景祐二年(1035)至皇祐二年(1050)间,就已将雅乐中的“依月用律”理论用于鼓吹乐。
今考鼓吹乐性质,实属燕乐范畴,其所用乐器金钲、节鼓、掆鼓、大鼓、小鼓、铙鼓、羽葆鼓、中鸣、大横吹、小横吹、觱栗、桃皮觱栗、箫、笳、笛等,均为燕乐乐器;其《导引》、《六州》、《十二时》、《降仙台》四曲所用宫调,如[正宫][黄钟宫][正平调][黄钟羽][大石调][道调][仙吕调]等(《宋史·乐志十五》)[6]380,实为“随月用宫”。
《宋史·乐志十五》:
自天圣已来,帝郊祀、躬耕籍田、皇太后恭谢宗庙,悉用[正宫]《导引》、《六州》、《十二时》凡四曲。景祐二年郊祀,减《导引》第二曲,增《奉禋歌》。初李照等撰警严曲,请以“振容”为名,帝以其义无取,故更曰《奉禋》。其后祫享太庙,亦用之。大享明堂,用[黄钟宫],增《合宫歌》。凡山陵导引灵驾,章献、章懿皇后用[正平调],仁宗用[黄钟羽],增《昭陵歌》。神主还宫,用[大石调],增《虞神歌》。凡迎奉祖宗御容,赴宫观寺院,并神主祔庙,悉用[正宫]。惟仁宗御容赴景灵宫,改用[道调],皆止一曲。[6]380
熙宁中,亲祠南郊,曲五,奏[正宫]《导引》、《奉禋》、《降仙台》。祠明堂曲四,奏[黄钟宫]《导引》、《合宫歌》,皆以《六州》、《十二时》。永厚陵导引警场,及神主还宫,皆四曲。虞主祔庙奉安,慈圣光献皇后山陵,亦如之。诸后告迁升祔,上仁宗、英宗徽号,迎太一宫神像,亦以一曲导引。率因事随时定,所属宫调,以律和之。[6]380
元符三年七月,学士院奏:“太常寺鼓吹局,应奉大行皇帝山陵卤簿,鼓吹仪仗并严更警场,歌词乐章,依例撰成。灵驾发引至陵所,[仙吕调]《导引》等九首,已令乐工协比声律。”从之。[6]380
据此,知仁宗、神宗、哲宗三朝鼓吹乐都是“依月用律”。罗蔗园先生所谓“至‘依月用律’及用中管为调,乃雅乐律法,隋唐以来,从未施诸燕乐”,实未曾考及宋代鼓吹乐所用燕乐曲调《导引》、《六州》、《十二时》等,完全是“随月用宫”(“依月用律”)这一史实。
二、大晟府依“月律”改定“燕乐诸宫调”
“依月用律”作为雅乐的基本法则,在徽宗朝不仅得到全面贯彻,甚至还成为改革乐律、创制新乐的基本乐法。*据《宋史·乐志四》(浙江古籍出版社1998年影印百衲本),政和三年四月,议礼局上亲祠宫架之制:“设十二鎛钟、特磬於编架内,各依月律。”又大祠宫架之制:“四方各设鎛钟三,各依月律。”政和七年十月,中书省言:“欲以本月律为宫,右旋取七均之法。”从之。自是而后,乐律随月右旋。此次“以本月律为宫,右旋取七均之法”,对后世乐律产生了极大影响,由此而成的乐律变化为学界所共识(杨荫浏《中国古代音乐史稿》,人民音乐出版社2004年版)。但是,徽宗朝成为雅乐共识的“依月用律”,是否真的对大晟燕乐产生了相应的影响呢?前贤对此多有否定,如罗蔗园先生即云“大晟诸人,仍未以月律入燕乐”(《唐宋词论丛·承教录》附录)[1]233。今考其说与史实不符。
按大晟府燕乐“依月用律”见于宋人原始史料,如:“(政和)四年正月,大晟府言:‘宴乐诸宫调多不正,如以无射为黄钟宫,以夹钟为中吕宫,以夷则为仙吕宫之类。又加越调、双调、大食、小食,皆俚俗所传。今依月律改定。’诏可。”(《宋史·乐志四》)[6]352依“月律”改定燕乐诸宫调,乃雅乐“依月用律”理论影响大晟燕乐的显证。宋人其他史料亦有记载。《宋会要·乐》五之三六、三七:“(政和)四年正月,礼部奏:‘教坊乐春或用商声,孟或用季律,甚失四时之序,乞以大晟府十二月所定声律,令教坊阅习。’仍令秘书省撰词。”[8]350-351《文献通考·乐考十九》、《宋史·乐志十七》同。据其所载内容,“礼部奏”乃“以大晟府十二月所定声律”,改定教坊乐;“大晟府言”则为依“月律”改定“宴(燕)乐诸宫调”。所述虽有所不同,其实均为依“月律”改定燕乐,实质是用“大晟律”强行统一雅、俗乐。[9]425-426《文献通考·乐考十九》对此有完整叙述,如:
政和三年,诏以大晟乐播之教坊,颁行天下。尚书省言:“大晟燕乐,已拨归教坊。所有习学之人,元隶大晟府教习,今当并令就教坊习学。”从之。(政和)四年,礼部奏:“教坊乐春或用商声,孟或用季律,甚失四时之序。乞以大晟府十有二月所定声律,令教坊阅习。”从之。仍令秘书省撰词。[5]1285
知政和三年大晟燕乐告成后,教坊隶大晟府管辖,大晟燕乐已“拨归教坊”,教坊乐与大晟燕乐合一。史料所谓“教坊乐春或用商声,孟或用季律”,亦即《宋史·乐志四》所谓“宴乐诸宫调多不正”。
大晟府依“月律”改定燕乐,还成立了专门的机构,曰“编修《燕乐》书所”。其依“月律”改定燕乐的直接成果,即“《燕乐》三十四册”的“镂板颁行”。《宋会要·乐》四之一:
(政和八年)九月二十日,宣和殿大学士、上清宝箓宫使兼神霄玉清万寿宫副使兼侍读编修蔡攸言:“昨承诏教坊、均(钧)容、衙前及天下州县燕乐旧行一十七调大小曲谱,声韵各有不同。令编修《燕乐》书所审按校定,依月律次序添入新补撰诸调曲谱,令有司颁降。今撰均度,正其过差,合于正声,悉皆谐协。时燕乐一十七调看详到大小曲三百二十三首,各依月律次序,谨以进呈,如得允当,欲望大晟府镂板颁行。”从之。[8]322
所谓“昨承……依月律次序添入新补撰诸调曲谱,令有司颁降”,乃指政和四年正月后大晟府依“月律”次序改定燕乐之事,这次“改定”工作约于政和六年十月前完成(《宋会要·礼》六二之五二[10]1720,《玉海》[4]778,《宋史·乐志四》[6]352),并有曲谱“令有司颁降”。又所谓“今撰均度……时燕乐一十七调看详到大小曲三百二十三首,各依月律次序,谨以进呈,如得允当,欲望大晟府镂板颁行”,乃指政和六年十月后大晟府以“今撰均度”依“月律”次序改定燕乐之事,这次“改定”工作约于政和八年九月之前完成,并有“大晟府镂板颁行”燕乐曲谱(《宋史·艺文志一》)[6]574。可以说,自政和四年正月以后至政和八年九月之前先后两次完成的燕乐曲谱,均为“依月律次序”改定而成。罗蔗园氏所谓“大晟诸人,仍未以月律入燕乐”云云,可谓不攻自破。
三、参与“依月用律”的词人辨正
对“依月用律”用于大晟燕乐这一点,前贤亦有甚相推许者。沈曾植云:“美成、不伐以后,则大晟功令,日趋平整矣。”[3]3607“美成”为周邦彦,“不伐”为田为,二人均为大晟府词人;“功令”即“依月用律”,沈氏认为在周邦彦、田为二人同为大晟府词人后,词曲创作便逐渐步入“依月用律”轨道。这种说法亦言过其实。考沈氏之说,实源于宋人史料。然宋人有关大晟府词人“依月律”撰燕乐词的记载,多系于崇宁年间。如:
崇宁间建大晟乐府,周美成作提举官,而制撰官又有七。万俟咏雅言……政和初,招试补官,置大晟乐府制撰之职。新广八十四调,患谱弗传,雅言请以盛德大业及祥瑞事迹制词实谱。有旨依月用律,月进一曲,自此新谱稍传。时田为不伐亦供职大乐,众谓乐府得人云。[11]87
(万俟咏)崇宁中充大晟府制撰,依月用律制词,故多应制。所作有《大声集》五卷,周美成为序。[12]655
迄于崇宁,立大晟府,命周美成诸人讨论古音,审定古调。……而美成诸人又复增演慢曲、引、近,或移宫换羽,为三犯、四犯之曲,按月律为之,其曲遂繁。[13]255
所谓崇宁间万俟咏(雅言)、周邦彦(美成)诸人“依月用律制词”或“按月律为之”,其时间划分过早。按大晟府依“月律”改定燕乐既在政和四年正月后,且其曲谱在政和六年十月前方告完成,则大晟府“依月律”撰燕乐词时间当不早于政和四年。
关于参与“依月用律”制词的人员,《碧鸡漫志》列有提举官周邦彦及制撰官万俟咏、田为等八人。今据相关史料考得大晟府“依月律”撰燕乐词时段乃在政和六年(1116)十月至宣和二年(1120)二月,历时三年有余。周邦彦(美成)任提举官,在政和六年十月至七年三月[14]116;田为(不伐)在“编修《燕乐》书所”(或称“燕乐所”)任制撰官,时间也在此时前后;万俟咏(雅言)自政和三年八月后直到宣和元年都在大晟府,这三人与“依月用律”制词时间相合。尤以万俟咏对“依月用律”制词贡献最大。按《碧鸡漫志》所谓“有旨依月用律,月进一曲”,乃在政和六年十月左右。如:
(政和六年)诏:“《大晟》雅乐,顷岁已命儒臣著乐书,独宴乐未有纪述。其令大晟府编集八十四调并图谱,令刘昺撰以为《宴乐新书》。”(《宋史·乐志四》)[6]352
(政和六年)十月,臣僚乞以崇宁、大观、政和所得珍瑞名数,分命儒臣作为颂诗,协以新律,荐之郊庙,以告成功。诏送礼制局。(《宋史·乐志四》)[6]352
《宋会要·乐》四之一[8]322、《玉海》卷一○五[4]778载“大晟府编集八十四调并图谱”,在“政和六年闰正月九日”,而至政和六年十月,“八十四调图谱”初步编成。《碧鸡漫志》“新广八十四调”、“以盛德大业及祥瑞事迹制词实谱”云云,与正史所载政和六年十月臣僚乞以“所得珍瑞名数”“作为颂诗,协以新律”相合。可知万俟咏与大晟府“依月律改定”燕乐曲谱及“制词实谱”工作均有贡献,其时段乃在政和六年十月至宣和元年八月间。
今依据宋人史料所载,大晟府词人中徐申、晁端礼二人均不可能“依月用律”。因大晟府“依月律改定”燕乐曲谱始于政和四年正月后,而大晟府词人“依月律”制词实谱时段在政和六年十月至宣和二年二月间。徐申大观二年十月即已离开大晟府[15]72,晁端礼卒于政和三年七月(晁以道《宋故平恩府君晁公墓表》[16]372,李昭玘《晁次膺墓志铭》[17]395),其时大晟燕乐尚未有“按月律进词”之说。故徐申、晁端礼没有“按月律进词”的可能,且史料中也没有徐申“按月律进词”的记载。《唐宋诸贤绝妙词选》卷七:“晁次膺,宣和间充大晟府协律郎,与万俟雅言齐名,按月律进词”[12]654,实属误传。又考周邦彦政和六年十月至七年三月入大晟府为提举官[14]116,其时虽值“按月律进词”时段,然查周邦彦所作词,大部分作于此时段之前。又据夏承焘先生考证,周邦彦词所用宫调之月份,与其词作所写月份不合,实际未尝“依月用律”(《词律三义》)[1]7-8。今考周邦彦词作,确实未发现有“依月用律”的痕迹。又据周邦彦晚年颇“悔少作”,其在大晟府期间虽曾“讨论古音,审定古调”,“按月律为之”(《词源》卷下)[13]255,那也只是依据“大晟律”审按校定“燕乐旧行一十七调曲谱”,并“依月律次序添入新补撰诸调曲谱”(《宋会要·乐》四之一)[8]322,其词的创作可能没有“依月用律”。大晟府词人中江汉、田为宋人史料中也无“依月用律”的记载。其中江汉政和六、七年间已离开大晟府任密州通判(《宋会要·兵》一二之二○[18]6962,《宋史·翟汝文传》卷三七二[6]1105,《浙江通志》卷一八一[19]75),其时正值大晟府“按月律进词”的起始阶段。宣和末年(1125)江汉为明堂司令[20]713,其时“按月律进词”时间已过去五年之久(大晟府奏请颁行“燕乐依月律撰词八十四调”在宣和二年二月),故江汉在“制词实谱”期间并没有在大晟府任职,宣和末年的工作性质也与“依月用律”无关。真正“依月用律”的其实只有田为、万俟咏二人。
史载万俟咏“依月用律,月进一曲”,田为“亦供职大乐”并为《大声集》作序(《直斋书录解题》卷二一[21]889,《文献通考》卷二四六[5]1944-1945)。其时田为在“燕乐所”任制撰官,并兼任“修制大乐局管勾官”,尔后又任大晟府典乐、乐令、大司乐(《宋会要·职官》六九之四[22]3931,《宋史·张朴传》卷三五六[6]1067,《清波杂志》卷一一[23]473)*有关万俟咏、徐申、晁端礼、江汉、田为在大晟府的职任及任时,详见《大晟府词人新考》(《浙江大学学报》2012年第6期)。。其在大晟府任职恰好为“按月律进词”时段,《碧鸡漫志》云“田为不伐亦供职大乐”,并不言其“依月用律”,现存田为词中也找不到“依月用律”的痕迹。其实,田为在“燕乐所”任制撰官期间,主要工作是“审按校定”“燕乐旧行一十七调大小曲谱”及“依月律次序添入新补撰诸调曲谱”(《宋会要·乐》四之一)[8]322,即“讨论古音,审定古调”(《词源》卷下)[13]255,这一点和周邦彦的工作颇相似。或许“依月用律制词”不是周邦彦、田为的职责,故二人现存作品中均找不到“依月用律制词”之作。
现知大晟府词人中“按月律进词”并有词例可考的只有万俟咏一人。这一点也为夏承焘先生所认可。
四、大晟府词人“依月用律”的内容蠡测
关于大晟府词人“依月用律”的内容,《碧鸡漫志》有所谓“新广八十四调,患谱弗传,雅言请以盛德大业及祥瑞事迹制词实谱。有旨依月用律,月进一曲”[11]87的说法,其所提供的信息至少有以下三点:
第一,所谓“依月用律,月进一曲”,乃依大晟府十二月“声律”依次每月进曲一首。“依月用律”不过是“随月用宫”,这在徽宗之前的鼓吹乐中已能做到(《玉海》[4]796-797,《文献通考·乐考二十》[5]1291)。今考万俟咏词,“随月用宫”者有《春草碧》一词:
又随芳渚生,看翠连霁空,愁满征路。东风里,谁望断西塞,恨迷南浦。天涯地角,意不尽、消沈万古。曾是送别长亭下,细绿暗烟雨。何处。乱红铺绣茵,有醉眠荡子,拾翠游女。王孙远,柳外共残照,断云无语。池塘梦生,谢公后、还能继否。独上画楼,春山瞑、雁飞去。
《钦定词谱》卷二六:“调见《大声集》,自注:‘中管高宫。’……俗谱以中管高为调名者,误。姜夔集有太簇宫《喜迁莺》词,自注:‘俗呼中管高宫。’”[24]465又云:“此词即咏春草,亦以题为调名。宋词仅见此首,无别首可校。”[24]465夏承焘先生说:“今所见惟万俟咏《春草碧》一首中用中管高中(宫),盖(万俟)咏在大晟府时依功令‘依月用律’之作。”(《〈白石道人歌曲〉校律》)[1]359-360亦认为万俟咏在大晟府“依月用律”之作。今据张炎《词源》“太簇宫,俗名中管高宫”[13]246,为正月之律,而万俟咏《中管高宫·春草碧》有“乱红铺绣茵”语,为暮春三月之景,与“功令”不合。可能大晟府“依月用律”之作只是要求写景大致具有节序意味,而并不要求严格的时令特征,这一点尚待考证。
第二,“新广八十四调”云云,亦有史籍可征。据《宋会要·乐》四之二:“(宣和)二年二月六日,大晟府奏:‘燕乐依月律撰词八十四调,乞颁行。’从之。”[8]322《玉海》卷一○五:“(宣和)二年二月,依月律撰燕乐词八十四调。”[4]778可知“新广八十四调”乃指“燕乐八十四调”。燕乐旧行十八调,北宋通行有“二十八调”燕乐理论。政和四年正月,大晟府依月律“改定”燕乐,遂将“燕乐八十四调”理论付诸音乐实践。政和六年闰正月,“改定”燕乐八十四调工作告成,乃命刘昺撰为《宴乐新书》。政和六年十月,万俟咏奏请“以盛德大业及祥瑞事迹制词实谱”。其中“燕乐八十四调”的内容,张炎《词源》有载。需要指出的是,“制词实谱”工作到宣和二年二月方告全部完成,并由大晟府奏请颁行,其时万俟咏已任“秦川茶马司第三等幹当公事”之职(《宋会要·职官》四三之一○二)[25]3324。至于何时离开大晟府,据《宋会要·职官》四三之一○二,则当在宣和元年八月之前[25]3324。很显然,“依月律撰燕乐词八十四调”,非由万俟咏一人完成,当成于众人之手。其标志性成果就是“燕乐依月律撰词八十四调”,并由大晟府奏请颁行。
第三,以盛德大业及祥瑞事迹“制词实谱”,目的在于谀颂而应制。《唐宋诸贤绝妙词选》卷七:“(万俟咏)依月用律制词,故多应制。”[12]655此应制非赓和宋徽宗之作,乃依徽宗旨意“依月用律,月进一曲”之义。据此,知现存万俟咏词曲中有应制字样者当为“依月用律”制词。如:
《安平乐慢·都门池苑应制》:
瑞日初迟,绪风乍暖,千花百草争香。瑶池路稳,阆苑春深,云树水殿相望。柳曲沙平,看尘随青盖,絮惹红妆。卖酒绿阴傍。无人不醉春光。有十里笙歌,万家罗绮,身世疑在仙乡。行乐知无禁,五侯半隐少年场。舞妙歌妍,空妒得、莺娇燕忙。念芳菲、都来几日,不堪风雨疏狂。
《钦定词谱》卷三二:“调见万俟咏《大声集》。”[24]580按此曲“都门池苑应制”云云,乃万俟咏“依月用律”制词之一。
《恋芳春慢·寒食前进》:
蜂蕊分香,燕泥破润,暂寒天气清新。帝里繁华,昨夜细雨初匀。万品花藏四苑,望一带、柳接重津。寒食近,蹴踘秋千,又是无限游人。红妆趁戏,绮罗夹道,青帘卖酒,台榭侵云。处处笙歌,不负治世良辰。共见西城路好,翠华定、将出严宸。谁知道,仁主祈祥为民,非事行春。
“进”云云,当为依徽宗旨意“依月用律,月进一曲”之义,与应制当为同一类型。《钦定词谱》卷三一:“调见万俟咏《大声集》。崇宁中,咏充大晟府制撰,依月用律制词,多应制之作。此词自注:‘寒食前进。’故以《恋芳春》为名也。”[24]568即以《恋芳春慢·寒食前进》为“依月用律制词”,当有一定依据,可从。“仁主祈祥为民”云云,当即叙“盛德大业”之义。
《三台·清明应制》:
见梨花初带夜月,海棠半含朝雨。内苑春、不禁过青门,御沟涨、潜通南浦。东风静、细柳垂金缕。望凤阙、非烟非雾。好时代、朝野多欢,遍九陌、太平箫鼓。乍莺儿百啭断续,燕子飞来飞去。近绿水、台榭映秋千,斗草聚、双双游女。饧香更、酒冷踏青路。曾暗识、夭桃朱户。向晚骤、宝马雕鞍,醉襟惹、乱花飞絮。正轻寒轻暖漏永,半阴半晴云暮。禁火天、已是试新妆,岁华到、三分佳处。清明看、汉宫传蜡炬。散翠烟、飞入槐府。敛兵卫、阊阖门开,住传宣、又还休务。
《钦定词谱》卷三九:“《乐苑》云:‘唐《三台》,羽调曲。’”[24]716按此曲“清明应制”云云,亦万俟咏“依月用律”制词之一。
《明月照高楼慢·中秋应制》:
平分素商。四垂翠幕,斜界银潢。颢气通建章。正烟澄练色,露洗水光。明映波融太液,影随帘挂披香。楼观壮丽,附霁云、耀绀碧相望。宫妆。三千从赭黄。万年世代,一部笙簧。夜宴花漏长。乍莺歌断续,燕舞回翔。玉座频燃绛蜡,素娥重按《霓裳》。还是共唱御制词,送御觞。
《岁时广记》卷三一:“宣和间,万俟雅言(咏)中秋应制,作《明月照高楼慢》,云:‘平分素商(词略)。’”[26]61按此曲“中秋应制”云云,为万俟咏“依月用律”制词之一。
《快活年近拍》:
千秋万岁君,五帝三皇世。观风重令节,与民乐盛际。蕊阙长春,洞天不老。花艳蟾辉,十里照春珠翠。闹罗绮。遥望太极光,一簇通明里。钧台奏寿曲,蓬山呈妙戏。天上人来,五云楼近,风送歌声,依约睿思新制。
《钦定词谱》卷一八:“《快活年近拍》,金词注‘黄钟宫’。”[24]318据张炎《词源》“无射宫,俗名黄钟宫”[13]250,为九月之律。万俟咏《快活年近拍》所谓“重令节”,当指九月九日重阳节,其律令恰应九月月令。
《雪明鳷鹊夜慢》:
望五云多处春深,开阆苑、别就蓬岛。正梅雪韵清,桂月光皎。凤帐龙帘萦嫩风,御座深翠金间绕。半天中、香泛千花,灯挂百宝。圣时观风重腊,有箫鼓沸空,锦绣匝道。竞呼卢,气贯调欢笑。暗里金钱掷下,来侍燕歌,太平睿藻。愿年年此际,迎春不老。
《岁时广记》卷一一:“景龙楼先赏,自十二月十五日便放灯,直至上元。万俟雅言(咏)作《雪明鳷鹊夜慢》,云:‘望五云多处春深(词略)。’”[26]60此为咏元宵佳节之词,与应制词言“盛德大业及祥瑞事迹”相合。
以上词如“身世疑在仙乡”、“五侯半隐少年场”(《安平乐慢·都门池苑应制》),“仁主祈祥为民,非事行春”(《恋芳春慢·寒食前进》),“散翠烟、飞入槐府。敛兵卫、阊阖门开”(《三台·清明应制》),“还是共唱御制词,送御觞”(《明月照高楼慢·中秋应制》),“千秋万岁君,五帝三皇世”(《快活年近拍》),“望五云多处春深”、“圣时观风重腊”(《雪明鳷鹊夜慢》),实际上都带有谀颂色彩,乃为“应制词”的体例。《唐宋诸贤绝妙词选》卷七:“雅言(万俟咏)之词,词之圣者也。发妙音于律吕之中,运巧思于斧凿之外。平而工,和而雅,比诸刻琢句意而求精丽者,远矣。”[12]658尽管从艺术角度衡量,此说不无道理,但内容多歌咏“盛德大业及祥瑞事迹”,并无可取之处。有关这些词的作年,《碧鸡漫志》、《唐宋诸贤绝妙词选》等说万俟咏“依月用律制词”在“崇宁间”、“崇宁中”、“宣和间”,均误。其时段乃在政和六年十月至宣和元年八月之前,因万俟咏宣和元年八月之前已不在大晟府任职。(《宋会要·职官》四三之一○二)[25]3324
五、对大晟府词人“依月用律”的评价
以上通过考察大晟府词人“依月用律”的情况,仅考得万俟咏一人有实证可依。就万俟咏“依月用律”之词来看,均为“节序应制”所作,与其所云“以盛德大业及祥瑞事迹制词实谱”基本吻合。其余词人如徐申、晁端礼、周邦彦、江汉、田为等五人,均无“依月用律”词例。大晟府词人“依月用律”时间,在政和六年十月至宣和二年二月之前,总共维持了三年零四个月。而由大晟府奏请颁行的“燕乐依月律撰词八十四调”(或“依月律撰燕乐词八十四调”),也只不过是一个粉饰太平、歌功颂德的样板。
可以说,大晟府词人“依月用律”,对宋词发展并没有起多少推动作用,但却被南宋人渲染至神秘的程度。《唐宋诸贤绝妙词选》卷七:“万俟雅言(咏)精于音律,自号词隐。崇宁中充大晟府制撰,依月用律制词,故多应制。”[12]655“晁次膺,宣和间充大晟府协律郎,与万俟雅言齐名,按月律进词。”[12]654杨缵《作词五要》云:“第二要择律。律不应月,则不美。如十一月调须用[正宫],元宵词必用[仙吕宫]为宜也。”[13]268张炎《词源》卷下:“迄于崇宁,立大晟府,命周美成诸人……按月律为之,其曲遂繁。”[13]255按“依月用律”在杨缵之前似还没有作为“择律”标准被提升至“词法”高度,至杨缵便以“依月用律”书之于《作词五要》,俨然已成为雅词创作实践必须遵守的法则。受杨缵影响较深的张炎,则更将大晟府“依月用律”作为雅词的新标准,将“大晟诸人附会古乐”的作法进一步推向极端,表现出强烈的崇“大晟律”倾向。后世词学家评《词源》道:“(《词源》)究律吕之微,穷分寸之要,大晟乐府,遗规可稽”[27]271-272;“犹幸《词源》一书,略存大晟府词乐遗范,宫调及腔谱拍之基本,均有线索可寻。”[28]3便是针对《词源》本身所散发的浓郁“大晟律”意味而言。
后人不明大晟府词人“依月用律”真相,往往被南宋黄昇、杨缵、张炎所眩惑,从而出现了种种理解上的误区。沈曾植云:
北曲兴而词变,大晟律吕之法,俗乐中荡然不存,而大晟雅乐,元袭宋,明袭元,一线相沿,未尝改作。……《续通考》、《明史·乐志》,皆载十二月按律乐歌,大略与《词源》合。正月太簇,本宫黄钟商,俗名大石,曲名《万年春》之类;二月夹钟,本宫夹钟宫,俗名中吕,曲名《玉街行》;三月姑洗,本宫太簇商(与太簇本宫黄钟商同例),俗名大石,曲名《贺圣朝》;四月仲吕,本宫无射徵,俗名黄钟正徵,曲名《喜升平》;五月蕤宾,本宫姑洗商,俗名中管双调,曲名《乐清朝》;六月林钟,本宫夹钟角,俗名中吕角,曲名《庆皇都》;七月夷则,本宫南吕商,俗名中管商角,曲名《永太平》;八月南吕,本宫南吕宫,俗名中管仙吕,曲名《凤皇吟》;九月无射,本宫无射宫,俗名黄钟,曲名《飞龙引》;十月应钟,本宫姑洗徵,俗名中吕正徵,曲名《龙池宴》;十一月黄钟,本宫夷则角,俗名仙吕角,曲名《金门乐》;十二月大吕,本宫大吕宫,俗名高宫,曲名《风云会》。雅俗之名,皆用宋世之旧。而中管五调,宋世俗乐所无,独太常雅乐有之。此明太常乐即宋大晟乐,最显证也。[3]3613-3614
以明太常乐“依月用律”之法与张炎《词源》比勘,认为即大晟府“依月用律”之遗。清人迷信“大晟功令”者,皆录而不加辨别,如:“晁(端礼)字次膺,崇宁中擢第,宣和间充大晟协律,与万俟雅言(咏)按月律进词。”[29]986“雅言(万俟咏)号词隐,崇宁中充大晟府制撰,与晁次膺(端礼)按月律进词。”[29]989“万俟雅言(咏)自号词隐,崇宁中充大晟府制撰,与晁次膺(端礼)按月律进词。”[30]1199“(万俟咏)崇宁中,充大晟府制撰,依月用律,有《大声集》五卷。”[31]1430甚者缘饰为美谈,如:“至如晁次膺(端礼)、万俟雅言(咏)之依月用律,进词应制,调名尚数百种未传。”[32]645“有提举大晟之官僚,按月律进词,承宣命珥笔,宠诸词人,良云盛事。”[30]1139按以上节录《碧鸡漫志》、《唐宋诸贤绝妙词选》、《词源》而不加甄别,辗转抄录中又添加臆说,以致讹误百出。如云晁端礼“崇宁中擢第,宣和间充大晟协律”,据李昭玘《晁次膺墓志铭》、晁以道《宋故平恩府君晁公墓表》,晁端礼实于熙宁六年擢第,政和三年充大晟府按协声律。又如云万俟咏“崇宁中充大晟府制撰,与晁次膺(端礼)按月律进词”,《碧鸡漫志》实云“政和初”,其“按月律进词”乃在政和六年至宣和元年,其时晁端礼已卒。又如云“有提举大晟之官僚,按月律进词”,则指周邦彦提举大晟府“按月律进词”,据考周邦彦虽有提举大晟府之事,但“按月律进词”却无证据。又沈曾植以《明史·乐志》所载“十二月按律乐歌”[33]160附会大晟府“依月用律”,亦勇于臆测,疏于考证。又如云“依月用律,进词应制,调名尚数百种未传”,亦未知何据。清儒考据之学大昌,然于词学不经意若此,其贻误后学亦难于屈指。夏承焘先生批评道:“‘依月用律’之说,本出大晟诸人附会古乐;词家伫兴之作,但求腔调谐美,何必守此功令。张炎、杨缵论词之书,张皇幽邈,以此自炫,由今观之,亦缘饰之辞,不足信也。”(《词律三义》)[1]10在指出南宋人“张皇”“缘饰”的同时,对于“‘依月用律’之说,本出大晟诸人附会古乐”的事实亦有肯定,对宋词“依月用律”的实质及其误解作了精到的辨析,批驳极为有力。任二北先生《研究词乐之意见》:“宋人之词,是否实行按月择律;当时普通词家皆实行,抑仅精音律者始实行;仅于节序之词实行,抑于一切之词皆实行。”[34]309对宋词“依月用律”范围作了积极的思考,有助于后学做进一步的考察。今据以上考证,可知宋词“依月用律”实始于徽宗朝以前,其范围亦不限于“节序之词”,而在鼓吹乐中即有广泛运用。不过,随着政和四年正月以“大晟月律”改定燕乐之后,大晟府词人不仅在理论上对“依月用律”作了部分建构(如“依月律次序”审按校定“燕乐旧行一十七调大小曲谱”并“添入新补撰诸调曲谱”等),且还付诸创作实践(如“依月律撰燕乐词”)。这一点因被南宋及清人作了夸大性的宣传,遂使后人在认识到南宋及清人的夸大不实之后,又容易对大晟府词人“依月用律”的真实情况作出全盘否定的评价。●
[参考文献]
[1] 夏承焘.夏承焘集(第2册)[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
[2] 彭国忠.大晟词派质疑[J].上海大学学报,2000(3).
[3] 沈曾植.菌阁琐谈(《词话丛编》本)[M].北京:中华书局,1986.
[4] 王应麟.玉海(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945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5] 马端临.文献通考[M].北京:中华书局,1986.
[6] 脱脱,等.宋史(影印百衲本)[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8.
[7] 沈括.补笔谈(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862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8] 徐松.宋会要辑稿(影印本第8册)[M].北京:中华书局,1957.
[9] 杨荫浏.中国古代音乐史稿[M].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2004.
[10] 徐松.宋会要辑稿(影印本第42册)[M].北京:中华书局,1957.
[11] 王灼.碧鸡漫志(《词话丛编》本)[M].北京:中华书局,1986.
[12] 黄昇.唐宋诸贤绝妙词选[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
[13] 张炎.词源(《词话丛编》本)[M].北京:中华书局,1986.
[14] 诸葛忆兵.周邦彦提举大晟府考[J].文学遗产,1997(5).
[15] 史能之.咸淳重修毗陵志(《续修四库全书》本)[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16] 晁以道.景迂生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17] 李昭玘.乐静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18] 徐松.宋会要辑稿(影印本第177册)[M].北京:中华书局,1957.
[19] 嵇曾筠,等.浙江通志(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524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20] 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21] 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22] 徐松.宋会要辑稿(影印本第100册)[M].北京:中华书局,1957.
[23] 周煇(著),刘永翔(校注).清波杂志[M].北京:中华书局,1994.
[24] 王奕清,等.钦定词谱[M].北京:中国书店,1983.
[25] 徐松.宋会要辑稿(影印本第84册)[M].北京:中华书局,1957.
[26] 陈元靓.岁时广记(《词话丛编》本)[M].北京:中华书局,1986.
[27] 伍崇曜.词源跋[G]//张炎.词源(《词话丛编》本).北京:中华书局,1986.
[28] 蔡嵩云.词源疏证[M].北京:中国书店,1985.
[29] 沈雄.古今词话(《词话丛编》本)[M].北京:中华书局,1986.
[30] 王奕清,等.历代词话(《词话丛编》本)[M].北京:中华书局,1986.
[31] 李调元.雨村词话(《词话丛编》本)[M].北京:中华书局,1986.
[32] 邹祇谟.远志斋词衷(《词话丛编》本)[M].北京:中华书局,1986.
[33] 张廷玉,等.明史(影印百衲本)[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8.
[34] 任二北.研究词乐之意见[C]//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古典文学研究室.词学研究论文集(1911—1949).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