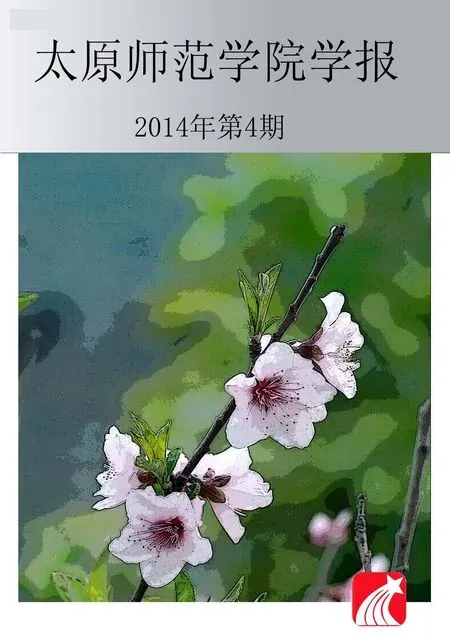白居易讽喻诗的困境及其他
(复旦大学 中国语言文学系, 上海 200433)
一、白居易的讽喻诗及其诗风
诗歌要为政治教化服务是白居易文学主张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思想既是儒家诗教传统在后代的延续,也是唐帝国由盛转衰后重建社会秩序、统一文化思想的现实需要。孔子将诗歌的政治作用和社会意义置于其文学价值之前,认为“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1]2525继之而起的汉代儒生在《毛诗序》中对“风、雅、颂、赋、比、兴”六义进行了系统的阐释,从而完成了对“文学—政治”互动关系的早期理论建构。然而这种互动不仅需要文学单方面的努力,还必须得到政治的保障与回应。而魏晋以降的动乱打破了政治上的统一,却促进了人的发现与解放,文学也开始出现自觉,为文学而文学的作品逐渐增多。在此审美观念的驱动下,诗歌风格变得愈加浮靡,到了唐初,这一现象已经引起许多文人的不满。加之安史之乱后,国家亟需对社会各方面实现控制与整合。在此背景之下,韩愈提出要恢复儒家的道统,而文学作品也被赋予了“文以载道”的使命。此后,儒家以文学匡助政治的主张再次为人所重视。
受此影响,白居易格外重视诗歌在政治活动中的作用。在他看来,一方面,帝王可以通过诗歌补察时政、了解民情;另一方面,士大夫可以“惟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2]43,通过采诗写诗上达民意。白居易认为“政有毫发之善,下必知也;教有锱铢之失,上必闻也”[2]3436,以此来调和社会矛盾,从而使得帝王能够“直道而行,垂拱而理”[2]2790。他希望能“学习古代圣人运用音乐来感化人心的成功经验,继承古代的君臣百姓以歌言政的古老传统,通过歌的形式达到‘上下通而一气泰’的理想政治局面”[3]103。
在此思想的指导下,白居易将匡救社会弊端的任务寄托在讽喻诗上,倡导“有阙必规,有违必谏”[2]3323。而这种类似于奏疏性质的诗歌则需要切乎现实。白居易所谓“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2]2791,不仅继承了汉乐府“缘事而发”的现实主义精神,而且更进一步,正如他在《新乐府序》中所说:“其事核而实,使采之者传信也”[2]136,说明其对真实性的重视甚至到了核实的程度。
既然政治讽喻才是诗歌的核心作用,而真实可信又是其必要的形式,那么对于讽喻诗而言,辞藻和韵律上的雕琢便显得无足轻重了,不仅于此,华丽的语言很可能会吸引读者的注意力,使其忽略诗歌内容本身所想表达的政治诉求。因此,白居易继承了唐代文人对六朝文学绮丽之风的批评,认为“俾辞赋合炯戒讽喻者,虽质虽野,采而奖之;俾诔有虚美愧辞者,虽华虽丽,禁而绝之”[2]3546,并提出“其辞质而径”、“其言直而切”、“其体顺而肆”[2]136的主张。在这一创作思想的指导下,白诗大多直白朴实、浅显平易,甚至老妪能解[4]7。苏轼在《祭刘子玉文》中说“元轻白俗”[5]1938,正是对白居易讽喻诗风格的最好概括。
二、讽喻诗的困境及其原因
白居易将讽喻诗视为自己劝谏天子的重要手段,但是由于白居易讽喻诗存在着内在与外在的双重矛盾,使得白诗陷入重重困境。
(一)内在矛盾
从诗歌本身的角度来看,白居易讽喻诗的艺术表现手法存在着明显不足。首先,白诗形式较为单一,甚至近似于“有韵律的奏章”[6]251。魏泰指出:“白居易亦善作长韵叙事,但格制不高,局于浅切,又不能更风操,虽百篇之意,只如一篇,故使人读而易厌也。”[7]327而且在其早期创作中“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公式化、概念化的倾向”[8]。其次,白居易有时过分强调对于内容的核实,排斥艺术的加工,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诗歌的表现力与劝解效果。从现代文艺理论的角度来看,我们注重的不是反映一件真实的事情,而是要真实地反映一件事情。再次,白诗的叙事过于浅显,语言过于直白,思想过于外露。与政论文章相比,文学作品的倾向性与目的性应当表现得更为隐蔽和婉转,但白居易却希望把全部信息都交代清楚,在留白的技巧上较为欠缺。他“没有充分估计读者的想象力,不肯给读者多留一些想象的余地。”[6]253有时甚至给人以繁复絮叨之感。就连白居易自己也曾意识到“词犯文繁”的毛病,并自我批评道:“不忍于割戴,或失于繁多。”[2]2796但是,这样的自我批评就像他的讽喻诗一样,并没有获得实效,下笔时虽有意克制,却终不能自已,于是乎只能空发“岂可轻嘲咏,应须痛比方”[2]2541的感叹了。最后,由于白居易的讽喻诗囿于先写景后议论的固定模式,使得议论部分常常与写景脱节,不仅孤立、机械,而且刻板枯燥。《胡旋女》、《折臂翁》、《二王后》等作品都有较明显的议论空洞、表现力匮乏的缺点。
(二)外在矛盾
从讽谏效果的角度来看,白居易过分估计了讽喻诗甚至是臣子讽谏本身的效果。首先,儒家之所以推重“诗教”,并非因为这是三代业已存在的传统,恰恰相反,诗歌的教化功能仅仅是儒生们为了实现自己从未实现的政治主张而幻想出来的“乌托邦”。此外,所谓《诗经》采自民间的说法在很大程度上亦出自后人的想象,具有明显官方色彩的雅与颂自不必说,国风同样多由贵族创作,而并非来自劳动人民。[9]其次,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局面似乎只短暂地出现在有宋一代,之后的明、清逐渐达到了中国社会君主专制的顶峰;而之前的隋、唐虽然对君权有所制衡,但能与之抗衡的也并非出身庶族的士大夫,而是那些门阀世家。白居易仅仅是庶族士大夫中不入流的小官,纵使在左拾遗任上,依然人微言轻。而且,在安史之乱后,增强皇权成为当务之急,加之宪宗英武,难免刚愎自用,白居易讽谏又多触及既得利益集团,于是被贬出京也在情理之中。最后,以《秦中吟》为代表的讽喻诗,其最早的读者群其实是“在长安通过科举考试得以为官的人,以及在陋巷破窗中还在梦想未来的荣光者,原本并非以为广泛的一般民众以及奏闻天子为第一目的的”[10]148。这些中层以下士大夫,或是在京担任小官,或是还在守选之期,但都寄居长安一隅,面对种种社会问题与“长安居大不易”的生活现实,只能以诗文酬唱,表达不满。因此,这些作品“私”的特点便十分明显。当然,作者也希望能得到更广泛的读者,而且在官居左拾遗时借机创作了为天子阅读的《新乐府》。但较之《秦中吟》,这些诗歌的攻击性明显减弱,往往多从天子的视角出发,从而具有“公”的性格特点。如此来看,与其说白居易的讽喻诗是士大夫苦心孤诣的奏议,毋宁说只是底层知识分子之间议论国是的牢骚。
事实上,以往的研究似乎过分高估了白居易讽喻诗的意义与价值,而这种评价往往来自于我们的想象和建构。对于白居易的讽喻诗,我们庶几可以这样说,其政治目的先于文学目的,史料价值大于文艺价值,上层影响广于下层影响,后世意义重于当时意义,私的层面高于公的层面。
三、白诗的类型及其尴尬
虽然实际效果有限,而且给自己带来了接二连三的贬谪之祸,但是白居易仍然极其珍重自己的讽喻诗。在《与元九书》这篇反映白居易诗歌主张的重要文献中,白居易不惜贬抑陶、谢、李、杜来大力提倡讽喻诗,后来更是将讽喻诗居于《白氏长庆集》之首,这便使得后世出现了一种误解——诗教说是白居易的核心主张,讽喻诗是白居易的主要作品。然而事实并非如此,正如王运熙先生所指出的那样,白居易在《与元九书》中对其他题材的诗歌痛下杀手仅仅是“在强调讽喻诗时的一时偏激之言……并不足以代表他的全部看法和主张”[11]。
在《白氏长庆集》中,除了讽喻诗之外,还有数量众多的闲适诗、感伤诗与杂律诗。在《与元九书》中,白居易表明了自己“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儒家立身原则,兼济之诗当然要数讽喻诗,而独善之诗则是闲适一类的抒情之作。这说明,白居易并非一根筋地将全部心血付诸讽喻劝谏,在其流传至今的作品中,存在着大量的其他题材和风格的诗歌,展现了白诗类型的丰富与多样。
而正是这样的多样性为白居易带来了不小的尴尬。
当时的读者所感兴趣的并不是白居易自命不凡的讽喻诗,反而是他那些酬唱亲友和歌咏闲情的作品。元稹在《白氏长庆集》的序言中介绍,白居易的《秦中吟》、《贺雨》等讽喻诗,“时人罕能知者”[2]3972,甚至白居易自己也意识到了这一问题,他说:“今仆之诗,人所爱者悉不过杂律诗与《长恨歌》已下耳。时之所重,仆之所轻。至于讽谕者,意激而言质;闲适者,思澹而词迁。以质合迁,宜人之不爱也。”[2]2795白诗中那些篇幅短小、文词优美、抒情委婉的律诗反而最为流行,其中亦不乏描写艳情之作,而后世对白诗的主要批评便集中在他的这些艳情诗上。杜牧在《唐故平卢军节度巡官陇西李府君墓志铭》一文中假借李戡之口对白居易毫不留情地批评道:“纤艳不逞,非庄雅人士,多为其所破坏,流于民间,疏于屏壁……淫言亵语,冬寒夏热,入人肌骨,不可除去。”[12]744在《新唐书》中则进一步对这种俚俗化、市民化的诗歌倾向进行严厉批评。而后世读书不慎的学者往往错将这一针对艳情诗的评价认为是北宋古文学家对白居易全部诗歌的批评,一方面受特殊政治环境的影响,在阶级斗争理论之下高歌白居易关心民生疾苦,另一方面又盲从史书,对白诗“一棒子打死”。
这实在是白居易的尴尬,更是我们的尴尬。
四、小结
白居易自己所看重的讽喻诗却在民间流传不广,而大受欢迎的闲适诗却又被后世激烈批评,在这些尴尬与矛盾的背后,似乎有一首诗歌例外,那便是《长恨歌》。也许,白居易曾试图将这个故事写成纯粹的讽喻诗,却在叙述和创作的过程中由“言志”而生成“缘情”,从而将这份真挚的爱情艺术化,最终洋洋洒洒地写出一篇千古传唱的爱情史诗。在诗中处处可见“讽喻”与“抒情”的矛盾,这种矛盾实际源于作者内心深处,白居易曾说:“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感人心者,莫先乎情,莫始乎言,莫切乎声,莫深乎义。诗者,根情、苗言、华声、实义。”[2]2790此诗恰恰是根情之作,又恰恰有圣人之教,白居易在矛盾中实现了这种统一。在康德看来,审美是无目的的合目的性。《长恨歌》中绮丽丰富的想象并不符合白居易一贯主张的“核实”标准,然而却在读者中得到了良好的回应,既为后世的历代君王提供了一扇切忌荒淫乱国的明镜,又为后世众多读者提供了津津乐道的美好爱情。
这种无目的的合目的性恰好跳出了讽喻的困境。●
[参考文献]
[1] 孔门弟子(撰),何晏(集解),邢昺(疏).论语注疏(影印阮元刻十三经注疏)[M].北京:中华书局,1980.
[2] 白居易(撰),朱金城(箋校).白居易集笺校[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
[3] 张煜.新乐府辞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4] 惠洪(撰),李保民(点校).冷斋夜话[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5] 苏轼(撰),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
[6] 袁行霈.中国诗歌艺术研究(增订本)[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
[7] 何文焕(编).历代诗话[M].北京:中华书局,1981.
[8] 陈祖美.白诗的得失及风格的变化[J].北方论丛,1985(1).
[9] 陈致.从礼仪化到世俗化:《诗经》的形成[M].吴仰湘,黄梓勇,许景昭,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
[10] (日)静永健.白居易写讽喻诗的前前后后[M].刘维治,译.北京:中华书局,2007.
[11] 王运熙.白居易诗歌的几个问题[J].学术研究,2003(5).
[12] 杜牧(撰),吴在庆(校注).杜牧集系年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