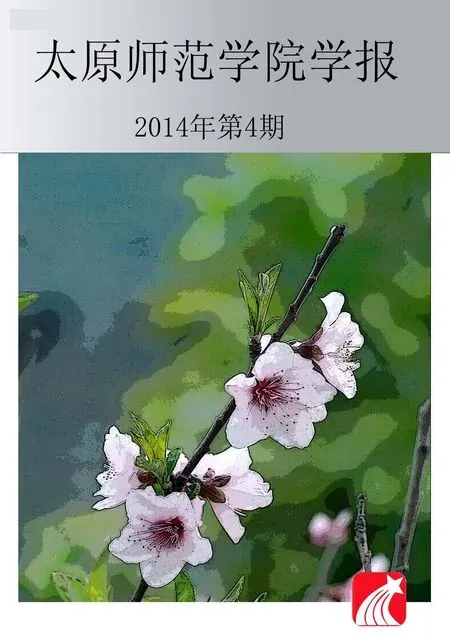游戏背后的沉重
——后现代主义文学浅论
赵升平
(太原师范学院 文学院, 山西 太原 030012)
担任国际文学理论学会秘书长的王宁曾在他的《“后理论时代”的文学与文化研究》中指出:“今天,我们谁也不可否认,后现代主义已经成为一个全球性的现象,它在客观上也预示了文化上必将出现的全球化趋势。”[1]211“尽管后现代主义首先是西方后工业社会的一个文化现象,但是我们切不可忘记这一事实,即它一旦进入一些经济发展异常迅速并且大众传媒十分发达的国家和地区,就会驻足并发生某种形变。”[1]212这就说明,虽然表面看后现代主义文学好像已经是西方“过去”了的一种现象,但实际它恐怕仍然存活于我们的“今天”,而且再去研究它恐怕仍然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一、存在主义文学的“极度冷漠”
大家知道,所谓后现代主义文学,指的就是二战之后最早在西方出现的一股文学思潮。它是随着后工业社会的到来而产生的。其主要流派中包括了存在主义文学、新小说派、魔幻现实主义以及垮掉的一代等等。而这种文学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与海德格尔和德里达的哲学理论相对应,无视任何规范,故意化解“深度”,在布局谋篇当中往往采取一种极度冷漠或荒诞不经的方式示人,造成一种满不在乎、什么都是游戏的假象。但实际上,只要你稍加注意,就不难发现在这种看似什么都无所谓的背后,却潜藏着沉重,甚至在某些方面,竟直逼我们的“道德底线”,让你感慨不已。
就让我们先从存在主义文学说起吧。
毫无疑问,存在主义文学的基本特征就是描写世界和人的存在的冷漠。其最主要的代表作家即大名鼎鼎的萨特和加缪。
萨特著述极多,光文学作品就有著名的长篇小说《恶心》、名剧《禁闭》等等。但在这里我只想举他的一个短篇小说《墙》,从中可以看出他是如何表现我们所说的“冷漠”的。
这是一部篇幅非常短的作品,所描写的自然也是虚构中发生在西班牙战争期间的一个故事:三名共和党人被法西斯分子逮捕,遭到严刑拷打,要他们招供另一名同伴的藏身之所。第二天,敌人把其中的两人处决,对主人公“我”继续审讯。我为了戏弄敌人随口瞎说了一个地名“某某墓地”,但不久我却得到了宽大处理免于死刑。我感到非常纳闷:因为我一没投降,二没与敌人合作,为什么会得到宽大处理呢?后来我才知道,原来我随口说出的那个地名竟然真是要我招供的同伴的藏身之所,结果同伴被抓走了。我听到这个消息后,不禁放声大笑,泪流满面。
乍一看这是个非常不负责任的“游戏”,故事中的“我”由于太过随便导致了要命的后果:明明是和敌人对着干,要戏弄敌人,结果反倒是给敌人提供了情报,出卖了同伴。而只有天知道,明明我压根就不知道同伴的藏身之所,但随口瞎说倒比真的知道还准确。这里的问题恐怕不在这种事情存在的概率到底有多大,而是需要琢磨一下它所表现的“意味”。有道是“片面的深刻”——尽管后现代作家扬言不要深刻,但我由不得还是要这么去想。显然在这里,萨特是用这样一种巧而怪的事例来表现他理解的“此在”。在萨特看来,人生充满了偶然,充满了莫名其妙,甚至充满了“专找麻烦”!难道不是吗?有心栽花,无意插柳;想要的不来,不想的偏至。关键是,你不是什么都无所谓吗?但结果怎么样呢?你能对这样的结果也无所谓吗?所以最后的“我”哭笑不得,实实在在地疯掉了!
我在读这部小说的时候不由得感叹,就是备感它的“经典”。它不仅反映出现代人面对世事的冷漠态度,以及那种入木三分的游戏表现,而且表达出一种让人叫绝的批判和思考,这就是什么叫自作自受!是的,欠债总是要还的,尽管世事无常,人生无常。那么我们到底应该如何面对这种“无常”呢?
再说书名《墙》,一个“墙”字真是太有意思了,它会让你产生好多联想。诸如冷漠人生的不可预知,还是因果报应的难以逾越?等等。
至于加缪的《局外人》,一向被看成是“没有温度”的小说。作者把主人公写得没有亲情,没有爱情,当然更没有友情,他甚至连自己莫名其妙地杀了人被判处死刑都无动于衷。所以这部小说和萨特的《墙》比起来可谓更加冷漠。然而你要细细琢磨一下的话,恐怕就不会那么轻松了。比如莫索尔无论“从头”还是“到尾”,始终给人的感觉都是无动于衷,但是真正到了死亡的前夜,他还是有所触动了,这就是他“第一次向这个世界敞开了心扉”,尽管他至死都感到幸福,但他的的确确真切地感到他要死了。我们说人死如灯灭,一切只有等待“来世”再去接着体会了,因为此时此刻一切都要结束了。所以这里无论如何都有一丝怅然表现了出来。
由此可见,存在主义小说虽然号称冷漠至极,对什么都无所谓,但在它们冷冰冰的背后,还是能让我们感到有一颗心在那儿跳动,只是它充满了一种身不由己的无奈。而这正是他们表现出的沉重。
二、颠覆传统的“新小说”
新小说派又叫反小说派,从名称上就可以看出它是与传统意义上的小说背道而驰的。这一派的作家不仅摈弃传统的小说观念,而且从情节、人物、主题、时间顺序乃至语言等各个方面极力进行全面革新。比如关于情节的问题,他们认为传统小说诱导读者进入作者事先安排好的虚构境界,这实际上是使读者进入一个“谎言的世界”,而他们就是要通过对外界事物如实的描写,从现代人复杂的、混乱的日常生活中找出奥秘的所在。关于人与物的问题,他们则认为现代人处在被物包围的世界中,而传统小说恰恰忽略了物的地位,所以一定要突出物等等。
罗伯·格里耶是新小说派的创始人,他的小说《橡皮》无疑是新小说的代表作。小说写一个恐怖组织计划把对国家政治经济起重大影响的某某集团成员一一杀死,其中包括政治经济学教授丹尼尔·杜邦。在杜邦被杀之前,他们已杀掉了八个人,而且每次都是在晚上七点半下手。但是杀手格伦蒂纳在刺杀杜邦的那个晚上,由于匆忙只开了一枪,结果杜邦没死,只是受了点轻伤。内务部长和杜邦关系密切,再加上杜邦手里还有好多关系重大的秘密文件,所以当他得知杜邦未死的消息后立即派青年侦探瓦拉斯从首都到外省的这个小城去调查。瓦拉斯受命之后便于当晚七点半之前潜伏到了杜邦的寓所。在此之前,杜邦曾委托一个大商人马尔萨到他的寓所去取文件,因为前面的刺杀活动已让他不敢再回到寓所。他本打算让马尔萨一拿到文件就立刻离开此地投奔内务部长的,但谁知马尔萨开始允诺,后害怕危险临阵逃脱,使得杜邦只好冒死亲自来拿文件。可是侦探瓦拉斯并不知道杜邦没死,他听到的传闻是杜邦已经被刺身亡了,所以当他看到杜邦的时候误以为是杀手,而且杜邦当时已有防备,手里握着手枪。结果瓦拉斯首先开枪,匆忙中要了杜邦的命。这样看来,这似乎就是一部曲折离奇的侦探小说,但是作者在他的构建中却故意把这个原本扣人心弦的故事打碎,变成没有头绪的碎片,然后再从不同的角度把它拼接起来,从而构成一个错综复杂、乱七八糟的叙述,甚至出现开头即结尾,结尾又回到开头的情况。比如小说故意不去描写人们关注的与案件有关的种种活动,像瓦拉斯如何深入调查、艰难取证等等,而是有一搭没一搭地描述这个侦探下意识地,或者说毫无意识地在迷宫般的街道中逛来逛去,就像没事人似的逛大街。他毫无目的地观看着街景、行人、房屋,他走进一家快餐店一边吃饭一边像中了魔似地盯着看做好的菜肴的各种形状,特别是他像个神经病似的反复走进一家文具店购买橡皮,而且橡皮的样子被反复描述。整个小说可以说是他想到哪儿到哪儿,其中的好多事情都与案件毫无关系。
而作者这样一种看似一点都不负责任,甚至可以说是胡编乱造的描写到底要表现什么呢?如果你稍微琢磨一下的话,我觉得起码有两点是不难体会到的,这就是:
第一,着力展现物象,凸显被物包围的世界。前面我们已经提到,新小说派就是要把人与物分开,并着力描写物。《橡皮》正是突出地表现了这一理念。在小说中,作家以瓦拉斯受命破案为幌子,实际表达的就是作家对这个物质世界的感受。其中有大量物象的描写,典型的事例有二:一是从运河的一头到另一头必经的一座“开合桥”,二是瓦拉斯三番五次到文具店寻买他曾经见过的没有其他物品可以替代的橡皮。而且这两件事即过桥和买橡皮被不断地叙述和描写。比如过桥的一段:
这开合桥是单悬臂的,转动的轴心是在运河的另一端。这些人从桥面底下抬头往上望,看着一些错综交叠的金属小梁和缆绳,逐渐从眼前消失了。接着,在他们视线前,出现可以通行的桥端,看起来像马路的一段横切面。这时他们突然看见光滑的柏油路面,夹在两条边沿围着栏杆的行人道中间,一直伸展到运河彼岸。他们的目光随着整个合桥的动作慢慢地往下移,一直到两个已被来往汽车的轮子摩擦得发亮的桥角,准确地对合起来。这时发动机的齿轮机件的隆隆声立即停息了。在一片寂静中响起了电铃声,通知行人可以重新过桥。
这个物象与案件有关吗?一点没有关系。但他为什么要写而且是非常详细地描写这个呢?就是要展现人被物包围、被物牵制的现实。因为没有这个开合桥,人就过不了河。而且这里有好多微妙的东西隐藏其中,比如自行车、汽车,比如合桥的完全机械化,以及要求到毫厘的精确度等等,让我们感受到的,无疑是一个高速发展的现代社会。
再如买橡皮的一段:
这位年轻的妇女(指售货员)试图拼凑出厂名,但是没有成功。绝望之余,她把店里所有的橡皮块全都拿出来给他看。她的店里的确具备各种各样的好橡皮——她热情地逐一夸赞不同的优点。不过全部不是太软就是太硬:“面包心”橡皮,柔韧得像可以塑捏的陶土,要不就是一些质地灰暗干硬的东西,用起来刮纸——充其量不过是可以用来擦掉墨水印渍吧;其余的都是普通擦铅笔用的橡皮块,都是长方形的,只不过有的长些,有的短些,质地有的白一些,有的不太白而已。
同样,这也与案件没有任何关系,小说反复写这个,我想就是在说现代人已经完全被物控制,不就是块橡皮吗?为何非得就是“它”而不能是别的呢?但瓦拉斯就是不能。
第二,以物写人,通过对物的“素描”折射人的心理。尽管新小说号称物是小说的主体,但它毕竟还是要涉及人的,而在涉及描写人(尤其是人的心理)的时候,新小说也与传统小说根本不同,它往往不是正面去表现,而是通过对物的观察、体味加以折射。比如写瓦拉斯来到一个快餐店就餐的情形,小说对他要的一道番茄菜作了这样的描绘:
这一片番茄真是完美无缺,它是用机器从一个组织结构对称完善的果实上切下来的。它四周的果肉紧密匀称,具有像化学剂中那种鲜艳的红色,夹在发亮的果皮和子房之间,既肥厚又匀称。子房里的黄澄澄的种子,按着大小排列,层次分明;一层绿色透明的凝固物使种子粘附在果心鼓起部分的边沿。那浅粉红色的、表面微呈颗粒状的果心,从底部凹陷处伸出一束白色的条纹,其中的一条伸至种子附近——但它伸延的方式有点难以明确。在这片番茄的上面顶端,发生了一种几乎无法察觉的意外情况:有一小块皮离开果肉约一两毫米,现在微微地翘起。
这段描述简直像电影镜头一样,由外至里、由远及近地“拍摄”出了这片番茄的全部特征。在如此“忠实”、一点不走样的表达中,既反映出饭店里的一种寂静氛围,同时也把瓦拉斯细腻而又不专注于工作的心理折射出来。试想,如果满脑子只想破案的事,哪儿还有闲心来琢磨番茄长什么样呢?恐怕早就三下五除二送进肚子里去了。当然这里的“走神”,恐怕还有别的意思在里边,比如有时候人对一件事太过专心也会导致分心的情况出现,瓦拉斯是不是属于这种情况呢?或者说在物质的世界里,物欲横流,想专注工作已变得不可能等等。
总之,格里耶的这部《橡皮》完全颠覆了传统小说的写法,他不仅把人与物作了区分,而且处处凸显物的地位和作用。通过这样的描写,既让我们看到了现代社会满眼物质的现实,也让我们感受到了人被物控制的窘态。正因如此,有评论称格里耶的创作理念就是“物本主义”。所以,对物的着力描写是小说非常核心的一个标志。而且小说留下许多空白,让读者去想象、去创作。当然《橡皮》刚出版时,并不被人看好,据记载是“读者寥寥”,但是到了20世纪60年代,发行量却超过了100万册。1968年他还亲自执导将其拍成电影,片名叫《撒谎的人》。而且1985年西蒙的《弗兰德公路》获诺贝尔文学奖,使这一流派再次引起人们的关注。诺奖授予西蒙的理由是:由于他善于把诗人和画家的丰富想象与深刻意识融为一体,对人类的生存状况进行了深入的描写。
三、“垮掉”中的崛起
在所有的后现代主义文学流派里,恐怕再没有比垮掉的一代更让人“另眼相看”了,因为他们是“以扭曲的心理反映扭曲的世界而产生的扭曲的文学现象”。
所谓垮掉的一代指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出现在美国的一个后现代主义文学流派。它滥觞于20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兴盛于50年代中到70年代末。其特点是,成员大多是一些青年学生(有的正在大学学习,有的刚刚涉足社会),以离经叛道、玩世不恭、行为放荡为标志,其中包括身着奇装异服,乱搞两性、同性关系,拼命酗酒、吸毒等等。而且他们还把这种行为写在他们的作品中加以表达,用他们的话讲就是“嚎叫”。他们宣称,他们的生活就是他们的作品,他们的作品就是他们的生活。而他们的生活和作品显然都是对社会正统及社会禁忌的挑战和反叛。代表人物有艾伦·金斯堡(诗集《嚎叫》)、杰克·凯鲁亚克(小说《在路上》)和威廉·巴罗斯(小说《赤裸的午餐》)等。
《嚎叫》一开始是这样写的:
我看到这一代最杰出的头脑毁于疯狂,饿着肚子歇斯底里赤身露体,黎明时分拖着脚步走过黑人街巷寻找一针来劲的麻醉剂,头脑天使一般的嬉皮士渴望与黑夜机械中那繁星般的发电机发生古老的天堂式的关系……
凯鲁亚克的小说《在路上》则有一句经典的“台词”:“因为我很穷,所以我拥有一切!”
而《赤裸的午餐》则是巴罗斯凭借自己十三年吸毒的经验,运用超现实主义手法,用世界上“最肮脏、最污秽、最令人作呕的语言,表现了人在吸毒后所产生的幻觉”。作品一出版,即遭查禁,法官判定这部作品是“淫秽的、下流的、不道德的、赤裸裸的色情作品”。
那么,我们到底应该如何看待这个独特的流派呢?
首先,垮掉的一代产生于二战之后,战争的梦魇是催生他们的一个重要原因。当时二战刚刚结束,战争造成的惨祸仍像梦魇一样纠结在人们的心头。于是这些人“在战后的疮痍大地上,在日趋浓烈的工业硝烟中,光着凡身带着滴血的翅膀,飞过美国物质主义的天空”。不过有人将其与一战后的“迷惘的一代”作了一番比较,说迷惘的一代虽然也深受战争的创伤,但他们并未因此而失去对人性的渴望。但“垮掉的一代”则不同,他们伤得实在太重,以致丧失了对人性的最基本的理解,所以他们在反抗社会的同时,也牺牲了他们自己,这包括他们畸异的人生。因此用“垮掉的一代”作为称谓也表达了公众对他们的失望和不满。
其次,垮掉的一代被文学史家称为“裸露的天使”,因为正是通过他们不加遮掩的反叛,现代工业社会的种种弊端被深刻地揭示了出来,从而惊醒人们对现实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反思和批判。毫无疑问,这个流派的最大特点就是叛逆,而这种叛逆又大大超出了文学的范围而延及了整个“文化圈层”,它甚至涉及了法律和伦理道德的层面。正因如此,该流派深深影响了不仅仅是美国的文学和文化思潮。我们现在看来,垮掉的一代其实就是那个特殊年代出现的“愤青”,尽管他们采取的社会批判方式还有待商榷,但毕竟其影响不容抹杀。
总之,文学总是不断发展的,越到现代越显示出了它的“离经叛道”或“独树一帜”。但无论如何——不管它如何变化,也不管它表面如何地毫无正经,撞击心灵恐怕始终都是它的要务或目的。正因如此,不管文学再怎么无足轻重,我们却总是将它割舍不下。●
[参考文献]
[1] 王宁.“后理论时代”的文学与文化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