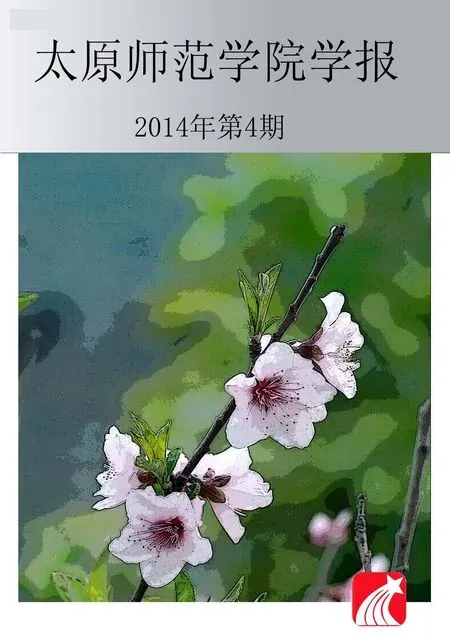中国生态批评的现状与发展
王晓晨,杨 东
(广西民族大学 文学院, 广西 南宁 530006)
中国的生态批评主要从本世纪开始建构。袁鼎生认为:“中国的生态批评,不是某些留学欧美的中国学者从国外带回来的物件,也不是国外侵入的物种,而是有着中华民族生态审美根性和世界生态文明通性的前沿学科。”这种看法强调了中国生态批评在西方理论传入前就已经开展,重视了中国传统中的生态意识内涵,不过他也认为“中国生态批评在中西方生态文明的交流中生发”。[1]78与基本由中国学者提出、发展的生态美学不同,我国生态批评的发展与欧美生态批评有直接关系。2001年,清华大学教授王宁编选的《新文学史—I》中包含了利物浦大学教授乔纳森·贝特(Jonathan Bate)的《生态批评》,这是我国学界第一次翻译国外生态批评文献,也是第一次使用“生态批评”这个中文术语。当下生态批评主要人物王诺的生态批评理念,也基本是与欧美生态批评接轨的。因此,中国生态批评受西方影响很大,未来还可以借鉴西方的经验。
生态批评在中国发展的这数十年,获得了丰硕的成就,也一直伴随着质疑、伴随着对偏误和修正的思索。中国的生态批评当前的状貌如何,将往何处去,始终是摆在诸多生态批评学者面前的问题。
一、国内生态文学与生态批评的现状
中国的生态批评已经有了一定的规模。纪秀明通过数据检索分析,查证出1979年至2008年上半年,生态研究文献共 1 272 条。[2]55但是,现在对中国本土作品进行的生态批评从比例来看并不很多。国内生态批评选择的文本大多是对华兹华斯等湖畔诗人、海明威、艾米莉·勃朗特以及美国自然主义等国外的生态文本进行分析。可以明显地看出,中国的生态批评习惯性地从国外的文本中找寻资源,并不是很注重中国本土文学的土壤。
近三十年来,国内也有很多对人与自然关系进行思考的生态文学作品。宋俊宏曾把中国的生态文学文本分为四类:第一类,挖掘国土流失的现状及其原因的作品,比如苇岸的散文集《太阳升起以后》;第二类,描述草原生态环境的恶化现状及其原因的作品,比如张抗抗的中篇小说《沙暴》和姜戎的《狼图腾》;第三类,描述森林被毁坏甚至被毁绝的现状的作品,比如徐刚的报告文学《伐木者,醒来》;第四类,描述对中国西部生态的思考,比如杜光辉的《可可西里狼》。但是现在国内的生态批评有意无意地忽略了这些生态文本。以李青松为例,李青松是国内知名的环境文学作家,他创作的《遥远的虎啸》、《林区与林区人》、《告别代木时代》、《秦岭大熊猫》、《孑遗》、《老号骆驼》是典型意义的生态文本,但是国内学者对其报告文学中的生态意识进行学术剖析的论文基本没有。
国内生态文学未在生态批评领域受到重视的原因有三:第一是中国当代文学文本自身程式化、浅表化问题。许多生态文学自身表现手法单一、风格雷同,缺乏有典型性的、可资阐释的文本。许多关注生态的文学作品一味疾呼遏制人类对环境的破坏,忽视文本的审美特性,久而久之,也就产生了审美疲劳。赵树勤说中国当代生态文学的创作“数量多而精品少、轰动性强而艺术性弱,日益陷入创作的迷误”,[3]107不是完全没有道理的。第二是 2007 年中国共产党十七大报告提出“要建设生态文明,基本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但由于对经济建设的重视,唯GDP论仍然盛行,生态批评希图重建最基本的思想文化原则、形成社会共识还任重道远,生态文学和生态批评目前远未获得应有的关注,未形成整体的优质生长。第三是中国生态批评数量虽然不少,但是比较单一化、雷同化,缺乏跨学科、跨文化视野,更缺乏具有抽象理论形态的批评文章。
中国生态批评所存在的最突出问题,首先是生态批评者往往局限于将其理解为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文本考察,对“生态”的理解过于片面化和简单化,仅从字面的生态、自然、田园等出发,套用生态存在论或审美生态学的术语来完成文学批评,而不去作深层的社会历史分析,这不利于生态批评理论的深化,也失去了使生态批评持续良性发展的动力。其次是批评者习惯于为自然代言,以“生态”来掩饰深藏的对人类利益的认可,这种矫饰的态度使生态批评显得虚弱,也削弱了生态批评的现实意义。王庆卫结合《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论述,从实践美学的角度指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最终目的还是为了人,人类的任何有理智的主张和行为都不可能反对自身”[4]467。那么,生态整体主义的“把生态系统的整体利益作为最高价值而不是把人类的利益作为最高价值”,只能是“放大了的人类中心主义”。王晓华的看法与王庆卫不谋而合。他以王诺对“生态整体主义”的定义为例,指出“以生态整体的名义说话—行动(尤其是将之上升为‘主义’)会导向另一种更为偏颇的人类中心论。也就是说,如此言说的他实际上摇摆于人类中心论和反人类中心论之间,其话语已经构成了明晰的悖论。”[5]35生态整体主义所追求的“生态系统的完整、和谐、稳定、平衡和持续存在”,很明显是从人类长期利益的角度进行的言说。其次,他指出中国生态批评合法性危机的具体表现为“从新宏大叙事到二元对立思维”,即中国生态批评家在习惯于以追求宏大叙事和深度模式的生态、自然、宇宙之身份的同时,又有意地设置两种二元对立:古—今;中—西,即以古代思想、中国文化为生态品格的体现,而批判现代、批判西方。而这种对立往往是不准确的。对中国生态批评的现状,马治军曾总结为精神资源的庞杂和批评话语的空泛、哲学根基的薄弱和终极追问的乏力、批评方法的单调和切入路径的因袭、文本细读的不足和审美体验的隔膜以及批评主流的漠视与批评力量的不足等重大问题,可谓切中肯綮。[6]53
对中国生态批评的这些批评,大多是善意的而且是具有启发意义的。不过,不能否定在中国古代生态思想解读上的成就,不能只看到缺点而忽视其积极的意义,将生态批评归结为中—西、古—今的对立,认为生态批评都以回归古代为基点,仍然是片面的。比如袁鼎生的生态审美场理论亦是着眼未来而不支持返回原始。生态批评仍然很年轻,应当正视生态批评建构中出现的这些问题。学科的建构必然会走过这样的一段道路。生态批评产生于生态危机频发的当代社会,通过对文本生态价值的解读可以推动人们关心生态,具有社会价值,它仍然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二、国内生态批评的地位
要考虑生态批评的发展,首先需要正视当前生态批评的地位问题。刘蓓指出,在西方,生态批评的对象、原则、核心范畴等已经基本建立,以美国内华达大学为代表的很多大学都开设了文学与环境、自然写作研究等课程,生态批评已成为有相当力量的文学批评潮流(当然,生态批评在西方文学批评中仍然处于边缘地带)。而在中国,系统地讲授生态批评或者生态美学课程的大学还很少,关于生态批评的认识也很分散,和国外与生态平民主义、环境保护运动结合起来的环境批评、生态批评还有很大差距。
其次,在生态批评的资源获得上,由于生态批评迎合了十七大的“生态文明”的构想,国家社科基金等通过了很多关于生态批评、生态美学的课题。纪秀明指出,自1979—2008年,相关生态研究文献共有11篇属于国家基金项目科研成果,省级成果有58篇。[2]56而2008年以后每年都有以生态批评为主题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立项,以生态批评、生态美学、环境美学为主题立项的国家社科基金达到了16项,可见项目资源愈来愈有倾向性。在文本资源方面,中国本土文化资源非常丰富,民族、民间文化中包蕴的生态意识很有挖掘余地。中国当代的生态文学文本固然有《淮河生态报告》、《黄河生态报告》这样的报告文学以及《可可西里狼》、《狼图腾》这样的生态批评小说,但是精品数量仍然比较少,实际影响也比较小。
再次,中国生态批评是否具有不同于西方的独立性,是否在西方话语之外建立了自己的体系。袁鼎生认为,“中国的绿色审美范式较之西方的绿色阅读范式,避免了生态诗理和绿色诗律的缺失,实现了生态性与审美性的平衡”[1]78。无论是王诺、鲁枢元还是袁鼎生,都曾提出生态批评需要生态性与审美性的平衡,王诺也曾批评劳伦斯·布伊尔给生态批评下的定义忽略了在审美层面上的特征[7]7,但是国内单一化、平面化的生态批评方式,很难说已经实现了这种平衡或表现出这种特征。同时,也不能将西方的绿色阅读范式视作毫无审美性,这恰恰类似于王晓华所称的“中—西”二元对立。比如布伊尔就曾提出,自然的文学创作应当同时符合“科学性事实”与“审美性真实”。事实上,当下中国生态批评的西方色彩还是很浓厚的,作为生态批评理论核心的“生态整体观”更多的是从西方的源流开始梳理,而人类中心主义、生态中心主义、生态平等等概念,也都是从西方近代的生态伦理学借用过来的。国内生态批评大致仍是在西方的理论基础上以西方生态批评的言说方式进行言说,建立起有特色的中国本土生态批评话语体系尚有待时日。
生态批评在文学批评中虽然已经吸引了大量的目光,甚至可以说成为“显学”而为许多学者所接受,但是其仍然处于甚至可能将长期处于边缘地位。当然生态批评现状还处于蓬勃上升期,还拥有强大的生命力。
三、西方的生态批评发展观阐述
对西方环境批评学者来说,环境批评是具有非常强烈的现实指向的。他们大都重视生态批评的社会价值,西蒙·埃斯托克指出:“生态批评不仅仅满足于构建自足的理论体系,还应当致力于使其观念产生社会效果,使之变成政策与行动。”[7]181996年,劳伦斯·布伊尔在他出版的《环境的想象》中为环境批评下了一个相当简洁的定义:“在献身环境运动实践的精神指引下的对文学与环境关系的研究”。[7]7布伊尔坚持环境批评的提法,他强调这是在环境运动精神指导下的批评,他注重学者们以文本分析的方式来改变人们的思维方式,为现实的生态危机和环境运动做出努力。在《环境批评的未来》中,他认为生态批评的未来发展方向是强化公众对地球命运的关切、强化人类对自然的责任感和对环境非正义的耻辱感、转变人们的思维以及生活方式等等。
纽约州立大学教授马泽克(Robert P.Marzec)则坦陈生态批评对社会的影响很小,但是它很重要。他主要从“表述”(representation)来看待生态批评。他认为康拉德在《黑暗之心》中对非熟悉环境的无力的表述根本上就是人与环境分离的最好体现,而吉卜林的《基姆》中,当地人基姆被教导去为印度土地测绘,这种赋予土地以形状的“对环境的同质化描述是人占领环境、改变环境的最好体现”。[8]237马泽克据此提出,环境不仅是被人类征服的对象“environment”,还是“栖居”——inhabitancy,但 inhabitancy被圈地运动抹杀、消除了。因此,生态批评未来所面临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开启表述新平台的可能性。在这个新平台上,人类将自然视为人和其他生物共同栖居的地域,采取在环境面前言说(speaking before)的态度来建立人与环境互生互长的新关系。严蓓雯根据马泽克的理论提出:“我们应该在文学创作与文学批评中,还原人与环境的本初关系,重建由一个个互相贯穿相连又各自为营的微系统构成的人与自然的大系统,这应该正是生态批评想要看到的未来。”[7]13
无论生态批评对社会的真正影响是大还是小,只要它还能重新审视甚至重建人们生活中最基本的思想文化原则,它就是有价值的。无论是致力于产生社会效果,还是开启新的表述平台,生态批评的未来都无非是以深层生态学的生态整体主义为起点,以批判现实为手段,重新树立人与自然亲和的价值观。因此王诺说:“在目前和未来很长一段时间里,生态批评的主要任务还是思想文化批评——挖掘揭示文学作品里的生态主义思想蕴涵和反生态的思想文化蕴涵。这不仅是因为生态美学的理论体系尚未完善,更重要的是生态批评原本就是作为应对生态危机的一种文学/文化现象而出现的。”[7]13
四、国内生态批评的未来焦点
中国生态批评与西方环境批评有互通之处,也有自己的独特性。袁鼎生认为,西方生态批评是一种生态功能性批评,它的理论基础是生态伦理学和主体间性哲学。而中国式生态批评,则需要兼顾功能性与审美性的统一。也有学者指出,欧美的生态批评家与生态美学家基本分属不同的学科,而我国的生态批评基本是在生态美学的影响下,甚至生态批评学者和生态美学学者是同一批人。这些观点都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更值得注意的是,西方环境批评基本在发达国家的学者引导下成长,本国的生态环境基本已比较稳定,社会对生态的认可度较高,而中国仍是发展中国家,生态批评所面临的现实局面比西方发达国家更严峻。因此,国内的生态批评应该更加注重生态批评的中国化——现实指向性和批判性,并加快疆域拓展。
首先,疆域的拓展。生态批评疆域的扩大是个历时的、不断延伸的过程。斯洛维克认为生态批评角度可以扩展到全部文本的范围。在过去,生态批评家所谓的“环境文本”(environmental text)大多被认为是以描写和歌颂大自然为主题的文学作品。刘文良认为生态批评的文本对象主要是两类:一类是“生态”文学艺术,一类是“反生态”文学艺术。斯洛维克则指出:“没有任何一部文学作品,不管它产生于何处,完全不能被生态地解读。”[7]27事实上,生态批评除了作为文学文本批评,还可以在审美文化研究的层面上具有政治伦理批评或艺术审美批评的功能。这是被它深层生态学的理论基础所决定的,同时也是被丰富的文化批评资源和生态批评本身跨文化跨学科的性质决定的。生态批评疆域的拓展除了要求批评者具有相当广博的知识基础,比如能够同时使用气象学、地理学、人类学、生态学等各种分析手段,甚至更加科学化,将田野调查、气象调查等方法引入生态批评之中,此外,生态从来不是单纯指自然生态,而是包含人居环境、社会生态和精神生态等等在内的一个立体。生态批评的焦点也不仅仅应当是物理环境以及人类与这些物理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更应当伴随着生态批评思想的深化、切入路径的创新和文本细读的贯彻,挖掘出在文本的虚拟性之下,意识形态以及其他社会的、历史的、文化的因素的重重渗透。这种长期积淀下来的固有意识以“无意识”的方式体现在文本的社会历史环境之中,这种深层批判使生态批评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为生态美学理论提供佐证的同时也能够“反哺”生态美学。
其次,国内的生态批评和现实的结合性仍然需要加强,这是生态批评最根本的价值所在。就像布伊尔在给生态批评下定义的时候所强调的:“献身环境保护实践”。鲁枢元早在2002年就提出:“生态批评者不仅是一个严谨的学者,还应当是一个古道热肠、勇于担当的‘操心之人’。”[9]9生态批评首要地应当关注现实、促进敬畏自然的生态伦理的思想文化原则被大众普遍接受,其原因主要有:首先,生态已经逐渐引起政治关注,成为政策制定中必须考虑的环节,政治力量延伸到文学领域,为生态批评的发展提供推动力;其次,关注生态的年轻人越来越多,他们有生态意识,也充满行动力;第三,生态批评是跨学科跨文化的批评方式,除文字本身的特殊魅力以外,不同学科理论的跨界融合,为生态批评提供了长期的生长点。这样,生态批评的特定模式——包括生态批评原则和生态批评方法,也可以称为明晰的生态批评范式——就能够树立在对当下思想文化、生态事件的进攻性和批判性之上,从而以模式为依托,建立相应的组织并合法化,确立起生态批评的合法性,从而为人类缓解直至消除生态危机发挥实际影响。
再次,生态批评的中国化。有学者称现在的国内生态批评研究为“两张皮”。一方面作品分析以及理论方面跟着西方走,受西方的影响非常大,比如“生态存在论”是受到西方存在主义美学影响的,王诺的生态批评思想很大程度上是在美国生态批评学者比如斯洛维克、布伊尔的启发下发展的。另一方面本土的创作比较低落,绿色阅读、绿色写作的概念还没有深入人心,而没有经典的生态文学作品就无法形成有力的生态批评潮流。陈飞龙从西方对自然的内在价值、系统价值的普遍强调来剖析生态批评的中国话语,“西方生态批评理论在批判人类中心主义时过度地渲染了人类的自我反思,……把人的主体地位置换成自然的主体地位,一味地抬升自然,‘人’却处于隐退的状态,这就把‘人’置于一个十分尴尬的位置上。”[10]13他要求以马克思主义哲学来超越主客二元对立思维模式,悬置中心命题并超越中心化思维。袁鼎生则强调,除了对中国本土民族文化、对中国传统生态智慧的剖析,生态批评还应立足于审美和艺术等文学内在的特性来表现生态批评的中国性。事实上,把中国化问题与生态批评的现实意义结合在一起,中国化问题也就不成为一个问题。生态批评的历史使命是唤回人们对自然的敬畏和热爱,当生态批评面对国内的生态事件,对本土深层的思想文化原则进行批判的时候,它就已经实现了中国化。生态批评与其从哲学基础、中心化、审美化等角度来主张生态批评的中国风范,不如从其批评对象来进行区分。无论是中国话语还是西方话语,只要能够关注那些对国内社会和生态造成威胁的问题,它就是中国化的。
[1] 袁鼎生.生态批评的中国机理[J].鄱阳湖学刊,2013(3).
[2] 纪秀明.近三十年中国生态文学研究综述(1979—2008)——兼论生态文学与批评在中国的演进[J].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1).
[3] 赵树勤,龙其林.中国当代生态小说创作的迷误及其思考[J].邵阳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1).
[4] 王庆卫.放大的人类中心尺度:从实践美学看生态观念[J].武汉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4).
[5] 王晓华.中国生态批评的合法性问题[J].文艺争鸣,2012(7).
[6] 马治军.中国生态文学批评的偏误与修正[J].当代文坛,2012(5).
[7] 王诺.生态批评与生态思想[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
[8] 严蓓雯.生态批评的未来[J].外国文学评论,2010(1).
[9] 鲁枢元.生态批评的知识空间[J].文艺研究,2002(5).
[10]陈飞龙.试论建立起中国本土的生态批评[J].文艺理论与批评,201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