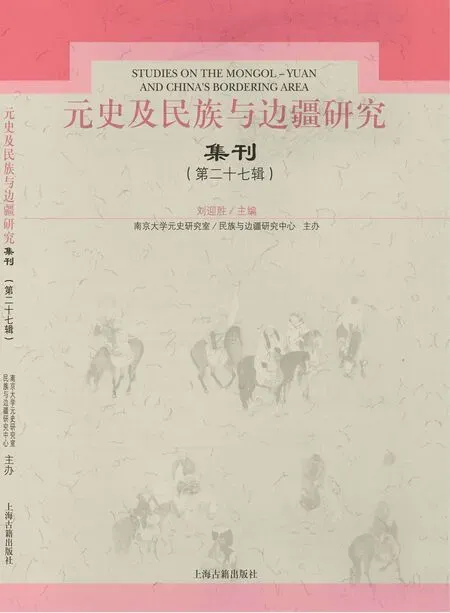试探成吉思汗灭夏的行军路线
温琪宏
试探成吉思汗灭夏的行军路线
温琪宏
本文以秦汉长城三座城堡遗址挖掘成果和古地图标示为切入点,阐述西夏北部疆界以及守卫边境的黑水镇燕、白马强镇、黑山威福三个监军司驻地。据此,论证成吉思汗灭夏战争的南侵入境、阿拉筛战场、兀剌海城、石门谷道、急渡黄河、包抄灵州、合围夏都、西扫残敌、过劳身故的史迹。根据耶律楚材扈从灭夏期间所作诗词,说明成吉思汗灵柩北辕的行踪。论文澄清蒙元和西夏史著作的若干错误,作出有益的尝试。
蒙古 成吉思汗 灭夏行军路线
成吉思汗西征中亚凯旋,立即谋划灭夏战争。其行军路线问题,自清代咸丰、同治年间李文田,光绪朝高宝铨、施世杰对《蒙古秘史》注释以来,直至民国时屠寄撰《蒙兀儿史记》、柯劭忞著《新元史》,都没有得到解决。新中国成立后的元史著作,也多沿用旧说。唯有岑仲勉于1948年写作的《元初西北五城之地理的考古》一文,提出新观点。现对岑文作些修正和补充,请求方家批评、指正。
一、 西夏军事防御体系
1225年冬,成吉思汗围猎堕马跌伤,部将脱仑(汗继父蒙力克的长子)进言:“唐兀是有城池的百姓,不能移动。如今且回去,待皇帝安了时,再来攻取。”a《蒙古秘史》卷一四,第265节,齐鲁书社,2005年,第196页;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046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280页。以下注释简称鲁版、蒙版、沪版,书名简称《秘史》。这说明蒙古军将领对西夏军事防御体系的了解很透彻,城堡必然是蒙古军攻打的目标。因此,探索成吉思汗灭夏战争行军路线,应从理解西夏的指挥系统和防御体系入手。
西夏毗邻蒙古的边界,设置三个监军司分兵把守,自西而东为黑水镇燕、白马强镇和黑山威福b徐德明、宋超智等《地图的见证 ——中国疆域变迁与地图发展》,中国地图出版社,2012年,第61页。该书认为,《西夏地形图》绘成于11世纪中期(第56页)。,作为对蒙古作战的连环型军事指挥系统,互相呼应。这是清代学者张鉴《西夏纪事本末》所附的《西夏地形图》标示的。从《西夏地形图》有“夏贼犯边之路”、“夏贼逃所”等谩骂性语言,可推断是战争敌对方宋朝军队所绘制,与当代学者考证一致,可信度极高。据白滨同志说明:
我查到与西夏有关的古地理图有伪齐阜昌七年(1137)刻的《华夷图》,图中刻有西夏境内一部分山、水与州名。石刻图藏西安碑林博物馆。此外在苏州市文庙还藏有一方古地理图石刻,据石刻图中王致远的题记,知图为宋绍熙元年(1190)任嘉
王邸翊善的黄裳所绘,献给南宋光宗皇帝的。于淳祐七年(1247)刻于石上。该图西北方标有“党项夏国”4字,并标有西夏部分州、军、山、水的位置和名称。a白滨《寻找被遗忘的王朝》,山东画报出版社,1997年,第189—190页。 盖山林《内蒙古西部地区西夏和党项人的文物》,载《前沿》1992年第3期。又载《盖山林文集》,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779页。现行蒙古语地名,按崔乃夫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名大辞典》(商务印书馆,1989年)的转写标注。
《西夏地形图》与成吉思汗灭夏之前绘制的两件石刻地理图部分契合,可以纠正《元史》将黑水、黑山混在一地的错误。“亦集乃路,下。在甘州北一千五百里,城东北有大泽,西北俱接沙碛。乃汉之西海郡居延故城,夏国尝立威福军。”b《元史·地理志》,见中华书局二十四史简体字本,2010年,第55册,第970页。以下《二十四史》引文,均为简体字本,只注册数页码。《元史》修撰者没有严谨考证,张冠李戴,才作出居延故城“夏国尝立威福军”的推论。
西夏北部军事防御体系,以内、中、外三道古长城作为前沿阵地。内长城为赵、秦时代就地取石垒筑的遗址,起于包头市固阳县九分子乡色尔腾山东坡的康图沟(沟东为夯土构筑,遗迹早已荡然),西经坝梁、西斗铺两乡,进入乌拉特前旗小佘太乡,再迤逦于中、后旗的狼山(古称连山)南坡诸山口。中长城为西汉抗击匈奴沿阴山西段北坡构筑,东起包头市达茂旗明安镇,往西偏北沿色尔腾山北坡进入乌拉特中旗新忽热苏木[Xin Нure Sum](蒙族聚居区称乡为苏木,村为嘎查;“忽热”意译“围墙”。以下括号均为蒙古语地名和人名译注),直西至川井苏木[Qongj Sum](“川井”意译“烽火台”),经后旗巴音前达门苏木[Bayan Qandaman Sum](“巴音”意译“富庶”,“前达门”意译“宝石”)和潮格温都尔镇[Qog Ondorzhan](“潮格”意译“富有朝气”,“温都尔”意译“高大”),在镇辖乌拉功嘎查折向西北入今蒙古国境,再返回额济纳居延故城北。外长城也建于西汉,起自包头市白云鄂博[Bayan Obo]矿区(原称“白音鄂博”,意译“富山”)北部,经西北的红旗牧场,往西至中旗巴音乌兰[Bayan Ulan](原设巴音、乌兰两苏木,合二为一,故称。“乌兰”意译“红色”)、川井两苏木,绵延于阴山西段以北的草原和台地,在后旗与中长城大体平行,距离最窄之处为巴音满都拉[Bayan Mandal](“满都拉”意译“兴旺”)、苏亥[Suhai](意译“红柳”)两嘎查之间地段,约5—20千米。再折向西北为牧草茂盛、地下水位浅、易掘井多清泉之地,古称 鹈泉。外长城过草地往北,进入今蒙古国古尔班赛堪[Gurban Sanqin]山(“古尔班”意译“三”,“赛堪”意译“豪杰”,山体称名巴伦[Barun,意译“西”]、敦达[Dund,意译“中”]、宗[Jun,意译“东”]三个赛堪组成)。
这三道长城遗址,经考古挖掘证实:在废弃千多年之后,西夏王朝重新利用,从原有走向的基础上进行改建、修缮、加固,作为抗击蒙古入侵的边防要塞。汉鸡鹿塞属内长城遗址,位于今巴彦淖尔盟磴口县沙金套海苏木[Xajin Tohai Sum](“沙金”意译“佛教”,“套海”意译“湾”)巴音乌拉村哈隆格乃山口西侧,在紧挨谷沟的陡壁上修筑正方形小石城,只有南墙有一门,扼守贯通狼山南北的要冲。石城内挖出两个历史遗物堆积层:“上层是西夏时期的,出土有房屋基址、灰土等,灰土中有甲片、铜弩机、铁镰刀和残陶瓷等遗物。西夏层之下,有一层历年风积的黄土,内无任何文化遗物,再往下为汉代的陶片等。”c白滨《寻找被遗忘的王朝》,山东画报出版社,1997年,第189—190页。 盖山林《内蒙古西部地区西夏和党项人的文物》,载《前沿》1992年第3期。又载《盖山林文集》,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779页。现行蒙古语地名,按崔乃夫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名大辞典》(商务印书馆,1989年)的转写标注。乌拉特后旗潮格温都尔镇西北的苏亥附近外长城有青库仑(汉蒙混合语,意译“青
色城堡”),挖出石夯、木椽、瓷片和马牛羊骨头,“都是西夏时代的遗存”a盖山林、陆思贤《内蒙古境内战国秦汉长城遗址》,载《中国考古学会第一次年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0年。又载《盖山林文集》,第694页。 王国维《鞑靼考》,载《王国维学术论著》,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151页;又载《观堂集林》(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403页。 同上,第156、第409页。;青库仑以西10余千米的中长城朝鲁库仑[Qulu Нure](汉译“石头城”),“上层有西夏的陶瓷器片、芦苇、木棍等物,下层是汉代文化层b盖山林《内蒙古西部地区西夏和党项人的文物》,载《前沿》1992年第3期。又载《盖山林文集》,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779页。。”鸡鹿塞和两个库仑均属黑山威福监军司设防区,而三道长城以西属白马强镇监军司设防区。考古成果以不可辩驳的历史遗存证实,外长城是蒙夏对峙的边界线走向。
西夏北部三个监军司辖境是多民族杂居之地,戍守古长城以“种落军”为主。“唐末五代以来,见于史籍者,只有近塞鞑靼。此族东起阴山,西逾黄河、额济纳河流域,至北宋中叶,并散居于青海附近。……欧阳公《五代史》之所传,王延德使高昌时之所经,李仁甫《续通鉴长编》之所记,皆是族也。”c盖山林、陆思贤《内蒙古境内战国秦汉长城遗址》,载《中国考古学会第一次年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0年。又载《盖山林文集》,第694页。 王国维《鞑靼考》,载《王国维学术论著》,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151页;又载《观堂集林》(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403页。 同上,第156、第409页。“阴山鞑靼,当即三十姓鞑靼或九姓鞑靼一部之南下者。”d同上,第155、第408页。有关三十姓鞑靼、九姓鞑靼、阴山鞑靼的族源和迁徙问题,可参阅张久和《原蒙古人的历史:室韦-达怛研究》(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和韩儒林《元朝史》(人民出版社,2008年 )第一章。“盖鞑靼与党项,自阴山、贺兰山以西,往往杂居,故互受通称。”e盖山林、陆思贤《内蒙古境内战国秦汉长城遗址》,载《中国考古学会第一次年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0年。又载《盖山林文集》,第694页。 王国维《鞑靼考》,载《王国维学术论著》,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151页;又载《观堂集林》(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403页。 同上,第156、第409页。西夏王朝招降邻国军民实施宽容政策。“那些远离边境的地方,同别国并无严格界线,我国全仗同吐蕃人、回鹘人和鞑靼人、女真人所建立之睦邻关系。如有寻找水草之牧民或猎户而走近两国边境,我国远近哨卡应命其返回原处,留住不愿返回者。”f《天盛年改旧定新律令》(李仲三译),宁夏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235条。“任何异国降附我朝者,应在其自愿臣服之处,将其编入边防、内防各军为卒,或编为辅正军杂役。”g同上,第387条。
二、 蒙夏阿拉筛之战
成吉思汗养伤期间,遣使质问夏主背盟,陪臣阿沙敢不[aša Gambü]出班回应:“要与我厮杀时,你到贺兰山(蒙古语音读“阿拉筛”)来战。要金银缎匹时,你往西凉(Eri☒e☒ü,蒙古语音读‘额里折兀’)来取”h《秘史》,鲁版第196页,蒙版第1046页,沪版第281页。《秘史》引文的人名、地名,按阿尔达扎布《新译集注蒙古秘史》(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5年)的拉丁字转写标注。。使者回报,成吉思汗“遂到贺兰山,与阿沙敢不厮杀”i同上。。这段史实,《元史》失载。
成吉思汗发动阿拉筛之战的行程,因“以夫人也遂从行”j同上。而居住车帐,只能走南下的车道,即唐代开辟的参天可汗道。“使者道出天德(唐朝军镇,遗址在今乌拉特前旗大佘太牧场k林幹《中国古代北方民族通论》,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333页。检《旧唐书·回纥传》载:“西城即汉之高阙塞也。西城北去碛石口三百里”(卷一九五,第32册,第3537页)。西受降城遗址,在今杭锦后旗乌加河北岸,即乌拉特中、后两旗交界处石兰计村以西的狼山口。)右二百里许,抵西受降城,北三百里许至 鹈泉。泉西北至回鹘牙
千五百里许。”a《新唐书·黠戛斯传》,第4673页。又《唐会要》卷七三载:漠北诸部酋“请于回纥以南,突厥以北,置邮驿总六十六所,以通北荒,号为参天可汗道,俾通贡马,以貂皮充赋税”。 孙进已《蒙古族的多源多流》,载《蒙元史暨民族史论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第97页。
阿拉筛之战是成吉思汗灭夏战争的重要战役之一,战场应在阿拉筛地区。“贺兰山及其临近地区在十三世纪蒙语(实际是沿袭突厥人的旧称)中读阿拉筛(alashai),近代则称阿拉善(alashan)。”b周清澍《读〈唐驳马简介〉的几点补充意见》,载《元蒙史札》,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315页。括号内文字是原文注释。检[唐]杜佑《通典·边防》卷一九七《突厥上》载:“其初国贵贱官号,凡有十等。或以形体,或以老少,或以颜色、须发,或以酒肉,或以兽名。……谓马为‘贺兰’,故有‘贺兰苏尼阙’;‘苏尼’,掌兵之官也。”(中华书局,2007年第5402页)据此可知,称名贺兰池说明古代湖形似马。阿拉筛,《秘史》旁注“山名”,是明代译者按第三次攻夏克夷门战役去理解而妄加。《西夏地形图》标示,贺兰山西北有“贺兰池”。近代地图称贺兰山为阿拉善山,难道贺兰池不能译阿拉善池吗?“贺兰池”为今著名的吉兰泰盐池,应属于贺兰山的“临近地区”。因此,理解阿拉筛不能局限于绵亘内蒙古西部和宁夏北部的贺兰山去认定,地域范围应扩大到贺兰池及以南,即白马强镇监军司辖境。阿拉筛,应按《秘史》的不同文段,酌情旁注“山名”或“地名”,如卷十四第265节应为“地名”。
吉兰泰盐池地处高原,是一个堆积盐坨的椭圆形银色的封闭残留湖泊,仅有季节性小溪流入湖,并无江河补充水源。因气候干旱,降雨量年均120毫米,多为秋雨,而蒸发量却高达4000多毫米,致使湖泊今天缩小到面积仅120平方千米,大部分液态卤水已结晶成固相盐磐,石盐储量约9600万吨,占总储85.6%。从地质构造看,盐湖位于贺兰、巴彦乌拉两山之间的断陷带,形成走向与巴彦乌拉山脊大体上平行的盆地,因断层岩上、下盘于南、北相对滑动,导致地势南高北低。据此科学推论,西夏时的贺兰池肯定面积辽阔,浸漫到巴彦乌拉山南麓。盆地塑造了湖形,登山遥望似马,称白马恰当。盐池周边无淡水,既不能作为监军司驻所,也不能当战场。
巴彦乌拉山以北的地势开豁,应为白马强镇监军司驻所。此地古名曰娄博贝,有巴彦乌拉[Bayan Ul](意译“富饶的山”,主峰1291米)、罕乌拉[Нan Ul](意译“高大的山”,主峰1883米)两山南北屏障的草原,面积约8000平方千米。现在的行政建制,仍能反映古代地貌:西为巴彦诺日公苏木[Bayannurun Sum],乡政府设在沙日布日都[Xar Burd],蒙古语“诺日公”、“沙日布日都”意译“山梁”、“金黄色的绿洲”,因挖地2米见水得名;东为罕乌拉苏木,乡政府设在乌兰呼舒[Ulan Нuxu],蒙古语“乌兰呼舒”意译“红山嘴”。这两个苏木为当年西夏统治下阴山鞑靼的牧地。漠北塔坦国应指九姓鞑靼,即“以后的乃蛮部”c《新唐书·黠戛斯传》,第4673页。又《唐会要》卷七三载:漠北诸部酋“请于回纥以南,突厥以北,置邮驿总六十六所,以通北荒,号为参天可汗道,俾通贡马,以貂皮充赋税”。 孙进已《蒙古族的多源多流》,载《蒙元史暨民族史论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第97页。,曾疯狂地掠夺娄博贝牧民财富。西夏天祐民安元年(1091),“塔坦国人马入西界娄博贝,打劫了人户一千余户,牛羊孳畜不知数目”d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七一,中华书局,2004年,第11238页。。
阴山西段的狼山与罕乌拉山东、西对峙,中间是宽约30千米、长约60千米的山坳,为一个大风口。在风蚀作用下,豁口内、外遍地砾石,成为荒漠。山口之外必然蒙夏两军交锋的战场。厮杀结果:
阿沙敢不败了。走上山寨,咱军将他能厮杀的男子并驮驮等物尽杀掳了,其余百姓纵各人所得者自要。a《秘史》,鲁版第196页,蒙版第1046页,沪版第281页。 《金史·伯德窊哥传》,第1777页。
在山坳以东有城堡依狼山构筑,名曰阿里湫城。它与娄博贝成犄角之势,互相呼应,而且扼制查素沟西口驿道,东出山口可通达内长城诸塞邮传。地处狼山西段的查素沟,今天是京新国家高速公路、临河至策克口岸铁路和S312省级公路的通道,具有交通咽喉的地位。当年蒙古军占领阿里湫城后,成吉思汗曾接见辽王耶律留哥的遗孀姚里氏。“丙戌(1226),帝还,姚里氏携次子善哥、铁哥、永安及从子塔塔儿、孙收国奴,见帝于河西阿里湫城。帝曰:‘健鹰飞不到之地,尔妇人乃能来耶!’赐之酒,慰劳甚至。”b《元史·耶律留哥传》,第2339页。大汗将阿里湫城指称为“健鹰飞不到之地”,只能与贺兰池生态环境有关。高盐分的湖区,既无大雁、天鹅、野鸭等禽鸟栖息,也不长草木不生虫,没有供猛鹰扑食的动物。这么荒凉和萧索之地,必然健鹰不来。阿里湫城只有在盐滩地之外倚山构筑,靠高山溪流解决人畜饮水。查素沟西口附近的敖伦布拉格[Olan Bulag]峡谷,为流水下切侵蚀作用形成的遗迹,可证实西夏时确有山泉。今天,蜿蜒的峡谷长达5000米,两侧为褐红色砾砂石,成刀切般的悬崖峭壁。因黄河改道、气候变迁、植被退化,导致今天峡谷已无水。蒙古语“敖伦布拉格”意译“多泉”,只能反映西夏时阿里湫城方位。
姚里氏到阿里湫城朝觐,肯定得到定居大黑河流域奚人的护送和引领。金兴定三年(1219),蒙古军攻破东胜州(今内蒙古托克托县,以下直指地名不再标注内蒙古),金朝西南路咩乣奚首领伯德窊哥、姚里鸦胡、姚里鸦儿组织部族忠义军抵抗,c《秘史》,鲁版第196页,蒙版第1046页,沪版第281页。 《金史·伯德窊哥传》,第1777页。失败后奚人归附蒙古,说明当时大黑河流域居住着奚族群(又称库莫奚,辽王之妻应为奚族)。今呼和浩特市东郊白塔机场附近(蒙元丰州故城),矗立着辽代建造的万部华严经塔,有六块碑铭,其中第三块却载“康家巷乣首善政”、“张家峪乣首王守清”等与奚人有关的题名,也证实确有奚人定居大黑河流域。库莫奚世居老哈河(今赤峰市境)和大凌河(今辽宁西部)两流域,被辽金统治者将某些部落强迁至边境,抗击西夏。如果没有同族帮助,姚里氏不可能从辽阳来到遥远的阿里湫城。
雪山方位,肯定离蒙夏两军厮杀战场不远。“成吉思在雪山住夏,调军去将阿沙敢不同上山的百姓尽绝掳了。”d《秘史》,鲁版第198页,蒙版第1047页,沪版第282页。这个雪山,只能是从西南走向东北的巴彦乌拉山,因地处北纬40.5°,春夏缺雨,秋偶有阵雨,又早寒冷。山阳湖水高蒸发,在刮东南风时气流与山体垂直,致使地形雨变成孟秋雪;山阴的积雪,因夏季阳光偏南斜照而不全溶。时至今日,盐湖变成盐矿,无水可蒸发,形成雪山的环境早已消失。当年西夏残败之兵只有弃守,沿着湖东的阿贵山(阿左旗与磴口县界山)南奔逃难,却摆脱不了被俘的命运。追击夏国残兵的蒙古将领,是左、右万户孛鲁和博尔术(《秘史》称名孛斡儿出)。孛鲁为木华黎之子,因父死于癸未(1223)而袭国王、左手军万户。“乙酉(1225)春,复朝行在所”,“丙戌(1226)
夏,诏封功臣户口为食邑,曰十投下,孛鲁居首”。a《元史·孛鲁传》,第1938页。 《元史·地理志》,第970页。 《元史·太祖本纪》,第15页。据此可证:两万户主力军都在大汗御前参与阿拉筛之战。
三、 黑城无战事
黑城被史家误解为成吉思汗统军亲征首先攻下的西夏要塞。错误源于《元史》记载:“二十一年丙戌……二月,取黑水城。”b《元史·太祖本纪》,第15页。但史文前后矛盾:“亦集乃路……元太祖二十一年内附。”c《元史·孛鲁传》,第1938页。 《元史·地理志》,第970页。 《元史·太祖本纪》,第15页。内附是主动请降,并非战争征服。从灭夏战况看,黑水镇燕监军司是被蒙古西路军切断后路而请降的。甲申(1224),成吉思汗在额儿的石(今流经我国新疆和哈萨克斯坦国的额尔齐斯河)地面过夏时,“帝欲征河西,以速不台比年在外(指西征中亚七年),恐父母思之,遣令归省。速不台奏,愿从西征(指灭夏)。帝命度大碛以往。丙戌,攻下撒里畏吾、特勤、赤闵等部(今内蒙古额济纳旗西部和甘肃安西、肃北两县),及德顺(今宁夏隆德县)、镇戎(今宁夏固原市)、兰、会、洮、河诸州,获马五千匹,悉献于朝”。d《元史·速不台传》,第1966页。速不台“度大碛以往”,必然途经额济纳黑城,因城外鞑靼牧民多叛离西夏,监军司只能在兵临城下时请降。另有一支阿塔赤统率的西路军假道高昌(今新疆鄯善县鲁克沁),“取甘(今甘肃张掖市)、肃(今甘肃酒泉市)等州。秋,取西凉府搠罗、河罗(两罗在今甘肃庄浪县)等县,遂逾沙陀,至黄河九渡(今宁夏中卫县的黄河渡口),取应里(今中卫县城)等县”。e《元史·孛鲁传》,第1938页。 《元史·地理志》,第970页。 《元史·太祖本纪》,第15页。西夏肃州守将“率豪杰之士,以城出献。又督义兵助讨不服”。f白滨、史金波《“大元肃州路也可达鲁花赤世袭之碑”考释》,载《民族研究》1979年第1期。难道依靠河西各州供应军需和粮食的黑水镇燕军还能抵抗吗?
黑水城何时内附,可从耶律楚材东归行程得到解释。耶律楚材自陈:“牢落十年扈御营。”g耶律楚材《用李德恒韵寄景贤》,载《湛然居士集》(以下简称《文集》)卷二,《四库全书》,第1191册,第501页。这十年,从1218年春应诏晋见成吉思汗开始,到1227年冬奉命“搜索经籍,驰驿来燕”h耶律楚材《西游录》,中华书局,2000年,第1页。为止,包括灭夏战争时期在内。据考,耶律楚材约有一年没有“扈御营”i向达《西游录前言》,载耶律楚材《西游录》,第6—7页。,而是随灭夏西路军东进,其行程:乙酉日南(1225年冬至)在高昌城,丙戌重午日(1226年端午)在肃州;此后有诗“憇马居延酒半醺,寂寥寒馆变春温”j耶律楚材《过天山周敬之席上和人韵二首》,载《文集》卷二,第504页。据王国维考证:周敬之为天山县太守,此诗写于壬辰(1232),回顾六年前(丙戌)过居延时设宴情景,与天山县宴席相似。的记载,应指在“汉之西海郡居延故城”。耶律楚材一生,只有丙戌年到居延的一次机会。如果成吉思汗率军从黑水城南下攻肃、甘两州,那么耶律楚材就没有必要到居延。寒馆是陋漏的驿站,显得很寂寥,只有设宴接待才有春温之感,一派和平景象。他离开西路军北上居延是奉诏返回汗营,时值成吉思汗在雪山住夏。
昔里钤部是护送耶律楚材的合适人选。有史为证:“命钤部同忽都铁穆儿招谕沙州
(今甘肃敦煌市)。州将伪降,以牛酒犒师,而设伏兵以待之。首帅至,伏发马踬,钤部以所乘马与首帅使奔,自乘所踬马而殿后,击败之。他日,帝闻曰:‘卿临死地,而易马与人,何也?’钤部对曰:‘小臣阵死,不足重轻,首帅乃陛下器使宿将,不可失也。’帝以为忠。”a《元史·昔里钤部传》,1989页。 高宝铨《元秘史李注补正》,载《秘史》,沪版第589页。 李治安、薛磊《中国行政区划通史·元代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87—188页。这是昔里钤部觐成吉思汗时的情景,前段是别人或者耶律楚材给大汗报告沙州事件中钤部的功绩,后段是大汗殿前与钤部当面对话,所指“他日”即沙州事件和肃州献城之后。这个史迹,可证昔里钤部护送耶律楚材返回汗营的推断是可信的。楚材在大汗身边当必阇赤,是个白面书生,如果没有党项人昔里钤部率众护卫,通行夏境实在寸步难行;昔里钤部因兄长为西夏坚守肃州有时,按大札撒(汉蒙混合语,“札撒”汉译“法度”)当戮,有求于耶律楚材在殿前说情,免杀其亲族。
四、 过兀剌海城
兀剌海方位,自清代以来史家争论不休。施世杰指认今甘肃龙首山b施世杰《元秘史山川地名考》,载《秘史》,沪版第649页。,高宝铨比定为明长城夏口城关(今甘肃山丹县城西十号村)c《元史·昔里钤部传》,1989页。 高宝铨《元秘史李注补正》,载《秘史》,沪版第589页。 李治安、薛磊《中国行政区划通史·元代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87—188页。,唯独岑仲勉坚持在“今狼山西口(古高阙)处之附近”d岑仲勉《元初西北五城之地理的考古》,载《中外史地考证》(下),中华书局,2004年,第539页。。虽然“古高阙说”,为现代的出土文物考古成果所否定e《元史·昔里钤部传》,1989页。 高宝铨《元秘史李注补正》,载《秘史》,沪版第589页。 李治安、薛磊《中国行政区划通史·元代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87—188页。。据测,新忽热古城遗址面积68万平方米,比额济纳黑水城(384×434)大三倍f李逸友《内蒙古元代城址概说》,载《元上都研究文集》,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54页。城倚黑山(今色腾尔山),可定名兀刺海。[日]江上波夫等《蒙古高原行纪》,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53页。该书载:1935年日本人曾到这座土筑古城遗址,并绘简图。,而且地处黑山,必为西夏威福监军司驻地。岑仲勉的考证虽有缺陷,仍有开创性的意义。
曾经作为西夏监军驻地的兀剌海城,其遗址在今乌拉特中旗新忽热苏木所在地北1千米的丘陵地上,濒临发源于哈达图山系南麓的摩楞河[Moroi,意译“弯曲”,河水流经内长城注入黄河]。古城四周高山屏障,地势险要:南靠肖崩[Xobong,意译“尖顶山”,高1599米];北望沙日恩格尔[Xar Engger,意译“黄色山阳”],山体西连希热花[Xire Нua,意译“桌子状的山”,高1784米];东有布拉山(高1671米),北坡的布拉根阿木[Bulaginam,意译“泉沟口”]为北流的开令河发源地,南坡外为红花脑包草原,可通石门。东、北山体外坡环绕着中长城,唯有古城东北20千米处的哈布其勒[Нobqil,意译“峡谷”],马、驼可便捷往返于各设防城塞和关隘。这样的地理环境,造就了威福监军司与中、外长城紧密的地缘关系。
色尔腾山由哈达图[Нadt](意译“岩石地”)、查斯泰[Qastai](意译“积雪处”,可证古代内蒙古西部有几个雪山)、白云常合三支构成,自东北向西南绵延,古代统称黑山。唐开元三年(715)“诏知运领朔方兵募横击之,大破贼众于黑山呼延谷”g《旧唐书》卷一○三《郭知运传》,第2161页。。据此,呼延谷肯定在黑山。又载“中受降城(遗址在今包头万水泉火车站以南的敖陶窑村)正北如东
八十里,有呼延谷,谷南口有呼延栅,谷北口有归唐棚,车道也,入回鹘使所经”a《贾耽四道记》,载《古西行记》,宁夏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41页;又载《新唐书·地理志》卷四三(下),第33册,第753页。 岑仲勉《元初西北五城之地理的考古》,载《中外史地考证》(下),中华书局,2004年,第531页。括号内文字为原文注释。 吴广成《西夏书事》卷四○。。现代史家解释呼延谷为昆都仑沟、呼延棚在昆都仑召,从而割断了呼延谷与黑山的关联。这个错误源于史文标点不当,应改“中受降城正北,如东八十里有呼延谷……”昆都仑河“如东”之地在固阳县城西南与乌拉特前旗交界处,距县城19千米,再折向北偏西20千米可达色尔腾山的康图沟北,即古称呼延谷南口。如此解释,符合“如东八十里”的记载。今包头火车东站到固阳县城约80千米(21世纪初,建成大青山隧道后里程缩短至62千米),如从包头火车站走昆都仑沟到县城约90千米,用于解释“中受降城正北如东八十里”b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安唐城发掘队《唐代长安城考古纪略》,载《考古》1963年第11期。该文确证:唐代三百步为一里,一步实为1.47米,故80里等于35.28千米。,实难讲通。
蒙古军攻打西夏多达六次,其中:第二、三、六次都曾到兀剌海城。该城方位,岑仲勉从《元史·地理志》“太祖四年(第三次攻夏),由黑水城北兀剌海西关口入河西,获西夏将高令公,克兀剌海城”的记载中提出问题:“明言兀剌海在黑水城北,若以龙首山当之,是兀剌海乃在一般人所称黑水之东南(尤其是那珂氏认黑水城在张掖河),即此而观,吾有以窥其未确矣。”c《贾耽四道记》,载《古西行记》,宁夏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41页;又载《新唐书·地理志》卷四三(下),第33册,第753页。 岑仲勉《元初西北五城之地理的考古》,载《中外史地考证》(下),中华书局,2004年,第531页。括号内文字为原文注释。 吴广成《西夏书事》卷四○。元朝在兀剌海设路(下路),与龙首山、夏口城所在的甘州路(上路)平级,也否定了黑水城在张掖河的推断。
“兀剌海西关口入河西”,是蒙古军第三次攻打西夏的行军路线。这次伐夏,“帝入河西,夏主李安全遣其世子率师来战,败之,获其副元帅高令公。克兀剌海城,俘其太傅西壁氏。进至克夷门,复败夏师,获其将嵬名令公”d《元史·太祖本纪》,第10页。。克夷门是拱卫西夏王城中兴府的重要门户,“两山对峙,中通一径,悬绝不可登。元昊时,尝设右厢朝顺监军司,兵七万守之”e《贾耽四道记》,载《古西行记》,宁夏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41页;又载《新唐书·地理志》卷四三(下),第33册,第753页。 岑仲勉《元初西北五城之地理的考古》,载《中外史地考证》(下),中华书局,2004年,第531页。括号内文字为原文注释。 吴广成《西夏书事》卷四○。。据今人考证,克夷门位于今石嘴山市大武口区“西北约百里,有通贺兰山以西的要路山口”,f王天顺《河套史》,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7页。按地望推测可能在今平罗县西北的白芨沟到汝箕沟之间,与《西夏地形图》标示“夏贼逃所”、“木栅行营”方位一致。因此,兀剌海西关口应在西行的中、外长城之间距离最狭窄之处,即今乌拉特后旗潮格温都尔镇西北的苏亥城障之地,有公路从南向北穿城而过,两道长城间隔约5千米。从此关口折向南,越过狼山某山谷,直奔贺兰山西北坡的今北寺(即《西夏地形图》标示“五台山寺”之地)附近,应为克夷门的西山口。蒙古军到此,因埋伏于山谷的夏军凭险出击,只好暂时退出山口。大汗以退为进,改变强攻战术,派军入谷引诱夏军追击,待进入伏击圈,群起围攻。夏军精锐遭歼,主将被俘。夺门之战相持两个多月之久。成吉思汗在灭夏时吸取教训,不再强攻贺兰山,只住雪山避暑,吸引夏军死守贺兰山诸山口(《西夏地形图》标示,贺兰山西北坡“有谷道九条”)。
兀剌海城在蒙古军第三次攻打西夏时已归属蒙元版图。第六次灭夏时,孛鲁任命部将贾搏霄为冀北元帅,临时统治黑山以西的新占领区。“王师西征,贤帅贾公留后,于云内
筑除戎堂于城之西阿,以练戎事,御武折冲,高出前古。”a耶律楚材《除戎堂序》,载《文集》卷七,第544页。王国维《耶律文正公年谱》,考定作于丙戌(1226),有误。序文:“予道过青冢,公召予宴于是堂。”应为丁亥冬湛然从沙井返燕途经青冢,诗只是回顾丙戌之事。丙戌夏起,楚材扈从灭夏,不可能到云内州。 [清]齐召南《水道提纲》卷五。 耶律楚材《过夏国新安县》,载《文集》卷三,第511页。诗中的“天山”,向达为《西游录》作《前言》解释:“元朝人一般称阴山为天山,而称新疆境内的天山为阴山。”王师西征指孛鲁随驾灭夏,而贾搏霄却留在后方,筑帅府于云内州。新帅职责是“坐镇大河兵偃息,居延不复塞尘惊”b耶律楚材《除戎堂》,载《文集》卷七,第544页。。可见,原西夏北部三个监军司设防之地,都归贾搏霄元帅掌控。
五、 喀喇木伦与黑水城
喀喇木伦为昆都仑河之异称。黄河“其北岸大者曰昆都仑河,即喀喇木伦也,源出毛明安界内,南经诸山,……南入黄河”c耶律楚材《除戎堂序》,载《文集》卷七,第544页。王国维《耶律文正公年谱》,考定作于丙戌(1226),有误。序文:“予道过青冢,公召予宴于是堂。”应为丁亥冬湛然从沙井返燕途经青冢,诗只是回顾丙戌之事。丙戌夏起,楚材扈从灭夏,不可能到云内州。 [清]齐召南《水道提纲》卷五。 耶律楚材《过夏国新安县》,载《文集》卷三,第511页。诗中的“天山”,向达为《西游录》作《前言》解释:“元朝人一般称阴山为天山,而称新疆境内的天山为阴山。”。蒙古语“喀喇”汉译黑;“木伦”,译水或河。昆都仑河,长130千米,发源于固阳、武川两县(清代属茂明安部,今分别属包头、呼和浩特)的界山,即大青山北支。上游自东向西流;中游从固阳县城西沿色尔腾山南侧折向西南,至明安川再向东南迂回山体之间;下游穿切大青山和乌拉山之间的山梁,折向南经包头市区流入黄河。喀喇木伦[Qara Moron]的称名,源于上游黑石林沟的地貌。地处河上游的银号乡以东界山(上世纪曾设东公此老乡),因黑石裸露又少林木掩蔽,受风雨浸蚀致沟壑纵横。雨天,黑洪奔流而下;晴天,河谷遍地黑沙。分水岭东坡延亘着古长城、城下道路古称白道。河下游穿切山梁处,两岸山壁高耸如门,但河道的谷地却平坦宽阔,可通车马,为穿行南北天崭的坦途,古称黑道。此地被北魏人称为石门,“河水又东流,石门水南注之。水出石门山,《地理志》曰‘北出石门障’,即此山也”d[后魏]郦道元《水经注》卷三。。
石门(今昆都仑沟,包白铁路至沟北有石门村车站)是蒙古大军隐秘南下的通道。随军扈从的耶律楚材于“丁亥(1227)九月望”作诗,记载前三年这一天蒙古大军的行踪,其中第二年(1226)诗句:“瀚海潮喷千浪白,天山风吼万林丹。气当霜降十分爽,月比中秋一倍寒。”e耶律楚材《除戎堂序》,载《文集》卷七,第544页。王国维《耶律文正公年谱》,考定作于丙戌(1226),有误。序文:“予道过青冢,公召予宴于是堂。”应为丁亥冬湛然从沙井返燕途经青冢,诗只是回顾丙戌之事。丙戌夏起,楚材扈从灭夏,不可能到云内州。 [清]齐召南《水道提纲》卷五。 耶律楚材《过夏国新安县》,载《文集》卷三,第511页。诗中的“天山”,向达为《西游录》作《前言》解释:“元朝人一般称阴山为天山,而称新疆境内的天山为阴山。”诗前阙上句,在“千浪白”之下注“一作十里雪”,可解读:成千的白沙丘似海浪,或者行军十里于白沙地。诗描绘的情景,显然是明安川(唐代称大同川)和昆都仑沟深秋季节的地貌。内蒙古西部沙漠呈黄色,唯有地处明安川的苏吉沙漠色白,原因在于昆都仑河远古时西流于白云常合山与乌拉山之间注入黄河(古代经流在河套之北,支流在套南)的故道,后来地层抬升才改道南流。原河道形成两山夹峙的河相盆地,在风蚀作用下变成走向东、西的长巷状白沙漠。f白沙主要化学成分是二氧化硅(SiO2),纯度高者显白,含杂质时成淡黄、深黑、紫等色。明安川现已建取砂铁路专用线,从包白线的朝阳车站至黑山湾。此处白沙是包头市机械工业铸造用型砂的基础材料,要求粒度均匀,不含杂色,才具有耐高温性能。当年成吉思汗统率的蒙古大军,从明安川到昆都仑沟正好马行一程。时值九月中旬的昆都仑沟是个大风口,蒙古高原的干燥寒风呼啸穿谷南下,霜冻比山南平原早一个月,石门两山才有“万林丹”的景观。
昆都仑河下游入黄河之地,即今包头市火车站西南有一座燕家梁古城,应为蒙元时代
的黑水城。称名除与喀喇木伦有关以外,方位在兀刺海城之南稍偏东,地望与《元史》记载吻合。此黑水城是黄河渡口,境属云内州云川县(治所今土默特右旗大城西乡)管辖,与西夏胜州西北部(今鄂尔多斯市达拉特旗昭君坟、解放滩两乡;解放滩本名碱坊滩,以近音改名)隔河相望,为蒙古水军的重要基地之一。当年成吉思汗大军从此渡黄河攻打西夏灵州,有诗为证。“去岁云川始见君,澄澄胸次净无尘。斗南第一珪璋士,冀北无双柱石臣。万顷云松斜谷外,千竿水竹渭河滨。”a耶律楚材《再用韵以美搏霄之德》,载《文集》卷三,第512页。 《元史·耶律楚材传》,第2299页。《宋史·夏国传下》,转引自王天顺《西夏战史》,宁厦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5页。又见李蔚《西夏史》,人民出版社,2009年,《中国历史》第10册,第13页。据《地图的见证》有金朝绘制于贞祐二年(1214)的《陕西五路之图》(第68页)标示,成吉思汗于丁亥春夏亲自率师西扫残敌时,侵入金国的陕西熙河路和秦凤路西境。此诗“柱石臣”之下注:“公领帅职故云。”显然赞赏贾博霄操持蒙古大军渡河的组织工作,征调成千水手待命,就像为秦皇渡渭河幸咸阳、长乐两宫那样周到。这个黑水城,在云内州辖境是唯一地处“万顷云松斜谷外”的渡口,有石门谷风劲吹,最适合扬帆急渡黄河。
黑水城渡口是攻打灵州最便捷的水道。西夏灵州辖境很大,包括今鄂尔多斯市鄂托克旗、鄂托克前旗沿河地带和乌海市。蒙古军过渡口后,沿黄河支流的南河边水草丰盛之地行进,很快可攻入灵州地界。“冬十一月庚申(初九),帝攻灵州,夏遣嵬名令公来援。丙寅(十五日),帝渡河击夏师,败之。丁丑(二十六日),……驻跸盐州川。”b《元史·太祖本纪》,第10页。
成吉思汗行军和东、西两军合围灵州的时间安排,肯定咨询过“通天文、地理、律历、术数及释老、医卜之说”c耶律楚材《再用韵以美搏霄之德》,载《文集》卷三,第512页。 《元史·耶律楚材传》,第2299页。《宋史·夏国传下》,转引自王天顺《西夏战史》,宁厦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5页。又见李蔚《西夏史》,人民出版社,2009年,《中国历史》第10册,第13页。据《地图的见证》有金朝绘制于贞祐二年(1214)的《陕西五路之图》(第68页)标示,成吉思汗于丁亥春夏亲自率师西扫残敌时,侵入金国的陕西熙河路和秦凤路西境。的耶律楚材,很符合河套地区季节更替和气候变化规律。九月中旬,昆都仑河洪季已过,只有清澈的涓涓细流,河滩宽阔,可行千军万马;过早了,往往月明如昼的夜晚,突然阴云蔽天,雷鸣电闪,大雨滂沱,随之而来的山洪,有如山崩地裂,水石撞击,巨响轰鸣,行军遇洪只有灭顶之灾。九月下旬,黑水城处于石门谷风控制之下,适合船舶扬帆南渡黄河; 早了,刮东南风无法过渡。十一月初九,刚过小雪,黄河冰层薄,蒙古军可从东、西两面夹攻灵州,而夏军马不能踏薄冰过河增援;十五日,已近大雪,冰层冻厚,很适合蒙古战马踏冰过河歼灭夏国援军。如果攻灵州时间提前,虽能破城,夏援军因黄河流凌也无法增援,但蒙古军也不能过河,坐失围城打援的机会。
六、 成吉思汗灵柩北辕
丁亥(1227)春夏,成吉思汗戎马倥偬,疲劳过度。“春,帝留兵攻夏王城,自率师渡河攻积石州(今青海循化县)。二月,破临洮府(今甘肃临洮县)。三月,破洮(今甘肃临潭县)、河(今甘肃临夏市)、西宁(今甘肃会宁县)三州。”“夏四月,帝次龙德(今宁夏西吉县将台乡以南的火家集),拔德顺等州。”d《元史·太祖本纪》,第10页。成吉思汗攻打的地方,超出西夏“东据黄河,西至玉门,南临萧关,北抵大漠,境土方二万余里”e耶律楚材《再用韵以美搏霄之德》,载《文集》卷三,第512页。 《元史·耶律楚材传》,第2299页。《宋史·夏国传下》,转引自王天顺《西夏战史》,宁厦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5页。又见李蔚《西夏史》,人民出版社,2009年,《中国历史》第10册,第13页。据《地图的见证》有金朝绘制于贞祐二年(1214)的《陕西五路之图》(第68页)标示,成吉思汗于丁亥春夏亲自率师西扫残敌时,侵入金国的陕西熙河路和秦凤路西境。的范围,战火已烧到金朝西部疆域。
成吉思汗病故是灵柩北辕的起点。五月“闰月,避暑六盘山。六月,……帝次清水县
西江(今甘肃清水县牛头河支流)。秋七月壬午(初五),不豫”a《元史·太祖本纪》,第10页。鲁人勇、吴忠礼、徐庄《宁夏历史地理考》,宁夏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41页。[清]萨囊彻辰《蒙古源流》,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90页。。不豫只是病重,并非死亡。“殁于图尔默格依城(清译灵州,《秘史》明译朵儿篾该[Dör megai ]),时岁次丁亥七月十二日。”b[清]萨囊彻辰《蒙古源流》,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89页。这个时间,与《元史》记载“己丑”相合。夏国灵州治所在今吴忠市北古城乡西北的古城村,“北魏始置灵州。唐、五代、北宋因之”c《元史·太祖本纪》,第10页。鲁人勇、吴忠礼、徐庄《宁夏历史地理考》,宁夏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41页。[清]萨囊彻辰《蒙古源流》,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90页。。此地是蒙古军围攻西夏都城的大本营,到清水县不会超过六天。因此,屠寄认为:“诸书皆称成吉思殂于六盘,不如《蒙古源流》殁于图尔默格依之可信。”d屠寄《蒙兀儿史记·成吉思汗纪》,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影印本,第56页。
大谔特克省嵬山是成吉思灵柩暂存之地。大汗归天之时正是三伏酷暑第九日,必须入殓送山入窟存放于阴冷处。“在阿拉坦山阴、哈岱山阳之大谔特克地方。”e《元史·太祖本纪》,第10页。鲁人勇、吴忠礼、徐庄《宁夏历史地理考》,宁夏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41页。[清]萨囊彻辰《蒙古源流》,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90页。谔特克,即今鄂尔多斯市鄂托克旗,清代称鄂尔多斯右翼中旗;“阿拉坦山即此右翼中旗西北之阿尔布坦山。该旗西北阿尔布坦山,旧名省嵬山。”f[清]张穆《蒙古游牧记》。西夏省嵬山,在20世纪中期从鄂托克旗划出归乌海市海南区管辖;因山得名的省嵬城遗址,现位于宁夏石嘴山市惠农县庙台乡,为古城考古所证实g《宁夏石嘴山市西夏城址试掘》,载《考古》1981年第1期。。但遗址原本在山下河东h《嘉靖宁夏新志》卷二《古迹》记载:“省嵬城,河东废城,未详其出。”可证为成吉思汗摧毁。,因黄河改道东移而变位河西,与山隔河相望。成吉思死后,秘不发丧,灵柩停放于省嵬山某石窟约一个多月之久。
耶律楚材是大汗灵柩北辕的见证人。“丁亥(1227)九月望”过夏国新安县,即今乌拉特前旗新安镇。夏国新安县地处黄河南流段的西岸。“河套黄河河道具体方位者,惟‘北河’为经流,‘南河’为支流此一基本形势不变,则至明代后期犹有明征。”i谭其骧《北河》,载《长水集》(下),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51页。以现代地图标示说明:从今磴口县巴彦高勒镇以下北流的乌加河,原本为黄河主干,称北河;从补隆淖分流向东偏北的一支,即今黄河,蒙元时是支流,称南河。乌加河北流,抵狼山下,东折成弓形,至乌拉山西山嘴,与南河合。地处古黄河南流段西岸的新安镇是西夏的一个渡口,东可渡乌拉山北,南至鄂尔多斯。
成吉思灵车在新安县渡河后,曾深陷泥淖。“行至穆纳之泥淖处,岱车之毂陷住、深达辐轴而移动不得,套上各色牲畜都拽不出。普土大国全体黎庶在忧虑,雪你惕(部落名)的吉鲁格台(人名)把阿秃儿(汉译勇士)禀说……奏毕,汗主垂恩,施以慈悯。于是岱车辚辚徐动,众庶欢欣,运往汗山大地。”j贾敬颜、朱风译《蒙古黄金史纲》,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32—35页;萨囊彻辰《蒙古源流》记载相同,第189—190页。
穆纳是山名,今称乌拉山。“穆纳之泥淖处”,应在今乌拉山西南的乌梁素海附近。元朝至顺元年(1330)十月“木纳火失温所居诸牧人三千户、濒黄河所居鹰坊五千户,各赈粮两月。”k《元史·文宗纪》,第519—520页。木纳,即穆纳;火失温[goši’un],蒙古语汉译“山梁尽头处”,或“山嘴”。l《蒙古黄金史纲》,第25页。牧
人三千户、鹰坊五千户肯定居住在同一个地方。明宣德九年(1434),蒙古北元内讧,阿鲁台大师在兀良哈(今内蒙古东部)被卫拉特拥立的脱脱不花可汗战败,逃窜漠南西部,败亡于“黄河母纳之地。”a《明史·瓦剌传》,第569页。 耶律楚材《扈从旋师道过东胜秦帅席上继杜受之韵》,载《文集》卷一四,第627页。 李逸友《内蒙古元代城址概说》,载《元上都研究文集》,第147页。这也证明黄河、穆纳距离很近。
蒙古军沿河东行,从夏国进入蒙元统治区,并未通知地方官员。沿河滩地,因春季水道流凌卡冰成坎而引发洪水泛滥所淹没,导致无人敢筑屋居住,但夏秋水草丰足。因此,在河漫滩地行军既有利于屏蔽大汗灵柩北辕信息,又有利于战马歇鞍吃夜草长膘。“一鞭赢马渡天山,偶到云川暂解鞍。独守空房方丈隐,更无薄酒一杯饯。诗书半蠹绝来客,釜甑生尘笑冷官。赖有觉非(原注:飞卿道号)怜野拙,长须为我馈盘餐。”b耶律楚材《谢飞卿饭》,载《文集》卷四,第515页。云川是蒙古军从夏国入境的第一个县,归云内州管辖。县城遗址,在今包头市土默特右旗大城西乡,南临河北靠山(元称天山),地形狭窄,扼守要道。蒙古军到云川时,市井萧条,百姓流离,一派战乱景象。
蒙古大军到东胜州,却别有天地。“东胜城无恙,西征事若何!凭高吟望久,尊酒酹长河。”c《明史·瓦剌传》,第569页。 耶律楚材《扈从旋师道过东胜秦帅席上继杜受之韵》,载《文集》卷一四,第627页。 李逸友《内蒙古元代城址概说》,载《元上都研究文集》,第147页。此诗题明“扈从旋师过东胜”。东胜州是古代从关中通往漠北的交通要道,城西大黑河口西侧有倚山古渡,与黄河对岸的西夏榆林城相望。榆林是胜州的属县和治所,遗址在今鄂尔多斯市准格尔旗十二连城乡以北,临河设榆关d李作智《隋唐胜州榆林城的发现》,载《文物》1976年第2期。因周围有12座古城遗址,得名“十二连城乡”。。辽国攻破西夏胜州,将其民迁河东,故称东胜州,其遗址在今托克托县城内西北隅的台地上,濒临大黑河口,俗称“大皇城”e《明史·瓦剌传》,第569页。 耶律楚材《扈从旋师道过东胜秦帅席上继杜受之韵》,载《文集》卷一四,第627页。 李逸友《内蒙古元代城址概说》,载《元上都研究文集》,第147页。。所谓“扈从”,指天子巡幸随从之人,可见成吉思灵柩北辕曾经东胜州,因秘不发丧仍按生前称呼作诗。虽然战乱没有波及,却缺繁荣气息。“荒城潇潇枕长河,古寺碑文半灭磨。青冢路遥人去少,黑山寒重鹰来多。”f耶律楚材《过东胜用先君文献公韵二首》,载《文集》卷三,第511页。青冢是汉代宫女王昭君的墓地。她出于维护民族团结大局,远嫁匈奴为单于后,死后葬在大、小黑河之间辽阔无垠的敕勒川,历代中原百姓和文人墨客经东胜州到此朝拜。其墓在今呼和浩特市南20千米,而“地多白草,此冢独青,因名”g[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山西大同府》(第四册)卷四四,中华书局,2010年,第2018页。。
成吉思灵柩从东胜州到沙井的路线,显然是溯大黑河、枪盘河而上,穿夹山谷地越过河源山梁,再沿希拉穆仁河[Xar Moron](“希拉”,意译“黄色”)顺流而下。到沙井时已经入冬,寒气袭人。“莫忘天山风雪里,湛然驼背和君诗”,夹注:“余昨至沙井乘牛车过前路,跨驼方达行在。”h耶律楚材《丁亥过沙井和耶律子春韵二首》,载《文集》卷二,第504页。诗题“丁亥过沙井和耶律子春韵二首”,也确证灵车经此出塞。沙井,在蒙元时代是汪古部世袭领地,遗址“在今四子王旗红格尔苏木[Нonggor Sum](“红格尔”,意译“可爱的”)所在地。”i李逸友《内蒙古元代城址概说》,载《元上都研究文集》,第144页。耶律子春的身世,可从该旗大黑河乡西北四十顷地村“王墓梁”陵园内的《耶律公神道之碑》知道其梗概。此碑是耶律子成后人所立,现存呼
和浩市内蒙古博物馆。据考:墓主是西域帖里薛人,在辽圣宗时被册封为太尉开府仪同三司,并赐辽国姓耶律氏。子成信奉基督教聂思脱里派,一生只是景教寺主,管领也里可温;其兄子春,在沙井总管府做官a盖山林《元“耶律公神道之碑”考》,载《内蒙古社会科学》1981年第1期。又载《盖山林文集》,第802—807页。 李逸友《内蒙古元代城址概说》,载《元上都研究文集》,第143页。 耶律楚材《再用韵自叹行藏》,载《文集》卷三,第512页。。湛然与子春相聚一夜,分别时的驼背和诗却流露大汗行踪,是成吉思灵车经沙井的确证。
沙井是大漠南北的重要交通要道。“天山之北皋,陆衍迤联,亘乎大莫。”b[元]陈旅《赠沙井徐判官诗序》,载《全元文》(第37册),凤凰出版社,2004年,第251页。它地处希拉穆仁河东岸,沿河南溯至净州(天山县治所,为辽金元三朝榷场,遗址在“今四子王旗城卜子村”c盖山林《元“耶律公神道之碑”考》,载《内蒙古社会科学》1981年第1期。又载《盖山林文集》,第802—807页。 李逸友《内蒙古元代城址概说》,载《元上都研究文集》,第143页。 耶律楚材《再用韵自叹行藏》,载《文集》卷三,第512页。)八十里,北邻金界壕。“出沙井,则四望平旷,荒芜际天,间有远山,初若崇峻,近前则坡埠而已,大率砂石。”d[南宋]彭大雅撰,徐霆疏《黑鞑事略》,载《王国维遗书》,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可见,从沙井北出边墙是一派大漠风光。成吉思灵车行走的这条路线,古称“白道”。
从沙井到边墙可乘牛车,出关后赶上大营必须跨驼。大汗家族不愿让耶律楚材知道安葬之地,以“搜索经籍”名义,将其打发回燕京。湛然原本有参加大汗葬礼的意愿,遭婉拒而误解为辞退。他返燕途中访友,作诗流露不满,准备隐退归田。“自古山河归圣主,从今廊庙弃愚臣。常思卧隐云乡外,肯效行吟泽国滨。”e盖山林《元“耶律公神道之碑”考》,载《内蒙古社会科学》1981年第1期。又载《盖山林文集》,第802—807页。 李逸友《内蒙古元代城址概说》,载《元上都研究文集》,第143页。 耶律楚材《再用韵自叹行藏》,载《文集》卷三,第512页。“挂冠神武当归去,自有夔龙辅可汗。”f耶律楚材《过云中和张仲先韵》,载《文集》卷三,第513页。“间眠白昼三杯醉,静对青松一曲琴。更看他年棲隐处,蓬山楼阁五云深”。g耶律楚材《过武川赠仆散令人》,载《文集》卷三,第513页。

综观灭夏战争,成吉思汗除在阿拉筛地区与夏将阿沙敢不厮杀之外,只是沿着夏国边境行军,目的在于吸引夏军主力布防易守难攻的贺兰山一线,取得声东击西的效应,以减轻蒙古西路军进攻的阻力。到九月,成吉思汗率军突然返回蒙古统治区,再迂回到黄河北岸南渡,形成包抄夏都态势。无援的孤城,经长达半年抵抗,夏主亲到灵州蒙古军大营只准帐外“晋见”,请求宽限一个月举国投降。其实,成吉思汗当时并不在灵州,只是演了一场假戏,答应请求。西夏降期将至的时刻,已经病入膏肓的大汗返回灵州大营,死前却下令屠城,以夏都百姓作殉葬,结局十分悲惨。
(本文作者为原珠海市计划委员会退休干部,青年时曾在内蒙古包头工作)
The Study of the route Činggis Qan destroyed the Kingdom of Tangut (Xi-Xia)
Wen Qihong
Thisarticle tries to clarify some m istakes in the historical studies of Mongol-Yuanand Tangut-Xixia based onacient mapsandarchaeological studies of three ruins of castlesalong the Great Wall of Нan Dynasty. Thearticle discusses thenorthern boundary of Tangut-Xixiaand the three garrison of Hei Shuizhen Yan (Black water; Qara Qota; Išina; Ejin), Bai Ma Qiangzhen (White horse),and Hei Shan Wei Fu (Black Нill; Uraqai). The route of Činggis Qan’s invasion should be from thenorth ot the southacross the Gobi Desert, thenalasha, Uraqai, Shimen Gudao (pass in thevalley of Shimen), crossing the Yellow River, surrounding the Lingzhou (Eriγaya~Iriγai), clearing enem ies in the west,and finally died outat the end of the war. Yelu chucai w rote somePoems when he was together w ith Činggis Qan’s troops. ThosePoems could helPtoProve the route of Činggis Qan’s cof fin from Tangut-Xixia back Mongolia.
Mongol; Genghis Khan; Činggis Qan; Tangut; Xi-xia; rout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