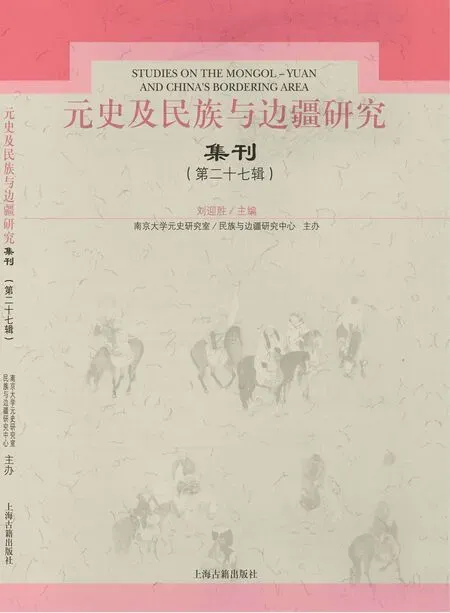南宋佚名《昭忠录》作者考*——兼论《昭忠录》与《昭忠逸咏》的关系
熊燕军
南宋佚名《昭忠录》作者考*
——兼论《昭忠录》与《昭忠逸咏》的关系
熊燕军
《昭忠录》一书,不著撰者名氏,通常认为系南宋遗民所作。笔者发现,元人刘麟瑞所撰《昭忠逸咏》五十首与《昭忠录》在体例编排和内容上高度一致,两书应出自同一人之手。
《昭忠录》 《昭忠逸咏》 刘麟瑞
《昭忠录》一书,不著撰人名氏。是书所记皆南宋末忠节事迹,自理宗绍定四年(1231)元兵克马岭堡,总管田璲等死节,迄于南宋灭亡时殉国之陆秀夫、文天祥、谢枋得等,共一百三十人,作者感情激越,对死难者褒扬备至,应为南宋遗民所作。《昭忠录》一书长期以抄本形式流传于民间,元明时期官私文献均未见著录。清初厉鹗撰《宋诗纪事》,于南宋末遗书搜罗殆遍,不见《昭忠录》之名。万斯同撰《宋季忠义录》,于《宋史》、各省府州县志及野史广为罗辑,亦无《昭忠录》之名。乾隆时修四库全书,以两淮马裕家藏本为底本,将其收入全书,此书才逐渐为人所知。嘉庆十三年(1808),张海鹏校梓《昭忠录》,并将之收入《墨海金壶》丛书,此书始有刻本传世a张海鹏校梓《昭忠录》底本不详。按张海鹏《墨海金壶》取材悉本四库所录,而以文澜阁本居首,从采刻旧钞录出者什之三,凡据永乐大典宋辑之遗编,亦全选入,余则虽有传本而板已久废之罕见书,始加著录。《墨海金壶》本《昭忠录》文字异于《四库全书》本,可能出自旧抄。张海鹏校梓《昭忠录》时间见卷终张氏题记。见上海博古斋据清张氏刊本影印本,民国十年(1921)。 《粤雅堂丛书》本《昭忠录》后有伍崇曜跋语,其中谈及《昭忠录》的刻板情况:“我朝厉鹗等撰南宋杂事诗,于宋末遗书搜罗殆遍,而引用书目(《昭忠录》,笔者注)与《咸淳遗事》均未之见,盖绝鲜流闻矣,亦石溪明经所藏钞本并付梓。”清道光时番禺人黄子高,字叔立,一字石溪,优贡生,生平留意掌故,考证金石,藏书甚富,尤重乡邦文献,多手录之本。明清尊称贡生为明经,故钱仲联称黄子高为“黄明经子高”(钱仲联《清诗纪事》(十五)道光朝卷,第10628页。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年),此处之石溪明经当即黄子高。按伍氏未明言《昭忠录》与《咸淳遗事》二书的初刻者是谁,但指出二书均出自石溪明经所藏抄本。《粤雅堂丛书》虽有《咸淳遗事》之目,实际失载此书,无法参考伍氏跋文。不过据《中国丛书综录》可知,二书的版本情况基本一致,最早的刻本均为《墨海金壶》本,故初刻者当为张海鹏。不过,张海鹏与黄子高生活时代不符,据“石溪明经所藏抄本并付梓”的应是伍氏《粤雅堂丛书》本《昭忠录》,伍氏可能未看到《墨海金壶》本和《守山阁丛书》本《昭忠录》,故行文中未加提及。。《墨海金壶》摹印仅百部,不久,书版烧毁,故流传极少。道光二十四年(1844),钱熙祚得张海鹏《墨海金壶》残版,又从文澜阁《四库全书》中录出流传较少之书,增补删汰校订,辑成《守山阁丛书》刊印b民国年间,商务印书馆印行《丛书集成》,其中《昭忠录》翻刻自《守山阁丛书》本。。《守山阁丛书》本《昭忠录》与《墨海金壶》本完全一致,应翻刻自《墨海金壶》。道光三十年(1850),南海伍崇曜据黄子高所藏抄本《昭忠录》付梓,并收入《粤雅堂丛书》c张海鹏校梓《昭忠录》底本不详。按张海鹏《墨海金壶》取材悉本四库所录,而以文澜阁本居首,从采刻旧钞录出者什之三,凡据永乐大典宋辑之遗编,亦全选入,余则虽有传本而板已久废之罕见书,始加著录。《墨海金壶》本《昭忠录》文字异于《四库全书》本,可能出自旧抄。张海鹏校梓《昭忠录》时间见卷终张氏题记。见上海博古斋据清张氏刊本影印本,民国十年(1921)。 《粤雅堂丛书》本《昭忠录》后有伍崇曜跋语,其中谈及《昭忠录》的刻板情况:“我朝厉鹗等撰南宋杂事诗,于宋末遗书搜罗殆遍,而引用书目(《昭忠录》,笔者注)与《咸淳遗事》均未之见,盖绝鲜流闻矣,亦石溪明经所藏钞本并付梓。”清道光时番禺人黄子高,字叔立,一字石溪,优贡生,生平留意掌故,考证金石,藏书甚富,尤重乡邦文献,多手录之本。明清尊称贡生为明经,故钱仲联称黄子高为“黄明经子高”(钱仲联《清诗纪事》(十五)道光朝卷,第10628页。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年),此处之石溪明经当即黄子高。按伍氏未明言《昭忠录》与《咸淳遗事》二书的初刻者是谁,但指出二书均出自石溪明经所藏抄本。《粤雅堂丛书》虽有《咸淳遗事》之目,实际失载此书,无法参考伍氏跋文。不过据《中国丛书综录》可知,二书的版本情况基本一致,最早的刻本均为《墨海金壶》本,故初刻者当为张海鹏。不过,张海鹏与黄子高生活时代不符,据“石溪明经所藏抄本并付梓”的应是伍氏《粤雅堂丛书》本《昭忠录》,伍氏可能未看到《墨海金壶》本和《守山阁丛书》本《昭忠录》,故行文中未加提及。。《粤雅堂
丛书》本《昭忠录》所据底本与《墨海金壶》本、《守山阁丛书》本不同,但文字及内容均无二致。以上版本与《四库全书》本文字偶有差别,以《四库全书》本为上a《昭忠录》“田璲”条,“绍定辛卯三月十三日,元兵自兴元府边面乘~关入境”,《四库全书》本记为“会”,《墨海金壶》本记为“无”。按:乘会关为关隘名,刘麟瑞《昭忠逸咏》:“忠义总管田公璲凤守李(公)寔”:“天西战士竞衔枚,乘会关夷路始开。”乘会关具体位置不详,大致在大散关与马岭之间。《四库全书》本中“会”字,《墨海金壶》本皆为“无”字。 《昭忠录》卷首所附提要。 彭元瑞《知圣道斋读书跋》,窦水勇校点,辽宁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11页。。下文如无特殊说明,所引《昭忠录》原文均出自《四库全书》本。
《昭忠录》一书的史料来源不详,清人彭元瑞谓“出于闻见”b彭元瑞《知圣道斋读书跋》,窦水勇校点,辽宁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11页。,可惜未能展开详细证明。虽然如此,因传世文献中南宋理宗以后的材料缺失严重,《昭忠录》一书仍以丰富的史料价值为人称许,四库馆臣写道:“其文间有详略,而大都确实可据。以《宋史·忠义传》互相检核,其为史所失载者甚多,即史传所有,亦往往与此书参错不合。” “庶一代忠臣义士未发之幽光复得以彰显于世,且俾读《宋史》者亦可藉以考正其疏略焉。”c《昭忠录》“田璲”条,“绍定辛卯三月十三日,元兵自兴元府边面乘~关入境”,《四库全书》本记为“会”,《墨海金壶》本记为“无”。按:乘会关为关隘名,刘麟瑞《昭忠逸咏》:“忠义总管田公璲凤守李(公)寔”:“天西战士竞衔枚,乘会关夷路始开。”乘会关具体位置不详,大致在大散关与马岭之间。《四库全书》本中“会”字,《墨海金壶》本皆为“无”字。 《昭忠录》卷首所附提要。 彭元瑞《知圣道斋读书跋》,窦水勇校点,辽宁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11页。目录名家周中孚也认为该书“随时叙次,为《宋史》所失载者甚多,此可以补《宋史》之阙,并可以订证《宋史》之参错焉” 。d《郑堂读书记》卷二十三《史部九·昭忠录》,载《国家图书馆藏古籍题跋丛刊》(第十一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2年,第670页。彭元瑞虽指出《昭忠录》所载文天祥脱身京口时从者十二人事有误,但也承认“中有《忠义传》所未载,足补《宋史》之阙”e《昭忠录》“田璲”条,“绍定辛卯三月十三日,元兵自兴元府边面乘~关入境”,《四库全书》本记为“会”,《墨海金壶》本记为“无”。按:乘会关为关隘名,刘麟瑞《昭忠逸咏》:“忠义总管田公璲凤守李(公)寔”:“天西战士竞衔枚,乘会关夷路始开。”乘会关具体位置不详,大致在大散关与马岭之间。《四库全书》本中“会”字,《墨海金壶》本皆为“无”字。 《昭忠录》卷首所附提要。 彭元瑞《知圣道斋读书跋》,窦水勇校点,辽宁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11页。。今人任崇岳也认为此书是研究宋元战争必不可少的参考材料f老铁主编《中华野史辞典》,大象出版社,1998年,第324页。《昭忠录》辞条为宋史专家任崇岳所撰。。然而,在不知道作者及史料来源的情况下,《昭忠录》的史料价值又有多少是真实可信的呢?关于《昭忠录》的作者、取材及史料价值,目前学界尚无专门著述g笔者所见只有一篇涉及,见闫群《〈忠义集〉研究》,华东师范大学2011届硕士论文。,限于篇幅,本文主要讨论《昭忠录》的作者问题,不当之处,还望批评指正。
一
《昭忠录》作者失考,其撰述过程及成书年代亦不详,四库馆臣写道:“详其词义,盖宋遗民之所作也。” “考袁桷《清容居士集》、苏天爵《滋溪文集》均有修元(辽金宋)史时采访遗书之目,不载此名,孔齐(孔克齐,笔者注)《至正直记》所列修史应采诸书亦无此名,知元时但民间传录,未尝上送史馆,故至正间纂修诸臣无由见也。”认为此书作者为南宋遗民,其成书在《宋史》之前,但仅限于民间传录,未尝上送史馆,故元人纂修《宋史》时未能参考《昭忠录》。周宝珠先生在《宋代忠义思想在反民族压迫斗争中的作用》一文中提到:“关于抗蒙的忠义人物,除《宋史·忠义传》包括部分人物外,专书则有元人赵景良的《忠义集》,明程敏政的《昭忠录》、清万斯同的《宋季忠义录》等。”h周宝珠《宋代忠义思想在反民族压迫斗争中的作用》,《河南大学学报》1990年第4期。诸葛忆兵持相同观点,亦未见说明。见氏著《宋词说宋史》,中华书局,2008年,第118页。认为《昭忠录》作者为明人程敏政,不知何据。事实上,程敏政为《宋遗民录》作者。
《昭忠录》的版本及流传情况不详,四库馆臣所谓“宋遗民之所作”缺乏直接证据,实
为猜测之词。纵然猜测为实,界定亦太过宽泛,对于我们深入揭示《昭忠录》的史料价值,意义不大。《昭忠录》的作者到底是谁?笔者发现《忠义集》所收元人刘麟瑞所撰《昭忠逸咏》五十首与《昭忠录》在体例编排和内容上高度一致,两书可能出自同一人之手。
先看体例编排。《昭忠录》记宋末忠节事迹,凡一百三十人,分为四十八条,“每条先列姓名官爵于前,而记其死难事迹于后”a《昭忠录》卷首所附提要。,而《昭忠逸咏》五十首也是记宋末忠节事迹,同样以姓名官爵作为诗歌标题,以忠义死难事迹作为诗歌内容,二书体例编排完全一致。
再看内容。《昭忠逸咏》为诗歌,体裁上异于《昭忠录》,难于直接就正文内容进行直观的比对,不过,因其编排体例相同,我们仍然能够通过对二书条目的对比分析,揭示两书内容上的密切关系。

《昭忠录》与《昭忠逸咏》条目对比情况表:

(续表)
《昭忠逸咏》旧题五十首,从上表可知,实际应为五十三首,个中原因,史无明载,不得而详。笔者注意到,《昭忠逸咏》每诗皆为七字八句,唯独《都统曹友闻及大安夜战死节诸将》一诗是七字十六句,而《昭忠逸咏》中与此诗情况类似者尚有四题,然皆分为二诗,即《丞相信国公文天祥》与《从文丞相诸公》、《淮东制置使李庭芝》与《都统姜才》、《丞相陆秀夫》与《枢密张世杰》、《处士林同》与《孺人林氏》b林氏为刘同子之妻、林同之妹。德祐二年,林同、刘同子起兵反元,兵败三人遂见害。事见《宋史·林空斋(同)传》,《昭忠录》“刘同子、林同、林孺人”条。。按《昭忠逸咏》与《昭忠录》一
样,虽然都是以人为标题,实际皆以事为中心,每诗一事,不应出现二诗一事的情况,上述八诗,所述实为四事,当为四诗,八诗应是后人整理时拆分所致,若将上述八诗还原为四首,则为四十九首,与旧题五十首不合。不过,林同与林氏两诗在编排次序上与其他诸诗不同,并非前后相续的关系,也可能一直以来就是两首,这样就刚好五十首。
从《昭忠逸咏》和《昭忠录》条目的对比情况看,我们不难发现:(1)两书条目数量极为接近。《昭忠逸咏》旧题五十首,五十首诗中,《少主纳款》所述为恭帝降元事,与忠节无关;另一诗《死节诸公》虽与忠节有关,但此诗乃是作者自述创作动机,并没有涉及具体的忠节事迹。林同与林孺人二诗所述为一事,当合并为一,《昭忠逸咏》所咏忠节事迹实为四十七条。《昭忠录》所记忠节事迹,通常认为是四十八条,但其中“赵崇源、汪立信”条中,赵崇源事有目无文,估计有缺页a《粤雅堂丛书》本《昭忠录》后附伍崇曜跋语。 邵懿辰、邵章《增订四库简明目录标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59年,第905页。,实际应有四十九条,与《昭忠逸咏》条目数量十分接近。(2)两书条目内容基本一致。《昭忠逸咏》四十七条忠节事迹,除“太学生徐应镳”、“潮州知州马发”二条外,其余均与《昭忠录》存在一一对应的关系。那些一一对应的条目,虽然有些在文字上存在一些差别,主要是人名的多与少、简与详b《昭忠录》条目中的忠义人姓名、官爵往往比《昭忠逸咏》全面、具体。比如《昭忠录》“湖南安抚知潭州李芾、刽级沈安”,《昭忠逸咏》为“湖南安抚知潭州李芾”;再如《昭忠录》“绵州知州范吉辰、怀安知军史显孙、汉州权州通判刘当可、宗室赵太保、汉州节制邵复、汉州知录罗由、教授袁拱辰、知县罗君文”条,《昭忠逸咏》简写为“绵汉简州诸公”。,这应该是体裁的不同所导致的,两书皆以事为中心,内容上并无不同。(3)两书条目的编排次序也比较一致。《昭忠逸咏》和《昭忠录》记宋末忠节事迹,大致都是依时间先后编排条目。自林同以上,两书条目的编排次序完全一致。林同以下材料,《昭忠逸咏》较为杂乱,其编排明显有违时间先后原则,很可能是后人整理所致。
二
要注意的是,《忠义集》虽有明弘治本、汲古阁本、四库全书本等不同版本c《粤雅堂丛书》本《昭忠录》后附伍崇曜跋语。 邵懿辰、邵章《增订四库简明目录标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59年,第905页。,内容却并无二致。所引《昭忠逸咏》除正文外,尚有大量小注,主要有两类,一类在诗前,主要是解释地名,一类在诗后,主要是详细解释其人事迹。要说明的是,《昭忠逸咏》中凡两诗共述一事的地方,其诗后小注也是两诗共之,这表明我们前面对《昭忠逸咏》条目数量的分析是正确的。
笔者注意到,《昭忠逸咏》诗后的小注,文字上与《昭忠录》高度一致。比如田燧(璲)死节诗后,其小注云:“辛卯三月十三日,大兵自兴元府边面乘会关入宋界,十八日闯凤州,至马岭堡,忠义总管田燧以兵三千驻堡,鏖战数日,援绝死之。四月二十七日,陷凤州,知州李寔、通判张度、教授张叔寅死之。”而《昭忠录》“田璲”条为:“绍定辛卯三月十三日,元兵自兴元府边面乘会关入境,十八日闯凤州,至马岭堡,忠义总管田璲以兵二千驻堡,鏖战数日,援绝死之。四月二十七日,城陷,知州李寔、通判张度、教授张叔寅死之。”除极个别文字有异外,二段材料完全一致。《昭忠逸咏》其余诸诗情况大体类似。
要说明的是,《昭忠逸咏》诗后小注与《昭忠录》虽然只是个别文字存在差别,但我们
仍然能够在这些细微差别背后发现一些规律,主要有以下几种情况:(1)《昭忠逸咏》诗后小注介绍人物生平时往往只书名而不著姓,如《都统曹公友闻及大安夜战死节诸将》诗后小注只云:“友闻,同庆栗里人。”而《昭忠录》通常姓名全著。(2)《昭忠逸咏》1271年(宋度宗咸淳七年,元世祖忽必烈至元八年。是年,蒙古改国号为元)前用干支纪年,1271年后用元朝年号纪年。而《昭忠录》只在南宋灭亡后(1279)用元朝年号纪年,其余时间统一采用南宋年号加干支的纪年法a《昭忠录》采用元朝纪年只有一例,出自“谢枋得”条:“至元二十五年九月,福建省参政魏天祐赍特旨宣唤(谢枋得)。”至元二十五年为1288年,是时南宋已亡,故以元朝年号纪之。要说明的是,《昭忠逸咏》注文中仍有一例采用宋朝年号纪年,《天水知军时当可》诗注:“丙申端平,制司檄时当可知天水军。”下文笔者将指出,《昭忠逸咏》小注曾经刘麟瑞系统改动过,此处应是刘麟瑞疏漏所致。 《昭忠逸咏》“田璲”条:“辛卯三月十三日,大兵自兴元府边面乘会关入宋界,十八日闯凤州。” 何乔新《忠义集序》,载赵景良《忠义集》卷二。。(3)《昭忠逸咏》小注中凡是“大兵”处,《昭忠录》皆为“元兵”。(4)《昭忠逸咏》诗后小注涉及南宋国境和君主时,往往有“宋境”b《昭忠逸咏》“李庭芝”条:“襄帅吕文焕降时,庭芝罢居镇江,宋朝俾再镇扬州。”、“宋朝”c《昭忠录》采用元朝纪年只有一例,出自“谢枋得”条:“至元二十五年九月,福建省参政魏天祐赍特旨宣唤(谢枋得)。”至元二十五年为1288年,是时南宋已亡,故以元朝年号纪之。要说明的是,《昭忠逸咏》注文中仍有一例采用宋朝年号纪年,《天水知军时当可》诗注:“丙申端平,制司檄时当可知天水军。”下文笔者将指出,《昭忠逸咏》小注曾经刘麟瑞系统改动过,此处应是刘麟瑞疏漏所致。 《昭忠逸咏》“田璲”条:“辛卯三月十三日,大兵自兴元府边面乘会关入宋界,十八日闯凤州。” 何乔新《忠义集序》,载赵景良《忠义集》卷二。、“宋主”d《昭忠逸咏》“林同”条:“至元十二年,泉福既归附,明年春,宋主在海上命将收复。”的称呼,《昭忠录》则无。
该如何看待《昭忠逸咏》诗后小注与《昭忠录》文字上的雷同与差异?笔者认为,两者文字上的雷同,表明它们或者出自同一史源,或者为直接抄录的关系,其中一方为另一方的底本;有规律的差异则表明,在抄录的过程中,有一方出于某种原因,对底本作了系统的改动。那么,谁是底本呢?因传世文献中关于《昭忠录》的记载几乎阙如,要弄清这个问题,我们只能从《昭忠逸咏》小注作者及添加时间说起。
《昭忠逸咏》小注不知是否为作者原注。元人讳言宋事e《昭忠录》采用元朝纪年只有一例,出自“谢枋得”条:“至元二十五年九月,福建省参政魏天祐赍特旨宣唤(谢枋得)。”至元二十五年为1288年,是时南宋已亡,故以元朝年号纪之。要说明的是,《昭忠逸咏》注文中仍有一例采用宋朝年号纪年,《天水知军时当可》诗注:“丙申端平,制司檄时当可知天水军。”下文笔者将指出,《昭忠逸咏》小注曾经刘麟瑞系统改动过,此处应是刘麟瑞疏漏所致。 《昭忠逸咏》“田璲”条:“辛卯三月十三日,大兵自兴元府边面乘会关入宋界,十八日闯凤州。” 何乔新《忠义集序》,载赵景良《忠义集》卷二。,刘埙和刘麟瑞父子不忍心宋季忠义事迹堙没无闻,故先后作《补史十忠诗》十首和《昭忠逸咏》五十首,希望“藉诗以存史也”f《忠义集》卷首附提要。。刘埙,字起潜,号水云村(或作水村),南丰(今属江西)人,宋末元初著名学者、诗人、文学评论家。至元二十年(1283),刘埙作《补史十忠诗》十首g[清]龚望曾《水村先生年谱》,载北京图书馆编《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第36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9年,第281页。,自序称:“采清议,得忠义臣十人,史不书,各赋十韵,纂其实,曰《补史诗》。”其在《补史十忠诗》末跋云:“右襄围以来死忠者,不止此,然多所不知,知其详且显者,莫如此十公。故先赋此十诗,尚俟续书,以著大节。噫,十诗存即十忠不亡,十忠不亡,吾十诗亦永存矣。是未易与俗子言之,儿辈深藏之,非深于诗、精于理者,勿轻示之云。”刘麟瑞继承其父遗志,续作《昭忠逸咏》五十首,“追维仗节死义之士,事日益远,岁日益深,遗老日益凋谢,旧闻日益销泯,其不与草木同腐者几希。暇日搜讨遗事,赋五十律,题曰《昭忠逸咏》”。要说明的是,《补史十忠诗》中存在小注,但主要是解释人名、地名,并未解释忠节事迹,刘氏父子面临的社会背景并无根本变化h《宋史》卷四四六《忠义传序》:“奉诏修三史,集儒臣议凡例,前代忠义之士咸得直书而无讳焉。”可见一直到元顺帝至正三年(1343),元政府才真正放松了对宋季忠节事迹传布的控制。而据刘麟瑞自述,《昭忠逸咏》成书于元英宗至治元年(1321)。,若《补史十忠诗》小注为刘埙所作,则刘麟瑞注解风格应当同其父一样,不应解释忠节事迹。当然,这看起来也符合刘氏父子“以诗存史”的初衷。
元至顺壬申(1332)年,刘麟瑞将《昭忠逸咏》送文学椽岳天祐阅览,岳天祐读后,作序一篇,“以识所曾观”。其中有云:“观其事迹具备,赞咏警策,诚有益于风教者焉。尝闻刘后村有《咏史》三百首,游清献公爱之,携入都堂。今如村之《逸咏》,实可备太史氏之采择,非特游公之赏识而已。”a岳天祐《昭忠逸咏序》,载赵景良《忠义集》卷二。 《昭忠逸咏》小注谓谢枋得出身“文天祥榜下第二甲第二人”,而《文节先生谢公神道碑》则记为“二甲第一人”,据《宝祐四年登科录》可知,谢枋得应为第二甲第一人;又两文关于谢枋得“叠山”称号由来的解释亦不同,《昭忠逸咏》谓“取重艮止止之义”,《文李先生谢公神道碑》谓“因谪所山门自命叠山”,据崔骥《谢枋得年谱》(《江西教育》1935年第四期、第七期),后说为是,故《昭忠逸咏》小注应未参考《文节先生谢公神道碑》。从“事迹具备”“可备太史氏之采择”看,诗后似有解释事件经过的注文。
二刘之后,乡人赵景良将《补史十忠诗》和《昭忠逸咏》合为一编,并附遗民诗,题曰《忠义集》。但仅“私相传录”,流传不广。明弘治年间,乡人赵玺在一老农家发现《忠义集》,遂“校补其讹缺”,赵玺整理好后,将手稿送何乔新阅览,何氏“因厘为七卷,录而藏之”。此本后由浙江佥宪王廷光刻版付梓。明弘治本卷首附何乔新《忠义集序》,其中云:“观文履善(文天祥,笔者注)对博啰之语,谢君直(谢枋得,笔者注)复留梦炎之书,为之慨然;观吴楚材答录事之诘,朱浚语兵士之词,毛发泪然,而不能自己也。”何乔新既然能看到“语”“书”“诘”“词”,此时小注应已存在。
三
虽然仍不能确定小注是否作者原注,但不论是谁,其身份都应是元人而非明人。前文述及,《昭忠逸咏》诗后小注行文中拒绝使用南宋年号,称南宋为宋朝,称元兵为大兵,明人以继宋正统自居,断不会在南宋尚未灭亡的时候就采用元朝年号,故小注必产生于元朝。又,《昭忠逸咏》所咏南宋忠节事迹止于谢枋得,谢卒于元世祖至元二十六年(1289)。仁宗延祐五年(1318),也即谢枋得卒后19年,周应极撰《叠山行实》,李源道撰《文节先生谢公神道碑》b俞兆鹏《谢叠山先生系年要录》,《江西大学学报》1987年第1期。,两文中,《文节先生谢公神道碑》极为翔实,然所载与《昭忠逸咏》谢枋得死节诗后小注多有不同,《昭忠逸咏》小注应未参考《文节先生谢公神道碑》c岳天祐《昭忠逸咏序》,载赵景良《忠义集》卷二。 《昭忠逸咏》小注谓谢枋得出身“文天祥榜下第二甲第二人”,而《文节先生谢公神道碑》则记为“二甲第一人”,据《宝祐四年登科录》可知,谢枋得应为第二甲第一人;又两文关于谢枋得“叠山”称号由来的解释亦不同,《昭忠逸咏》谓“取重艮止止之义”,《文李先生谢公神道碑》谓“因谪所山门自命叠山”,据崔骥《谢枋得年谱》(《江西教育》1935年第四期、第七期),后说为是,故《昭忠逸咏》小注应未参考《文节先生谢公神道碑》。,故小注的产生时间应在1289年至1318年之间,或者稍稍迟于1318年。
其实,《昭忠逸咏》诗前小注亦可证小注产生于元朝。笔者发现,《昭忠逸咏》诗前小注在解释地名沿革时,下限往往止于宋朝,如《处士林同》注云:“福州在福建路。扬州域。周七闽地,闽子孙分七种。楚秦为闽中郡,闽君摇为越王,都冶。汉分冶地为会稽、东南二郡,故曰东冶。陈置闽州,隋改泉州,唐更福州,闽王王审知升武威军。宋朝升福安府,领县十,福清是其一县也。”有些注文也提到了“今”的情况,然皆在宋朝之后,如《援襄都统张顺》诗前小注云:襄阳,“隋唐皆为襄州。唐升为山南东道节度,以襄州为襄阳府。宋朝因之。真宗潜藩升襄阳府。宝庆间以京湖制置安抚兼领。今统郡七,领县四,治襄阳”。《昭忠逸咏》其他诗前小注类此。注文既以宋朝为古今断限,则小注必产生于元朝。
能不能就此推测出小注产生的详细年代?前引襄阳府注文时提到:“今统郡七,领县四,治襄阳。”“统郡七”含义不明,宋元地方行政制度中并无“郡”的设置,只在封爵及文
人行文时以“郡”代指“州”a李昌宪《中国行政区划通史》(宋西夏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98页。 《宋史》卷八五《地理一·襄阳府》,中华书局,1977年,第2113页;徐松《宋会要辑稿》方域五之一八,中华书局,第7392页。 比如《大元混一方舆胜览》记录地方行政体系时就只载县不载司。刘应李《大元混一方舆胜览》,郭声波整理,四川大学出版社,2003年。。南宋时,京西南路下辖襄阳府、随州、均州、房州、郢州、枣阳军、光化军七州军,以襄阳为首府b祝穆著、祝洙增订《方舆胜览》卷三二《京西路》,施和金点校,中华书局,2003年,第573页。其实,南宋京西南路辖区并不固定。建炎初,京东西、淮南、湖北等地,多沦入土豪、群盗之手,宋仿藩镇法,设襄阳府、邓、随、郢州镇抚使;绍兴四年,以襄阳府、随、郢、唐、邓州、信阳军为襄阳府路;六年以襄阳府路为京西南路;绍兴十一年,领襄阳府、随州、均州、房州、郢州、信阳军、光化军七州军;绍兴十九年,信阳军拨隶淮西;嘉定十二年,升随州枣阳县为枣阳军,端平元年,增唐、邓、息三州。见王象之《舆地纪胜》卷八二《京西南路》,江苏广陵刻印社,1991年,第697页。。襄阳府下辖襄阳、谷城、宜城、南漳四县c李昌宪《中国行政区划通史》(宋西夏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98页。 《宋史》卷八五《地理一·襄阳府》,中华书局,1977年,第2113页;徐松《宋会要辑稿》方域五之一八,中华书局,第7392页。 比如《大元混一方舆胜览》记录地方行政体系时就只载县不载司。刘应李《大元混一方舆胜览》,郭声波整理,四川大学出版社,2003年。。元置河南江北等处行中书省,辖襄阳府路等十三路。元初襄阳路辖四县一司(录事司),至元十九年(1282),割光化、枣阳二县和均、房二州来属,辖六县一司二州,州辖四县d《元史》卷五九《地理二·襄阳路》,中华书局,1976年,第1409页。。元制,路治所设录事司。录事司与县大抵平级,合称司县。前引注文“领县四”中,襄阳路所辖有县无司,与元朝地方行政体系不合,虽然元朝文献中也有只记载县的情况e李昌宪《中国行政区划通史》(宋西夏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98页。 《宋史》卷八五《地理一·襄阳府》,中华书局,1977年,第2113页;徐松《宋会要辑稿》方域五之一八,中华书局,第7392页。 比如《大元混一方舆胜览》记录地方行政体系时就只载县不载司。刘应李《大元混一方舆胜览》,郭声波整理,四川大学出版社,2003年。,但“统郡七”也与元朝史实不符。笔者怀疑,注文中提及的“今”不是指元朝,而是指南宋,所谓“统郡七”指京西南路辖七州军,“统县四”指襄阳府辖四县,而京西南路和襄阳府皆治襄阳。
事实的确如此。笔者发现,这段材料其实就出自南宋文献。《方舆胜览》卷三二《京西路·襄阳府》“建置沿革”条:“《禹贡》荆、豫之域。……秦兼天下,自汉以北为南阳,今邓州是也;自汉以南为南郡,今荆州是也;襄阳乃南阳、南郡二郡之地。东汉刘表为荆州刺史,始理襄阳。魏分南郡置襄阳郡,自赤壁之败,魏失江陵,南守襄阳。西晋为荆州治所,羊祜、杜预皆镇襄阳;东晋于襄阳侨置雍州,遂为雍州刺史治所。梁置南雍州。西魏改曰襄州。隋、唐皆为襄州,唐复升为山南东道节度,以襄州为襄阳府。皇朝因之,真宗潜藩,升襄阳府,宝庆以京湖制置安抚使兼领。今统郡七,领县四,治襄阳。”f祝穆著、祝洙增订《方舆胜览》卷三二《京西路·襄阳府》,施和金点校,中华书局,2003年,第573页。很明显,前引襄阳府注文抄录自南宋志书《方舆胜览》“隋、唐皆为襄州”以下一段,作者除将“皇朝”改为“宋朝”并省略“复”“间”二字外,其余一字未改。笔者注意到,《昭忠逸咏》诗前小注中凡是提到“今”的地方,“今”所指都是南宋,而非元朝g除襄阳外,笔者再举一例。《大社吴楚才》诗前小注:“建昌,……南唐升为建武军,宋朝改建昌军,绍兴八年,析南城县上五乡置新城县,于黎滩镇又析南丰县之半置广昌县于揭坊耆,今领县四。”按南宋建昌军辖南城、南丰、新城、广昌四县,元初置建昌路,辖四县一司,至元十九年,升南丰县为州,直隶行省,建昌路所辖改为三县一司。小注的记载同样与元朝文献不合。《方舆胜览》卷二一《建昌军》“建置沿革”条:“……唐末、五代,伪唐升南城县为建武军。皇朝改建昌军。今领县四,治南城。”前引注文“今领县四”不知是否源于此。。
要说明的是,《昭忠逸咏》诗前小注并非全部出自《方舆胜览》。限于材料,今天我们已不能一一指出注文的原始出处,但小注既产生于元朝,而注文在解释地名沿革时却无一例真正涉及元朝,这表明所有诗前小注的原始出处应该都是南宋文献。小注作者在引用
这些文献时,除将“皇朝”改为“宋朝”以区别时代外,其他内容估计基本未变。
为什么元人在解释地名沿革时,引用南宋文献而不引用本朝文献呢?是出于故国之情吗?从诗后小注行文中拒绝使用南宋年号以及自序中颂扬元朝太祖、世祖功业a刘麟瑞《昭忠逸咏自序》,赵景良《忠义集》卷二。 郭声波《〈大元混一方舆胜览〉研究二题》,《九州》2007年第四辑。 刘麟瑞《昭忠逸咏自序》,载赵景良《忠义集》卷二。看,应该是另有原因。笔者认为,合理的解释应是小注产生较早,未能参考元修地理总志。元朝共有二部地理总志,一为《元一统志》,一为《大元混一方舆胜览》。《大元一统志》始修于元世祖至元二十二年(1285),至三十一年成书。不久增修,成宗大德七年(1303)纂修成书。成书后有节录本传出,但全本直至顺帝至正六年始刻板刊行b《元一统志》整理本“前言”,载孛兰盻等《元一统志》,赵万里校辑,中华书局,1966年。。《大元混一方舆胜览》成书时间不详,大德十一年(1307),《大元混一方舆胜览》作为《翰墨大全》的后甲集卷一一至卷一五、后乙集卷一至卷六刊行c刘麟瑞《昭忠逸咏自序》,赵景良《忠义集》卷二。 郭声波《〈大元混一方舆胜览〉研究二题》,《九州》2007年第四辑。 刘麟瑞《昭忠逸咏自序》,载赵景良《忠义集》卷二。。小注的时间似乎应该在成宗大德以前或稍后。
要强调的是,诗前小注的产生时间可能不会早于成宗大德年间。前已述及,大德七年,《大元一统志》成书,并有节录本传出,但刘麟瑞未尝入仕元朝,仅为一“逸士”d岳天祐《昭忠逸咏序》,赵景良《忠义集》卷二。,他应该没有条件接触节录本。《大元混一方舆胜览》虽初刊于大德十一年,但可能印数有数,流传不广,故泰定元年(1324)再次刻印。出于身份原因,刘麟瑞也无法查看元朝中央保存的全国各地建置申报的统计资料。
《昭忠逸咏》成书于元英宗至治元年(1321)e刘麟瑞《昭忠逸咏自序》,赵景良《忠义集》卷二。 郭声波《〈大元混一方舆胜览〉研究二题》,《九州》2007年第四辑。 刘麟瑞《昭忠逸咏自序》,载赵景良《忠义集》卷二。,但从上文可知,不论是诗后小注,还是诗前小注,其产生时间都可能早于至治元年,小注怎么可能早于诗歌正文呢?其实,小注即源自刘麟瑞创作《昭忠逸咏》搜集的材料。刘埙《补史十忠诗序》:“采清议,得忠义臣十人,史不书,各赋十韵,纂其实曰《补史诗》。”刘麟瑞《昭忠逸咏自序》:“追维仗节死义之士,事日益远,岁日益深,遗老日益凋谢,旧闻日益销泯,其不与草木同腐者几希。暇日搜讨遗事,赋五十律,题曰《昭忠逸咏》。”可见刘氏父子在创作《补史十忠诗》和《昭忠逸咏》时都搜集有一定材料,这些材料应该就是小注的底本。刘麟瑞极有可能在创作完《昭忠逸咏》后,顺便将这些材料以小注的形式附于诗中。
四
小注会不会是后人整理的结果呢?即刘麟瑞创作完《昭忠逸咏》后,并没有把这些材料附于诗中,但这些材料并未被毁掉,而是被保留了下来,后人在整理传抄的过程中,发现了这些材料,于是将材料以小注的形式附于诗中。
就已知情况看,元朝《昭忠逸咏》的整理者,似乎只有赵景良一人f赵景良生平事迹不详,大致与刘麟瑞同时或稍后。见祝尚书《宋代总集叙录》卷一○《忠义集》,中华书局,2004年,第505页。。笔者发现,《忠义集》卷六、卷七所附汪元量、方回诸人所撰诗中,往往有小注解释人名或事件。比如“自修程先生忘吾”条下,小注云:“洛阳人,孝友,好读书,翰林元裕之上其言行,除礼部郎中,自修闻而遁。”程忘吾《痛哭》诗标题后注云:“此咏洛陵也。公洛人,必尝亲履陵阙,故感伤如此。宋以腐儒误国,犹西晋以清谈误国,伟哉雄论,可为宋戒。”曾子良《挽知临安府兼浙西
制置使曾公(渊子)》诗后注云:“公字广微,自号留达,亦南丰派也,析居金溪。淳祐庚戌,黄甲及第,徳祐乙亥同知枢密院事、知临安府兼浙西制置使,国事急,贾似道得罪,陈丞相宜中当国,公遁归里,被劾,窜雷州。临安失守,景炎祥兴,建朝于南中,起公参知政事,已而北兵逼行朝,公走安南而卒。族侄平山公作诗四章遥挽之,岁久始有负其遗骸归者,哀哉!”
这些小注到底为何人所作?笔者注意到,《忠义集》“附录诸公诗”有七首与元人杜本《谷音》所辑相同。陈冠梅《杜本及〈谷音〉研究》:“元人赵景良又采录其中丁开《可惜》、鲍輗《重到钱塘》、柯茂谦《鲁港》、程自修《痛哭》、安如山《曹将军》、师严《出襄阳渡江》《咸淳庚午朱尚书席上醉歌》七诗入《忠义集》,与其他述赞宋末文末祥、陆秀夫、江万里、李庭芝等忠义之臣的诗相与为伍”a陈冠梅《杜本及〈谷音〉研究》,东方出版社,2007年,第8页。,指出《忠义集》“附录诸公诗”中丁开《可惜》等七诗选录自《谷音》。
要说明的是,上述七诗虽选录自《谷音》,小注的文字却略有不同。如《忠义集》丁开的注文是:“湖南长沙人,负气敢言,安抚向士壁被罗织,开诣阙陈士壁功大,军府小费不宜推究。似道怒,羁管扬州,岁余卒。”而《谷音》原文为:“开负气敢言,安抚向士壁被问,开独诣阙上疏,具陈士壁功大,军府小费不宜推究。书奏,羁管扬州,岁余卒。”有时也会有内容上的差异,如前述程自修《痛哭》诗后小注,《谷音》则无。总体而言,两集的记载文字上虽有出入,所指却大同小异,《谷音》中的小传文意更为顺畅,而《忠义集》中的小传则多补充了贾似道当国的背景,有些诗篇还补充了对事件的解释,这表明赵景良在选录的时候对原注文进行过加工。
“附录诸公诗”中其余诸诗的选录情况不明,前引曾子良诗小注云“族侄平山公作诗四章遥挽之”,按平山公即曾子良b《忠义集》卷六“曾子良”条下小注:“故家南丰,徙居抚之金溪。咸淳进士,仕至淳安令,国事变,隐居陶塘,号平山。”,其所作挽诗即《挽知临安府兼浙西制置使曾公(渊子)》,故诗后小注当非曾子良所作,估计亦应为赵景良所作。赵景良所作注解,格式与《昭忠逸咏》类似,《昭忠逸咏》小注是否亦是赵景良所作?笔者注意到,前引曾子良诗注文中,多次出现南宋年号,毫不避讳,与《昭忠逸咏》小注的行文风格完全不同,《昭忠逸咏》的小注尤其是诗后小注应该不是出自赵景良之手。此外,《昭忠逸咏》每诗皆有注解,这也与《忠义集》所附南宋遗民诗部分注解的形式不符。
笔者以为,刘麟瑞所搜为南宋末年忠节事迹,其叙事详细明瞻,应该主要是出自南宋方面的文献,在南宋尚未灭亡的时候,行文中不当出现元朝纪年,也不当有“宋主”“宋朝”“宋境”等称呼,小注的行文应该是经过了人为的改动。倘若《昭忠逸咏》小注非刘麟瑞原注,而是由赵景良根据刘麟瑞搜集的材料整理而成,那么赵景良应该对材料作了系统改动。但前引曾子良诗注文中,多次出现南宋年号,故改动者当非赵景良。如此一来,改动者只能是刘麟瑞。
如果仅仅是为诗歌创作提供素材,则刘麟瑞是绝对不会改动材料的,那样做除徒费精力外,没有任何意义。刘麟瑞一定是要将这批材料作为注文附于诗中,因为事涉禁忌,故必须对行文作些改动,以避免招致元朝统治者的不满,从而实现保存南宋忠节事迹的目的。
刘麟瑞对材料的改动,实际上是为了凸显元朝的正统地位。元初因纂修辽金宋三史的原因,在谁为正统的问题上陷入争论。有的主张以《宋史》为正史,以辽、金入载记,如杨维桢认为:“中华之统,正而大者,不在辽、金,而在于天付生灵之主也昭昭矣,然则论我元之大一统者,当在平宋,而不在平辽与金之日,又可推矣!”a杨维桢《正统辨》,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三,中华书局,1959年,第36页。 危素《上贺相公论史书》,《危太朴文续集》卷八。 《危太朴文续集》卷九《书张少师传后》。有的主张辽、金为北史,宋太祖至靖康为宋史,建炎以后为南史。如修端认为:“宋太祖未生,辽祖比宋前兴五十余年,已即帝位,固难降就五十之后,包于宋史为载记,其世数相悬,名分颠倒,断无此法。既辽之世际,宋不可兼。……辽自唐末,保有北方,又非纂夺,复承晋位,加之世数名位,远兼五季,与前宋相次而终,当为北史;宋太祖受周禅,平江南,收西蜀,白沟迤南,悉臣于宋,传至靖康,当为宋史;自建炎以后,中国非宋所有,宜为南宋史。”b修端《辨辽金宋正统》,载《元文类》卷四十五。更有人认为宋、金都不是“正统”,如危素说:“本朝立国于宋、金未亡之先,非承宋、金而有国也。”c杨维桢《正统辨》,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三,中华书局,1959年,第36页。 危素《上贺相公论史书》,《危太朴文续集》卷八。 《危太朴文续集》卷九《书张少师传后》。危素为了突出元朝的地位,认为元朝与宋朝、金朝之间没有传承的关系。刘麟瑞观点应与危素类似,故《昭忠逸咏》诗后小注自1271年忽必烈改国号“元”后即采用元朝年号纪年。也许正因为此,虽然事涉禁忌,《昭忠逸咏》在元朝仍有人提及d元人多次提及《昭忠逸咏》,除岳天佑、赵景良外,《忠义集》卷六还收录王介夫《题刘如村昭忠逸咏》一首。,相比之下,赵景良所作南宋遗民诗注因无禁忌,结果《忠义集》在元朝无人提及。
小注整理者会不会就是危素呢?危素,字太朴,生于元成宗大德七年(1303),卒于明洪武六年(1372),抚州金溪人,著名的史学家。危素出身官宦世家,早年师从名儒祝蕃、吴澄、范梈、虞集等,至正二年(1342),危素受张起岩、揭傒斯、苏天爵等大臣举荐,入经筵为检讨。至正三年,元顺帝下诏置局修史,危素厕身其中,负责订补南宋高、孝、光、宁四朝史料e杨维桢《正统辨》,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三,中华书局,1959年,第36页。 危素《上贺相公论史书》,《危太朴文续集》卷八。 《危太朴文续集》卷九《书张少师传后》。。四年,受中书省委派前往河南、江浙、江西诸地,访摭遗阙。危素访书成效卓著,仅在宁波就得书七千余卷f宋禧《庸庵集》卷十二《代刘同知送危检讨还京师序》。,其中有些书籍极其珍贵,比如故宋礼部侍郎邓剡家藏陆秀夫及邓剡所著南宋末年二王事迹g《宋史》卷四五一《陆秀夫传》:“方秀夫海上时,记二王事为一书甚悉,以授礼部侍郎邓光荐(邓剡)曰:‘君后死,幸传之。’其后厓山平,光荐以其书还庐陵。大德初,光荐卒,其书存亡无从知,故海上之事,世莫得其详云。”危素《西台恸哭记注跋》(见《宋遗民录》卷三)记邓光荐著有《续宋书》。又刘诜《桂隐文集》卷四《题危太朴与邓子明书后》:邓剡回庐陵后,“以所闻见集录为野史若干卷,藏不示人”,在危素感召下,其后人邓晋终于“抱其先祖所著上进史馆”。。危素回到史馆后,又进行材料整理工作h《危太朴文集》卷八《史馆购书目录序》。,并在此基础上分修宋史《忠义传》i《危太朴文集》卷七《昭先小录序》:“仰惟今皇帝示天下以至公,明诏史臣毋讳死节。素待罪史官,分修《忠义传》,网罗放失,夙夜兢兢。”要说明的是,宋史《忠义传》的内容并非全部出自危素之手。可参孔繁敏《危素与〈宋史〉和纂修》,《燕京学报》1996年第二期。。按刘麟瑞为南丰人,南丰紧邻抚州,又《昭忠逸咏》在元朝虽是诸儒“私相传录”j何乔新《忠义集序》,载赵景良《忠义集》卷二。,流传不广,但并非堙没无闻,危素有可能收集并整理《昭忠逸咏》及相关材料。但是,一方面危素搜求遗书及分修《忠义传》皆在至正三年后,此时脱脱已确定“三
史各与正统”,危素似不必大费周章改动材料;另一方面,前已述及,小注的产生时间应在元朝前期,而危素的生活时代在元朝后期。此外,危素传世文字中有许多与访摭遗书、整理史料、撰修宋史相关的记载,其中无一条涉及《昭忠逸咏》;又危素既为史官,而小注的一些明显史实错误都未与更正a比如前述谢枋得科举出身的记载。 张金吾《爱日精庐藏书志》卷三五。 闫群《〈忠义集〉研究》,华东师范大学2011届硕士论文。,《昭忠逸咏》小注应是刘麟瑞原注。
要说明的是,《昭忠逸咏》除刻本外,尚有抄本流传的记载b参祝尚书《宋代总集叙录》卷一○《忠义集》,中华书局,2004年,第504-512页。,这些记载也反映出《昭忠逸咏》小注是作者原注。张金吾《爱日精庐藏书志》卷三五:“《昭忠逸咏》六卷,《补史十忠诗》一卷,陆氏敕先(陆贻典,笔者注)校本。陆氏手跋:黼季购得顾修远家藏钞本,校过两次,尚是此书原本。‘忠义集’乃后人所加名也。”c比如前述谢枋得科举出身的记载。 张金吾《爱日精庐藏书志》卷三五。 闫群《〈忠义集〉研究》,华东师范大学2011届硕士论文。此本今未见著录。后瞿镛又得一校本,乃陆贻典、毛扆用同上顾氏本校改毛晋家刻本《忠义集》,《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卷二三:“《昭忠逸咏》六卷,《补史十忠诗》一卷,校本。元刘麟瑞撰并序,又岳天祐、何乔新序。《补史诗》,刘埙撰。赵景良尝合编之,易名为《忠义集》。此毛斧季以旧钞本校改家刻,卷第字句皆与初刻异。”d瞿镛《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卷二三,瞿果行标点,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675页。此本今藏国家图书馆。除将“忠义集”校改为“昭忠逸咏”并改卷第等外,尚有文字校补。如《忠义集》卷二《西和知州陈公(寅)守将杨公(锐)》诗注:“初,杨锐为摧锋统制,领千兵戍守,与陈寅率兵民凭城死战,俘杀甚众。”在“率兵民”后校补“三十七万九千单八口”九字。按此本乃陆氏用顾氏抄本校改毛氏刻本的本子,今刊本基本出自明弘治本,而无此九字,则此九字应出自抄本。又抄本与赵景良合编本体制不符,应是“此书原本”。原本有此九字,则《昭忠逸咏》小注起码是诗后小注为作者原注。
五
回到《昭忠录》的作者上来。前文述及,《昭忠逸咏》小注起码是诗后小注为刘麟瑞原注,由于《昭忠录》与《昭忠逸咏》诗后小注内容高度一致,且《昭忠录》条目内容又较《昭忠逸咏》详细,则《昭忠录》应非抄录自《昭逸咏逸》诗后小注。又,刘麟瑞自述“暇日搜讨遗事”,且刘麟瑞《昭忠逸咏》五十首之前,尚有其父《补史十忠诗》十首,内容大体一致,故刘麟瑞不可能全盘抄录《昭忠录》,《昭忠录》的作者应该就是刘麟瑞。刘麟瑞将收集到的宋季忠义事迹整理为《昭忠录》,并在此基础上创作《昭忠逸咏》,同时将《昭忠录》的行文改动后以注的形式附于诗中。迫于形势,刘麟瑞不敢在《昭忠录》上署上自己的姓名,也不敢将之公诸于众。相反,《昭忠逸咏》因为迎合了元朝统治者对正统的要求,故刘麟瑞不仅署上了自己的姓名,而且在书成11年后,将书送文学掾岳天祐阅览。闫群认为,《昭忠录》系明末清初人辑自《昭忠逸咏》诗后小注e比如前述谢枋得科举出身的记载。 张金吾《爱日精庐藏书志》卷三五。 闫群《〈忠义集〉研究》,华东师范大学2011届硕士论文。,与事实不符。《昭忠录》内容既详于《昭忠逸咏》,如何辑录?既是明清人所辑,自不必有所畏惧,何必隐去其名?既是辑录,为何全部转录自《昭忠逸咏》一书?况且明清时《昭忠逸咏》远较《昭忠录》常见。
最后要说明的是,虽然两书中也有一些文字差别与正统无关,这应该是后人整理所
致。两书长期流传于民间,流传的过程中又皆有讹缺,而后人整理时又未能互相参考a《昭忠录》和《昭忠逸咏》皆收于《四库全书》,但四库馆臣并没有注意到二者之关系。一直到清道光年间时才有人用二书对校。上海图书馆所藏清抄本《昭忠录》所附跋语:“道光戊申秋七月十有九日,先以汲古阁刊本《忠义集》校一过。镜泉识。越一日,又以四库本《昭忠录》《忠义集》对校。”然它本似仍未有注意。,难免出现一些文字上的差别。
(本文作者为韩山师院历史系副教授)
Research on theauthor ofzhaozhong Lu(昭忠录)
Xiong Yanjun, Нistory Department, Нanshannormal college
the book ofzhaozhong Lu(昭忠录) hadno recordabout theauthor. It was speculated that theauthor wasadherent of Southern Song Dynasty. Stylistic rulesand layout ofzhaozhong Yi Yong(昭忠逸咏) which was w ritten by Liu Linrui(刘麟瑞)highly consistented w ithzhaozhong Lu.zhaozhong Yi Yongandzhaozhong Lu were w ritten by Liu Linrui.
zhaozhong Lu;zhaozhong Yi Yong; Liu Linrui
* 本文曾于2011年11月提交“十至十三世纪中国的政治与社会学术研讨会暨岭南宋史研讨会第二届年会”(广州·中山大学)讨论,承李伟国、戴建国二位教授提出宝贵意见,谨致谢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