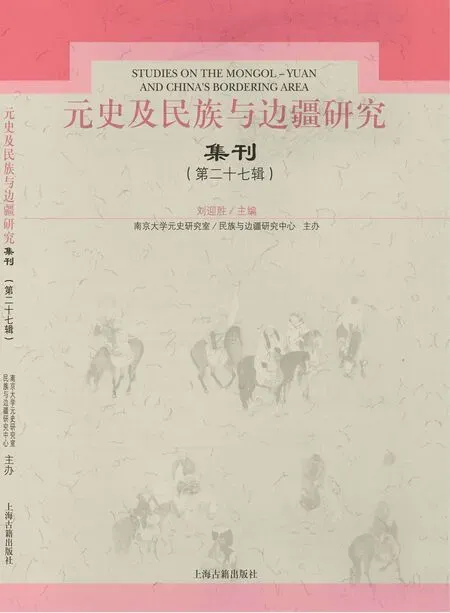元代陕西行台设废原因蠡测
蔡晶晶
元代陕西行台设废原因蠡测
蔡晶晶
陕西诸道行御史台设立于元世祖至元年间,从至元二十七年到延祐二年,历时二十六年,行台三废四设,如此频繁的废设必有其原因。本文第一部分叙述了陕西行台的设废过程;第二部分从地理角度论证了西部地区设立行御史台的必要性;第三部分探讨了江南行台对西台的影响;第四部分则指出了陕西行台设立的必然性。
元代 陕西行台 设废 原因
关于元代的陕西诸道行御史台a元代陕西诸道行御史台,《元史》、《宪台通纪》和元人文集中有陕西诸道行御史台、陕西行御史台、陕西行台、西台等多种称谓。 郝时远《元代监察制度概述》,《元史论丛》(第三辑),中华书局,1986年。 李文以《元代监察机关架阁库述略》,《档案学研究》2002年第1期,第24—26页。的研究成果,目前并不多见。除了丹羽友三郎《元の西台について》一文b[日]丹羽友三郎《元の西台について》,《名古屋商科大学论集》(9卷),1964年。外,大多数与陕西行台相关的研究都出现在对元代监察制度综合性的论述中,如郝时远的《元代监察制度概述》c元代陕西诸道行御史台,《元史》、《宪台通纪》和元人文集中有陕西诸道行御史台、陕西行御史台、陕西行台、西台等多种称谓。 郝时远《元代监察制度概述》,《元史论丛》(第三辑),中华书局,1986年。 李文以《元代监察机关架阁库述略》,《档案学研究》2002年第1期,第24—26页。,李治安的《元代政治制度研究》第二章第六节《元代行御史台述论》d李治安《元代政治制度研究》,人民出版社,2003年。,李文以的《元代监察机关架阁库述略》亦有涉及。e元代陕西诸道行御史台,《元史》、《宪台通纪》和元人文集中有陕西诸道行御史台、陕西行御史台、陕西行台、西台等多种称谓。 郝时远《元代监察制度概述》,《元史论丛》(第三辑),中华书局,1986年。 李文以《元代监察机关架阁库述略》,《档案学研究》2002年第1期,第24—26页。与陕西行台相关的史料较少,主要出现在《元史》和《宪台通纪》中,元人文集中也有相关零星记载。资料不足可能是造成陕西行台研究成果不丰的重要原因。陕西行台主管元代西部地区的监察事务,是元代监察体系中不可缺少的一环,然而在四朝二十六年间,陕西行台历经四设三废才最终成为固定机构。陕西行台屡兴设废,必有原因。故本文拟对此加以探讨。
一、 陕西行台的设与废
元代在陕西、四川、甘肃、云南一带设立行御史台的历史,可以追溯到至元十九年初设立的河西行御史台。河西行御史台的建立时间,《元史》没有记载。郝时远《元代监察制度概述》指出,河西行御史台设立于至元十九年初,是一个主管畏兀儿人口的监察机构,其设立与畏兀儿地区的形势变化直接相关f郝时远《元代监察制度概述》,第84页。。《元史》至元二十年三月条下有“丁巳……罢河西行御史台”g《元史》卷一二《世祖纪九》,中华书局校点本,1976年,第251页。,照此推测,河西行御史台存在的时间大约为一年左右。
河西行御史台既罢,直到至元二十七年,五月己巳,朝廷又设立了云南行御史台
(治所在云南中庆路)a《元史》卷一六《世祖十三》,第337页。云南行台的设立年代,《元史·世祖本纪》记为至元二十七年五月己巳。《元史·程思廉传》(“至元二十六年,立云南行御史台,起复思廉为御史中丞。”)及《程思廉传》所本《河东廉访使程公神道碑》记载设台时间为至元二十六年。(王思廉《河东廉访使程公神道碑》,《国朝文类》卷六七:“至元二十六年立云南行御史台,擢拜中丞。”)《元史·程思廉传》校勘记指出“二十六年立云南行御史台 本书卷一六《世祖纪》至元二十七年五月己巳条、卷八六《百官志》皆系二十七年。《新元史》改‘六’为‘七’,是。”云南行台正式设立的年代应该是至元二十七年,程思廉于元贞二年正月去世,《神道碑》作于大德元年冬,去至元二十六年不过七八年。排除笔误的可能性,程思廉于至元二十六年任陕西行台御史中丞的记载未必有误。可能云南行台动议设立是在至元二十六年,程思廉于该年被任命为云南行台御史中丞,但直到至元二十七年五月,云南行台才成为一个正式的机构。另外,根据《元史》卷一五《世祖纪十二》记载,至元二十六年六月,云南复立提刑按察司。卷八六《百官志二》有“(至元)二十七年,以云南按察司所治,立云南行御史台”。云南设立行台的决议,应该是在至元二十六年六月之后。程思廉如果在至元二十六年就被任命为云南行台御史中丞,其时间也应当是在二十六年六月后。究竟《程思廉传》及《神道碑》所言“至元二十六年”是否是在传抄过程中的笔误,尚待新资料证明。 《元史》卷一七《世祖纪十四》,第371页。 《宪台通纪·立陕西行御史台》,《宪台通纪(外三种)》,第40页。《元史》卷一九《成宗纪二》大德二年十一月条:“罢云南行御史台,置肃政廉访司。”据《宪台通纪·立陕西行御史台》记载,大德元年七月二十三日朝廷下旨命令设立陕西行台的确切时间。《元史》卷六○《地理志三》“陕西等处行中书省”“奉元路”条下记载:“大德元年,移云南行台于此,为陕西行台。”这是陕西行台设立于大德元年的另一个证据。《元史》卷一九《成宗纪二》大德二年六月条下,有“西台侍御史脱欢以受赂不法罢”,可证最晚在大德二年六月前行台已经改名为陕西行台,移治陕西。此外,《元史》卷一六七《张立道传》:“大德二年,廷议求旧臣可为梁王辅行者,立道遂以陕西行台侍御史拜云南行省参政。”可为大德二年陕西行台已经确立之佐证。大德二年十一月罢云南行台是否为大德元年十一月之误?然而《元史》本纪部分依据元朝各帝《实录》修纂而成。《实录》应为编年体,不太可能出现大德元年之事误记在大德二年下的情况。《元史》卷六一《地理志四》“云南诸道路肃政廉访司”下有:“大德三年,罢云南行御史台,立肃政廉访司。”《宪台通纪·复立京兆廉访司》记载大德三年正月九前,陕西行台已被朝廷下令撤销。无论陕西行台究竟在大德元年还是二年设立,都可以确定,大德三年所罢,确为陕西行台。《地理志四》记载的“大德三年”可能为“大德元年”之误,或者是编纂者将云南行台与陕西行台当作同一个机构,陕西行台沿用了云南行台的旧称,误将陕西行台被废之事记在了云南行台下。清代汪祖辉《元史本证》卷二六《证遗三·地理四》,林涓《〈元史·地理志〉之“云南行省”篇校注》(林超民主编《西南古籍研究(2001年)》,云南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42页)根据《成宗本纪》大德二年罢云南行台一条,指出《地理志》大德三年罢云南行台为误。。但至元二十九年九月二十三日,云南行台被罢,同时,云南廉访司设立。b《元史》卷一七《世祖纪十四》,第366页。这是云南行台第一次被罢。五个月后,即至元三十年二月,云南行台复设。c《元史》卷一六《世祖十三》,第337页。云南行台的设立年代,《元史·世祖本纪》记为至元二十七年五月己巳。《元史·程思廉传》(“至元二十六年,立云南行御史台,起复思廉为御史中丞。”)及《程思廉传》所本《河东廉访使程公神道碑》记载设台时间为至元二十六年。(王思廉《河东廉访使程公神道碑》,《国朝文类》卷六七:“至元二十六年立云南行御史台,擢拜中丞。”)《元史·程思廉传》校勘记指出“二十六年立云南行御史台 本书卷一六《世祖纪》至元二十七年五月己巳条、卷八六《百官志》皆系二十七年。《新元史》改‘六’为‘七’,是。”云南行台正式设立的年代应该是至元二十七年,程思廉于元贞二年正月去世,《神道碑》作于大德元年冬,去至元二十六年不过七八年。排除笔误的可能性,程思廉于至元二十六年任陕西行台御史中丞的记载未必有误。可能云南行台动议设立是在至元二十六年,程思廉于该年被任命为云南行台御史中丞,但直到至元二十七年五月,云南行台才成为一个正式的机构。另外,根据《元史》卷一五《世祖纪十二》记载,至元二十六年六月,云南复立提刑按察司。卷八六《百官志二》有“(至元)二十七年,以云南按察司所治,立云南行御史台”。云南设立行台的决议,应该是在至元二十六年六月之后。程思廉如果在至元二十六年就被任命为云南行台御史中丞,其时间也应当是在二十六年六月后。究竟《程思廉传》及《神道碑》所言“至元二十六年”是否是在传抄过程中的笔误,尚待新资料证明。 《元史》卷一七《世祖纪十四》,第371页。 《宪台通纪·立陕西行御史台》,《宪台通纪(外三种)》,第40页。《元史》卷一九《成宗纪二》大德二年十一月条:“罢云南行御史台,置肃政廉访司。”据《宪台通纪·立陕西行御史台》记载,大德元年七月二十三日朝廷下旨命令设立陕西行台的确切时间。《元史》卷六○《地理志三》“陕西等处行中书省”“奉元路”条下记载:“大德元年,移云南行台于此,为陕西行台。”这是陕西行台设立于大德元年的另一个证据。《元史》卷一九《成宗纪二》大德二年六月条下,有“西台侍御史脱欢以受赂不法罢”,可证最晚在大德二年六月前行台已经改名为陕西行台,移治陕西。此外,《元史》卷一六七《张立道传》:“大德二年,廷议求旧臣可为梁王辅行者,立道遂以陕西行台侍御史拜云南行省参政。”可为大德二年陕西行台已经确立之佐证。大德二年十一月罢云南行台是否为大德元年十一月之误?然而《元史》本纪部分依据元朝各帝《实录》修纂而成。《实录》应为编年体,不太可能出现大德元年之事误记在大德二年下的情况。《元史》卷六一《地理志四》“云南诸道路肃政廉访司”下有:“大德三年,罢云南行御史台,立肃政廉访司。”《宪台通纪·复立京兆廉访司》记载大德三年正月九前,陕西行台已被朝廷下令撤销。无论陕西行台究竟在大德元年还是二年设立,都可以确定,大德三年所罢,确为陕西行台。《地理志四》记载的“大德三年”可能为“大德元年”之误,或者是编纂者将云南行台与陕西行台当作同一个机构,陕西行台沿用了云南行台的旧称,误将陕西行台被废之事记在了云南行台下。清代汪祖辉《元史本证》卷二六《证遗三·地理四》,林涓《〈元史·地理志〉之“云南行省”篇校注》(林超民主编《西南古籍研究(2001年)》,云南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42页)根据《成宗本纪》大德二年罢云南行台一条,指出《地理志》大德三年罢云南行台为误。
元成宗大德元年四月四日,御史中丞崔彧等建言数事,其中一条建议将云南行御史台迁至陕西,云南复设肃政廉访司d王晓欣点校《宪台通纪·整治事理》,《宪台通纪(外三种)》,浙江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42页。。同年七月二十三日,朝廷下诏同意将云南行御史台迁至陕西,改名为陕西行御史台e《元史》卷一六《世祖十三》,第337页。云南行台的设立年代,《元史·世祖本纪》记为至元二十七年五月己巳。《元史·程思廉传》(“至元二十六年,立云南行御史台,起复思廉为御史中丞。”)及《程思廉传》所本《河东廉访使程公神道碑》记载设台时间为至元二十六年。(王思廉《河东廉访使程公神道碑》,《国朝文类》卷六七:“至元二十六年立云南行御史台,擢拜中丞。”)《元史·程思廉传》校勘记指出“二十六年立云南行御史台 本书卷一六《世祖纪》至元二十七年五月己巳条、卷八六《百官志》皆系二十七年。《新元史》改‘六’为‘七’,是。”云南行台正式设立的年代应该是至元二十七年,程思廉于元贞二年正月去世,《神道碑》作于大德元年冬,去至元二十六年不过七八年。排除笔误的可能性,程思廉于至元二十六年任陕西行台御史中丞的记载未必有误。可能云南行台动议设立是在至元二十六年,程思廉于该年被任命为云南行台御史中丞,但直到至元二十七年五月,云南行台才成为一个正式的机构。另外,根据《元史》卷一五《世祖纪十二》记载,至元二十六年六月,云南复立提刑按察司。卷八六《百官志二》有“(至元)二十七年,以云南按察司所治,立云南行御史台”。云南设立行台的决议,应该是在至元二十六年六月之后。程思廉如果在至元二十六年就被任命为云南行台御史中丞,其时间也应当是在二十六年六月后。究竟《程思廉传》及《神道碑》所言“至元二十六年”是否是在传抄过程中的笔误,尚待新资料证明。 《元史》卷一七《世祖纪十四》,第371页。 《宪台通纪·立陕西行御史台》,《宪台通纪(外三种)》,第40页。《元史》卷一九《成宗纪二》大德二年十一月条:“罢云南行御史台,置肃政廉访司。”据《宪台通纪·立陕西行御史台》记载,大德元年七月二十三日朝廷下旨命令设立陕西行台的确切时间。《元史》卷六○《地理志三》“陕西等处行中书省”“奉元路”条下记载:“大德元年,移云南行台于此,为陕西行台。”这是陕西行台设立于大德元年的另一个证据。《元史》卷一九《成宗纪二》大德二年六月条下,有“西台侍御史脱欢以受赂不法罢”,可证最晚在大德二年六月前行台已经改名为陕西行台,移治陕西。此外,《元史》卷一六七《张立道传》:“大德二年,廷议求旧臣可为梁王辅行者,立道遂以陕西行台侍御史拜云南行省参政。”可为大德二年陕西行台已经确立之佐证。大德二年十一月罢云南行台是否为大德元年十一月之误?然而《元史》本纪部分依据元朝各帝《实录》修纂而成。《实录》应为编年体,不太可能出现大德元年之事误记在大德二年下的情况。《元史》卷六一《地理志四》“云南诸道路肃政廉访司”下有:“大德三年,罢云南行御史台,立肃政廉访司。”《宪台通纪·复立京兆廉访司》记载大德三年正月九前,陕西行台已被朝廷下令撤销。无论陕西行台究竟在大德元年还是二年设立,都可以确定,大德三年所罢,确为陕西行台。《地理志四》记载的“大德三年”可能为“大德元年”之误,或者是编纂者将云南行台与陕西行台当作同一个机构,陕西行台沿用了云南行台的旧称,误将陕西行台被废之事记在了云南行台下。清代汪祖辉《元史本证》卷二六《证遗三·地理四》,林涓《〈元史·地理志〉之“云南行省”篇校注》(林超民主编《西南古籍研究(2001年)》,云南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42页)根据《成宗本纪》大德二年罢云南行台一条,指出《地理志》大德三年罢云南行台为误。,治所在陕西安西路f皇庆元年改安西路为奉元路。《元史》卷六○《地理志三》,第1423页。。行台这一机构并未被废除,只是治所从云南迁至陕西,且云南行省也同时复立肃政廉访司,由云南诸道路肃政廉访司负责云南行省的监察事务。
大德三年初,陕西行台再次被废。正月九日,朝廷下旨罢西台后,在陕西复立陕西汉中道肃政廉访司a《宪台通纪·复立京兆廉访司》,《宪台通纪(外三种)》,第44页。 《元史》卷二一《成宗纪四》,第455页。《元史》卷二五《仁宗纪二》,第569页。;二月,陕西行台正式被废b《元史》卷二○《成宗纪三》,第426页。。这是元朝负责监察西部事务的行御史台再次被设而复废的过程。大德七年十月辛卯,朝廷再次复立陕西行御史台c《宪台通纪·复立京兆廉访司》,《宪台通纪(外三种)》,第44页。 《元史》卷二一《成宗纪四》,第455页。《元史》卷二五《仁宗纪二》,第569页。。大德十一年,成宗驾崩,武宗即位。武宗年间,陕西行台没有大的变动。元仁宗延祐元年九月,陕西诸道行御史台被罢,这是负责元朝西部诸省监察事务的行台第三次被废d《元史》卷二五《仁宗纪二》,第566页。。但次年五月一日,朝廷再次设立陕西行台e《宪台通纪·复立京兆廉访司》,《宪台通纪(外三种)》,第44页。 《元史》卷二一《成宗纪四》,第455页。《元史》卷二五《仁宗纪二》,第569页。。
算上云南行台的历史,从至元二十七年到延祐二年的二十六年间,经历世祖、成宗、武宗、仁宗四朝,云南—陕西行台共被设立四次、废弃三次。至元二十七年五月,云南行台初设,二十九年九月被罢,是云南行台存在的第一阶段,存在时间为两年零四个月;至元三十年二月,云南行台复立,到大德三年二月再次被罢,是云南—陕西行台存在的第二阶段,其时间约为六年;大德七年十月到延祐元年九月是陕西行台设立的第三阶段,大约持续了将近十一年。延祐二年五月陕西行台第四次设立,从此成为元代一个固定的政治机构。
虽然陕西行台是中央御史台的下属机构,但行台台官和察官的级别与中央御史台相同。f中央御史台下设殿中司和内察院,行台下仅设察院,其属官品级与内察院相同。《元史》卷八六《百官志二》,第2178—2180页。中央御史台、江南行台与陕西行台并不能深入国家的每一个角落,故而在御史台与行御史台下,朝廷将全国分为二十二道,设置了二十二道肃政廉访司。
肃政廉访司原称提刑按察司。至元八年,陕西汉中道提刑按察司设立;至元十九年,西蜀四川道提刑按察司设立;至元二十年,设云南道提刑按察司;至元二十四年,设河西陇右道提刑按察司,同年,云南道提刑按察司被罢。二十六年六月,云南提刑按察司复立g《元史》卷一五《世祖纪十二》,第323页。。
至元二十七年,云南行台设立。二十八年,提刑按察司改称肃政廉访司。大德元年,云南行台迁至陕西,改称陕西行台,云南复立肃政廉访司h《元史》卷八六《百官志二》,第2180页。。陕西行台两次被罢,都随即设立了肃政廉访司。陕西行台成为固定机构后,其下辖四道肃政廉访司:陕西汉中道、河西陇北道、西蜀四川道和云南诸路道i《元史》卷八六《百官志二》,第2182页。。
二、 地理因素
地理因素是云南—陕西行台屡被废设的重要因素。西部地区地域广大、地形复杂是原因之一。云南行台作为一个暂时性机构,不能长久存在,是设立陕西行台的另一个原因。这两点原因决定了陕西行台设立的必然性。
陕西等四省地域广大,地理位置极为重要。元代分天下为二十二道,中书省辖八道,其范围大致是中书直辖区和河南江北行省;江南行台辖十道,其范围大致是江浙行省、江西行省和湖广行省。从地域上看来,陕西行台辖陕西、四川、云南、甘肃四省,与中央御史台、江南行台所辖范围不相上下,甚至面积更广。
从地图上看,四省位于元朝疆域的西部,从西北延伸至西南一线,其北部为蒙元皇室的龙兴之地,原属于中书省直接管辖,后改设和林行省a大德十一年(1307)设立。《元史》卷五八《地理志一》,第1383页。《乌台笔补·论抚治川蜀事状》,《宪台通纪(外三种)》,第354页。 《元史》卷八六《百官志二》,第2180页。,不久改名为岭北行省b皇庆元年(1312)改和林等处行中书省为岭北等处行中书省。《元史》卷五八《地理一》,第1383页。。四省的西北部紧邻察合台汗国,西南部则与宣政院辖区(吐蕃)接壤。西台东部是中书直辖区、河南行省和湖广行省。川蜀地区从宋代起就被“号为左臂”,控制了“荆吴上游”c大德十一年(1307)设立。《元史》卷五八《地理志一》,第1383页。《乌台笔补·论抚治川蜀事状》,《宪台通纪(外三种)》,第354页。 《元史》卷八六《百官志二》,第2180页。。正因为陕西、甘肃、四川、云南等四省“关中东控中夏,西南北极边陲”,因此朝廷才在此地“树之行台,俯制部属”d许有壬《敕赐重修陕西诸道行御史台碑》,《至正集》卷四五,清文渊阁四库全书补配清文津阁四库全书本。。
陕西、甘肃、四川、云南四省的地域范围如此广阔,地理位置又颇为重要,加上越往南方,地势越复杂,中央与这些省份联络并不方便。虽然各省都设置了肃政廉访司,但这些肃政廉访司直属于中央御史台管辖,凡事必须上报中央,诸省与中央之间公文往来,可能需要数月乃至半年。中央与地方之间来耗时太久,不利于行政事务的及时处理。
四省之中,云南行省与中央御史台的距离最远,地形最复杂多样。云南属于高原地区,高山峡谷相间,湖泊山川起伏纵横,地势相对平缓的土地较少,适宜于人类居住的诸多断陷盆地形成了一个个“坝子”,这些断陷盆地决定了云南适宜人类居住的地方被隔成了相对独立的区域,彼此间交通往来不便,在通讯手段落后的年代,地方政府对这些地区无法实现有效的监察管理。
云南行省在至元二十四年云南道提刑按察司被罢e大德十一年(1307)设立。《元史》卷五八《地理志一》,第1383页。《乌台笔补·论抚治川蜀事状》,《宪台通纪(外三种)》,第354页。 《元史》卷八六《百官志二》,第2180页。到二十六年六月云南提刑按察司复立的两三年间,一直没有设立专门的监察机构,该省的监察事务可能就近由西蜀四川道负责,但四川盆地与云贵高原之间地形地势复杂,西蜀四川道管理云南行省境内的监察事务终究鞭长莫及,不能面面俱到。这可能是元朝政府首先决定在云南设立行御史台的原因。
许有壬在追溯云南行台时,只提到云南立“提刑按察司治之,寻升行台,以按边儌”。边儌安宁之后,才“相地之宜”,将行台迁移到陕西f许有壬《敕赐重修陕西诸道行御史台碑》。。可见云南行台设置的主要原因之一是为了安定边疆,它设立的目标是短期的,一旦边疆局势稳定,那么这个机构就达成了主要目的,也就无多大用处。换言之,云南行台是元朝政府在当时云南被征服不久、形势不稳的情况下设置的一个暂时性机构。既是暂时性机构,一旦目的达成,自然会被撤销。
云南行御史台究竟是只管理云南一省的监察事务,还是如后来的陕西行台管理四省的事务,史书中没有明确的记载。云南行台如果管辖云南、陕西、甘肃和四川四省监
察事务,那么将其余三省的事务统统汇报到云南,再由云南向中央汇报,既无必要,也更耗费时间。
假设云南行台管辖四省,其地域大小与中央御史台、江南行台大致相等,但其他三省,尤其是陕西行省,紧邻中书直辖区,如果归属云南行台管理,陕西道肃政廉访司与中央御史台的直接联系就被切断,必须绕道云南,再由云南行台与中央御史台联系,事务的处理结果、中央御史台的命令必须先经云南,再到陕西。云南行台的设置没有加强中央与地方的沟通,故此云南行台没有长期存在的理由。同时可以判定,在云南行台时期,陕西行省并不隶属云南行台管辖。从云南行台设置的初衷和现实需求来看,在第一次设立时云南行台极有可能只管理云南一省的监察事务,但考虑到行政疆界的划定与实际地势走向不完全吻合,云南行台的管辖范围与云南行省也可能并不完全重合。在四川行省的南部与云南行省接壤的地区,由云南行台管辖的可能性更大。
如果云南行台只辖云南一省,比之中央御史台辖中书直辖区、河南江北行省、甘肃、陕西、四川诸省,江南行台专莅江南之地,规模太小,没有和江南行台成为平行机构的条件。何况云南原本就由提刑按察司管理,云南一省的事务是由云南诸道提刑按察司还是由云南行台向中央御史台负责并没有太大区别,这可能是云南行台设立两年零四个月后就被废弃的主要原因。行台废置后,云南行省随即复设肃政廉访司管理监察事务。
管辖云南的行御史台不能长期存在,但西部一带地域广大,“甘肃、陕西两处行中书省,控御西北边境,诸王驸马驻扎去处,钱粮出入,支持浩大。四川、云南两处行省,亦系边远蛮夷地面,不渐声教,形势险恶”。西部地区终究需要设置一个行台。大德元年四月四日御史中丞崔彧建言整治事理,其中一条就提到“今云南立行御史台,甘肃、陕西、四川各立肃政廉访司,轻重倒置,耳目有所不及”。崔彧建议:“若将云南行台移置安西路陕西等处,其云南止设肃政廉访司,又陕西道元立肃政廉访司,却于凤翔府酌中处设置,并甘肃、四川两处肃政廉访司,通计四道,隶属陕西等处行御史台节制,四省文卷,每年监察御史找照刷。其甘肃边境等处,每年行台官亲行镇遏军民、纠察非违。其于国家便益,不可尽言。”a屈文军点校《宪台通纪(外三种)新点校》,华夏文化艺术出版社,2006年,第27页。《宪台通纪·整治事理》,《宪台通纪(外三种)》,第42页。“轻重倒置”王晓欣校本作“轻重例置”,屈文军校本据文义改。《宪台通纪·立陕西行御史台》,《宪台通纪(外三种)》,第42页。正由于种种益处,元成宗在大德元年七月二十三日,下旨将云南行台迁至陕西,设立陕西行御史台。陕西行省东邻中枢,西控甘肃,南接川蜀,在西部监察区中距中央最近。行台设于陕西势所必然。
圣旨还提到,陕西行台“比着江南四省b指江浙行省、福建行省、江西行省和湖广行省。大德三年,福建行省撤销,归属江浙行省。南台所辖行政区划由四省变为三省。谭其骧《元福建行省建置沿革考》,《长水集》(上),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48页。呵,钱粮、百姓虽是少呵,这四省地宽远……比着江南立定呵,勾当上有益去也”c屈文军点校《宪台通纪(外三种)新点校》,华夏文化艺术出版社,2006年,第27页。《宪台通纪·整治事理》,《宪台通纪(外三种)》,第42页。“轻重倒置”王晓欣校本作“轻重例置”,屈文军校本据文义改。《宪台通纪·立陕西行御史台》,《宪台通纪(外三种)》,第42页。。至元十四年设立的江南行台已经充分展示了行御史台作为御史台派出机构,在监察地方官员、镇遏军民、荐举贤良等事务中发挥的积极作用。将江南行台的经验推及国家西部,在西部设立行御史台,负责对该地区进行监察,是陕西行台得以设立的另一个原因。
三、 南台的影响
江南行台是最终促成陕西行台成为稳定机构的重要因素。行台与行省同治一地是江南行台影响之下的产物。
陕西行台治所设在陕西奉元路。之所以选择奉元路作为西部行台的治所,是因为在陕西、甘肃、四川、云南四省之中,陕西行省不但“据要重以控西北南三陲”,“当天下一面”a许有壬《陕西行中书省题名记》,《至正集》卷四二,清文渊阁四库全书补配清文津阁四库全书本。《元史》卷一六《世祖纪十三》,第344页。 虞集《御史台记》,《道园学古录》卷二二,四部丛刊景明景泰翻元小字本。,且与中央直辖区接壤,距离中枢最近。这是其他三省都不具备的有利条件,也是陕西行省被划入陕西行台管辖范围的重要因素。陕西行台的治所与陕西行省的治所同在奉元路,因袭了云南行台与云南行省的治所同在中庆路的传统,而这种行省、行台治所同在一地的设置则是受到了江南行台的影响。
至元十三年南宋灭亡,同年元朝政府在临安设立两浙大都督府,是后来江淮行省与江浙行省的前身。至元十四年,元朝政府又在南宋故地设立江南行台。南宋故地归附不久,人心不稳,元朝对这些地区的统治基础还不牢固。从至元十四年到至元二十六年,江淮行省的治所在扬州与杭州之间反复迁移。治所设在扬州,是因为扬州是南北交通的枢纽城市,在唐朝中后期经济重心转移到南方后,扬州作为长江与运河的交汇点,掌握了扬州就等于控制了南方粮食运往北方的通道。杭州则是南宋故都,在过去的一百多年中一直是江南地区的行政中心,行省治所设于杭州的政治意义不言而喻。b李治安、薛磊《中国行政区划通史·元代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211—212页。在江淮行省治所的反复迁移中,江南行台的治所也随之在杭州、扬州间反复迁徙,有时和江淮行省的治所同在一个城市。
行台主要的功能是对辖区内的各行省进行监察。至元二十八年,元世祖下诏“行御史台勿听行省节度”c许有壬《陕西行中书省题名记》,《至正集》卷四二,清文渊阁四库全书补配清文津阁四库全书本。《元史》卷一六《世祖纪十三》,第344页。 虞集《御史台记》,《道园学古录》卷二二,四部丛刊景明景泰翻元小字本。,进一步确立了行台监察行省官员的权力。此外,行省与行台日常公务往来极多,治所同在一地使省、台的联系更为紧密。江南行台的治所随着江淮行省治所的变动而迁移,极有可能是出于两方面的考虑:强化行台对行省的监察和加强行台与行省联系。
至元二十八年,江淮行省的江北地区划入河南行省,江淮行省改名为江浙行省,治所杭州,江南行台在次年移治建康。由于杭州地理位置比较偏僻,不如建康府便当d《南台备要·移台事》,《宪台通纪(外三种)》,第171页。,故行省与行台不同治一地。此外,建康和扬州一样,都是地处长江下游的江畔城市,有利于通过长江,对位处于其上游的江西行省和湖广行省进行监察。至元二十八年,扬州划归河南江北行省,江南行台迁至建康,“专莅江南之地”e许有壬《陕西行中书省题名记》,《至正集》卷四二,清文渊阁四库全书补配清文津阁四库全书本。《元史》卷一六《世祖纪十三》,第344页。 虞集《御史台记》,《道园学古录》卷二二,四部丛刊景明景泰翻元小字本。。
行台与行省治所同在一地,无疑有利于行台对行省的监察与监控。云南行台与云南行省同治中庆路,陕西行台和陕西行省同治奉元路,加强了行台对行省的监察,不能不说是因袭了江南行台的旧制。陕西行台的治所在奉元路。奉元路即唐代京兆府,从西周到唐代一千多年间,有多个王朝建都于此,其政治意义与历史意义不亚于南台治所集庆路。
同时,奉元路的地理位置并不偏僻,因此陕西行台和陕西行省的治所始终同在一路,直到元末都没有变化。
四、 设立陕西行台的必然性
云南—陕西行台虽然屡经设、废,但并不意味着在行台废弃期间,西部诸省就没有朝廷机构进行监察。从至元六年起,元朝政府就在其统治区内设立提刑按察司,代中央御史台监察各地a虞集《御史台记》。 云南—陕西行台罢废时期依次持续了五个月、四年零八个月、八个月。 《宪台通纪·廉访分司出巡日期》,《宪台通纪(外三种)》,第65—66页。。西部地区从至元初年起就有河东陕西道提刑按察司监察,至元八年设陕西四川道,十九年设西蜀四川道,二十年设云南道,二十四年设河西陇右道。西部诸省官员一直有监察机构对其进行监督,只是由于职权的大小,监察的实际效果可能比不上内台八道和南台十道。
从至元二十五年到延祐二年的二十六年间,云南—陕西行台的存在时间为十九年零四个月b云南—陕西行台存设时期依次持续了两年零四个月、六年、十一年。,废弃时间约为五年零九个月c虞集《御史台记》。 云南—陕西行台罢废时期依次持续了五个月、四年零八个月、八个月。 《宪台通纪·廉访分司出巡日期》,《宪台通纪(外三种)》,第65—66页。,存在时间明显长于废弃时间,可见云南—陕西行御史台的存在不但有必要,也发挥了一定的作用。虽然从大德三年二月到大德七年十月,陕西行台废置四年零八个月之久,但虞集在《御史台记》一文中追溯陕西行台的设立过程时甚至没有提及这一段历史,只提到陕西行台在“西行台初由云南廉访司升行台。大德元年,移治陕西,号陕西诸道行御史台,莅陕西、甘肃、四川、云南之地。延祐间暂废,随复其官,秩如南台”d虞集《御史台记》。。大德三年到七年,陕西行台被废置四年零八个月之久的原因尚不明确,但在此期间四省各有肃政廉访司进行监察是确凿无疑的。
陕西行台屡屡被罢,可能与西部四省地域过于广阔而人口不多、监察事务较少有关。中央御史台辖中书直辖区及河南江北行省,分为八道;江南行台辖三省,分为十道;陕西行台辖区四省面积较内台、南台更大,每一省只设立一个肃政廉访司。这样的设置并不代表陕西行台的地位不如中央御史台和江南行台重要,仅说明从实际需要的角度看,与内台和南台相比,陕西行台所辖四省尽管地域广阔,但其监察事务少得多。肃政廉访司每年出巡,照刷案牍,监察地方官吏军民,时间为每年八月中至次年四月中e虞集《御史台记》。 云南—陕西行台罢废时期依次持续了五个月、四年零八个月、八个月。 《宪台通纪·廉访分司出巡日期》,《宪台通纪(外三种)》,第65—66页。。在同样的时间里,西部四道肃政廉访司比其余十八道巡视的地方大得多,可见所需处理的事务较之其余十八道少得多。朝廷起初可能因西部四道事务较少,不必另设行御史台管理,但久而久之,西部地域广阔的特点就逐渐显露出来。中央与西部诸省相隔太远,需处理的事务虽少,但一来一往之间,消耗的时间、人力与物力颇多。
元仁宗延祐元年再罢陕西行台后不久就“为罢了西台上头,那里百姓每生受”,最重要的是,元世祖时期就是因为“迤西是紧要地面上头”,所以才“教镇遏么到立着行台来”f《宪台通纪·复立陕西行御史台》,《宪台通纪(外三种)》,第61页。。陕西行台在设、罢之间来回摇摆,最终因为陕西行台所起的积极作用,例如不再令百姓们“生受”,以及考虑到西部地区的地理位置、地域广阔等自然条件,在经历了一段时
间的设、罢后,朝廷比较了设立陕西行台的利弊,做出了设立的决定。
从设立御史台的目的看来,御史台一直是朝廷的耳目之官,掌纠察百官善恶、政治得失。a《元史》卷八六《百官志二》,第2177页。 《宪台通纪·复立陕西行御史台》,《宪台通纪(外三种)》,第61页。 《元史》卷六六《河渠志三》,第1658—1659页。天历间丞相燕铁木儿在元明宗刚即位时指出,治理天下最重要的机构就是“中书省、枢密院、御史台”。明宗表示赞同,并将国家比作一个人的身体,“天下国家,譬犹一人之身,中书则右手也,枢密则左手也。左右手有病,治之以良医,省、院阙失,不以御史台治之,可乎?凡诸王、百司,违法越礼,一听举劾。风纪重则贪墨惧,犹斧斤重则入木深,其势然也。朕有阙失,卿亦以闻,朕不尔责也”b《元史》卷三一《明宗纪》,第696—697页。。御史台的纠察对象不止百官,也包括诸王,甚至中书省、枢密院也在御史台的监察范围内。
行御史台作为御史台的派出机构,不但在官员级别上与御史台相同,职权范围也与中央御史台相仿。行御史台监察地方,上至行省、行枢密院高官,下至管辖区内的所有军民,都是行御史台的监察对象。作为一个区域,行省、行院和行台可以比作“省呵,是身体一般,院是手足一般,台是耳目一般,省、院、台都只是一个勾当有”c《元史》卷八六《百官志二》,第2177页。 《宪台通纪·复立陕西行御史台》,《宪台通纪(外三种)》,第61页。 《元史》卷六六《河渠志三》,第1658—1659页。。将行省比作身体,行院比作手足,行台比作耳目,说明了行省、行院、行台本就是一体,缺一不可。对元朝统治下的一个地区而言,行省、行院、行台通力合作是中央有效控制该地区的必要条件。何况废置行台之后,“大勾当里好生妨废着有”d《宪台通纪·复立陕西行御史台》,《宪台通纪(外三种)》,第61页。,因为西台被罢,耽搁了重要事项的处理时机,权衡之下,立西台有百利而无一害,罢西台却带来了种种不便之处,甚至会贻误处理重要问题的时机,没有人会弃西台不用。
陕西行台在延祐二年后成为一个固定的行政机构,负责监察元代西部四省,直到元末。在行台设置期,陕西行台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至大元年,西台御史王琚建议在丰利渠上开石渠,该渠沿用到至正年间,由陕西行省复行修治,灌溉农田达四万五千余顷e《元史》卷八六《百官志二》,第2177页。 《宪台通纪·复立陕西行御史台》,《宪台通纪(外三种)》,第61页。 《元史》卷六六《河渠志三》,第1658—1659页。;近至大三年,陕西行台御史王承德建议在泾阳洪口展修石渠,“为万世之利”f《元史》卷六五《河渠志二》,第1630页。洪口渠在陕西奉元路。。这只是陕西行台日常公务中的一小部分,但已经使百姓颇为受益,更不必提行台与肃政廉访司在监察官员、审理刑狱、荐举人才等日常工作中发挥的积极作用了。但陕西行台毕竟是专制时代的产物,其监察功能能否完全发挥有时受到人为因素的制约。至正年间丞相脱脱之弟也先帖木儿败兵于河南,西台监察御史十二人弹劾其丧师辱国,脱脱将西台御史大夫与十二名监察御史一起降职,导致了“由是人皆莫敢言事”的恶果g《元史》卷一三八《脱脱传》,第3345—3346页;《元史》卷一三九《朵尔直班传》,第3359页。。
西部四省特殊的地理状况是影响云南—陕西行台屡次设立、废置的重要因素。江南行台设置的影响,行台与廉访司不同的职权范围是促使陕西行台设立的动因。在屡次设废之间,朝廷评估了陕西行台的价值,权衡设立、废弃陕西行台的利弊,最终确定了行台的设立。二十六年间频设频废,一方面是因为元初国家制度尚未臻于完善,陕西行台不是唯
一屡被废设的唯一机构。另一方面,云南、甘肃、四川、陕西在元朝统一以前分由西夏、大理和南宋统治,制度差异自不待言,其在统合a萧启庆《内北国而外中国:蒙元史研究》(上册),中华书局,2007年,第18页。《元朝的统一与统合:以汉地、江南为中心》一文中引用了政治学者的“国家统合”的概念:“‘国家统合’乃指消弭构成国家的各部门——包括区域、民族、阶级——之间的差异而形成一个向心力高、凝聚力强的政治共同体。‘国家统合’虽为政治统合的一个层次,但亦牵涉经济、文化乃至心理等方面……‘统一’为‘统合’的先决条件,但统一的国家未必产生国家的统合。”的过程中政治、经济、文化、民族与心理多方面因素的影响。设置国家机构的目的在于服务政治,其设立、调整与废置都是为了适应现实的需求。在探讨元代陕西行台的设废原因时,不能不将此纳入考虑范围。
本文在写作过程中获得南京大学杨晓春副教授的多次指导和帮助,特此致谢。
(本文作者为南京大学元史研究室/民族与边疆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
Reasons of the Establishmentand theabolishment of Shanxi Branch Censorate
cai Jingjing, Institute ofasian Studies,nanjing University
Shanxi Branch censorate (Shanxizhu Dao Xing Yu Shi Tai) was established during thePeriod ofzhiyuan (至元,1264—1294). From the 27th year ofzhiyuan to the 2ndyear of Yanyou (延祐,1314—1320), lasted for 26 years, Shanxi Branch censorate was established for four times, yetabolished for three times. Thisarticle fi rst describes theProcess of the establishmentandabolishment of Shanxi Branch censorate. Then it discusses thenecessity of the establishment from theangles of geography. Italso talksabout the in fl uence towards the Jiangnan Branch censorateand theneed of the establishment of Shanxi Branch censorate.
Yüan Dynasty; Shanxi Xing Tai; Establishmentandabolishment; Reason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