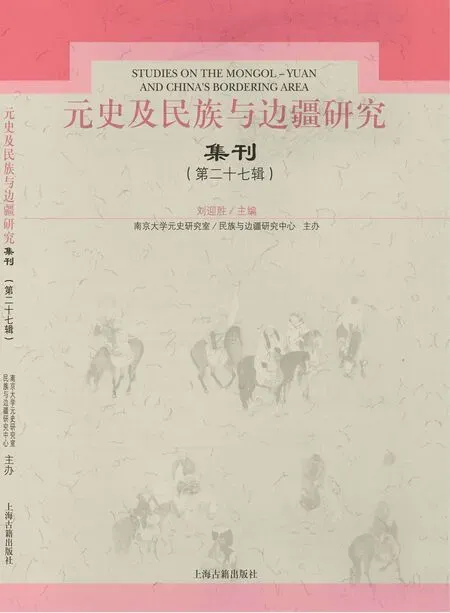《元史·太宗纪》太宗三年以后纪事笺证
刘迎胜
《元史·太宗纪》太宗三年以后纪事笺证
刘迎胜
三年辛卯春二月,克凤翔,攻洛阳、河中诸城,下之[1]。
[1] 钱大昕《廿二史考异(以下略称《考异》)卷八六:据《金史》,凤翔之陷在四月,非二月也。下文云:“十月帝围河中,十二月拔之。”则此时不应有攻下河中事。汪辉祖《元史本证》(以下略称《本证》)卷一证误一:案:下文云十月“帝围河中”,十二月“拔之”,则二月未尝下河中也。
《圣武亲征录》:“辛卯(1231)春二月,遂克凤翔,又克洛阳、河中数处城邑而还。——[清]何秋涛校正《校正元圣武亲征录》一卷,清光绪小沤巢刻本,王国维校注并跋,北京图书馆。《蒙古史料四种》本中无“二月”。 又,《圣武亲征录》:“冬十月初三日,上攻河中府。十二月初八日克之。”金河中府,治今山西永济县。
《永乐大典》卷一〇八八九录元明善《清河集》中《按竺迩神道碑》:“辛卯,大军复围金凤翔。公攻西南陬,城陷,追斩守将刘兴哥。从击西和。宋将强俊壁数万人,清野以老我师。公将死士诟城下挑战诱俊。俊怒击我,公佯北,贼逐利去城稍远,奇兵入夺其城,要其归师。贼亦殊死战,斩首数千级,生获俊。余众退保仇池,击之乃溃。”
夏五月,避暑于九十九泉[1]。命拖雷出师宝鸡[2]。遣搠不罕使宋假道,宋杀之[3]。复遣李国昌使宋需粮[4]。
[1] 《圣武亲征录》:“避暑于官山。”
[清]李文田《元史地名考》(第23页):《辽志》:“丰州天德军有大盐泺、九十九泉、没越泺、古迹口、青冢,即王昭君墓。”张鹏《使俄罗斯行程录》:“叶不孙郭儿地稍平,衍清水北流有九十九泉,元太宗尝避暑于此,其水发源官山,流为黑河,云是蒙古祖冢。” 何秋涛注《圣武亲征录》时提到:“宫山当作官山。《纪》作九十九泉,当是一地。考《元一统志》,官山在废丰州东北一百五十里,上有九十九泉,流为黑河,即其地也,在今归化城境内。北魏《太祖纪》:天赐三年八月丙辰,西登武要北原,观九十九泉。即此。然《水经》□水注又谓:沮阳城东八十里有牧牛山,下有九十九泉,山上有道武皇帝庙、沮阳故城。在今宣化府怀来县南,即《水经注》所称,乃妫水上源也。疑北魏有两九十九泉。”
阿布拉莫夫斯基注(33):九十九泉位于官山;形成南穿今归绥县之黑河(《明一统志》卷二二,叶八;《蒙古游牧记》卷五,叶五;《归绥县志》,叶一四)。《元朝秘史》节272提到,1231年窝阔台于失剌迭克禿儿,龙虎台(按,此地名《秘史》音写为失剌近克禿儿,旁注为龙虎台)驻夏。这与《元史》所述不一致,因为此地位于北京西北的南口(有时称居庸关)(Dieneunundneunzig Quellen befanden sichauf dem Kuan-shan; sie bilden
den Hei-Fluss, der südlichvom heutigen Kuei-sui-hsienverläuft. (Ming-i-t’ung-chih, 22, 8r, Meng-ku yu-mu-chi 5, 5v, Kuei-sui-hsien-chih, 14r). GG §272 berichtet, dass Ögedei den Sommer 1231 in Šira-dektur, Lung-hu-t’ai,verbracht habe. Dies stimm tnicht m it derangabe im YS überein, da dieser Ortamnan-kou-(bzw. Chü-yung)Pass,nordwestlichvonPeking liegt)。——《太宗纪》德译,第140页。
辽重熙十三年(1044)九月“壬申,会大军于九十九泉,以皇太弟重元、北院枢密使韩国王萧惠将先锋兵西征”。——《辽史》卷一九《兴宗纪》。
《元史》卷一一五《睿宗传》:“辛卯(1231)春,破洛阳、河中诸城。太宗还官山”。——第2885页。
据检索,近二十余年中有关“九十九泉”较为重要的研究有:
李逸友《北魏九十九泉御苑遗址》,《内蒙古文物考古》,1998年,第1期。
常谦《北魏长川古城遗址考略》,《内蒙古文物考古》,1998年,第3期。
张文生、曹永年《隋炀帝所幸启民可汗牙帐今地考》,《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8年,第3期。
孟克巴雅尔《九十九泉》,内蒙古大学硕士论文,导师白音查干,2006年6月。
白音查干《九十九泉与匈奴文化》,《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2006年,S1期。
孟克巴雅尔《历史上的九十九泉》,《蒙古史研究》第10辑,2010年,等。
九十九泉位于内蒙古乌兰察布市察右中旗科布林镇南、阴山北麓的辉腾锡勒草原,指此处为数众多的小湖。
[2] 阿布拉莫夫斯基注(34):在官山的一次忽里台大会上确定,分两路攻金。此计谋出自金降人李昌国(《元史》卷一一五《拖雷传》,叶一,参见注(36))。拖雷应从南方发起进攻,因此必须通过宋境。试比较奥托·福兰阁《中华帝国史》第四卷,页286 (Man hatteauf einem qurultaiauf dem Kuan-shan beschlossen, die chinvonzwei Seitenanzugreifen. DerPlan dazu sollvon Li ch’ang-kuo (s.anm. 36), einem chin-Deserteur, stammen. (Biogr.von Tolui, YS 115, 1v). Tolui sollte denangriffvon Süden her führen, und musste deswegen durch Sung-Gebietziehen.vgl.auch O. Franke IV, S. 286)。——《太宗纪》德译,第140页。
[3] 阿布拉莫夫斯基注(35)表示此人不可考,仅提出有关汉字“搠”在元代的读音,参见伯希和1934年刊于《通报》第31期文页158 (Nichtzu identi fizieren.zuraussprache “ch’o” für 搠,zur Yüan-Zeit,vgl.P.Pelliot, TP31 (1934), S. 158)。——《太宗纪》德译,第140页。
其实有几种史料提及搠不罕使宋事。如《秘史》第251节提到:在后,成吉思汗差使臣主卜罕(中)等,通好于宋,被金家阻挡了(旁译)。其中之“主卜罕”,当即此人。《蒙鞑备录》[宋]孟珙撰、王国维笺证《〈蒙鞑备录〉笺证》,《蒙古史料四种校注》:“近者入聘于我宋副使速不罕者,乃白鞑靼也。每联辔闲,速不罕未尝不以好语相陪奉慰劳,且曰:‘辛苦无管待,千万勿怪。’”按此记载,搠不罕为汪古人。 [宋]魏了翁《应诏封事》(《鹤山全集》卷一八“奏议”,四部丛刊景宋本):“虏将[别]大赤辈已纵骑焚掠,岀没吾地。而虏使速不罕方以议和留兴赵原,我使王良能、李大举方以报聘,诣凤翔府。”同氏《故太府寺丞兼知兴元府利州路安抚郭公墓志铭》(《鹤山全集》卷八二):“四季正月,鞑人又至,则径属他官往武休议和,事甚秘,公弗及知。虏又出嫚书索粮二十万斛。五日取若干斛,其使速
不罕诸人裴回兴赵原,而别大赤辈已纵骑焚掠,出没自如。制帅方令诸将毋得擅出兵,沮和好,且遣王良能、李大举诣凤翔。” 《元史》卷一一五《睿宗传》(第2886页):“拖雷总右军自凤翔渡渭水,过宝鸡,入小潼关,涉宋人之境,沿汉水而下。期以明年春,俱会于汴。遣搠不罕诣宋假道,且约合兵。宋杀使者。”
关于这位搠不罕(Ĵubqan),罗亦果有详论,见氏著《元朝秘史》英文译注,下册,页909—910(Igor de Rachew iltz, The Secret History of the Mongols,a Mongolian Epic Chronicle of the Thirteenth Century, Translated w itha НistoricalandPhilological commentary,vol. 2, Brill, Leiden-Boston, 2006, seeP.909—910)。
[4] 阿布拉莫夫斯基注(36):这里涉及的是李邦瑞,其传记在《元史》卷一五三,叶12—13 。其名字为昌国(国昌乃误!)。此为他第三次使宋,为与之达成一项我们尚不详知内容的和议。参见福兰阁《中华帝国史》第五卷,页154—155 (Es handelt sich hier um LiPang-jui, dessen Biograpie im YS 153, 12v—13r steht. SeinPersönlichernamer war ch’ang-kuo (Kuo-ch’ang is falsch!). Dies war seine dritte Gesandtschaftzu den Sung, er handelte m it ihnen einabkommenaus, über das w irabernichts genaueres erfahren. Siehe O. Frankev., 154-155.)。——《太宗纪》德译,第140—141页。
阿布拉莫夫斯基证据甚为充分,查清代以来续《元史》诸家,包括屠寄均未发现《元史》此处之错误。李邦瑞与耶律楚材交往密切,《湛然居士文集》中保留了几首楚材与之唱和之诗,多可证其使宋事。详见卷一五三《李邦瑞传》。
秋八月,幸云中。始立中书省,改侍从官名[1]。以耶律楚材为中书令,粘合重山为左丞相[2],镇海[3]为右丞相[4]。是月,以高丽杀使者[5],命撤礼塔[6]率师讨之,取四十余城。高丽王[7]遣其弟怀安公请降[8]。撒礼塔[9]承制设官分镇其地,乃还[10]。
[1] 李涵《宋辽金元史论集暨师友杂议》(2002年12月初版,第17—21页)在唐长孺先生的基础上,对元代中书省制度的演进有研究。
[2] 《元史》卷一五七:“时耶律楚材为右丞相,凡建官立法,任贤使能,与夫分郡邑,定课赋,通漕运,足国用,多出楚材,而重山佐成之。”粘合重山为金金紫光禄大夫、中都留守粘合合答之孙,金大安三年(1211年)入质蒙古宫廷,窝阔台在位时任中书左丞相。刘晓对其有研究,见《〈全元文〉整理质疑》,《文献》,2002年第1期。
[3] 《元史》卷一二〇有传。
阿布拉莫夫斯基注(39):伯希和的《中亚与远东的基督教》页626中有其简传(Eine kurze Lebensbeschreibung findet sich inPELLIOT, chrétiens, s. 628)。——《太宗纪》德译,第141页。
[4] 《圣武亲征录》:“是年秋八月十四日至西京。秋涛案:西京仍金旧名《本纪》云幸云中是也。执事之人各执名位:兀都原作相,秋涛校改。撒罕中书令,粘合重山右丞相,镇海左丞相。张石州曰:《纪》作以耶律楚材为中书令、粘合重山为左丞相、镇海为右丞相。秋涛案:《镇海传》亦作右丞相。”
楚材(字晋卿,契丹人,或称中书侍郎),曰粘合重山(女真人,或称将军),共理汉事;曰镇海,专理回回国事。”按只,据王国维考证:“彭氏所指,疑即《秘史》之额勒只吉歹。《秘史》续集卷二:‘皇帝圣旨,众官人每著额勒知吉歹为长,依著额勒知吉歹的言语行事。’是太宗即位时,额勒知吉歹实为宰相。”额勒知吉歹与按只(eljigidei)是同一人名的不同汉译。以蒙古人(黑鞑人)为长是元朝任官的惯例,蒙古国时期更应如此。耶律楚材被称为中书令,王国维为了弥合《黑鞑事略》与《太宗纪》的矛盾,因此又推论说:“明年,乃以耶律楚材代之。”但《太宗纪》载始立中书省是在彭大雅使金的壬辰年的前一年辛卯,因此,不能以“明年(癸巳)乃以耶律楚材代之”来解释。……《重山传》称“耶律楚材为右丞相”,这与“中书令”、“中书侍郎”一样,只是汉语对比阇赤的不同称译。耶律楚材是1218年受成吉思汗之召至漠北,或许是因为耶律楚材是契丹帝裔,契丹与蒙古同为金人世仇,所以位居从敌国来附的“金源贵族”粘合重山之上。
[5] 指太祖十九年(1224)蒙古使臣著古欤被杀事。
[6] 《本证》卷三七证名一:撒里答、吾也而传。撒儿台、耶律留哥传。撒里台、王荣祖传。撒里塔、洪福源传。传又作撒里荅、撒礼塔。撒里塔,阿布拉莫夫斯基注(41)(《太宗纪》德译,第141页)已将此名还原为蒙古语Sartaq——此名意为“回回”。
[7] 高丽高宗。
[8] 标点本校勘记[一]:怀安公,本书卷一四九王珣传附王荣祖传、高丽史卷九〇宗室传均作“淮安公”,当以作“淮”为是。——第40页。
《元史》卷二〇八《外夷·高丽传》:“太宗三年八月,命撒礼答征其国,国人洪福源迎降于军,福源所率编民千五百户,旁近州郡亦有来师者。”——第4680页。
[朝鲜]权近等撰《朝鲜史略》:“蒙古兵分屯京城四门外,王遣闵曦往犒,仍结和亲。时元帅撒礼塔驻军安北都护府,三军皆降。王遣淮安公侹讲和。初蒙使,爪古与还国道死蒙人疑我杀之构为衅。”——民国国立北平图书馆善本丛书景明万历四十五年赵宦光、葛一龙等刻本。淮安公侹在《高丽史》中出现多次,兹不一一赘引。
[9] 《圣武亲征录》:“自此使遣撒哈塔火儿赤征收高丽,克四十余城还。”王国维注:“征高丽者,《秘史》为札剌亦儿歹豁里赤,与此撒哈塔火儿赤盖一人也。《(元)史·塔出传》:蒙古札剌儿氏,父札剌台,历事太祖、宪宗。”秋涛案:“《纪》作撒礼塔”。阿布拉莫夫斯基注(41)(《太宗纪》德译,第141页)亦以为“撒礼塔”即前述《元史》卷一三三《塔出传》所提及之塔出之父“札剌台”(详论见下),但他注意到此传未提及其征高丽之役(Dort w irdabernichtvon seinem Feldzugnach Korea berichtet)——《塔出传》确实言及札剌台征高丽之役,不过系之于甲寅年(元宪宗四年,1254)。
按,前已指出撒里里塔,可还原为蒙古语Sartaq,意为“回回”,与札剌台(Jalayirtai——蒙古语意为“札剌亦儿部男子”)当非同一人名。《塔出传》明言札剌台征高丽事在甲寅年(元宪宗四年,1254),与此处太宗三年征高丽应非一事。元代史料中有关撒里塔此次出征事,有如下记载:
《元史》卷二〇八《高丽传》:“太宗三年(1231)八月,命撒礼塔征其国,国人洪福源迎降于军,得福源所率编民千五百户,旁近州郡亦有来师者。撒礼塔即与福源攻未附州郡,
又使阿儿禿与福源抵王京,招其主王瞮,瞮遣其弟怀安公王侹请和,许之。置京、府、县达鲁花赤七十二人监之,遂班师。”——第4608页。其他有关记载,详后注。
此战郑麟趾的《高丽史》记载最详,其多处提及撒礼塔,如辛卯年(1231)八月壬午:“蒙古元帅撒礼塔围咸新镇,屠铁州。……曦与兵马判官员外郎崔桂年承三军指挥往犒。蒙兵有一元帅,自称权皇帝,名撒礼塔,坐毡庐,饰以锦绣,列妇人左右。乃曰:‘汝国能固守则固守,能投拜则投拜,能对战则对战,速决了也。汝职为何?’对曰:‘分台官人。’曰:‘汝是小官人。大官人速来降。’”——《高丽史》世家卷二三《高宗二》,明景泰二年朝鲜活字本,云南大学图书馆藏。
[10] 《元高丽纪事》(叶三):九月,上命将撒里塔火里赤,领兵(争)[征]讨。国人洪福源迎军投降,附近州郡亦有来归者。撒里塔火里赤,即与洪福源攻未附州郡。撒里塔火里赤又差阿儿禿与福源,赴其王京招其主王。遣弟怀安公请和,随置王京及诸州郡达鲁火赤七十二人镇抚,即班师。
冬十月乙(酉)〔卯〕[1],帝围河中[2]。十二月[3]己未,拔之[4]。
[1] 标点本校勘记[二]:冬十月乙(酉)〔卯〕,是月癸丑朔,无乙酉日。圣武亲征录有“冬十月初三日,上攻河中府。十二月初八日,克之”。按十月初三日为乙卯,十二月初八日为己未,与下文“十二月己未,拔之”合。今据改。——第40页。
[2] 《元高丽纪事》(叶三)对次月记:“十一月二十九日,元帅蒲桃、迪巨、唐古等三人,领兵至其王京城。高丽遣监察御史闵曦、郎中宋国瞻等,奉牛酒迎之。”
《元史·洪福源传》:“十一月,元帅蒲桃、迪巨、唐古等领兵至其王京,遣使奉牛酒迎之。”——第4608页。
[3] 对于此月高丽之役,《元高丽纪事》(叶三):“十二月一日(按,壬子),高丽王遣曦,诣元帅行营问劳。二日,曦与元帅下四十四人,入王城,付文牒。五日(按,丙辰),国王遣怀安公王侹、军器监宋国瞻等,诣撒里塔屯所犒师。”
《元史·洪福源传》:“十二月一日,复遣使劳元帅于行营。明日,其使人与元帅所遣人四十余辈入王城,付文牒。又明日,遣王侹等诣撒礼塔屯所犒师。”——第4608—4609页。
记载最详者为《高丽史》:“十二月壬子(按,初一日)朔,蒙兵分屯京城四门外,且攻兴王寺。遣御史闵曦犒之,结和亲。翼日,曦又往蒙古屯所,偕蒙使二人、下节二十人以来。命知阁门事崔珙为接伴使,备仪仗出迎宣义门外。入宣恩馆时,撒礼塔屯安北都护府,亦遣使者三人来谕讲和。……丙辰(按,初五日),遣淮安公侹以土物遗撒礼塔。……丁卯(按,初六日),遣人遗唐古、迪巨及撒礼塔之子银各五斤,纻布十匹,粗布二千匹,马韂、马缨等物。甲戍(按,十六日)将军赵叔昌与撒礼塔所遣蒙使九人持牒来。……三军阵,主诣降权皇帝所。……庚辰(按,二十二日)蒙古使赍国赆黄金七十斤、白金一千三百斤、襦衣一千领、马百七十匹而还。遣将军曹时著以黄金十二斤八两、多般金酒器重七斤、白银二十九斤、多般银酒食器重四百三十七斤、银瓶一百十六口、纱罗锦绣衣十六、紫纱袄子二、银镀金腰带二及犴布襦衣二千、獭皮七十五领、金饰鞍子具马一匹、散马一百五十匹遗撒礼塔。”——《高丽史》世家卷二三《高宗二》。
[4] 《大元仓库记》(《广仓学宭丛书》甲类第二集,圣仓明智大学刊行,叶九)记此年或次年事:辛卯(按太宗三年,1231)、壬辰年(按太宗四年,1232),元科州府每岁一石,添带一石,并附余者拨燕京。令陈家奴、田芝等用意催督,一时漕运毋违慢。其通州北起仓,据见可收物处。仰达鲁花赤管民官,备木植差夫,令和伯拨泥匠三人、木匠三人、铁匠一人速修,及差守仓夫役三人,半年交替,如失盗就令均陪。
四年壬辰春正月戊子,帝由白坡[1]渡河[2]。庚寅,拖雷渡汉江[3],遣使来报,即诏诸军进发[4]。甲午,次郑州。金防城提控马伯坚[5]降,授伯坚金符,使守之。丙申,大雪。丁酉,又雪。次新郑。是日,拖雷及金师战于钧州[6]之三峰,大败之[7],获金将蒲阿[8]。戊戌,帝至三峰。壬寅,攻钧州,克之,获金将合达[9]。遂下商、虢、嵩、汝、陕、洛、许、郑、陈、亳、颍、寿、睢、永等州[10]。
[1] 《圣武亲征录》记太宗三年十二月初八日取河中府后:“时有西夏人速哥者,来告黄河有白坡可渡,从其言。”(屠寄《蒙兀儿史记》称速哥为克列亦惕(按,克烈)人。——《斡歌歹可汗本纪》,叶六)
阿布拉莫夫斯基注(43):在河南,今孟津西南。——《太宗纪》德译,第141页。
[2] 《圣武亲征录》:“壬辰(四年)春正月初六日,大兵毕渡,及获汉船七百余艘。”
《金史》卷一七《哀宗纪》:天兴元年(1232,按,此年本为正大九年,正月改元开兴,四月再改元天兴。)春正月“丙戍(按,正月初五,1232年1月28日),大元兵既定河中,由河清县白坡渡河。丁亥(按,正月初六),长乐、撒合引兵至封丘而还。戊子(按,正月初七),左司郎中斜卯爱实上书请斩长乐、撒合以肃军政,不从。都尉乌林答胡土一军自潼关入援,至偃师,闻大元兵渡河,遂走登封少室山。壬辰,卫州节度使完颜斜捻阿不弃城走汴。甲午(按,正月十三),修京城楼橹及守御备。”
《金史》卷一一一《乌林答胡土传》: “正大九年正月戊子(按,正月初七,1232年1月30日),北兵以河中一军由洛阳东四十里白坡渡河。白坡故河清县,河有石底,岁旱水不能寻丈。国初以三千骑由此路趋汴,是后县废为镇,宣宗南迁,河防上下千里,常以此路为忧,每冬日命洛阳一军戍之。河中破,有言此路可徒涉者,已而果然。北兵既渡,夺河阴官舟以济诸军。时胡土为破虏都尉,戍潼关,以去冬十二月被旨入援,至偃师,闻白坡径渡之耗,直趋少室,夜至少林寺。”
上述《哀宗纪》与《乌林答胡土传》所记白坡渡河日期差两日,《亲征录》与《金史》差一日。
《元史》卷一一九《塔察儿传》:“太宗伐金,搭察儿从师,授行省兵马都元帅。分宿卫与诸王军士俾统之。下河东诸州郡,济河破潼关,取陕洛。辛卯,从围河中府,拔之。壬辰,从渡白坡。”——第2952页。
[3] 阿布拉莫夫斯基注(44):汉水此时大致为金宋边界。拖雷在所派应是请求大军借道宋境的使臣被杀之后,越境向宋,并征服了彼处多个城池。此时他引所部军从南进攻南京(开封)。参见福兰阁:《中华帝国史》,卷四,页286 (Der Нan-Fluss bildetzu dieserzeit etwa die Granzezw ischen chin und Sung. Tolui hatternach der Ermordung des Gesandten, der den durchzug der Truppen durch Sung-Gebiet erbitten sollten, die Granzenach
Sung überschritten und dort mehrere Städte erobert.nun führte er seine Truppenvon Süden herzumangriffaufnan-ching (K’ai-feng). Siehe O. Franke, IV, S. 286)。——《太宗纪》德译,第141页。
[4] 《圣武亲征录》:“太上皇遣将贵由报,集军兵等已渡汉江,上亦遣使于太上皇,曰:‘汝等与敌战日久,可来合战。”
《金史》卷一一二《完颜合答传》:“戊辰,北兵渡汉江而北,诸将以为可乘其半渡击之,蒲阿不从。丙子,兵毕渡,战于禹山之前,北兵小却,营于三十里之外。二相以大捷驿报,百官表贺,诸相置酒省中,左丞李蹊且喜且泣曰:‘非今日之捷,生灵之祸,可胜言哉!’盖以为实然也。先是,河南闻北兵出饶峰,百姓往往入城壁、保险固,及闻敌已退,至有晏然不动者,不二三日游骑至,人无所逃,悉为捷书所误。”
《元史》卷一一五《睿宗传》:“乘骑浮渡汉水,遣夔曲涅率千骑驰白太宗。太宗方诣汉水,将分兵应之,会夔曲涅至,即遣慰谕拖雷,亟合兵焉。”——第2886页。
[5] 阿布拉莫夫斯基注(46):有关此人未发现更多史料(Über ihn waren keinenäherenangabezu finden)。——《太宗纪》德译,第141页。
其实在史料中尚能找到几则有关马伯坚的记载:
《圣武亲征录》:“上于正月十三日至郑州,守城马提控者以城降。”何秋涛注:“本纪作马伯坚。”
《金史》卷一七《哀宗纪》:天兴元年(1232)春正月甲午“大元兵薄郑州,与白坡兵合,屯军元帅马伯坚以城降,防御使乌林答、咬住死之” 。
《元史》卷一二二《槊直腯鲁华传》:“壬(申)[辰]正月,太宗自白(波)[坡]济河而南,睿宗由峭石滩涉汉而北。撒吉思卜华集西都水之舟,渡自河阴。至郑,郑守马伯坚降。”——第3014页。
《元史》卷一五一《王善传》:“壬辰,从征河南,至郑州。州将马伯坚素闻善名,登陴大呼曰:‘藁城王元帅在军中否?愿以城降之。’善直前,免胄与语,伯坚果率众出降。善令军中秋毫无犯,民皆按堵,愿从善北渡者以万计授之土田,以安集之。”——第3573页。
[6] 今河南禹州市。
[7] 《圣武亲征录》:“太上皇既渡汉水,有金大将哈答秋涛案,《金史》、《元史》俱作合达。麾下钦察者,逃来告:哈答伏兵于邓西隘截,等候太上皇。是夜会兵明烛而进,哈答、移剌闻知,入邓以避其锋。”
《金史》卷一七《哀宗纪》:天兴元年(1232)“乙未,大元游骑至汴城。丁酉,大雪,大元兵及两省军战钧州之三峰山。两省军大溃,合达、陈和尚、杨沃衍走钧州,城破,皆死之。枢密副使蒲阿就执,寻亦死” 。
同书卷一一二《完颜合答传》:“九年正月丁酉,两省军溃于阳翟之三峰山。初,禹山之战,两军相拒,北军散漫而北,金军惧其乘虚袭京城,乃谋入援。时北兵遣三千骑趋河上,已二十余日,泌阳、南阳、方城、襄、郏至京诸县皆破,所有积聚焚毁无余。金军由邓而东,无所仰给,乃并山入阳翟。既行,北兵即袭之,且行且战,北兵伤折亦多。恒山一军为突骑三千所冲,军殊死斗,北骑退走。追奔之际,忽大雾四塞,两省命收军。少之,雾散乃前,前一大涧,长阔数里,非此雾则北兵人马满中矣。明日,至三峰山,遂溃,事载蒲阿传。合达知大事已去,欲下马战,而蒲阿已失所在。合达以数百骑走钧州,北兵堑其城外攻之,
走门不得出,匿窟室中,城破,北兵发而杀之。时朝廷不知其死,或云已走京兆,赐以手诏,募人访之。及攻汴,乃扬言曰:‘汝家所恃,惟黄河与合达耳。今合达为我杀,黄河为我有,不降何待?’
“合达熟知敌情,习于行阵,且重义轻财,与下同甘苦,有俘获即分给,遇敌则身先之而不避,众亦乐为之用,其为人亦可知矣。左丞张行信尝荐之曰:‘完颜合达,今之良将也。’”
同书同卷《移剌蒲阿传》:“十二月,北兵济自汉江,两省军入邓州,议敌所从出,谓由光化截江战为便,放之渡而战为便、张惠以‘截江为便,纵之渡,我腹空虚,能不为所溃乎?’蒲阿麾之曰:“汝但知南事,于北事何知。我向于裕州得制旨云,‘使彼在沙碛,且当往求之’,况今自来乎。汝等更勿似大昌原、旧卫州、扇车回纵出之。”定住、高、樊皆谓蒲阿此言为然。合达乃问按得木,木以为不然。军中以木北人,知其军情,此言为有理,然不能夺蒲阿之议。
顺阳留二十日,光化探骑至,云:‘千骑已北渡’,两省是夜进军,比晓至禹山,探者续云:‘北骑已尽济。’癸酉,北军将近,两省立军高山,各分据地势,步迎于山前,骑屯于山后。甲戍,日未出,北兵至,大帅以两小旗前导来观,观竟不前,散如雁翅,转山麓出骑兵之后,分三队而进,辎重外余二万人。合达令诸军:‘观今日事势,不当战,且待之。’俄而北骑突前,金兵不得不战,至以短兵相接,战三交,北骑少退。北兵之在西者望蒲阿亲绕甲骑后而突之,至于三,为蒲察定住力拒而退。大帅以旗聚诸将,议良久。合达知北兵意向。时高英军方北顾,而北兵出其背拥之,英军动,合达几斩英,英复督军力战。北兵稍却观变,英军定,复拥樊泽军,合达斩一千夫长,军殊死斗,乃却之。
北兵回阵,南向来路。两省复议:‘彼虽号三万,而辎重三之一焉。又相持二三日不得食,乘其却退当拥之。’张惠主此议,蒲阿言:‘江路已绝,黄河不冰,彼入重地,将安归乎?何以速为。’不从。乙亥,北兵忽不知所在,营火寂无一耗。两省及诸将议,四日不见军,又不见营,邓州津送及路人不绝,而亦无见者,岂南渡而归乎?己卯,逻骑乃知北军在光化对岸枣林中,昼作食,夜不下马,望林中往来,不五六十步而不闻音响,其有谋可知矣。
初,禹山战罢,有二骑迷入营,问之,知北兵凡七头项,大将统之。复有诈降者十人,弊衣羸马泣诉艰苦,两省信之,易以肥马,饮之酒,及暖衣食而置之阵后,十人者皆鞭马而去,始悟其为觇骑也。
庚辰,两省议入邓就粮,辰巳间到林后,北兵忽来突,两省军迎击,交绥之际,北兵以百骑邀辎重而去,金兵几不成列,逮夜乃入城,惧军士迷路,鸣钟招之。樊泽屯城西,高英屯城东。九年正月壬午朔,耀兵于邓城下。北兵不与战,大将使来索酒,两省与之二十瓶。癸未,大军发邓州,趋京师,骑二万,步十三万,骑帅蒲察定住,蒲察答吉卜,郎将按忒木(按,当即上文之按得木),忠孝军总领夹谷爱答、内族达鲁欢,总领夹谷移特剌,提控步军临淄郡王张惠,殄寇都尉完颜阿排、高英、樊泽,中军陈和尚,与恒山公武仙、杨沃衍军合。是日,次五朵山下,取鸦路,北兵以三千骑尾之,遂驻营待杨武。
杨武至,知申、裕两州已降。七日至夜,议北骑明日当复袭我,彼止骑三千,而我示以弱,将为所轻,当与之战。乃伏骑五十于邓州道。明日军行,北骑袭之如故,金以万人拥之而东,伏发,北兵南避。是日雨,宿竹林中。庚寅,顿安皋。辛卯,宿鸦路、鲁山。河西军已献申、裕,拥老幼、牛羊取鸦路,金军适值之,夺其牛羊饷军。癸巳,望钧州,至沙
河,北骑五千待于河北,金军夺桥以过,北军即西首敛避。金军纵击,北军不战,复南渡沙河。金军欲盘营,北军复渡河来袭。金军不能得食,又不得休息。合昏,雨作,明旦变雪。北兵增及万人,且行且战,致黄榆店,望钧州二十五里,雨雪不能进,盘营三日。丙申,一近侍入军中传旨,集诸帅听处分,制旨云:“两省军悉赴京师,我御门犒军,换易御马,然后出战未晚。”复有密旨云:‘近知张家湾透漏二三百骑,已迁卫、孟两州,两省当常切防备。’领旨讫,蒲阿拂袖而起,合达欲再议,蒲阿言:‘止此而已,复何所议。’盖已夺魄矣。军即行。
北军自北渡者毕集,前后以大树塞其军路,沃衍军夺路,得之。合达又议陈和尚先拥山上大势,比再整顿,金军已接竹林,去钧州止十余里矣。金军遂进,北军果却三峰之东北、西南。武、高前锋拥其西南,杨、樊拥其东北,北兵俱却,止有三峰之东。张惠、按得木立山上望北兵二三十万,约厚二十里。按得木与张惠谋曰:‘此地不战,欲何为耶?’乃率骑兵万余乘上而下拥之,北兵却。须臾雪大作,白雾蔽空,人不相觌。时雪已三日,战地多麻田,往往耕四五过,人马所践泥淖没胫。军士被甲骨僵立雪中,枪槊结冻如椽,军士有不食至三日者。北兵与河北军合,四周边之,炽薪燔牛羊肉,更递休息。乘金困惫,乃开钧州路纵之走,而以生军夹击之。金军遂溃,声如崩山,忽天气开霁,日光皎然,金军无一人得逃者。
武仙率三十骑入竹林中,杨、樊、张三军争路,北兵围之数重,及高英残兵共战于柿林村南,沃衍、泽、英皆死,惟张惠步持大枪奋战而殁。蒲阿走京师,未至,追及,擒之。七月,械至官山,召问降否,往复数百言,但曰:‘我金国大臣,惟当金国境内死耳。’遂见杀。”
《永乐大典》卷一〇八八九录元明善《清河集》中《按竺迩神道碑》:“睿宗分兵迂道,并山南间入金境。公前驱趣散关,宋人已烧绝栈道。乃由两当出鱼关,军沔州。而宋制置使桂如渊守兴元,议使如渊假道。公在行,语如渊曰:宋雠金若何?胡不肆我兵锋,一洗国耻?我欲假南郑道,道洋、金牧马唐邓,与王师会,櫇金孱王,宋因之刓其利。师压君境,势不徒还,谓君不得不吾假也。如渊即输刍粮,使百人导之东。适汉水可涉,达邓西,破小关子,金人大骇神我。其平章完颜合答、枢密使移剌蒲[阿]、元帅十七,都尉、兵数十万,御师于邓,不与战,直蹴钧州。金师陈三峰山下,会大雪,交战。公先所部摧其前拒,众乘之奋,金师败绩。由是金不能国。睿宗以玉杯盘生口二十赏公假道功。”
《元史》卷一二一《按竺迩传》改为:“宋制置使桂如渊守兴元。按竺迩假道于如渊曰:‘宋雠金久矣,何不从我兵锋,一洗国耻。今欲假道南郑,由金、洋达唐、邓,会大兵以灭金,岂独为吾之利?亦宋之利也。’如渊度我军压境,势不徒还,遂遣人导我师由武休关东抵邓州,西破小关,金人大骇,谓我军自天而下。其平章完颜合达、枢密使移剌蒲阿帅十七都尉,兵数十万,相拒于邓。我师不与战,直趣钧州,与亲王按赤台等兵合,陈三峰山下。会天大雪,金兵成列。按竺迩先率所部精兵,迎击于前,诸军乘之,金师败绩。” ——第2983—2984页。
黄溍《答禄乃蛮氏先茔碑》:“壬辰,从睿宗大破金兵于钧州三峰山,尽歼其众,金人自是不复能军。睿宗表其功于太宗”——《金华黄先生文集》,卷二十八续稿二十五,四部丛刊本;并见《元史》卷一二一《抄思传》“壬辰,兵次钧州,金兵垒于三峰山,抄思察其营壁不坚,夜领精骑袭之,金兵惊扰,遂乘击之,拔三峰山。睿宗以抄思功闻于朝。” ——第2993页。
元人郝经有诗《三峰山行》:
“朔方善为干腹兵,岂肯掠地还攻城。北王战罢马首回,十年大军不南行。
西域既定杀李王,疾雷破桂关中惊。鸷鸟匿形深且蟠,汴梁不悟空椎冰。
突骑一夜过散关,汉江便著皮船渡。襄阳有兵隔岸看,邓州无人浑不顾。
纵入腹心将安归,彼骑岂足当吾步。脱兔一去不可及,却兵洛涧苻坚误。
日日鏖战深且艰,我帅益忙敌亦闲。短兵相击数百里,孤穷转斗甲尽殷。
直向虎穴探虎子,既入重地宁肯还。扫境尽至欲一赌,前后百匝相回环。
就中真人有天命,跃马直上三峰山。黑风吹沙河水竭,六合乾坤一片雪。
万里投会卷土来,铁水一池声势接。丞相举鞭摔当言,大事己去吾死节。
彦章虽难敌五王,并命入敌身与决。逆风生堑人自战,冰满刀头冻枪折。
一败涂地真可哀,钧台变作髑髅血。二十万人皆死国,至今白骨生青苔。
壕堑己平不放箭,城门著炮犹自开。大臣壅蔽骨肉疏。事急又送曹王来。
至了不去误国贼,向非汝南死社稷,欲为靖康不可得。”——《陵川集》卷一一《歌诗》,[明]正德二年李瀚刻本,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册91,书目文献出版社影印本,第572页。
同氏《合达平章》:
“乘舆已播迁,乾坤在孤注。维时忠荩有哈达,应敌东西无定住。
职兼将相为国桢,身系安危如尚父。贼国布色深冒嫉,小臣献谗极谄附。
飞章诬陷罢兵柄,几把功臣荐刀锯。子仪召入奉朝请,彦章不用大事去。
事急复起使迎敌,即日上道无喜怒。并命鏖战来报捷,每从中制肘屡掣。
峣关透漏斡腹出,大河绝流两军接。天欲亡人不可为,六合横倾数丈雪。
人自为战身伴僵,空拳无皮冻枪折。力竭慷慨赴敌死,死恨不能存社稷。
至今三峰山,白骨尽衔铁。老臣一片忧国心,惨淡悲风与寒月。”——《陵川集》卷一一,第574页。
又同氏《仲德行院》:
“士穷见节义,国乱出忠勇。仲德帝室胄,虎文将家种。
俨俨静且深,辨事不赖宠。帝闻彭城有逆节,诏公密取不敢泄。
临行斩首挂马鞍,万众不欢皆妥帖。仗钺东南当一面,寇去看书寇来战。
中枢大府无人声,儒将威名满淮甸。甫临秦巩遮长安,大军失利三峰山。
径穿敌垒数千里,乘舆己出空泪澘。过门不入急赴难,犯围直向黄河岸。
照碧堂空幸汝南,贼臣新诛卫士散。自古未有降天子,君臣血视付一死。
夫人徒步自拔来,命妇般炮自我始。夫妇死国无与侔,至今闻者涕泗流。” ——《陵川集》卷一一,第575页。
《元史》卷一一九《塔思传》(按,即查剌温):“壬辰春,睿宗与金兵相拒于汝、汉间,金步骑二十万,帝命塔思与亲王按赤台、口温不花合军先进渡河,以为声援。至三峰山,与睿宗兵合,金兵成列,将战,会大雪,分兵四出,塔思冒矢石先挫其锋,诸军继进,大败金兵,擒移剌蒲瓦,完颜合达单骑走钧州,追斩之,遂拔钧州。”——第2938页。
同书卷一四九《郭德海传》(郭宝玉子)“冬十一月,至钧州。辛卯春正月,睿宗军由洛
阳来会于三峰山,金人沟地立军围之。睿宗令军中祈雪,又烧羊胛骨,卜得吉兆,夜大雪,深三尺,沟中军僵立,刀槊冻不能举。我军冲围而出,金人死者三十余万,其帅完颜哈达、移剌蒲兀走匿浮图上,德海命掘浮图基,出其柱而焚之。” ——第3522—3523页。
三峰山之战是中国历史上著名战例,较为重要的研究文章有:
陈高华《说蒙古灭金的三峰山战役》,《文史哲》,1981年03期;
朱玲玲《蒙金三峰山之战及其进军路线》,《军事历史研究》,1987年04期;
石坚军《蒙金三峰山之战新探》,《兰州学刊》,2010年第10期等。
[8] 蒲阿即移剌蒲阿,与完颜合答均为金军统帅,两人传遍均见《金史》卷一一二。《本证》卷三十七证名一:蒲瓦、塔思、史天倪、李冶传。蒲兀、郭德海传。
《圣武亲征录》:“ 太上皇正月十五日至钧州,雪作。上遣大王口温不花、国王答思将军兵至。十六日,雪又作。是日与哈答、移剌合战于三峰山,大败之,遂擒移剌。”
耶律铸:“《战三封》太宗皇帝马渡大河,睿宗皇帝马渡汉江,与金人大战于三封之原。会雪蔽天金人大溃也。豁然雪霁月色如昼,一袭殆尽,因志其事云:
河汉吞声自请平,冷光横绝见长庚。是岁长庚见,数月不灭。
骤挥戈去日西坠,触折柱来天北倾。
威控望舒延苦战,势征滕六纵疑兵。获泽阳之美,尝谓:是日雪之作也,惟见旌旗阵马,蔽天而下皆北兵也。予怪其言,而访诸他人,一如其说。
若非不世云龙变,一举谁收万古名。”——《双溪醉隐集》卷四,民国辽海丛书本。
《元史》卷一一五《睿宗传》:“拖雷既渡汉,金大将合达设伏二十余万于邓州之西,据隘待之。时拖雷兵不满四万,及得谍报,乃悉留辎重,轻骑以进。十二月丙子,及金人战于禹山,佯北以诱之,金人不动。拖雷举火夜行,金合达闻其且至,退保邓州,攻之,三日不下。遂将而北,以三千骑命札剌等率之为殿。明旦,大雾迷道,为金人所袭,杀伤相当。拖雷以札剌失律,罢之,而以野里知给歹代焉。未几,败金军。
壬辰春,合达等知拖雷已北,合步骑十五万蹑其后。拖雷按兵,遣其将忽都忽等诱之,日且暮,令军中曰:‘毋令彼得休息,宜夜鼓噪以扰之。’太宗时亦渡河,遣亲王口温不花等将万余骑来会。天大雨雪,金人僵冻无人色,几不能军,拖雷即欲击之,诸将请俟太宗至破之未晚。拖雷曰:‘机不可失,彼脱入城,未易图也。况大敌在前,敢以遗君父乎。’遂奋击于三峰山,大破之,追奔数十里,流血被道,资仗委积,金之精锐尽于此矣。余众迸走睢州,伏兵起,又败之。合达走钧州,仅遗数百骑。蒲阿走汴,至望京桥,复禽获之。 ”——第2886—2887页。
[9] 《本证》卷三七证名一:合(鞑鞑)[达](据点校本元史改。)雪不台传。哈达、郭德海传。合答、李冶传。
《圣武亲征录》:“十七日上行视战所,嘉之。二十一日克钧州,哈答匿于地穴,亦擒之。”
参与三峰山之战的还有史天泽。王磐《中书右丞相史公神道碑》记:“壬辰歳,太宗由白波渡河,疾趍阳翟与睿宗相会,破合答军于三峰山。”——《元文类》卷五八,四部丛刊本。
《元史》卷一一五《睿宗传》:“太宗寻至,按行战地,顾谓拖雷曰:‘微汝,不能致此捷也。’诸侯王进曰:‘诚如圣谕,然拖雷之功,著在社稷。’盖又指其定册云尔。拖雷从容
对曰:‘臣何功之有,此天之威,皇帝之福也。’闻者服其不伐。从太宗攻钧州,拔之,获合达。”——第2887页。
金朝方面的主要将领,非汉文史料《秘史》与波斯史籍亦有提及。据志费尼记载,为(QDaY RNKW)与(QMRnKWDR)两人。《秘史》节251记为三人“亦列(Ile)、合答(Qada)、豁孛格秃儿(Нöbögetür)”。
至于《秘史》所记之三人,罗亦果有详论,即亦列(Ile)即移剌,乃耶律之另称,指移剌蒲阿;合答(Qada)即完颜合答;而豁孛格秃儿(Нöbögetür),他引那柯通世之意见,以为即完颜陈和尚。——罗亦果《元朝秘史》英文译注,下册,第911—912页。
[10] 《圣武亲征录》:“又克昌州、廓州、嵩州、曹州、陕州、洛阳、濬州、武州、易州、邓州、应州、寿州、遂州、禁州等来降秋涛案:《本纪》云:遂下商、虢、嵩、汝、陕、洛、许、郑、陈、颍、寿、睢、永等州县,与此多异。考金时河南无昌、漷、易、应、遂、禁等州,疑昌、漷即商、虢之音讹,应即颍之音讹,遂即睢之音讹,禁即永之音讹。余未详也。”阿布拉莫夫斯基未注意到这些地名有误,见《太宗纪》德译,第141页,注(52)。
有关本月征高丽事,《元高丽纪事》(叶三):“四年壬辰正月,遣使持玺书谕高丽。”
《元史·洪福源传》:“四年(1232)正月,帝遣使以玺书谕。” ——第4609页。
三月,命速不台等围南京,金主遣其弟曹王讹可[1]入质。帝还,留速不台守河南[2]。
[1] 标点本校勘记[三]:金主遣其弟曹王讹可入质, 按金史卷一七哀宗纪、卷九三宣宗诸子传,讹可为荆王守纯子,金哀宗守绪之侄,此处称“弟”,史文有误。——第40—41页。
刘祁《归潜志》:“南渡之后,为将帅者多出于世家,皆膏粱乳臭子,若完颜白撒,止以能打球称。又完讹可,亦以能打毬,号(杖)[板](据黄丕烈、施国祁校本改)子元帅者。”—卷六,崔文印点校本,中华书局,1983年,页64。“完颜讹可”称“板子讹可”亦见于其他史料,如《金史》卷一七《哀宗纪上》:八年十二月“河中府破,权签枢密院事草火讹可死之,元帅板子讹可提败卒三千走乡。诏赦将佐以下,杖讹可二百以死。”同书卷一〇一《内族讹可传》:“完颜讹可,内族也,时有两讹可,皆护卫出身。一曰草火讹可,每得贼好以草火燎之;一曰板子讹可,尝误以宫中牙牌报班齐者为板子,故时人各以是目之。”
[2] 《圣武亲征录》:“速不歹拔{相}[都]、忒木[歹]火儿赤、贵由拔{相}[都]、塔察儿等适与金战,金遣兄[荆王守仁]之子曹王入质,我军遂退,留速不台拔{相}[都]以兵三万守镇河南。”日本学者堤一昭对此有考证(《忽必烈政权的建立与速不台家族》,张永江译自日本《东洋史研究》第48卷第1号,《蒙古学资料与情报》,1991年第2期,见第9页)。
至于此年高丽情况,《元高丽纪事》(叶四):“三月,高丽遣中郎将池义源、录事洪臣源、金谦等,赉国赆文牒,送撒里塔屯所。”
夏四月,出居庸,避暑官山[1]。高丽叛,杀所置官吏,徙居江华岛[2]。
[1] 《圣武亲征录》:“上与太上皇北渡河,避暑于官山。”
[清]李文田《元史地名考》:《睿宗拖雷列传》:“出北口住夏于官山。”《特薛禅传》:“葬官人山。”《金志》:“西京路大同府宣宁县有官山。”宋彭大雅《黑鞑事略》云:“居庸关北如官山、金莲川等处,虽六月亦雪。”——第23页。
《元高丽纪事》(叶四):“五月,复降旨谕高丽。”
《元史》卷二〇八《高丽传》:“五月,复下诏谕之。”——标点本,第4609页。
《元高丽纪事》(叶四):“六月,本国叛,杀各县达鲁花赤,率王京及诸州郡人民,窜与海岛拒守。洪福源集地界四十余州县失散人民保聚。撒里塔火里赤,中流失卒。别将铁哥火里赤领兵回。其已招降之地,复令福源管领,屯于各处。”
《元文类·征伐·高丽》:太宗“四年(1232)六月,杀达鲁花赤而叛,保海岛”。——卷四一,四部丛刊本。
《圣武亲征录》:“是年,高丽复叛,再命撒儿搭火儿赤征收。”
《元史》卷一五四《洪福源传》:“壬辰夏六月,高丽复叛,杀所置达鲁花赤,悉驱国人入据江华岛。”——第3627—3628页。
朝鲜权近等撰《朝鲜史略》:“崔瑀胁王迁都江华。杀指谕金世冲。瑀欲迁都以避蒙兵,与宰枢议于其第。人情安土重迁,然畏瑀,无敢言者。俞承旦极言其不可,世冲排门而入诘瑀迁都之误,瑀怒杀之。王发开京,入御江华客馆。”——卷八,民国国立北平图书馆善本丛书景明万历四十五年赵宦光、葛一龙等刻本。
[清]李文田《元史地名考》:明人所偁觉华岛即其地也。《提纲》卷一:“海西经松山、杏山,又西经宁远县东南水口口东,有桃花、菊花二岛。”菊花即明觉华岛也。——第23页。
阿布拉莫夫斯基注(55):此岛位于汉江入海口,汉城/首尔西南( Die Insel ist der Mündung des Нanggangvorgelagert, südöstlichvon Seoul)——《太宗纪》德译,第141页。
至于此月其他政事,《大元马政记》“马政杂例”(《广仓学宭丛书》铅印本,上海仓圣明智大学,民国5年(1916),甲类第二集,叶三十三):“太宗皇帝四年壬辰六月二十四日,圣旨:谕西京脱瑞勾索等,即目见阙饮马槽。除东胜、云内、丰州外,依验本路见管户,计一千六百二十七户。每户办槽一具,长五尺,阔一尺四寸,蒙古中样。各处备车牛,限七月十日以内赴斡鲁朵送纳,不得违滞。如违,断按荅奚罪。准此。”
《大元毡罽工物记》“杂用”(《广仓学宭丛书》铅印本,甲类第二集,叶七):“ 太宗皇
帝四年壬辰六月,敕谕丰州云内、东胜二州达鲁花赤官员人等,今差毡匠诣彼居。止岁织(韩)[斡?]耳朵大毡四片,长一丈六尺。给以羊毛五百斤、毛一百斤及染颜色物料,验三州各管。见在军数均科外,旧欠羊毛并今岁者就纳足之。后依例科,取毯匠达鲁花赤都束并诸匠家属三十人,续添二十五,计口五十五,人日支米一升,于云内支付,就报宣差征收禄税所,于秋税内尅除。云内州官应付大屋、二门囗木二株,长一丈四尺。造毕驿递斡耳朵送纳。”
秋七月,遣唐庆使金谕降,金杀之[1]。
[1] 《圣武亲征录》:太宗四年“秋七月,上遣唐庆使金促降,因被杀之”。
唐庆使金事,亦见于《归潜志》卷十一《录大梁事》:天兴元年(元太宗四年,1232):“秋七月,北兵遣唐庆等来使,且曰:‘欲和好成。金主当自来好议之。’末帝托疾,卧御榻上,见庆等掉臂上殿,不为礼。致来旨毕,仍有不逊言,近侍皆切齿。既归馆,饷劳。是夕,飞虎军数辈,愤庆等无礼,且以为和好终不能成,不若杀之快众心。夜中持兵入馆,大噪,杀庆等。馆伴使奥屯按出虎及画二人亦死。案明抄本及聚珍本画皆作昼。迟明,宰执趋赴馆视之,军士露刃诣马前请罪。宰相惶遽慰劳之,上因赦其罪,且加犒赏。京师细民皆欢呼踊跃,以为太平,识者知其祸不可解矣”。——卷十一,崔文印点校本,中华书局1983年,第124页。
《金史》卷一八《哀宗纪》:天兴元年“甲申(七月五日),飞虎军士申福、蔡元擅杀北使唐庆等三十余人于舘,诏贳其罪,和议遂绝” 。同书卷四四《兵志》:“此外招集义军,名曰忠义,要皆燕、赵亡命,虽获近用,终不可制。异时擅杀北使唐庆,以速金亡者即此曹也。”
另,[宋]宇文懋昭撰《大金国志》卷二六《义宗皇帝》:天兴元年(元太宗四年,1232)“春,天使复至,命帝黜尊号,拜诏称臣,去冠冕,髡剔发,为西京留守,交割京城。主难之。防城提辖张玉饵‘飞虎军’三百人为变” 。——《〈大金国志〉校证》,崔文印校证,中华书局,1986年,第363页。
唐庆曾于元太祖二十一年(1226)及次年两次使金,《元史》卷一《太祖纪》:十二月“是岁皇子窝阔台及察罕之师围金南京,遣唐庆责岁币于金”。次年“五月遣唐庆等使金”。——标点本,第24页。
《金史》卷一一一《纥石烈牙吾塔传》:正大“六年(1228)十月上命陕省以羊、酒及币赴庆阳犒北帅,为缓师计。北中亦遣唐庆等往来议和,寻遣斡骨栾为小使,径来行省”。此处将唐庆使金事置于正大六年(1228),有待研究。
八月,撒礼塔复征高丽,中矢卒[1]。金参政完颜思烈[2]、恒山公武仙[3]救南京,诸军与战,败之[4]。
[1] 四年(1232)“八月又遣撒里塔讨之,中流矢,军回”。——《国朝文类》卷四一《征伐·高丽》,四部丛刊本。
《元史》卷一五四《洪福源传》:“秋八月,太宗复遣撒礼塔将兵来讨,福源尽率所部合攻之,至王京处仁城,撒礼塔中流矢卒,其副帖哥引兵还,唯福源留屯。”——第3627—
3628页。
《元史》卷二〇八《高丽传》:“八月,复遣撒礼塔领兵讨之,至王京南,攻其处仁城,中流矢卒。别将铁哥以军还。其已降之人,令福源领之。”——第4609页。
《高丽史》世家卷二三:“撒礼塔攻处仁城,有一僧避兵在城中,射杀之。”又同书列传卷十七《金允侯传》:“金允侯,高宗时人,尝为僧,住白岘院。蒙古兵至,允侯避乱于处仁城。蒙古元帅撒礼塔来攻城,允侯射杀之。王嘉其功,授上将军,允侯让功于人,曰:‘当战时,吾无弓箭,岂敢虚受重赏。’固辞不受,乃改摄郎将。”
[朝鲜]权近等撰《朝鲜史略》卷八:“金允侯射杀蒙古元帅撒礼塔。允侯尝为僧,避乱处仁城。撒礼塔来攻,允侯射杀之。王嘉其功,授上将军,不受,乃改摄郎将。”
[2] 元好问《照了居士王彧》:“正大壬辰,参知政事宗室思烈行台洛阳,以知非(笔者按,知非为王彧字)有重名,力致之,使参议台事。城陷,不知所终。”——元好问辑《中州集》壬集卷九,四部丛刊景元刊本。
同氏《李讲议汾》:“既而恒山(笔者按,即武仙)与参知政事思烈相异同,颇谋自安,惧长源言论,欲除之。遁之泌阳,竟为所害。” ——《中州集》癸集卷九。
完颜思烈,《金史》中多见,《金史》有传,见一四九《内族思烈传》:“内族思烈,南阳郡王襄之子也。资性详雅,颇知书史,自五、六岁入宫,充奉御,甚见宠幸,世号曰自在奉御。当宣宗入承大统,胡沙虎跋扈,思烈尚在髫龀,尝涕泣跪抱帝膝致说曰:‘愿早诛权臣,以靖王室。’帝急顾左右,掩其口。自是,帝甚器重之。后由提点近侍局迁都点检。天兴元年,汴京被围,哀宗以思烈权参知政事,行省事于邓州。会武仙引兵入援,于是思烈率诸军发自汝州过密县,遇大元兵,不用武仙阻涧之策,遂败绩于京水,语在《武仙传》。”
[3] 《金史》有传,见卷一一八。有关此人,吉林大学张哲先生有硕士论文《金末汉人地主武装人物武仙研究》(导师程妮娜)专论。
[4] 《圣武亲征录》:“八月,金之参政完颜思烈、{桓}[恒]山公武仙将兵二十万会援南京,至郑州西,合战。”
《金史》卷一八《哀宗纪上》“丙午,参知政事完颜思烈、恒山公武仙、巩昌总帅完颜忽斜虎率诸将兵自汝州入援。以合喜为枢密使,将兵一万应之。命左丞李蹊劝谕出师,乃行。八月已酉朔,合喜屯杏花营,又益兵五千人,始进屯中牟故城。庚戍,发丁壮五千人运粮饷合喜军。辛亥,完颜思烈遇大元兵于京水,遂溃。”
九月,拖雷薨[1],帝还龙庭[2]。
[1] 《元史》卷一一五《睿宗传》:“五月,太宗不豫。六月,疾甚。拖雷祷于天地,请以身代之,又取巫觋祓除衅涤之水饮焉。居数日,太宗疾愈,拖雷从之北还,至阿剌合的思之地,遇疾而薨,寿四十有阙。”——标点本,页2887。《元朝秘史》与波斯史家拉施都丁亦有类似记载,《秘史》见节272,《史集》见第二卷,周良霄汉译本,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202页;余大钧、周建奇汉译本,商务印书馆,北京,1985年,第201—202页。
有关论文参见甄金《从拖雷之死谈起——对蒙古帝国早期内讧问题的探讨之一——质疑》,《内蒙师院学报》,1979年02期。
陆峻岭、何高济《从窝阔台到蒙哥的蒙古宫廷斗争》,《元史论丛》第一辑,中华书局,北京,1982年。
罗贤佑《从拖雷、贵由和阿里不哥的死因论大蒙古国的分裂》,《民族研究》,2006年04期。
[2] 阿布拉莫夫斯基推测,这里的龙庭指和林,见《太宗纪》德译,第142页注(61)。
有关此月及次月元高丽关系纪事,《元史》卷一五四《洪福源传》:“辛卯(1231)秋九月,太宗命将撒里答讨之,福源率先附州县之民,与撒礼塔并力攻未附者,又与阿儿禿等进至王京。高丽王乃遣其弟怀安公请降,遂置王京及州县达鲁花赤七十二人以镇之,师还。”按,撒里塔已于八月中矢卒,《洪福源传》此处当有误。
冬十一月,猎于纳兰赤剌温[1]之野。
[1] [清]李文田《元史地名考》(第24页):是年九月,帝还龙庭。则此地乃和林左近之地,纳兰河名,武宗大德十一年以纳兰不剌粮赈旁近饥民。《土土哈传》:“败海都之将于兰不剌纳兰之河上。”其他有赤剌温山也,此与《武宗纪》及《土土哈传》之纳兰皆隷和林旁近之地。按,《大元仓库记》(《广仓学宭丛书》甲类第二集,叶六):“纳兰不剌建仓宁夏府。”并不在漠北。
屠寄在《蒙兀儿史记》卷四《斡歌歹可汗本纪》中认为,此即和林之北之日月山。
阿布拉莫夫斯基提出此名可还原为蒙古语“太阳石”(=mong.naran čilao’un)“Sonnenstein”,并支持屠寄之意见,据《元史》卷七二《郊祀》上的记载,提出自蒙哥之后,此处应一直为施行祭天供奉之所(Von derzeitvon Möngke Qanan, sind dort Opferan den Нimmelvollzogen worden)。——《太宗纪》德译,第142页,注(62)。
十二月,如太祖行宫[1]。
[1] 有关此年其他政事,《大元仓库记》(叶九):辛卯(太宗三年,1231)、壬辰年(太宗四年,1232),元科州府每岁一石,添带一石,并附余者拨燕京。令陈家奴、田芝等用意催督,一时漕运毋违慢。其通州北起仓,据见可收物处,仰达鲁花赤管民官,备木植差夫,令和伯拨泥匠三人、木匠三人、铁匠一人速修,及差守仓夫役三人,半年交替。如失盗就令均(陪)[赔]。
五年癸巳春正月庚申[1],金主奔归德[2]。戊辰,金西面元帅崔立杀留守完颜奴申[3]、完颜习捏阿不[4],以南京降[5]。
[1] 《考异》卷八六:《金史》作己未,先一日。
[2] 《圣武亲征录》:“癸巳春正月二十二日,金主出南京,入归德。”
刘祁《归潜志》:“末帝既出,人情愈不安,日夜颙望东征之捷。俄闻北渡,前锋方交战,有功,取蒲城。进取卫州,白撒等望见北兵,遽劝上登舟船南渡,从官多攀从不及,死
于兵。而骁将徒单百家、高显、刘奕辈初不知上去,已而军士皆散没,上以余兵狼狈入归德,杜门,京民大恐,以为将不救矣。”——卷十一,崔文印点校本,中华书局,1983年,第126页。
[3] 《金史》卷一一五有传。
[4] 刘祁《归潜志》作“完颜习你阿不”或“完颜习你阿勃”,《金史》作“斜捻阿不”。详见下。阿布拉莫夫斯基注(67):《金史》无传。——《太宗纪》德译,第142页。
[5] 元好问《内翰王公墓表》: “明年春正月,京城西面元帅崔立劫杀宰相,送欵行营。”——《遗山集》卷一九,四部丛刊影明弘治本。同书《奉直赵君墓碣铭》:“壬辰,避乱京居。车驾东狩,崔立劫杀宰相,都人闻变求死无所。”——卷二二。同书《聂孝女墓志铭》:“壬辰之冬,车驾东狩。……明年正月二十有三日,崔立举兵反,杀二相。”——卷二五。
刘祁《归潜志》:“天兴改元,末帝东迁,留二执政居守,元吉预焉。崔立之变,二执政死,元吉亦被创甚。”——卷五,崔文印点校本,中华书局,1983年。
同书:“十二月,朝议以食尽无策,末帝亲出东征。丞相塞不、平章白撒、右丞完颜斡出、改工部尚书权参知政事李蹊、枢密院判官白华、近侍局副使李大节、左右司郎中完颜进德、张衮、总帅徒单百家、高显、刘奕皆从。上与太后、皇后、诸妃别,大恸,誓以不破敌不归。仪卫萧然,见者悲怆。留参知政事完颜奴申、枢密副使完颜习你阿不权行尚书省兼枢密事。以余兵守南京。……廿十有一日,忽闻执政召在京父老、士庶计事,诣都堂,余同麻革潜众中以听。二执政立都堂檐外,杨居仁诸首领官从焉。省掾元好问宣执政所下令告谕,且问诸父老便宜。完颜奴申拱立无语,独完颜习你阿勃按,上文作‘习你阿不’反复申谕:‘以国家至此,无可奈何,凡有可行,当共议。’且继以泣涕。诸愚叟或陈说细微,不足采。余语麻革,将出而白前事。革言:‘莫若以奏计密陈。子归草之,吾当共上也。’余以是退,将按,黄丕烈、施国祁校本作‘俟’明日同革献书。其夕,颇闻民间称有一西南崔都尉、药招抚者将起事。众皆曰:‘事急矣,安得无人?’余既归,夜草书,备论其事。迟明,怀以诣省庭,且邀革往。自断此事系完颜氏存灭,且以救余民,虽死亦无愧矣。是旦,大阴晦,俄雨作,余姑避民闾。忽闻军马声,市人奔走相传曰:‘达靼入城矣。’余知事已不及,遂急归。路闻非北兵,盖西南兵变,已围尚书省矣。
时崔立为西面都尉、权元帅,同其党韩铎等举兵。药安国者北方人,素骁勇,为先以进,横刀入尚书省,崔立继之。二执政见而大骇曰:‘汝辈有事当好议。’安国先杀习你阿不《金史》作斜捻阿不,次杀奴申。又杀左司郎中纳合德晖一作德浑,击右司郎中杨居仁、聂天骥,创甚。省掾皆四走,窜匿民家。
崔立既杀二人,提兵尚书省,号令众庶曰:‘吾为二执政闭门误众,将饿死,今杀之以救一城民。’且禁诸军士:‘取民一钱处死。’阖郡称快,以为有生路也。食时,忽阴雨开霁,日光烂然。立提兵入宫见太后,具陈其事,太后惶怖听命,拜立为左丞相、都元帅、寿国公。
立以太后令,释卫邸之囚,召卫王故太子梁王某按,梁王名从恪。监国,遂取卫族皆入宫。即遣使持二执政首诣军前纳降款。
明日,立坐都堂,召在京父老、僧道、百姓谕言,皆曰:‘谢丞相得生。’立又自诣军前投谒归附。命归,令在京士庶皆割发为北朝民。
初,立举事止三百人,杀二执政。当是时诸女直将帅四面握兵者甚多,皆束手听命,无一人出而与抗者。”——卷一一,第127-128页。
《圣武亲征录》:“金人崔立遂杀留守南京参政二人,开门诣速不台拔都(Sübe’hedei ba’atur)降。”
胡祗遹《德兴燕京太原人匠达噜噶齐王公神道碑》:“壬辰,苏布特(速不台/ Sübe’hedei)围南京城。守崔立遣使纳欵,情伪未可知。公与来使同往,立出降。”——《紫山大全集》卷一六,四库本。
《金史》卷一八《哀宗纪下》:“戊辰,安平都尉、京城西面元帅崔立与其党韩铎、药安国等举兵为乱,杀参知政事完颜奴申、枢密副使完颜斜捻阿不,勒兵入见太后,传令召卫王子从恪为梁王,监国。即自为太师、军马都元帅、尚书令,寻自称左丞相、都元帅、尚书令、郑王。弟倚平章政事,侃殿前都点检,其党孛朮鲁哥御史中丞,韩铎副元帅兼知开封府,折希颜、药安国、张军奴、完颜合答并元帅,师肃左右司郎中,贾良兵部郎中兼右司都事,又署工部尚书温迪罕二十、吏部侍郎刘仲周并为参知政事,宣徽使奥屯舜卿为尚书左丞,户部侍郎张正伦为尚书右丞,左右司都事张节为左右司郎中,尚书省掾元好问为左右司员外郎,都转运知事王天祺、怀州同知康瑭并为左右司都事。开封判官李禹翼弃官去。户部主事郑著召不起。是日,右副点检温敦阿里,左右怀员外郎聂天骥,御史大夫裴满阿虎带,谏议大夫、左右司郎中乌古孙奴申,左副点检完颜阿散,奉御忙哥,讲议蒲察琦并死之。遂送款大元军前。癸酉,大元将碎不(按,速不台/Sübe’hedei)进兵汴京。”
《金史》卷一一五《崔立传》:“崔立,将陵人,少贫无行,尝为寺僧,负钹鼓,乘兵乱从上党公开,为都统提控,积阶遥领太原知府。正大初,求入仕,为选曹所驳,每以不至三品为恨。围城中,授安平都尉。天兴元年冬十二月,上亲出师,授西面元帅。性淫姣,常思乱,以快其欲。药安国者,管州人,年二十余,有勇力,尝为岚州招抚使,以罪击开封狱。既出,贫无以为食立,将为变,潜结纳之。安国健啖,日饱之以鱼,遂与之谋。先以家置西城上,事不胜,则挈以逃。日与都尉扬善入省中,候动静。布置已定,召善以早食杀之。二年正月,遂帅甲卒二百,撞省门而入。二相闻变,趋出,立拔剑曰:‘京城危困,二公欲如何处之?’二相曰:‘事当好议之。’立不顾,麾其党张信之、孛朮鲁长哥出省,二相遂遇害。驰往东华门,道遇点检温屯阿里,见其衷甲,杀之。即谕百姓曰:‘吾为二相闭门无谋,今杀之,为汝一城生灵请命。’众皆称快。是日,御史大夫裴满阿忽带、谏议大夫左右司郎中乌古孙奴申、左副点检完颜阿散、奉御忙哥、讲议蒲察琦、户部尚书完颜珠颗皆死。立还省中,集百官议所立。立曰:‘卫绍王太子从恪,其妹公主在北兵中,可立之。’乃遣其党韩铎,以太后命往召。从恪须臾入。以太后诰命梁王监国,百官拜舞山呼,从恪受之。遂遣送二相所佩虎符,诣速不纳款。”
王国维《耶律文正公年谱》(《王国维遗书》第十一册,上海古籍书店,1983年版。第14页)注:五年癸巳春正月庚申,金主奔归德。戊辰,金西面元帅崔立杀留守完颜奴申、完颜习捏阿不,以南京降。蒙古制,凡敌人拒命,矢石一发,则杀无赦。汴京垂陷,首将速不台遣人来报,且言此城向相抗日久,多杀伤士卒,意欲尽屠之。公驰入奏曰:“将士暴露数十年,所争者地土人民耳。得地无民,将焉用之?”上疑而未决。复奏曰:“凡弓矢甲仗金玉等匠及官民富贵之家皆聚此城中,杀之则一无所得,是徒劳也。”上始然之。诏除完颜氏一族外,余皆原免。时避并在汴者户一百四十七万,仍奏选工匠儒释道医卜之流散居
河北,官为给赡。其后攻取淮汉诸城,因为定例。(《神道碑》)
德国学者黑尼士曾发表过有关崔立叛乱的论著《有关叛军将领崔立的纪念碑》(Нaenisch, Die Ehreninschrift für Rebellengeneral Ts’ui-Lih, Berlin, 1944),见《太宗纪》德译,第142页注(65)。国内有关研究可参见狄宝兴《元遗山在崔立碑事件中的动机及其评价》,《山西大学师范学院学报》,1994年02期;孙智勇《金末崔立叛乱原因浅析》,《太原城市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3年01期。
二月,幸铁列都[1]之地。诏诸王议伐万奴[2],遂命皇子贵由[3]及诸王按赤带[4]将左翼军[5]讨之。
[1] [清]李文田《元史地名考》(第24页):《太祖纪》:“帝复伐薛彻、大丑,追至帖烈徒之隘。”即其地也。故泰赤乌部盖在大漠之偏东,盖万奴故女真地也。《北边备对》:“回纥部,其先匈奴也,后呼铁勒。” 按铁列与帖烈皆铁勒之声转。又按,铁勒亦有两部。
同氏《元秘史注》:“独撒察别乞泰岀两人罄身走至迭列秃(Tele’etü)口子行被太祖拏住。《本纪》曰:帝遣六十人征兵于辥彻别乞,薛彻别乞以旧怨故杀十人,去五十人衣。帝怒,因帅兵逾沙碛,攻之,杀虏其部众,唯薛彻太丑仅免。越数月,帝复伐薛彻太丑,追至帖烈徒(Tele’etü)之隘,灭之。按,帖烈徒(Tele’etü)即迭烈秃(Tele’etü)对音,然迭烈禿(Tele’etü)即‘口子’之义。后文王罕被乃蛮将帖列格禿百姓掳去,与此并非一地。并称帖列格秃为口子,足见帖列格秃与迭列秃即口子。《太宗纪》:五年,幸铁列都之地,亦即此口子矣。” ——清光绪二十二年渐西村舍本。
阿布拉莫夫斯基注(69):蒙古语“帖列禿”=“帖列禿 阿马撒剌”,即《秘史》第136节之帖列禿山口,并参见伯希和《〈圣武亲征录〉注》,页262—263(Mong. “telētü”=Telegetüamsar, die Schlucht Teletü. (GG §136). SieheauchPELLIOT, campagnes, S. 262—263)——《太宗纪》德译,第142页。
按,蒙语telege,意为“车”,telegetü,此言“有车地”。
[2] 蒲鲜万奴。阿布拉莫夫斯基注(70)有此人简介,见《太宗纪》德译,第142页。
[3] 周良霄译注《成吉思汗的继承者——〈史集〉第二卷》(天津古籍出版社 1992年8月版,第27页):长子贵由Güyük 彼之禹儿惕在称为——地之霍博Qobaq之地、叶密立Emil或——。[原注(即波义耳的注释):贵由之封地位霍博(今新疆北部之和布克赛尔)与叶密立(今伊敏)之间。后一名似为QWM SNKR之讹,当即横相乙儿Qum-Sengir。按:俄译本此句作:“彼之禹儿惕在称为Бepи-Maнгpaκ之地的KyMaκ、ИMилб与Ypшayp”。叶密立,名从《元史·宪宗纪》,在汉文史料中又作也迷里(《元史·速不台传》)、叶密立(《耶耶律希亮传》)、也迷失(《西北地附录》)和业瞒(《西使记》)。加宾尼作Omyl,谓其为窝阔台所筑之新城。然考之朮外尼,此城乃耶律大石西征中所创筑(《世界征服者史》第一卷,第355页)。霍博,名从《元史·太宗纪》,有火孛(《耶律希亮传》)、虎八(《亲征录》)诸译。《元史·速不台传》有也迷里霍只部,无疑亦即其地。《耶律希亮传》云:叶迷里“乃定宗潜邸汤沐之邑”。]
[4] 成吉思汗弟合赤温之子,又作按只带、按只吉歹、阿勒赤歹(El☒itei, El☒igidei,alčidai)等。关于此人,可见韩百诗、伯希和:《〈元史〉卷一○七〈宗室世系表〉译注》,来
顿,1945年(Louis Нambis, Les chapitre cVII du Yuan che,avec desnotes supplementairesParPaulPelliot, Leiden, 1945),见29页。
[5] 阿布拉莫夫斯基注(73):左翼同意为“东部”(Linker Flügel ist gleichbedeutend m it “östlichem Gebiet”)。——《太宗纪》德译,第143页。
夏四月,速不台进至青城[1],崔立[2]以金太后王氏、后徒单氏及(荆)〔梁〕王从恪[3]、(梁)〔荆〕王守纯等至军中[4],速不台遣送行在,遂入南京[5]。
[1] [清]李文田《元史地名考》:青城者,汴梁城外之地。——第24页。
屠寄《蒙兀儿史记》卷四《斡歌歹可汗本纪》:“在南薰门外,本宋祭天斋宫所在。别有北青门,在封邱门外”。——叶八。
阿布拉莫夫斯基注(74)沿袭屠寄:地在南京(开封)之南薰门前。早先宋在此祭天(Der Ort lagvor demnan-hsün-Torvonnan-ching (K’ai-feng). Die Sungvollzog dort früher ihre Нimmelsopfer)——《太宗纪》德译,第143页。
[2] 崔立后为降宋金将李伯渊所杀。据[元]刘一清《钱塘遗事》“三京之役”条记:“宝庆乙酉(按,二年,1225。崔立被杀事在1234年,此处纪年有误),赵葵、赵范、全子才奏:‘因降人谷用安之言,欲乘时抚定中原,建守河据关之议,以闻于朝。’乃命起范开阃于光黄之间。六月,全子才合淮南兵万余人赴汴,以十二日离合肥,七月二日抵东京,距城二十里,驻兵五日,整兵入城。行省李伯渊先期以文书来降,愿与谷用安、范用吉结约,乃杀所立崔立,率父老来降。”——卷二,清光绪刻武林掌故丛编本。
此事有两种史料记载较详,一为《元文类》卷六九中所收曹居一《李伯渊奇节传》:
“居一北渡河,常欲作李伯渊传,既少暇,且未详其事,窃有待焉。岁戊申(按,元定宗贵由三年,1248)夏,卧病相州。俄故人僧洞然过客舍,因语及曏壬辰(按,元太宗四年,1232)之变之后之事,始悉伯渊诛崔立之所自,盖惠安长老恩公有力焉。初,京城荒残,恩公徙居皇建院。一日(莫)[暮]夜,侍者入告曰:‘有戎衣腰金符者,醉堕马门外,从者不能起,或致寇,吾得无累乎?’令视之,识者谓:‘总帅李伯渊也。’使扶诣方丈憇。俟其醒,语之曰:‘当此大丧乱,公何心嗜酒如是?生为男子,与其徒沉溺于乱世,曷若立身后不朽之荣名哉?’伯渊矍然,若有契于衷者见于色。黎眀,乃召同志黄慖元帅者,相与拜恩而师焉。居无何,往诣恩,屏人而言曰:‘崔立狂竖,乘国家倾危,天子播越,辄敢叛乱乃尔。吾欲诛之久矣。师谓男子身后不朽之荣名,其在是耶?’恩拒不可,曰:‘尔何遽出此速祸语?殆非老僧所敢闻者。’伯渊泣且誓,恩察之诚也,乃握手叹曰:‘吾情亦不能匿矣。公知老僧故不去此祸乱之地否?吾天地间一闲人,自相州遭遇,宣宗荷国厚恩二十余年矣,图报万一,此何爱焉!在吾教中有大报恩七篇,是固当为者,但患力微援寡,事不济耳。今幸闻公举非常之事,树万世之名,使老僧朝见而夕死无憾,合爪加额曰惟以必中为公贺。’未几,适驿使有相困者,伯渊因之入见崔立,绐曰:‘丞相避扰不岀,则今日之事有大不安者。’立欲岀,心动乘堕,辄欲回。伯渊厉声曰:‘我辈兵家子,偶堕马又何怪焉?’因强其行,至故英邸之西通衢中。忽有人突出抗言,曰:‘屈事,愿丞相与我作主!’且呼且前,伍伯诃不止,直诣立马首,挽其鞚。时伯渊骖右,即拔刃抱而刺之,洞贯至自中其左掌,与之俱坠马。崔尚能语,曰:‘反为贼奴所先。’随毙。伯渊暨黄慖等五人,实共其事,乃大
呼曰:‘所诛者,此逆贼耳。他人无与焉!’稍稍鼠窜,蜂逝帖如也。遂磔崔立之尸,祭于承天门下,一军哀号,声动天地。翼日,奔宋。恩公在其行,时甲午(按,元太宗六年,1234)秋七月也。呜呼!金之亡也,以忠义闻者,不为不多。至于表表独见于后世者,得三人焉。”
二为《金史》卷一一五《崔立传》:“李伯渊者,宝坻人,本安平都尉司千户,美姿容,深沉有谋,每愤立不道,欲仗义杀之。李贱奴者,燕人,尝以军功遥领京兆府判,壬辰冬,车驾东狩,以都尉权东面元帅。立初反,以贱奴旧与敌体,颇貌敬之。数月之后,势已固,遂视贱奴如部曲然。贱奴积不能平,数出怨言,至是与琦等合。三年六月甲午,传近境有宋军,伯渊等阳与立谋备御之策。翌日晚,伯渊等烧外封丘门以警动立。是夜,立殊不安,一夕百卧起。比明,伯渊等身来约立视火,立从苑秀、折希颜数骑往,谕京城民十五以上、七十以下男子皆诣太庙街点集。既还,行及梳行街,伯渊欲送立还二王府,立辞数四,伯渊必欲亲送,立不疑,仓卒中就马上抱立。立顾曰:“汝欲杀我耶?”伯渊曰:“杀汝何伤。”即出匕首横刺之,洞而中其手之抱立处,再刺之,立坠马死。伏兵起,元帅黄掴三合杀苑秀。折希颜后至不知,见立坠马,谓与人斗,欲前解之,随为军士所斫,被创走梁门外,追斩之。伯渊系立尸马尾,至内前号于众曰:“立杀害劫夺,烝淫暴虐,大逆不道,古今无有,当杀之不?”万口齐应曰:“寸斩之未称也。”乃枭立首,望承天门祭哀宗。伯渊以下军民皆恸,或剖其心生啖之。以三尸挂阙前槐树上,树忽拔,人谓树有灵,亦厌其为所污。已而有告立匿宫中珍玩,遂籍其家,以其妻王花儿赐丞相镇海帐下士。”
[3] 标点本校勘记[四]:(荆)〔梁〕王从恪, 据金史卷九三卫绍王子传改。考异已校。——第41页。
[4] 标点本校勘记[五]:(梁)〔荆〕王守纯,据金史卷九三宣宗诸子传改。考异已校。——第41页。
阿布拉莫夫斯基注(75):《金史》卷十八记载,据说两位元亲王及金主从属男子均被杀,仅二皇后被送往哈剌和林(cS 18, 6v berichet, dass die beidenPrinzen undalleanderen männlichenangehörigen des Нerrscherhauses der chin getötet worden seien,nur die beiden Kaiserinen seiennach Qaraqorum geschickt worden)。——《太宗纪》德译,第143页。
[5] 关于此月元与高丽关系,《元高丽纪事》(叶四—五)记:“五年癸巳四月二十四日,谕王悔过来朝。诏曰:‘汝表文奏告事理具悉,率谄妄推托之辞,彼此有何难知。汝若委无谄妄,可来朝觐。自昔时讨平丹贼,杀讫札剌之后,未尝遣一人赴阙。尔等曾无遵依大国法度施行,此汝之罪一也。赉擎长生天之训言省谕,去者使命,尔等辄敢射回,此汝之罪二也。尔等又将著古欤谋害,推称万奴民户杀坏。若获元告人,此事可明。如委系万奴将尔国排陷,朕命汝征讨万奴,为何逗留不进,此汝之罪三也。命汝进军,仍令汝弼入朝。如此明谕,尔敢抗拒不朝,窜诸海岛,此汝之罪四也。又令汝等民户俱集见数,尔称若出城计数,人民惧杀,逃入海中,尔等尝与天兵协力征讨,将尔等民户诱说出城,推称计数,妄行诛杀,辄敢如此妄奏,此汝之罪五也。除此罪之外,尔等谄妄过恶,岂可胜言。长生天之训言省谕去时,不为听从,欲行战争。仰赖上天之力,攻破城邑,将执迷不降之人,歼勦者有之。或伏降出力之人,虽匹夫匹妇,未尝妄杀。尔之境内,西京金信孝等所管十数城应有人民,依奉朝命,计点见数,悉令安业住坐。除外,普天下应有民人,何啻亿万,悉皆输贡,按堵如故。尔或未知信,可遣使前来,朕将领尔观之。朕惟天之圣训省谕之后,将
尔等悯恤思济。尔等曾未之悟,窜入水中,引惹争战之语,良以此耳,止托天之威力,克取尔国,固亦小端。尔等或存或亡,初无利害。朕惟上天圣训省谕之后,欲令尔等输贡服力。今则汝若不为出海来朝,苟避一时之难,我朝何如。上天其监之战,以尔拒命不服,申命大军,数路进发。以尔反覆二心,惜乎服力之兆民,妄遭杀戮。斯民垂死之际,莫不憾恨,归咎于汝,底于灭亡也。汝欲六师还旆,汝可躬领军民,进讨万奴勾当。尔或坚执不朝,又不躬行征讨,自陷罪恶死亡之地也,止缘万奴勾当及汝谄妄之故。世间真伪,朕胸中了然矣。尔与黎民灼然可见之事,何难之知。数皆何丧,定不可逃。以致尔等自贻其咎,自抵灭亡耳。’”
六月,金主奔蔡,塔察儿率师围之[1]。诏以孔子五十一世孙元(楷)〔措〕袭封衍圣公[2]。
[1] 《圣武亲征录》:“四月,速不台拔都至青城。崔立又将金主母后、太子二人暨诸族人来献,遂入南京。六月,金主出归德府,入蔡[州],塔察儿火儿赤统大军围守。”
阿布拉莫夫斯基注(77):塔察儿,他是帖木哥斡赤斤之侄,见韩百诗:《〈元史〉卷一百七〈宗室世系表〉译注》,表13;卷一一九Tačar. Er was(按,此处误为英文,应为war) ein Enkelvon Temüge očigin (Нambis, chapitre cVII, Rab. 13). Biogr. 119, 15v—17r)。——《太宗纪》德译,第143页。
这里塔察儿所戴名号为“火儿赤”(qorči),在蒙古语中意为“箭桶士”,属怯薛执事之一种,其地位与斡赤斤之侄的尊贵身份不符。阿布拉莫夫斯基虽然提及《元史》卷一一九《塔察儿传》,但显然并没有读过此传。该卷所有传主均非宗室。《塔察儿传》传中写明,这位参与灭金之战的塔察儿,为成吉思汗“四杰”之一博儿忽之从孙。《黑鞑事略》所记“曩与金虏交兵关河之间”,与速不、忒没并列的将领“塔察儿”,即此人。他虽然与斡赤斤之侄同名,但非同一人。
[2] 标点本校勘记[六]:元(楷)〔措〕,据本书卷一四六《耶律楚材传》、卷一五八《姚枢传》改。《类编》已校。——第41页。
阿布拉莫夫斯基注(78):据《金史》卷一百五,此处所言即孔元措,他在1192年即从金获此头衔(Es handelt sich um K’ung Yüan-ts’uo, der bereits im Jahr 1192von den Chin diesen Titel einhalten hatte(cS 105, 5v))。——《太宗纪》德译,第143页。
[金]孔元措辑《孔氏祖庭广记》所记较《金史》早一年:“五十一代元措,字梦得,揔之长子,年十一。章宗明昌二年(1191)四月,补文林郎,袭封衍圣公,管勾祀事,特旨令视四品。其诰云:‘圣谟之大,遗范百王。德祚所传,垂光千祀。盖立道以经世宜,承家之有人。文宣公五十一代孙元措,秀阜衍祥,清洙流润,芝兰异禀,蔚为宗党之英。诗礼旧闻,蚤服父兄之训语,年虽妙论,德已成肆。疏世爵之封,仍换身章之数。非独增华于尔族,固将振耀于斯文,勉嗣前修,用光新命。”——卷一,四部丛刊续编景蒙古本。
宋子贞《耶律楚材神道碑》:“初,汴京未下,奏遣使入城,索取孔子五十一代孙,袭封衍圣公元措。令收拾散亡礼乐人等,及取名儒梁陟等数辈。”——《元文类》卷五七,四部丛刊本。
王恽《立袭封衍圣公事状》:“国朝自壬辰年间钦奉圣旨,于南京取到五十一代孙孔元措,赴阙令袭封于鲁。”——《秋涧集》卷八五,四部丛刊景明弘治十一年马龙、金舜臣
刻本。
秋八月,猎于兀必思[1]地。以阿同葛等充宣差勘事官,括中州户,得户七十三万余[2]。
[1] 屠寄《蒙兀儿史记》卷四《斡歌歹可汗本纪》:“今地未详,当距和林不远”。——叶八。
阿布拉莫夫斯基注(79):此地无法确指(Der Ort konntenichtnäher lokalisiert werden)——《太宗纪》德译,第143页。
《辽史》卷二《太祖纪》载天赞三年九月西征,“次古回鹘城,勒石纪功”,又“砻辟遏可汗故碑,以契丹、突厥、汉字纪其功。”同月,“破胡母思山诸蕃部”。辽末,耶律大石在漠北会十八部王众,其中有“忽母思”部。虞集《句容郡王世绩碑》记,钦察大将土土哈之子创兀儿帅师至“和林兀卑思之山”,周良霄以为兀卑思即“胡母思”——见氏撰《关于西辽史的几个问题》,《中华文史论丛》,1981年,第3辑,第246页)。这些文献提到的胡母思、忽母思、兀卑思,在古鹘城,即和林城附年,即此“兀必思”。波斯史家拉施都丁在其《史集·部族志》中记札剌亦儿人的十个部落时说,其中一部名Kūmsāūt,或可还原为Qumsa’ut,其单数形式或为Qumus(参见刘迎胜:《〈史集·部族志·札剌亦儿传〉研究》,刊于《蒙古史研究》,第四辑,中国蒙古史学会编,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93年;同氏《辽与漠北诸部族——胡母思山蕃与阻卜》,《欧亚学刊》第3辑,2002年),应即此胡母思/忽母思/兀卑思/兀必思。
[2] 屠寄《蒙兀儿史记》卷四《斡歌歹可汗本纪》:“《亲征录》作按脱,即阿同葛异译。”——叶八。
阿布拉莫夫斯基注(80):阿同葛无传。—这个华北被征服地区的人口统计数在1238年更为详尽,见页131(a-t’ung-ko hat keine Biographie.—Diesezählung der Bevölkerung der eroberten Geboetvonnord-China wurde im Jahre 1238vervollständigt. Siehe S. 131》——《太宗纪》德译,第143页。
九月,擒万奴[1]。
[1] 有关次月元与高丽关系,《元高丽纪事》(叶五):五年癸巳“十月,复遣兵,攻陷已附西京等处降民,亦劫洪福源家。时福源以前为高丽所侵,后为女真契丹等贼来攻。福源上言讫,领降民,迁居辽阳等处” 。
冬十一月,宋遣荆鄂都统孟珙以兵粮来助[1]。
[1] 《圣武亲征录》:“十一月,南宋遣太尉孟珙等领兵五万,运粮三十万石,至蔡来助,分兵南面攻之。”
屠寄《蒙兀儿史记》卷四《斡歌歹可汗本纪》:“按,太尉系珙加官,今依《宋史》本传。”屠寄改为“鄂州江陵府副都统孟珙。”——叶八。
阿布拉莫夫斯基注(82):《宋史》卷一一二传记所言时间引人注意(Biographie in SS
412, 1r—14r; S. 6r-v behandeln den hier interessieren denzeitraum)——《太宗纪》德译,第143页。
十二月,诸军与宋兵合攻蔡,败武仙[1]于息州。金人以海、沂、莱、潍等州降[2]。
[1] 阿布拉莫夫斯基注(83):参见《金史》卷一八二。——《太宗纪》德译,第143页。
[2] 《圣武亲征录》:“金人举沂、莱、海、潍等州来降。”
是冬,帝至阿鲁兀忽可吾行宫[1]。大风霾七昼夜。敕修孔子庙及浑天仪[2]。
[1] [清]李文田《元史地名考》(第24页):世祖至元七年纪:“赈兀鲁吾民户钞。”疑即其地。按,此议毫无根据。
屠寄《蒙兀儿史记》卷四《斡歌歹可汗本纪》:“旧《纪》作阿鲁兀忽可吾行宫,译音差误不备。阿鲁,当作斡儿洹;兀忽可吾,当作兀忽可纳浯儿。张德辉《纪行》曰:自浑独剌水西北行五驿,过大泽,周回六、七十里,水极澄彻,北语‘吾误竭脑儿’。自泊之南而西,分道入和林。按,吾误竭,即兀忽可之异译,义谓大;脑儿,即纳浯儿之异文,义谓泊。今赛因诺颜部鄂尔浑河上游古崖,邹译图有乌格淖尔。胡刻图作额归泊者,即此兀忽可纳浯儿。德辉以汉语译言大泽是也。” ——叶八。
阿布拉莫夫斯基注(85):似乎此处涉及位于鄂尔浑河与塔密儿河汇流处附近之乌格湖之地(Es scheint sich hier um das Gebiet des Ugej-Seeszu handeln, der in dernähe deszusammen fl ussesvon Tam ir und Orkhon liegt),并在此后引述上举屠寄之意见。——《太宗纪》德译,第143页。
[2] 阿布拉莫夫斯基注(86):在燕京。——《太宗纪》德译,第143页。
有关此年政事,《大元马政记》记:“太宗皇帝五年癸巳,圣旨:谕田镇海、猪哥、咸得不、刘黑马、胡土花,小通事合住、绵厕哥、不速、孛伯,百户阿散纳、麻合马、忽赛因、贾熊、郭运成并官员等,及该不尽,应据斡鲁朵商贩回回人等,若曰,其家有马牛羊及一百者,取牝马、牝牛、牝羊一头入官;牝马、牝牛、牝羊及十头,则亦取牝马、牝牛、牝羊一头入官。若有隐漏者,尽行没官。如各处收拾放牧,开具何人头匹,备细花名数目闻奏,听后支拨,不得违错。如违慢者,人岂不断罪。外据张德常、郭运成、蒙古,并山西东西两处燕京路。但有迭百头口官员等,一体施行。准此。”——叶二九。
《大元仓库记》:“太宗皇帝五年癸巳诏:前令随处官司就差元设站夫修治运粮河道,可疾遣站夫自备粮物速为修治,工军放还专委。运粮河所属各州县长提举河道,差能干官吏及约粮差夫以时巡护,不致贼盗滋生。若遇失盗,不以官私之物,并勒提举河道及巡护者赔偿。如元赃不获,依条断罪。如有河岸缺坏,不分昼夜多差丁夫并力修筑,违慢迟滞并以违制论。仍仰沿河以南州府达鲁花赤等官,各于濒岸州城置立河仓,差官收纳每岁税石,旋依限次运赴通州仓,其立仓处差去人取。”——叶九。
六年甲午春正月,金主传位于宗室子承麟[1],遂自经而焚。城拔,获承麟,杀之。宋兵取金主余骨以归。金亡[2]。
[1] 阿布拉莫夫斯基注(87):无有关此人进一步信息。参见奥勒布里希特《关于两个帝国的衰落》(p. Olbricht,zum Untergangzweier Reiche, W iesbaden, 1969),页10,注16及18;Franke奥托·福兰阁《中华帝国史》第四卷,页290;第五卷,页157(Otto Franke, Geschichte des chinesischen Reiches, Bd. IV, Berlin, 1952, S.290,v,S.157)。——《太宗纪》德译,第143页。
[2] 《圣武亲征录》:“甲午春,正月十日,塔察儿火儿赤急攻蔡,城危逼,金主传位于族人承麟,遂缢焚而死。我军入蔡,获承麟,杀之。金主遗骸,南人争取而逃,平金之事如此。”
《大金国志》卷二六:正月“初十日,摘三面精锐军备西城。未明,大军果复来,方大战,南面宋兵万余已薄城矣。国主知城必破,乃诏大臣逊位于东面总帅(丞)[承]麟。(丞)[承]麟西向固让,金主自持符玺授之,(丞)[承]麟伏地拜泣,不敢受。国主曰:‘朕所[以]付卿者,岂得已哉?以朕肌肥,不便鞍马,城陷之后,驰突必难。顾卿平昔以趫疾闻,且有将略可称,万一得免,使国祚不绝,此朕志也。’因起授符玺,(丞)[承]麟惶恐跪受,帝乃退” 。——[宋]宇文懋昭撰,崔文印校证《〈大金国志〉校证》,中华书局,1986年,第369页。并见《金史》卷一八《哀宗纪》下。
是春,会诸王,宴射于斡儿寒河[1]。
[1] 今蒙古国鄂尔浑(Orqan)河。
夏五月,帝在达兰达葩[1]之地,大会诸王百僚[2],谕条令曰:“凡当会不赴而私宴者,斩。诸出入宫禁,各有从者,男女止以十人为朋,出入毋得相杂。军中凡十人置甲长,听其指挥,专擅者论罪。其甲长以事来宫中,即置权摄一人、甲外一人,二人不得擅自往来,违者罪之。诸公事非当言而言者,拳其耳;再犯,笞;三犯,杖;四犯,论死。诸千户越万户前行者,随以木镞射之。百户、甲长、诸军有犯,其罪同。不遵此法者,斥罢。今后来会诸军,甲内数不足,于近翼抽(捕)〔补〕足之[3]。诸人或居室,或在军,毋敢喧呼。凡来会,用善马五十匹为一羁,守者五人,饲羸马三人,守乞烈思[4]三人。但盗马一二者,即论死。诸人马不应绊于乞烈思内者,辄没与畜虎豹人。诸妇人制质孙燕服不如法者,及妒者,乘以骣牛徇部中,论罪,即聚财为更娶。”[5]
[1] [清]李文田《元史地名考》(第24页):达葩者,山岭之名,此山名达兰,故曰达兰达葩,《醉隐集》:“达兰河,河名也,在和林北百余里”云云。据此则达阑山乃达兰河所岀,即本年所住之荅阑荅八思之地。《定宗纪》:“皇后临朝,会诸王百官于荅阑荅八思之地。”即此达兰达思之对音。
关于《圣武亲征录》中的“答兰答八思”,王国维提出:“《元史·太宗纪》作达兰达葩,《双溪醉隐集》五《达兰河》诗注云:‘河名也。在和林北百余里。’疑此是也。”——《圣武亲征录校注》,第84页。
屠寄释曰:“地名见《亲征录》,义谓‘平野之山梁’。旧《纪》作达兰达葩,释地详下八里里荅兰荅八思下。”——《蒙兀儿史记》卷四《斡歌歹可汗本纪》,叶九。
周良霄《〈元史〉点校献疑》(载于《内陆亚洲历史文化研究——韩儒林先生纪念文集》):答阑答巴思名屡见于《元史》,其义为七十山口。
阿布拉莫夫斯基注(89):达兰达葩,“七十山口”。参见伯希和《〈圣武亲征录〉译注》,页244;及《哈剌和林注》(Notes on Karakorum, Ja, 206,372—375), 页313(Dalan daba, die“ SiebzigPässe”. SiehePelliot, campagnes, S.244 undnotes, S. 313)。——《太宗纪》德译,第143页。
[2] 《圣武亲征录》:“是年夏五月,于答兰答八始建行宫,大会诸王百官,宣布宪章。”
[3] 标点本校勘记[七]:抽(捕)〔补〕足之,从殿本改。——第41页。
[4] 阿布拉莫夫斯基注(93):乞烈思为西部蒙古语kirya“栓马处”之复数kiryas之汉语音译。参见德福《新波斯语中的蒙古语与突厥语因素》,卷一,页464,第330条(ch’i-lieh-szu乞烈思 ist die chinesische Wiebergabevon westmongolisch“ kiryas”,Pl.von kirya =Sattelplatz. Siehe G. Doerfer, Türkische und Mongolische Elemente imneuperischen I,S. 464; sub. 330)。——《太宗纪》德译,第144页。
[5] 有关此月元与高丽关系,《元高丽纪事》(叶五—六)记:六年甲午五月一日,赐高丽降人麟州探问神骑都领洪福源金牌,俾领元降民户于东京居住。初,福源率民千五百户来降,且有请曰,若大事底于成,天子当念臣愚忠,其或败事愿就地弗敢辞。至是有旨,以元降民户令福源管领。复谕之曰,尔能戮力效职,则后降者皆令尔领之。是日,遣使持玺书,谕高丽国未降人民节该,若将高丽国王王及元谋构起战争人员,执缚来朝者,与先降洪福源,一同优加恩恤任用。若天兵围守之后,拒我者死,降我者生,其降民悉令洪福源统摄。
秋七月,以胡土虎[1]那颜为中州断事官。遣达海绀卜[2]征蜀。
[1] 《圣武亲征录》:“又遣忽{相}[都]忽主治汉民,别遣塔海绀孛征蜀。”
宋子贞《耶律楚材神道碑》所记“甲午(1234),诏括户口,以大臣忽睹虎领之。国初,方事进取,所降下者,因以与之。自一社一民,各有所主,不相统属。至是始隶州县。朝臣共欲以丁为户,公独以为不可。皆曰:‘我朝及西域诸国,莫不以丁为户,岂可舍大朝之法而从亡国政邪?’公曰:‘自古有中原者,未尝以丁为户。若果行之,可输一年之赋,随即逃散矣。’卒从公议。时诸王大臣及诸将校所得驱口,往往寄留诸郡,几居天下之半。公因奏括户口,皆籍为编民”,即为此事之背景。
王国维将《圣武亲征录》中的对应史文订正为:“遣曲出、忽都都伐宋。忽都忽籍到汉民一百一十一万有奇。”并提出:“《太宗纪》作‘胡土虎’,乃误以忽都忽当之。”——《圣武亲征录校注》,第85页。
周良霄译注《成吉思汗的继承者——〈史集〉第二卷》(天津古籍出版社 1992年,第67页):周按:胡土虎以太宗六年七月充中州断事官,故《铁蔑赤传》称忽都行省,与八年主括中州户口之大臣忽睹虎(《元文类》卷五七,宋子贞《中书令耶律公神道碑》)同为一人无疑。关于此人推测甚多,或以为即成吉思汗之弟失吉忽禿忽(Šigi Qutuqu)(王国
维《黑鞑事略》注),敬山则又以七年与曲出伐宋之胡土虎当蒙哥次子忽都禿,而充中州断事官者则为忽禿忽。
[2] 《本证》卷三十七证名一:塔海绀不、河渠志二三白渠。塔海甘卜、拜延八都鲁传。塔海绀卜、探马赤、帖木儿不花、塔海帖木儿、耶律禿花、李守贤传。(点校者按,卷一五〇李守贤传作塔海绀布)速不台、郝和尚拔都、刘亨安传止称塔海。答海绀卜、忽都传。答海绀卜、刘黑马传。
是秋,帝在八里里答阑答八思[1]之地,议自将伐宋[2],国王查老温[3]请行,遂遣之。
[1] 《本证》卷四九证名一三:答兰答八思,(宪)[定]宗纪首。(据元史卷二定宗纪改。宪宗纪首不见此名。)答兰答八,察罕传。
[清]李文田《元史地名考》:《定宗纪》:“太宗崩,皇后临朝,会诸王百官于荅阑荅八思之地,议立帝。”《察罕传》:“太宗即位,从略河南,北还清水荅阑荅八思之地。”则八里里者,八剌河,汉语乃清水二字也,西番语谓河为里,太祖初起于八剌忽,又驻军于荅阑版朱思之野,此云八里里当即八剌合黑河,番语以河为里也,荅阑荅八思即荅阑版朱思之异文,译云有缓急,故每有异字耳。——第24页。
屠寄《蒙兀儿史记》卷四《斡歌歹可汗纪》:“旧《史》《察罕传》:太宗即位,从略河南,北道清水荅兰荅八思之地。按清水即八里里之译名,即此八里里荅兰荅八思之地。耶律铸《双溪醉饮集·荅兰河诗》注云:达兰河,在和林北百余里。按,达兰河,即清水,亦即八里里。所谓荅兰荅八思,即在此达兰河之濒无疑也。”——叶十。
周良霄译注《成吉思汗的继承者——〈史集〉第二卷》:周按:此处之“八里里答兰答巴思”即《元史·定宗纪》:“会诸王百官于答兰答八思之地,遂议立帝。”“答兰答八思”Dolan-Daba,义为“七十山口”。而《察罕传》载是年窝阔台返自河南,居“清水答兰答八之地”。“八里里”之义不明。至若清水,则与青色之湖之Köke-Na’ur自可联系。前文窝阔台本纪谓阔阔脑兀儿为大汗秋狩之地,离和林四日程,疑答兰答八思地近阔阔脑兀儿,故中外所纪,名虽不同,地望实一也。——第213页。
同氏《〈元史〉点校献疑》又记:答阑答巴思名屡见于《元史》,其义为七十山口,与八里里当分标专名号。
阿布拉莫夫斯基未查上述诸家意见,其注(98):八里里可能是一个附近之地方(Pali-li ist möglicherweise einenähere Ortsbestimmung)。——《太宗纪》德译,第144页。
[2] 《考异》卷八六:按,是春伐金之役,与宋合攻,金亡之后与宋约和,以陈蔡东南为宋,西北为蒙古,各引兵还矣。乃宋相郑清之忽主收复二京之议,遣全子才等率淮西兵万余人,以六月出师,七月二日抵汴,而赵文仲以淮东师五万继至,乃遣徐敏子为监军西上,二十八日入洛阳。元戍兵先期空城而去矣,宋兵粮尽不能守,引还。八月二日,元兵追击之,大败。敏子中流矢,徒步间行,由浮光遁。子才在汴,闻洛东丧师,亦于二十五日弃城遁。此元太宗所以有自将伐宋之议也。纪于分地约和及宋背约北侵事俱不之及,则议伐宋为无名矣。
[3] 《考异》卷八六:即木华黎之孙塔思也。
“查老温”(Čilao’un),蒙古语意为“石”;“塔思”(Taš),突厥语亦意为“石”。
冬,猎于脱卜寒地[1]。
[1] 屠寄:“脱卜寒,义谓山梁,地当与荅兰荅八思相近。”——《蒙兀儿史记》卷四《斡歌歹可汗本纪》,叶十。阿布拉莫夫斯基注(100):Topqan?未详其地(Nichtzu identieren)。——《太宗纪》德译,第144页。
有关此年政事,《大元毡罽工物记》(《广仓学宭丛书》甲类第二集,叶七)记:六年甲午,元帅习剌奉剌聚诸工七千余户。
七年乙未春,城和林[1],作万安宫[2]。遣诸王拔都[3]及皇子贵由、皇侄蒙哥征西域[4],皇子阔端征秦、巩,皇子曲出[5]及胡土虎[6]伐宋,唐古征高丽[7]。
[1] 《圣武亲征录》:“乙未(按,元太宗七年,1235)春,建和林城宫殿。”
《醉隐集·取和林诗》注云:“和林城,苾伽可汗之故地也。乙未,圣朝太宗皇帝城此,作万安宫,城西北七十里有苾伽可汗宫城遗址,城东北七十里有唐明皇开元壬申御制御书阙特勤碑。”
[2] 周良霄译注《成吉思汗的继承者——〈史集〉第二卷》:周按:《刘敏传》:“己丑,太宗即位,改造行宫幄殿。乙未,城和林,建万安宫,设宫闱司局。”据此,窝阔台宫殿兴建之次第,略可概知。耶律楚材《湛然文集》卷十三《和林城建行宫上梁文》:“抛梁南,一带南山揖翠岚,创筑和林建宫室,侯功业冠曹参。”侯当即喻刘敏。和林之定都,据许有壬《至正集》卷四五《敕赐兴元阁碑》谓在成吉思汗之十五年,《元史·地理志》同。然疑惑甚多,颇难肯定。至若土木宫殿之兴建,实始于窝阔台之七年。此城之概况,据鲁不鲁乞所纪:“至于说到哈剌和林,我可以告诉您,如果不把大汗的宫殿计算在内,它还不及法兰西的圣但尼Saint Denis村大,而圣但尼的修道院的价值,要比那座宫殿大十倍。城里有两个地区:一个是萨拉森人区,市场就在这个区里。许多商人聚集在这里,这是由于宫廷总是在它附近,也是由于从各地来的使者很多。另一个是契丹人区,这些契丹人都是工匠。除这些地区外,还有宫廷书记们得若干座巨大宫殿、十二座属于各种不同民族的异教徒的庙宇,两座伊斯兰教寺院(在寺院里公布着摩诃末的教规);一座基督教徒的教堂(坐落在城市的最末端)。城的周围环绕着土墙,并有四个城门。东门出售小米和其他谷物,不过,那里难得有这些谷物出售;西门出售绵羊和山羊;南门出售牛和车辆;北门出售马匹。”(《出使蒙古记》第203页)——第85页。
[3] 《元史译文证补》卷五有《拔都补传》。
[4] 此即《秘史》节270总译所记之“长子西征”:“斡歌歹既立,与兄察阿歹商量,成吉思皇帝父亲留下未完的百姓有巴黑塔惕种的王合里伯,曾命绰儿马罕征进去了,如今再教斡豁秃儿,同蒙格秃两个做后援征去。再有康里、乞卜察等十一种城池百姓,曾命速别额台征进去了,为那里城池难攻拔的上头,如今再命各王长子巴秃(Batu)、不里(Büri)、古余克(Güyük)、蒙格(Möngke)等做后援征去。其诸王内,教巴秃为长。在内出去的教古余克为长。凡征进去的诸王、驸马、万、千、百户,也都教长子出征。这都教长子出征的缘故,回兄察阿歹说将来。长子出征呵,则人马众多,威势盛大,闻说那敌人好生刚硬,我兄察阿歹谨慎的上头,所以教长子出征,其缘故是这般。”罗亦果有关此事的释文见《元朝
秘史》英文译注,下册,第989页及以下。
志费尼记(何高济汉译本,上册,第234页):“因为钦察与克列儿(Keler)各部尚未完全摧毁,所以,征服和消灭这些部族就成为首要的任务。诸王拔都、蒙哥可汗、贵由,领命指挥这次战役,他们率大食和突厥大军各返己营,准备在来年初春出师。他们作好这次远征的准备,在预定的时间出发。”其中与钦察并列的克列儿(Keler),波斯文原文写作(KLaR),伯希和在《金帐汗史评注》中指出,即《秘史》邛262、270之克列勒(Keler),源自马札儿语király,乃“国王”这个词之讹。参见《世界征服者史》何高济汉译本,上册,第236页,注(3),补林沉钦察之战。
宋子贞《耶律楚材神道碑》(《元文类》卷五七)中有一段记载非常值得注意:“乙未(1235),朝议以回鹘人征南,汉人征西,以为得计。公极言其不可,曰:‘汉地西域相去数万里,比至敌境,人马疲乏,不堪为用。况水土异冝,必生疾疫。不若各就本土征进,似为两便。争论十余日,其议遂寝。”这段记载中的“朝议”,当发生于和林。所议调用汉人征西域,即当指“长子西征”之役。既往的研究多集中于诸王贵戚各出长子之事。据宋子贞的记载,当初蒙古国朝廷讨论西征军的组成时,曾考虑过征发汉人的问题,因耶律楚材反对,廷议争论十余日而后才放弃。如果此议得行,历史可能要改写。
[5] 周良霄《元代投下分封制度初探》(《元史论丛》第二辑):此“曲出”当为“阔出”之误。同氏《成吉思汗的继承者——〈史集〉第二卷》(第67页):周按:此处之曲出,证以《阿剌罕传》、《察罕传》、《铁蔑赤传》、《脱欢传》、《元文类》卷二五《曹南王世德碑》皆作“阔出”。惟《塔思传》有:太宗六年(甲午),“命与王子曲出总军南征”。《太宗纪》八年冬:“皇子曲出薨”。《蒙兀儿史记》卷四《斡哥歹可汗本纪》改曲出作阔出,一若“曲”字为误植。然则曲出即阔出,译音以方言也。
《圣武亲征录》:“冬十一月,[曲]赤{曲}、{阙}[阔]端等克西川。”
[6] 屠寄《蒙兀儿史记》卷四《斡歌歹可汗本纪》:按胡土虎,即忽都秃转音。《阿剌罕传》谓岁乙未,从皇子阔出,忽都秃南征。——叶十。
[7] 《元高丽纪事》:七年乙未,命将唐古拔都鲁,与福源,同领兵征高丽。攻拔龙岗县、凤州、海州、洞州。九月,山城、慈州等处。——叶六
秋九月,诸王口温不花[1]获宋何太尉[2]。
[1] 阿布拉莫夫斯基注(106):口温不花,成吉思汗弟别里古台子。见《元史》卷一一七;韩百诗:《〈元史〉卷一百七〈宗室世系表〉译注》页49,注2(Kü’ün buqa, der Sohnvon Činggis Qans Bruder Belgütei. YS 117, 1v; Нambis, Le chapitre cVII, S. 49,n.2)。——《太宗纪》德译,第145页。
[2] 屠寄《蒙兀儿史记》卷四《斡歌歹可汗本纪》:人名、地名均失考。——叶十。
冬十月,曲出围枣阳,拔之,遂徇襄、邓,入郢,虏人民牛马数万而还。十一月,阔端攻石门[1],金便宜都总帅汪世显[2]降。中书省臣请契勘大明历,从之。
[1] 屠寄《蒙兀儿史记》卷四《斡歌歹可汗本纪》:西和州本石门镇升。——叶十一。
[2] 《元史》有传,见卷一五五。
八年丙申春正月,诸王各治具[1]来会宴。万安宫落成[2]。诏印造交钞行之[3]。
[1] 屠寄《蒙兀儿史记》卷四《斡歌歹可汗本纪》:所谓治具,旄车载酪湩而已。——叶十一。
[2] 《圣武亲征录》:“丙申,大(庆)[广]和林城宫。”
[3] 阿布拉莫夫斯基注(111):蒙古统治下最早纸币似乎在1224至1227年间已在山东博州流通。参见傅海波:《蒙古统治下的货币与经济》,页35(Das erstePapiergeld unter den Mongolen scheint bereitszw ischen 1224 und 1227 inP.-chou 博州 (in Shan-tung) in Um lauf gewesenzu sein. Siehe Н. Franke, Geld und Wirtschaft, S. 35)。——《太宗纪》德译,第145页。
二月,命应州郭胜、钧州孛朮鲁九住、邓州赵祥从曲出充先锋伐宋[1]。
[1] 《考异》卷八六:按郭胜等三人,史皆无传,唯姚燧撰《邓州长官赵公神道碑》于祥事颇详。祥字天麟,蔡之平兴人。金天兴癸巳(二年,1233),天兵围蔡,城中粮绝,公率部曲发富室藏粟,突围上馈,授提控。明年甲午(三年,1234),将麾下归宋,授信效左军统制,遣戍邓州。乙未(1235)十月,天兵略地汉上,开门纳降。居两月,太子即曲出也,南征还过,教以是城甚近襄阳,虞力孤不能自完,且岁荒,与邓、均、唐三州民徙洛阳之西三县,邓治长水,均治永宁,唐治福昌,许公权宜行省事。乃先劳分苦,佐乏药疾,府寺田庐于粲一始。丙申,襄樊亦徙洛阳。其年入觐,特赐金符锦衣,许出战督军,入守字民,别降银符八十,金符八,以酬从公将佐同力者。盖祥降元以后,即徙治内地,别无从曲出伐宋之事。元初不立史官,后来修实录者,大约道听途说,十不存一。故太祖四朝纪,大率疏舛,无可征信。——《牧庵集》卷十八;《元文类》卷六四。
阿布拉莫夫斯基注(112):无郭胜传记资料。孛朮鲁九住即范用吉,在《金史》卷一一四中有一则简注。赵祥在《新元史》卷一四五中有传(Von Kuo Sheng gibt es keine Lebensbeschreibung.Po-chu-lu chiu-chu ist identisch m it Fan Yung-chi, über den eine kurzenotiz im cS 114 16vvorhanden ist. chao Нsiang hat eine Biogrphie im НYS 145,10r-v.)。——《太宗纪》德译,第145页。
三月,复修孔子庙及司天台。夏六月[1],复括中州户口,得续户一百一十余万[2]。耶律楚材请立编修所于燕京,经籍所[3]于平阳,编集经史,召儒士梁陟[4]充长官,以王万庆、赵著副之[5]。
[1] 屠寄《蒙兀儿史记》卷四《斡歌歹可汗本纪》:耶律楚材旧传作秋七月。——叶十一。
[2] 屠寄《蒙兀儿史记》卷四《斡歌歹可汗本纪》:《亲征录》事在乙未,数字是一百二十万。——叶十一。
洪金富《从“投下”分封制度看元朝政权的性质》(《中研院史语所集刊》第58期第四分,第853页):癸巳(1233)、乙未(1235)两次所载籍户数,记载颇多歧异。爱宕松男以为《元史·太宗纪》:丙申(1236)“夏六月,复括中州户口,得续户一百一十余万”中的一百一十余万户,并不包括癸巳年所籍的七十三余万户。换言之,两次共籍到一百八十余万(110万+73万)。见《蒙古人政权治下の汉地に于ける版籍の问题》,《羽田博士颂寿记念东阳市论丛》(京都,1950),页387—298。按,乙未年一百一十余万户含癸巳年所籍七十三万余户在内。《圣武亲征录》(《蒙古史料四种》本)页105a载:“忽都忽籍到汉民一百一十万有奇。”《元史》卷98《兵志一·兵制篇》:“忽都忽等籍到诸路民户一百万四千六百五十六户。”宋子贞《中书令耶律公神道碑》说:“初,籍天下户,得一百四万。”(《国朝文类》卷57)这几个数字与一百一十万相近。《元史》卷98《兵志一·兵制篇》另段记载,有“断事官忽都虎新籍民户三十七万二千九百七十二人数内……”云云,可知《太宗纪》“得续户一百一十余万”云云,乃合癸巳年七十三万与乙未新籍三十七万,计一百一十万之谓。
阿布拉莫夫斯基注(113):请比较页128及注80(按,指《太宗纪》德译页及注)。按《元史》卷一四六《耶律楚材传》提供的资料,这一括户是在失吉忽禿忽领导下实施的。同时比较舒尔曼《〈元史·食货志〉译注》,页67.(Vgl. S.128 undanm.80.angaben in der Biographievon Ye-lü ch’u-ts’ai (YS 146, 7r)zufolge, wurde diesezählung unter der Leitungvon Šigi Qutuqu durchgeführt.vgl.auch Schurmann, S. 67)。——《太宗纪》德译,第145页。
(日)爱宕松男《东洋史学论集卷四元朝史》:《圣武亲征录》载:“(太宗七年乙未)忽都忽籍到汉民一百一十万有奇。”《元史·本纪》载: “(八年) 复括中州户口,得续户一百一十余万。”作者认为两书所载日期虽不一致,却并不代表记载的是两件不同之事。宋子贞撰《耶律楚材神道碑》载: “甲午诏括户口。以大臣忽睹虎领之……丙申秋七月。忽睹虎以户口来上。”所谓的由忽睹虎那颜主持的中原的民户抄数通常是指乙未年括户。从《耶律楚材神道碑》可见,其初始实际是从太宗六年开始的,实际的完成是在太宗八年。——三一书房,1998年,第215—216页
方龄贵《通制条格校注》卷二《户令·户例》:《元史》等史籍“所记户口数并不一致。以意度之,籍户或非一朝一夕可就之事,谅系太宗六年创议,七年初有成果而上其数,八年最后卒事。然则七年所上户数,当以《地理志》所录八十七万三千七百八十一为近是,八年所上户数,当以《兵志》所录三十七万二千九百七十二为近是;合之,得户一百二十四万六千七百五十三。《亲征录》所著录之一百一十一万(按:他本或作一百二十万)有奇,《研北杂志》之一百一十一万,及《元史·太宗纪》八年之一百一十余万,与此相去不甚远;但‘得续户’云云,似不足据,盖合七年、八年两次所籍之户而计之耳。《亲征录》系于乙未岁,疑亦同此。至于为户一百二十四万六千七百五十三与一百一十一万、一百一十余万、一百一十一万有奇之出入,或当由于其中有逃户之故。贾敬颜《圣武亲征录》校本亦曾考论及此,可参考”。中华书局,2001年,第27—28页注(1)。
[3] 赵琦《金元之际的儒士与汉文化》:苏天爵《题诸公与参议先生书启》,《滋溪文稿》卷三十。文中说“是时耶律公楚才领中书政务,命诸路置经籍所以儒者司之,盖欲士明经学,兴起文治。”但从现有材料看,似乎只有燕京、平阳和京兆设置过编修所或经籍
所,而且其创设与耶律楚材和胡天禄等人有密切关系。——第60页。
[4] 宋子贞《中书耶律公神道碑》提及:“初汴京未下,奏遣使入城索取孔子五十一代孙袭封衍圣西元措,令收拾散亡礼乐人等,及取名儒梁陟等数辈。于燕京置编修所平阳置经籍所以开文治。”——苏天爵编《元文类》卷五七,四部丛刊景元至正刊本。
其后裔即蒙古国与元初名臣梁暗都剌,按王恽记载,其“故曾祖金中奉大夫、司农少卿陟,早登科第,顕历仕途,履正奉公,才优国计,持难抗节,身为大闲,在先儒耆德之间,有泰和能臣之誉,经纶事往,道义日尊,流泽远及于子孙,致位有开。”——《追谥故都运梁公通宪先生制》,《秋涧集》卷六七,叶八上。“暗都剌”,为阿拉伯语‘abdal-allāh“真主之奴仆”音译,乃回回人名。
[5] 阿布拉莫夫斯基注(114):只有赵著稍有名:他是燕人,充编修官(《困学斋杂录》);《蒙兀儿史记》补充下列内容:使直释九经,进讲东宫,令大臣子孙执经听讲(Nur über chao chu ist ein wenig bekannt: Er stamm teaus Yen und warals Kom ilator (pien-hsiukuan) tätig (KНcTL, 18v);MS 4, 12r ergänztnoch folgendes: Sie sollten die 9 K lassikerausgegen und den Kronprinzen darin unterweisen.auch die Söhne und Enkel der hohen Minister solltenan diesen Unterweisung teilhaben)。——《太宗纪》德译,第145页。
秋七月,命陈时可[1]阅刑名、科差、课税等案,赴阙磨照。诏以真定民户奉太后汤沐[2],中原诸州民户分赐诸王、贵戚、[3]斡鲁朵[4]:拔都,平阳府[5];茶合带,太原府[6];古与,大名府[7];孛鲁带,邢州[8];果鲁干,河间府[9];孛鲁古带,广宁府[10];野苦,益都、济南二府户内拨赐[11];按赤带,滨、棣州[12];斡陈那颜,平、滦州[13];皇子阔端[14]、驸马赤苦[15]、公主阿剌海[16]、公主果真[17]、国王查剌温[18]、茶合带[19]、锻真[20]、蒙古寒札[21]、按赤那颜[22]、坼那颜[23]、火斜、朮思[24],并于东平府户内拨赐有差[25]。耶律楚材言非便,遂命各位止设达鲁花赤,朝廷置官吏收其租颁之,非奉诏不得征兵赋[26]。阔端[27]率汪世显等入蜀,取宋关外数州[28],斩蜀将曹友闻[29]。
[1] 阿布拉莫夫斯基注(115):他是燕人,在金为翰林学士,蒙古统治时期为燕京课税官(见页125——按,指《太宗纪》德译页)。《困学斋杂录》及《归潜志》(Er stamm teaus Yen, unter chin wurde er Нan-lin Gelehrter, unter den Mongolen Steuernkomm isarvon Yen-ching. (Vgl. S.125). KНcTL 18v und Kuei-ch’ien-chi 14, 7r)。——《太宗纪》德译,第145页。
[2] 《考异》卷八六:按:《食货志》:“睿宗子阿里不哥大王位:丙申年,分拨真定路八万户。”盖太后汤沐之邑,后为睿宗所有。
洪金富《元代文献考释与历史研究——称谓篇》:“太后”为唆鲁禾帖尼。原来名单写有唆鲁禾帖尼(唐妃)之名,名列第四,而与其前的三人依序代表太祖正妻所生的长子、次子、三子、四子。《元史·太宗纪》上的顺序是后来的更动。——《中研院史语所集刊》第81本,第4分,2010年,第747页。
洪金富此议甚是。将唆鲁禾帖尼称为太后,是宪宗朝以后事。原《实录》所记顺序当为术赤位元、察合台位、窝阔台位与拖雷位。此处将唆鲁禾帖尼封户列于第一,当系后来所改。
[3] 阿布拉莫夫斯基注(118):《元史》卷九五有民户分封的详情及数字(Eineausführlicheaufzählung, m itangaben über diezahl derverteilten Нaushalte findet sich im YS 95, 1v—34r)。——《太宗纪》德译,第145页。
[4] 阿布拉莫夫斯基在此处将斡鲁朵视为人名,即拔都之兄斡儿答,读为“斡鲁朵、拔都”,并译为Wo-lu-to und Pa-to。他在注(119)中表示:斡儿答和拔都,《新元史》卷一百六,成吉思汗长子朮赤之子。(Orda und Batu, НYS 106, 4v. Söhnevon Činggis Qans ältestem Sohn Jöči)。——《太宗纪》德译,第145页。
[5] 《考异》卷八六:《食货志》:“朮赤大王位:分拨平阳四万一千三百二户。”拔都者,术赤之子。
按,察合台(Čaγatai),成吉思汗次子,察合台汗国的创立者。
[7] 《考异》卷八六:《食货志》:“太宗子定宗位:分拨大名六万八千五百九十三户。”定宗名贵由,此作古与,声相近。
按,贵由(Güyük),元太宗长子。
[8] 《考异》卷八六:《食货志》:八答子“丙申年,分拨顺德路一万四千八十七户”。顺德路即邢州,则孛鲁带疑即八答子矣。《世祖纪》:邢州有两答剌罕,其一为启昔礼,即哈剌哈孙之大父,其一则《太祖纪》所谓把带,即八答子也。或云启昔礼之子,名博理察,与孛鲁带声亦相近。
屠寄《蒙兀儿史记》卷四《斡歌歹可汗本纪》:《食货志》:孛罗台右万户位下五户丝,丙申年(1236)分拨,洺水州七千户。按《金史·地理志》:洺州,广平郡,领县九,治永平。其九曰洺水,是洺水为县名,非州名,旧《纪》(按,《地理志》非《纪》)称州,误也。《元史·地理志》:太宗六年置邢洺路总管府,以邢洺威隶之。至元十五年,升广平路总管府。据此,旧《纪》之邢州,《食货志》之洺水州,当是邢洺州之误。——叶十二。
阿布拉莫夫斯基注(122):邢州(即顺德路)及一万四千八十七户均封给八答子(《元史》卷九五,叶21背面)。哈佛燕京引得将八答子与博理察视为同一人,但这一点无法证实。(Hsing-chou (=Shun-te-lu) wurde m it 14,807 haushaltenan Pa-ta-tzu gegeben.( YS 95, 21r). Laut Нarvard-Yenching-Index ist Pa-ta-tzu m it Po-li-ch’a identisch, dieangabe dort konnteabernichtnachgeprüft werden)。——《太宗纪》德译,第146页。
[9] 《考异》卷八六:《食货志》:“阔列坚太子河间王位:分拨河间路四万五千九百三十户。”果鲁干,即阔列坚也。
按,阔列坚(Kölgen),成吉思汗庶子,排位第六子。参阅韩百诗《宗室世系表》译注,第51页;阿布拉莫夫斯基注(123),《太宗纪》德译,第146页。
屠寄《蒙兀儿史记》卷四《斡歌歹可汗纪》:按广宁在辽东,非中原地。《食货志》改正。——叶十二。
别里古台(Belgütei)为成吉思汗庶弟,《元史》卷一一七有传。
[11] 《考异》卷八六:《食货志》:“搠只哈撒儿大王子淄川王位:分拨般阳路
二万四千四百九十三户。”淄川王,名也苦,即野苦。
按,也苦(Yekü),成吉思汗弟搠只哈撒儿之子。参阅韩百诗《宗室世系表》译注,第24页;阿布拉莫夫斯基注(125),《太宗纪》德译,第146页。
[12] 《考异》卷八六:《食货志》:“哈赤温大王子济南王位:分拨济南路五万五千二百户。”济南王,名按只吉歹,即按赤带也。
按,按赤吉歹(alčidai),成吉思汗弟哈赤温之子。韩百诗《宗室世系表》译注,页29罗列此人名称的不同拼法;见阿布拉莫夫斯基注(126),《太宗纪》德译,第146页。
[13] 《考异》卷八六:《食货志》:“斡真那颜位:分拨益都等处六万二千一百五十六户。”案斡陈,即斡赤斤,其后为辽王,则纪云平、滦者,为得其实。
按,斡赤斤(Očigin)即铁木哥·斡赤斤(Temüge Očigin),成吉思汗三弟。参阅韩百诗《宗室世系表》译注,第23页;阿布拉莫夫斯基注(127),《太宗纪》德译,第146页。
[14] 《考异》卷八六:《食货志》:“阔端太子位:分拨东京路四万七千七百四十一户。”东京,盖东平之讹。《元典章》有东昌路达鲁花赤探马赤前去永昌府,将军粮交付了当云云。则东昌乃阔端太子分地。元初,其地隶东平行省也。
按,阔端(Köden),元太宗子。
[15] 《考异》卷八六:《公主表》,郓国公主位:禿满伦公主适赤窟驸马。即此赤苦也。《食货志》:“郓国公主位:丙申年,分拨濮州三万户。”
《本证》卷三十七证名一:赤窟,公主表。
按,赤苦(Čikü),成吉思汗女帖木仑公主驸马。参阅韩百诗《元史·诸王表》译注,第160页,注2;阿布拉莫夫斯基注(129),《太宗纪》德译,第146页。
[16] 《考异》卷八六:《公主表》,赵国大长公主阿剌海别吉适赵武毅王孛要合。《食货志》:“赵国公主位:分拨高唐州二万户。”
阿剌海(alaqai)公主,成吉思汗女。参见参阅韩百诗《元史·诸王表》译注,第25页;阿布拉莫夫斯基注(130),《太宗纪》德译,第146页。
[17] 《考异》卷八六:《公主表》,昌忠武王孛禿继室,以太祖女昌国大长公主火臣别吉。火臣,即果真也。《食货志》:“昌国公主位:分一万二千六百五十二户。失书地名。”
火臣(Goĵin)公主,成吉思汗女。参见参阅韩百诗《元史·诸王表》译注,第30页;阿布拉莫夫斯基注(131),《太宗纪》德译,第146页。
[18] 《考异》卷八六:《食货志》:“木华黎国王:分拨东平三万九千一十九户。”查老温,即木华黎之孙。
按,前已提及,查剌温(Čilao’un,蒙古语意为“石”),即木华黎孙塔思(Taš,突厥语亦意为“石”)。
[19] 《考异》卷八六:茶合带,未详何人,恐是衍文。
屠寄《蒙兀儿史记》卷四《斡歌歹可汗本纪》(叶十二):所谓茶合带,决非成吉思汗之子察阿歹,因上文已见“茶合带,太原”也。他在《蒙兀儿史记》中的相应段落中行文中,删去茶合带,当是遵从上述《考异》意见。
这位茶合带(Čaγatai),韩百诗《元史·诸王表》译注,系表五怀疑为木华黎之侄;参见阿布拉莫夫斯基注(133),《太宗纪》德译,第146页。按,其名接于查剌温之下,或与木华黎家族有关。
[20] 《考异》卷八六:按朮赤台有孙端真拔都儿,袭爵郡王,即锻真也。高觽传,父守忠,从段真郡王取中原有功。《食货志》:“朮赤台郡王:丙申年,分拨德州二万户。”
屠寄《蒙兀儿史记》卷四《斡歌歹可汗本纪》:锻真,《食货志》不见。《秘史》卷八有客台,为八十八功臣之一,即主儿扯歹之子怯台郡王。按旧史《朮赤台传》:朮赤台,兀鲁兀台氏,子怯台以劳封德清郡王。丙申,赐德州户二万为食邑。子端真拔都儿龚爵为郡王。太宗时与亦剌哈台战胜,帝即以亦剌哈妻赐之,辨见《主儿扯歹传》注,然端真仕太宗朝固事实也,据此知旧《纪》(按,即此《元史·太宗纪》)之茶合带为怯台之音差,而锻真即端真之异文。又按《畏答儿传》曰:“岁丙申,忽都忽大料汉民,分城邑以封功臣,授忙哥泰安州民万户,帝讶其少,命增封为二万户。兀鲁争曰:忙哥旧兵不及臣之半,今封户顾多于臣。帝曰:汝忘而先横鞭马鬃耶?兀鲁遂不敢言,正指是分户事。兀鲁,即兀鲁兀,端真之氏。德州是时隶东平。——叶十二。
阿布拉莫夫斯基注(134):锻真,朮赤台之孙。《元史》卷一二〇(Dönĵin(?), Enkelvon Jočidai. YS 120, 8r—10r)。——《太宗纪》德译,第146页。
[21] 《考异》卷八六:按畏荅儿之子忙哥,封郡王,疑即蒙古也。《食货志》:“愠里荅儿薛禅:丙申年,分拨泰安州二万户。”愠里荅儿,即畏荅儿,寒札未详。
屠寄《蒙兀儿史记》卷四《斡歌歹可汗本纪》:《秘史》八十八功臣之一,《亲征录》木哥汉札,《畏答儿传》作忙哥。《食货志》:温里答儿薛禅位下五户丝,丙申年(1236)分拨泰安州二万户。按,温里答儿即畏答儿,亦即《秘史》忽亦勒答儿。此人死于成吉思汗未即位之前。《志》以位言,故仍称温里答儿,《纪》以人言,故径书蒙古札寒。——叶十二。
阿布拉莫夫斯基注(135):蒙古寒札,忙兀部首领畏答儿之子(Mönggü qalĵa, Sohnvon Quyidar, chef der Mangγut (chaptre cVIII, S.176))。——《太宗纪》德译,第146页。
[22] 《考异》卷八六:按赤那颜(按赤那颜,即国舅按陈那颜也。《食货志》:“鲁国公主位:丙申,分拨济宁路三万户。”
屠寄《蒙兀儿史记》卷四《斡歌歹可汗本纪》: 即宏吉剌部德薛禅长子,《秘史》作阿勒赤,八十八功臣之一。——叶十二。
姚景安编《元史人名索引》汇集此人不同名称写法:按嗔那颜(按赤那颜、按赤那延、按只那演、按陈、按陈那衍、济宁王、河西王、忠武、济宁忠武王、鲁忠武王。又王恽《追封皇国舅济宁王谥忠武制》文(《秋涧集》卷六七,叶五上 )与程钜夫《皇太后故曾祖父追封济宁王谥忠武、加追封鲁王仍谥忠武制》(《雪楼集》卷三,叶一一上)均写为按赤那演。
阿布拉莫夫斯基注(136):按赤那颜,成吉思汗妻孛儿帖之兄弟(alĵinnoyan, Brudervon Börte, der Frauvon Činggis Qan)。——《太宗纪》德译,第146页。
[23] 《考异》卷八六: “坼”当是“折”字之讹,哲别以骁勇事太祖,与虎必来、者勒蔑、速不台称四先锋。纪、传或书遮别,或书者别,郭宝玉传作柘柏,吾也而传称折不那演,巴而朮阿而忒的斤传称者必那演,实一人也。《食货志》:“和斜漫两投下一千二百户。丙申年,分拨曹州一万户。”和斜漫,即火斜木思也。而坼那颜则志遗之。
阿布拉莫夫斯基注(137)亦将此人视为哲别(Ĵebenoyan, der berüm te Gemeral Činggis Qans)——《太宗纪》德译,第146页。
屠寄《蒙兀儿史记》卷四《斡歌歹可汗本纪》(叶十二)则将坼那颜改为册那颜,并表示“册那颜,阿勒赤那颜之弟。旧《纪》、《食货志》作坼那颜,据《德薛禅传》改”。即将此
人视为宏吉剌部人。
[24] 钱大昕读为“火斜木思”,《考异》卷八六:《食货志》:“和斜漫两投下一千二百户。丙申年,分拨曹州一万户。”和斜漫,即火斜木思也。
屠寄在火斜与术思之间不点断,并改“火斜术思”为 “豁儿赤塔思”。他写道:“原作火斜术思。按旧史《忙古台传》曰:蒙古达达儿氏,祖荅思火儿赤,从太宗定中原有功,为东平达鲁花赤。《食货志》云:塔思火儿赤位下五户丝,丙申年(按,1236)分拨东平穜田一百户,即火斜术思也。‘火斜’之异译为‘火儿赤’,异文为‘豁儿赤’,为佩櫜鞬宿卫之官。‘术思’疑本作‘荅思’,形近之讹。魏氏源《元史新编》作‘和斜术’,谓即《食货志》之‘火斜温’,丙申年分拨旧州一万户,误也。” ——《蒙兀儿史记》卷四《斡歌歹可汗本纪》,叶十二。
阿布拉莫夫斯基德译文在火斜与术思之间亦不点断,并在注(138)中表示此人不可考(Konntenicht identi fiziert werden)——《太宗纪》德译,第146页。
[25] 《考异》卷八六:又按:志所载丙申年分拨者,尚有太祖叔荅里真官人、火雷公主、孛罗先锋、行丑儿、乞里歹拔都、笑乃带先锋、带孙郡王、孛鲁古妻佟氏、孛罗台万户、忒术台驸马、斡阔烈阇里必、合丹大息千户、也速不花等四千户、也速兀儿等三千户、帖柳兀禿千户、灭古赤、塔思火儿赤、折米思拔都儿、迭哥官人、黄兀儿塔海、添都虎儿,纪俱不载。
屠寄《蒙兀儿史记》卷四《斡歌歹可汗本纪》(叶十二)注文基本同此。
《本证》卷一证误一:案《食货志岁赐》当作“东京路”。(按,纪是。诸王岁赐民户均在中原,而东京路即后之辽阳路,不属中原。校点本《元史》已改“京”为“平”。)
[26] 宋子贞《耶律楚材神道碑》:“其秋七月,忽睹虎以户口来。上议割裂诸州郡分赐诸王贵族,以为汤沐邑。公曰:‘尾大不掉,易以生隙。不如多与金帛,足以为恩。’上曰:‘业已许之。’复曰:‘若树置官吏,必自朝命,除恒赋外,不令擅自徴敛,差可久也。’从之。是岁,始定天下赋税,每二戸出丝一斤,以供官用;五户出丝一斤,以与所赐之家。上田毎畒税三升半,中田三升,下田二升;水田五升。商税三十分之一,盐毎银一两四十斤。已上以为永额。朝臣皆谓太轻。公曰:‘将来必有以利进者,则已为重矣。”
屠寄此处注:“按《食货志》,丙申年分拨五户丝者,尚有阿里不哥,真定路八万户;郓国公主,濮州三万户;鲁国公主,济宁路三万户;火雷公主,延安府九千七百九十六户;孛罗先锋,广平等处穜田一百户;行丑儿,大名穜田一百户;乞里歹拔都,东平一百户;笑乃带先锋,东平一百户;孛鲁古妻佟氏,真定一百户;八荅子,顺德一万四千八十七户;忒木带驸马,广平路磁州九千四百户;帖柳兀禿千户,河闲路临邑县一千四百五十户;火斜温两投下,曹州一万户;灭古赤,凤翔府一百三十户;折米思拔都儿,怀孟等处一百户;孛哥帖木儿,真定等处五十八户;迭哥官人,大名清丰县一千七百一十三户;黄兀儿塔海,平阳一百四十户;添都虎儿,真定一百户。旧纪不悉载,坿注于此以待考。”——《蒙兀儿史记》卷四《斡歌歹可汗本纪》,叶十二。
钱大昕与屠寄虽然在此处均比照《食货志》,但因对人名解读不同,因而录《食货志》文时取舍有别。
[27] 窝阔台第三子。
[28] 阿布拉莫夫斯基德译注(142)中表示无法确定此处究指何处(Es konntenicht
festgestellt werden, um welches Gebiet es sich genau handelt)——《太宗纪》德译,页146。[宋]曹彦约所撰之《与蜀帅桂侍郎札子》提到:“或谓近日议论有欲弃关外四州者,以其费多而守备众也。不知四州之急起于中兴,失关陇则四州急;弃四州则梁、洋、沔、利急;地愈狭则急愈甚矣。”——:《昌谷集》卷一三,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按此,关外之地当指关中的西界大散关以外诸地。
[29] 阿布拉莫夫斯基德译注(143):宋著名将领曹彬的一位后裔,《宋史》卷四四九,叶十二上—十六上(Einnachfahre des berühm ten Sung-Generals Ts’ao Pin. SS. 449, 12v—16v.)。——《太宗纪》德译,第146页。
冬十月,阔端入成都。诏招谕秦、巩等二十余州,皆降。皇子曲出[1]薨。张柔[2]等攻郢州,拔之。襄阳府来附,以游显[3]领襄阳、樊城事。
[1] 即阔出,窝阔台第四子。
[2] 《元史》卷一四七有传。《太宗纪》与《定宗纪》自太宗八年(1236)起,提及张柔的次数远远超过其他人,似显示此二本纪所据之原始资料与张柔家传有关。
[3] 游显,字子明,《元史》中数见。其神道碑《荣禄大夫江淮等处行中书省平章政事游公神道碑》为姚燧所撰,收入《牧庵集》卷二二。
九年丁酉春,猎于揭揭察哈之泽[1]。蒙哥征钦察部[2],破之,擒其酋八赤蛮[3]。
[1] [清]李文田《元史地名考》:九年春、十年夏、十一年春、十三年春均猎于揭揭察合之泽,《提纲》三十二:“鄂勒昆河东北流折西北二百里有尔马台河,自西南来会,亦曰朱勒马台河,岀额黑铁木儿山,南麓东南流,绕布库铁木儿山足三面,东北流曲曲二百余里,瀦为池曰察罕鄂模,广数十里。”后卷《宪宗纪》作怯蹇义罕,即其地也。同书(页25):《宪宗纪》:“三年,猎于怯蹇义罕之地。” 殿在揭揭察罕泽上,故曰揭揭察罕殿,察罕者,白也,湖水色白,此湖亦名揭揭脑儿,转写亦作颗颗脑儿也。《宪宗纪》云云即此殿,《明宗纪》:“次洁坚察罕之地。”亦即此地也。《地志》云:“太宗乙未年,城和林,作万安宫。丁酉,治迦坚茶寒殿,在和林北七十余里。”
屠寄当之以《秘史》之“的的克撒合勒”之泽,并称按图今赛音诺颜汗右翼中旗有察罕泊,在达剌尔和喀喇巴尔噶孙之西。喀喇巴尔噶孙即唐回纥苾伽可汗宫城,窝阔台之迦坚茶寒殿在泽上。——《蒙兀儿史记》卷四《斡歌歹可汗本纪》,叶十二。
阿布拉莫夫斯基德译注(148):蒙古语“Gegen chaγan”。这些湖泊位于哈剌和林以北约70里处。1237年夏窝阔台在此区域建迦坚茶寒宫。《元史》卷五八,叶三八上。并见波义耳《窝阔台大汗的季节性居地》(按,The Seasonal Residence of the Great Khan Ögedei,Schriftenzur Geschichte und Kultur desalten Orients, Berlin, 1974 (protokollband der XII.PIac): 145—151),頁146(Mong. “Gegen chaγan”. Diese Seen lagen etwa 70 linördlichvon Qara-qurum. In dieser Gegend liess Ögedei im Sommer 1237 den Chia-chien ch’a-hanPalast errichten. YS 58, 38v. Sieheauch BOYLE, Seasonal Residence, S. 146). ——《太宗纪》德译,第147页。
陈得芝《元和林城及其周围》:揭揭察哈~迦坚茶寒,是蒙语Gege(n)-chagha(n)的音译,意为“洁白”。揭揭察哈之泽即“洁白湖”,窝阔台与蒙哥每年春天多到这里游猎。扫邻城、迦坚茶寒殿即建于湖旁。据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一和《经世大典·站赤》中的“扫邻”,该词大约指驿站的顿舍,当为蒙文sa’urin的音译,有座位或驿站顿舍的意思。这里所谓“扫邻城”,应是大汗的春猎地行宫。《元史·地理志》未载筑扫邻城事,仅言“治迦坚茶寒殿”,本纪屡载太宗、宪宗春季猎于迦坚茶寒之地,亦未言及扫邻城。可见并无所谓“城”,大约只是建筑了一座宫殿,四周围一道围墙而已。拉施都丁《史集》记载说:“合罕(窝阔台台)命木速蛮(穆斯林)工匠于距和林一日程之地建造了一所宫殿”,这座宫殿就是迦坚茶寒,在今察罕泊西南。
周良霄译注《成吉思汗的继承者——〈史集〉第二卷》:按《元史·太宗纪》:九年夏四月,“筑扫邻城,作迦坚茶寒殿。”《新元史·地理志》:岭北行中书省,“丁丑,治迦坚茶寒殿,在和林北七十余里。”又《双溪醉隐集》卷二《取和林》:“和林城,苾伽可汗之故地也。岁乙未,圣朝太宗皇帝城此,起万安宫城。西北七十里有苾伽可汗宫城遗址。城东北七十里有唐明皇开元壬申御制御书阙特勤碑。”揭书中提及的坚察哈Gegen-chaghan无疑即苾伽可汗宫城遗址。原注(即波义耳的注释):此地名之第一部分布洛歇本作KR,维尔霍夫斯基本在译文中采之(Karchagan),然他的稿本作KНZ,其字形更接近于其原形KKН即Gegen chagan(意为“明亮和白色”。这明显地是哈剌和林以北二十五公里处至群湖的名称。它可能即在鄂尔浑河上近古畏吾儿都城Qara Balghasun)之附近。——第89页。
[2] [清]李文田《元史地名考》(第25页):《宪宗纪》:“尝攻钦察,其酋八赤蛮逃于海岛。”《西北地附录》有钦察,《醉隐集》:“麆沆,马挏也,以马乳为酒,愈挏治则味愈甘,甘谓之麆沆,奄蔡语也。奄蔡,西汉《西域传》无有,《大宛传》:‘宛王昧蔡。’师古曰:‘蔡,千葛切,《书》:“二百里蔡。”’毛晃韵:葛,桑葛切,广韵亦然,奄蔡,蔡,千葛切为是。今有其种,率皆从事挏马。”按耶律铸以钦察二字不古,当仍写《汉书》之奄蔡而读为钦察耳 ,沈壵云:“钦察部,近宽田吉思海,在斡罗思思西阿。”
沈垚《落帆楼文集》卷一二外集六《西北地名杂考》:“元钦察部近宽田吉思海,《速不台传》,癸未太祖十八年,速不台请讨钦察,许之。遂引兵绕宽定吉思海,展转至太和岭,凿石开道,出其不意。至则遇其酋长玉里吉及塔塔哈儿,方聚于不租河,纵兵奋击其众,溃走,矢及玉里吉子,逃于林间,其奴来告而执之。余众悉降,遂收其境。按太和岭有二,一在钦察境,《速不台传》所言是也;一在大同,《成宗纪》大德四年二月置西京太和岭屯田。《百官志》,太和岭千户所于大同路昌邑县本隘置司。又《地理志》,至元十八年从诸王阿只吉请自太和岭至别失八里置新站三十,亦大同之太和岭也。《土土哈传》,钦察去中国三万余里,夏夜极短,日暂没即出。《地理志》西北地附录,钦察属月祖伯分地。《朮赤传》,朮赤者,太祖长子也,国初以亲王分封西北,其地极远,去京师数万里,驿骑急行二百余日方达京师。朮赤薨,子拔都嗣,拔都薨,弟撤里苔嗣,撤里答薨,弟忙哥帖木儿嗣,忙哥帖木儿薨,弟脱脱忙哥嗣,脱脱忙哥薨,弟脱脱嗣,脱脱薨,弟伯忽嗣,伯忽薨,弟月即别嗣。盖自后部落遂以为号矣。月即别即月祖伯也。钦察去京师极远,则宽定吉思海去中国亦极远矣。《地理志》,岁丁酉,师至宽田吉思海旁,钦察酋长八赤蛮逃避海岛中,适值大风吹海水去,而干生禽八赤蛮。则海中有山,今塔尔巴哈台之西临边有巴尔噶什泊,泊中有山。
以钦察去京师三万余里较之,则宽田吉思海当尙在此泊之外,巴尔喀锡泊之东北千数百里有慈谟斯夸泊,中亦有山,其为元之宽田吉思海乎?慈谟斯夸泊之西北八九千里有额纳噶泊,中亦有山,以去中国三万余里言之,必额纳噶泊足当钦察之海,然其地益远矣。按钦察与斡罗思、阿速、康里诸国为邻,《元史》述征诸国事,《曷思麦里传》与《速不台传》正相倒,《速不台传》先钦察,而斡罗思、阿速;《曷思麦里传》由西域诸城转战而北,先阿速而斡罗思,而康里,而后钦察。两传所述,正一时事而先后乃相反,然《曷思麦里传》先言帝趣哲伯疾驰以讨钦察,则征钦察究在先,曷思麦里徇西域诸城而北先至阿速。则阿速在钦察之南,疑即今之哈萨克,阿速与哈萨音亦相近也。然则钦察在斡罗思之西,阿速之北矣,宽田吉斯海当于西北远地求之,意者额纳泊,其即八赤蛮所逃乎。”
按,钦察(Qïpčaq),突厥部落,操北部方言,居于今乌拉尔、伏尔加两河下游之间,里海北岸草原,元代有多种译名。
[3] 《考异》卷八六:按《元史》载征钦察事,纪、志、传互异,此纪及《宪宗纪》,俱以八赤蛮为钦察之酋长。《地理志》:太宗甲午年,命诸王拔都征西域钦叉、即钦察、阿速斡罗思等国。岁乙未,亦命宪宗往焉。岁丁酉,师至宽田吉思海傍,钦叉酋长八赤蛮逃避海岛中,适值大风吹海水去而干,生擒八赤蛮。亦与本纪略同。而《速不台传》则云岁己卯,太祖十四年。大军至蟾河,与灭里吉遇,尽降其众。其部主霍都奔钦察,速不台追之,与钦察战于玉峪,败之。癸未,太祖十八年。速不台请讨钦察,许之。遂引兵绕宽定吉思海,辗转至太和岭,凿石开道,出其不意。至则遇其酋长玉里吉及塔塔哈儿方聚于不租河,纵兵奋击,其众溃走。矢及玉里吉子,逃于林间,其奴来告而执之,余众悉降,遂收其境。乙未,太宗命诸王拔都西征八赤蛮,命速不台为先锋,与八赤蛮战,继又令统大军,遂虏八赤蛮妻子于宽田吉思海。八赤蛮逃入海中。然则钦察与八赤蛮,本是两部,速不台以太祖癸未平钦察,太宗乙未走八赤蛮,相距十有三年。而宪宗擒八赤蛮在丁酉岁,距钦察之平,盖已久矣。土土哈传,太祖征蔑里乞,即灭里吉。其主火都即霍都奔钦察,钦察国主亦纳思纳之。太祖命将往讨,亦纳思已老,国中大乱,亦纳思之子忽鲁速蛮遣使自归于太祖。而宪宗受命帅师,已叩其境,忽鲁速蛮之子班都察举族迎降。其叙被兵之状,与《速不台传》合,而酋长之名,彼此互异。且速不台平钦察之时,宪宗仅十六岁,初无受命帅师之事,而《土土哈传》并而为一,益不然矣。
《本证》卷一证误一:案《宪宗纪》亦以八赤蛮为钦察酋长。《地理志》“钦察”作“钦叉”,事与纪同。考《速不台传》,败钦察在太祖己卯,平钦察在太祖癸未。其征八赤蛮,则在太宗乙未,距钦察之平已十有三年。此以八赤蛮为钦察酋长,误矣。
屠寄《蒙兀儿史记》卷四《斡歌歹可汗本纪》:那诃通世引《多桑蒙古史》云:蒙古之军以一千二百三十六年夏间,进发。秋,拙赤之子斡儿朵(按,斡儿答)达不勒噶儿国,相近佛儿噶(按,伏尔加)河之畔。是冬,蒙古之诸王遣速不台击阿昔、不勒噶儿。速不台先进不勒噶儿,攻其都城,屠其民,又掠为奴隶,引去。有酋长二人,自诣诸王来降,赦之,既而复叛去。再遣速不台往,平之。喀喇姆津之《鲁西亚史》云:一千二百三十六年,巴提驻冬于佛儿噶河近旁。其地距不勒噶儿国都尚远。一千二百三十七年,其都始破坏。多桑依喇失惕书(按,即《史集》)谓,蒙古诸王军事会议定扩其军,如围猎然:广布其陈,分道决进。曼古率左军进向里海,擒乞魄察克之酋豪一人曰八出曼,并阿薛别部酋喀察儿斡果剌。先是,八出曼避追兵久之,沿路招集盗贼逃民,常苦蒙古军,时时掠夺行旅。匿于阿
提勒河(按,伏尔加河之突厥语名)畔之林中,屡变其住所,以故难于捕获。曼古乃制小船二百艘,每艘载百人,与弟不者克各率船队之半,分搜两岸之林。见一老妇,在蒙古新弃之营陈处,检觅遗物者。询之,据告八出曼已入岛,是处无一舟。曼古欲追不能,将折回矣。俄强风起,括水去。蒙古之军乃徒涉岛,出其不意禽八出曼,其众多溺死,兼被杀殆尽。八出曼愿手刃。曼古命不者克斩之,并阿薛之酋喀察儿斡果列云。
“不勒噶儿”即“不里阿儿”;“乞魄察克”即“乞卜察克”;“阿昔”、“阿薛”即“阿速”;“阿提勒河”即“亦的勒水”,佛儿噶河下游之名;“巴提”即“巴禿”;“曼古”即“蒙格”;“不者克”即“拨绰”;“巴出曼”即“八赤蛮”。
按旧史《土土哈传》,钦察国王名亦纳思;《速不台传》钦察酋名玉里吉。西域书及马札儿国史均谓乞卜察克王名库滩。而旧史《太宗纪》及《地理志》又曰,其酋八赤蛮。盖乞卜察兀为里海海北游牧大部。一大部中包有诸小部。犹之蒙兀一大汗国,内有众小汗也。库滩自是大汗,若亦纳思、玉里吉、八赤蛮,盖其别部之小汗耳。彭大雅:《黑鞑事略》云:“西北曰克鼻稍,初顺鞑,后叛去,阻水相抗。忒没真生前常曰:‘非十年功夫,不可了手。若待了手,残金又繁盛矣。不如留茶合镇守,且把残金绝了,然后理会。’癸巳年(1233)茶合□,尝为其太子所劫。”徐霆注云:克鼻稍,回回国,即回纥之穜。寄按,克鼻稍,即乞卜察兀之音差,其部本奉谟罕默德之教,故曰回回国。其人本五代时库莫奚穜,非回纥穜也。初顺鞑者,成吉思末年乞卜察兀尝为速别额台所征服也。阻水相抗云者,阻亦的勒河、宽田吉思海相抗也。其地为拙赤、巴秃父子所镇守,非察阿歹所镇守。《事略》所称茶合,当是传闻之误。癸巳年茶合为其太子所劫,中西书籍皆无征,然据西书称巴出曼招集盗贼逃民,常苦蒙古军,时时掠夺行旅,则癸巳年巴秃或尝为所困,未可知也。”——叶十二。
阿布拉莫夫斯基德译注(150):详见布莱特施乃德(按,《中世纪研究》,上、下卷,伦敦,1888年(Mediaeval Researches from Easternasian Sources, I u. II, London 1888)),页310—312;伯希和《库蛮考》,页166;志费尼书(按,波义耳英译本Juvaini, The History of the World-Conqueror, Manchester, 1958),页553正面;拉施都丁书,页58正面(按,其第二卷波义耳英译本The Successors of Genghis Khan,New York und London, 1971)(Einzelheiten bei BRETScНNEIDER, S. 310—312;pELLIOT,a propos des Comans,S. 166; JUVaINI, S. 553 f; RaSНID, S. 58 f). ——《太宗纪》德译,第147页。
夏四月,筑扫邻城[1],作迦坚茶寒殿[2]。
[1] 《圣武亲征录》:“丁酉,夏四月,筑扫邻城。”[清]李文田《元史地名考》(第25页):《辍耕录》“内八府宰相”条有云:“埽邻者,宫门外院官会集处也。”何秋涛《元史类编》云在和林北七十余里。
阿布拉莫夫斯基德译注(151):Sa’urin。从宫殿的蒙古语名称“Gegen chaγan”推断,两者均建于和林之此之湖边。试对照注(148)(按,指德译注)。《元史》,叶八,页三八上。试对照波义耳《窝阔台大汗的季节性居地》,页145—146(Sa’urin.vomnamen desPalastes, mong. “Gegen chaγan” herzu schliessen, wurden beide, Sa’urin und derPalast,
an den Seennördlichvon Qaraqorum (vgl.anm. 148) errichtet. YS S.8, 38v.vgl. BOYLE, Seasonal Residences, S. 145—146). ——《太宗纪》德译,第147页。
陈得芝《元和林城及其周围》:扫邻当为蒙文Sa’urin的音译,有座位或驿站顿舍的意思。这里所谓“扫邻城”,应是大汗的春猎地行宫。参阅九年纪事“揭揭察哈”注。
[2] 参阅九年纪事“揭揭察哈”注。
六月,左翼诸部讹言括民女。帝怒,因括以赐麾下[1]。
[1] 屠寄《蒙兀儿史记》卷四《斡歌歹可汗本纪》(叶十二):《秘史》:斡歌歹汗自言一件,听信妇人言,取斡赤斤叔叔的女子,即指此事。此议误。
阿布拉莫夫斯基德译注(152):据汉文史文此情节颇难理解,而在《卡尔辟尼游记》、志费尼书与拉施都丁书中有所描述。在斡亦剌忒部中谣传合罕要为其后宫选女。为了不碰上此事,斡亦剌忒人让他们的女儿们迅速热恋并成婚(Vom chinesischen Text her bleibt diese Eposode unverständlich. Sie w ird bei caRpINI, S.143 JUVaINI, S. 235, RaSНID, S. 93 geschildert; Unter den Oiraten sei das Gerüchtaufgekommen, dass der Qan Mädchen für seinen Нaremauswählen wolle. Umnicht davon betroffenzu werden, hatten die Oiraten ihre Töchter schnellverlobt undverheiratet)。——《太宗纪》德译,第147页。
宋子贞《耶律楚材神道碑》:太宗九年“侍臣脱欢奏选室女,敕中书省发诏行之。公持之不下,上怒,召问其故。公曰:‘向所刷室女二十八人尚在燕京,足备后宫使令。而脱欢传旨又欲遍行选刷,臣恐重扰百姓,欲覆奏陛下耳。’上良久曰:‘可。‘遂罢之。”
此事甚至传至西域,以致志费尼亦有记载:“在千户……的部落中,出现谣言说有招括该部的少女去配人。因为给这个消息吓坏了,人们就把他们的闰女在族内婚配,有些他们实际上是送上男家。有关的消息一口传一口,传到皇帝耳中。他派一队异密到那里去,调查此事。查明属实后,他下诏指导七岁以上的少女都集中起来,当年许配人从夫家追回。四千名各有打动男人心弦处的星星般少女,就这样聚集一处。……首先他命令把那些异密之女和另的分开来,接着所有在场者奉命糟蹋她们。其中两个月儿般的少女毙命。至于剩下的纯洁少女,他让她们在斡耳朵前列队,那些品貌堪充下降的送往后宫,另一些则被赐给豹子和野兽的看管人。还有一些赏给宫廷的各类奴仆,再有的送至妓院和使臣馆舍侍候旅客。至于那些仍然剩下来的,有诏叫在场的人,不分蒙古人和穆斯林,可以把她们带走。而他们的父兄、亲属和丈夫,观看着,不能透气或出声。这是他的诏令严厉执行,他的军队顺从的一个绝对证明。”——何高济汉译本,上册,第270页。何高济已发现与《太宗纪》所记系同一事件,并指“左翼诸部”为斡亦剌部,见页276,注(66)。
秋八月[1],命朮虎乃[2]、刘中[3]试诸路儒士,中选者除本贯议事官,得四千三十人[4]。
[1] 《庙学典礼》所记应与此事有关:丁酉年八月二十五日,皇帝圣旨道与呼图克、和塔拉、和坦、谔噜、博克达扎尔固齐官人每:自来精业儒人,二十年间学问方成,古昔张置学校,官为廪给,养育人才。今来名儒凋丧,文风不振。所据民间应有儒士,都收拾见数。若
高业儒人,转相教授,攻习儒业,务要教育人材。其中选儒士,若有种田者,输纳地税,买卖者,出纳商税,开张门面营运者,依行例供出差发。除外,其余差发并行蠲免。此上委令断事官蒙格德依与山西东路征收课程所长官刘中,遍[行]诸路一同监试,仍将论及经义、词赋分为三科,作三日程试,专治一科为一经,或有能兼者,但不失文义者为中选。其中选儒人,与各住处达噜噶齐、管民官一同商量公事勾当者,随后照依先降条理,开辟举场,精选入仕,续听朝命。准此。——《元代史料丛刊》,王颋点校,浙江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9页
[2] 《本证》卷三七证名一:术忽乃,选举志一科目。
阿布拉莫夫斯基德译注(153):有关朮虎乃无详情可提供。在《元史》卷八一也提到此次考选,此人作为断事官朮忽朮被提及(Über chu-hunai warnichts genaueres in Erfahrungzu bringen. In YS 81, 2v, woauchvon diesenPrüfungen berichtet w ird, ist erals tuan-shih-kuan (Richter) chu-hu Taiaufgeführt)。——《太宗纪》德译,第147页。
苏天爵《题咸淳四年进士题名》(《滋溪文稿》卷二九,陈高华、孟繁清点校本,中华书局,1997年,第491页):“我国家初定中原,岁次丁酉,诏遣断事官术虎乃宣差山西东路,征收课税所长官刘中遍诣诸路,收金遗士程试所学以复其家。”即此事。按,朮虎乃为聂思脱里教名,元代又常译写为朮忽难,操东部突厥语者往往读为“月合乃”(汪古氏马祖常的本名即此)等,今译为约翰。
[3] 刘中,阿布拉莫夫斯基德译注(153):刘中同样也无传;1230年他作为课税官司被置于宣德(参见德译页125)(Liu chung hat ebenfalls keine Biographie; er wurde 1230als Steuerbeam ter für Нsüan-te eingesetzt. (Vgl. S. 125))。——《太宗纪》德译,第147页。见前注。
[4] 《圣武亲征录》:“秋,八月,试汉儒,选擢除本贯职位。”
《元史》此处“得四千三十人”有误。据《元史》卷八一《选举志》“得东平杨奂等凡若干人,皆一时名士,而当世或以为非便,事复中止。”此次科举之事,《元史·选举志》与本卷记载相同,均在太宗九年,即1237年。但元好问撰《杨奂墓碑》载在戊戍年,即1238年。碑文见杨奂《还山遗稿》附录,《适园丛书》本。参见黄时鉴《元好问与蒙古国关系考》,《黄时鉴文集Ⅰ》,中西书局,2010年,第5页。
冬十月,猎于野马川[1]。幸龙庭,[2]遂至行宫。
[1] 阿布拉莫夫斯基德译注(154):蒙古语qulan,无法更准确地定位(Mong. qulan “W ildpherd”. Konntenichtnäher lokalisiert werden)。——《太宗纪》德译,第147页。
[清]李文田《元史地名考》(第25页):定宗元年,猎黄羊于野马川。明《岷峨山人译语》:“野马川在宣府西路膳房堡外。”不确,此野马川当在漠北和林附近。
据黄溍《宣徽使太保定国忠亮公神道碑》:“成宗宾天,公北迓武宗皇帝于野马川,归正宸极。” ——《金华黄先生文集》卷二四,四部丛刊本。
黄溍《敕赐康里氏先茔碑》(《金华黄先生文集》卷二八)也记,成宗逝后,海山听说太后在选择帝位继承人问题上犹豫,康里人阿沙不花“至野马川”。应即此。元明史料中有关此地的记载还可找到一些,兹不一一引述。
[2] 屠寄《蒙兀儿史记》卷四《斡歌歹可汗本纪》:龙庭指阔迭兀阿剌勒行宫,成吉思汗之大斡儿朵思。——叶十三。
阿布拉莫夫斯基德译注(155):“龙庭”此处似与成吉思汗之斡耳朵有关(“Drachenhof”(vgl.anm.61.) scheint sich hierauf das Ordovon Činggis Qanzu beziehen)。——《太宗纪》德译,第147页。
元好问《清真观记》(《元遗山集》卷三五,四部丛刊影明弘治本)记丘处机“往赴龙庭之召”,可见“龙庭”在蒙古国之初确指成吉思汗之斡耳朵。
是冬,口温不花[1]等围光州,[2]命张柔、巩彦晖[3]、史天泽[4]攻下之。遂别攻蕲州,降随州[5],略地至黄州。宋惧请和,乃还[6]。
[1] 成吉思汗异母弟别里古台次子。
[2] 阿布拉莫夫斯基德译注(157):今河南潢川县——《太宗纪》德译,第147页。
[3] 《元史》卷一六六有传。
[4] 《元史》卷一五五有传。
[5] 阿布拉莫夫斯基德译注(161):光州之西,今湖北——《太宗纪》德译,第147页。
[6] 阿布拉莫夫斯基德译注(162):《宋史》卷四二(本纪)未提及求和及蒙古人撤军之事(SS (pen-chi) 42, berichetnichtvon einer Bitte um Frieden odervon einemabzug der Mongolen)——《太宗纪》德译,第147页。
《元高丽纪事》(叶六)记此年及此前事:八年至九年,攻拔归信城、金山城、金洞城。
十年戊戌春,塔思[1]军至北峡关[2],宋将汪统制[3]降。
[1] 为木华黎子查剌温的突厥语名称。查剌温为蒙古语čila’un之音译,汉言“石”;塔思对应于突厥语taš,意亦为“石”。
[2] 阿布拉莫夫斯基德译注(164):地在安徽舒城县南四十里。——《太宗纪》德译,第147页。
[3] 当为时任南宋两淮统制职之汪怀忠。
夏[1],襄阳别将刘义叛,执游显等降宋。宋兵复取襄、樊[2]。帝猎于揭揭察哈之泽。筑图苏湖[3]城,作迎驾殿[4]。
[1] 《元高丽纪事》记此年夏事:十年戊戍五月十二日,降旨,宣谕高丽新降人赵玄习、李元祐等。时玄习辈率二千人迎军降,命东京安置,受洪福源节制,且降御前银牌,使玄习等佩之,以招来降户民。寻又有李君式等十二人来降,亦依玄习例抚慰之。且谕唐古,就活里察时磨里地,取洪福源族属十二人付之。——叶六。
《大元马政记》:太宗皇帝十年戊戍六月二日,降圣旨:宣谕札鲁花赤胡都虎、塔鲁虎□、讹鲁不等节该。自今诸路,应有系官诸物,及诸投下宣赐丝线匹段,并经由燕京、
宣德、西京经过。其三路铺头口,难以迭办。今验紧慢定立铺口数目,验天下户数,通行科定,协济三路通该旧户二百一十七户四分著马一匹;新户四百三十四户八分,著马一匹;旧户一百六十九户二分,著牛一头;新户三百三十八户四分,著牛一头。圣旨到日,仰即便差人,与各路差去人,一同前去所指路分,著紧催促验数,分付各路收管。见得以南路分马匹牛畜难得,今约量定立到马一匹,价银三十两;每牛一头,价二十两。仰各处皆验燕京,酌中时直,折纳轻赉匹段、沙罗、丝线、绢布等物,用铺头口转递交付,却令三路置库收贮。明附文历支销回易诸物。于迤北民户内,逐旋倒换头口用度。若各自愿计置头口分付者,听从民便。不得因而刁蹬抑勒,多要轻赉。除各路别给御宝文字外,据燕京路合得协济路分,开具下项。东平府路所管州县城,验户二十三万四千五户免征外,实征二十二万八千七百三十五户。内有本路课税所从实勘当新旧户记,照依铺头口分例,另行科征送纳。总合著马七百八十八匹五分五厘,牛一千一十七头二分四厘。旧户一十一万五千二百四十七户,合著马五百二十九匹一分五厘,牛六百八十一头八分。新户一十一万三千四百八十八户,和著马二百五十九匹四分,牛三百三十五头四分四厘。民户二十三万二千六百二十九户,重数户课税所户在内摽拨与宗王口温不花、中书吾图撒合里,并探马赤查剌温火儿赤一千七百五十八户,内民户一千七百一十二户,驱户四十六户。民户内,旧户八十一户,新户一千六百三十一户。宗王口温不花拨讫一百户,内旧户三户,新户九十七户。中书吾图撒里合里拨讫新户三百四十五户。禿赤怯里马赤拨讫新户六户。查剌温火儿赤件等回回大师拨讫新户三十户。讹可曹王拨讫新户一十户。罗伯成拨讫新户三户。夺活儿兀兰拨讫新户七户。查剌温火儿赤并已下出气力人拨讫一百八十五户。乞里并已下出气力人拨讫三百三十六户。内旧户三十八户,新户二百九十八户。笑乃并已下出气力人拨讫四百六十七户。内旧户二十七户,新户四百四十户。孛里海拔都拨讫一百户。课课不花拨讫五十五户。合旦拨讫一百一十六户,内旧户一十一户,新户一百五户。外驱户八十二户,回回户九十六户,打捕户二十户。——第4页。
[2] 钱大昕在其《复襄樊年月不同》中曾辨析过克复襄樊事:
“《宋史·理宗纪》:淳祐十一年(1251)十一月京湖制司表都统高达等复襄樊。按《纪》于端平三年(1236)失襄阳之后,至此始书复襄樊。而《元史·太宗纪》乃云:戊戌(1238)即嘉熙二年岁,襄阳别将刘义叛,执游显等降宋。宋兵复取襄樊。《孟珙传》亦云:嘉熙三年(1239)正月,刘全复莫城,遂复襄阳。虽有一年之差,然较之高达复襄樊,相去至十二三年。意者嘉熙收复之后,仍不能守,至高达始有之乎?《元大一统志》:端平丙申(1236)襄阳失守,淳祐辛亥(1251)高达复襄,亦不载嘉熙收复事。盖自刘义降宋以后,元已弃襄而不有,亦不立镇戌。至淳祐辛亥,始复屯驻重兵于此,非以兵力取之。在宋虽有拓边之劳,在元未有失地之实也。《元史·宪宗纪》不载高达取襄樊。盖自戊戌(1238)以后,襄樊已为宋土矣。又考姚燧撰《邓州赵长官碑》云:乙未(1235)太子南征还,令邓、均、唐三州民徙雒阳西三县。明年丙申(1236),襄樊亦徙雒阳。是丙申襄阳失守之时,蒙古已徙其民子,雒阳区区空城,本不作留成计也。”——《十驾斋养新录附余录》卷八,《竹汀日记抄》,清嘉庆刻本,上海图书馆。
[3] [清]李文田《元史地名考》:揭揭察哈即前文迦坚茶寒殿所由命名也,此于泽畔再筑一城而名曰迎驾,则在中站可知。《地志》云:“戊戍,营图苏湖迎驾殿,去和林城三十余里。”——第25页。
阿布拉莫夫斯基德译注(168):图苏湖八里,按志费尼与拉施都丁的说法,在哈剌和林以东约7英里处,《元史》卷五八指出超过30里。参见波义耳:《窝阔台合罕的营地》,页146;柯立甫:《德黑兰博物馆的蒙古文文献》,《哈佛亚洲研究》,卷16,页90(Tuzγu Baliq;nach JUVaINI und RaSНID etwa 7 Meilen östlichvon Qaraqorum, YS 58, 38 b gibtals Entfer(n)ung über 30 lian. Siehe BOYLE, Seasonal Residences, S. 146; cLEaVES, Mongolian Documents in the Musée de Téhéran, НJaS 16,S. 90)。——《太宗纪》德译,第148页。
陈得芝《元和林城及其周围》根据《世界征服者传》、《史集》、《元史》的记载认为:从汪吉东营地返和林,走的是南北向的路,图苏湖城似应在和林之南。危素《危太朴续集》卷七,《耶律希亮神通碑》记载希亮“生于和林城南四十里之禿忽思凉楼”。“禿忽思”当系“禿思忽”之误。罗洪先《广与图》于和林之南标有“禿思忽凉楼”,即此。所谓“凉楼”,是文人妄加“雅名”,实际上牛头不对马面。这个和林城南的禿思忽凉楼,应该就是上述的图苏湖城(迎驾殿)。只是《耶律希亮碑》所记的里数较《元史》和《史集》多一些。
[4] 《圣武亲征录》:“戊戍夏,筑禿思儿忽城。”
秋八月,陈时可、高庆民[1]等言诸路旱蝗,诏免今年田租,仍停旧未输纳者,俟丰岁议之[2]。
[1] 王国维《耶律文正公年谱》:《送燕京高庆民行》。——《王国维遗书》第十一册,上海古籍书店,1983年版,第20页。
[2] 至于此月元与高丽往来,《元高丽纪事》:十年戊戍“十二月二十四日,遣其将军金宝鼎、御史宋彦琦等,奉表入朝”。——叶六。
十一年己亥春,复猎于揭揭察哈之泽。皇子阔端军至自西川[1]。
[1] 《圣武亲征录》九年“冬十一月,[曲]赤{曲}、{阙}[阔]端等克西川”。
至于此月元与高丽往来,《元高丽纪事》:十一年己亥四月,奉旨遣宝鼎僚属校尉黄贞允、义州别将朴希宝,从诏使先还。五月一日,降诏,征入朝曰:前来颁降长生天之圣训去后,尔不为听从,为尔不行省悟,是以出军进讨,明致天罚。尔又不即迎军出降,并无出力供职之辞。乃敢窜诸海岛,苟延残喘。昔降宣谕,命汝亲身入朝,却令还国。此诏见在彼中,若能钦依元降诏旨,躬亲赴阙,所有一切法制宣谕了毕,即当班师。尔等违背诏书,辄来奏告,乞令军马回程,于理未应,此非尔等之罪也。如此诏谕,尔等或有违贰,我朝安能知之。上天其监之哉。十一日,诏告取洪福源族属。六月,遣其礼宾卿卢演、礼宾少卿金谦,充进奉使副,奉表入朝。——叶六。
秋七月,游显自宋逃归。以山东诸路灾,免其税粮[1]。
[1] 《元高丽纪事》:十一年己亥“九月,宝鼎、彦琦,从诏使还国。十月十三日,降旨,宣谕曰:据来具奏悉,云缅贡诚忱,辄中感戴,已具陈于前表。据回降宣谕,已令元
使赉去。又奏先妣柳氏倾逝,仰瞻天阙,未有所诉。如有所奏,实能拜降出力。仰于庚子年亲身朝见,但有条画事件,至日省谕。如违元表,诬奏,我国焉能知,上天其监之。”——页七。
冬十一月,蒙哥率师围阿速蔑怯思[1]城,阅三月,拔之。
[1] 《本证》卷四九证名十三:灭怯思,昔里钤部传。[清]李文田《元史地名考》(25页):阿苏,《西北地附录》云阿速亦以水为名,今俄罗斯阿速海。《明史·外国传》:“阿速近天方撒马儿罕,幅员甚广,城倚山面川,川南流入海,有鱼盐之利,不宜耕牧 。”又沙哈鲁在阿速西海岛中。又(第26页):蔑怯思城,《昔里铃部传》作灭怯思,《土土哈传》作麦怯斯,《拔都传》作麦各思, 明艾儒略《职方外纪》有莫斯哥未亚国,此城当即其地。按,《明史》与《职方外纪》所云皆不确。
屠寄《蒙兀儿史记》卷四《斡歌歹可汗纪》:城名据昔里钤部旧《传》、太宗旧《纪》同。即蒙文《秘史》所谓蔑格惕也。但旧《纪》书是役于己亥冬十一月,而钤部旧《传》亦云:己亥冬十一月至阿速蔑怯思城,负固久不下。明年春正月,钤部率敢死士十人,蹑云梯先登,俘十一人。大呼曰:“城破矣!”众蚁坿而上,遂拔之。与《纪》年月合。然按多桑书依辣施特说,谓:一千二百三十八年,即太宗十年戊戍冬,失班、不者克、不里侵臣察克之别部蔑哩姆国。巴儿孩败奇魄察克,禽其别部蔑克哩惕之酋长。冬,曼古、不哩、喀丹共攻曼噶思城。围之六重而后取。
按,“失班”即“昔班”;“不者克”即拨绰;“不哩”即“不里”;“巴儿孩”即“别儿哥”;“曼古”即“蒙格”;“喀丹”即“合丹”;“臣察克”即“乞卜察兀”;“曼噶思”即“蔑怯思”异文。据此,则旧史纪传攻围蔑怯思年月误差下一年。又按“蔑怯思”,《定宗纪》作木栅寨,《土土哈传》作麦怯斯,《拔都儿传》作麦各思,蒙文《秘史》作蔑客秃,又作蔑格惕。阿不勒弗荅引亦奔赛笃书曰:阿阑之主要寨名曰马速的,为世界坚城之一。此寨在阿阑国喀卜克山之闲,大河之畔,云卜列惕施乃迭儿,曰马速的城,在帖列克河上游。喀自别克山坿近有名之荅哩额勒山峡,盖即抹哈蔑愓教徒之地理家巴必阿勒阑所谓“阿阑之门”,古史之珀儿荅高喀昔亚云:马速的,即蔑思愓异文。马速二字,与《定宗纪》之木栅音尤近。喀卜克,即喀别自克,亦即吉利吉思山。——叶十四。
阿布拉莫夫斯基德译注(172):灭怯思阿兰人在高加索地区的都城,参见《秘史》第275节;布莱特施耐德《中世纪研究》,卷二,页84—91等。关于此役的准确年份,史料说法不一。这里所言之1239年,为《昔里钤部传》(《元史》,百衲本卷一二二,叶十三b—叶十四b)所支持。而在《新元史》卷一○六《拔都传》(叶四a—叶十a),称为1238年,《史集》(页60)亦如此(Meges. Die Нauptstadt deralanen im Kaukasus.vgl. GG 275; BRTScНEIDER II, S. 84-91, I 316. Über das genaue Jahr, in dem die Belagerung stattfand, herscht in den Quellen keine übereinstimmung. Das hierangegebene Jahre 1239 w ird durch dir gleicheangabe in der Biographievon Нsi-li ch’ien-pu (YS 122 13r-14 r) gestützt. In der Biographievon Batu (НYS 106, 4v-10v) w ird das Jahr 1238 genannt, ebenso RaSНID, S. 60)。——《太宗纪》德译,第148页。
十二月,商人奥都剌合蛮[1]买扑[2]中原银课二万二千锭,以四万四千锭为额,从之[3]。
[1] 刘迎胜《旭烈兀时代汉地与波斯使臣往来考略》:太宗时代的奥都剌合蛮应与忽必烈时代派去波斯查计忽必烈在波斯的份子收入的奥都剌合蛮区别开来。据《史集·部族志》(波斯文合校本,页四五五,页五二二;汉译本,页三〇七)、《史集·忽必烈合罕纪》(见德黑兰一九五九年刊本,页六四七;俄译本第二卷,页一七一至一七二;英译本,页二七〇至二七一),阿里不哥失败后,旭烈兀去世之前,朝廷与伊利汗国有一次极为重要的使臣往来,忽必烈派赤老温之孙撒礼答以及奥都剌合蛮去波斯,而伊利汗国派伯颜来华报聘。志费尼的《世界征服者史》和《史集》第二卷的英译者波义耳都认为忽必烈时代的奥都剌合蛮就是太宗旧臣、乃马真皇后摄政时受到重用的奥都剌合蛮。而《史集》(德黑兰刊本,第一册,而五七〇;《史集》第二卷,俄译本,页一二〇;英译本,页一八三)记载贵由汗即位后,下令将华北地区的行政权归牙老瓦赤,并处死了奥都剌合蛮,因此,忽必烈派到波斯会计大汗份子的奥都剌合蛮与太宗时代的奥都剌合蛮是两个人。——中国蒙古史学会编《蒙古史研究》第二辑,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28—29页。
同氏:“奥都剌合蛮,(‘abdal-Rahmām),‘abd, 阿拉伯文,译言奴隶、仆人;al,定冠词;Rahmām,意为仁慈的。‘abdal-Rahmām,译言仁慈之仆。今写作阿卜拉·拉赫曼。刘敏中《南京路总管府事赵公神道碑中》(《中庵先生刘文简公文集》,元刻本,卷七,页十五)又译作奥都鲁哈蛮。——见《元代摄思廉、益绵、没塔完里及谟阿津等四回回教职考》第186页注释,载《西北民族文丛》,1984年,第二期,第176-192页。
[2] “买扑”一词,查龙潜庵编著《宋元语言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85年),袁世硕主编《元曲百科辞典》(山东教育出版社,1989年),卜键主编《元典百科大辞典》(学苑出版社,1991年),李修生主编《元曲大辞典》,凤凰出版社,2003年)均未收入。买扑又写作扑买。《吏学指南》卷七《钱粮造作》:“扑买,即包议办纳也。”(元刻本,北京图书馆),即指断买断,此系宋代旧制。
[3] 有关西域人扑买中原课税事,宋子贞《耶律楚材神道碑》记:戊戍(1238)“燕京刘忽笃马者,隂结权贵,以银五十万两扑买天下差发。涉猎发丁(Sharafal-Din)者,以银二十五万两扑买天下系官廊房、地基、水利、猪鸡。刘庭玉者,以银五万两扑买燕京酒课。又有回鹘以银一百万两扑买天下盐课,至有扑买天下河泊桥梁渡口者。公曰:‘此皆奸人欺下罔上,为害甚大。’咸奏罢之。尝曰:兴一利不若除一害,生一事不若减一事。人必以为班超之言盖平平耳,千古之下自有定论。’……初公自庚寅(1230)年定课税,所额毎歳银一万定。及河南既下,户口滋息,増至二万二千定。而回鹘译史安天合至自汴梁,倒身事公以求进用。公虽加奖借,终不能满望,即奔诣镇海,百计行间。首引回鹘奥都剌合蛮扑买课税,増至四万四千定。公曰:‘虽取四十四万亦可得,不过严设法禁,隂夺民利耳。民穷为盗,非国之福。’而近侍左右。皆为所,上亦颇惑众议,欲令试行之。公反复争论,声色俱厉。上曰:‘汝欲闘搏耶?’公力不能夺,乃太息曰:‘扑买之利既兴,必有蹑迹而簒其后者,民之穷困将自此始。’于是政出多门矣。”(谢方录文将“于是政出多门矣”断为楚材语,置括弧内——《湛然居士文集》谢方点校本,中华书局,1986年,页332。)
奥都剌合蛮原系商人,其得用系安天合推举。安天合原为金译史,金亡后归蒙古求进用。其名“天合”当为聂思脱里教名Denha。爱薛有子名“腆合”(《文宗纪》又写为“典
哈”),此即此名。
参见舒尔曼《〈元史·食货志〉译注》,第3—4页。
关于此月蒙丽关系,《元高丽纪事》(叶七):十一年己亥“十二月十二日,遣其新安工王恮,与宝鼎、彦琦等一百四十八人,奉表入贡” 。
十二年庚子春正月,以奥都剌合蛮[1]充提领诸路课税所官[2]。皇子贵由克西域[3]未下诸部,遣使奏捷[4]。命张柔等八万户伐宋[5]。
[1] 《本证》卷三七证名一:奥鲁剌合蛮、耶律楚材传。奥都剌、刘敏传。奥鲁合蛮、刘秉忠传。
[2] 《圣武亲征录》:“己亥。庚子春正月,命暗都剌合蛮主汉民财赋。”
赵琦《金元之际的儒士与汉文化》:【波斯】志费尼:《世界征服者史》(何高济据波伊勒英译本译,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1部第34节《脱列哥那哈敦》:“有个叫法蒂玛的女人,她在脱列哥那哈敦手下获得巨大的权势,……她提拔奥都剌合蛮,把他派到契丹去代替马合木(即马合木牙老瓦赤)。”牙老瓦赤在1241年受命“主管汉民公事”,出任燕京行省,但很快罢任(参见蔡美彪:《脱列哥那后史事考编》,《蒙古史研究》第3辑)。奥都剌合蛮并非由于法蒂玛的关系才受任用,他在太宗末期就已主管中原地区课税事。但牙老瓦赤下台后,由他接替出任主管中原事物的燕京行省是有可能的。——第43页。
李庭秀“丁酉(1237,太宗九年),兼权本路征收课税副官。戊戍(1238),升郎中,提控左右司。时公方四十,已兴怀止足。后二年(1240,太宗十二年),宣差提领诸路课税所,以公廉悉著,特授监□平阳路征收课税官” 。——同恕《中书左右司郎中李公新阡表》,《榘庵集》卷五,四库本。这里提到的李秀庭的上级“宣差”,当即奥都剌合蛮。
[3] [清]李文田《元史地名考》:《耶律希亮传》云:“叶密里城,乃定宗潜邸,汤沐之邑也”云云。意当时克西域时所居与。不确,此处西域指“长子西征”之地,即钦察、斡罗思、孛烈儿及马札儿等地。——第26页。
[4] 阿布拉莫夫斯基德译注(175):此为一则有关这位储君贵由的极为强调的证词。而业已言及的抱怨其在西征中的行为的原由,则出之于《秘史》第275—277节( Dies is eine sehr belastendeaussage über denzukünftigen Kaiser Güyük. Dass seinverhalten bei dem Feldzug im Westenanlasszu Klagen gegeben hatte, gehtaberaus GG 275—277 deutlich hervor.)——《太宗纪》德译,第148页。按,《秘史》有关贵由的贬义描述,当系蒙哥即位之后史臣所改,不足据。
[5] 《元高丽纪事》:十二年庚子三月,瞮遣右谏大夫赵修、门只候金城宝等,奉表贡献。五月,诏谕瞮曰:所奏事具悉,语皆不实。如果无虚诈,尔等若能依元奏之事,又何难见。止为合车、箚剌已死,奏此谄妄之语。知此事之人俱在,尔等所奏,先曾出力之事,我非童穉,岂能欺我哉!自先出力之事,我亦知矣。来章赞祝,更复何言。我国处正宣谕如此,依其所奏,悉能无二,固可嘉尚。若果无二心,迁出海岛民户,悉令见数。如差去使臣未到间,切勿令出。候使到日,然后出迁。令使臣一一点数,据谕去使臣(来)[未]到间,切勿令之出言。尔等勿谓不令出海,止是伺候使臣到日迁出,仍令一就点数民户毕,然后出海。据海内所有民舍,尽令烧毁。尔等必有再往之意,如再入海,必有拒敌之谋。若
将民户数目隐匿,依大朝条例治罪。其民户见数,据合出禿鲁花人数,然后明降谕去。出海抚定之后,别无详细人使,继岁取发贡赋。如不出海,以大军攻取。又昌朔州民户来宾,尔等辄将家口杀掠。据擅行杀掠之人,岂非罪欤?将为首始谋万户、千户官员人等,仰捉拏发遣前来。尔等既称一国,一国之中,岂有此事。彼处被劫落后流移人数,尽数刷集分付。如将行劫之人,不行捉拏发遣。及将流移民户,故不起发,岂为出力供职之事耶?如尔等教令杀掠,故不捉拏。若不曾教令,必捉拏分付。著古欤之事,当时尔等特頼亏加下所违德愆,除已发罪讫,即目犹似亏加下出理。伐亏加下罪时,曾助多少军马。今后既为一国,凡有来宾人民,邀当匪当也。若将大国条画抗拒,必有叛背之意。迁出海岛,点数民户,出禿鲁花,捉拏有过之人,惟此四事谕去,何足多言。如能出海,数见户数,出禿鲁花。凡有条画,至是省谕,及汝弟恮口奏告,有兄瞮令奏:凡有皇帝圣训,必不违背。据奏过事目别录付去,汝当知之。如此宣谕,却行不出海岛来奏云,必不违背。如是却违前言,我国焉能知。上天其监之。攻拔昌州等处。——叶七—八。
冬十二月,诏贵由班师[1]。敕州郡失盗不获者,以官物偿之。国初,令民代偿,民多亡命,至是罢之[2]。
[1] 阿布拉莫夫斯基德译注(177):对比布莱特施耐德《中世纪研究》,卷1,页318,注758. 拉施都丁系此事于1240年,然而后来(其书第176—177页),他又说,在其父去世的那个时刻(1242)年,他尚未从钦察返回。(Vgl.BRETScНEIDER I. S. 318,anm. 758. RaSНID (60f) bringt dies unter dem Jahr 1240. Doch weiter hinten (S. 176-178)sage er, Güyük seizumzeitpunkt des Todes seinesvaters (1242)nochnichtaus Qipčaqzurückgekehrt)。——《太宗纪》德译,第148页。
[2] 宋子贞《耶律楚材神道碑》“国初盗贼充斥,商贾不能行,则下令凡有失盗去处,周岁不获正贼,令本路民戸代偿其物,前后积累动以万计。及所在官吏取借回鹘债银……”《神道碑》未言民户逃亡及官吏借回鹘银的原因。对照《太宗纪》可知,所积债务,当系民亡无处追偿所致;而官吏贷回鹘银系因为耶律楚材要求官代为偿还而造成。
至于此年此月其他事,《通制条格》记:庚子年十二月十八日,怀州刘海奏:王荣未反已前定女师哥为妇,不曾娶过。王荣反背,今将王荣男断与纯赤海,合无成亲。准奏。反背的人孩儿,怎生将有功的人女孩儿与得?刘海你不寻思有功的儿嫁与那什么?——黄时鉴点校,《元代史料丛刊》,浙江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48页。
是岁,以官民贷回鹘金偿官者岁加倍,名羊羔息,其害为甚,诏以官物代还,凡七万六千锭。仍命凡假贷岁久,惟子本相侔而止,著为令[1]。籍诸王大臣所俘男女为民。
[1] 《黑鞑事略》:“其贾贩,则自鞑主以至伪王、诸伪太子、伪公主等,皆付回回以银,货之民而衍其息,一铤之本展转十年后,其息一千二十四铤。”——明嘉靖二十一年抄本,北京图书馆。
宋子贞《耶律楚材神道碑》:“及所在官吏取借回鹘债银,其年则倍之,次年则并息又倍之,谓之羊羔利,积而不已,往往破家散族,至以妻子为质,然终不能偿。公为请于上,悉以官银代还,凡七万六千定。仍奏定,今后不以岁月远近,子本相侔,更不生息,遂为定
制。”该神道碑与苏天爵《元名臣事略》置此事于丙申年(太宗八年,1236)。
《元史》卷一五二《王珍传》:“岁庚子,入见太宗,授总帅本路军马管民次官,佩金符。珍言于帝曰:‘大名困于赋调,贷借西域贾人银八十铤,及逋粮五万斛,若复征之,民无生者矣。’诏官偿所借银。复尽蠲其逋粮。”
罢羊羔息之事,影响甚大,西域亦闻之。志费尼记:“契丹国有一座叫太原府(*Tayanfu)的城市,该地的百姓提交一份申请说:‘我们欠了八百巴里失的债,它将使我们遭到破产,而我们的债主正在要求偿还。倘若降旨叫我们的债主宽限我们一个时期,那么我们能够还步偿还他们,将不会破产流离。’合罕说:‘如果我们叫他们的债主宽限他们,他们要蒙受巨大损失,但如我们置此事于不顾,百姓又将倾家荡产。’他因此命令出一个告示,在整个国内公布说,凡有债权者可提出契约,要么负债者可指出债主,他就可以从国库领取现金。’那从未关闭的国库大门,大大敞开,于是百姓们前去领取巴里失;很多人没有债务,装成债主和负债者,也领取巴里失;因此他们所得倍于所求……”——《世界征服者史》汉译本,上册,第246页。
“在《合罕言行录》一章中,志费尼极力颂扬窝阔台的乐施好善。除去那些浮夸之辞和不实之处外,这章内包含了窝阔台统治时期的一些重要史实。其中有如下一个有趣的事件。志费尼说,在契丹国有个叫做☒,aYM‘W的城市 ,该城的居民上书称,他们欠了八百八里失的债,请求下诏给债主,缓期归还。窝阔台说,如果叫债主缓期,那债主要受到损失,如果置之不理,那人民又要倾家荡产,因此好心的窝阔台吩咐从国库中偿付。诏令一下,欠债的和收债的都前去国库领取现金。这个故事,我们从《元史》中找得到若干条例证,例如,《太宗本纪》曾载录……
志费尼提到的城名☒,aYM‘W,波伊勒把它订正为☒,aYNFW,即Tayanfu,山西的太原府。这个订正是缺乏根据的。志费尼书的各个抄本在著录这个地名时均保留了鼻音M,拉施特的《史集》同。维尔荷夫斯基俄译拉施特书把这个地名转写为Tai-m in-fu,至少拉施特书的一个抄本实作此形(维尔荷夫斯基译拉施特书,第52页,注(57))。志费尼书的一个抄本(D本)作☒,aNMΓW,我们可以把它看作是Tam infu的讹误。从这些线索看,志费尼所说的这个城市,不是山西的太原府,而应为河北的大名府,志费尼和拉施特均无错误。按《元史》卷一百五十二《王珍传》载:‘岁庚子(1240),入见太宗,……珍言于帝曰:大名困赋调,贷借西域贾人银八十铤,及逋粮五万斛,若复征之,民无生矣。诏官偿所借银,复尽蠲其逋粮。’这里说的官司偿所借银,和志费尼的记述颇有相同之处,但志费尼的记述更为生动和详细。大概在窝阔台统治时期,确实有过由政府偿还大名府百姓欠债的事。”——《世界征服者史》汉译本,上册,译者序,第8—9页。
西域人本息迭加的羊羔息,人皆知其害,但在元代并未因太宗的命令而绝迹。王磐《史天泽神道碑》(《元文类》卷五八)提到,宪宗时“兵火之余,民间生理贫弱,往往从西北贾人借贷,周岁辄出倍息,谓之羊羔利。稍积数年,则鬻妻卖子不能尽偿。公奏:乞令民间负债出息至倍则止。上从之,遂为定法”。
《平章廉文正王》(苏天爵《元名臣事略》卷七)引廉希宪《家传》亦记宪宗时“富民贷
钱民间,至本息相当,责入其本,又以其息为券,岁月责偿,号羊羔利。其征取之暴,如夏以火迫,冬置凌室,民不胜其毒。公正其罪,虽岁月愈久,毋过本息对偿,余皆取券焚之。后著之令” 。
十三年辛丑春二月,猎于揭揭察哈之泽[1]。帝有疾,诏赦天下囚徒[2]。帝瘳。
[1] 蒙语Gege(n)-chagha(n)的音译,意为“洁白”。
[2] 《耶律楚材神道碑》记:“辛丑(1241)春二月,上疾笃,脉绝。皇后不知所以,召公问之。公曰:‘今朝廷用非其人,天下罪囚必多冤枉,故天变屡见,宜大赦天下。’因引宋景公荧惑退舍之事,以为证。后亟欲行之,公曰:‘非君命不可。’顷之,上少苏,后以为奏,上不能言,颔之而已,赦发,脉复生。”
[1] 阿布拉莫夫斯基德译注(181):参见享通《高丽——蒙古入侵》,莱顿,1963年,第105页,第118页,注13,14(Siehe hierzu Нenthorn, Korea, S.105, 118 (anm.13,14))。——《太宗纪》德译,第149页。
冬十月,命牙老瓦赤[1]主管汉民公事[2]。
[1] 《本证》卷三七,证名一:牙剌瓦赤、宪宗纪元年。牙鲁瓦赤、世祖纪、刘敏、姚枢传。
[2] 《圣武亲征录》:“冬十月,命牙老瓦赤主管汉民。”
牙剌瓦赤/牙老瓦赤(Yalawač),花剌子模人,与其子麻速忽均为蒙古国重臣。
[1] [清]李文田《元史地名考》:《宪宗纪》:“诸王大会于阔帖兀阿阑,共推即位于斡难河。”此纪之劕铁渱胡兰山,即斡难河之濶帖兀阿阑也。《辍耕录》:“太宗崩于胡阑山。”——第26页。
屠寄《蒙兀儿史记》卷四《斡歌歹可汗本纪》:义谓冷红山,旧《史》作劕铁钴胡兰山,今依《秘史》译例改正。《蒙古游牧记》云:赛因诺颜中前旗牧地,跨济尔玛台河、鄂尔昆河、翁金河西北至奎屯岭,注右翼中右旗界。按,奎屯,蒙兀语冷,异文为阔迭兀,即此阔迭兀忽剌安山也。——叶十五。屠寄所释不妥。
突厥语Ötegü qulan,见伯希和《马可波罗注》(Notes on MarcoPolo,Paris, 1959),页321;阿布拉莫夫斯基德译注(183):无法确定大致地望。(nichtnäherzu lokalisieren)——《太宗纪》德译,第149页。
陈得芝《元岭北行省建置考(上)》:讹铁钴胡兰山在《元史·宪宗纪》里作月帖古忽兰Ötegü qulan,意为老野马,也是从前克烈可汗的驻冬营帐所在地,一二五三年末卢勃鲁克所到的蒙哥汗营帐应即此地,其地理位置大约在翁金河上游。
[2] 前已提及,据《耶律楚材神道碑》,回回译史安天合依靠耶律楚材政敌镇海得用,并引奥都剌合蛮扑买课税。太宗嗜饮贪杯与奥都剌合蛮有很大关系。奥都剌合蛮在任真定课税所长官时,曾向太宗进酒。据刘敏中《少中大夫同知南京路总管府事赵公墓道碑铭》记载:“公讳□,字君宝,世家弘州,后徙燕,遂为燕人焉。公资开敏刚正,未冠失父,与兄璧侍母避乱,迁魏,又迁长安。益长,辞母东游,过真定,寓神霄宫,掌教识其先世,怜之,留使从学,遂至于有立。始以真定课税所辟干靖海场盐官,市帛当送输京。众惮之,公独请行。既输,从领省奥都鲁哈蛮觐和林。一日,太宗方宴,缚领省出锢,直庐中,莫测所以罪。从者皆散匿,独公在侧。领省勉使去,竟弗动。翌日,内出酒一碗,敕领省饮。酒墨色,知赐死,领省伏饮,公从旁亦取饮。既移晷,静无所觉。敕使视之问曰:向酒汝所进,果何酒也?领省悟,对曰:臣所进尊白金,新制药淬,未久渉远,故酒败色渝,斯诚臣罪当死。帝悉其诚,释之。领省义公异常人,奏授领中书郎中以归。”——《中庵集》卷七,元刻本,第15页。
因所进酒变质色黑,太宗盛怒,命将奥都剌合蛮缚帐中,并以所进酒赐死。后因奥都剌合蛮饮后并无不良反应,才释罪。
关于此人的进一步细节,见刘迎胜《旭烈兀时代汉地与波斯使臣往来考略》中《两位奥都剌合蛮辨》一节,原文刊于《蒙古史研究》第2辑,1986年,收于氏著《蒙元帝国与13—15世纪的世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北京,第25—27页。
[3] 太宗嗜饮曾遭耶律楚材劝阻。《耶律楚材神道碑》记:“上素嗜酒,晚年尤甚,日与诸大臣酣饮。公数谏,不听。乃持酒槽之金口曰:‘此铁为酒所蚀尚如此,况人之五脏有不损耶?’上悦,赐以金帛,仍敕左右日进酒三钟而止。”
[4] 《耶律楚材神道碑》记:“冬十一月,上勿药已久。公以太一数推之,奏不宜畋猎。左右皆曰:‘若不骑射,何以为乐?’猎五日而崩。”太宗丁亥(1241年12月7日)大猎,庚寅(12月10日)还,辛卯(12月11日)凌晨去世,前后合计确为五日。
[5] 《圣武亲征录》“十一月初七日,至地名月忒哥忽阑,病。次日崩,寿至五十六,在位一十二年。”此“月忒哥忽阑”,即前文中提到之“讹铁钴胡兰山”,《宪宗纪》中作“月帖古忽兰”,原名为蒙古语Ötegü qulan,此言老野马。
[6] 阿布拉莫夫斯基德译注(185):伯希和与同黑尼士(见《大亚洲》卷9,第549页)一样,支持起辇谷并非一个蒙古语地名的音译,而意为“在那里抬起大车的峡谷”,也就是说,是将轻车抬入墓地的地方。(《马可波罗注》,第330—332页)。而波义耳认为,很可能窝阔台与贵由不同于成吉思汗与其他蒙古皇皇帝一样葬于自己的地方(即不儿罕·哈剌敦),而是在其新疆北部的斡儿朵地区(《窝阔台大汗的葬地》,第50页)(pELLIOTvertritt w ie НaENIScН (inasia Major 9, S. 549) die ch’i-lien sei keine Transkrition für einem mongolischen Ortsname, sondern bedeutte “das Tal, wo man den Karren hebt”, d.h. wo der Leichenwagen ins Grab gehoben w ird. (Notes, S. 330-332). BOYLE hält es für wahrscheinlich, dass Ögedei und Güyüknichtam selben Ort w ie Činggis Qan und dieanderen mongolischen Kaiser (alsoam Burqan Qaldun) begraben wurde, sondern
im Gebiet ihres Ordo innor-Sing-kiang. (The BurialPlace, S. 50) )。——《太宗纪》德译,第149页。
陈得芝《成吉思汗墓葬所在与蒙古早期历史地理》(《中华文史论丛》二〇一〇年第一期,总第九十七期,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古籍出版社主办 《中华文史论丛》编辑部出版, 2010年3月20日,第11页):据载,太祖成吉思汗以下蒙元诸帝均葬于此(其实太宗窝阔台和其子定宗贵由没有葬在这里)。学界对这个地名曾有过多种说法。有些学者认为应该是指克鲁伦河上游肯特山南坡的某处谷地,这是综合了《史集》和《黑鞑事略》的记载得出的,就大范围而言基本正确;或以“起辇谷”为克鲁伦(Kelüren)的音译,推论的方位大抵与此同。还有学者以“起辇谷”为汉语,意为“乘辇起程的山谷”。亦邻真在《起辇谷与古连勒古》(《起辇谷与古连勒古》,《内蒙古社会科学》1989年第3期;又见《亦邻真蒙古学文集》,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747—753页)一文中,评论了前人对此地的各种个说法,提出新说:“起辇谷”是音译名,就是《圣武亲征录》所载“曲邻居山”、《元朝秘史》(明初汉译本)作“古连勒古”(Gürelgü)的同名异译。其语言学、历史学的论证都十分精到,令人信服。《元朝秘史》多处记载到这个地名,使我们可以据以判断其方位。第89节载:(帖木真逃出泰赤兀人的囚禁后,溯斡难河上游支流乞沐儿合小河寻找母、弟)“在那里相会之后,便到不儿罕·合勒敦山阳的古连勒古之中桑沽儿小河的合剌只鲁干的阔阔纳兀儿,扎下营盘”(明初音写“古连勒古”、“合剌只鲁干”均旁注“山名”)。第94节、122节、129节、141节都记载有这两个地方,或注“山名”,或注“地名”。在这里,帖木真被追随他的蒙古各氏族头领推举为“汗”(qan),订下盟约,并指派了佩弓箭、佩刀和管饮膳、马群,负责哨探等人员,建立起蒙古乞颜部贵族联盟,据有克鲁伦河上游各地,包括萨里川(今克鲁伦河、土拉河上游间地)。可以说,古连勒古是蒙古乞颜氏和成吉思汗的始兴福地,徐霆所谓“相传忒木真生于此,故死葬于此”,应该是“兴于此,故死葬于此”。蒙古考古学家丕尔烈认为这个地名应是指东经109度/北纬48度、曾克尔河上游流域一片相当大的地段;亦邻真参照其说定为曾克尔满达勒一带(注释:亦邻真《起辇谷与古连勒古》)。综观《秘史》各节记事,其地应在“不儿罕山前(南)”,是可以容纳众多牧民居住的水草丰富的原野,曾克尔满达勒一带位于肯特山南麓,原野宽广,符合“古连勒古”之地的条件。《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七册所标“曲邻居山”(古连勒古)方位大体不误,似略偏北。作为成吉思汗及蒙元诸帝葬地的“起辇谷”来说,还要具备文献所载“平原”地形和能够挖掘较深墓穴的土层条件。总之,在曾克尔河中上游一带的肯特山南麓坡地寻找蒙元诸帝墓葬,方位应该大致不误。
帝有宽弘之量,忠恕之心,量时度力,举无过事,华夏富庶,羊马成群,旅不赍粮,称时治平。
(本文作者为南京大学元史研究室/民族与边疆研究中心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