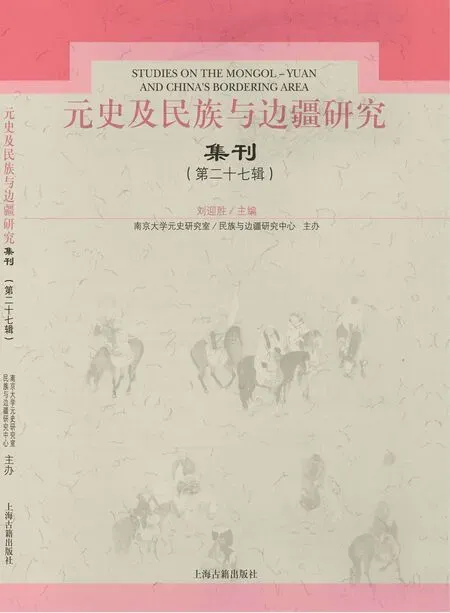《辍耕录》的两个问题
——摘叶著书与抄录他书
高建国
《辍耕录》的两个问题
——摘叶著书与抄录他书
高建国
《南村辍耕录》是元代一部非常有分量的私人笔记著作。关于其成书,历来流传着“摘叶著书”的故事。历代学者在关注其丰富的史料记载的同时,也指出该书存在着抄录他书的问题。本文通过辨析,指出“摘叶著书”的“叶”字,并非是树叶之叶,而是“书页”之意。通过仔细的数据统计,本文指出《辍耕录》一书抄录的部分,占到全书约29%的内容。笔者在检讨了陶宗仪的史学态度后认为,对《辍耕录》中的抄录问题,无须苛责。
辍耕录 摘叶著书 抄录
元末明初的隐士学者陶宗仪,留下一部有名的笔记小说——《南村辍耕录》,这部笔记,以其30卷的部头和182条有关蒙元史的记录而备受元史研究者的关注。本文在前人研究基础上,着重讨论《辍耕录》成书的传奇故事——摘叶著书和抄录他书的问题。
一、 摘叶著书之“叶”字辨析
隐居云间的陶宗仪,“读书养素,得其趣则曳杖于松蹊菊圃之间,疲则箕踞于平坡磐石之上,或登高眺远,则九山之秀与目谋,泗水之清与心谋,林木之蔚茂者与神谋也。”a[清]卞永誉《式古堂书画汇考》卷五一《南村记》,《文渊阁四库全书》。 [明]徐伯龄《蟫精隽》卷一三《南村外史传》,《文渊阁四库全书》。“艺圃一区,果蔬薯蓣,度给宾祭巳。余悉种鞠,栽接溉壅,身自为之。间遇胜日,引觞独酌,歌所自为诗,抚掌大噱,人莫测也。”b[明]孙作《沧螺集》卷四《陶先生小传》,《文渊阁四库全书》。“凡见闻所及必录而识之,耕暇,则课家童灌花莳菊,与野人方士饮酒为乐。”c[清]卞永誉《式古堂书画汇考》卷五一《南村记》,《文渊阁四库全书》。 [明]徐伯龄《蟫精隽》卷一三《南村外史传》,《文渊阁四库全书》。友人孙作在为陶宗仪《南村辍耕录》所作序文中说:
余友天台陶九成,避兵三吴间,有田一廛,家于松南。作劳之暇,每以笔墨自随。时时辍耕,休于树阴,抱膝而叹,鼓腹而歌。遇事肯綮,摘叶书之,贮一破盎,去则埋于树根,人莫测焉。如是者十载,遂累盎至十数。一日,尽发其藏,俾门人小子萃而录之,得凡若干条,合三十卷,题曰《南村辍耕录》。d[明]孙作《沧螺集》卷四《陶先生小传》,《文渊阁四库全书》。
这段记载,就是为后人所津津乐道的“摘叶著书”的故事来源。按照现代白话文的意思来理解,大体就是说,陶宗仪在劳作之余,休息于树底下,遇到觉得重要的事情,就抬手
摘片树叶记在上面,然后随手扔进事先放在树低下的大缸中。这样经过十年的积累,他让弟子们把树叶都拿出来,把上面的文字都抄录下来,于是就有了《南村辍耕录》这部很有意思的笔记小说了。
这段记载,被后来学者广为引用。清代邵元平在著述《元史类编》时,就引录了这段文字,“每记一事辄摘叶书之”。不过邵元平似乎还没有说明摘的是树叶还是什么。1958年中华书局将其作为元明史料笔记的一种而点校出版,在卷首的“出版者说明”中说:“这部《辍耕录》据说就是在松时所作,他每当空暇的时候,经常在树荫下摘采树叶子来做笔记,写完了贮放在盆内,十年间他放满了十几盆,抄录下来编成三十卷,名曰《南村辍耕录》。”a[明] 陶宗仪《南村诗集》,《文渊阁四库全书》。 [清]叶德辉《书林清话》,北京燕山出版社,1999年,第25—26页。1982年《语文教学与研究》第五期刊载了钱元杰《耕余信笔著文章——陶宗仪与〈辍耕录〉》一文。绘声绘色地讲述了陶宗仪采摘树叶记录文字的故事。1984年永力在《逻辑与语言学习》第一期中再次讲述了陶宗仪采摘树叶著书的故事。
如果要说陶宗仪经十年积累终不放弃的话,这个故事很动听很适合。但是,后人均说陶宗仪采摘树叶记录文字,这恐怕就值得商榷了。不要说具有科学知识的现代人,就是在清代,就有人为此而辨析过。清代卢文弨在《抱经堂文集》卷十一中就说:“孙大雅序谓:‘其拾树叶而书之。’夫树叶非竹简羊革比也,其能容百名以上乎?殆同戏论。”b[清]卢文弨《抱经堂文集》卷一一《辍耕录跋》,见于《续修四库全书》。2003年,《光明日报》发表东方龙吟《树叶与书叶》一文,对此问题,就曾发表意见。
要打破“摘叶著书”的传说,关键在于理解其中的“叶”字的含义。用今天的话来理解,必为树叶之意。可是如果我们拿今天的话来理解古籍,就要闹笑话了。关于“叶”字的意思,清代学者叶德辉在《书林清话》一书当中,有详细的说明。大意是说,在当时世俗称一张纸为一页,但是“页”字在《说文解字》当中,乃是“稽首”之“稽”本字,与书页没有关系。而用“叶”来表示书页,自有书本就有这种称呼。“叶”字的本字,乃是“枼”。“一叶之叶本当做枼,亦取其薄而借用之,非其本意如此也。吾尝疑叶名之缘起,当本于佛经之梵贝书,释氏书言西域无纸,以贝多树叶写经,亦称经文为梵夹书,此则以一翻为一叶,其名实颇符。”c[明] 陶宗仪《南村诗集》,《文渊阁四库全书》。 [清]叶德辉《书林清话》,北京燕山出版社,1999年,第25—26页。叶德辉也进一步指出:“古者简籍之式,或用竹或用木。竹以一简为一葉,木以一版为一葉。” 《树叶与书叶》一文已经指出,其实早在唐代以前,中国人便有了“书叶”的历史。该文并据《邵氏闻见录》指出在印刷术兴起之时,“宋元印书,已经在外口印有一、二、三等数字,但它都称‘叶’。因为‘叶’有正反两面,这与当时折起来装订的书籍正相吻合。许多‘叶’合装成册,称作‘叶子册’d东方龙吟《树叶与书叶》,载《光明日报》2003年6月19日版。。”也即在印刷术兴起后,“叶”用来表示如今“页”字的意思。关于这一点,我们在阅读古籍时,就可以留意到确实如此,甚至在清末人曾纪泽的日记中,还在使用“叶”字来表示“页”字的意思。
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再来看孙作原文的意思,就是说陶宗仪经常以笔墨自随,在耕作之余暇,休息于树荫之下,听到什么、看到什么以及想起什么,都会随手抽取一页纸片,记录下来,放在所谓的“盎”里并且埋在树底下。十年之间,他积累了十几“盎”的卡片资料,最后一起搬出来,整理成书,这就是《南村辍耕录》。所以说他是随手抽取了一张纸
片,是因为《南村辍耕录》三十卷中,每卷都是由若干不成系统的条目组成,而每条条目的字数,从几十个字到上千字都不等。如卷六“奴材”条:“世之鄙人之不肖者为奴材。郭子仪曰:‘子仪诸子,皆奴材也。’”全部才进二十三个字,而综观《南村辍耕录》一书,多数都是这种卡片资料形式的记录。
所以“摘叶书之”,应该理解为“拿了张纸把这件事记录下来”,而不是神神秘秘地说摘了片树叶把字写在上面,然后又埋在“盎”里,这样理解简直就是“怪力乱神”。一个很明显的证据,就是陶宗仪同时代的学者就没有误解孙作的意思,檇李贝琼所撰的《南村外史传》说:“有田廛,筑草堂以居,闭门著书,自号南村外史。凡见闻所及必录而识之,耕暇,则课家童灌花莳菊,与野人方士饮酒为乐。”明人凌迪知的《万姓统谱》说:“陶宗仪……然雅好著述,虽在畎亩,恒以笔砚自随。尝预置一瓮于树间,遇有所得辄书以投其中,久之,遂取次成帙,名曰《南村辍耕录》行于世。”清代编纂的《浙江通志》也持此说。以上诸说,都没有说写在树叶上面的疯话。
二、 陶宗仪的史学态度
《辍耕录》自问世以来,受到历代学者的关注。然而学者们对这部书的褒贬,各有不同。褒扬者称该书是一部“百科全书式的著作”,而自明代郎瑛以来的贬低者,矛头都对准了《辍耕录》抄录他书这个问题。经笔者统计,《辍耕录》共抄录《山居新话》45条,抄录《遂昌杂录》14条,抄录《广客谈》7条,全文抄录或者部分抄录前人笔记等作品46条,转录友人讲述以及前人诗文、公文有57条。《辍耕录》全文共计585条,抄录的条目共计有169条,占了《辍耕录》全书条目约29%。
“史料笔记均为私人著述,是作者将生活中所见、所闻、所历得来的材料书之于笔端而形成的著述。其内容有的得之于眼见,有的得之于耳闻,有的得之于身历,有的得之于书本。其书法或随笔直录,或精司考析。”a王雄《古代蒙古及北方民族史史料概述》,内蒙古大学出版社,第104—105页。 [元]邵亨贞《南村辍耕录疏》,见《南村辍耕录》,四部丛刊三编本。其中也不乏抄录的例子,但是像《辍耕录》这样大部头的史料性书目,其中竟有约29%的条目可以被视为抄录,不禁让人怀疑“在何种程度上,某一部作品算是作家个人的创作,而不仅仅是杂抄呢?”b[德]傅海波《杨瑀和他的〈山居新话〉》,北京师范大学古籍与传统文化研究院编《中国传统文化与元代文献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论文集》第二辑,中华书局,2009年,第903页。对此,笔者想先就陶宗仪在《辍耕录》中所流露出来的历史态度,做一番考察。
陶宗仪为什么要创作《辍耕录》?摘叶著书的故事,只能提供给我们这样的信息:陶宗仪是一个笔耕不辍的有心人。他的“有心”,正如其好友邵亨贞在《辍耕录》的序文中所说的那样“朋游间咸欲为之版行以备太史氏采择”c王雄《古代蒙古及北方民族史史料概述》,内蒙古大学出版社,第104—105页。 [元]邵亨贞《南村辍耕录疏》,见《南村辍耕录》,四部丛刊三编本。,也就是说陶宗仪有一种保存史料的写作态度。他的这种态度,在《辍耕录》中多处强烈地流露了出来。
在《辍耕录》中很多条的条末,有陶宗仪的个人评论,其中有几条条末有“南村野史曰”这样的评论形式,很像司马迁《史记》卷末的“太史公曰”。这些条目分别是卷八“志苗”,卷十“越民考”和卷十四“忠烈”条。“志苗”记述了至正末年江南大乱,官府无力镇压而借助杨完者所率领的苗兵,结果导致引狼入室。杨完者部众烧杀抢掠无恶不作,甚至
劫持了江浙行中书省丞相达识帖木儿以邀取官位,杨完者最终导致民官俱愤而兵败自戕。陶宗仪在其后的“南村野史曰”中首先严厉批评了元朝将相的愚昧短见,他说:“为之将若相者,在于明黜陟,严赏罚,奉将天威,降者招之,逆者讨之,以培国家之本,可也。顾于此而不为,又无他奇谋远略,而乃借重于非类,正犹开虎儿之匣而使赴犬羊耳。尚冀保民命,为社稷计,一何愚哉。”同时对于烧杀抢掠的苗兵自取其亡的罪行也进行了论述,尽管有为杨完者开脱的倾向,但是陶宗仪在最后说:“吾恐国家之本,铲刈殆尽。虽有智谋之士,亦无如之何矣!天乎人乎?吾不得而知也。”虽然他说未来局势不能预见,但是他已经敏锐地感觉到元朝根本已经动摇,即使有智谋之士也回天无力了。
卷十“越民考”记述了绍兴路录事司达鲁花赤迈里古思的事迹。当杨完者部众在绍兴路荼毒民众的时候,迈里古思以一介文人之肩,聚众保乡,得到越民的爱戴和朝廷的重用。御史大夫拜住哥想要拉拢迈里古思而遭到严厉拒绝,最后迈里古思被拜住哥用卑鄙的手段杀害,越民闻之如丧考批,帮助迈里古思部将黄中为其复仇。陶宗仪在“南村野史”中评论说:
……夫迈里古思受任之初,殊有古贤县令之风。一握兵柄,志满意得,酣觞废事,轻谋首乱,不旋踵而身首异处,盖亦平昔越己之过有以酿成此祸与?微中,则老母稚子亦皆几上之肉耳!原其忠君爱民之心。欣然与日星相昭明者,则无可议也。拜住为国大臣,坐镇四省,百官庶司,孰不听令?迈之不奉台檄,擅兴师旅,明问其罪,黜之可也,斩之可也,而乃阴结小丑,作为此态,是盗杀之,非公论矣。民心之所以不服,良以是也。噫!享有尊爵重禄,而当国步艰难之日,既不思涓埃补报之道,又不责自己贪饕之非,反以谋害忠良为先务,谓之无罪,得乎?故其妻妾子女遭罹戮辱,实自取之,尚复可怜哉?
陶宗仪对迈里古思的成功与失败做了两面的评述,对于黄中不杀拜住哥的做法也给予赞誉。对于不顾大局、谋杀忠良而祸民误国的拜住哥,则给予了严厉的批评。所以清代李慈铭在《越缦堂读书记》中说道:“九成天台人,故载元末江浙事尤详。若张士诚之起事,及取浙西诸部之本末;杨完者之功罪;迈里古思之被祸,皆详载曲折,得是非之公。”a[清]李慈铭《越缦堂读书记》卷八,中华书局,2006年,第987—989页。
卷十“忠烈”条,记述了五位烈士在元末战乱中为大元王朝尽忠而死的事迹。“南村野史曰:
天下之事战争,十有余年于兹矣。为臣辱国,为将辱师,败降奔窜,不可胜计。甚者含诟忍耻,偷生冒荣,以为得志,名节大闲,一荡去弗顾。求其忠义英烈,于千百之中莫克什一。噫!忠义英烈虽出于天性,要亦讲之有素,处之甚安。故于造次颠沛之际,决然行之而无疑。如李总管黼、王州尹伯颜、樊参政执敬、张御史桓、林教授梦正、萧处士景茂之杀身成仁,视死如归,是必讲之熟而处
之当。一旦出于人所不肯为,遂以惊动天下,而精英忠烈之气在宇宙间与嵩华相高者,自不容泯。若桓之居在闲地,乘之久坐废黜,梦正之分颛讲教,视握将帅之权,受民社之托,任大而责重者,有间矣。一皆从容就义,是尤难也。景茂,里中一儒生耳。初未尝得斗升之禄以养其父母,尺寸之组以荣其身,始于保民,终于保国,临大节而不可夺,古称烈丈夫,又岂能过是与?至于子为父死,妇为夫死,声光赫奕,照映史册,使百世而下,知纲常大义之不可废,天理人心之不可灭如此,其有功于名教为何如。是亦深仁厚泽涵养所致,孰谓百年之国而无人哉!
虽然陶宗仪的评论原则不出儒家君臣纲常的范围,可是笔者认为这些死于大义的烈士、义士,是应该得到陶宗仪这么高的赞誉的。
以上几条,陶宗仪都以“南村野史曰”的形式,在条末做了恰当的评论。而其实在《辍耕录》中很多条的条末,陶宗仪都表达了自己的看法,只是没有用到“南村野史曰”这样形式。比如在卷一“独松关”条末,就有这样的评论:
宋之亡也,非有桀纣之恶,特以始之以拘留使者,肇天兵之兴,终之以误杀使者,激世皇之怒耳。藉使独松之使不死,宋之存亡未可知。其亦有数也与。
古人常用“天数”的迷信来解释王朝的兴亡更替,在同卷的“宋兴亡”条,陶宗仪这样说:
宋之兴,始于后周恭帝显德七年,恭帝方八岁。及其亡也,终于少帝德祐元年,少帝时四岁名显。而显德二字,竞与得国时合。周以主幼而失国,宋亦以主幼而失国;周有太后在上,宋亦有太后在上。始终兴亡之数,昭然如此。
这样的言论在今天看来几近于荒谬迂腐,但是毕竟我们不能苛求古人。
综上所述,在《辍耕录》许多条目中,陶宗仪都有自己的评论,尤其是像带有“南村野史曰”这样评论形式的条目,更是显示了陶宗仪保存史料的努力和近乎史学家风范的态度。
三、 对《辍耕录》抄录问题的态度
鲁国尧在《陶宗仪〈南村辍耕录〉等著作与元代语言》一文中说:“需要指出的是,《录》中有些关于元代的条目源于其师友笔记或文集,陶氏引录或改写,但未言明……”《历代笔记概述》一书评价说:“《辍耕录》是一部有参考价值的书,其中也夹杂着不少神怪迷信和琐屑无聊的记载;摘引前人述作,不标书名,亦属一般笔记的通病。”其实早在清代的卢文弨,对这个问题已经做过评价:“郎仁宝讥其巢《广客谈》以为己说,此自秦汉以来诸子之书已有互相出入者,即郎氏《七修类稿》中不亦有闲取是书者乎?然所著书家,诚能自抒新得,不袭陈编,更足贵也。”a[清]卢文弨《抱经堂文集》卷十一,《续修四库全书》。这样看来,后人在研究的过程中,不仅已经
充分注意到了《辍耕录》的这个缺点,并且能够以批判的态度宽恕这个缺点,进而肯定了《辍耕录》全书所载史料的价值。
古代社会,因为受到历史条件的限制,知识分子的文化交流活动,最多地体现在诗酒唱和的活动当中。笔记小说的出现,是对这种单一的交流方式的一种历史突破。通过这种自由的记载形式,知识分子随意记录下了当时社会的一些重大事情、奇闻轶事、个人学术思考以及儒家思想所提倡的忠臣烈妇故事。因此,同一故事出现在不同的笔记当中,也就不足为奇,而出现抄录问题,也是一种必然了。以《东园友闻》和《南村辍耕录》为例:
《东园友闻》也是记载元代史实的私人笔记。它的作者,一般认为是陶宗仪的朋友孙道易——它的成书时间要比《辍耕录》晚近三十年。根据《学海类编》本《东园友闻》的记录,全书只有二十二条故事,而其中与《辍耕录》相同的故事就有十三条之多。其中除第十二条后明确注明“南村陶宗仪书”外,其它十二条相同的内容,虽然所记故事相同,但是从其注明的出处、文字的规模以及语序上来看,明显不存在抄录问题。陶宗仪和孙道易是好朋友,年龄也相差不多,他们生活的时代背景是一样,两人不约而同地记录下了一些有影响的史实,这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了。比如说世祖年间江南释教总统杨琏真珈发宋陵寝、南宋灭亡时死于贞烈的五位女性的故事,这两件事情,前者从事实上严重践踏了儒家思想的君臣纲常理论,后者却又极强地增添了儒家忠臣烈妇思想的光辉。所以这两件事在元明之际的笔记小说中,因为知识分子的相互谈论和抄录而被广泛地记录下来。
所以笔者认为,对于《辍耕录》中大量抄录它书的这种行为,我们也不能给予苛责,因为以当时文化交流的形式来看,以陶宗仪隐士的身份来获取资料,最好的办法也许就是如此了。而在元代为数不多的文人笔记资料中,《辍耕录》在规模上远远凌驾于别书之上,它的价值是应该得到后人肯定的。
(本文作者为延安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讲师、博士)
Two Problem s onnancun Chuogenglu: Picking off Leaves for W riting Booksand Copy Others
Gao Jianguo, center for Mongolian Studies, Inner Mongliia University
Nancun Chuogenglu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historical materials on the studying of Yuan history. There wasalwaysa story “picking off leaves for w riting books”about this book’s compilation. Since the late imperialPeriod, many scholars hadPaidaattention on the contents of this book, meanwhile theyPointed that many contents of this books indeed copied from others. ThisarticlePoints that in thePhrases “picking off leaves for w riting books”, the correct form wasPage (页),not leaves (叶). Besides, statistics shows that 29% of the contents were from others books.
nancun chuogenglu ,Picking off leaves for w riting books, cop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