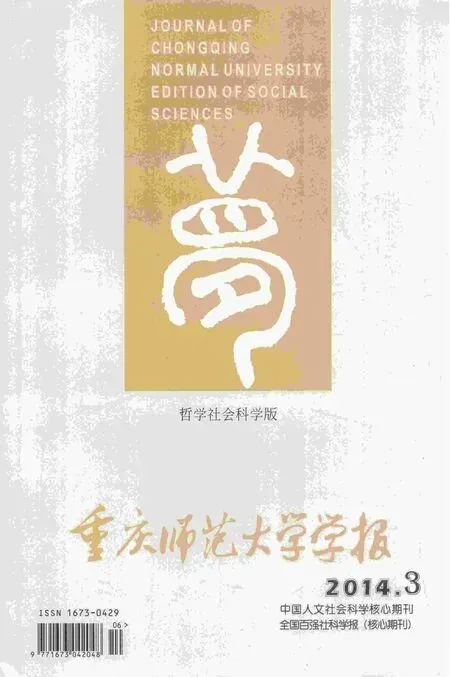哈奇森、休谟、边沁与哲学功利主义的兴起
汶红涛
(长安大学 政治与行政学院,陕西 西安710064)
在近代功利主义的兴起和形成中,古希腊的快乐主义、近代洛克的新经验主义认识论以及英国情感主义道德理论都为其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尤其是英国情感主义道德哲学将情感作为道德之基础的思想,为功利主义从功利性角度解释道德行为与道德现象提供了理论模式。但在这一过程中,休谟作为一个关键的过渡性角色,长期以来被研究者们所忽略。尤其是从哈奇森到边沁完备的功利主义体系的形成过程中的诸多延续和脉络,休谟从中所起到的作用和扮演的角色不容忽视,因此,对这一过渡性意义的探讨是极为必要的。
一、哈奇森的“道德感”理论
哈奇森作为苏格兰启蒙哲学的开创者,第一个在道德基础问题上提出了自己的原创性理论。“道德感”理论是哈奇森哲学的核心理论。“道德感”一词在苏格兰启蒙哲学语境中译为“moral sense”,意在强调道德感是一种感觉器官。但这一概念并不是哈奇森首创,而是由莎夫茨伯利于1709年提出。哈奇森这一理论的确立,有两方面的来源:一是近代洛克的经验论,二是莎夫茨伯利的道德理论。根据洛克的经验主义认识论,人类的观念主要来自对外界事物的感知所获得的感觉以及人对自身心灵的反思。哈奇森承认洛克的观点,认为一切观念都来自感觉与反思,但他认为,我们的每一种简单观念都对应着一种感觉器官,除了外部感官之外,还有“内部感官”如“道德感、美感等,而这与我们对洛克所谓的第二性的质的感知十分相似。哈奇森确信这些内部感觉和外部感觉并无二致。因此,在他那里,道德感就是一种与外在感官相对应的内在感官,是人类心灵具有的天然的知觉能力。这样,哈奇森在人性的生理机能上为道德感找到了合法性依据。
与霍布斯认为“人从根本上是自私的和反社会的”的观点不同,莎夫茨伯利认为人类有着丰富的情感,这些情感使人类成为天生的群居动物。关于自然情感和道德之间关系问题是莎夫茨伯利道德理论的特色所在。莎夫茨伯利认为,人天生具有趋善避恶的能力。[1](129)人具有一种能感悟道德善恶的内在感官——道德感。人的这种内在道德感如同人的眼睛和耳朵等外部感官对美丑的直接分辨一样,也能直接感觉出行为善恶的性质。因此,人们对道德善恶的感知不是凭借理性的推理,也不是经验归纳的结果,而是人的内在感官的直接感悟。但莎夫茨伯利没有详细论证道德感究竟是如何分辨善恶的。情感与理性也常常交织在一起,没有清晰的界定。换言之,莎夫茨伯利并未明确表示道德的基础究竟是理性还是情感。哈奇森进一步完善和发展了莎夫茨伯利的观点。首先,他承认我们对道德善恶的知觉来源于人的道德感。但他认为道德感与外部感官不同,外部感官的职能是感知外物对自己有利或有害,而内在的道德感知觉到的是道德上的善与恶。道德感的本性是见德则爱之,见恶则恨之。从哈奇森对洛克与莎夫茨伯利的理论的继承和发展,可以确定:第一,道德感是一种判定善恶的内在感觉器官;第二,道德的基础究竟在于理性还是情感,莎夫茨伯利并未明示,而哈奇森则明确表示,道德感是道德判定的基础。
那么,道德感究竟具有什么样的特点?如何进行道德判断呢?哈奇森强调说:“所谓道德感,只不过是我们心灵在观察行为时,在我们判断该行为对我们自己为得为失之前,先具有的一种对行为采取可爱与不可爱意见的作用。”[2](790)既然道德善恶的判定不是依赖于利益考量,那么,如何才能权衡德行,进行道德判定呢?哈奇森认为是“仁爱”。“仁爱”是哈奇森道德哲学中最核心的概念。哈奇森认为,仁爱是一种“本能”,它“先于理性而始于利益”[1](123),但又弱于利己。仁爱普遍存在于激励人们的各种情感或激情中,驱使我们发现自然之善,并为他人谋取幸福。哈奇森道德哲学的基本观点是:仁爱是所有德性的基础。也就是说,在道德评判上,只有完全排除利益考量而出于仁慈动机的行为才是德行。一切有道德价值的行为都应当是出于仁爱的情感,“凡一切被认为出于这样的感情,对某些人为仁爱,同时又不危害他人,这种行为,在道德上便是善的。”[2](801)因此,在哈奇森的道德哲学中,仁爱是道德感的对象,它不是利己的附属品,“倘若某种行为可以揭示施动者的善意或仁爱,即为他人谋幸福之愿望,则当这种行为在我们的头脑中形成观念时,与这些观念相连的快乐之感便能呈现德行的观念”。[1](130)以仁爱作为道德感的对象,权衡行为善恶,必然排除理性在感知善恶或判定某种行为是否德行中具有决定权的可能。但哈奇森并不排除理性可以修正我们的道德感和外部感觉,理性在道德评判中的作用是有限的,理性不能让我们感知到善恶。
从哈奇森的论述可以明显地看出,道德善恶的判断是一种纯粹情感的活动,是一种与自爱、理性无关的情感感知活动,因此,道德感理论实质上是一种以情感为核心的感情主义伦理学。哈奇森不仅确定了道德感是道德判定的基础,而且进一步明确了道德感的涵义和特点,即道德感是一种以仁爱为对象的情感,这种以仁爱为对象的道德感是道德判断和道德区分的依据和基础。相较于莎夫茨伯利,哈奇森第一次明确地将“情感”作为道德判定的基础,提出并确立了“情感高于理性”的信念,以及情感在人性构成中的基础地位,从而否定了理性在道德判定中具有决定权的观点。因此,哈奇森的道德感理论开启了理性主义道德理论向情感主义道德理论的转向,同时,为后来更为体系化、明确化的休谟的情感主义道德哲学产生了重要影响。
二、休谟的“效用”概念:向功利主义的过渡
休谟赞同并接受了哈奇森关于“道德感普遍存在于人心中”的观点,同样认为道德感是一种情感,是行为者的行为或品格在我们心中引起的快乐与不快乐的情感,道德评判就是以此为依据。但是,在确定了道德判断的基础是情感之后,休谟便与哈奇森分道扬镳了。
《人性论》第三卷“道德学”(of morals)是休谟第一次系统论述其道德哲学和政治哲学的部分。在第一章“德与恶总论”中,休谟明确地探讨了道德的基础和区分问题。首先,休谟回应和批判了道德理性论者将理性作为道德基础的观点,同时界定了理性的适用范围、功能及其界限。在“道德学”的第二节中,休谟从正面强调了道德区分的情感基础:“由德发生的印象是令人愉快的,而由恶发生的印象是令人不快的”[3](510),而这些区别道德善恶的印象,“只是一些特殊的痛苦或快乐(particular pains or pleasures)”[3](498),即特殊的苦乐感。所以,区分道德善恶的机制在于人类的情感,休谟将这一区分道德善恶的情感机制称为“道德感”。在《道德原则研究》中,休谟提出了四种道德评价的标准:对自己有用;对他人有用;令自己愉快;令他人愉快。概括起来,一种是快乐或痛苦的情感,一种是带来利益和有用性的倾向,而“有用性是令人愉快的,博得我们的赞许”[4](69),因而,不论是对自己或他人有用还是给自己或他人带来快乐,都可以引起我们情感上的快乐,并以此对人的行为和品格做出道德评判。
需要强调的是,效用性之所以作为德性评判的标准,并不是因为“效用”本身,而是因为“效用”引起了愉悦的情感,从而给予德的评价。“有用性”作为德性的评判标准,在休谟的道德哲学和政治哲学中,并不是引起道德赞许的直接原因。“有用性”引起了我们愉悦和赞许的情感,而这一“道德感”才是引起道德赞许的直接原因。那些对社会有用的品质之所以得到赞许,是因为它促进了公共利益。通过同情,我们感受到了因对公共利益的关切而带来的愉悦感。人们赞许仅对自己有用的品质,是因为它对品质拥有者有用。通过同情,我们感受到了因对他人利益的关切而带来的愉悦感。因而,不论是对社会有用还是对自己有用,都是因其“效用性”而带来赞许的情感,因而成为一种德行。
因为同情,我们会关切“效用性”给社会带来的公共利益;因为同情,我们也会关切“效用性”给他人带来的个人利益,不论是公共利益还是个人利益,都会引起我们情感上的愉悦和赞许。这种愉悦和赞许的情感是道德评判的直接基础和依据。
在道德哲学的基础上,休谟提出了他的正义理论。该理论的核心思想是,正义“乃是由于应付人类的环境和需要所采用的人为措施或设计”[3](517),即正义是为了应对人性与人类生存的自然环境的实际状况而采取的一种人为的补救措施和设计。它是出于人类的“需要”和“利益”而产生的。正义的规则和制度对于我们而言是“有用的”,它的“有用性”就在于保障和维护社会的公共利益。对公共利益的同情,是引起我们对正义的道德认同的根本原因。因为,政治社会的成员们基于对公共利益的同情产生了“正义感”。他们感觉到,凡是遵守正义规则的行为就能维护公共利益,凡是违犯和破坏正义规则的行为则会损害公共利益。对公共利益的维护或损害,直接引起人们的快或不快的感受,也即正义感或不正义感。在这一感觉之上,我们对之给予道德或不道德的评判。正义的规则和制度在这种意义上是“有用的”,即它们是作为满足某一目的的手段,而这一目的就是公共利益。因此,正义是一种人为美德,其实际含义在于,遵守正义规则的行为和品格是一种德行,违反正义规则的行为和品格则是不道德的。
从休谟的道德哲学看来,他和哈奇森一样,确定道德判断的基础在于情感,并提出了和哈奇森相似的概念“道德感”(当然两个概念之间存在着很大差异),自此,休谟便与哈奇森分道扬镳了。第一,休谟认同哈奇森关于出于仁慈动机的行为属于德行的观点,但不赞成哈奇森将出于自利动机的行为排除出道德判定范围。在休谟看来,出于自利动机的行为同样具有道德价值,只要行为者的行为或品格能在我们心中引起快与不快的情感,不论是出于仁慈还是自利,都具有道德价值。在关于“正义作为一种人为德性”中,正义规则的建立以及对正义规则的遵守,是基于公共利益的维护,而公共利益是同情感原则联系起来的个体自利的共识。维护或损害公共利益实际上是维护或损害了自我利益。遵守正义的行为被视为一种德行,破坏正义规则的行为被视为一种恶行。因而,利己是遵守正义之规这一自然义务的基础,自利动机引发的行为当然具有道德价值。第二,哈奇森认为是上帝赋予了人道德辨认的能力,它是道德感的来源和最终依据,而休谟断然否定了这一观点。休谟认为道德感是一种苦乐情感,情感作为反省印象或次生印象,源于人心灵中接受到的经验知觉,并没有什么神秘的东西赋予我们情感感受的能力和确保道德辨认的能力。他摒除哈奇森关于道德感源自上帝的思想,也是他与哈奇森的一大区别。
总之,在休谟那里,“有用性”或“效用性”是一种作为手段的效用观念,休谟对“效用”概念的手段性使用,将“效用”作为一条重要的道德评价的准则,以及从人类的“需要”或“利益”这一历史经验的角度出发解释以正义规则为核心的政治社会的起源,将政治社会视为人类基于“需要”或“利益”而在历史经验生活中逐渐人为建构的产物,为后来的功利主义提供了新的思考路径和理论框架。休谟作为一个关键的过渡性人物,在近代功利主义的兴起过程中,其意义是显而易见的。
三、从休谟到边沁:哲学功利主义的兴起
作为道德哲学中的重要概念,“功利”与“功利主义”的完整观念是在近代功利主义哲学家边沁那里形成的。边沁并非“功利”一词的首创者,他对功利概念的发展以及功利原则的提出,不可否认的得自于休谟效用概念的启发。边沁就是在读了休谟的《人性论》和《道德原则研究》之后,明确地把效用归结为功利。在《政府片论》第一章第三十六节中,边沁做了一个较为详尽的注释,明确地表达了休谟对他“一切善德的基础蕴藏在功利之中”这一观点的形成所产生的重要影响。边沁说:“当我读了这本著作中有关这个题目(指一切善德的基础蕴藏在功利之中——译者)的部分,顿时感到眼睛被擦亮了。从哪个时候起,我第一次学会了把人类的事业叫做善德的事业”。[5](149)对于功利主义原则,边沁说:“任何行动中导向幸福的趋向性我们称之为功利;而其中的背离的倾向则称之为祸害。”[5](115)边沁将此功利原则定义为:我们对任何一种行为表示赞成或不赞成(或道德判定)取决于这种行为是增加了还是减少了我们的幸福。因此,功利原则所涉及的内涵,一是个人的利益(个人自身行为的目的是追求快乐和幸福),一是社会的利益、集体的利益,即达到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不仅是判断个人行为的道德标准,而且是判断政府一切行政和立法行为的道德标准。边沁之后,密尔进一步修正和完善了功利主义学说。但不论是边沁还是密尔,他们在功利主义的基本原则上是一致的:“功利”是一切行为道德判定的准则,也是人类行为的唯一目的。
那么,功利主义者是如何继承和发展休谟的“效用性”概念的呢?功利主义者的功利原则和休谟的效用观念又存在怎样的区别?在休谟看来,人是一个利益主体,我们对一切行为与品质的道德判断,都基于利益主体的苦乐感受。“效用性”(Utility)是道德判断的基础,也是解释人类行为的重要因素。我们对社会中人们的个体行为和品质以及政治行为和品质的道德评判,都不能离开其“有用性”,对个体行为和品质的评判依赖于其行为和品质引起的愉悦感,对政治行为和品质的评判依赖于其给公共利益带来的有用性,有用性引起愉悦性。但是,休谟并不认为追求“效用”或“功利”就是人们的唯一目的,是否符合功利就是判定人类行为正当与否的唯一价值原则。前文已做分析,效用并不是德性判定的唯一基础,也不直接成为德性判定的基础,而是因促进公共利益从而引起愉悦感才发生道德认同。因此,效用在休谟这里是达至公共利益的手段,而对公共利益的关切所引起的情感才是德性评判的直接基础。由此看来,休谟并没有把效用作为道德评判的唯一价值原则,更没有将其作为一种规范性原则,而只是说,一些行为和品质是有利于公共利益的,有总比没有好。也就是说,有用性或功利性在休谟这里,并不是一种规范性的原则。
事实上,作为规范性原则的功利主义是边沁第一个提出来的,是他发明了哲学上的功利主义。相比于休谟对效用性的解释和运用,边沁走得更远。边沁认为,休谟把人视为一个利益主体的同时也承认了人有其慷慨和仁爱的一面,那么利益就不是一种完全确定且具有规范性的原则,作为道德哲学和政治哲学基础的人性必须具有坚固的原则。所以,边沁认为,功利是人的基本天性,人总是趋乐避苦的,这是一个无需证明的事实,它不需要任何形式的形而上学辩护和先验神学论证,它是清楚的、无可争议的。“趋乐避苦”是人一切行为的根本动机和最终目的,也是道德评判的唯一基础和根据,快乐与痛苦是伦理原则的根本准则。在边沁看来,我们衡量一种行为和偏好的准则在于其“功利”,即快乐与痛苦,凡是符合或增进最大快乐的行为就是善的行为,不符合或阻碍快乐的行为就是恶的行为,这便是边沁功利主义的基本原则。不论是边沁还是密尔,在对功利主义的解释和运用中,都不仅将“功利”视为人的本性,视为衡量一切人类行为的道德基础,而且也将其作为人类行为的应然目的。密尔说:“我们最后目的乃是一种尽量免掉痛苦,尽量在质和量两方面多多享乐的生活,照功用主义的看法,这种生活既然是人类行为的目的,必定也是道德标准。”[6](12-13)他们都从人总是趋乐避苦的事实认定中推断出人应该追求功利,追求功利是正当的这一价值判断。“关于‘目的’的问题,换言之,就是关于什么事物是可欲的(或可追求的)问题,功利主义的理论,认为幸福是可欲的,是惟一作为目的而可欲求。一切其他的事物,只是作为致此目的的手段而可欲求任何东西之为可欲的,其唯一可能的证据,就是人们实际欲求它”。[2](263)很明显,边沁和密尔等功利主义者相比休谟对“效用”或“功利”的运用和解释,走得更远。在这里,“功利”不仅是一切道德判定的基础,也是人类行为的应然目的。
作为功利主义主要代表的密尔,在其政治哲学中,对政治权力或政府、国家的合法性与合理性的“功利性”解释,不仅展现了功利主义政治哲学基本的理论基础和理论框架,也呈现了这一理论基础和理论框架的休谟渊源。政治问题以及对政治的评价总是以对人的理解为基础,也总是与人们的道德判断息息相关,因而任何一种政治哲学都必然以某种形式的伦理学为基础,“那些想把政治与道德分开论述的人,于两者中的任何一种,都将一无所获”[7](7)。密尔的政治哲学当然也是以其伦理学为基础的,并在功利主义的基础和原则之上解释人类政治生活和政治现象的。在密尔看来,我们应当从人类的实际利益、需要和经验习惯出发来寻找人类政治社会的根本性原则,解释人类政治生活和政治现象。政治社会或政府、国家并不是以契约理性的方式建构起来的,而是人类的实际需要和经验习惯的产物,是人类利益诉求的产物。政治社会中人们对权威的服从,也并非契约论者所说的是基于自己许诺的义务,而是取决于人们的好恶与功利(或利益)需求。也就是说,在密尔看来,政治社会的基础和来源并非任何形式的先天原则,而是“功利”,即“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在此基础上,政治社会才具有其合法性和正当性。从功利主义政治哲学出发,密尔反对契约论者以“权利”作为解释政治社会的产生与合法性的基础。他说道:“凡是可以从抽象权利的概念(作为脱离功利而独立的一个东西)引申出来而有利于我的论据的各点,我都一概弃置未用。”[8](11)他认为,政治社会不能从抽象的权利中推导出来,只能来自于人类的“利益”或“功利”需要,对人类政治社会及其制度框架的解释和评价只能建立在人类的功利基础之上。简言之,政治社会及其制度框架是人类利益和需要的产物。对于人类而言,其合理性在于它是作为满足人类利益需要的一种手段,这一手段的意义在于,它符合增进人类社会整体利益的目的。在此意义上,可以看出,“利益”或“功利”不仅是政治社会及其制度框架产生的基础和目的,也是检验政治社会及其制度框架好坏的准则。密尔对政治社会的“功利性”解释,展现了19世纪功利主义政治哲学所具有的完全不同于近代契约论政治哲学的理论基础和理论框架。事实上,19世纪的功利主义政治哲学已不满足于近代契约论以自然法学说、契约论以及理性主义的方式解释和建构政治社会及其制度框架的思想了。以密尔为代表的功利主义政治哲学家从经验与事实出发,强调从政治领域以外的经验世界寻找政治原则的基础与政治价值的依据,它的实质就是“把经验论与价值论结合起来,由经验的内容来规定价值标准”[9]。因而,“利益”或“功利”就成为了功利主义政治哲学思考的理论基础和理论框架。不容忽视的是,休谟作为近代契约论向功利主义转向中的过渡人物,为功利主义提供了直接性的理论渊源和理论框架,是休谟促成了哲学功利主义的兴起与形成。
但是,如前所述,在对“效用”或“功利”概念的使用上,尤其是功利主义政治哲学家们以“功利”作为道德的基础、评判准则以及人类的应然目的,则远远超出了休谟对“效用”的手段性运用,而发展出一种具有规范性原则的目的—效用理论。边沁对功利的解释和密尔在政治哲学中对“功利”原则的运用,在理论上造成了和休谟一致的结论:对近代契约论政治哲学的批判和否定。休谟的经验论立场使他不可能接受近代自然法和自然权利学说的理论基础和理论框架,而功利主义政治哲学家将功利作为人的目的,事实上也否定了人具有任何先天的目的和本质,也消解了自然权利论者的理论主张。然而,边沁和密尔对功利概念的运用和发展,依然是基于休谟所反对的理性主义。无论是边沁还是密尔,他们都相信我们不仅能通过理性的计算区分出行为和偏好带给我们快乐和痛苦的数量,以此作为道德判定的、唯一的规范性原则,而且也可以通过理性的衡量建构一个正当的政治社会及其制度框架,实现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的一致。与边沁和密尔对理性的信任不同,休谟明确表达了理性在人性构成中相对于情感的次要地位的观点,并在道德哲学和政治哲学中否定理性作为道德与政治根本性原则的基础性地位,他也反对以任何形式的理性主义基础与方式建构和论证人类道德生活与政治生活的原则、规范和现实框架。而功利主义者对“功利”的事实认定到价值认定的僭越性解释和运用,更是休谟所反对的。这里实际上涉及到休谟的“是-应当”问题,休谟认为,“是”与“应当”分别是理性和情感发挥作用的领域,两者的功能和运用领域不能混淆,从理性之所司的事实领域不能直接过渡到情感之所司的价值领域。所以,在“道德学”的第一章第一节最后一段,休谟批评说,以往的道德理论家都是从各种各样的“是”和“不是”陈述开始,然后“突然”形成一些其系词是“应当”或“不应当”的陈述,但并未对这一过渡作出解释和说明。因此,边沁等功利主义者试图超越休谟而积极建构的功利原则的根据,正是休谟所批评和反对的从“是”推导出“应该”来的“自然主义的谬误”。
总之,休谟对效用概念使用,的确为后来功利主义政治哲学的兴起和形成提供了新的思考路径和理论框架,但是,休谟并不属于任何形式的功利主义者。更重要的是,与功利主义政治哲学将“功利”作为政治哲学的理论基础、理论前提以及理论框架相比,休谟的观点是有限的。他和功利主义在根本上存在着极大的差异。
[1] 亚历山大·布罗迪.苏格兰启蒙运动[M].浙江大学出版社,2010.
[2] 周辅成.西方伦理学名著选辑(上卷)[Z].商务印书馆,1987.
[3] 大卫·休谟.人性论[M].商务印书馆,1997.
[4] 大卫·休谟.道德原则研究[M].商务印书馆,2007.
[5] 杰里米·边沁.政府片论[M].商务印书馆,1997.
[6] 约翰·密尔.功用主义[M].商务印书馆,1957.
[7] 卢梭.社会契约论[M].商务印书馆,1997.
[8] 约翰·密尔.论自由[M].商务印书馆,1996.
[9] 黄伟合.为功利主义辩护[N].文汇报,1989-01-0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