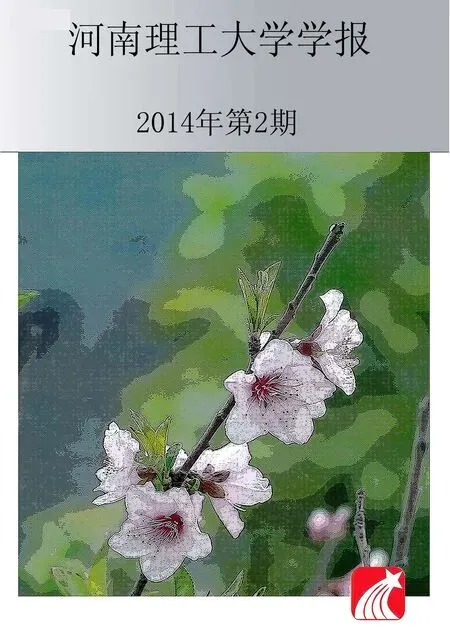《竹取物语》对中国嫦娥奔月的接受及化用
王春苗
(电子科技大学中山学院,广东中山528400)
日本古典文学《竹取物语》约成书于10世纪初期,是日本现存最早的用假名写成的物语作品。《源氏物语》(绘合卷)中记载:“物語の出で来はじめの親なる竹取の翁”[1],意为“物语之始祖《竹取翁》”。 “竹取翁”正是“竹取物语”的异名,由此可见《竹取物语》在日本古典文学史上地位十分重要。
关于《竹取物语》的研究由来已久。围绕《竹取物语》的书名、作者、成立过程、素材背景、创作手法等,中日学者进行了诸多论考。其中,《竹取物语》中对汉文典籍的引用及其故事类型源流一直备受关注。特别是20世纪60年代,由中国田海燕搜集整理编成的藏族民间故事集《金玉凤凰》传到日本,其中收载的《斑竹姑娘》一文和《竹取物语》的惊人相似引起了日本学者的高度重视。自70年代起,日本学者伊藤清司、君岛久子[2]等人先后发表了一系列的论文论著,就《竹取物语》和《斑竹姑娘》的故事原型及交涉关系进行了探讨。这种研究也引起了中国学者的注意,赵虹[3]以图表的方式详细探讨了《竹取物语》和《斑竹姑娘》中求婚过程的相似性,并指出二者在主人公的出场和结尾部分的不同,进而分析了两部作品主题的差异。王玲[4]从二者的主要内容和结尾进行了类比分析,指出两部作品在文化背景和审美观上的差异。
《竹取物语》和《斑竹姑娘》结尾部分的不同显而易见。《斑竹姑娘》中斑竹姑娘通过出难题成功地拒绝了五个富豪子弟的求婚,之后全文以一句话结束:“斑竹姑娘呢,和朗巴成了夫妻”[5]。而《竹取物语》中五个贵公子求婚失败后故事并没有马上结束,而是以较长的篇幅叙述了天皇与赫夜姬之间长达三年之久的求婚、拒婚及书信往来过程,最终赫夜姬给天皇留下了一封书信和长生不老药,升入了月宫。这一结局以及“长生不老药”、“月宫”等字眼不难让人联想到中国的嫦娥奔月传说。可以说,《斑竹姑娘》的结尾部分只是对求婚难题结局的说明,而《竹取物语》在求婚难题之后又展开了一个新的故事。这种差异如果只是归纳为大团圆结局与否,并从中推论出中日文学特质的差异在于倾向喜剧还是悲剧的话,无疑是不恰当的。
然而,如上所述,在研究《竹取物语》与中国文学的交涉关系时,学者多将视线聚焦在与《斑竹姑娘》求婚难题与故事结局的对比上,对赫夜姬重返月宫这一情节本身多有忽视。偶有研究,也大多是从中国神仙思想对《竹取物语》影响的论述[6],而鲜有从全文结构的角度来考察奔月情节的设置。因此,本文拟就《竹取物语》对中国奔月神话的接受及化用进行探讨,并从奔月情节的设置来分析《竹取物语》的结构与主题,从而探明《竹取物语》引用奔月神话的意义所在。
一、日本古典文学中的观月禁忌
对于拒绝了天皇的求婚即将升入月宫的赫夜姬,《竹取物语》中有如下一段描述:“春のはじめより、かぐや姫、月のおもしろういでたるを見て、つねよりも、物思ひたるさまなり。在る人の「月の顔見るは、忌むこと」と制しけれども、ともすれば、人間にも、月をみては、いみじく泣きたまふ。”[7]笔者试译为:“自某年初春,当月亮升上夜空,赫夜姬每每望月哀叹,尤胜以往。周围人出言制止:观看月亮乃不吉之事。但在无人之时,赫夜姬仍不时望月垂泪。”之后,赫夜姬养父竹取翁也直言劝道:“月な見たまひそ。これを見たまへば、物思す気色はあるぞ”[7]。试译为:“不要望月,望月只会徒添烦恼。”
赫夜姬不时望月哀叹,周围的人和竹取翁都对其进行了劝阻。由此可见古代日本对于观月的朴素认知,即认为观月乃不祥之举,观望月亮是被禁止的。这种观月禁忌在日本平安时代的其他文学作品中也屡见不鲜。《伊势物语》第八十八段记录了一群友人聚会,其中一人望月咏道:“おほかたは月をもめでじこれぞここつもれば人の老いとなるもの”[7]。其意为月亮虽美,但不得轻易观赏,观之过多则容颜易老。《源氏物语》宿木卷中中君于月夜哀叹自身悲惨境遇,身边服侍之人劝道“今はいらせたまひね。月見るは忌みはべるものを”[8],认为观月是不吉利的,劝中君赶快到房间里去。
渡边秀夫认为,在古代日本,月亮与皇权存在着密切联系,并且由于人们对发光之物的本能畏惧,所以月亮是让人敬畏的特殊存在,由此产生了古代日本的观月禁忌[9]。其实,这种观月禁忌从日本古代神话中也可以找到合理的解释。在《古事记》和《日本书记》记载的神话故事中,日本的造物神伊邪那岐从黄泉回到九州后为洗去污秽举行了洁身仪式。接着,从他的左眼中生出了天照大神,从他的右眼中生出了月读命,从他的鼻子中生出了须佐之男命。其中,月读命被奉为日本的月亮之神,负责管理夜国。而在《万叶集》中,还出现了把月亮拟人化的“月读男”一词。这都表明,在古代日本,月亮是被作为拟人化的神灵高高在上受人崇拜,而不是被观赏品鉴的客观存在。望月禁忌的产生与此不无关联。
因此,赫夜姬不时的望月之举,正是触犯了古代日本的观月禁忌,才会遭到周围人的劝阻。但是,对于周围人的劝阻,如上文所述,赫夜姬并没有听从,而是趁无人之时犹自望月流泪。此外,对于竹取翁的警告,赫夜姬则公然反问:“いかで月を見ではあらむ (为何不能望月)”[7],其后依然时常望月哀叹如故。赫夜姬的此种言行,无疑是有悖于当时的社会常识的,与周边环境格格不入。这一方面源于后文赫夜姬对竹取翁夫妇 “おのが身は、この国の人にもあらず。月の都の人なり(我非本国人,乃月宫中人)”[7]的自我身份告白,同时也是《竹取物语》中的奔月受到外来文化影响的有利佐证。
二、中国古代的奔月神话
相对于日本古代的观月禁忌,在中国,明月却是文人墨客争相歌咏的对象。东汉的《古诗十九首》中有诗云“明月何皎皎,照我罗床帏。忧愁不能寐,揽衣起徘徊”。关于此诗历来有两种解释,一是女子闺中望夫,二是游子思乡难眠。无论是思乡亦或是怀人,通过明月寄托思念表达感情由此成为中国诗歌中常见的手法。例如李白《静夜思》中的“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月下独酌》中的“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张九龄《望月怀远》中的“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杜甫《月夜忆舍弟》中的“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等都是对月吟唱的代表诗句。由此可见,不管是表达思乡之情还是孤寂之心,在中国古代文学中,明月不是令人望而生畏的对象,而是可以遥望进而可以借之抒怀的客体,常常作为美好情怀的寄托。
与月亮相关的中国古代四大神话之一的嫦娥奔月更是源远流长,家喻户晓。嫦娥奔月神话随着历史的变迁不断丰富和发展,其文本也经历了诸多流变。其最早记载是战国初年的《归藏》,此文献在后世的《文选》和《文心雕龙》等作品中均可以看到相关引注,但其真伪有待考究。而1993年出土的王家台秦简中嫦娥奔月的记载则成为《归藏》的最确切文献,也是近年来嫦娥奔月研究的重要资料。根据洛阳市文物局戴霖先生的整理,其内容为: “昔者恒我窃毋死之…… (奔)月而 (枚)占”[10]。其中指出了嫦娥窃药奔月,但是并没有指明嫦娥与后羿的夫妻关系。王家台秦简发现了之前一直被认为是嫦娥奔月神话最早文献的《淮南子·览冥》中记载:“譬若羿请不死之药于西王母,姮娥窃以奔月,怅然有丧,无以续之。”[11]高诱注:“姮娥,羿妻也。羿请不死之药于西王母,未及服食之。姮娥盗食之,得仙,奔入月中为月精。”[11]而后世相关文献如《灵宪》、《搜神记》中嫦娥奔月的记载大致与此相同。不难看出,这是传承至今的嫦娥奔月神话的基本原型。虽然戴霖根据王家台秦简指出嫦娥与后羿本非夫妻,“弃夫奔月”乃是两汉时人撮合的结果,但是,不管是王家台秦简还是《淮南子》,嫦娥奔月的以下几个基本要素与特征是一脉相承的。首先,嫦娥的身份原本为凡人,吃了不死之药后才成仙升入月宫,因此中国的嫦娥奔月是一则凡人升天的故事。其次,嫦娥获得不死之药的手段为“窃”,很明显是一种不光彩的行为。由此引出嫦娥奔月的第三个特征,即总体而言嫦娥是一个被贬低被丑化的形象。高诱注中称嫦娥“奔入月中为月精”,而《搜神记》中记载的嫦娥奔月故事则称“姮娥遂脱身于月,是为蟾蜍”[12]。“精”意为“精灵,神怪”,与仙女、仙子相去甚远。而“蟾蜍”在古代虽然常用来代表月亮,但绝不是一个美好的形象。两汉时期嫦娥奔月与后羿故事糅合,“弃夫奔月”更成为嫦娥形象的一个标签。
其实,在中国的远古神话中,月亮也曾作为有生命形态的神灵而存在,传说日神的母亲羲和和月神的母亲常曦是帝俊的两个妃子,日神和月神都是帝俊的儿女。严绍璗指出,中国古代“日月神本体论”向“日月神课题论”转化的契机在于,秦汉时期大量“方士”在寻求长生不死等所谓“方术”的活动中,臆想在大地之外的海洋和天空中存在着“不死之地”,从而开始了把人送往月亮中成仙的构想[13]。这一论述很好地解释了嫦娥奔月故事产生的社会根源,同时也指出了中国古代人们对于月亮认知的变迁。自秦汉以后,月亮多被视为一个具有地理和空间概念的客体,这也正是中国古代诗词中大量出现赏月望月诗文的原因所在。而从全世界神话范围来看,月亮客体化以及在此基础上的嫦娥奔月,正是中国古代文化的特性。
三、《竹取物语》中的“奔月”
《竹取物语》中,赫夜姬服下不死之药后奔月这一主要情节无疑是受到了中国嫦娥奔月神话的影响,但是通过文本比较不难看出二者的不同。
首先,与中国嫦娥奔月凡人升天不同,赫夜姬是在竹节中被发现的,有着不同于凡人的出身。此外《竹取物语》中有多处指出赫夜姬本非凡人。对于毫不理会青年男子们求婚的赫夜姬,竹取翁劝道:“変化の人と申しながら、ここら大きさまでやしなひたてまつる心ざしおろかならず。”[7]赫夜姬自称“変化の人”,并且这一事实是竹取翁和赫夜姬本人都毫不避讳的。根据新全集《竹取物语》中的注释,“変化”此处指的是神佛暂时现身于世,化身为凡人。由此可见赫夜姬的不凡身份,而这一身份在后文中也被反复提及。之后,天皇借狩猎之名偷窥赫夜姬,看到她的美貌后决意迎其入宫。赫夜姬说道:“おのが身は、この国に生まれてはべらばこそ、使ひたまはめ、いと率ておはしましがたくやはべらむ。”[7]明言自己并非本国之人,对于入宫之事恕难从命。最后,在即将升入月宫之前,赫夜姬向竹取翁坦白了自己的真实身份:“おのが身は、この国の人にもあらず。月の都の人なり”[7]。明确指出自己非本国人,而是月宫之人。由上可见,赫夜姬的奔月并不是一个凡人成仙的故事,而是一个下凡到人间的神灵重返月宫的故事。
其次,赫夜姬得到不死之药的途径也与嫦娥截然不同。有关嫦娥奔月的记载中,无一例外提到嫦娥获取不死之药的途径是“窃”,虽然部分文献称嫦娥不死之药是窃自西王母,但多数文献中指出嫦娥是偷了后羿从王母处得到的不死之药。反观《竹取物语》,不死之药是从月宫下来迎接赫夜姬的天人带过来恭恭敬敬奉上的。天人带来的两个盒子中,一个装着羽衣,一个装着不死之药。其中一个天人对赫夜姬道:“壷なる御薬たてまつれ (请您吃下药吧)。”[7]从“御”“たてまつれ”等敬语表达,可以看出赫夜姬之前在月宫的崇高地位。同时,天人又强调,服用不死药的目的在于除去人世间的污秽。可见,与嫦娥偷吃不死之药后由一个凡人升入月宫中成仙不同,赫夜姬服用不死药更多是一种净身仪式,除去凡间的污秽,为重返月宫做准备。而天人同时交给赫夜姬的羽衣,也是下凡至人间的仙女重返天庭的重要道具之一。
再者,赫夜姬和嫦娥的地位很明显是不同的。如上文所述,嫦娥奔月故事中,嫦娥因为弃夫偷药是一个受到贬低的形象。而赫夜姬则恰恰相反,在整篇故事当中都具有相当高的地位且颇受尊敬。自竹节中被竹取翁发现后,赫夜姬带给了竹取翁无尽的财富,并助其迅速跻身贵族之列。赫夜姬长大成人后因美貌名动天下,世人争相求娶,其中五位身份显赫的贵公子更是历经磨难,更勿论天皇为之遣散后宫。之后,在月宫来使迎接赫夜姬时,包括天人之王在内谈及赫夜姬时都使用了敬语。而且赫夜姬对天人所带的不死之药拥有处置权,她把一些不死之药与自己脱下的衣服一起作为留念包了起来,并交代宫人把不死之药和自己写的一封信转交给天皇。可见赫夜姬地位之尊,嫦娥地位自然不可与之相提并论。
四、“奔月”与《竹取物语》的主题和结构
对于把月亮作为神灵本体来崇拜的古代日本来说,由中国传来的嫦娥奔月无疑是另类和不协调的。因此,《竹取物语》中在对月宫来使迎接赫夜姬的描述中,直接引用了大量的汉语言词汇,从衣饰到车架直至升天所需道具,无不是对中国文化的照搬。这反映出以中国作为学习模仿对象的古代日本对吸收中国文化的极大热衷。但是,如上文所述,《竹取物语》在吸收了中国嫦娥奔月传说的同时,又对这一传说进行了极大的化用。那么,《竹取物语》设置赫夜姬升入月宫这一情节的意义何在?
在月宫天人下凡迎接赫夜姬重返月宫时,天人之王对赫夜姬下凡到人间的原因进行了说明。“かぐや姫は罪をつくりたまへりければ、かく賎しきおのれがもとに、しばしおはしつるなり。罪の限りはてぬれば、かく迎ふる。”[7]意为赫夜姬因为在月宫中身负罪障,因此才被贬到污秽的凡间短暂停留,现其罪障已消除,特来迎接。“罪”在古代日语中多指佛教上的罪孽,意为对神灵或禁忌的触犯。此处虽未言明赫夜姬所负罪孽的实质,但却明确指出,赫夜姬降临人间到重返月宫乃是一个赎罪的过程,而这一过程正契合了日本古代文学史上常见的“贵种流离”。
“贵种流离”最初是由折口信夫提出的概念,指的是神灵或像神一样尊贵的主人公,由于某种罪孽而离开故地漂泊于偏远地带,历经种种痛苦与磨难,最终或重返故地获得无上的幸福,或客死他乡以悲剧而告终的故事类型。这一故事类型在日本古代文学作品中屡见不鲜。比如,《伊势物语》中以在原业平为原型塑造的男主人公,由于和入宫前的二条后高子私奔未遂被发现,不得已离开京都远赴东国。而《源氏物语》的主人公光源氏,由于和政敌之女胧月夜的恋情曝光,自贬离京,历经两年半颠沛流离于须磨和明石,最终重返京都,并因为流离期间与明石君所育女儿而获得了显赫的富贵。对于尊贵的主人公来说,他乡流离是一种磨难和修行,也是成长和再生的通过礼仪。
对于赫夜姬而言,月宫实为其故地,而《竹取物语》中屡次提到的“污秽的人间”正是其流离之所。赫夜姬降临凡间是因为某种罪障,而通过在人间的试练得以消除罪障重返月宫。整个《竹取物语》可以视为月宫之神赫夜姬由月宫到人间再重回月宫的流离过程。因此,无论是前半部分五名贵公子的求婚难题,还是后半部分拒绝天皇升入月宫,都可以认为是流离人间的赫夜姬重返月宫的必要条件,也可以说是赫夜姬在人间的试练。最终,赫夜姬成功拒绝了五名贵公子和天皇的求婚升入月宫,顺利完成了“贵种流离”这一仪式。对赫夜姬来讲,这种结局无疑是一种成功和圆满。因此,从“贵种流离”这一故事类型来看《竹取物语》的全文结构,赫夜姬抛却凡间种种升入月宫不失为另一种意义上的大团圆结局。
五、结 语
《竹取物语》中赫夜姬升入月宫的故事情节很明显吸收了中国嫦娥奔月传说的故事元素。但是嫦娥是一个窃药之后弃夫奔月的贬义形象,而赫夜姬原本即为月宫之人,身份地位高贵,不死之药也是月宫来使恭敬奉上的。因此,赫夜姬并非嫦娥般凡人升天,而更符合日本古典文学中常见的“贵种流离”这一故事类型,奔月只不过是流离过程中的一个环节和必要途径。以此角度纵观全文,前半部分求婚难题与后半部分重返月宫有效地统一起来,从而能够更好地理解《竹取物语》的主题和结构。
不可否认,《竹取物语》和《斑竹姑娘》中的求婚难题情节跌宕起伏,异彩纷呈。但是,作为日本最早物语文学的《竹取物语》创作于10世纪初,而收录《斑竹姑娘》的藏族民间故事集《金玉凤凰》却成书于1961年。成书时间的巨大差异说明单从这两部作品来进行求婚难题故事的中日比较研究是不科学的。那么,中国古代文学典籍中是否收录有更早的求婚难题方面的故事和传说?而在日本文学史上,《竹取物语》之外的求婚难题故事又有哪些?关于中日两国求婚难题故事的发展脉络及相互影响关系,笔者将作为今后的课题另著论文探讨。
[1] 阿倍秋生ら.新編日本古典文学全集——源氏物語② [M].東京:小学館,1996:380.
[2] 乌丙安.藏族故事藏族故事《斑竹姑娘》和日本《竹取物语》故事原型研究 [DB/OL].(2012-07-11)[2013-09-11].http://www.chinesefolklore.org.cn/web/index.php?Page=1&NewsID=3366.
[3] 赵虹.《竹取物语》与《斑竹姑娘》的比较研究[J].日本研究,2003(2):67-71.
[4] 王玲.藏族民间故事《斑竹姑娘》与日本故事《竹取物语》的类比性研究 [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7(8):182-185.
[5] 田海燕.金玉凤凰 [M].上海: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1961:154.
[6] 卢静达.《竹取物语》中“不老不死”思想的研究[D].长春:东北师范大学,2009.
[7] 片桐洋一ら.竹取物語·伊勢物語·大和物語·平中物語 [M].東京:小学館,2008.
[8] 阿倍秋生ら.新編日本古典文学全集——源氏物語⑤ [M].東京:小学館,1996:404.
[9] 渡辺秀夫.詩歌の森 [M].東京:大修館書店,1995:14-18.
[10] 戴霖,蔡运章.秦简《归妹》卦辞与“嫦娥奔月”神话 [J].史学月刊,2005(9):16-21.
[11] 何宁.淮南子集解 [M].上海:中华书局,1998:501.
[12] 马银琴,周广荣.搜神记[M].上海:中华书局,2009:261.
[13] 严绍璗.比较文化研究中的“原典性的实证”的方法论问题[C]//佟君.中日比较文学比较文化研究.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4:3-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