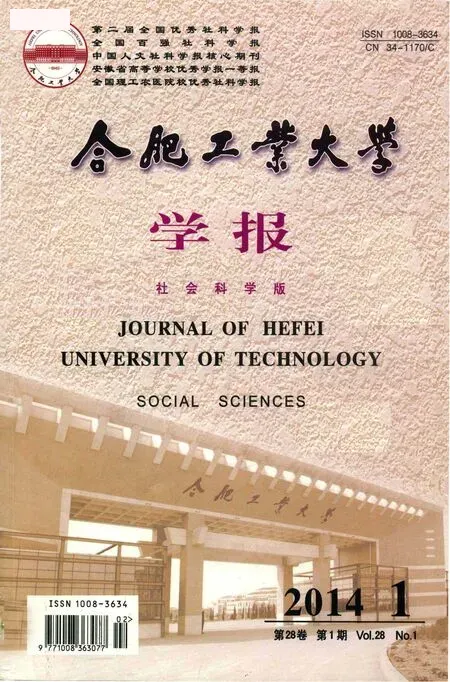刘庆邦小说的农家女进城书写与城市意象
许心宏
(安徽财经大学 文学与艺术传媒学院,安徽 蚌埠 233030)
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农民工生存空间的迁徙,荷载着文化身份与社会地位冲突的问题。由于城乡二元户籍制度的对于人的社会地位与文化身份的规约,在人与城的文学构想中,刘庆邦更为关注这种制度下的“进城者”,尤其是女性进城者的现实困境。在为底层小人物代言的叙事中,他的小说如多棱镜般地展示了农家女进城的生存状态、文化身份、家园意识与婚恋等问题。在对其生存遭遇的悲剧性叙事中,小说写出了她们的生存苦难史与辛酸史,这使得城市呈现出灰色的文化面影。
一、保姆视角:亲历者与发现者
(1)保姆的心理暗伤 农家女进城做保姆,她们与雇主之间存在着形色各异的矛盾冲突,她们“像是打入城市的尖兵,又像是潜入城市的卧底。”[1]在描述其职业的亲历与体验中,揭示出了她们的生存地位与文化身份问题。《金戒子》中的保姆与其说是窃取了女主人的金戒指,不如说是为体验城里人的文化身份而暂用一下。从饰物层面上说,戒指的饰带体现了人的社会地位与文化身份,然而保姆的虚荣心却遭致了女主人的奚落与蔑视。就揭穿真相而言,女主人执意要揭丑,而男主人则竭力劝诫妻子切勿伤了保姆的自尊心。实际上,男主人的古道热肠潜隐着作者文化身份的踪迹,即他在进城前也是农民,因此他在呵护人性的美好的同时,也是对其当前文化身份的救赎。当然,妻子的做法有其合理性的一面,但结果却是使保姆仅有的一点虚荣心破灭,继而对其生存地位与文化身份造成了重创,最终背负沉重的心理重负弃城返乡。在此意义上,小说写的是小人物的生存愿景与身份失落的话题,她们的遭际带给她们的无疑是灵魂深处的心理暗伤。《走投何处》中,进城当保姆的则是乡下的母亲,她进城为儿子照看孩子,这在中国也是普遍的现象。儿子是通过考试从乡村走出的“金凤凰”。由于社会地位、文化身份与生活习惯等诸多差异,致使农家大学生在与城市“孔雀女”缔结的婚姻生活中多是“夹板男”的生存状态——因为左边是夫妻关系,右边是母子关系,婆媳之争带给他们的多是欲说还休的苦恼。如果说传统的婚姻观念讲究的是门当户对,那么当代的“凤凰男”娶城市“孔雀女”为妻,多呈现出以学历弥补门第差异的特征,然而身份的某种内在歧视却是默不作声的话语在场。《走投何处》中的乡下母亲早年丧偶,进城后农村的房舍早已坍塌,土地交由他人耕种,因而返乡已无可能。其实,迫使她返乡的则是儿媳的弟弟要结婚,而儿子借住的则是岳母家的另一套房子,于是亲家母与儿媳合谋让女儿一家三口搬至岳母家暂住,但不包括乡下的婆婆,亲家母与儿媳以无声冷落的方式暗示这位乡下母亲哪里来哪里去。有幸的是,在母亲无处栖身之际,街道居委会主任为其做媒介绍了一位丧偶的城里老人,乡下母亲以保姆身份嫁给了他。小说以“含泪的微笑”结尾,然而过程却是凄惶却与苦涩的。
(2)性骚扰的私密叙事 《习惯》写的是发生在家庭内部的性骚扰问题。城里女雇主为因患病而行动不便的父亲雇佣保姆,然而相继雇来的十个保姆工作时间都不长,原因是父亲喜欢摸保姆手心的小动作让保姆心生厌恶,细微的肢体动作暗示的是老人的性焦渴。“食色,性也”。性有自然性的一面,亦有伦理性的一面,而老者的“为老不尊”自然被保姆视为骚情与心术不正。雇主为父亲雇佣的十位保姆虽年纪不同,但从事的都是苦活、累活、脏活。在私密化的家庭内部,其基本人格得不到尊重,特别是最后一位保姆受到老者的淫猥后,雇主既未向其道歉也未给予物质补偿,因而,小说写的是保姆身心受辱的有苦难言。在《钓鱼》中,农家女李秀美已婚,她在给城里的离异男人做保姆时,雇主以伪装粗心演绎欲擒故纵的伎俩,即在换洗衣服时故意落下数目不等的钱,保姆从开始的如数上报到后来的据为己有,其实那是雇主蓄意设的套,因为在保姆看似钓到一定数额的钱款时,雇主以告发李秀美为由迫使她就范。在这场钓鱼游戏中,雇主以自己阳痿的谎言达到消除李秀美戒备心理的目的,在其以退为进的猎色陷阱中,最终以醉酒之名猎获了李秀美的身体,因而雇主看似憨厚实则是条披着羊皮的狼,看似酒后失德终不过是为己找到脱罪之名。细加分析,他主导了这场钱的诱惑与性的猎获的戏剧。在经历了这场“钓鱼”事件后,李秀美打算回乡下老家过年,且发誓再不进城当保姆。不难发现,保姆从事的职业劳作给其带来的是或明或暗、或深或浅的心理伤害,但是这种内伤又无处告白,内中裹挟着的是精神受伤史与身份伤痕史。
(3)保姆的婚恋叙事 在现代城市工商业社会中,“二奶”与“情人”的存在凸显的是现代人婚姻观与价值观的问题。从农家女进城做保姆角度来说,在空间化人物意象的设置上,城里人的钱权势使保姆在无意识中产生依附与屈服意识,而这也发生在私密化、暧昧化的家庭内部。在《找不着北》的雇主家里,妻子退休了,丈夫开着公司。保姆在城里夫妻互不挑明的默契同盟中,不过是尚不知一己处境与身价的“二奶”,城市男人发妻的难得糊涂用意有二:一是满足丈夫的生理欲望,二是家里需要一个体力劳动者。在小说的叙事声音中,作者搁置了孰是孰非的道德判断,揭示了家庭内部幽暗未明的婚恋状态,因为在貌似婚外情的外衣下,体现出农家女卖力与卖身相交集的现象。就这种暧昧化的存在而言,如果对其做道德评判确实勉为其难,而在法律层面又难以作事实界定或者说它游离于道德与法律的边缘,因而小说叙事呈现出写实主义特征。除了这种暧昧化的“二奶”婚恋形式,尚有嫁给城里人的婚姻形式。《升级版》中的雇主之妻因病过世后,保姆成了雇主的续弦。在相差二十来岁的逆龄婚恋中,所谓的升级版保姆,不过是乡下女性因其隐忍与宽厚,善待退休后因中风而瘫痪的雇主,继而从保姆升格为妻子。其实,保姆婚后有过身孕但还是放弃了当母亲的念想,而雇主却有一子且已成家立业。因此,周围人对雇主的艳羡心理,折射出的不过是对保姆的道德褒奖。但这种逆龄化的婚姻亦非主流化的婚姻形式,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保姆又是以其年龄优势获得了雇主的认可。换言之,城市不过是其寄寓之所,她换取的也不过是一种外在身份。如果说《找不着北》与《升级版》中保姆的婚恋发生于雇主的家庭内部,那么在《我有好多朋友》中保姆的婚恋则从家庭内部走向社会外部。小说中的农家女看似有很多朋友,然而终不过是虚拟化、想象化中的朋友。就保姆对女雇主的善意谎言来说,实则是自欺欺人的强颜欢笑,其目的不过是换回些许的身份与心理的自尊。就这种自尊而言,心理层面为内在的隐,身份层面为外在的显,因为她看似读懂了城里人的婚恋自由,然在匿名性、流动性的城市陌生人社会,她所结交的男友却无安全性与可靠性而言,缺失的是乡下熟人社会的知根知底。保姆即便认识与结交了同为农家出身的一名厨师,但对方却隐瞒了自己的婚史,因而,这种识面却不知心又暗藏着情爱的陷阱,其婚姻诉求成了一则没有结尾的故事。
(4)发现者的视角 在《路》中,吴启雪来自边远的农村,因贫困辍学而进城当保姆,她所照料的是因车祸受伤的城里人赵兰刚。赵的父母皆是知识分子。在雇主父母的帮扶下,保姆考上了当地的一所职业学校,圆了她在农村无法完成的读书梦。在刘庆邦的保姆系列小说中,这种城里人对农家女的帮扶之情,显现了人性的温婉。然而最主要的是,在吴启雪眼里,赵兰刚的女友可谓是物质化的女孩,在男友遭遇车祸后便消失了踪影。小说通过边缘化、底层化的保姆视角,批判了城里人婚恋关系中的寡情与功利。同样,《骗骗就得了》中的保姆担当了卧底者的角色,她发现雇主前妻尚病卧在床,他却已另筑家室。若说少年夫妻老来伴,那么丈夫在发妻弥留之际的冷漠与寡情,反讽的是他的某种病残心理,揭露的是人间大爱的缺失。再就是在《走进别墅》中,保姆是一位大学生,她卧底于城里白领家庭内部,继而在窃密式、体验式与参与式的当保姆过程中,获取了亲历化的创作资源。与此同时,在其保姆职业的伪饰下,她经历了行色各异的雇主的窥视与骚扰,内中开掘了雇佣市场晦暗化与私密化的雇主多元文化心态。
二、道阻且长:城难进与乡难返
(1)迷失于城乡之间 在城乡二元社会壁垒下,是城里人还是农村人,表征着文化身份贵贱与社会地位高低的差异。农村人要成为城里人,一般通过招兵、招工与考学等途径完成。在《回来吧,妹妹》中,农家女青华进城读书却一去不归,原因是她接到的大学录取通知书是假的,哥哥带着父母的重托进城寻找妹妹却无处可寻。在小说对农家女城市遭遇的淡化书写中,青华既未实现大学梦也居无定所,因而,小说标题的“回来吧,妹妹”实为农家女进城梦败北的写照。其次,打工妹的进城。《兄妹》中的农家女进城打工后,遭致诱骗,失身后又沦落风尘,这期间哥哥进城探望妹妹是假,索要点钱财是真,然而妹妹却有着难以言表的伤痛。因为,她虽有着灵魂的干净,但钱的来路毕竟不正,因而无可告白也无法告白。妹妹认为委身于小姐行列是“做辱没祖宗的丑事”,戏剧性的一面却是,哥哥进城后却招了妓女。妹妹痛骂妓女时,倒被对方揭穿了她自己“不要脸”的真相。源于这种心理重创她对哥哥说“我不是你妹妹,你也不是我二哥,咱们谁也不认识谁。你回去告诉村里的人:心死了,心早就死了!”[2]因而,她隐瞒实情与断绝亲情的苦衷,一是源于乡土伦理的道德禁忌,二是精神内伤的无法剖白。特别是哥哥的招妓彻底击垮了她仅有的一点自尊心,使其悲情的伤痛无法转化成活着的理由,因而,离乡进城的结果就是城里不好进乡下也难回的双向迷失。
如果说《回来吧,妹妹》与《兄妹》还是短篇小说的农家女进城遭遇书写,那么中篇小说《家园何处》则宕开了笔墨,描摹了农家女的城乡双向的生存悲痛史与血泪史。在乡下,这种苦难表现在女主人公父母双亡,虽跟着哥嫂过活,但大哥与三哥相继患了绝症与摔断了腿,因而农村生活亦可谓举步维艰。时值农民外出打工的潮流涌现,停选择了逃离乡下依附性的寄寓生活,她走上了打工之路。小说情节的戏剧性的凸显,就是停外出前与小学老师方建中相亲后即欲“献身”于他,因为村里人认为“外面的地方人欲横流,凶险遍地,不是骗人,就是被骗,不是吃人,就是被吃,到处都很恐怖。农村的女孩子只要进城就完了。”[3]因而,如是“自毁”的私密潜隐着停对城市的惧怕与复仇心理,因为她想“越是被城市看重的就先毁掉”[3]。在小说结构的整体观中,这种“自毁”无果又为停的城市遭遇埋下了伏笔。其实,大量类似主题的文本中,比较普遍地存在着结果预设的叙事,言说的是对外面世界的恐惧,即受到压迫、欺侮与蹂躏等。从离乡到进城,果不其然,同乡小包工头对停看似呵护实则猎色,继而又成为其讨好大包工头的工具。与此同时,停与同乡的暧昧关系传至乡下后,同乡小包工头迫于大舅哥的权势辞退了停,然后停在大包工头的引荐下走向了小姐行列。应该说小说行文至此,基本完成了小说对农家女进城的结果预设,自此以后停的人性发生了变异,在以身体为资本的钱色交换中,攫取金钱成为她最大的目标。然而停的三哥因为丧失劳动能力,他进城找停无非是索要钱财,因而,手足之情的应然让位于金钱多少的实然,这加剧了停的生存悲剧成分。当然,如果说小说存在着人性的闪光点,那就是方建中“千里迢迢来到她身边,对她没有流露出任何鄙视之意。”[3]因而,在没有人将其当人看之际,方建中成为其值得托付终身的对象,方也因之成为停人性迷失的拯救者。当然,这种困境中的美好情感又氤氲着“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的古典诗意。问题是,方建中在寻找停的过程中被宾馆的保安毒打后,停也逃离了卖笑场所,但他们又没有重返乡下,那他们会去哪里呢?何处才是他们的归程呢?小说的结尾是开放的,就这种开放性结尾而言,亦可谓是迷失于城乡之间。
(2)进城与返乡的双极书写 这里的双极指的是城难进乡难返,两者在叙事基调上呈现出悲剧的特征,它较为典型地体现在《到城里去》与《嫁东风》两部中篇小说中。在《到城里去》中,农家女宋家银的进城诉求源于其对于自身的文化身份的焦虑,但她不是进城打工的在场者,相反却是一位缺席的在场者。对其文化心理进行探幽,则可知城市则是其改变身份与社会地位的文化符号。体现在婚恋史上,其初恋的对象是一名工人,但因为工人与农民文化身份的差异,男友去了外地工作后就失去联系。源于这种原点的心理旧伤,她发誓嫁给工人或城里人,显然,这种艳羡情结的背后又是她对自身文化身份的愤恨与抗争。就其心理偏执而言,如丈夫从临时工到进城打工,她都暗示与渴望自己是身份不一般的农妇。体现在日常生活场景中,农村的孩子一般喊父亲为爹,但她却让孩子喊父亲为爸爸。这种称谓背后,既是其急于改变一己文化身份的真实写照,亦为其扭曲化的贬低乡下人的心理呈现;再如拒绝登门为儿子提亲的媒人,因为她认为儿子一旦考上大学就是城里人。然而击破她急切改变文化身份梦想的,是她探望拾破烂的丈夫的进城之旅。她发现“城市是城里人的。你去城里打工,不管你受多少苦,出多大力,也不管你在城里干多少年,城市也不承认你,不接纳你。除非你当了官,调到城里去了,或者上了大学,分配到城里去了,在城里有了户口,有了工作,有了房子,再有了老婆孩子。你才真正算是城里人了。”[4]因而,从丈夫的败北到子女的无望,渴望做城里人的梦想不断梦碎。就儿女而言,女儿初中毕业后就进城务工了,她对女儿难以成为城里人的自知自明,反证的是其文化心理挫败的伤痛;将希望寄在儿子身上,儿子却在高考前夜进城打工了,留信说不混个人样就不回来。其实,宋家银看似喜剧性人物,实则是悲剧性人物,因为在整个故事情节中,她就像一个“讲故事的人”,讲述的是城市像一座城堡,而她却无力进入的故事。
如果说《到城里去》中的宋家银是进城无望的缺席者,那么《嫁东风》中的米东风则是返乡无望的在场者,两者形成了两极互反的人物意象。就米东风而言,其城市生活是缺席的,如是叙事之策,凸显的是其悲剧性的婚恋遭遇。她从外出务工到返乡嫁人,不期然成了被怀疑、敌视与攻讦的对象,因为在世俗化的心理中,人们认为男人有钱就变坏,女人变坏就有钱。因而,人们认为米东风赚的钱来路不明,自然也就没有走上正路。对此,父亲的言词躲闪等于默认了确有其事,于是愿意倒贴嫁女儿。但几经介绍却无人敢娶,因为在“莫须有”的乡间“三人成虎”的谣传中,她成了被孤立、被边缘化的人物,这反映出乡间道德伦理经验的文化优先性。最终她像“物”一样从娘家被转移到了婆家。在世俗的偏见与谣言的中伤中,丈夫不过是完成了形式化的婚姻仪式,其内心深处并未接纳她为妻,相反米东风不过是其“玩物”。因为,就这则婚姻而言,丈夫是以自己的妥协而向女方父亲抛来的物质诱惑缴械投降,因而,从相亲到婚后生活,米东风在夫家成了无自由、受规训、被打骂的对象。特别是婆婆立于传统“贞洁”文化的道德高地上,痛骂东风是“婊子、不能下蛋的鸡”等[5],而丈夫也在嗜赌成瘾中怂恿妻子去卖身。在这种非人化的生活中,米东风的奋起反抗标志着女性意识的觉醒。然而从开始的出逃失败到成功,小说倒也写出了一个神性的人物,这个人就是米东风的小叔子。小叔子虽沉默寡言但却有着大爱与大恨,他以自己的死亡换取了嫂子的成功出逃,这种以弱者的死亡换取弱者的生存自由,彰显了在与兽性抗争中的人性的崇高。按理说,故乡是温情的,也是精神家园的最后归依地,不过米东风的返乡之旅却成了孤绝的逃逸之旅。
三、城市意象:文学的批判与建构
对于农民工进城可从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伦理学等多个学科层面予以解读。然而在文学镜像中,在人与城的载体化写作中,人成了“城市意象”得以文本创造、情感表现与文化评判的载体。在刘庆邦的小说文本中,就农民工进城而言,若从性别意义上来划分则有男女之别,但总体来说,女性进城的小说文本远多于男性进城的文本。就性别意义上的农家女进城而言,卖力与卖身成为模式化的人物叙事类型,但这还是静态的划分,除此之外尚有显著的生存转向叙事,即从卖力到卖身的过程化、暧昧化与灰色化的生存叙事,内中涉及生存地位、社会身份、伦理观念、婚恋诉求与家园意识等问题。当然,从进城求生的内驱力上来说,就是进城寻求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一定程度上也是女性社会地位提高的体现,但“经济上接纳,地位上排斥”的尴尬处境却也时有发生。体现在小说文本中,作者在为小人物“代言”的叙事中,城市始终呈现出灰色的精神面影。这其中,城市陷阱呈现出惯性化的预设叙事,典型的为性陷阱叙事,如《兄妹》、《家园何处》、《月儿弯弯照九州》、《停》等小说文本,作者的用意指向了“性”之外的文化分析,如农家女社会地位的卑微、文化身份的低矮、商业社会的消费逻辑、社会保障制度的缺失等,应该说,作者关注的问题也是当今社会关注的焦点问题与难点问题。勿庸多言,新世纪十年来,每年的中央一号文件都是关注农村、农业、农民的“三农问题”。不过,在作者的小说叙事中,小说多取用的是悲剧性的文学叙事,表述着农家女进城的生存苦难史与身份卑微史。
总之,刘庆邦的农家女进城叙事中,“城”是人们求生求变的具有历史征召力的文化符号;“城”也体现出中国城市化、工业化进程中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社会现实。但是,源于户籍制度的城乡二元与文化身份的分殊,进城后的农家女往往寄寓于城市屋檐下,她们往往自感为一群城市“外来者”、“边缘人”与“异乡人”,一种“城市过客”的文化心理往往油然而生。但是,城市又仿佛是一块磁场,她们爱的是城市,恨的也是城市,对城市产生的是爱恨交加的悖反心理。这其中,进城是时代化、功利化的需求,而返乡要么是进城败北的不证自明,要么就是返乡无望的重返城市。当然,从文学到现实,农家女进城或打工、或做保姆、或从事服务行业,这是现实版的农家女进城务工的主流形态。然而结果预设的视城市为是非之地、寡情之地、陷阱之地、受难之地等,它带来的又是一种双向伤害,即轻伤的城市重伤的人,因而城市的历史进步性、文化多元性被遮蔽起来。值得注意的就是,如保姆职业的家庭化、小姐行业的私密化等,内中诸多的戏剧化情节与心理描写等,作者不在现场却要写出现场化的人和事,显然作者在目的意象性的文学构想中,往往在既难证实也难证伪的叙事可靠性与不可靠性的“擦边”中,揭示出她们的生存屈辱史与心理暗伤,在批判矛头指向城市之际,发出的是“不平则鸣”的历史愤恨之声。当然,在这种不平之声的背后,留给社会的则是如何为农民工进城铺好道路的多方位思考。
[1]刘庆邦.进入城市内部[J].北京文学,2012,(5):39.
[2]刘庆邦.兄妹[J].作家,1995,(6):50-55.
[3]刘庆邦.家园何处[J].小说界,1996,(6):131-164.
[4]刘庆邦.到城里去[M].广州:花城出版社,2010:77.
[5]刘庆邦.东风嫁[J].十月,2012,(4):4-37.